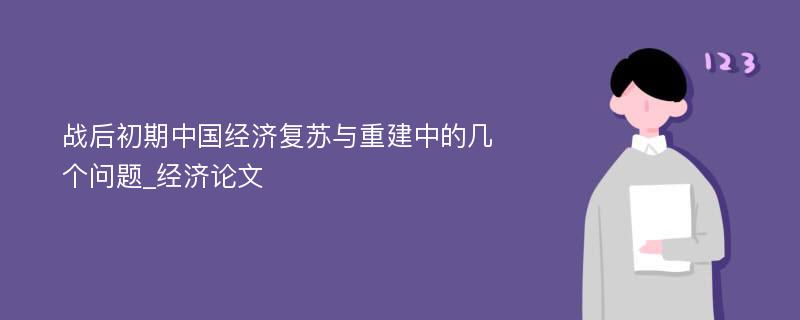
战后初期中国经济恢复与重建的若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战后论文,若干问题论文,初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1)04-009
从1945年抗战胜利,到1949年国民党失败,由于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国经济实乏善可陈,因此研究者亦较少涉及(注:关于战后中国经济尚缺少专门研究,相关研究可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第2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年版;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三联书店1963年版;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董志凯:《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虽然国民党也曾企图进行经济恢复与重建,但为时甚短。随着内战重起,国民党军事由盛而衰,其统治区日渐缩小,经济形势亦江河日下,正常的经济活动已很难进行,更无论发展了。本文即以经济恢复与重建为中心,勾画出战后初期中国经济之概貌,并研究其间之土地分配、国家资本、通货膨胀等若干问题,期以为战后中国研究之拓展有所助益。
一、未如理想的经济恢复与重建
由于多年战争,中国原有经济体系被割裂,生产力或多或少受到影响,抗战胜利后亟待恢复与重建。有利面是,日资产业被接收,既增加了国家经济实力,又减少了外资对华资的挤压(注:关于接收敌伪产业的总数量,现有统计数字不一,估计在3.3亿美元至8亿美元之间(“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日本投降与我国对日态度及对俄交涉》,台北1966年版,106-107页;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70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122页;《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604页。);恢复与重建的市场需求旺盛,对经济是重要的刺激因素。不利面亦非常明显,政局不稳,社会不安,交通受阻,内战重起,统一市场无法形成;东北、华北工矿业集中地区受到战争影响,损失严重;币值不稳定,通货膨胀压力巨大,各方投资意愿低落。总体而言,经济恢复与重建困难多多,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1945年11月26日,国民政府设立最高经济委员会,作为负责全国经济工作的枢纽性机构。兼任该会委员长的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提出战后经济政策纲领为:一、扶助民间事业,协调国营民营关系,使它们的配置轻重合理;二、平衡政府收支,协调各部门利益;三、与友邦进行经济合作,坦白互惠(注:《大公报》(重庆)1945年11月27日。)。由于蒋介石“在政治上关心对付旁的政党,特别是共产党,超过他对经济建设的关心”(注:《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266页。),宋子文因而主导了战后初期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其核心是通过开放金融市场,稳定币值,重建统一的经济体系,恢复经济活力。但是宋子文虽自诩为经济专家,却深知实现这一任务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他在答复参政员质询时说:“我没有离奇巧妙的办法,不过无论任何办法,必须切合国内外情势环境,……目前的困难尤多,因此,我极希望有能力的人来代替,本人能力薄弱,与各位所理想的人,相距甚远。”(注:《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68册,930页。)即便宋子文如此低调,他的经济政策仍引起社会各界以及国民党内部其他派系的普遍不满。在其任期内,经济政策不是扶助民营而是偏于国营,政府收支不仅不能平衡反而赤字愈增,对外经济关系因进口剧增而严重影响国际收支平衡,其经济计划可谓均成泡影。就实际情形而言,内战重起之后,战争再次成为国民党面对的中心问题,继宋子文之后的历任阁揆,经济无确切政策可循,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拆东墙补西墙,以维持经济基本面的形势。
在经济恢复与重建方面,轻工业中的棉纺织业由于日资退出与复员所需,加之低价美棉大量进口,以及投机囤购因素,恢复较快。1947年,全国华资厂的纱锭和布机数分别超过战前59%和1.1倍,纱、布产量分别超过战前17%和3.3倍。面粉业,虽然华资厂数和生产能力均超过战前,但由于原料缺乏,美国面粉进口大增,产量逐年下降,1948年仅及战前产量1/3。火柴产量较战前略有增长,纸的产量则超过战前1.9倍。重工业中的采矿、冶金业基本在低谷徘徊,产量下降较多,惟有电力工业恢复较快,产量亦有大幅度增长。就地区而言,沿海城市经济,由于复员对消费的刺激和资金的流入,加上其原有的经济基础较好,首先得以恢复。1947年,上海新登记工厂数达到9285家,创历史记录。同时期上海、天津、广州、青岛四市华商工厂工人数占全国总数之比例,由战前的41%增至70%,显示经济活动更进一步集中至上海等沿海城市。而后方工业则因厂商急于清货复员,资金紧缺,加之本身就是战时产物,缺乏坚固基础,战后几一蹶不振。1945年底,后方工业指数较8月间下降20%以上,其中重工业下降了一半左右。(注:本段资料均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640-667页。各项统计均为华资,战前统计不包括东北和台湾。)
关于以工业为主的战后经济恢复与重建之程度,就工厂和工人数统计,1947年底全国登记工厂数为15048家,工人100万人,比1936年分别增长了1倍多和64%。就实际生产量统计,1947年华资企业产煤1949万吨,铁3.6万吨,钢6.3万吨,电37亿度,棉纱170万件,棉布4763万匹,面粉5565万包,火柴85万箱。与1936年比较,除了面粉下降50%外,其它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电力增长3.8倍,棉布增长3.3倍。但如与包括外资在内的1936年全国总产量比较,则火柴为0.70,棉纱0.67,煤0.52,面粉0.37,钢0.17,铁0.05,只有电为1.21,棉布为1.28。由此可见,战后轻工业尚未完全恢复到战前水平,而重工业距战前尚有相当距离(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644、794-795页;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143、146-147页。1947年如加上外资企业产量,恢复程度可能更高一些。但由于外资在工业资本中所占比例已自战前的51%大幅度下降至战后的17%,同时公用事业占外资工业资本的比例,则从战前的25%上升至战后的44%(《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722-723页),因此外资工业品产量占全部生产量的比例可能已不足10%,对经济恢复程度的影响不算很大。如棉纺织业的外资比例已下降至1%,其影响已微不足道。)。这主要是由于传统重工业基地东北因苏军强拆装备而损失巨大,东北和华北又为内战之中心,恢复与重建受到严重影响。据今人研究,从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看,战后除了新式交通运输业指数较战前上升了22%以外,其它近代工业生产指数均在下降,其中近代化工厂制造业下降21%,矿冶业下降更高达58%,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由战前的21.81%,下降到战后的19.7%。(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743、793-796页。本文所论之经济恢复与重建,均以1936年作为比较的参照系,因为该年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高峰年,而且统计资料相对完整。实际上,由于战争的影响,战后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环境较之战前有了很大变化,以战前作为参照系的比较是否完全合适,尚有讨论余地。限于篇幅,本文不论,或可另文探讨。)
在战后经济的恢复与重建中,也有两点具有积极意义的现象。其一,由于战争的因素,在华外资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有较为明显的下降。1948年,外资总额为1936年的0.81,其中直接投资为0.48。与此相对应,外国资本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亦明显下降。如按1936年币值计,在中国全部资本总值中,外国资本占8%(战前36%),其中产业资本为11%(战前57%),商业资本为4%(战前25%),金融资本为6%(战前19%)。这就为一直苦于外资挤压的华资腾出了一定发展空间,也是战后华厂工业品产量全面超过战前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二,民营重工业的发展有了明显进步,煤产量超过战前16%,铁产量超过39%,发电量则超过89%。尽管这些产品的实际产量并不高,但这种增长对于一向以轻工业为主的民营工业而言,还是有一定意义的(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600、646-647页。)。不过由于内战重起,经济形势日渐恶化,这些具有积极意义的发展未及形成势头即告消沉。
对于经济恢复与重建,国民党一度寄希望于美国借款。先是宋子文向美国提出20亿美元贷款要求,其后美国进出口银行又有以5亿美元贷给中国的计划,但最终均因内战造成的形势不稳和偿还计划缺少合理的保证而未能实现。对于国民党而言,贷款目的不仅是为了经济恢复与重建,更重要的是为了显示美国支持,安定国内人心。蒋介石曾告宋子文:“此款于我完全为对内政一时之作用,如果此借款成,则政局当可比较稳定,关于国民大会与改组政府,皆可如计完成,至少亦可增加美国协助我政府形式上之效用也。”(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3册,106-107页,112页。)然而美国贷款是为其内外政策服务的,要求“特别注意于适合当地政治环境”,并附有指定用途之条件(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3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104页。)。而中国形势的发展不可能完全如美国所愿,使美国对此项贷款的意愿始终处于两可之间,态度也随着时间的演变而变为“不如以前积极”(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3册,112页。)。因此使此项沸沸扬扬、喧腾经年的借款终无结果。国民党既将重建经济的希望寄托于美援,而在美援迟迟未来的情况下,国民党重建经济,安定国内的计划也落了空。(注:至1948年底,美国进出口银行对华信用贷款总数为8280万美元,实际支付6540万美元。虽然在租借、出售剩余物资名义下的信用贷款数额达到41100万美元(包括上述信用贷款),在租借、捐助、转让等名义下的无偿赠与更高达159670万美元,但基本是以实物形式用于战争,对经济重建作用不大(The China White Paper,vol.1,pp.405-406,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California,1967)。)
战后经济的恢复与重建,主要发生在抗战胜利到1947年的大约二年左右时间。但即便在这一时期,经济重建仍然面临重重困难。由于内战再起,军费剧增,能够用于经济恢复与建设的费用少得可怜。据估计,战后用于经济建设的政府投资和国外借款总数为28200万美元,不及战时损失的一个零头。而政府用于经建的经费占军费支出的比例,最高为1946年的0.5%,最低为1949年的0.17%(注:《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第2册,787、791页。)。本身实力有限的中国经济,一度又受到宋子文开放市场政策的强烈冲击,国产货难与大量价廉物美的进口货竞争。1946年外贸入超猛增为47430万美元(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456、584页。),除了棉纺织业得益于廉价美棉外,其它如面粉、卷烟、水泥等工业都受打击。日渐高涨的通货膨胀,也大大不利于正当经营,波动不已的币值,令任何现实的投资者望而生畏,投机心理如同癌症般弥漫于有产者心中(注:在生产活动日渐萎缩的同时,商业、金融业和投机活动却显得十分活跃。战后与战前相比,全国商业银行数猛增8倍以上,还有比银行多出2倍以上的银号和钱庄。另据估计,战后初期上海一地的游资即达8千亿元,按官定汇率约合4亿美元,可以在市场上不断兴风作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669-672页)。)。加之国民党当时的注意力全在如何对付共产党上,根本无暇顾及经济。1947年以后,因为战争范围的扩大,生产与消费均大受影响,国内市场再度被分割,再加以恶性通货膨胀,消蚀了所有尚存的经济活力,经济运行陷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更谈不上发展了。
二、依旧徘徊的农业经济与土地问题
中国农业经济因为其很大程度上的自然经济性质,受外部环境的影响相对较小,但是大规模战争对生产环境的破坏,军队征发对劳力的占用,田赋征实对农民生产物的低价以至无偿占有等,对于战后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不利影响仍然不容低估,农业生产只能在低水平上徘徊。1947年全国稻、麦等六种主要粮食作物总产量为22.5亿市担,为1936年产量的97%,相差不大。但棉花产量下降较大,1946年只及1936年的43%(注:《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360页。),远不能满足棉纺工业的需要,导致美棉大量进口,而廉价美棉的进口,亦不利于棉花生产的恢复。
作为民生基本的粮食问题仍然是国民党面临的难题之一。粮食消费有增无减,各地粮价也因此不断上涨。尤其是收复区受抢购军粮和复员还乡的影响,粮价攀升更为剧烈。以至“各地粮情之紊乱,粮价之暴涨,无凭遏止”(注:青年远征军第二零八师政治部编:《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二中全会缉要》,1946年版,67页。)。1946年,全国粮食消费亏空高达446万吨,而粮食进口因国际配额管制,只能弥补供应缺口的1/10(注:行政院新闻局编:《全国粮食概况》,1947年版,15、6-7页。)。为了保证军粮和主要城市粮食的供应,国民党仍然实行战时采用的征实征借征购政策,但因为形势的恶化及其统治区面积的减少,实征数趋于下降。战后初期的两个年度内,实征7210万石,1948年度则剧降为2千万石,预示着实物征收制度也难以为继(注:《民国财政史》,197页。)。由于粮食供应无法满足消费需求,在城市里经常发生抢购粮食风潮,导致社会不安及民心动荡。
农业经济复兴的关键仍然是土地问题。据22个省的统计,战后佃农占农户总数的33%,半自耕农占25%,两者合占58%,较战前增长了4个百分点,显示自耕农数在下降(注:《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276页)。如何从土地分配入手,提高大多数农业生产者的积极性,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所在。国民党内亦有不少人认识到,“土地问题是解决国民经济的中心,土地问题合理解决,政治与军事便迎刃而解”。1946年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提出:即刻规定耕者有其田之实施步骤及办法,由政府发行土地债券,收购大地主土地,分配于退伍士兵及贫农,并切实扶植自耕农,保护佃农。行政院亦于同年12月修正通过《二五减租办法》,规定本年度豁免田赋省份一律减租1/4,下年度豁免田赋省份亦照此实行(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编:《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记录》,1946年版,104页。国民党的扶植自耕农计划分甲乙两种,甲种为政府征收土地,放给农民耕种;乙种为政府贷款给无地农民,由其购地自耕。前者曾在7个省试行,后者曾在11个省试行,但数量均极为有限。)。但平均地权、减轻租赋是国民党当政20余年始终未能解决的问题。它一方面要打出这面旗帜,以拉拢人心,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在实践中迁就、照顾土地所有者的利益,维护自己的统治基础。地政部在答复国大代表质询时承认:关于耕者有其田政策,拥有土地者多持反对态度,而省县参议会亦有请求暂缓实施者,今后全国土地改革之推进,政府固须努力,尤赖全国人民之策动,地主阶级之觉悟,以及人民团体之协助。因此,行政院对解决土地问题的答复,始终是“正在拟订实施办法”。(注:国民大会秘书处编:《国民大会代表询问案(地政部)之答复》,1946年版,34-35页。)终国民党之统治,土地、农民和农村问题一直没能得到真正的解决,其所有关于农村的政策,无论理论上多么完美多么有效,一到实行时则如大海中之一滴水,很快便消失于无形。
在国民党战后农村政策中,比较特殊的一类是对所谓“绥靖区”(即原中共占领区)的政策。由于这些地区在中共治理下实行了土改或减租政策,得到多数民众拥护,因此国民党企图对这些地区的政策作出某些调整,主要是改革土地收益关系,给直接耕作者以实利,同时在政治上与中共的土改政策相抗衡,争取广大乡村民众的支持。全面内战爆发后,蒋介石决定农村经济政策应着重下列各点:一、解决土地问题,应一本国父平均地权之旨;二、发行土地债券;三、设立农村合作社;四、创办农民银行。(注: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版,221页。)这些措施的关键在平均地权,而蒋强调在“绥靖区”实行,明显含有与中共争夺民众的意义。他训诫部下,我们“特别要注意土地的处理和分配,要比共匪处理土地的情形,还要表现更好的成绩出来,使一般民众皆能了解我们的土地政策是真正为民众解除痛苦,使农民得到利益。然后国际的观感,也可因而改变。”(注: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卷,台北1984年版,1845页。)国防部长白崇禧也承认:“我们要和共产党争斗,单靠军事的力量仍感不够,一定要兼靠政治的力量”,“一定要有实惠,才能博得民众的同情。”(注:《白崇禧在绥靖区政务会议上的讲话》,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档号一八五—20。)
尽管国民党认识到与中共争夺农民的重要性,但其正式出台的政策仍然偏向于土地所有者。1946年10月31日,国民政府公布《绥靖区施政纲领》,规定:绥靖区内之农地,其所有权人为自耕农者,得凭证收回自耕,其所有权人为非自耕农者,在政府未依法处理前,得凭证保持其所有权,但其农地应由现耕农民继续佃耕;绥靖区内之佃农,对地主纳租,其租额不得超过农产正产物三分之一;收复前佃农欠缴之佃租,一概不得追缴;绥靖区内之农地,经非法分配,地主失踪,或无从恢复原状者,应由县政府征收,其地价应依法估价折合农产物,由中国农民银行发行土地债券,给予合法所有人,分年偿付。(注: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秘书处编:《绥靖区行政法令汇编》第1辑,1946年版,1页。)行政院亦公布了《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以产权恢复原主为原则,将土地问题的处理具体化。这些规定,一方面强调地归原主,对于所谓“绥靖区”内已经通过中共土改得到土地的广大乡村贫农,实为一次再剥夺;另一方面又不能不照顾到上述地区土改后的现状,对于现耕作者给予一定优惠。国民党内有人承认,中共的土改“其原旨核与耕者有其田主张实为吻合,只要收复区各县市对于土地问题遵照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加以合理的处置,彻底的执行平均地权,亦可收到完满的效果。”(注:《山东省政府绥靖政务报告》,1947年2月,二档,档号一八五—62。)然而理虽如此,这些规定的实施范围却非常有限,只在6个省划出14个县实验,其中开始实行的不过5个县。更普遍发生的情况是,流亡在外的地主以还乡团名义跟随进攻的国民党军回到原住地,“查封奸匪家属全部财产并驱逐之”,“不特不奉行二五减租办法,除强迫佃农对半分租外并追算历年未对半分租之旧帐”。而此种情况之出现概因“各地方官绅均为地主官绅,既与地主打成一片,故中央各种收揽民心安定社会秩序之法令相率阳奉阴违”(注: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6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457页。)。在苏北和山东,这种情况更为严重。徐州绥署曾制订了还乡团组织办法,规定还乡团受当地县长及党政军联席会报指挥监督,必要时得派军队掩护,这意味着土地所有者可以在武力支持下向农民追索失去的财产。(注:《绥靖政工手册》,1946年版,丁编22目。)因此,国民党在仍然依靠地主作为农村统治支柱的情况下,不可能得到最广大农民的支持(注:每到形势不利,国民党内总有人企图以土改争取民心。1948年底,国民党军事失利,全盘形势极度恶化,国防部因此上呈蒋介石,提出在土地国有原则下,重新颁定全般土地政策,实行耕者有其田,但这样的建议最后仍被束之高阁(《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戡乱时期)》第14册,631页,藏台北“国史馆”)”,而土地所有权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不解决,农业经济的复兴和发展就只能是空中楼阁。
三、国家资本的膨胀
战后中国经济恢复与重建中的突出现象是国家资本的急速膨胀(注:国民党政权控制下的国家资本,有多种实现形式。经济学家王亚南将其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是官僚所有资本,即由官僚自己参股或经营的企业;其二是官僚使用或运用资本,即名为国营企业但由官僚处置;其三是官僚支配资本,即既非自己经营,也非通过国营形式运用,但却因种种原因在多方面受官僚支配的私人资本(王亚南:《官僚资本之理论的分析》,《文汇报》1947年3月25日)。在这三种形式下,第三种形式牵涉较广,概念有欠严密,姑可不论。第一种形式属于官僚个人资本,亦即纯粹意义上的官僚资本。而通常所说的国家资本大多以第二种形式出现,即名为国营公司,并可能有多方参股,但企业运作基本处于政府控制下,并打上了企业负责人即官僚个人的印记。本节所论,即主要为第二种形式的国家资本。)。其直接原因,是接收日伪产业中的相当一部分以或自营,或转让,或标售等方式,转移到国家手中,使民国时期的国家资本发展到其最高峰。据估计,按1936年币值计,战后国家资本占中国资本总值(142亿元)的54%(战前为32%),其中产业资本占64%(战前为22%),金融资本占89%(战前为59%)。国家资本已在中国产业资本中占据了相当优势,在金融资本中则占据压倒优势。从1936年到1947/1948年,在产业资本中,外资年均下降16.35%,民营资本年均下降2.05%,只有国家资本年均增长6.27%(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727、731页。只有商业资本,民营占其总值比例从战前的75%增长到战后的95%,原因一是因为中国商业向以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交易为主,故民营资本占有优势;二是国家资本中的商贸机构大户,如中央信托局、资源委员会等被列入了其他部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731-732页)。)。反映出国民党历经20余年的经营,已经建立了一套由国家政权掌控的、集中在政府官僚经营下的经济体系。
战后国家资本的膨胀,一方面是原有单位规模的扩大,如四行二局、资源委员会等,另一方面是新建了若干垄断性公司,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蚕丝公司、中国盐业公司等,其中尤以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最引起社会关注与非议。战后接收的日伪产业以棉纺织业最成规模(仅上海一地就接收了纱锭96万枚,织机1.7万台),虽然民营呼声很高,然政府以“一时难以确定价格标准,无法标售,益以鉴于当时商人方面,对于原有之商营纱厂,尚难继续经营,自无余力再行承购”为理由(注:《国民大会代表询问案(经济部)之答复》,6页。),于1945年12月成立国家控股的中纺公司,总公司设于上海,另在天津、青岛和东北设有分公司。据1947年的统计,中纺公司下属85家企业,囊括了纺织业的几乎所有部门,有员工7.5万人,纱锭176万锭,线锭35万锭,布机3.6万台,纱线锭占全国总数的44%,布机占55%,棉纱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0%,棉布占70%,居于垄断地位。中纺公司享有种种特权,如低息贷款、官价外汇、低价美棉等,还可免于政府限额收购,垄断棉纺业进出口贸易,以低吸高抛方式谋利,对于民营纺织业具有特殊优势地位。(注:陆仰渊:《中纺公司的建立及其性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代表民营资本的全国棉纺同业联合会对于中纺公司的成立“深表诧异与不满,认为不特违背国家既定之经济政策,且系与民争利”。有参政员提议,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以国家资本为后盾,供少数人盘踞利用之”,“害国病民,此为尤甚”,要求停办中纺公司(《黄逸峰等:《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575页;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编:《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二次大会提案原文》下册,1946年版,审4第47号案》)。因篇幅所限,本文未将战后民营资本的境遇作为重点研究。)
战后发展最快的原有国家资本单位首推资源委员会。1946年5月,资源委员会由原隶属于经济部改为直属行政院,其任务是:创办开发及管理经营国营基本重工业,办理政府指定之其他国营工矿事业。对其下属的庞大产业,资委会决定,对于后方战时事业,纯为战时需要者停办,适应地方需要者转让地方,有价值者酌量紧缩,属于基本工业者继续维持;对于接收的敌伪产业,化零为整,集中力量全力经营,力求企业化。1947年,资源委员会下属96个单位,291个厂矿,员工22.3万人(注:“国史馆”编:《资源委员会档案史料初编》上册,台北1984年版,82、131、142页。)。生产量占全国产量的百分比为,电力50%以上,煤炭33%,石油100%,钢铁80%,有色金属的绝大部分,可以说基本上控制了全国的重工业生产(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商经济组编:《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8页。)。资源委员会1946年赢余365亿元,1947年赢余1317亿元,但赢余率由1946年的13.4%急剧下降到1947年的2.56%,显示其经济效益在战乱影响下已无法得到保证。(注:《国民大会代表询问案(资源委员会)之答复》,4页。)
战后国家资本的膨胀,有其主客观因素。客观上是大量接收产业为国家资本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主观上是国民党企图以此为其统治建立有力的经济基础,而国家资本企业对于国民党政权确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以中纺公司为例,1947年账面纯利润5932亿元,其中上缴国库4087亿元,每年无偿供应军用布匹300余万匹,价值超过1000亿元,以及配售公教人员实物棉布。(注:陆仰渊:《中纺公司的建立及其性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因此,国家资本对于国民党的意义不仅仅是个人或团体的利益(如宋子文、孔祥熙或CC系),它对于维系整个国民党统治的作用不可低估,这也是国民党在各界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国营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国家资本的发展还与国民党奉行的经济理念以及后起国家通过计划经济方式追求现代化的模式不无联系。(注: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作者拟另文探讨。)但由于国家资本企业机构庞大、人浮于事、管理混乱,其生产效率不如民营企业。1947年国家资本占全部产业资本的64%,但其产值只占全国总产值的42%,其中经营情况最好的电力工业,设备容量占全国的74%,但发电量只占61%(注:《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第2册,767-768页;《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625、666页。)。由于国营企业效率不高,有研究者因此认为:“抗战胜利后,国家垄断资本虽然因接收了巨额的敌伪产业和美国的援助而高度膨胀,但并没有发挥生产力的作用,而是处于瘫痪状态。它像一个充气的巨人,貌似强大,内部却是孱弱的。”(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603页。)
不可否认的是,确有一批官僚豪门,利用权势,控制国营企业,上下其手,以国家的经济资源为一己谋私利。在这样的情势下,所有国家资本,无论其运作形式如何,有无官僚豪门插手,均被社会舆论指为官僚资本,遭至社会各界的猛烈攻击。傅斯年曾经痛斥说,中国的国家资本“糟的很多,效能两字谈不到的更多。推其原因,各种恶势力支配着(自然不以孔宋为限),豪门把持着,于是乎大体上在紊乱着、荒唐着、僵冻着、腐败着。恶势力支配,便更滋养恶势力,豪门把持,便是发展豪门。”亦曾有国民参政员提出议案,痛斥“官僚资本往往假借发达国家资本,提高民生福利等似是而非之理论为掩护,欺骗社会。社会虽加攻击,彼等似亦有恃无恐。盖官与资本家已结成既得利益集团,声势浩大,肆无忌惮也”(注:陈昭桐主编:《中国财政历史资料选编》第12辑(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123页;《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6册,402页。)。这种对官僚资本的反对声浪自抗战中后期起即日渐升高,至战后更是蔚为潮流。
对于官僚资本问题,国民党内部亦有不少反对声音,各个不同派系间更因利益不同而因此互相冲突,借机发难,CC系对当政的宋子文发起攻击即为一例。CC系文宣系统的核心《中央日报》多次发表社论,抨击“官僚资本操纵整个的经济命脉,且官僚资本更可利用其特殊权力,垄断一切,以妨碍新兴企业的进展。所以代表官僚利益的官僚资本,如果不从此清算,非仅人民的利益,备受损害,抑且工业化的前途,也将受严重的影响”;要求“查一查党内的官僚资本家究竟有若干?他们的财产从何而来?……然后实行一次大扫荡的运动,从党里逐出官僚资本的渠魁,并没收其全部的财产,正式宣告官僚资本的死刑。”(注:《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二中全会辑要》,114、123页。)CC系还借官僚资本问题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对宋子文等发起猛烈攻击,要求行政院如不能解决问题,应即辞职(注:《国民党二中全会面目》,1946年版,40-44页。)。上述言论固然不乏国民党党内斗争因素(注:宋子文一意垄断接收产业和物资处理权,引起国民党内其他派系尤其是CC系的不满,陈立夫曾当面指责宋之经济政策不当。蒋介石因此训诫陈立夫:“以后对外不可再发表对于经济财政有关之言论,须知此时无论任何人或任何政策,担任财政与经济必无良效,只有增加党团之艰危,尤其是社会纷乱,敌党环攻之时,更不能自相攻讦,以加张敌方之力量也”(《蒋中正总统档案·筹笔(戡乱时期)》,15895号)。),但这一问题能够公开见之于传媒,并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共鸣,显见又不单是国民党党内矛盾问题,官僚资本及其引发之社会矛盾已成为国民党官方也无法讳言的不争事实。可是各级官僚毕竟是国民党统治的重要基础,因此国民党始终不能痛下决心,采取合适的方法,解决官僚资本问题,只能听任其发展招致社会越来越大的不满,成为导致其统治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注:纯粹意义的官僚个人资本更易引起社会的不满,如宋子文、孔祥熙家族的公司。蒋介石虽曾对宋、孔的行为颇不以为然,但格于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之关系,仍不能不对他们曲以维护。1948年8月国民党实行币制改革,蒋经国受命前往上海平抑物价,以“打虎”自居,触及孔氏家族的扬子公司。宋霭龄急向蒋介石告状。此时正值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形势已至危急关头,10月18日,蒋介石由北平飞沈阳督战,但他于军务倥偬之中仍不忘徇私情,当天即赶回北平,给吴国桢去电,告以“关于扬子公司事,闻监察委员要将其开办以来业务全部检查,中以为依法而论,殊不合理,以该公司为商业而非政府机关,该院不应对商业事业无理取闹。如果属实,则可属令雇聘请律师,进行法律解决,先详讨监察委员此举是否合法,是否有权。一面由律师正式宣告其不法行动,拒绝其检查,并以此意约经国切商,勿使任何商民无事受屈也。”(《蒋中正总统档案·筹笔(戡战时期)》,16280号)此举名为对监察院,实不无警告蒋经国意。扬子公司被查处事从此烟消云散,蒋经国亦自认失败,只能偃旗息鼓,垂头丧气离开上海,国民党也因此失去了挽回人心的最后机会。)
四、接近破产的财政与通货膨胀的加速
由于种种原因,法币发行自抗战中后期开始日渐增加,通货膨胀由此成为如影随形之顽症困扰着当局。抗战结束后,这一问题除了在最初一二个月内有所缓解外,仍然在继续发展,并已成恶性化之势。
随着抗战的胜利,后方不少人期待复员还乡,急于处理手中的物品,同时沦陷区的接收,使法币使用范围陡然扩大,从而导致后方物价一度急剧下降。重庆物价指数10月较8月下降了1/3,黄金价格只及高峰时的1/5,美元兑换价亦下跌40%以上。而在收复区,由于法币与伪币兑换率被高估,使得物价指数最初亦为下降。上海物价指数9月较8月下降了36%,黄金与伪中储券的比价只及高峰时的1/6(注: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33、198页。)。这是自抗战后期物价高涨以后绝无仅有的现象。然而这种现象实为对胜利的即时反应,并无坚实基础,从11月起各地物价重又上涨,12月的物价指数大致又恢复到8月的水平,而在收复区,由于高估法币币值,造成法币大量拥入,物价上涨更为明显。上海物价指数11月较9月上涨1.87倍,涨幅为抗战以来所少有(注:《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21、168页。)。
从根本上说,物价上涨是政府财政依赖发行造成的恶果。大量纸币充斥于市,又没有相应的硬通货或物资作后盾,当然造成物价高涨;同时物价上涨又迫使政府发行更多的纸币,促使物价进一步上涨,导致恶性循环。战后物价的新一轮上涨,表明涨价的内在动因并未消除,尤其是政治形势的不稳定,内战带来的军费大幅度增长,使赤字财政愈演愈烈,如何处理通货膨胀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政治经济动荡是国民党面临的最大难题。
宋子文以经济专家身份出任行政院长,对于如何解决这一难题一度颇具信心,原因是他手头确有若干砝码是他的前任所不具备的。战后政府掌握了近9亿美元黄金外汇储备和上万亿元的接收物资,为稳定物价提供了有力的物质基础。宋子文为此采取了一些相当大胆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实行金融开放的经济自由化政策,以为这样“对外贸易便可畅通,各项物资尤可随人民的需要而增加,游资之流入投机市场,以助长物价之波动者,亦可纳入商业正轨,国外原料及机械,也可因对外贸易之恢复,源源进口,来配合国内工业之发展,足以使增加生产,并收平定物价的效果”(注:《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二中全会辑要》,21页。)。他通过开放金融市场,钉住法币与美元比价,以稳定法币币值;通过刺激进出口贸易,以大量进口和出售接收物资缓解市场物资供应不足,压抑物价;以开放上海黄金市场,出售黄金,回收泛滥于市的法币,减少市场通货。这些措施一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使1946年上半年的物价上涨势头有所减缓。然而宋子文知道,物价上涨的关键是政府收支不平衡,只有使预算收支大体平衡,才能少发通货,对物价釜底抽薪。他认为:“胜利以后,健全财政,实为首要,而必须求收支趋于平衡之途径,则通货膨胀,自可逐渐遏止,一切金融经济等问题,始可获得解决。”(注: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484页。)
收支不平衡是困扰国民党政府的一大难题。宋子文上台后,在增收节支方面动了不少脑筋。增收方面,大幅度增加了货物税税率,提高了进口货税率,使这两种税有了较大增长。节支方面,宋子文认为政府支出最大的是军费,“在战争结束以后军费应积极减低”,“同时一切政费,凡于经济复员不是切实需要的,也必须在合理范围内极力撙节”(注:《国民党二中全会面目》,70页。)。然而在这方面,他的成就非常有限,他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但却无力改变,因为国民党坚持以战争解决中共问题,军费便不可能减少。庞大的军费完全靠中央银行垫款也就是靠无限制发行纸币解决,因此宋子文不能不声明:“事实上在预算外之支出,为数过巨,且多系临时支出,事前难以预计,收支相较,差距巨大,仍不能不赖于中央银行之垫借。此种超额之支出,则以军费为最巨。”(注:《宋子文评传》,488页。)据统计,军费和特别支出(另一种形式的军费)在国民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比例,1945年为71%,1946年为54%,1947年为60%(注:吴冈:《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153页。),军费成为一个无底洞,消耗了几乎所有可用的资源,最终也导致经济和政府财政的崩溃。
因为收入远不抵支出,法币的发行只能不断增加。1945年8月,法币发行额为5569亿元,为战前的395倍;到1947年2月,则达到48378亿元,为战前的3430倍。1946年初,法币月增发1千多亿,而到1947年4月,月增发额已超过1万亿(注:《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95页。)。同一时期物价的上涨幅度更超过了法币发行的增加幅度,1945年底至1946年底,法币发行月增11.3%,同期物价指数月增16.9%;经过八年抗战,物价上涨倍数超过法币发行倍数的22.5%,而战后第一年即超过111.5%,并且这一差距还在继续增大,两者互相刺激,互为影响,使通货膨胀进入恶性加速阶段(注:《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50页。)。由于法币过量发行,而黄金外汇储备毕竟有限,在金融开放政策实行一年后,1947年2月发生了上海黄金风潮,导致法币币值剧跌,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宋子文只能黯然下台,经济政策也由自由一变而为管制。经济自由化政策本应是和平时期刺激经济之所为,战时经济更适合严加控制的经济统制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宋子文确实犯了错误。但他对此未必不晓,他实行此一政策多少是建立在国内和平之预期上,当内战重起后,此一政策之失败即成必然(注:有关黄金潮问题,请参阅汪朝光的《简论1947年的黄金风潮》,《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
在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正常的收支预算已经无法反映真实的收支状况,预算成了数字游戏,每年编制的政府预算也失去了意义。根据财政部长俞鸿钧的报告,1946年政府收入19791亿元,支出55672亿元;1947年收入138300亿元,支出409100亿元。张嘉璈提供的数字为,1946年收入28770亿元,支出75748亿元;1947年收入140644亿元,支出433939亿元。无论哪一说,赤字均高达60%以上(注:《民国财政史》,171页。)。政府财政已完全成为赤字财政,靠印钞票过日子。而且物价上涨倍数已经高出预算增长倍数,1946年高出36%,1947年则高出215%,表明政府的实际开支处于萎缩之中(注:《历年总预算数与物价增长倍数比较》,二档,档号六—2462。)。由于钞票越来越不值钱,即便政府收支也不得不运用实物(如田赋征实)进行。以往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税收,由于币值变动过于频繁而难以计算;填补亏空的重要手段公债,由于法币信用的低落难以发行。1946年,税收在总收入中只占42.3%,非税收入(包括出售黄金外汇和接收物资)则占到57.6%。在非税收入已经占据政府收入大半的情况下,一旦此项收入枯竭(如停售黄金),填补财政赤字的方法就只剩下印钞票一项,法币信用便失去了最后一道防波堤,其崩溃就不可避免了。
恶性通货膨胀导致广大普通百姓生活水准的下降。法币购买力指数,从战争结束时的0.289,下降到1947年3月的0.0089,幅度之大,是一般工薪阶层难以承受的。虽然实行了以生活指数发放薪金的方法,并按时调整生活指数,但仍赶不上物价的上涨。从物价指数与生活费指数的关系看,1945年9月,上海物价指数为战前的346倍,生活费指数为299倍,此后物价指数与生活费指数互有涨落,互有高低,但自1947年5月以后,直到1949年5月,物价指数始终高于生活费指数。在物价指数高于生活费指数的情况下,工薪阶层的收入绝对下降,而在物价指数低于生活费指数的情况下,因为指数编制的滞后效应(按季或按月进行),以及编制时的操作(如按低价而不按基准价编制),因此以实物计算的收入仍在下降。另据统计,上海生活费指数与物价指数之比,如以1937年为1,则1945年8月为0.68,1947年12月又降至0.49,表明即使按指数计算,生活水平也至少下降50%以上。这种下降在社会各阶层中的表现不一,受影响最大的是所谓公教人员,即各级政府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员和大中学校教师。据统计,昆明的一个大学教授,1945年下半年的月工资为战前的300倍以上,但同期生活费指数上涨6039倍,因此实际收入只及战前的1/20(注:《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84、168-170、335-337页;杨培新:《中国通货膨胀论》,生活书店1948年版,53-54页。蒋介石侍从室六组组长唐纵1946年每月工资收入10余万元,但开支需40余万元,其妻每与他争吵,他也感无可奈何。以唐纵这样的高官尚且如此,惶论一般百姓(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615页)。)。所谓公教人员,是维持政府及社会正常运作的重要环节,他们生活水平的大幅度下降,必然导致其对自己服务的政权态度的变化,从而威胁到这个政权的统治基础。在收入水平大幅度降低的情况下,他们或者是洁身自好,清廉自守,但要忍受清贫的折磨;或者是得过且过,甚或贪污腐败,以至政风日下,民怨四起。国民党统治后期的吏治败坏,确乎不完全是官僚个人品质的好坏问题,而与经济状况尤其是恶性通货膨胀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经济牵动政治,政治又影响到经济,两者形成恶性循环,对国民党统治的衰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国民党统治下的通货膨胀,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其整个统治的政治问题。国民党自己也承认:“风气败坏,军纪废弛,行政效能低落,其最大原因,首为军警公教人员,生活待遇之未尽合理”(注:《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二中全会辑要》,36页。为了缓解通货膨胀对公教人员生活的影响,国民党决定对公教人员实行实物配给制度,1947年3月先在京沪两地实行,供应量为:每人每月米8斗,盐4斤,糖2斤,油3斤,煤球200斤,布每半年20尺(《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第2册,995页)。但这一措施不过施行于部分公教人员,而且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通货膨胀对他们生活水平的影响。)。
国民党对于通货膨胀导致民心涣散的严重性并非不知。宋子文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作政治报告时,通篇所谈内容几完全为经济问题,关键又是如何控制通货膨胀,但他对解决这一问题拿不出行之有效的办法,提出的方案无非增加收入,减少支出的老套。谁都知道,平衡预算的关键是减少军费,而内战带来的军费支出成了预算的无底洞。宋子文知道军费必须裁减,但又承认这“还需要相当时期,方能成就”(注:《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二中全会辑要》,17-18页。)。关键是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决定了军费不可能大幅度削减。1947年2月黄金风潮爆发,宋子文被迫下台,他在立法院报告时声称:“政府对于收入极为有限,但为应付各方开支要求起见,不能不仰仗于增加发行。本人深悉此种途径,足以引起可能之严重局势,因此本人和同僚们,日夜为这个问题担心,但是各方面总以为本人是在一味拂逆他们的意志。如此忍受各方的责备,几乎只可认为命运所支配。”(注:《行政院长易选》,《东方杂志》第43卷6期;《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70册,53页。)此种表示暗含了他对不能削减开支也即军费,结果导致他下台的抱怨与不满。军费降不下来,赤字问题便解决不了,恶性通货膨胀便难以遏止(注:张嘉璈就任中央银行行长后,曾面见蒋介石,要求银行垫款应有限度,紧急支付命令宜经过审核再付,结果财政部长俞鸿钧首先反对,“谓军费支出,无法拒绝,何能规定中央银行垫款限度。主席(指蒋介石—作者注)亦以俞部长所言为然”。张嘉璈深感无奈(《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下册,828页)。)。如时论所言,从“根本上讲,物价的病根在于通货,通货的病根在于内战。内战不停,生产不能进展,通货不能停发,物价便无法收拾”;“今天中国的经济财政病症,任何专家设计,任何医生开药方,其前提只有一个,就是停止内战,实现和平”(注:严仁赓:《检讨黄金政策》,《世纪评论》第8期;《由上海市场看国家需要》,《大公报》(上海)1947年2月6日。)。通货膨胀一旦进入恶性阶段,首先摧毁的是当政者自身的经济基础和统治基础,所谓得不偿失,饮鸩止渴,此之谓也。
战后中国经济的恢复与重建,由于上述各种主客观因素而无法正常进行。中国经济非但未能在战后全面恢复并超过战前水平,反在抗战损失基础上又加一重损失,使经济体系更为残破,最终导致整个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其间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内战重起,使经济发展根本无法得到一个稳定环境的支持。在近代中国长期战乱的特定条件下,稳定的环境较之于经济政策对于经济发展可能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没有把握国内人民望治心切的历史契机,没能以求实的态度实现国内和平。结果,内战不仅使国民党失去了人心,而且是上述经济恢复与重建中的种种困难的根本原因。在已经残破的经济基础上,进行又一场战争,不仅导致经济体系难以承受,从而使经济恢复与重建成为泡影,而且最终也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统治的经济基础。失去了经济基础的国民党,只能以失败为自己在大陆的统治划上句号。
[收稿日期]2001-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