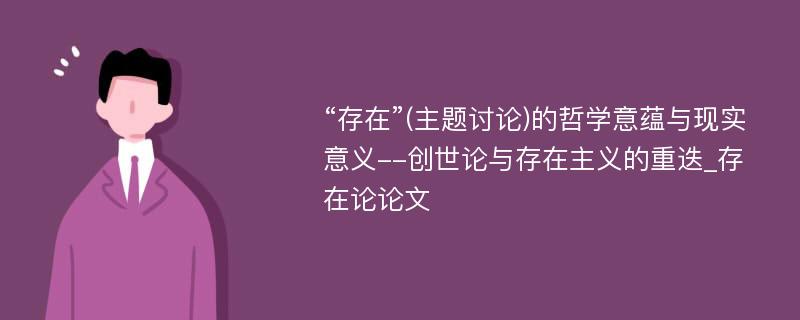
“存在”的哲学蕴含与现实意义(专题讨论)——创世论与存在论的重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专题讨论论文,现实意义论文,哲学论文,创世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4)02-0012-17
无论物的世界是自然发生还是造物主所创,这对人来说并无存在论上的差别。脱离宗教语境而作为哲学概念的造物主其实就是伟大自然的同义词。神性并非物的世界所必需,自然的伟大超越性已让人绝对敬畏。按照老子的说法,自然是不仁的,不具伦理意义,而自然正因没有伦理意义而具有自然正确的必然力量。存在之一般本意就是永在。存在除了“继续存在”这个公开的重言式意图,并不蕴含别的什么秘密。换言之,存在除了同义反复地实现其自身状态,并无秘密可揭。存在的本意既然是重言式的,也就毫无新意,毫无奇迹和历史,不值得记述,也不需要反思。一句话,重言式的存在一如既往地没有提出任何问题,我们对存在也提不出什么问题。如果存在论试图研究存在,则必定一无所获,因为存在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这个所谓的问题与其答案是同一的,尚未提问,即结束。因此,语言不是存在的家园,当语言把存在变成言论或思想的对象,就离间了人与存在。人只有遗忘存在,才与存在浑然一体,而当用语言去呼唤存在时,反而把存在置于远方。对于存在,人只能不置一词。
只有当人有可能把某种存在变成不存在,使如此存在变成不如此存在,或者说,只有当存在的必然性变成了存在的可能性,存在才变成一个问题。把不存在变成可以选择的一种可能性,就是超越存在的必然之死。存在的必然之死不是问题,而是属于事物的一种必然性,而存在的可能之死则是存在论问题。比如说,人会死,这不是问题,而为正义而赴死,就是问题了。当存在必须选择存在的未来,当存在的未来性不再是一如既往的存在,而变成了可以选择且必须抉择的诸种可能性,一个超越了必然性的问题产生了:何种可能性是更可取的?价值问题就这样在选择未来时无中生有地出现了,甚至无须引入关于价值的概念,诸如善恶、优劣等,价值问题先于语言的一切概念而出现在对可能性的选择中:有可能性a,b,c,d……那么选择b。选中b就是以行动假定了b是更好的,尽管无人知道b是否确实是更好的。这是理解事的世界的一个关键:对可能性的选择先于任何价值概念或价值标准,并且无中生有地制造了价值问题,而这个价值问题马上成为存在的根本困惑。
如上所论,存在之本意是永在,为了达到永在就需要善在,因为只有善在才能有效保证存在。这意味着,当存在的前行之路出现分叉(行的原义),就必须选择能够保证善在的那个可能性。因此,当存在的未来出现可以选择的多种可能性,存在为了善在,就不能再重言地重复自身,而只能时时刻刻存在于选择之危机中。虽然存在不是问题,但存在的选择却是根本问题。存在的选择使存在无中生有地具有了价值,由此引发了各种价值问题,伦理、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笔者相信,这是对休谟关于存在和价值疑难问题的一个存在论解决,尽管这不是一个知识论的解决(因此休谟恐怕不会完全满意)。毫无疑问,对存在之未来诸种可能性的选择没有知识理由,没有人能够预知未来,人们不可能对未来的诸种可能性进行优劣比较,因此,关于价值问题不可能有一个知识论的解决。但这里重要的不是能够明辨优劣的知识,而是人们对未来可能性作了选择,而这个选择性的存在行为无中生有地创造了价值。即使永远无从知道选择的对错,选择行为仍然开创了价值问题,仍然证明了存在能够提出价值问题,尽管不是逻辑地推出价值。
自由使存在有了征用诸种可能性的机会,因此,即使一个人只愿意选择毫无变化的未来,选择平凡或正常,这种选择也在诸种可能性的比较背景下变成一种价值选择。于是,选择平凡也是一个不平凡的选择,或者说,当存在的未来是多种可能性,那么,在存在论意义上说,任何一种选择都是创造性的。存在论意义上的创造性并不在于新奇性,而在于超越了必然性。未来的多种可能性迫使人们创造性地选择做某种事情,所以说,有为是存在的始发状态。同时,有为而在是永远的存在论状态,而任何行为都是创造,这就是存在论的初始问题,也是永远的问题。这个存在论问题甚至对于造物主也是如此,假如造物主仅仅存在,万古永在却不创造,那么其存在也是无内容和无意义的。世界的意义由创世者去定义,同时创世者的意义就在于创造了世界。存在与创造是一致的。这意味着,一种能够反思存在本源性的存在论必定同时是一种创世论。这是真正的第一哲学。
只有必须抉择的事情才需要反思,创世是最大的抉择,存在论正是对创世的反思。既然每个行动都是自由选择,因而尽管每个行动都是在接着先前的行为而做某事,也同时是事情的新起点或转折点。换言之,每件事情以及事情的每一步都是事情的临界点,都有可能使事情“从此不同”。因此,每件事情以及事情的每一步在存在论意义上都具有初始性。在这种永远的初始状态下,自由选择必定陷于绝对的犹豫:做这件事还是做那件事?这样做还是那样做?如果说做事是一切问题之源,犹豫就是一切问题的本质。这是先于知识局限或伦理困惑的纯粹存在论犹豫。在根据知识思考某件事情对与不对或根据伦理判断某件事情好与不好之前,人首先须思考何事可做,假如无事可做,则知识和伦理也都失去了其意义。比如说,解一道复杂的几何题也使人犹豫,尤其当两种以上的解题路径都似乎可行时,这是知识论的困惑;面对一个伦理两难同样使人犹豫,因为两条互相矛盾的道德准则都是正当的,这是伦理学的迷茫。这些犹豫都是有理可依条件下的困惑,都是在已有概念和信念之间的犹豫。但存在论的犹豫与此不同:必须做事而不知何事可做,也无从确定何事更好,这种绝对犹豫是先于任何概念和信念的存在论犹豫,也就是创世的犹豫。当没有知识或伦理概念可以参照,人所犹豫的就不是“做什么是对的”而是“做什么”。换言之,在原创状态中,人所犹豫的不是怎样符合游戏规则,而是需要发明什么样的游戏。发明游戏的困惑显然比遵循规则的困惑深刻得多:假如人们对足球、篮球、高尔夫等所有游戏都感到厌烦,于是想要发明一个足够有趣的新游戏,那将是一件极其不易的事情。同样,假如人们对君主制、贵族制、专制和民主制等所有制度都不满意,也会对发明一种足够好的新制度感到力不从心。
做事永远在创造着原生性的问题,因而事的世界永远都处于创世状态,做事的原创性困惑永远不会结束,而将一直持续在创造事的世界的无限过程的每一步之中。因此,人永远生活在存在论的绝对犹豫之中,也就是创世的犹豫之中。既然做事就是开创可能生活,而可能生活所定义的世界就是事的世界,那么,做事就是创世。创造一个构成生活的世界——事的世界,正是人作为人的存在论证明:人作为事的世界的创世者而存在。事的世界证明人的自由存在的本意不仅是“生生”,而且是“创造”。显然,对生活的一切问题的反思都必须追溯到人的创世行为才能得到彻底的本源性解释,而存在论正是对创世行为的反思。因此,人的创世问题就是第一哲学的第一问题。存在和有为是同一的,做事和创造是同一的,所以,存在论与创世论是同一的。作为创世论的存在论蕴含着人的存在的全部秘密,这是属于人的秘密,与神学毫无关系。任何神学背景的解释都是对人的存在的误导,人的存在没有什么历史的目的或终结,与完美概念无关,也没有什么使命,所有那些神学或仿神学解释都缺乏任何在场证据,无法实践地或实质地否定任何一种存在的可能性,不能显示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必然的惩罚”,因此无法消除做事或创造的存在论犹豫。
不能解释创世问题,就不可能理解世界,由此可以进一步清楚地理解关于物的世界的存在论为什么劳而无功。既然人不是物的世界的创世者,那么,关于物的世界的存在论就只限于观察者的想象,而不是当事者的反思,然而当事者视角的缺失使人无法解释关于物的世界的创世问题。所以,脱离了创世问题的存在论是无根的。换言之,如果并非同时是创世论,就不可能是一种奠基性的存在论。传统意义上的存在论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后创世的知识论问题,或是作为美学观点的形而上学。在与创世论无涉的观察者的角度中,人们至多明知故问地询问何物存在(事物是明摆着的),知识论至多澄清了不同事物在不同可能世界中的存在论承诺,却无能力追问事物何以存在。
与此完全不同,在事的世界中,存在既非“如其所是”的形而上学问题,也非“如见所是”的知识论问题,而是一个“有为而在”的存在论问题。显然,单纯的存在仅仅蕴含自身之在(存在仅仅蕴含存在),因此存在不能超越自身,只是按照既定方式继续存在,所以“无事”。“有为”是对存在的超越,迫使存在始终处于抉择之中,因此必定“生事”。做某事或不做某事的抉择,不仅决定了何种可能性是否变成现实,而且同时直接决定了当事者自身的存在状况。换言之,“有为”不仅选择了世界,而且选择了当事者的存在方式。存在论的抉择问题一般表现为“如此存在或不如此存在”两种可能性选择,而其极端表现则是莎士比亚问题“存在还是不存在”。“有为”所面临的选择越是严重,存在论问题就越清晰可见。莎士比亚似乎比许多哲学家更清楚地看到了存在论问题之所在,也就是存在论的绝对犹豫状态。
人类是事的世界的创世者,却永远完成不了创世的工作。因此,只要存在落实为做事,只要“我在”落实为“我行”,存在的第一状态就必定是绝对犹豫。我们确信,存在就是谋求永在,而谋求永在就必须追求善在。可是,既然自由的存在不可能重复既往之在而必须创造而在,既然存在的未来不是既定的必然性而是诸种可能性,那么,人又如何能够知道何种可能生活是善在?这个对于能够看透所有可能性的造物主来说不成问题的事情对人而言却是最大的问题,创世问题使人不知如何是好,因此陷入存在的绝对犹豫。创世者的迷茫是悲壮而伟大的,是主动行为的迷茫,这与个人陷于世界之中等待“被拯救”之孤独、厌烦或绝望的被动迷茫毫无关系。
尽管永远处于存在论的犹豫中,人们却无法停步而必须即刻作出选择,这使得做事具有一种悖论性质:永远犹豫但永远不能犹豫。既然无规可循,那么,做事的唯一出路就只能是创造。但创造并未克服存在论犹豫,而是把存在论犹豫直接转化为现实,这样就把不可解的形而上问题化为可解的形而下问题。显然,对诸种可能性作出事先判断是不可完成的工作,而保护或推翻某种具体现实却总有相应的具体理由和根据。因此,做事必定成为创造,只有创造了某种事情,才有理由否定某些可能性,没有否定就不构成选择——这是人之为人的存在论起点(关于人猿揖别的临界点,实证意义上的临界点也许不易确定,但存在论上的临界点就是:当人类说出“不”这个否定词,就超越了必然性而自由地面对可能性,就开始了人的创世)。做事对可能性的选择就是创世,创世意味着人为之事皆为自由的奇迹,劳动是奇迹,权利是奇迹,责任是奇迹,幸福是奇迹,爱情是奇迹,可是要小心——奇迹是个中性的存在论词汇——人为的一切灾难也是奇迹。
人类一直试图通过反思去拯救真理。对于事的世界,人既是当事者又是观察者,人以当事者的身份去创造可能生活,同时以观察者的身份去反思可能生活。但事的世界的创世是永不完成的行动,真理尚未存在,于是,反思做事或创造就遇到了无所参照的困难。在反思创世问题时,我们不断无助地反问自己: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而不是做那样的事情?为什么这样做而不那样做?为什么选择这样的生活而不是那样的生活?为什么创造这样的世界而不是那样的世界?科学对于回答这些问题毫无帮助,因为事的世界超越了物的世界;逻辑也不能解答这些问题,因为逻辑只能解释必然性而无法解释创造性;信仰更不能解答这些问题,信仰拒绝了存在论犹豫,因而信仰本身就是问题。人无处可逃,唯有在做事之中自求解释,别无他途。可是,既然做事总在创世之迷茫之中,又如何能够自证其善?这似乎是一个悖论。
逃脱这个悖论的唯一机会是,人在诸种可能性之中的抉择无中生有地制造了价值问题——这是最大的奇迹。在通常意义上,存在是存在,应在是应在,应在和存在是两个互相独立的问题,就像平行线不相交,可是,做事迫使这两个问题重叠汇合:既然选择了b而没有选择a,那么,b就被假定为更好的。毫无疑问,这个选择并无事先根据而纯属创造,因此,这个选择本身不能证明b真的是更好的,而仅仅是意向b是更好的。但这就足够了,这个有意选择已经成功地制造了价值问题,而不是掷骰子式的盲目选择。这是关键的第一步,它意味着,做事迫使存在具有价值,这个转化迫使存在论蕴含了道义论问题。不过,这里所说的道义论并非一种伦理学观点,而是一切伦理学问题的存在论基础。既然某事被选定为应在之事,于是,应在变成了存在的理由。在这里,价值问题与存在问题汇合为一。但真正的困难刚刚开始:如何证明所选定的应在之事就是善在?显然,应在仍然需要存在论的证明,也就是说,应在又必须求助于存在。既然除了做事之外别无可资利用的,那么,一切可能的存在论证明就只能落在做事的未来展开中。也就是说,证明就在做事的未来性之中:未来的存在论回报就是唯一的存在论证明。
意识能够自证其完满性,这个无与伦比的优势说服了许多哲学家选中意识作为哲学的支点。笛卡儿证明了“我思故我在”,康德证明了意识的先验效力,胡塞尔进一步证明了“我思其所思”,从而建立了意识的内在完整结构,几乎证明了万事皆备吾心之理(王阳明虽早有此说,却不曾给出一个普遍有效的论证)。虽然普遍的我思能够建构完满的所思世界,却不足以解释事的世界。问题在于,所思可以心同此理,所为却其心必异,当具体事情将普遍通用的主体落实为具体当事人,我之所思是否能够落实成真,却非我思所能独立决定,而必须求得他人同意。更严重的是,即使是最美好的愿望,几乎人人乐见其成,却也未必能够成真。如列维纳斯之想象,看到一张人脸就应直接意识到“不要杀人”的绝对伦理呼声,这种善良意识就几乎人人同意(极少数杀人狂不算),可谓心同此理,然而,无数行为事实却证明事情并非如此。又如,人们可以想象一个最好的社会,一个人间天堂,在那里每个人的需求都得到满足,其自我和自由都得到实现,历史也因为功德圆满而终结。这种想法估计有不少人同意,但也没有真实意义,因为不存在也不可能创造出一个能够满足每个人的需求、自我、自由和幸福的社会,除非那是一个无穷大的虚构世界。
唯心论总是试图证明主观世界是自身完满而自足的(就像胡塞尔试图证明的那样)。可是,即使意识真的是自足的,也至多证明了“我思”具有内在的客观性,仍无法解决“我在”所遇到的诸种外在性。也就是说,即使“我思”是自足的,“我在”仍然不是自足的。比如,完满的我思无力拯救饥寒交迫的我在。我思不可能解释存在论问题,也解决不了基于存在论问题而产生的伦理学、政治学或经济学问题。这个局限性使得我思不可能像笛卡儿或胡塞尔所想象的那样成为一切哲学的基础。无论我思多么完满地解释了所思,却决定不了也阻止不了世界上任何事情的发生,无论多么完满的我思也对付不了战争、谋杀、剥削、压迫、欺骗和背叛等祸事,也解释不了爱情、友谊、救助、献身、自由、人权和公正等幸事。我思对一切发生在历史和世界中的伦理、政治或经济问题都束手无策,对所有生活困惑都无计可施。即使我思之所思是毁不掉的绝对意识,只要我思不能防止一切罪行或落实任何拯救,就在存在论上既失去物的世界也失去事的世界。总之,我思不可能说明我在的任何问题。
“我思故我在”只是一个逻辑证明,并非存在论证明。属于我思的观念世界与我所在的生活世界之间有着存在论鸿沟。即使一件事情能够被我思定格为在心中永不磨灭的所思,但所思之事却与所为之事不对称,我思的意向性跟不上我行的创造性,事情的未定性使我思至多能够思想一半事情,因为事情的另一半总是尚未创造出来,永远隐藏在难以定夺的诸种可能性之中,而我行之犹豫未决使事情的性质、方向和意义永远处于未定状态,无法被概念化,无法被我思的意向所指定。
既然决定命运和历史的各种事件属于事的世界,既然不是我思而是我行创造了事的世界,那么,事的世界所表明的原则就是:“我行故我在”。我行才是我在的存在论证明,而既然人是事的世界的创造者,有为必然意味着创世。于是,“我行故我在”就同时意味着“我创世故我在”。存在论证明须提供实在业绩,不能仅靠推理。我在的存在论证明就在于行为创造了事的世界。我思只不过看见了世界,因此我思之我只是一种虚在;我行使我拥有世界,我行之我才是实在。只有创造了事的世界,我才有了所在之处,才有了生活,所以,一切哲学问题都始于人的创世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存在的家园不是语言,不是概念,不是思想,也不是信仰,而是行善或作恶所形成的可能生活。
人的创世行为并不限于开天辟地的划时代大事,每个人对未来可能性的选择都是创世行为,因为每个选择都可能使得事的世界因此有所不同。既然人们可以选择让一种事情发生或不发生,可以选择让一件事情成为这样或不成为这样,那么,任何事无巨细的选择都在创造着人人所在的事的世界。喝一杯酒、供一碗饭或说一句话,都可能是创世行为,都可能给他人甚至世界造成灾难或带来幸福。这里可以看出做事所蕴含的根本问题:既然做事创造事情,而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仅仅是我的事情而必定也是他人的事情,因而做事并非仅仅证明我的存在,其在证明我在的同时必定证明他人之在。
做事必定卷入他者,这不是说,我做了某事,然后某事对他人产生影响,而是指如果我的行为没有卷入他人,没有邀请或强迫他人共同行为,根本就做不成任何事情,甚至无事可做。而如果事情不存在,事的世界也就不存在,我就无从进入事的世界,而仅仅是物的世界中的一个物理或生物存在。即使有的行为似乎是我独自完成的,也是某事的一个构成部分——事情不是个体事物,而是无形伸延流动着的关系。假如一个行为不是某事的构成部分,这个行为就仅仅是一个生物或物理动作。这意味着,在做事所创造的事情中,我虽然是语法上的主语,但在存在论意义上,我却不可能是唯一当事人,我必定卷入他人成为共同当事人(通常是无数他人)。于是,做事的语法主语是我,但其存在论主语却是我们。一切事情都意味着我和他人的同时在场性,我不可能独占任何事情,更不可能独占未来,而只能与他人共有未来,因此没有他人也就没有未来。我作为个体存在于物的世界中,却作为一个无法独立的当事人存在于事的世界中。这正是事情的本质:事情不属于任何一个人,但任何一个人都属于某个事情,每个人都代表或代理着未来的某种可能性而成为事情的一个构成部分。
当我以自我为存在,我才是仅仅属于我,但这个独立自足的我却一无所有,旁观世界而并不拥有世界;只有当我成为创世者,我才拥有世界,同时成为事中之在,成为事情的一个可能性,事中之我不可能独立存在,而是与他人共在,共同因事而在。事中之在才是充分实现的存在,因为唯有事中之在才具有在场性,事情就是我得以出场之场所,如果没有这个场所,我就生无在场之地,就存而不在。超历史的我思先验地拥有概念化的世界或世界的概念,但概念化的世界是观念性的,我无法生存于其中,所以说,仅仅作为我思之我虽存而无以为在。Cogito仅仅证明了我的虚在,一个存而未在的语法主语,尚未成为主事的存在论主语。只有在主事的做事中,我才真在,而我之真在在创世的同时就成为事的世界的一个可能性而失去其孤立性和自足性,不再超历史,不再超现实。
既然做事绝对优先,具有初始性和开创性,做事就是召集他人现身的行为,每个人通过做事而成为他人的召集人。每个人都是超越者,都是创世者,因此当他人被召集在某事中现身,就同时成为共同召集人,成为事情的共同创造者——我的事情就同时成为他人的事情。因此,任何一件事情都先验地证明了我和他人的存在,或者说,任何事情的内在结构都是共同当事人之间的互动关系,都先验地承诺了我与他人的事中存在。这一点,也是我行作为哲学支点的一个存在论优势:即使我思能够证明我在,却不能证明他人之在,也不能证明世界之在,而做事不仅证明我在,而且同时证明了他人之在,而做事同时是创造,也就证明了事的世界的存在。每个人都是事中之在,都是事情的召集人,既然当事人都是召集人,就无人是事情的主人,任何人都不可能对任何事情完全做主,这一点否证了唯我论和主体性原则。做事所证明的不仅是我的超越性,而且同时证明了他人的超越性,于是,事的世界的内在结构是我与他人互为超越的关系。这是我行故我在的要义。
人们喜欢追问人的存在的意义或目的。这个问题多少涉嫌过度反思,但并非一个无意义的问题。假如这个问题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就能阻止关于人的问题的过度反思。本来,存在就已经是对存在的完全解释,但问题在于,人的存在是创造性的,因此人的存在意图明显超出了存在的重言式意图。在这个意义上,人的存在的意义并非一个无意义的问题,人至少必须解释人想做什么。神学目的论曾试图以神意去解释人的目的,神学解释虽然便捷,却缺乏必然依据。如果神果真有所示意,也必定直接表现在所造万物的显然征兆之中(例如《周易》所直观所知的存在之生生本意),而无须假道先知难以保真的翻译(万能的神不需要先知的帮助)。另外,即使神乃一切存在的意义所在,那么,一切意义都是神的意义而不是属于人的意义,人就终究没有意义——缺乏自足意义就等于无意义。因此,在人的存在之外的任何目的论都不足为证,人必须就在人那里证明人的意义,才是对人的存在的意义的完美自证。
人之自然存在本身未必有目的,但人却在创世中创造了目的,因而使自身存在具有意义。也就是说,人不是因为自身存在有意义才去做事,而是因为做事才有了意义。人在做事中召集(请入或卷入)他人来为所作之事的意义作证,而既然人人都是召集人,于是人们在共在之事之中互相作证,而这种互相循环作证表明了人的意义就内在于生活之中,内在于事的世界之中。假如一个人提问人的意义在哪里,或者人要到哪里去,则是在提出无意义的问题,因为人的意义就在生活中,人哪里也不去,就在人这里。
人的存在的意义就在创世所为之中。但人的存在如何善在,如何创造最好的可能生活,自从人开始反思生活就一直是未解之谜,而且随着反思越来越深入,就愈加困惑,尤其是现代和后现代的反思,终于使价值失去一切标准。尽管人们可以批评现代性对古代传统价值标准的过度反叛,或者批评后现代对一切价值的过度质疑,但不等于传统价值或现代价值无可置疑。任何价值和标准之所以能够被质疑,是因为所有价值标准确实都难以自圆其说,没有一个价值标准是足以自证的。人所做的事情越多,就越暴露出人的存在论犹豫的深度和广度,人的选择困惑就越来越无法掩饰。尽管我思能够借助理性去捍卫自我以及所思的确定意义,却也无力捍卫任何价值标准的普遍性。于是,我们只剩下我行这个最后的根据。我行必须解决所制造的问题,必须能够自证其选择的正确性,而真正严重的挑战就在这里:我行唯一可以指望的证明在于未来性,而未来尚未存在也尚未确定,那么,又如何指望未来的证明?
我们已经论证,既然我行是创造,那么,事情就是接踵而至的奇迹。我行的每一步都是事情的新起点或转折点。未来具有可选择性,这就要求诸种可能性具有可比性,却缺少可比标准。能够选择未来,既是存在的幸运(因为有机会选择更好的),但也是一种形而上的痛苦,因为不知道何者更好——但我们又必须需要知道何者更好。这似乎是一个不合理的要求。假如要判断一种事情的价值,就必须事先拥有标准,但在意识中是找不到这样的标准的,因此我们不可能指望我思,而只能指望我行。于是,我行不仅无中生有地制造了价值问题,而且还必须继续无中生有地证明什么是好的。
既然我行所能利用的唯一资源就是未来,那么,提前分析未在之未来的唯一机会就是把未在性化为在场性来考察,也就是把不可见的可能性转化为可见的可能性。未来由逻辑上的一切可能性组成,这是不可见的可能性。然而,对于事的世界,有效的可能性大大少于逻辑的可能性,事的世界的未来可能性必定是人所欲的可能性,于是,未来的可能性就被约束为人的可能选择,人所希望的可能性才是可能中选的未来。每个人的意向选择无法必然如愿地决定未来,因为他人有异议,异议就是最强的约束条件,于是,未来的可能性通过异议而成为在场的可能性。在这里,我们得到一个化未来为在场的方法:未来的诸种可能性映射在人们的可能意向中,每个人的意向都代表了未来的某种可能性,于是,未来的诸种可能性显现为在场的各种意向。尽管未来仍不可预言,我们无法预言什么事情将必然发生,但既然未来的可能性已被转换为在场的诸种意向性,我们至少有望证明何种可能生活是善在。换言之,我们不可能阻止愚蠢的行为,但有望知道什么是愚蠢的行为。
笛卡儿对我思的证明模式令人深受鼓舞,当然,我们并不满足于证明我行的确实性,而是试图证明,在什么情况下的我行不会导致自身否定。也就是说,一种我行如何不会在其未来性中被否定。显然,假如一种我行不可能导致自身否定的结果,那么,它所创造的事情就是善在。做事成败的秘密就隐藏在行为的回应性之中。做事所引发的回应行为决定了未来,因此,回应性就是事的世界之存在论线索,由此线索可以理解事的世界之治乱分合、成败兴衰、荣辱苦乐、战争与和平、幸福与不幸、变革与保守等一切变化。他人的选择是对我的选择的回应,反过来,我的行为也是对他人行为的回应,或为报复,或为报答。他人的回应决定了我行是否被否定,如果没有他人的同意,一种行为就不可能形成事情。于是,他人的同意决定了事情的存在论有效性。更准确地说,每个当事人都同意的事情就具有存在论有效性。事情的存在论有效性意味着“无人被排斥”的原则:一件事情在存在论上是有效的,当且仅当,这件事情没有排斥任何一个当事人的存在,没有否定任何当事人的在场性,没有剥夺任何当事人的未来。这个原则说明,如果我行能够保证不被否定的未来性,就必定邀请他人到场合作并共享所创造的事情。换言之,我行必须迎入他人共同成为事中之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