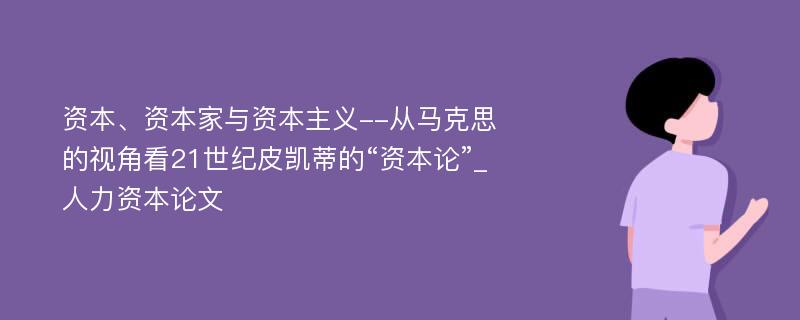
资本、资本家与资本主义——从马克思看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资本论论文,资本家论文,资本主义论文,凯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的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甫一出版,即引起强烈反响,更是受到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21世纪资本论》这个中文译名很容易使人想到一个半世纪以前马克思的《资本论》,而且皮凯蒂也的确不断地提及马克思,并在很多问题上表达了或同或异于马克思的观点。本文立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对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有关资本与劳动、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以及与此相关的资本主义未来走势的论述作一番分析、比较,希望藉此更好地了解皮凯蒂,也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尤其是,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当今危机四伏的世界和人类不确定的未来! 一、资本:“物”抑或生产关系? 1.什么是“资本”?皮凯蒂提出了至少两个不同的定义。一个是:“资本指的是能够划分所有权、可在市场中交换的非人力资产的总和,不仅包括所有形式的不动产(含居民住宅),还包括公司和政府机构所使用的金融资本和专业资本(厂房、基础设施、机器、专利等)。”①可见,要成为资本,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其所有权可以析分和转让,二是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 根据这一定义,皮凯蒂把“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区别开来,强调他所“提到的‘资本’均不包括经济学家们经常提及的……‘人力资本’”,从而在资本的定义中排除了人力资本。其中所谓“最显而易见”的原因便是:由于“人力资本通常包括个人的劳动力、技术、熟练程度和能力”,所以,“人力资本无论何时都不能被另一个人所有,也不能在市场中永久交易。这是人力资本与其他形式的资本最显著的区别”②。 其实,“人力资本”理论并不新鲜,一些庸俗经济学家早就“把劳动能力称作工人的资本,说它是这样一种基金:工人通过某次个别的交换并没有把它消耗掉,相反,他在他作为工人的生命期间能够不断重复这一交换”。就此,马克思指出:第一,“按照这种说法,同一主体[反复经历的]过程[的基金都是资本],例如说,眼睛的实体是视力的资本等等”。这不过是一些“只有对于蹩脚的美文学家和信口开河的饶舌家们才是有用的”美文学的言辞,这种言辞“按照某种类比任意把一切东西拉扯在一起”,“把极不同类的东西混为一谈”。第二,固然,只要工人能够劳动,劳动总是工人同资本进行交换的新的源泉,“这是包含在概念规定本身中的”,就是说,“工人出卖的只是对自己劳动能力的定时的支配权,因此,只要工人得到相当数量的物质,能够再生产他的生命表现,他就可以不断重新开始交换”。但是,“对于工人只要睡足吃饱就会活下去,因而可以每天重复一定的生活过程这一点,无须表示惊讶”,相反,“倒是应该看到:工人在不断重复劳动之后,仍然只能拿自己的直接的活劳动本身去交换。[过程的]重复本身实际上只是表面现象”。对工人来说,活劳动本身始终是唯一可用于交换的东西,而劳动过程的不断重复,无非是为了保持这种劳动能力的再生产,进而保证工人能够活下去。劳动力怎么能是资本呢?第三,工人同资本进行交换的,是他例如在20年内可以耗尽的全部劳动能力。只不过,资本给工人的全部劳动能力的报酬不是一次付清,而是像工人把劳动能力分期提供给资本支配一样,分期支付,例如按周支付。可见,“这丝毫也不会改变事情的本质,并且绝对没有理由得出结论说,因为工人必须休息10-12小时才能重复他的劳动和他同资本的交换,所以劳动就构成工人的资本”。实际上,“在这里被理解为资本的东西,是工人劳动的界限,是工人劳动的中断,就是说,工人不是永动机”③。与劳动力一样,劳动也不可能成为工人的资本,因为,工人从资本家的分期支付中所得到的,不是“劳动”的报酬,而是再生产“劳动力”所需的费用,是“不劳动”时的花销。因此,“把劳动能力理解为工人的资本”是极其荒谬的④。 在此,马克思对“人力资本”这个概念本身就持否定态度,与此不同,皮凯蒂认为:“在奴隶社会……一个奴隶主可以完全彻底地拥有另一个人的人力资本,甚至是那个人的子孙后代。在这样的社会中,奴隶们可以在市场上买卖、通过遗产继承,同时将奴隶算入奴隶主的财富是十分常见的情况”。“除了这些特殊的历史案例之外,尝试将人力资本加入非人力资本是不太合理的”⑤。皮凯蒂所反对的,仅仅是把“人力资本”并入“非人力资本”这样一种混淆,或者说,他并不一概否定人力资本理论。面对近年来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这些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他的解释是:它们“没有一个受益于大规模的外商投资”,而是“自己投入了发展所需的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⑥。皮凯蒂在这一问题上的自相矛盾可见一斑。 2.资本的第二个定义是:“所有形式的资本都具有双重角色:既有存储价值,也能作为一种生产要素。”鉴于此,皮凯蒂认为没有必要“严格地区分财富与资本,这样会更为简单”。或者说,“为了简化文字”,他所“使用的‘资本’与‘财富’含义完全一样,两个词可以相互替换”⑦。可见,举凡资本,既可以用于存储,也可以用来进行生产,因此,资本就是财富,财富就是资本。 根据这一定义,皮凯蒂反对把黄金排除在资本之外。例如,一些定义认为:“财富中只有直接用于生产过程的那部分才能称为‘资本’”。这样,黄金就被归入财富而非资本,因为“黄金被认为只有储值的功能”。皮凯蒂则认为:“这个限制既不可取也不可行”,因为,“黄金可以成为生产要素,不只用于珠宝的生产,同时还可用于电子设备和纳米技术的生产”。有人将“非生产性”的居民住宅排除在资本之外,理由是:“居民住宅不像‘生产性资本’(工业厂房、写字楼群、机器、基础设施等)那样,可以被公司和政府所使用”。皮凯蒂反驳道:“事实上,所有形式的财富都是有用的、生产性的,同时也反映了资本的两种主要经济功能。居民住宅提供了‘住宅服务’,而服务的价值可以用等价的租赁费用来衡量,因此居民住宅可以被视为资本”⑧。这样看来,用于生产的黄金是资本,放在保险柜里的黄金也是资本;出租给别人的住宅是资本,用于自家居住的住宅也是资本。 皮凯蒂给出的两个资本定义,其内涵并不一致,这自不待言。在谈到生产要素时,马克思说:“就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单纯过程来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形式所共有的”⑨。即是说,生产要素是劳动过程即物质生产所不可或缺的,因而也是一切社会形态的劳动过程所共同具有的。从这一标准来看物质生产,既可以说它是由“两要素”构成的,也可以说它是由“三要素”构成的。对于前者,马克思有下列不同的表述:“劳动过程,就我们……把它描述为它的简单的、抽象的要素来说……我们不必来叙述一个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这就够了”。“劳动过程所需要的一切因素: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⑩。因此,构成物质生产的两个要素,一个是人及其劳动或者说劳动力,这是“人”的要素,另一个就是自然及其物质或者说生产资料,这是“物”的要素。马克思还将它们叫做“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11),或者叫做“主体”因素和“客体”因素(12)。对于后者,一如马克思所讲的:“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其中,劳动资料作为“劳动者直接掌握的东西”,“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13)。显然,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从来就不是什么“生产要素”。 3.皮凯蒂从不同的标准出发,对资本的种类进行了划分。其一,假设所有物品都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就可以“将‘国民财富’或者‘国民资本’定义为在某个时点某个国家的居民与政府所拥有的全部物品的市场价值之和。这包括了非金融资产(土地、住宅、企业库存、其他建筑、机器、基础设施、专利以及其他直接所有的专业资产)与金融资产(银行账户、共同基金、债券、股票、所有形式的金融投资、保险、养老基金等)的总和,减去金融负债(债务)的总和”(14)。在此,资本被划分为“金融资本”和“非金融资本”。 其二,虽然人力资本因其不能在市场上交换(奴隶社会除外)而被排除在资本的定义之外,但在皮凯蒂那里,“资本并不仅局限于‘物质’资本(土地、建筑、基础设施以及其他的一些产品)”,而是“将‘非物质’资本(如专利以及其他知识产权)也包括了进来,以两种形式呈现:(1)如果个人直接拥有专利,那么算入非金融资产;(2)如果个人通过持有公司股份来拥有专利(这种情况更为常见),那么这些是金融资产。更广泛来说,通过公司在股票市场上的资本化,许多形式的非物质资本都可以被考虑进来。例如,一个公司的股票市值一般取决于企业的声誉、商标、信息系统、组织模式、投资等,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都是为了让公司的产品和服务更具有吸引力。这些都反映在公司的股票和其他金融资产的价格上,同时也反映在了国民财富中”。在此,资本被划分为“物质资本”(或“实物资本”)和“非物质资本”(15)。 其三,“非人力资本……简单称之为‘资本’……包含了私人(或私人团体)可以拥有并且能够在市场上永久交易的所有形式的财富。在现实中,资本能够被私人所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称之为‘私人资本’),或者被政府或者政府机构所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称之为‘公共资本’)。同时,也存在着中间过渡形式的资产,它们为了追求特殊的目标以集体所有的形式被‘法人’所有(例如基金会和教会)。”在此,资本被划分为“私人资本”、“公共资本”和“法人资本”,它们合起来就是所谓的“国民资本”(16)。 由此可见,在皮凯蒂笔下,资本是一个极为宽泛的概念。针对这样一种资本定义,即:“根据某些定义,用‘资本’这个词来描述人们积累的财富更为合适(房屋、机器、基础设施等),这种定义排除了土地和自然资源,这些资源一般被认为是人天生就有的而无须积累。因此,土地被认为是财富的组成部分,但不是资本的组成部分”。皮凯蒂提出的反对意见是:“我们很难将建筑的价值从其所建造的土地上单独剥离出来。更难的是。我们几乎无法排除人们在土地上增加的附加价值(例如排水系统、灌溉设施、肥料等)而单独测量土地的原始价值(人们在千百年前发现的那样)。石油、天然气、稀土元素等自然资源的价值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们很难将人们在勘探采掘中所投入的价值剥离出来,单独计算自然资源的纯粹价值。”因此,他“将这些形式的财富都归入了‘资本’中”。土地作为财富是“土地资本”,自然资源作为财富便是“自然资本”(17)。 然而,在马克思看来,商品才有价值,不是商品就没有经济学意义的价值;而没有商品生产,就没有商品和商品价值。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谁会计算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价值呢?即使在商品生产条件下,离开人的农业劳动,怎么会有土地的所谓“原始价值”呢?离开人的采掘劳动,怎么会有自然资源的所谓“纯粹价值”呢?更何况,无论是商品还是货币,这些具有价值的东西不一定就是资本。马克思指出:“劳动的客观条件不是像在原始状态下那样表现为简单的自然物……而是表现为已被人类的活动改造过的自然物。”“作为简单的自然物,它们从来不会是资本。”(18)因此,并不存在什么土地资本和自然资本,皮凯蒂的观点是一种典型的“泛资本论”。 不仅如此,如果把土地和自然资源都看成是资本,就会把资本自然化、永恒化和绝对化,因为,“按照这种说法,资本存在于一切社会形式中,成了某种完全非历史的东西”。作为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土地和自然资源构成物质生产的实际内容,而资本则是物质生产的一种社会形式。“如果这样抽掉资本的一定形式,只强调内容,而资本作为这种内容是一切劳动的一种必要要素,那么,要证明资本是一切人类生产的必要条件,自然就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抽掉了使资本成为人类生产某一特殊发展的历史阶段的要素的那些特殊规定,恰好就得出这一证明”。但是,问题的要害在于:如果把资本等同于物质生产中的物质内容,即等同于对象化劳动,或者,“如果说一切资本都是作为手段被用于新生产的对象化劳动,那么,并非所有作为手段被用于新生产的对象化劳动都是资本”(19)。 诚然,皮凯蒂也一再强调“资本的概念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资本自身的性质发生了彻底改变”,甚至认为资本“反映出了每个社会的发展态势及该社会普遍的社会关系”。但是,他所理解的资本概念的历史变化仅仅在于:“从18世纪的土地和其他不动产变为21世纪的产业和金融资本”。马克思之所以“将李嘉图的资本价格模型以及稀缺性原则作为强化资本主义动态分析的基础”,就是因为“当时资本主要是工业设备(比如机械、厂房等)而非土地资产,因此原则上资本累积数额没有限制”(20)。在此,姑且不论在马克思那里资本积累的无限性是否由土地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变所决定,可以肯定的是:皮凯蒂所讲的与其说是资本概念和性质的变化,毋宁说是资本类型和结构的变化,即马克思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工业资本,之前是土地资本,之后则是金融资本。而无论是否居于统治地位,把不同社会形态中的土地统统都界定为资本,资本的“历史性”就被遮蔽掉了。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前资本主义(如封建主义)的土地所有权与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权具有质的区别。 最后,皮凯蒂的资本观是一种典型的“拜物教”观念,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经济学家们把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受这些关系支配的物所获得的规定性看作物的自然属性,这种粗俗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同样粗俗的唯心主义,甚至是一种拜物教,它把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内在规定归之于物,从而使物神秘化”(21)。而且,与庸俗经济学家们一样,皮凯蒂这种“拜物教”或“拜物教观念”是“不加考虑地、无意识地和天真地从资本主义的思想方式接受来的”(22)。 4.针对庸俗经济学家的资本观,马克思指出:“资本仅仅被理解为它借以存在的那些商品的使用价值(资本对象),而不是被理解为形式规定性,以商品为承担者的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这表明,同任何经济范畴一样,资本具有“形式规定性”,或者说它是一种“形式规定”。一方面,资本反映和体现着特定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构成其“本质规定”;另一方面,它又被特定的物质存在(如劳动产品)所承载,这种载体构成其“物质规定”。如果把资本等经济范畴看作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那么,其躯体就是物质存在,其灵魂则是生产关系,由此便不难理解马克思所说的“作为生产关系的资本的概念”的含义了(23)。马克思不仅区分了资本的躯体和灵魂,即资本的物质规定和本质规定:“生产的这些对象条件本身不是资本,只有当它们表现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时才成为资本”;而且区分了资本的躯体和生命,即资本的物质规定和形式规定:“产品本身属于任何劳动方式,而不论劳动方式的一定的社会形式如何。产品只有在它表示一定的、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时才成为资本”(24)。 与此不同,庸俗经济学家无力把经济范畴的物质规定和本质规定区分开来,因为,“在政治经济学家的头脑中,它们(指作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物。——引者注)的这个资本主义灵魂和它们的物质实体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致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当它们正好是资本的对立面的时候,他也把它们称为资本”(25)。同时,他们也无力把经济范畴的物质规定和形式规定区分开来,因为,“在这些经济学家们那里,资本的物质要素和资本作为资本的社会的形式规定性(即和资本作为支配劳动的劳动产品的对抗性质)是如此地生长在一起,以致他们提出的任何一个论点都不能不自相矛盾”(26)。特别是,如果把资本看成是物,看成是物所具有的性质,“这一点就被利用来为资本辩护,把资本与一般简单劳动过程的一种要素混淆或等同起来,从而说什么用于生产另外一种产品的产品就是资本,原材料是资本,或者劳动工具,生产工具是资本,因此,资本是同一切分配关系和社会生产形式无关的、一般劳动过程的因素、生产的因素”(27)。 以此来看,当皮凯蒂把银行储蓄一概看成是一种资本存量的积累的时候,或者,当他把社会主义苏联的生产资料看成是一种国家控制的资本的时候(28),其思想倾向与马克思所批评的庸俗经济学家并无二致,他们都忽略了生产关系对“物”所具有的经济意义,都把具有不同社会性质的“物”混为一谈。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一块土地、一台机器,还是一间房屋、一笔存款,总之一种物是否是资本,要看它与生产关系的关系,要看它所处其中的生产关系的性质,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正如生产者所消费的他自己的产品不是商品一样,充当生产者本身的就业手段和生存资料而不合并他人劳动以自行增殖的分散的生产资料,也不是资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财产,不是资本。它们只有在同时还充当剥削和统治工人的手段的条件下,才成为资本”(29)。 二、资本家:“富人”抑或剥削阶级? 1.皮凯蒂认为:“所有产出必须以某种收入的形式分配到劳动或资本上”,因此,收入包含两部分: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前者“作为对工人和在生产过程中贡献了劳动力的人的报酬”,包括工资、薪水、酬金、奖金、工资以外劳动所得,以及“其他法定划分为与劳动有关的报酬”;后者“作为对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资本的所有者的报酬”,包括利润、利息、股利、红利、租金、版税(版权所得),以及“其他因拥有以土地、房地产、金融工具、工业设备等形式存在的资本所带来的收入”。可以说,“无论是公司账户、国家账户还是全球经济,相应的产出和收入都可以分解为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国民收入=资本收入+劳动收入”。这就表明,人们既可以拥有资本,也可以拥有劳动;资本为其带来资本收入,劳动则为其带来劳动收入。资本是一个存量,而收入则是一个流量。前者作为“此前所有年份获得或积累的财富总量”,指的是“某个时点上所拥有的财富总额”,后者则是指“某段时间内(一般为一年)生产和分配的产品数量”(30)。 以此来看,虽然皮凯蒂承认“有些收入(例如非工资的个体经营收入和创业所得)很难拆分为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即看到了收入问题的复杂性;但是,由于把劳动和劳动力、资本和物等具有不同性质的概念混为一谈,所以,他所说的一些资本收入,在马克思看来恰恰是一种劳动收入,如版税或版权所得等。或者既不是资本收入也不是劳动收入,如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地租金。而他所说的一些劳动收入,在马克思看来恰恰是一种资本收入,如所谓“投资者”的资本运营(研究投资机会、调配投资项目等)带来的收入等(31)。或者既不是劳动收入也不是资本收入,如普通居民的房屋租金等。在马克思看来,不能就收入论收入,就像不能就物论物;不能把从物而来的收入都看成是资本收入,就像不能把物都看成是资本。房屋出租收取租金,银行存款得到利息,但不能说这房屋和存款就一定是资本。一种物是否是资本,要看生产关系的性质;同样,一种收入是否是资本收入,也要看生产关系的性质。 在马克思看来工资是劳动收入这种说法是很荒谬的,因为,“一般说来,价格只是价值的一定表现”,所以“劳动—工资,劳动的价格……这种说法显然是和价值的概念相矛盾的,也是和价格的概念相矛盾的”。就是说,工资只能是工人劳动力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即价格,而活的劳动作为商品价值的源泉,它本身并没有价值,因而也就没有价格。同样,利润或利息是资本收入这种说法也是很荒谬的。因为,“如果资本被理解为一定的、在货币上取得独立表现的价值额,那么,说一个价值是比它的所值更大的价值,显然是无稽之谈”;而如果资本被理解为某种“物质实体”,理解为“作为劳动生产条件的使用价值,如机器、原料等等”,那么,“一方是使用价值,是物,另一方是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是剩余价值”,这明显地是“让两个不能通约的量互相保持一种比例”(32)。 把收入划分为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不仅不能说明、相反却是遮蔽了收入的真正来源。皮凯蒂认为:资本收入是“资本所有权带来的所有收入”(33)。但资本所有权何以会带来收入呢?在商品生产条件下,收入是一种价值,难道说从资本所有权中能够生产出商品的价值来吗?马克思指出:“对那些生产当事人来说,资本、土地所有权和劳动,表现为三个不同的、独立的源泉,每年生产的价值——从而这个价值借以存在的产品——的三个不同的组成部分,就是从这些源泉本身产生出来的;因此,不仅这个价值作为社会生产过程的各特殊因素所分得的收入的不同形式,是从这些源泉产生出来的,而且这个价值本身,从而这些收入形式的实体,也是从这些源泉产生出来的。”(34)与庸俗经济学家一样,皮凯蒂把价值的不同“收入形式”和价值的“实体”混为一谈,由此便产生一种幻觉,即“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35)。显然,皮凯蒂所谓的“收入”不过是一个统计概念,其建构的收入模型也不过是一种价格理论,而不是价值理论。例如他讲:“居民住宅提供了‘住宅服务’,而服务的价值可以用等价的租赁费用来衡量,因此居民住宅可以被视为资本。”(36)皮凯蒂这里不仅把资本与物(住宅)混为一谈,而且把价格与价值、产品与商品统统混为一谈。当然,他可以借助于统计方法对人们的收入进行统计,然后借助于这些统计数据,建立起各种数学模型,并绘制出各种图表曲线,进而研究社会的分层问题。 2.皮凯蒂认为,收入层级不同于财富层级。例如,“劳动收入分配的最上层10%或最底层50%不是构成财富分配最上层10%或最底层50%的同一批人。收入最高的1%不是占有财富最多的1%”。因此,“劳动收入、资本占有和总收入(包括劳动和资本)的前10%和前1%群体是分别定义的”(37)。尽管如此。根据收入情况,可以把人们区分为“下层阶层”、“中产阶层”和“上层阶层”,他们分别是处于收入最底层的50%、收入中间的40%和收入最上层的10%。而且,必要时还可以使用百分位数甚至千分位数对这些人群进行更精细的划分,以便“更精确地记录社会不平等的连续性特征”,从中会看到,“在每个社会,甚至在最平等的社会里,最上层的10%人群其本身的确就是一个世界。其中,有些人的收入仅比平均值高两三倍,其他人的财力则高一二十倍,甚至更多”。在他看来,“归于最上层10%或1%人群的收入(或财富)比重才是判断一个社会有多不平等的有用指数,因为它不仅反映了极高的收入或极大财富的存在,也反映了获得这种报酬的人数”(38)。 这样,皮凯蒂笔下的当事人,就不是或不主要是“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更不是“地主”和“农民”,而是或主要是“穷人”和“富人”,即贫穷的人和富裕的人。上层阶层属于富人,下层阶层属于穷人,中产阶层则处于二者之间:相较于富人,他们属于穷人;相较于穷人,他们又属于富人。当然,还有其他的区分方法和名称。例如,最上层的1%被称为“统治阶层”,余下的9%则被称为“富裕阶层”或“小康阶层”;中产阶层有“世袭中产阶层”和“非世袭中产阶层”之分(39);在富人中,又有“小食利者”、“中等食利者”和“超级食利者”之别;还有一些人则被归入“高级管理层”、“超级经理人”(40)、“超级富豪”、“超级精英”和“超级明星”的行列(41)。 虽说社会之间是截然不同的,但皮凯蒂认为,上述统计概念“能让我们使用大家基本都能接受的共同语言,来比较那些原先无法比较的不平等现象”,或者说,它们使得“不同社会的定义方式完全相同”,这样就“可以跨越时空进行严格而客观的比较,既不否认每个特定社会的内在复杂性,也不排斥社会不平等结构的基本连续性”。例如不同的社会,“不管是1789年的法国(1%~2%的人口属于贵族)还是2011年的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将批评矛头对准最富裕的1%人口),最上层的1%都是一个庞大的人群,足以对社会面貌和政治经济秩序产生重大影响”。这也表明了为什么前10%和前1%的群体是重要而有趣的研究对象,因为,通过“认真考察这两个群体,评估流向两者的国民财富和收入比重”,就可以“去比较1789年的法国和2011年的美国社会不平等的区别”;由此,还能够确定是路易十六还是乔治·布什以及奥巴马治下的“1%”更有权势(42)。 问题是,上述统计概念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概念,皮凯蒂自己也承认这些名称“显然是相当主观的”(43)。拿“中层阶级”或“中间阶级”来说,马克思虽然早就注意到在一些国家中,“已经出现了财富和中间阶级迅速增长的情况”(44);但是他认为:“就中层阶级而言……在某种意义上是有道理的。但是这里所要谈的根本不是穷人和富人之间的这种无概念的关系,而是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45)用穷人和富人这样的概念,既无法说明同一社会形态中不同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例如雇佣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更无法说明不同社会形态中不同人的地位和身份方面的质的差异,例如作为富人的资本家、地主和奴隶主,作为穷人的雇佣工人、农民和奴隶的不同经济性质。实际上,以一定的收入为标准,对社会分层状况进行考察,这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表面的类比、计算和归纳,除了能够发现一些表面的现象特征和外部联系以外,它根本无法把握社会深层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联系。 特别是,任何统计概念和数学模型都无法说明:富人何以能致富?穷人何以会致穷?富人之富与穷人之穷有无联系?有什么联系?尽管皮凯蒂讲:“对于那些除了劳动力一无所有且生活拮据的人来说……他们很难接受资本的所有者——那些继承了至少一部分财富的人——能够占有这么多由他们的劳动创造的财富这一事实”。但是,这种分析逻辑在皮凯蒂那里既不鲜明也不坚定。例如,他认为“超级经理人”的崛起引发了劳动收入的不平等,同时又把超级经理人的富有归因于每个社会都有的“社会规范”,并认为“这些社会规范从何而来以及如何演变,这显然更多的是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和政治历史问题以及信仰和认知要研究的课题,而不单是经济学本身的问题”(46)。这样,皮凯蒂最终也没能讲清楚超级经理人的超高收入和富裕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不仅遮蔽了富人致富和穷人致穷的社会根源,而且遮蔽了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经济联系。但在马克思那里,问题的答案既简单又明了:富人如资本家的收入来源于对工人的“剥削”,资本家的富有与工人的贫穷构成一种因果关系。这些超级经理人是生产资料的实际控制者,因而是资本职能的实际执行人。同时,雇佣工人的贫穷具有其独特的历史规定性,它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者农民和奴隶的贫穷有着质的区别。因为,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的贫穷,是技术条件有限、生产力落后所致,而工人的贫穷则是生产力发展和技术进步所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越发展劳动者就越贫穷。同时,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的贫穷与自己的劳动不构成因果关系,而工人的贫穷恰恰是自己的劳动所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劳动的时间越长强度越大,他就越贫穷。 最后,皮凯蒂虽然区分了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并由此出发区分了不同的人,但是,由于对资本认识的浮泛,把资本等同于物,所以不仅混淆了不同性质的收入,而且混淆了不同性质的人。他所说的富人,在马克思笔下既可能是资本家,也可能不是资本家;而他所说的穷人,在马克思笔下既可能是雇佣工人,也可能不是雇佣工人。前者如作为富人,商人和餐馆老板是资本家,而医生、律师、大学教授和政府高官则既不是资本家,也不是雇佣工人(47);后者如作为穷人,农场工人和商店店员是工人,而家庭佣人、普通公务员和中小学教师则既不是工人,也不是资本家(48)。在皮凯蒂那里,以他人劳动为基础的大私有者,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小私有者,甚至普通住宅的拥有者,这些人充其量只具有一种“量”的差异,很难看出他们之间的“质”不同。他虽然认为一部分劳动者“一无所有”,但是,这与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的一无所有却相去甚远,后者指的是物质生产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马克思立足于生产领域、从“生产关系”出发划分人,而皮凯蒂则立足于流通领域、从分配关系和交换关系出发划分人。可以说,在对社会不平等的“量”的微观分析方面,皮凯蒂是颇有成效的,但是,在对社会不平等的“质”的宏观把握方面却难有马克思的理论深度和高度。 3.针对庸俗经济学的收入分配公式,马克思指出:“由每年新追加的劳动新加进的价值,——从而,年产品中体现这个价值并且能够从总收益中取出和分离出来的部分,——分成三个部分,它们采取三种不同的收入形式,这些形式表明,这个价值的一部分属于或归于劳动力的所有者,另一部分属于或归于资本的所有者,第三部分属于或归于地产的所有者。因此,这就是分配的关系或形式,因为它们表示出新生产的总价值在不同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中间进行分配的关系”(49)。可见,不同的收入形式,是对物质生产劳动者创造的总产品和总价值的分割和分配,因此,收入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分配关系,而分配关系的基础则是生产关系。马克思说:“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地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的人类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相互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这些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表现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分配关系本质上和这些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这些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和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地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50)就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而言,它根植于物质生产过程,首先是物质生产关系,其次才是分配关系或收入关系。不能把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割裂开来,撇开生产关系而抽象地谈论收入关系和分配关系。“把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看作不是同类的关系,这是荒谬的。例如,约·斯·穆勒和其他许多经济学家就是这样,他们把生产关系看作自然的、永恒的规律;而把分配关系看作是人为的、历史上产生的和受人类社会控制等等的关系”(51)。这一评价同样适合于皮凯蒂。 在马克思看来,正是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才产生了不同的阶级和阶级关系。雇佣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对立”,就产生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即“一方是生产条件的占有者,另一方是劳动的占有者”(52)。是什么形成阶级?或者说是什么使雇佣工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三大阶级的成员?“乍一看来,好像就是收入和收入源泉的同一性。正是这三大社会集团,其成员,形成这些集团的个人,分别靠工资、利润和地租来生活,也就是分别靠他们的劳动力、他们的资本和他们的土地所有权来生活。”而实际上,这充其量不过是基于劳动分工的“阶层分化”,而不是基于生产关系的“阶级分化”。因为,“从这个观点来看,例如,医生和官吏似乎也形成两个阶级,因为他们属于两个不同的社会集团,其中每个集团的成员的收入都来自同一源泉。对于社会分工在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中间造成的利益和地位的无止境的划分,——例如,土地所有者分成葡萄园所有者,耕地所有者,森林所有者,矿山所有者,渔场所有者,——似乎同样也可以这样说”(53)。因此,要认清阶级关系及其形成的根源,就不能停留于分配关系和收入关系的表层,而必须进到生产关系的深处。尽管皮凯蒂强调认识“阶级问题”即“社会阶级的结构”的重要性,认为“阶级斗争”或“阶级冲突”还没有让位于“代际斗争”或“代际冲突”(54),但是,他所谓的“阶级”,决不是基于物质生产关系的阶级关系,而是基于劳动分工和统计数据的阶层关系。藉此,能否进行严格而客观的科学分析不说,至少不同社会中“劳动者”(如农民和雇佣工人)和“剥削者”(如封建地主和资本家)的不同质的规定被取消了。 皮凯蒂所关注的是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之间的不平等,而资本的剥削性、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剥削关系则不在其视野中。马克思则认为,阶级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剥削关系和奴役关系。他说:“在现实的运动中,资本并不是在流通过程中,而只是在生产过程中,在剥削劳动力的过程中,才作为资本存在。”(55)“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转化同时表现为生产者的殉难史,劳动资料同时表现为奴役工人的手段、剥削工人的手段和使工人贫穷的手段,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同时表现为对工人个人的活力、自由和独立的有组织的压制。”作为生产关系,如果说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体私有制具有“排他性”,那么,资本主义私有制则不仅具有排他性而且具有“对抗性”。在个体私有制中,要占有他人的东西,就必须让渡自己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排他”,它所体现的是个体私有者之间平等交换劳动的关系。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中,资本家不通过交换就占有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在自己致富的同时把他人推向贫困的境地,从而使劳动之穷与资本之富互为因果。这就是所谓的“对抗”,它所体现的则是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不平等交换的关系。马克思说:“工厂主的财富如何随着劳动力剥削的加强而增加,单是下面这个事实就可以证明:英国棉纺织等等工厂的平均增长额,从1838年到1850年间是每年32个,而在1850年到1856年间是每年86个。”(56)皮凯蒂既看不到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更无法理解阶级剥削所反映的生产关系的对抗性。他抽象地谈论财富,永远也无法理解资本主义财富的本质,即“这是始终以贫穷为前提、并且只有靠发展贫穷才能使自己得以发展的财富”(57)。 4.从方法论来看,马克思对当事人的考察,分别在本质抽象和现象具体两个层面展开。单从现象具体层面的局部状况和个别情况来看,人们的社会身份及其相互关系不仅多样而且多变,充满了随机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静态观之,一个自然人可以是资本家,同时是劳动者,即兼具资本家和劳动者的身份。在谈到管理劳动和监督劳动时,马克思认为:“一部分管理劳动只是由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敌对状态、由资本主义生产的对抗性质引起的”,这种劳动实际上是一种“非劳动”,由此得到的收入是剥削收入而非劳动收入,其执行者是资本家而非劳动者。同时,一部分管理劳动“不是剥削他人劳动的职能的名称”,这种劳动是由协作、分工等技术的(而非权力的)社会关系引起的,它同资本完全无关,因而“这种劳动并不随着资本的消失而自行消失”(58)。由此得到的收入是真正的劳动收入,其执行者是劳动者而非资本家。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说:“资本家可能担任的‘监督劳动’归入工资之内。从这方面看,资本家是雇佣工人,即使不是别的资本家的雇佣工人,也是他自己的资本的雇佣工人”(59)。这种情况在“小资本家”那里最具代表性,因为,由于“一般说来,资本家的劳动和他的资本量成反比,就是说,和他成为资本家的程度成反比”,所以“小资本家还有较多的自己的劳动”(60)。马克思把这些小资本家叫做“半资本家”(61)。 动态观之,资本家可以变为劳动者,劳动者也可以变为资本家。例如,“如果过去占有劳动条件、并用这些条件劳动的那部分人,——如独立的手工业者、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以及小资本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作用而丧失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对它们的所有权),那么,他们就可能变为雇佣工人”(62)。小资本家最易沦为雇佣工人。反之,“有的工人可以指望有朝一日也能剥削工人”,从而成为资本家(63)。例如,“个别工人有较多的机会例外地进行相当的储蓄,并且依靠特别幸运的情况使自己成为……资本家”(64)。 但是,从本质抽象层面的整体特征和总的趋势来看,人们的社会身份及其相互关系又是非常明显、非常确定的。静态观之,对那些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来说,他固然会参加劳动,但也可以不参加劳动,而且,由于“剩余价值……表现为整个生产过程的目的并决定着这个过程的性质”(65),所以他必须生产剩余价值,为此,又必须与工人建立雇佣劳动关系,或者必须去剥削他人的劳动。否则,就不成其为资本家,就不存在资本家阶级。同时,“只有当一定数量的人丧失对劳动条件——首先是土地——的所有权,并且除了自己的劳动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出卖的时候”,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作为阶级,从而资本和雇佣劳动作为阶级关系才会出现(66)。试想,如果社会上的大多数劳动者可以不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可以不去受雇于资本,就不会有雇佣工人阶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会丧失其存在基础。因为,“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67),“没有雇佣劳动的资本家,是荒谬的”(68)。 动态观之,雇佣劳动与资本家的阶级分化,就形成并存在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常趋势和发展规律,是使生产资料越来越同劳动分离,使分散的生产资料越来越大量积聚在一起,从而,使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使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69)。一个人的资本量越大,就越是靠近资本家的概念;反之,就越是远离资本家的概念。马克思说:“产业资本家取得的‘工资’和资本的量成反比:资本小的时候,它就大(因为在这里资本家是介于他人劳动的剥削者和靠自己劳动生活的劳动者之间的中间人物),资本大的时候,它就很微小,或者像在有经理的情况下,它就完全和利润分离。”(70)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恰恰是,资本家与劳动者、从而利润与工资最终会彻底分离开来。在存在领取工资的经理的情况下,就是如此。从总的趋势看,工人阶级的工资收入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工资收入过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就难以充当雇佣工人;反之,工资收入过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就可以不去当雇佣工人。例如,“在资本的统治地位或者资本主义生产基础还没有充分发展的殖民地,工人得到的东西多于再生产他的劳动能力所需要的东西,于是他很快就能成为自耕农等等;因此[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最初关系在那里并没有不断地再生产出来”(71)。 皮凯蒂详细考察了个体层面的分配状况,说明了现象具体层面的分配关系及其多样性和复杂性。例如他提醒人们:“要记得,所谓的‘资本收入’,其中有一部分可能是‘企业家’的劳动收入,而这部分的‘劳动’无疑应该与其他形式的劳动同等对待”(72)。这与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家管理劳动的二重性是一致的。同时,皮凯蒂也非常重视对分配关系的整体状况和长期趋势的考察。例如,他采用“长期视角”,“既考察了国家层面资本/收入比的动态变化,也考察了国民收入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整体分配情况”,并且概括出了像“资本导致的不平等总比劳动导致的不平等更严重,资本所有权(及资本收入)的分配总比劳动收入的分配更为集中”这样的分配规律(73)。但是,由于他没能深入到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的本质抽象的层面,所以,在方法论上始终未能跳出个人主义的窠臼,当事人始终是一些“原子式”的个人。由于把“物”从生产关系中分离出来,把“人”从阶级关系中分离出来,孤立、抽象地理解人的社会性质和物的经济性质,所以,其分析难以揭示社会的阶级关系和剥削关系及其对抗性,也难以揭示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关系和剥削关系及其对抗性。而且,由于把资本与物混为一谈,把一些非劳动看成是劳动,把一些剥削收入看成是劳动收入,所以,其结论在客观上起了抹煞阶级矛盾、掩盖资本剥削的作用。而在马克思那里,由于生产关系“始终是作为整体来看的生产中的个人的社会关系”(74),所以,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关系是一种“整体关系”而不是“个别关系”,是一种“总的趋势”而不是“片断特征”。以此来看雇佣工人及其货币收入,不管他拥有什么样的财产——房子、储蓄,甚至是自驾上班的小车,只要他“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那就是劳动者,其收入——无论是劳动报酬,还是存款利息和房屋租金,就都不过是取得劳动收入的不同社会形式,因而与资本家阶级的资本收入有质的区别。对此,皮凯蒂或许是永远也无法理解的! 三、资本主义向何处去? 1.皮凯蒂并不赞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悲观结论。在他看来:“马克思的理论实际上建立在长期生产率增长为零的严格假设之上”。这是资本家越来越多地积累资本“这一无限欲望的最终结果”,并且“将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对于自己的结论,皮凯蒂认为并“不如马克思的无限积累原则和永恒分化原则所暗示的那样具有灾难性”。因为,在他采用的模型中,“财富分化不是永恒的,只是未来几种财富分配可能走向中的一种”(75)。作为“‘资产阶级自掘坟墓’的核心机制”,马克思的无限积累原则表明:“资本家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资本,最终必然导致利润率(即资本收益率)下降和自身的灭亡”。但实际上,从18世纪到21世纪,英法两国的“资本纯收益率一直围绕每年4%~5%这个中心值上下浮动,或者说大体在每年3%~6%这个区间内波动,其中没有明显的长期向上或向下趋势”。问题是:由于彼此对资本、资本积累、资本收益率等概念的理解不同,所以,皮凯蒂对马克思理论的评判并不具备起码的前提条件。例如,他认为在未来几十年,资本收益率因“更加复杂和多样的证券投资产品”而有可能“回归高水平”(76)。而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证券投资属于投机行为,不仅不会提振资本的利润率,恰恰相反,它会进一步拉低这一比率,因为证券投资并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而只会改变剩余价值的分配格局(77)。 同时,皮凯蒂也反对库兹涅茨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乐观主张。他认为:“从19世纪李嘉图和马克思的经典理论到20世纪西蒙·库兹涅茨的研究分析”,可以说,“经济学家已经从对末日预言的过度阐述逐渐转变为对理想主义或者至少是对圆满结局的过度偏好”。在库兹涅茨那里,“不管经济政策如何选择或者不同国家间的其他差异,收入不平等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自动降低,并最终稳定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上”(78)。现实情况却是:当下“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尤其是在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最富裕的10%人群占有国民财富的约60%”。而最令人惊讶的事实无疑是:“在所有这些社会里,半数人口几乎一无所有:最贫穷的50%人群占有的国民财富一律低于10%,一般不超过5%”。“当今社会的不平等正达到新的历史高度。……这种不公平不再是一部分上层社会对比大众,而是一种渗入各人口阶层的普遍的不公平”。因此,在皮凯蒂看来,“现代经济增长与信息传播虽然规避了马克思理论演进结果的发生,但是并未改变资本深层结构与社会不平等的现实”,至少不像“二战”之后十年中一些乐观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尽如人意(79)。 对此种渗透到各个阶层中的普遍的不平等,皮凯蒂发现了以下规律:“劳动方面的不平等一般较为轻微或者比较适度,甚至是合情合理的”。这一点当然不应被夸大,在一定限度之内这种不平等才是合理的。相比之下,“资本方面的不平等则总是很极端”,“资本导致的不平等总比劳动导致的不平等更严重”,反之,“劳动方面的不平等总是比资本方面的不平等小得多”(80)。因为,“资本所有权(及资本收入)的分配总比劳动收入的分配更为集中”,这使得“资本所有权分配……在哪里都是极端不平等的”,或者说,“财富的不平等,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本收入之间的不平等,事实上比劳动收入的不平等要大得多”(81)。而“总收入不平等的水平居于劳动收入不平等和资本收入不平等之间”,而且,由于“劳动收入一般占国民总收入的2/3~3/4”,所以,“总收入不平等更接近劳动收入不平等而不是资本收入不平等”。试想,“如果资本所有权是平均分配的,并且每一个工人在自身工资的基础上还获得相同的利润份额”,有谁“会在意收入在利润和工资之间的划分”呢?因此,在现实中收入不平等造成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而“劳资之间的分立造成了诸多冲突,首要原因是资本所有权的高度集中”(82)。这样,皮凯蒂就将矛头直接指向了资本所有权。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循此思路,继续对资本所有权本身进行深度挖掘,而是认为,尽管说“在动态过程中,资本经营具有极高的收益这一事实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资本集中度之所以非常高,主要原因是继承财产的重要性及其累积效应:例如,如果你继承了一套公寓并因此节省了房租费用,你将更容易通过储蓄积累财富”(83)。在此,皮凯蒂将分析重心转移到“财产继承”上,而不是像马克思那样,把对资本收益率和资本集中度同劳动者受剥削的程度联系起来进行剖析。 所谓“继承财产”,指的是继承、馈赠和储蓄等财产转移和货币积累行为,皮凯蒂认为这是资本积累的重要方式,因而同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资本化的积累概念有重大差别。与继承财产的累积效应相联系,皮凯蒂认为,拥有资本越多的人,就越是不需要劳动;反之,拥有资本越少的人,就越是不得不劳动。结果势必是:有一些人蜕变为“食利者”,即完全脱离劳动、“靠收取租金过活的人”,而“租金是指某笔资本所产生的年度收入……如今由资产产生的租金通常就是指资本回报,无论其形式是租金、利息、股息、利润、版税还是其他法律规定的收入形式,只要其本质是无须通过劳动而是通过对某资产所有权获得的收入”(84)。与此同时,有一些人必然是“一无所有”,即几乎没有任何资本。最下层50%的穷人就是如此,其净财富或净资本为负数,或零,表现在他们没有什么财富留下来给子孙。皮凯蒂把这样一种社会叫做“食利者社会”或“超级世袭社会”,并认为在其中“总收入层级由非常高的资本收入主导,尤其是继承资本”,因此“继承财富非常重要,财富集中度达到极端水平”,即“最上层10%人群一般占有全部财富的90%,仅最上层1%就占有50%”(85)。从现实情况来看,“世事轮转,继承财富在当今世界再次崛起,尤其是在2010年以来的法国。……对那些出生在1970年之后的人而言,继承财富将占其一生财富资源(包括来自继承和劳动)的1/4。因此如果看总额,继承财富对现代人的重要性已经接近对19世纪出生的人群”。虽然与19世纪相比,财富的集中度在当今社会因“高级管理层”的兴起、财富与收入间的联系加强而大大降低,但这只是继承财富的分布产生了变化,而继承并没有终结,“我们的社会从数量稀少的庞大食利者变成了数量众多的小型食利者,即由小型食利者组成的社会”。放眼全球,“继承财富占全球总财富的一半以上。目前可接受的先验假设是,继承财富应占全球财富总额的60%~70%”(86)。 皮凯蒂所担心的,正是这种“食利者社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回归或复辟。作为资本主义的一种存在形式,他把这种食利者社会叫做“承袭制资本主义”,在其全球性存在的意义上则叫做“全球承袭制资本主义”(the globalized patrimonial capitalism)。可见,尽管皮凯蒂一再拒斥任何历史必然性论断和对历史走向的预测:“收入和财富的历史总是非常政治化的、无规律的,而且是不可预测的。历史会怎么演变取决于社会如何看待不平等,以及采取怎样的政策和制度去衡量和改变不平等。没有人能够预见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事情会怎样变化,但是历史的经验是有益的,因为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在下一个世纪里我们将要面临何种选择以及哪种动态变化会起作用”(87)。这表达了他与马克思主义者的不同。但是,皮凯蒂还是在承认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严重不平等事实的基础上,确认了承袭制资本主义回归的历史可能性。这表达了他与库兹涅茨等自由主义者的区别。 2.马克思并不否认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种种不平等现象,例如,“遗产继承以及使由此引起的不平等永久化”(88)。但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论断赖以建立的基础,并非任何意义上的不平等(包括资本剥削所引起的不平等)和道德缺陷(对资本主义的谴责是一种苍白无力的道德说教),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及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独特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这种[矛盾的]发展是由生产力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决定的,也是由生产力实现这种发展的方式决定的。”(89) 具体而言,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了其生产目的是也只能是实现“价值增殖”,即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创造,而工人剩余劳动或剩余劳动时间的存在则是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的必要前提;另一方面,受超额利润或超额剩余价值的驱使,每一单个资本家或资本主义企业都竞相提高自己的“个别生产力”,其结果便是形成“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的总的趋势。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则意味着,物质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越来越少,这势必会限制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的利润空间。资本有机构成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提高,从而促使资本的平均利润率在总体上趋向下降,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集中体现。 虽然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意味着,生产一定量满足社会需要的物质产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断减少,由此会造成工人劳动力商品价值的不断减少和对工人剥削率的不断提高,进而会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平均利润率下降,但是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这一下降趋势。原因在于,资本家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把全部剩余价值都用于生活消费,而是会把其中一部分拿出来投入生产,即进行资本积累。这固然会使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使剩余价值和利润总量不断增加,但与此相应的却是:其一,生产规模的扩大抬高了投资门槛,那些再生产难以为继的中小企业会被排挤出来,将资本投向非物质生产领域,其中大多数是用于投机。这些资本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同时又要分割剩余价值,由此会拉低资本的平均利润率。特别是,其二,雇佣工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及其货币表现即工资被限制在一定的水平上,致使社会有效需求相对不足,剩余价值即使能够顺利地生产出来,也无法通过商品交换得以实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一定点上会引发严重经济危机,而在危机期间,资本不仅得不到剩余价值和利润,连资本本身的价值都会因破产而损失掉,这势必会造成资本平均利润率更大程度的下降。 这就表明:“资本本身在其历史发展中所造成的生产力的发展,在达到一定点以后,就会不是造成而是消除资本的自行增殖。”“超过一定点,生产力的发展就变成对资本的一种限制;因此,超过一定点,资本关系就变成对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一种限制。一旦达到这一点,资本即雇佣劳动就同社会财富和生产力的发展发生像行会制度、农奴制、奴隶制同这种发展所发生的同样的关系,就必然会作为桎梏被摆脱掉。”(90)概言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终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正是生产力的发展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送上历史断头台。 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增长趋势,或者说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性,实质上就是指对剩余价值这种“抽象财富”的无止境追求,就是指资本主义剥削的无限性。这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现象,因为“很明显,如果在一个经济的社会形态中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剩余劳动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围的限制,而生产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造成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91)。如果物质生产的目的是使用价值,基础和手段是自己的劳动,需求就是有限的,物质生产就是有限的;相反,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剩余价值,基础和手段则是他人的劳动,需求自然是无限的,物质生产自然是无限的。 由此可见,皮凯蒂完全错误地理解了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和生产增长理论,而且造成资本主义灭亡的与其说是资本积累的无限性(92),毋宁说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工人作为商品的买者,对于市场来说是重要的。但是作为他们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是把它的价格限制在最低限度。”(93)当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还可以有其他表现形式,例如,人与物的颠倒。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价值增值是生产的目的,工人则沦为手段和工具。相应地,其工资被归入生产过程的“成本项”因而受到最大程度的限制。与此不同,“如果工人不是工人,而是从事劳动的所有者,那么,在工人看来,在产品完成以前他所消耗的生活资料不是这个意义上的生产费用,因为,相反地,在他看来,整个生产过程只是生产他的生活资料的手段”(94)。 3.皮凯蒂的批判锋芒所指向的,是收入分配关系的不平等,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他说:“我一向对‘反资本主义’那些传统而粗糙的论调免疫,有些论调直接忽略了共产主义运动在历史上的失败,很多则与超越它所必需的理性手段背道而驰。我没有兴趣去谴责不平等和资本主义本身——特别是,只要是合乎情理的,社会不平等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就不平等而言,皮凯蒂所批判的,也只是特定意义上的不平等,而不是不平等本身。在他看来,“不平等本身未必是坏事,关键问题是判断它是否为正当的,是否有存在的理由”。因此,“重要问题是不平等的合理性而不是程度”(95)。历史地看,在“‘二战’之后的几十年里,继承来的财富不再重要,并且也许是历史上第一次,工作和学习成为出人头地的最可靠路径”,自此,“源于个人天赋和勤奋的不平等”被认为“比其他不平等更合乎情理”,从而奠定了“现代民主的基础”。从其阶级立场看,皮凯蒂公开声明自己“并不是要为工人反对所有者的例子辩护,而是想尽可能对现实有一个清晰的观察”(96)。 皮凯蒂认为,承袭制资本主义及其极端的不平等,严重威胁着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很明显,“在所有文明中,资本所有者不用劳动就可以获取国民收入的一个可观份额,资本收益率每年通常在4%~5%这一事实都会激起激烈的(常常是愤怒的)抵制”。“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的不平等问题会引起强烈的情绪……因此对于时而由此引发的肢体冲突事件,我们几乎不感到惊讶”,因为,“对于那些除了劳动力一无所有且生活拮据的人来说……他们很难接受资本的所有者——那些继承了至少一部分财富的人——能够占有这么多由他们的劳动创造的财富这一事实”(97)。同时,皮凯蒂认为“食利者”是“民主之敌”,承袭制资本主义与所谓“民主社会”的世界观是背道而驰的。因为,“民主社会的根基在于崇尚奋斗的世界观,或至少是通过奋斗而实现价值的信念,即社会普遍认为,财富不均等更多的是由能力和努力程度决定而不是遗产和租金。这种信念和希望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原因很简单:在民主体制中,全体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权利与实际生活条件的不平等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要想克服这对矛盾,社会的不公平就必须是由理性和普世真理造成而不是强制偶然性因素。因此不平等必须符合正义,而且对人人有用,至少从道理上说是如此并且在现实中要能尽量实现”。承袭制资本主义“与我们关于什么是公正、什么是不公正的普遍认识是冲突的”,它“可能有违现代民主社会最为根本的精英价值观和社会公正原则”。因为,由于“资本收益率是不可预测的,财富可以以多种方式增加”,所以这就“构成了对传统精英模式的挑战”。例如,“当一个人初始资本禀赋更高时,平均实际资本收益率可能就会更高”。这已经是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现象(98)。 可见,皮凯蒂所批判的,并不是资本主义本身,而是作为其独特形式的“承袭制资本主义”。在其中,经过资本的不断自我复制和加速积累,不仅“每个创业者最终都会变成食利者”,而且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他们的“子女成为食利者”,由此会引发严重的不平等,进而威胁资本主义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99)。皮凯蒂所批判的,是“承袭制资本主义”而不是“剥削制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食利性”,而不是其“剥削性”。问题是,与“消费”一样,“承袭”并不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当上升的资本主义社会本身还没有学会把剥削和消费结合起来,还没有使享用的财富从属于自己时,享用的财富对它来说,是一种过度的奢侈”(100)。钱决不会自动生钱;没有资本主义的剥削,任何食利者都会失去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没有剥削制资本主义,就没有承袭制资本主义。同时,只要有资本主义剥削,就必然会出现食利者;只要有剥削制资本主义,就必然会有承袭制资本主义。当然,剥削者并不都是食利者,而食利者一定是剥削者而不是劳动者。由此想到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评:“只听钟声响不知钟声何处来”(101),皮凯蒂的观点与蒲鲁东何其相似!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现实,却无力看清造成这种不平等的历史动因和社会根源。 从其理论主旨看,皮凯蒂表示,他“更热衷于讨论组建社会的最优方式,以及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秩序所需要的最合适的制度和政策”。此外,他“希望看到在法律框架下实现有效而高效的公平正义,法律应该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并且是通过民主辩论而形成的大众都能理解的法规”(102)。这种以民主辩论为基础、以法律为框架、以消除社会不平等为目标的制度和政策究竟是什么呢? 第一,皮凯蒂认为:要管理21世纪的全球承袭制资本主义,最理想的政策和工具就是“全球范围内的累进资本税”。在他看来,资本累进税“是一种新的思路,是明确为21世纪全球化承袭制资本主义所设计的”(103)。作为一种“对全球财富的年度累进税”,资本税可以规定:“最大的财富将被征收更重的税,并且所有形式的资产都将被包括在内:不动产、金融资产和商业资产——没有例外”。与20世纪的收入累进税不同,资本累进税可以防止贫富差距无限拉大,“避免无休止的不平等的螺旋上升,并且能够控制令人担忧的全球资本集中”,从而重新实现对财富积累的控制(104)。全球资本税的优点和好处在于:它“既能保持经济的开放性,又能有效规范全球经济,并且公平地在国家之间以及一国之内分配利益”;它“让财富置于民主监督之下,这对于有效监管银行体系和全球资本流动也是必要条件”;它“有助于让公共利益超越私人利益,同时又可保持经济的开放度和自由竞争”(105)。历史地看,“累进税”(包括“累进所得税”和“累进遗产税”)是20世纪财政和税收方面的重大创新。特别是有证据表明,“对超高收入和巨大财产课以累进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自1914~1945的冲击后,财富集中程度从未达到‘美好年代’时期的水平。相反,自1980年以来,美国和英国收入累进税的大幅下降(即便两国都曾经是‘二战’后累进税的引领者),也许能够解释超高水平收入的增加”(106)。 第二,皮凯蒂进而提出一种设想,即“我们是否可以设计出某种政治体系,对如今的全球化承袭制资本主义进行公平和有效的制约?”这种政治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建设“社会国家”(social state)。简言之,就是要“加大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充分发挥国家和政府在推行全球累进资本税、调节收入分配关系中的作用。过去,“政府只能履行基本的‘王权’职能(警察、法庭、军队、外交以及一般管理等),而不能介入太多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与此不同,“政府在‘二战’后的几十年内形成了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核心作用”,近几十年来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更是“发挥着空前大的作用”,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越来越强(107)。所谓的“社会国家”,指的就是承担着更多经济社会职能的国家。这些职能尽管因“过于复杂而难以让公众理解”,但“财税和转移支付体系”则是其中的核心。在目前情况下,皮凯蒂认为社会国家的规模急剧扩张既不可行也不可取,但若没有社会国家的作用,征收累进资本税这种“现代化财富再分配机制”就难以想象(108)。 第三,皮凯蒂认为:“如果只能在某些国家或针对某些机构实行资本税,那么效果可能就不会那么明显”,因为,富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把资本转移到国外,进入那些所谓的“避税天堂”(109)。因此,征收累进资本税,是一项“全球性”的任务,“需要高水平的国际协作”。而困难也恰恰就在于此,“一项真正的全球范围内的资本税无疑是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因为,“这对早些时候社会就已达成妥协的民族国家而言很难实现”。有鉴于此,皮凯蒂又提出:“如果最理想的政策无法实现,那么可能也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如果这样的理想化状态无法达到,那么不妨尝试地区性或在某个大洲实行资本税,尤其是在欧洲,这项政策可以从愿意实行的国家开始”。在此意义上,皮凯蒂相信“只有区域政治一体化可以实现对21世纪全球承袭制资本主义的有效管理”(110)。问题是,哪个大洲或哪些国家愿意实行呢?而且,这是一个主观上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吗? 第四,皮凯蒂认为:“如果我们想要重新控制资本主义,就必须把赌注都压到民主上——在欧洲,是欧洲范围的民主。”这就是所谓“资本的民主控制”问题。为实现之,“未来数年最重要的事情”,也是“21世纪的主要挑战之一”,就是“在民族国家的平台上”,发展“新的所有权形式”,即“介于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的共享产权”。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已经有很多领域,比如教育、医疗、文化和媒体,其主导的组织和所有权形式”既不是“极端的纯粹私人资本(参照完全为股东所有的股份公司)”,也不是“纯粹的公共资本(基于相似的自上而下逻辑,主权政府决定所有资产)”,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的”所有权形式(111)。同时,“没有真正的会计和财务的透明度和信息共享,就不可能有经济民主”。各种“不同形式的、资本的民主控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个相关个体获取经济信息的可能性”。因此,实现对资本的民主控制,还需要配合非常高度的“经济和金融透明度”。在这方面,“重要的不是有关个人收入和财富的透明度”,而是“私人公司(还有政府机构)”公布详细账目和会计信息,以便保证工人及其代表在参与企业投资决策时,对经济现实有足够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形成关于公司决策的意见”,从而实现民主参与和民主干预(112)。 虽然说,皮凯蒂触及到了所有制问题,而且对公有制的一些看法也难能可贵;但总体而言,他所提出的是一种收入分配关系层面的变革主张。把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即“把分配问题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这是其明确的理论诉求。他的一些政策建议——例如可能的资本累进税安排:“100万欧元以下的财富税率为0.1%或0.5%,100万到500万欧元之间为1%,500万到1000万欧元之间为2%,几千万或数十亿欧元的税率高达5%或10%”——尽管极为细致,但目标也仅限于“遏制全球财富不平等的无限扩大”和防止继承财富基础上的“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回归”,而不是消除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对这条改良路线的可行性和现实效力,连皮凯蒂自己都缺乏自信:“全球累进资本税……这类制度和政策的设立在相当大程度上需要密切的国际协作。不幸的是,针对这一问题的实际回应(包括各国自身的回应)在实践中并不那么乐观”(113)。 4.马克思并不一概否定国家和法律的作用,例如,“为了‘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国家法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的契约而把自己和后代卖出去送死和受奴役”(114)。同时,马克思也不会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环境而抽象地看待国家和法律的作用,例如,“英国的工厂法是通过国家,而且是通过资本家和地主统治的国家所实行的对工作日的强制的限制,来节制资本无限度地榨取劳动力的渴望”。对其历史动因,马克思认为:“即使撇开一天比一天更带威胁性地高涨着的工人运动不说,也有必要对工厂劳动强制地进行限制,正像有必要用海鸟粪对英国田地施肥一样。同是盲目的掠夺欲,在后一种情况下使地力枯竭,而在前一种情况下使国家的生命力遭到根本的摧残。英国的周期复发的流行病和德法两国士兵身长的降低,都同样明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其实,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有哪一条法律是单纯通过民主辩论而来的呢?就是正常工作日的规定,也“是几个世纪以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斗争的结果”(115)。 既然说,生产关系是分配关系的基础,分配关系不过是生产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那么,收入不平等和分配问题就不能通过分配关系本身加以解决。马克思指出:“那些把生产当作永恒真理来论述而把历史限制在分配范围之内的经济学家是多么荒诞无稽。”(116)例如,“西斯蒙第……企图通过别的调节收入和资本、分配和生产之间的关系的办法来缓和矛盾,而不理解分配关系只不过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生产关系”(117)。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话说,这是在“围绕着分配兜圈子”(118)。今天的皮凯蒂也是这样,不反思物质生产和生产关系,只是把注意力放在分配关系的调整和变革上,似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是从来就不需要追究的永恒真理。而实际上,正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收入的极端不平等和两极分化的必然性;要消除之,就必须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否则,就只能流于幻想和空想。 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马克思指出:“这些矛盾会导致爆发,灾变,危机,这时,劳动暂时中断,很大一部分资本被消灭,这样就以暴力方式使资本回复到它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生产力而不致自杀的水平。但是,这些定期发生的灾难会导致灾难在更高的程度上重复发生,而最终导致用暴力推翻资本”(119)。这里,前一种“暴力”指的是经济危机,它以暴力的方式强制回复各种必要的比例关系;后一种“暴力”则是指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革命的必然性就在于,面对与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本质性关联的各种全局性和全球性问题,诸如经济危机、贫富分化、军事冲突、环境恶化等,人类假如不想灭亡的话,就“必须”也“必然”会选择新的生产方式。在此问题上,如果说皮凯蒂所做的“统计学”分析,只是看到了社会革命爆发的现象特点,即“如果最上层10%人群占有年产出的90%(和财富分配情形一样,最上层1%占有50%),就可能发生革命,除非有特别有效的压制手段阻止它发生”(120);那么,马克思则揭示了社会革命爆发的经济根源和阶级根源。 从现实进程来看,累进所得税制度在资本主义从古典形态向当代形态演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所谓“后革命时代”,确实收到了缓和阶级矛盾的功效,甚至可以说,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无奈之举”,它是对资本本性的一种“事后扬弃”。但是,它能否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呢?又能否消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呢?它能否有效解决各种文明病症和全球性问题呢?这些都有待现实和历史的检验。因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无非就是实现劳动者当家做主,其实质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使生产力“归人民所有”(121)。问题是,只要存在着对抗性的生产关系,就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就存在着剥削、压迫和社会不平等。“一方面要保留现存的阶级,另一方面又要使这些阶级的成员平等”,这是一种不可容忍的荒谬见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即使怀着最良好的愿望,甚至在他们好像已经掌握真理的时候,也是本能地沿着错误道路走的”(122)。这一评价完全可以用在皮凯蒂身上。如果说,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旨在通过历史统计数据向资本主义发出警告,那么,马克思的《资本论》则志在通过革命实践向资本主义发起冲锋!这就是二者的根本区别! 注释: ①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46页。 ②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4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251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1页。 ⑤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47页。 ⑥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70页。 ⑦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48、47页。 ⑧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48页。 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0页。 ⑩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5页。 (1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3、718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 (1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8、209页。 (14)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48~49页。 (15)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49~50、70页。 (16)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47、567、568页。 (17)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47~48、586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8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3、214页。 (20)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47、42、10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3、251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181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175~176页。 (2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8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26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页。 (28)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249、128页。 (2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09、878页。 (30)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46、18~19、51页。 (31)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54、209页。 (3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25~926页。 (33)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246页。 (3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31页。 (35)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 (36)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48页。 (37)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258页。 (38)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256、257页。 (39)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256~257、355、311页。 (40)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388、340页。 (41)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257、268页。 (42)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256、258页。 (43)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255页。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1、345页。 (46)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41、311、340~341页。 (47)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208、284~285页。 (48)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284~285、290页。 (4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93页。 (5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99~1000、994,998页。 (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1~182页。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页。 (5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2页。 (54)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33~34、250、23页。 (5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84页。 (5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79、478页。 (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7页。 (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65、357页。 (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页。 (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95页。 (6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3、507页。 (6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3页。 (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8页。 (6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3页。 (6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1页。 (6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 (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1页。 (6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5页。 (6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1页。 (7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64~365页。 (7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页。 (72)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41页。 (73)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249、241、248页。 (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页。 (75)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28、582页。 (76)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231、210页。 (7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65页。 (78)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11页。 (79)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261、434~435、1~2页。 (80)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248、259页。 (81)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248、261、40页。 (82)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266~267、40页。 (83)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250页。 (84)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438~439、387、435~436页。 (85)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264~265、352、268页。 (86)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431、433、457页。 (87)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485、531、36页。 (8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页。 (8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01页。 (9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页。 (9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页。 (92)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28页。 (93)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50页。 (9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页。 (95)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32、20、268页。 (96)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246、245、40页。 (97)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547、40~41页。 (98)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435、40、28页。 (99)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406、269页。 (10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9页。 (10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8页。 (102)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32页。 (103)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531、485、548页。 (104)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533、488、531页。 (105)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532、485~486页。 (106)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507、510页。 (107)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485、491、488~489页。 (108)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491、488、495~496页。 (109)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486、571、538页。 (110)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591、486页。 (111)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591、586~587页。 (112)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587、531页。 (113)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16、590~591、28页。 (11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9页。 (11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6~277、312页。 (1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页。 (1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7页。 (1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页。 (1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0页。 (120)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267页。 (1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1页。 (122)《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09、333页。标签:人力资本论文; 21世纪资本论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论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商品价值论文; 社会资本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产品概念论文; 人力资本理论论文; 社会财富论文; 投资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