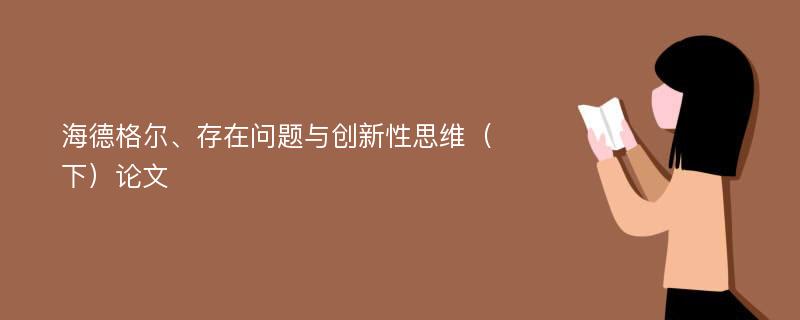
海德格尔、存在问题与创新性思维(下)
王庆节
(续上篇,上篇发表于本刊2019年第1期第49页)
十、海德格尔:搅局者式的哲学家还是新时代的先知?
说到这里,我们就回到了开始时提到的问题,即如何来看待海德格尔关于“存在问题”的思考和发问?在我看来,海德格尔实际上是对存在的意义问题给出了一个了不起的揭示,他不仅仅是一个来搅局的哲学家,而且更像是一个新时代的思想先知。他在将近100年前就预告了我们这个以电脑网路的“虚拟实在”为起点的新时代的到来。
英国有一位哲学家,也是治思想史的大家,名叫以赛亚·柏林,他曾经有过一个非常有名的说法。他讲历史上的哲学家分为两类,一类叫“刺猬型”的哲学家,一类叫“狐狸型”的哲学家。狐狸型的哲学家思想非常灵活,经常变换研究的主题,从一个问题跳到另一个问题。刺猬型的哲学家则不然,一生一世,只研究一个问题,锲而不舍,从不动摇。按照这个说法,海德格尔当然是一位“刺猬型的哲学家”。柏林的这个分类方式明显是从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的角度,但若从哲学和思想研究的意义来说,我更愿将历史上的大哲学家们分为另外的两类。一类是代表着一个时代思想或时代精神的巅峰,因而也是“总结型”的哲学家。 这类哲学家的工作是要说明这个时代的基本精神是“如何可能”以及“如何正当”的,他们的思想是为他们所处的那一整个时代奠基的,譬如康德哲学之于我们的这个“科学时代”以及托马斯阿奎那哲学之于中世纪的“基督教时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则属于古代思想的巅峰。另一类的哲学家则是哲学史上的“异类”或者“异端”。他们生来的任务就是“搅局”或者“解构”,是对现存的体系和其赖以为基的和不为人知的前提提出根本性的疑问,所以也最具有挑战性和批判性。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生不逢时,以失败告终。只有极少的几位,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世界观或新的哲学的开启者,成为未来“主流”的开端和“先知”, 譬如笛卡尔的哲学。我们知道,笛卡尔是现代哲学的开创者,但笛卡尔在他那个时代被认为 是异端,他处在中世纪和现代之间,对于中世纪时代来说,他是一个异端和破坏者,是一个搅局者,但对于科学时代而言,它是一位开局者,先知先觉和先行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也会说,海德格尔对存在意义的发问也让他不仅成为旧时代的搅局者,更成为未来或正在到来的新时代的先知。
海德格尔有位学生,也是当代德国哲学中的一位响当当的人物,叫卡尔·洛维斯,他在20世纪60年代出过一本关于海德格尔的书, 书名就叫《海德格尔:一个匮乏时代的思想家》。[1]按照传统的理解,我们当今的时代是科学昌明,文化发达,物质富足的时代。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无法和之比较,怎么在哲学家的眼中成了“匮乏时代”?海德格尔的另一位著名的学生是德国当代哲学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军人物。他叫马尔库塞,他的名著《单向度的人》[2]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因为这本书,马尔库塞和法国的萨特并列,成为20世纪中叶席卷欧美的年轻人思想解放和社会反抗浪潮的精神导师。无论洛维斯还是马尔库塞,他们所描述的真实反映了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生存匮乏和异化的现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会说,海德格尔就是我们这个“科学主义”时代的批判哲学家,他实际上要反对或者要批判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时代,因为这个时代的本质就在于把所有的“存在”变成科技主义的“单维度的存在物”,把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
海德格尔写《存在与时间》,他的整个思路实际上就是想回到这个世界的原本根基、回到存在的根基处去,重新出发去思考,去发问存在意义的问题。我们前面讲过存在本身与现实的区别,发问这个存在本身就是要回到全部思想的那个源头,回到“光”的源头。在海德格尔看来,那就是我们的自然,后来他把它叫做天、地、神、人共存共栖的“四方域”。在这里,我们看到,海德格尔更像是以一位“先知”的身份现身。
十一、走投无路:我们走在大路上
有人说海德格尔文章很难读,但你读读他的哲理散文,那是写的很漂亮的。在离他所任教的弗莱堡大学不远的德国南部黑森林山区,有一个滑雪胜地,山谷秀丽,杉树挺拔,苍鹰盘旋,风景怡人。海德格尔很早就在那里盖了一座小木屋,以逃避城市的喧杂,专事写作和思考。在一篇描述他的这个“工作世界”的散文中,海德格尔这样写道:
她与孩子外出,并不指导方向,总是默默跟随其后,观察,聆听,不受注意地保护他们,由他们活泼奔跑,做一切感兴趣的事情。他指责她对孩子的态度太过纵容和自由散漫,认为应该讲求规则。她说,真正的规则是人内心的信念。他们只能在实践中具备信念,而不是所谓的该往东还是该往西,该洗手还是该睡觉的规则。人要先把自己弄脏,弄痛,知道失望和伤害是什么,才会知道什么是真实。也许。说这样的话,也显示出一种理所当然的轻率。过程的复杂性总是会超过人的经验,但她依旧具备一种信心。
要思考和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回到上面的关于“分析判断”的典型例子。我们说“单身汉是未婚的男人”是“分析的”判断,其标准是:对这个判断后件,即“是未婚的男人”的否定,必然会导致在这个判断中出现逻辑悖谬。但要满足这一点,我们必须假定,“单身汉”与“未婚的男人”在其逻辑意涵上完全等价或者前者蕴含在后者之中。而要满足后一个条件,我们还需要假定另外的前提,例如我们关于“婚姻”和“男性”的理解。一旦这最后的前提发生动摇,正如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发生的那样,我们很难再说“单身汉是未婚男人”是一个分析判断而非综合判断。有人可能会说,“单身汉是未婚的男人”从来就不是一个典型的分析判断。那么让我们来看另外的一个,“三角形的三个内角和等于180 度”。这个所谓纯粹的先天分析判断的成立前提,是我们传统关于平面空间的理解。一旦这个理解不再成立,上述判断的分析性马上发生改变,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假设某种三个内角之和大于180度的三角形存在,而并不导致逻辑上的悖谬出现。反过来,一个有关经验事实的综合性判断所以并非逻辑上必然,是因为我们对制约这一境况的前提条件所知不充分,或者说,我们关于这个事物或事件的了解还不够“清楚” 和“明白”。一旦我们完全达到了“清楚”和“明白”,这个所谓的经验性、事实性的综合判断就成了“分析判断”。
“我自己从不‘观察’这里的风景。季节转换之际,我日夜体验斯时斯刻的变化。群山无言而庄重,岩石原始而坚硬,杉树生长,缓慢而精心,花朵怒放,草地绚丽,散发朴素的光彩。漫长的秋夜,山溪的奔涌,积雪的平原肃穆单一——所有的这些风物变幻,都穿透日常存在,在这里凸显,不是在“审美的”沉浸或人为勉强的移情发生的时候,而仅仅在人自身的存在整个儿融入其中之际……”。[3]
在这里,海德格尔坦言他从来不像科学家那样和这个世界的“存在”打交道,也就是说,既不像物理学家那样去客观“观察”,也不像心理学家、艺术家那般去主观地“审美”和“移情”。相反,他更是简单地像生于斯,长于斯,栖居于此的那些个农民一样,“仅仅将人自身的存在整个儿融入其中”,只有这样,海德格尔接着说,“我们对存在本身的追问,就变得更加单纯,富有质感,产生的成果只能是原始而犀利”。[3]
关于人的这一存在境况和特点,法国17世纪哲学家中有一个叫巴斯卡的,他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说人就像一根芦苇,但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巴斯卡用芦苇比拟人的脆弱,想说明只有思想让我们人类强大。所以,人在这个地球上,比其他的万事万物都有非常多不足的地方。我们没有狗跑得快,没有鸟飞得高,但是,人怎么经过几万年的时间,就从食物链的下层爬到了顶端?因为我们有思想。所以巴斯卡才会说: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而思想是跟理性,跟哲学连在一起的。
“出巡处处,奔波,茫然无出路”。这是一句出现在索福克勒斯的诗句中的名言,海德格尔却用它来描画,现代人在我们这个科技时代里思想和存在的“匮乏”。海德格尔说,我们现代人,在生活的道途上,无时不刻都在奔波忙碌。看似我们的道路四通八达,我们在这样的大道上日行千里,凯歌高进。但诗人为什么说我们“茫然无出路”呢?海德格尔解释说,我们不会在四处碰壁,无路可走的外在意义上走投无路。
让我们再来设想一个有所改变的情形。现在设想的不再是一个“围棋宇宙”,而是一个由“语词”组成的“语言宇宙”。我们知道,无论在汉语还是西方语言中,语词按照一定的规则与方式进行排列和组合。古今中外的伟大作家们据此创造出了人类历史上许许多多伟大的作品。这个“语言宇宙”与我们前面设想的“围棋宇宙”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围棋宇宙”是已经创造出来的,其基本规则和运行方式不再改变,因为如果改变了,那就不是“围棋”。“语言宇宙”没有一个单一的“创世主”,它是我们每一个使用语言文字的人的“杰作”。这是一个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而且在不断参与创造的宇宙,因为任何活语言的词汇量,甚至它的基本规则,使用方法及其程序,由于我们一代又一代使用者的加入和使用,仍然在不断地增加和发生变化。当然,这种变化是缓慢的,往往不为个体使用者察觉。
组织实施阶段首先要明确各项目中不同阶段的学习任务和相应的学习内容,即明确在项目中“先什么”“后做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将项目各阶段的学习内容用一个合乎逻辑的顺序排列出来,将每个子项目的重难点呈现,内容设计是根据旅游专业发展需求,结合学校实际实训条件,对普通话所有教学内容进行加工整合再放入所设计的项目中。项目教学法的应用在确保普通话的教学质量的同时,也全面提高学生的普通话水平及应用能力。具体实施内容举例:
减译法是指在不影响原文思想和内容的情况下,把重复多余的文字省去,或在不影响译语读者理解的情况下,用更加简明的语言形式代替原文繁琐语言的一种翻译方法,比如:
海德格尔这一解释的深意在于,我们现代人“走投无路”,那是因为我们安于现成,不再拥有那莽劲森然的、创发性的存在强力。我们自废武功, 不再去质疑和沉思, 我们志得圆满,趾高气昂地走在已开辟出来的“康庄大道上”,一路向前,向前。
海德格尔的这段解读让我想起小时候唱过的一首老歌“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奋发,斗志昂扬……”我们曾经何等的意气奋发,相信我们掌握了宇宙真理,走在了通往天堂的阳光大道上。这个歌词还很有意思,改过几次,第一次是“大跃进”的时候。那时大家唱得非常投入,结果整个国家的发展走了弯路。第二次是“文革”的时候,也唱《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们太相信自己对真理的把握,以为每次都是走在阳光大道上。但我们忘了对存在本身的“敬畏”和对我们人类有限性本质的体认,所以每一次我们都遭受重大挫折,“茫然无出路”。所以,海德格尔讲的道理是一样的。我们人类创造了当今的科技世界,我们似乎走在一条“阳光大道”上。他在这里区分了“上道”与“走在道上”。我们在现成的道上,一直往前走,不回头,但却丧失了我们的那份原初的思考,我们失去了那原初“上道”时拥有的莽劲、原朴的力道。那个原朴的力道是什么?就是“存在”本身给我们的。所以海德格尔反复说,要重提“存在意义”的问题,这个问题,长久以来,已经被人遗忘。
十二、上帝的“创造”与“智性直观”
海德格尔关于“存在意义”的重新思考和发问无疑会帮助我们反思人类“创新”和“发明创造”的生存论和存在论本质。从哲学上讲,人类的创新活动究竟首先是天才人物在知识论意义上的主体观念性创造和实践性设计,还是作为人类亲在的生存活动,在“超越”自身存在的界限和界域时,或者说,在其向着存在本身“撞界”式过程中偶然性的互动性“事件发生”(Ereignis)?要想澄清这一点, 还是让我们回到康德。
在哲学思想史上,康德也许是第一个在纯粹哲学上将上帝的无限性“创造”与人的有限性“创新”区别开来的人。康德将上帝或神的无限性创造称为“智性直观”(intellektuelle Anschauung),又称为“原创性直观”(intuitus originarius)。这是只有上帝或者作为造物主的神才特有的。相形之下,我们人只有“感性直观”(sinnliche Anschauung),这种直观依赖于感性对象,不但不能创造事物,相反,它一定的被动刺激下才有可能,所以,人的感性直观又被称为是“派生性直观”(intuitus dirivativus)。① 参见Kant, Immanuel. “Schriften zur Anthropologie, Geschichtsphilosophie, Politik und Paedagogik.” In Werkausgabe Band XII, edited by Wilhelm Weischedel.Suhrkamp Verlag. 1964.S.466. 也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2版,B145. 所以,是否具备对客体对象的“源初的”“创造力”就成为人和神之间的根本界限。
自从一开始提出,康德的关于“智性直观”的说法就让人费解,各家各派的解释也都莫衷一是。我们目前大概可以确定的有两点。第一,这是属神的,不是属人的;第二,这一直观同时具有无条件的原创性,它不依赖于任何客体,相反,它是所有客体本身成为可能的最后条件。那么,这样说可能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妨从我们熟悉的感性直观谈起。
华堂村所在的嵊州市是浙江丝蚕的主产地,历来是当地主要的传统农业项目,当地农户种桑养蚕十分普遍.解放前村内办有缫丝厂,加工当地农户丝蚕生产蚕丝.
收集并记录每位入组高危孕妇的基本资料,每次由专业护士对研究对象进行血压测量并记录。对每位入组的28~34周孕妇收集血液样本并保存。随访每位孕妇的妊娠结局信息。子痫前期的诊断及分类标准依据谢幸主编的《妇产科学》第8版。所有的入组孕妇均填写知情同意书。
关于我们人类的上述两种“知”的方式,哲学家们有过很多的研究和探讨。例如,英国哲学家休谟就曾经据此将我们的知识分为两类,一类基于经验的事实关系,另一类基于观念之间的推论关系。
十三、人的有限“直观”与 强大的“理智”
如果比直观,我们人比其它动物,没什么优势。但我们人有“理智”,或者说我们的理智能力要比我们所知道的所有生物都要强。那么,理智是什么?通过理智,我们可以看到和做到我们原先看不到和做不到的事情。例如,通过直观我们直接就看到“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这就是典型的直观。但是,我们直观不到“在一个平面上,一个直角三角形的斜边长度与其直角边的长度之间,不能有一个整数的比值”。不过,人可以从上面关于直线的直观出发,加上其它一些类似的直观,得到五条基本的“公设”,再加上一些拟定的公理、规则和定义,从此就会推论出,或者说,间接地“看到”后面的“定理”。而由这些公设,加上推出的定理,我们又能推出更多的定理。我们知道,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就是这么做的。而这样做的结果,欧几里得就建构出我们今天所谓的欧式几何的知识大厦。今天的科技理性,无论就其论证和计算程度来说,无论发展的如何高级和繁杂,但究其本质而言,都还是从这里开始。
我们的“直观”是感性直观,受到我们的感官、身体以及时空存在方式的局限,行之不远,而且常常犯错。而我们的理智或理性从一开始所起的作用,就是“帮助”或者“辅助”感性直观,让之“行”的更远一点、更高一些、更真实一些,例如,让我们的眼睛视线,超出苍鹰;让我们的双腿行速,越过飞马,……。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理性,已经变得非常强大,而且会越来越强大。正是因为如此,我们超出地球上的所有生物,成了“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
海德格尔看到了我们今天这个科技至上的科学主义时代所出现的问题。在海德格尔对古希腊诗人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第一合唱歌《人颂》的哲学解读中,他一反传统颂歌式的解释,即歌颂人类如何从原始草苍的野蛮时代,经过理性启蒙和开发,发明渔猎,创造文明,建立国家。这样的解释展现的是一部奋力向上,用文明战胜野蛮,用理性取代蒙昧的人类历史。但海德格尔在此发问,这个历史真的发展向上,无限乐观吗?还是我们已经从曾经伟大的时代跌落,丧失了人类曾经有过的那种莽劲森然的原始生命强力和嗷嗷叫的存在力道?海德格尔认为,导致现代人这般乐观想法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我们被教育认为,历史的开端都是原始野蛮、落后蒙昧,所以也是弱小无力的。但事实也许恰恰相反,开端才是那最莽劲森然与最强力者,后继的东西不是发展,而是散发开来的肤浅化,它不能保住开端的内在气势,它让开端变得无关紧要,让开端的伟大成为浮夸,成为纯粹数量意义上的庞大臃肿与扩容。[4]182
尽管理智的力量很强大,但我们不要忘了,理智的起点和目的,却都是直观。换句话说,理智是为直观服务的,直观是所有理智、理性的主宰。只是由于我们的直观范围,即直接感觉和行动的范围有限制,理智和理性让我们能够以“迂回”、“间接”的方式看到和做到我们原本看不到和做不到的事情。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类如此这般的理智力量,有没有界限?如果有,界限在哪里?
十四、经验性的事实知识与观念性的推论知识
首先,什么叫直观?直观简单地就是“看得明白”和“看的彻底”,看的“一目了然”。当然这个“看”不仅仅指作为感官的眼睛的看。同时为哲学家和数学家的笛卡尔曾经将它称为“清楚”(clear)、“明白”(distinct)。但什么叫“清楚”和“明白”?似乎很少有人讲的“清楚”和“明白”。让我们还是回到小蚂蚁的例子。小蚂蚁在爬行的路上,遇到一块巨大石头挡路,它看不清楚,不“知道”是否应当往“上”爬,还是绕着走,还是干脆打道回府。它需要“思考”--如果它也有思考的话。一个居高临下的“巨人”,譬如在小蚂蚁眼中的人,一眼就看穿蚂蚁应该绕路或回头,因为这石头上面还有一把火,蚂蚁爬上去定要粉身碎骨。但蚂蚁们看不到,它们完全靠本能,碰运气,有些继续往上爬,有些绕路,有些打道回府。另一个更好的例子也许是“捕蝇网”或“捕蝇瓶”。它的基本设计理念就是将进路设计的很大,但出口很小。苍蝇飞进去很容易,但要飞出来,仅靠直观,它们很难找到飞出去的出口。但我们人,居高临下,就会觉得很容易。如果苍蝇有我们人的“直观”,那逃出来就绝对不是问题。同样的道理,我们人的“感性直观”,就是让我们天生一下子就能“看”的明明白白的东西。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本领,例如天凉了,我们想都不想就会添加衣服;肚子饿了,想都不想就会“知道”要吃饭。动物也一样。在有些“直观”方面,我们人比动物强,有些则不行。例如,在山林里,狮子或者老虎这些大型的独居猛兽都有自己的觅食领地。方圆几里的山林范围内,来了什么东西,它们一下子就“知道”,我们人不行,所以古时候我们人常常成为这些猛兽的盘中餐。据说有些昆虫,像某些蚂蚁,能预先“知道”地球的地质自然变化,所以能“预测”地震。我们人类,就感官感觉而言,完全比不过。即使今天的科学预测,也常常还是不靠谱。在我们人类中间,也有些人直观能力强一些,有些人弱一些,有些人甚至有“特异功能”,这都很自然。但无论如何“特异”,我们人或者其它生物的“直观”,都是有限的,这几乎没有什么异议。
观念之间的推论关系或者说逻辑关系,是诸如我们的数学、几何等知识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判断性知识,叫分析判断。纯观念之间的关系不依赖于我们的经验,例如当我们说到一位父亲时,“父亲”这个概念就蕴含“是男性的”。当然我们现在这个概念开始发生变化,现在可能有同性恋“父亲”,其自然性别未必为“男性”。又比如说逻辑关系A = A,或者我们用哲学家们经常举的例子,“单身汉就是未婚的男人”。[5]这里讲的是观念之间的同一关系,这种观念之间的关系不依赖于任何经验性存在。因为我们不是在讲这个人究竟存在还是不存在,而是说如果他作为一位父亲存在,他就必然是“男性的”, 或者如果他作为“单身汉”存在,他就必然是“未婚的”。如何认定一个判断是否为分析判断呢?哲学家们往往说,因为这是一个纯逻辑的关系,所以,当一个分析判断的后件,也就是我们的例子中的“男性的”或“未婚的男人”为假的时候,它们的前件,即“父亲”或“单身汉”不可能为真,否则,就会导致逻辑矛盾。
与分析判断不同的是反映经验事实关系的综合判断。综合判断是传统物理学、生物学、化学等经验科学的基础。比如我们说这张桌子是木制的,“桌子”的概念中并不必然包含有“木制”的概念,但“父亲”的概念中必然包含“男性”的概念。在现实世界中,“这张桌子”有可能是“木制的”,也有可能“不是木制的”,这并不取决于“桌子”的观念,而取决于经验世界中的“事实”。正因如此,当我们说出“这张桌子不是木制的”判断时,我们并没有陷入矛盾悖谬之中,相反,我们可能发现了一个新的经验事实。这个事实可以被验证,也可能被证伪。
一般来讲,分析判断都是先天的知识。在近代哲学中,“先天”首先讲的是“先于经验”,这个“先于”有两层含义,第一,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经验,第二,它具有普遍必然的意义。像数学知识就是这样的、通过纯粹理性的推论、推演而来的知识,所以它不依赖于我们的经验而存在,并且是普遍必然的。与此相应,综合判断构成后天知识,又称为经验知识,它需要经验事实的证据来验证或否证。我们的知识无非是这样两类知识构成的。在近代哲学思想中,我们就是这样来区分和理解观念和事实、先天和后天、分析和综合的。
十五、在什么意义上“分析性的”知识又是“综合性的”?
学校可为学生构建科技教育系列活动,即组织全校师生每学年听一次科技创新报告、每学期组织一场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展示、每月举行一次科技信息发布、各班每组编写一份手抄报等活动来加强科技创新教育。
(3)通过个别座谈了解到,对于高职高专类学生,教师还需从多方面培养其学习兴趣及自主学习习惯,并利用各种手段加强对自主学习过程的督促和检查。
这样说来,我们关于世间任何事物或事件知识的真理性,无论综合判断的知识还是分析判断的知识,首先并非由这个事物或者事件的经验事实来决定,而是由其发生的存在论的前提和条件决定的。所谓“分析判断”说的是这一判断发生的所有限定前提,以及由这些前提导致的结局都“一清二楚”或者可能“清楚明白”。例如我们说“明天可能下雨或者不下雨”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分析判断”,因为这个判断穷尽了所有的可能性,它的逻辑形式在根本上无异于逻辑同一律,即A=A。为什么我们人的经验判断是综合的,那是因为我们人就存在的本质而言,就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可能性,所以,无论我们如何智力超群,我们不可能排除我们大部分知识判断的偶然性和综合性。我们所以有一部分知识以分析判断的形式出现,那是因为这些判断的前提是我们人为规定或定义的。
现在让我们来想像有一位全智全能的神,例如上帝,或者我们中国人讲的老天爷,祂的存在就是所以一切其他存在的前提和根据。这样,祂根本不需要理智或其他力量的帮助,就创造和清楚明白地“看”到了世间所有的一切,我想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康德所讲的“智性直观”或“原创性直观”。相形之下,我们人类的创新创造,只能是有限感性的“派生性的”直观和“迂回性”的理智的结果。所以,智慧、理智、哲学、科学是属人的。人为什么需要思考?因为我们的直观不够。神的直观本身就是创造,祂创造了一切,因此祂对所有的一切,事无巨细,都一目了然。而人类,由于我们的身体限制,由于我们认识结构的限制,只能看到我们周围的一点点,我们通过思维的力量往外去推。所以,人的力量叫什么?人的力量是展现,康德称之为“原生性的展现”,这种“展现”又分生产性的和再生性的,两者都是一种往外推演的思维或认识,都是有限的。正因为我们人需要理智和思考的帮助,需要哲学和科学,所以,才有这样的说法: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十六、围棋的算法和“阿尔法狗”的秘密
我们不妨假设有一个“围棋的宇宙”,在这个“宇宙”中,所有事物的运行和事件的发生,都按照围棋的规则发生和进行。实际上,这个“宇宙”内所有事物的运行和所有事件的发生,在这个围棋游戏诞生之际,即当围棋的棋盘、棋子数目和运行规则确定下来之际,就已经被“先天”地确定和“存在”了。围棋的每一步走法,天才棋手“创造”出来的每一个“高招”,都只是这个“存在”在具体情境中“在出来”的方式罢了。再假设这个围棋游戏的创造者有非常强大的“运算”或“计算”能力,可以一下子洞悉所有的算法步骤,那么,这位创造者就是这个“围棋宇宙”的“造物主”,他在这个“围棋宇宙”中就具有一种“智性直观”的能力。所有的一切,包括正在发生的、已经发生的、尚未发生的和未来可能发生的一切,对他而言,都一目了然。究其本质而言,这大概就是我们当今见到的阿尔法狗的根本机制。就智力的程度而言,阿尔法狗与人类棋手,在这个“围棋宇宙”中,也许将来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小蚂蚁和人的区别。
“围棋宇宙”运行的“算法”步骤,据说已经比我们所知的任何一个天文数字都还要大,例如要比我们所知宇宙中的所有物质中的原子数还要大上数倍。这已经难以想象了,但即便如此,我们知道,这还是一个有限的数目,因为我们明显已经设定,这个围棋的棋盘、棋子和博弈规则不再改变,但我们知道,这些并不是绝对不可变化和更改的。
“走投无路的真实情形毋宁说倒是这样:他不断在其亲身开辟的道路上被抛掷而回,因为他栽在了他自己的道路上,陷在车辙里。在此深陷中,他围绕着自己的世界转圈,自身纠缠在显似的假象中,于是,他自我放逐于存在之外。”[4]182
“围棋宇宙”也好,“语言宇宙”也罢, 都是我们现存的“存在宇宙”的一部分,而且这个“存在宇宙”,由于我们以及世上万事万物的参与,还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不断涌现出新的“存在可能性”或者被发现有新的“存在可能性”,这也许就是中国传统思想所讲的“道”或者“生生不息”的“自然大化”。如果有一个“创世主”,有一个神,祂“创造了”这一切,那么祂就会对所有这一切有着“清楚明白”的“智性直观”。而我们人,尽管我们也有直观,那只是有限可怜的“感性直观”;尽管我们有“理智”和“计算”,这使得我们高踞于众物之上,但我们的创造与创新,相形之下,就永远只能是有限的行为。
十七、哲学的本性与创新性思维
对于人来说,我们认识事物、获得知识的途径无非是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但我们看到,在神那儿不存在综合判断和分析判断,不存在先天和后天,不存在事实和观念的区别。通俗地讲,神的世界和认知方式与人完全不同,也是我们人无法了解的,在神的世界里,我们也许就和一只二维的小蚂蚁差不多。
休谟关于观念关系和经验事实的区分,以及由此而来的“分析”与“综合”,“先天”与“后天”的区分,言之凿凿,也非常有道理,似乎已成定论。但是,我们会进一步发问,人类知识这两个种类,之间关系如何?这种划分是绝对的吗?或者说,“分析性的”知识在何种意义上也可能成为“综合性的”?而“综合性的”知识又在何种意义上可能成为“分析性的”?
我们前面讲到苏格拉底,讲到哲学的本性。苏格拉底说哲学的本性就是爱智慧,其中一个最根本的东西是要自知自己的无知,苏格拉底说知道自己的无知并不是在故作谦虚。无知是人的本性,比起神的知识,人的知识永远是有限的,就像一个分母无限大的分数,无论作为有限数的分子有多大,其数值依然近乎于零。所以,我们人在神面前,在知识本身的面前,永远是无知的。但是,人类在本性上的“无知”并不代表人就会自暴自弃,不再进取。恰恰相反,正因为人类本质上的有限性,才使得人类天生有一种不甘堕落的宿命,要不断地超越人类的现存的有限性,不断地突破自身,“撞击”自身存在与存在本身之间的“界限”。这就是苏格拉底又讲哲学是对智慧的“爱欲”的要害。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亚里士多德与康德都曾讲过,哲学或形而上学是人类的本性。因此,如果我们将我们人类认知和人类行动的“锚”,锚定在这个人的存在与存在本身的“界限”处,我们就会更加理解人的存在的本质,少几分无知与狂妄,多几分理解我们真实的存在境况和人类“创新”的真谛。
看到《罪与罚》这个名字自然就会想到《圣经》中的救赎主题,这与作品内容十分贴切。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起名“罪”和“罚”。但是笔者更倾向于于试探性的主题。
归纳课文的主要内容是小学生必须掌握的一项重要的能力目标。沪教版第十册第七、八单元归纳课文主要内容是建立在第五册—九册基础上,要求学生综合运用所学方法进行概括,从三年级开始循序渐进地培养学生的概括能力。三年级通过由典型的段式的概括训练掌握提炼的方法,四年级根据课文的体裁特点,在教师的引导下逐步掌握各种概括的方法。五年级上半学期复习巩固所学的概括方法进行归纳主要内容,五年级下半学期主要提升到综合运用。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我们人类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家,和我们现今具有创新性思想的卓越人士,怎样看待他们的“创造性”工作的本质。
右坝肩上部不整合接触带进行了掏槽混凝土封堵处理,处理后满足建坝要求。对趾板建基面以下岩体进行了固结灌浆和帷幕灌浆,对两坝肩进行了帷幕灌浆防渗处理,满足设计要求。
牛顿无疑是人类历史上名列前茅的最富创新性思维的科学家。据说爱因斯坦曾经这样评价牛顿的创新成就:“在人类的历史上,能够将物理实验、数学理论、机械发明结合为科学艺术的人只有一位,那就是牛顿”。① 转引张文亮“牛顿:科学路上捡贝壳的人”,《智慧中国》2016年,第9期。 那牛顿自己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呢?临近生命的终结,牛顿留下这样一番让人感慨不已和沉思的话语:“我好像是一个在海边玩耍的孩童,不时为拾到比平常更光滑的石子或更美丽的贝壳而欢欣。但展现在我面前的,却是一片完全未探明的真理大海”。② 参见 Issac Newton - Wikiquate, https://en.wikiquote.org/wiki/Isaac_Newton
另一个我想到的人物是日本的当代韩裔企业家孙正义。孙正义谈不上有什么伟大的科学创新,但他无疑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创新性思维的人物之一。但他的创新更多地属于技术发明,和我们的日常实用相关,这说明“创新”并非全都是那些个“惊天动地”的事情。相反,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日常创新,也能从不同的方面显现出人类创新活动的本质。按照孙正义的说法,我们发明创新的诀窍就在于将已经存在,但尚未被联系起来事物展现出来和实现出来。这样的创新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和敏感深邃的思维力,而这些都是可以训练的。例如他发明的,用形状加颜色表示的交通信号灯。传统交通信号灯都是用颜色,例如红黄绿标明是否允许通行的信号,但这会对色盲者带来困难和危险。孙正义将信号灯的颜色形状从传统的一种改成了圆、正方、三角三种,分别代表三种信号,并和红黄绿三种颜色般配,设计在了一起,这样的信号灯,即便是色盲者也可以辨别自如了。本来在我们存在的世界里,不仅有颜色存在,也有形状存在,我们不仅用颜色指示信号,也有用形状指示信号。而且,颜色加形状的指示信号也存在,只是这种存在是“潜在的”存在,还没有被人们“看到”或“看出”,成为“实在”而已。我们的生活存在,或者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我们的“在世界之中的”活泼泼的“亲在”走在了我们的“观念”之先。而所谓的人类“创新”,在大多情形下,只是将这些“已经存在”的联系“实现出来”而已。孙正义的另一个“创新”是今天大家都习以为常的“收录机”。但在孙年轻的时代,虽然收音机已经存在,录音机也已经存在,收音机和录音机的“合体”尚不存在。不过,这一联系的可能性开始出现,于是,具有创新想象的孙正义将这两个存在物之间的联系“实现”出来,我们就有了“收录机”。大家想一想,我们这个时代有多少的科技发明创新是这样出现的呢?“手机”可以看作是“移动电话”与“电脑终端”的结合性联系得到实现;“航天飞机”可以看作是“火箭(上天)”和“飞机(降落)”的结合性联系。沿着这个思路,年轻时的孙正义,甚至为了训练自己的创新想象,把想到的一些英文词写在卡片上,每天花5分钟,随机地将几张组合起来,看能否实现其中的存在性关联。
斯蒂夫·乔布斯无疑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创新精神的人物之一,他的“苹果”创新以及伴随而来的移动互联网创新也许会成为将我们人类从此带入一个全新时代的“入口”。关于创新的本质,乔布斯曾经这样说过,其大意如下:
创新就是把各种事物整合到一起。当你问有创意的人是如何创新的,他们可能会感到一丝负罪感,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创造什么。他们只是看到了一些联系。他们总能一眼就看出各种事物之间的联系,因为他们习惯于将他们的各种经验联系起来,然后整合形成新的东西。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具有比别人更加丰富的经验,或者他们对自己的经验思考得更多。不幸的是,这是一种非常稀缺的品质。我们行业中的很多人缺乏多方面的经验。因此,他们就没有很多点可供联系,对待问题就只能提出线性的解决方案,而没有宽广的视野。我们对于人类的体验了解得更深更广,我们的设计就会越出色。
乔布斯的这个说法与牛顿、康德的说法非常接近,是对自己一生创新创造活动的哲学总结。牛顿也好,乔布斯也好,虽然他们在世时,很多人将他们视为神一般的人物,但他们并不神奇。在他们看来,我们人类并没有神的“创世”般的“创造”能力,并不能从绝对的“无”中“创造”出“有”来。我们人类有的只是“创新”。什么叫创新?人类的任何一种创新都是将已经存在着的可能性实现出来而已,这种可能性实际上是宇宙里无穷无尽的可能性中的一种,它本来就存在,只是碰巧在某个时候、通过某些天才人的努力,它偶然得到了实现,它没有实现的时候不说明它不存在,它只是还没有转化成实在而已。所以,我们人类的科学工作和艺术(技术)创新,其本质就在于在于“连接”,在于把那“已有的存在”和“正在开始的存在”“连接”起来,或者将这种“连接”在现实中实现出来。
贯彻“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实施行动导向教学方法,学生以小组形式,在教师的引导下通过项目的完成,达到专业知识学习和专业技能训练的目的。
在西方的哲学中,上帝能创造,而我们人只是创新。人是有限的,只能在创造出来的东西中间给它们做一个连接。我们只是看到了事物之间潜在的一些联系,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比普通人更能看出各种事物之间的联系,因为他们习惯于将各种经验联系在一起,大胆尝试去整合,形成新的东西。这就是人和神的区别,神是一眼就看到了,不需要像我们一样要去不断“迂回”地学习、思考、尝试。
参考文献
[1] Karl Loewith.Heidegger - Denker in duerftiger Zeit[M].2nd edition, Vandenhoeck & Ruprecht,1960.
[2] Herbert Marcus. One Dimentional Man[M]. Beacon Press,1964.
[3] 海德格尔.人,诗意地栖居:超译海德格尔[M].郜元宝编译,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
[4]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新译本)[M].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82.
[5] W. V. Quine, “Two Dogmas of Empiricism”[M].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2nd edition, ed. by A.P.Martinic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6-39.
[中图分类号] B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182(2019)02-0051-08
[收稿日期] 2019-01-16
[作者简介] 王庆节,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杜兰大学哲学系博士。
(责任编辑:肖德生,韦家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