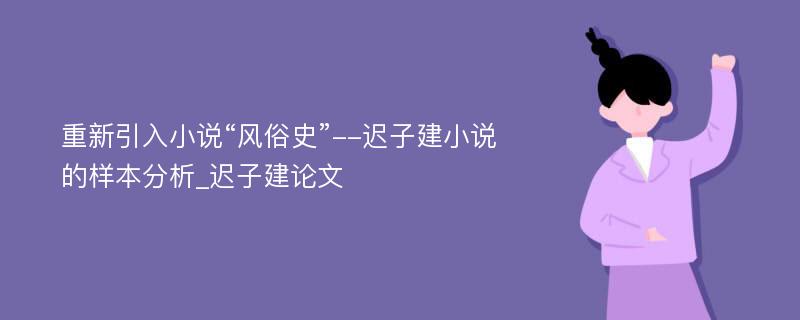
重提作为“风俗史”的小说——对迟子建小说的抽样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说论文,风俗论文,迟子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作家中,迟子建应该算被评论得比较多的作家。印象中许多优秀的批评家都做过迟子建的专题研究。对于这样的作家,再去研究她是要从遗忘开始,忘记别人怎样谈论她,转而从最诚实的阅读开始,尊重自己最朴素的阅读感受。从二○○八年秋天开始,我对照迟子建提供的目录进行近半年的“编年”式阅读。在读完她差不多所有的作品之后,我相信好作家是可以在他们的作品中闻到属于他们自己的气息。迟子建作品所散发的气息接通她生命出发之地的“地之灵”。虽然现在看迟子建,她辽阔得也许已经不只是那个在写作中频频回望故乡——北极村的“逆行精灵”了,但如她所说,“我作品中的善良天性”,“人性之善,如果追根溯源,可能与我从小生活的那个村子有关”①。
沉默者的风俗史
文学史中的一些老话题,一些习焉不察的常识,有时会被后世的作家在他们所处的时代翻出新意。阅读迟子建,我总是想起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提出的作为“风俗史”的小说。当然现在我们谈论“风俗史”的小说,不仅仅是指“百科全书式”的,作家对某一个时代的地域风情、日常生活场景、器物、语言、衣食住行、风俗仪式等的熟道和自然主义式的精确。这纯粹是一个“技术”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案头资料准备和田野调查获得。事实上,迟子建在她两部重要的长篇小说《伪满洲国》和《额尔古纳河右岸》写作之前都做过这方面的工作②。而且,我们应该注意到,在巴尔扎克的视野里,作为“风俗史”的小说被赋予了这样的意义,“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编制恶行和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刻画性格、选择社会上主要事件、结合几个性格相同的性格的特点揉成典型人物,这样我也许可以写出许多历史学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就是说风俗史”③。因此,作为“风俗史”的小说涉及的归根结底是作家介入现实的立场、视角、声音和叙述方式等等。
还是从迟子建这一年的写作说起吧。这一年多,迟子建发表的作品也就《草原》(《北京文学》二○○八年第一期)、《一坛猪油》(《西部·华语文学》二○○八年第五期)、《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中国作家》二○○八年第八期)、《解冻》(《作家》二○○九年第一期)等可数的几篇,对于一个正值创作盛年的作家,即使不和一些所谓的高产作家比,在迟子建自己二十余年的写作生涯中也是算比较少的。就是这些小说,迟子建似乎也自守着一种自己与生俱来、珍惜不已的腔调。在今天这个日日逐新的时代,能够固执地自持恒与常确实需要相当的勇气。迟子建在考验着自己的耐心,也在考验着热爱她的读者的耐心。《草原》讲一趟出差,《一坛猪油》说一坛猪油,《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纠结于山林小站的小酒馆,《解冻》缠绕在春天泥泞的小坑。迟子建喜欢日常生活的“传奇”。《一坛猪油》写乡屠霍大眼暗中将一个绿宝石的戒指藏在一坛猪油里,那个他偷偷喜欢的女人抱着这坛用房子换来的猪油去投奔大兴安岭的男人。临到目的地女人却将护得紧紧的坛子打破。男人的同事崔大林昧下藏身于猪油之中的戒指,戒指引得皮肤白净的女教师嫁给他,而他因为良心不安丧失了性功能,后来女教师因为丢了戒指丢了命。这坛猪油可谓情愫暗生于焉,而又苦果结蒂在斯。小说寓沉痛于戏谑,女人怀孕吃多了猪油招致胎儿太大,以至于难产而跑到国境那边的苏联才生下孩子,而“文革”时这又成了丈夫的罪状。更为“传奇”的是女教师丢掉的戒指竟然被女人长大的儿子打鱼打上来,而这在异国生下的儿子恋上异国的女子最后跑到了国境那边。
和古典小说“无巧不成书”不同,现代小说追求的是故事的自然流淌,讲究的是春梦了无痕,少有像迟子建这样公然在短篇小说的格局里容纳下这么多的“偶然”和“巧合”。像这样的小说我们恍若回到了中国古典小说说书人的时代,一日复一日的且听下回分解,让听者提着心气撑到故事的终了。这样的小说听着杀馋,写下来好看。是啊,很多时候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小说应该是“引人入胜”的好看。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迟子建的小说就是“好看”的小说呢?再说《解冻》呢?一封事后证明只是看一场内部电影的急件,却让了无新意的刻板夫妻生活,划拉出女人对男人的柔情,而却又终归于淡漠。迟子建小说有大时代闪烁其间,更有像《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中古老的中国谨守而至今日的道义和德性潜隐深藏于焉。
迟子建的小说也写智识阶层、上流社会、中产阶级,但迟子建小说最多的还是在“下层人”中打滚。一九八○年代中期,写了三十万字的迟子建在回顾自己的创作时说自己的作品,“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写下层人的生活的”④。而时过境迁,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迟子建就从来没有离开过“下层人”。今天“底层文学”这么热闹,却好像很少有人把迟子建放在“底层”这个文学谱系来考量。
无论是中国还是异域,文学从来没有停止过“底层”关注。五四之后现代中国的“底层”关怀差不多是衡量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果从文学书写的角度,中国现代文学史,差不多是一部“底层”小人物的命运史。二○○一年第八期《读书》发表了查特吉的《关注底层》,此文无论是对“底层”的理论资源的梳理,还是对其现实意义的阐发都远较我们后来的许多关于“底层”的思考深刻。查特吉认为,“底层”“昭示了印度作为殖民地的经历和体验”。但有一点需要指出的,在新世纪中国,“底层”并不是“作为对殖民地精英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精英主义的反抗而出现的”⑤。它更不是福柯和德勒兹那里指称工厂工人、囚徒和精神病患者的“底层人”,也不局限西方女权主义者为之代言的“第三世界”妇女⑥。不过,应当看到,新世纪中国的底层研究和底层书写挟“底层”而抒智识阶层胸臆的欲望相当急切,因而,当今的“底层”研究和底层书写难免借题发挥的“文人腔”。一定程度上,新世纪的文化和文学中的“底层”不仅仅是对文学突入现实可能性的试金石,而且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日渐边缘化的知识分子所占据的最后道德制高点。其实,不只是新世纪的“底层文学”叙述,“底层”翻作“文人腔”在新时期是有前科的。一九九○年代前后,“新写实”文学和“新生代”文学是先锋文学的本土化和世俗化,实质上则是,一九八○年代以残雪、余华、莫言、苏童、孙甘露、格非等为代表的先锋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集体退场。先锋文学凭借想象力“炫技”式的对现实的逃逸和重构,被“新写实”文学和“新生代”文学的“仿真”式的原生态还原所取代。因此,在新世纪初“底层”写作登场之前,中国当代文学已经用十多年的时间将“仿真”式的原生态文学书写操练得相当娴熟。
斯皮瓦克曾经提出过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命题:“底层人能说话吗?”⑦ 有意思的是尽管语境和内涵各不相同,二○○五年作家刘继明也追问到:“我们怎样叙述底层?”面对当下文学中的“三农文学”、“打工文学”等等,我们能够说已经解决了“文学叙述底层”的问题了吗?假定我们承认客观存在着一个曾经被遮蔽的“底层”经验有待作家去叙述,但一旦作家进入了叙述多大程度上能够保证“底层叙述”的实现。如果不对今天的“底层”文学书写进行细致的辨析,很有可能在一些常识性的问题上让一些早已经摒弃的东西借尸还魂,比如“道德优先”的“题材决定论”,比如对苦难把玩的“炫痛”,比如对“底层”的诗意想象等等。因此,如果没有清醒的反思,很有可能占据“道德的高地”却无法抵达“文学的高地”。
因此,无论对于底层预置多少“意义”,“叙述底层”一个必要的前提是能不能、多大程度上让底层人说话,而不是“底层”翻作“文人腔”。其实如果仔细梳理,我们今天的小说书写丢掉的还不只是小说的手艺传统。有些东西由于曾经被庙堂征用,我们更是弃之如敝屣,比如耳熟能详的“阶级立场”、“阶级感情”。问题是如果我们不囿于“阶级”,一个作家应该不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立场”和“感情”?作为思想的传播者,一个好作家应该有自己安身立命的文学栖地,他的“立场”和“感情”当然也属于和他生命、精神相关的一部分人。再看迟子建呢?比如她二○○四年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小说的“矿难”题材是典型的“中国经验”。贫困、苦难、阴暗、善无善报的“中国”在这篇小说中以令人惊悚的景象呈现。这不但在迟子建的小说中罕见,甚至在当代同类题材的小说中也少见。但小说中更重要的是,一个身受丧夫之痛的智识女性,走向民间底层,冀望在“民歌和鬼故事”中疗救自己的苦痛,最终将自己的一己疼痛汇流到更为辽阔的中国大地的苦痛中。事实上,现在知识界的写“下层”必须经历这样痛痒相关的“下底层”,才能在“重”中照见自己的“轻”,进而在这样的轻重相较中“叙述底层”。
如果我们承认迟子建叙述的是“底层”,我不知道迟子建是不是认同一个曾经被污染的词——“代言人”。我们看迟子建这二十余年的写作,她也会有自己的忧伤和自闭,有所谓的“文人腔”,但更多的时候迟子建都是选择和“下层人”,和弱者,和被侮辱被损害者站在一起。《树下》的七斗是沉默者,《越过云层的晴朗》的狗是沉默者,《伪满洲国》是一个沉默的“国家”,《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个沉默的“民族”。迟子建写作为风俗史的小说,但迟子建是一个把自己看得很渺小、微弱的作家,她的风俗史是一部属于北中国大地沉默者的风俗史。以《伪满洲国》为例,迟子建采用一种仿“地方志”写法,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年谱”。其实更早的时候,迟子建就曾经用“年表”为一个早夭的孩子作“史”,这篇叫《烟霞生卒年表》的小说本来可以作为考察迟子建历史观的一个恰当的例子,却没有被批评家充分注意。《伪满洲国》“地方志”的历史建构本身就体现着个别性和边缘性,现在迟子建的仿“地方志”则进一步把“风俗史”的书写重点移置到“地方的日常生活”之上,这就是迟子建所谓“小民们”的“卑琐平凡的实际生活”。二十世纪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裹挟其中的作家已经习惯追新逐变,对时代变动的敏感成为衡量作家对现实进入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但现在迟子建却走向反面,在“变”中感知凝定的“常”。“我觉得那个时代,动荡中还是有平静的生活的,当然这种‘平静’,打着屈辱的烙印。”⑧ 某种意义上,迟子建的《伪满洲国》的时间要“古老”得多;在“伪满洲国”,时间没有空间并置、参照中的进步与落后,也没有沧桑巨变中的惊悚。迟子建的笔下,“时间”往往是一天又一天,慢慢地成长、衰老,这中间有难以言说的苦痛和细碎的挣扎,更有所谓实际生活和精神上“盛举”的无聊、微小的快乐。《伪满洲国》,多少的家仇国恨,我们几乎以为迟子建要变出腔调拖曳出大咧咧的国族叙事史诗。可刀光血影、家国之仇,“小”民还是要忍辱偷生。迟子建不否认壮烈和庄严,她写杀戮和抗争,但世界之“大”之“雄壮”从来不是“小”、“隐微”的死对头。在一个“大”且“雄壮”的时代,那些“小”、“隐微”中间自然有生命的尊严和体面。
“我的文字是粗糙而荒凉的”
迟子建“编制恶行和德行”风俗史的“清单”,而且熟谙由恶至善调控的转换术。在今天这个复杂得让我们晕头转向的世界,迟子建却执意于简而直的善恶两分。
迟子建有她的信仰。我曾经在一篇谈论迟子建中篇小说的书评里说,迟子建是一个为我们今天的文学时代持一盏简朴灯的女人⑨。就像《逝川》里写到的“泪鱼”,我相信迟子建念念在心的痛惜与爱怜、温暖与爱意也是能够给我们带来“福音”的“泪鱼”。迟子建总爱写到月光与灯盏,总喜欢让她的小说闪烁着亮光。迟子建卫护着生命的美丽与庄严。《岸上的美奴》题记说,“给温暖和爱意”。迟子建对一切美好、易逝的东西抱有伤怀之美的爱怜,但迟子建的小说从来不回避“人之恶”。她趋善向美却不隐恶遮丑。“我的手是粗糙而荒凉的。我的文字是粗糙而荒凉的”⑩。这来源于成长经验。“嗅着死亡的气息渐渐长大”,“稚嫩的生命糅入了一丝苍凉的色彩”(11)。从她早期的《北极村童话》一路读下去,迟子建小说的“人之恶”总会在迷离的梦幻和柔软的善良中浮现出来,尖锐地刺痛苦我们。而越是靠近,时易世变,迟子建小说的“人之恶”就像一树一树的阴影一枝一叶地扩大。《白银那》中趁着鱼汛囤盐提价致使整个村子的鱼腐坏的小店主,《青草如歌的午后》中溺亡自己傻儿子的父亲,《相约怡潇阁》、《第三地晚餐》中的不忠者,《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更是一个如人间地狱一样暗黑、冰凉的世界……自私、猜疑、嫉妒、贪婪、残忍,所有的人性之恶像怀揣着匕首的刺客随时割破我们世界的温情。
有对世界如此的洞悉,迟子建完全可以种植出“恶之花”,但迟子建却让“温暖和爱意”的光照亮世界。要看到世界的光,作家内心首先要有光。迟子建对鲁迅作出这样的理解,其实也是在反观自己。“我总想鲁迅在骨子里其实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只不过我们把他定位在‘民族魂’这个高度后,更多地注意了他作品的现实和批判的精神,而忽略了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内心深处都具有的浪漫主义情怀。从他的故居直至老街,我感受的是栩栩如生的鲁镇,它闲适、恬静、慵懒、舒缓,这种环境是能让人的想象力急遽飞翔的地方”(12)。我们相互敌意、伤害,但我们又相濡以沫。这是一个苦难的世界,我们却支撑活着。像《亲亲土豆》、《五丈寺庙会》、《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予爱亲人,予爱萍水相逢者。作为一个作家,迟子建似乎在证明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同样可以是一个彻底的理想主义者。就像她说的:“我觉得生活肯定是寒冷的,从人的整个生命历程来讲,从宗教的意义来讲,人就是偶然抛到大地的一粒尘埃,他注定要消失。人在宇宙是个瞬间,而宇宙却是永恒的。所以人肯定会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苍凉感,那么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这个苍凉的世界上多给自己和他人一点温暖。在离去的时候,心里不至于后悔来到这个苍凉的世事一回,我相信这种力量是更强大的。我从小在北极村长大,十月份至次年的五月,都是风雪弥漫的时候,在那个环境中,如果有一个火炉,大家就很自然地朝它靠近。”(13) 正因为如此,迟子建喜欢雨果和托尔斯泰。因为雨果也很少把一个恶人逼到绝境,像冉阿让这种人都会让他心灵发现。托尔斯泰写的《复活》,也是这样。迟子建的小说很少写大奸大恶,所以像《雾月牛栏》、《夜行船》、《西街魂儿》、《百雀林》……迟子建都给迷失者自我觉悟、返回本性的路途。
“芳草在沼泽中”,“飘飞的剪影在暗夜中有一种惊世骇俗的美”(《五丈寺庙会》),迟子建的小说写光之于暗,善之于恶,梦想之于绝望。如《热鸟》所写,正是大鸟的逍遥梦才能让赵雷见出父母亲生活的虚伪和假面。“我一直以为这样尽善尽美的环境没有给想象力以飞翔的动力,而荒凉、偏僻的不毛之地却给想象力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可惜这样的地方又缺少足够的精神给养。没有了满足感、自适感,憧憬便在缺憾、失落、屈辱中脱颖而出,憧憬因而得以比现实本身更为光彩夺目。”(14) 迟子建坚持认为,一个作家要自觉地去寻找并葆有大风雪中这个小火炉。所以,她对俄罗斯作家拉斯普京的《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序言中的一句话有着深刻的会意。这句话说,“这个世界上的恶是强大的,但比起恶来,爱与美更强大”。当我们读迟子建的小说,从她的悲悯和宽宥之心看去,我们每个人原来都揣着良善之心,或者只要我们愿意把那些自私、猜疑、嫉妒、贪婪、残忍从我们的心底赶走,世界将会重新接纳我们。我不知道什么原因,迟子建特别喜欢写旅行,《热鸟》、《向着白夜旅行》、《踏着月光的行板》、《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观彗记》、《逆行精灵》、《第三地晚餐》、《草原》……是不是她私心里总愿意把人生看作向善的行旅?《岸上的美奴》中的美奴、《鸭如花》中的逃犯、《青草如歌的午后》中的父亲母亲,还有许多在尘泥中颠簸的“罪人”,迟子建对他们同样也充满痛惜与爱怜。而且就像迟子建在《蒲草灯》和《第三地晚餐》中所直面的,许多时候罪人获罪常常因为他们就预先生活在一个有罪的世界里,犯罪者同样是我们世界中的被侮辱被损害者。沉入到世道人心的最幽深细弱之处,痛惜与爱怜、温暖与爱意在迟子建那里差不多长成一种“信仰”了;哪怕这样的“信仰”像《观彗记》中的彗星那样难以遭逢,哪怕“信仰”之后得到的只是《日落碗窑》中唯一的金色泥碗。
迟子建终究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迟子建能够体会到巴尔扎克深切地体会到的:“历史的规律,同小说的规律不一样,不是以一个美好的理想作为目标。历史所记载的,或应该是,过去发生的事实,而小说却应该描写一个更美满的世界……可是,如果在这样庄严的谎话里,小说在细节上不是真实的话,它就毫不足取了。”(15) 因此,有一点必须得到澄清,迟子建并不像有的研究者所认为的就是一个温情主义者。事实上,单一的温情主义是虚弱的、避世的。迟子建给人“憧憬”,但她自己清醒“庄严的谎话”和“真实的细节”的尺度和界限,甚至要不惜将“憧憬”的幻影戳破。从这个角度看,迟子建《秧歌》的意义就不只在呈现了一个丰盈的民间和底层世界,小说最为惊心动魄的是会会为了一睹小梳妆这个传奇式的“标致得不同寻常”的女子掘了小梳妆的坟。迟子建是“醒”着的。迟子建的长篇小说《树下》和《越过云层的晴朗》写一人一狗在苦难的大地上行走。《树下》的最后却写:“他们重温了那种无法言说的美丽的温情,他们似乎有些疲倦了。天大概要亮了,黑夜带着全农场人的沉甸甸的温情满意地离去了。单薄苍白的白天即将到来。必须睡上一觉了,他们这样说着,彼此沉入了梦乡。七斗在那个沉沉的梦乡中见到了那匹久违于她的白马,白马暴露在月光下,醒来后,她有一种说不出的忧伤。”而《越过云层的晴朗》中的狗在弥留之际所感受的是:“我很快越过云层,被无边无际的光明笼罩着,再也看不到身下这个在眼里只有黑白两色的人间了。”
所以,我坚持认为迟子建小说的底子终是苍凉。迟子建写《额尔古纳河右岸》时说,“这是一个我满意的苍凉自述的开头”(16)。看到这句话,我忽然感到迟子建从一九八○年代的《那丢失的……》、《沉睡的大固其固》、《北极村童话》开始就有一个“苍凉自述的开头”。
迟子建如何进入文学史?
几乎每一个谈论迟子建的研究者都指出迟子建是少有的没有进入当代文学史叙述谱系的重要作家。一般说,能够进入文学史叙述谱系的作家必须在“经典”或者“样本”方面为一个时代的文学提供新经验。因此,进入文学史的作家也许不一定是我们想象的代表一个时代最高文学水准的“经典”的写作者,他也可能只是提供了反映一个时代文学症候的“样本”。如果从经典性的角度来做取舍,现在关于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文学史叙述所涉及的作品估计有一大半要被剔除。以伤痕文学为例,类似于《伤痕》、《班主任》这些进入了文学史叙述的小说,它们的审美性、文学性能够称得上“经典”吗?所以说,一个作家是否能够进入文学史叙述的谱系,关键要看他是否在恰当的时候写出了恰当的作品。而且从当代中国文学史写作的现实来看,文学思潮和流派常常是关注的重点。那么一个作家如果没有恰当的流派可以依傍,而又在思潮之外自顾自地写作,要进入文学史叙述就相当难了。
迟子建如何进入文学史?当然不妨做一番假想。可以假定不改变现在的文学史叙述秩序和格局,承认现在关于新时期文学史叙述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迟子建写作的起点应该是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迟子建最早被大家关注的《北极村童话》写遥远的边地生活,虽然在地域性指标上接近寻根文学,但作为一篇对于童年往事的追忆之作,《北极村童话》显然经不起寻根文学式的文化解读。而且从文化立场上看,以《初春大迁徙》为例,迟子建写一个村子向蛮荒之地的迁徙和回归。一定意义上,其路径和寻根文学是背向的。再说先锋文学,迟子建小说从来不以“炫技”见长。“我不喜欢现在的中国文学,这种文学实质上是读了一些博尔赫斯等西方小说舶来品之后对它的一种拙劣的模仿。”(17)这样的文学观决定了她“反技”的先锋文学之外的写作姿态。一九九○年前后的“新写实”成就了女作家方方和池莉,而这时的迟子建也连续在重要的文学刊物《收获》、《人民文学》、《钟山》等上发表了《遥渡相思》、《原始风景》、《怀想时节》和《炉火依然》,我坚持认为这是迟子建作为一个优秀作家的重要转折时期。但这是一个属于“原生态”的文学时代,而迟子建这个时候的文学却是空灵、冥想,和自己的一场“心变得更为狼狈”的爱情相关(18)。这是迟子建整个创作中最远的一次“出走”,可随后迟子建又在故乡“恢复了往日的平静”(19),富有意味的是迟子建似乎要把这次“出走”永远地隐藏起来。在江苏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迟子建文集》和上海人民出版社二○○八年出版的《迟子建中篇小说集》中,这个时期的小说都只收入了一篇和《北极村童话》相近的《原始风景》。应该说,从现在看,《遥渡相思》、《怀想时节》和《炉火依然》呈现了迟子建写作另一方面的才能,它在后来的《向着白夜旅行》和《逆行精灵》中有影影绰绰的印痕,但越是接近后来迟子建和批评家都有意无意压抑这方面的才能。
一九九二年,迟子建进入了一个“旧时代”的写作阶段,这里面包括《旧时代的磨房》、《秧歌》、《香坊》等。应该说,这是迟子建写作生涯中和所谓文学思潮最靠近的一次。这些小说,包括后来的《伪满洲国》,“新历史小说”是可能把这些小说收编其中的。但我们文学史叙述对“新历史小说”的兴趣更多地放在对近现代“革命”的颠覆和重述上。在庶民的历史没有得到充分尊重的时代,迟子建小说草民“旧时代”的历史之“新”当然很难凸显。而且对草民“旧时代”的历史,迟子建的把握和拿捏也是节制、收敛的。“新历史小说”需要的是“三十年河东,三十河西”的“复辟”,而不是迟子建式的历史一如往昔的“徐慢慢、杨学礼夫妇、苏应时的母亲以及大地主张得富先后离开了人世”。“我们那小镇一如往昔地存在着。种地的,他依然种着地;卖粮的,他也依然卖着粮;行医的,也依然照顾着病人。小学校的学生毕业了无数,校长也换了几届,可钟声依然如往昔那般沉闷、悠远。”(《东窗》)至于《伪满洲国》从在《钟山》发表的《满洲国》到后来出版的《伪满洲国》,我们是不是可以发现许多意味深长的东西?从小说与现实的关系看,小说从来就是“作伪”的,那么《伪满洲国》之“伪”究竟在强调小说的文体规定性,还是在规避可能的意识形态禁忌。
一九九○年代中后期是迟子建创作的成熟期。《逝川》、《亲亲土豆》、《雾月牛栏》、《清水洗尘》、《灰街瓦云》、《向着白夜旅行》、《岸上的美奴》、《逆行精灵》、《观彗记》、《五丈寺庙会》、《伪满洲国》等重要作品都写于这个时候。这是新时期女性作家的骚动和哗变期,但文学史所强调的女性性别意识是与“男性”或者“男权”相区别的“女性”、“女权”的性别对抗,而迟子建小说中“搀杂着性别中天性的东西”,“女性对万事万物,在天性上比男人更敏感”(20)。因而,迟子建那种和整个人类与生俱来的、温和与宽宥的“女性”世界观一定程度上和“男性”是共生、缠绕,甚至和解和互补的。
新世纪的迟子建有了更为辽阔和沉静的气象。对于一个作家而言,“中年写作”是一个自我澄清的结果。那些能够留下来的已然经过一次次摸索和淘洗。《一匹马两个人》、《雪坝下的新娘》、《微风入林》、《一坛猪油》、《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第三地晚餐》和《额尔古纳河右岸》……这些小说,迟子建的焦虑、惘然、忧戚和伤怀浮动。在一个大动荡的时代,迟子建怎么能生生地从残缺、苦难处出发而归于弥合和温煦呢?迟子建的小说中开始出现化解不了的冷硬和荒寒。《灰街瓦云》、《雪坝下的新娘》、《野炊图》、《起舞》、《额尔古纳河右岸》这些小说或者爱失风尘,或者恶行当道,迟子建娴熟的由恶向善的转换术失灵。迟子建自己质疑着自己,书写着“比起恶,爱与美更强大”的反例。一个新的迟子建俨然呼之欲出。如她自己所说:“我从没有要把自己和文学创作有意识地进行定位。顺其自然,风格的转变、对艺术的理解以及文学观都不知不觉就改变了。在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正值二十来岁,大自然在我眼里充满了诗情画意,而年纪大了,很多想法都变了,与现实有直接关系。并不是在文学上大彻大悟了,而是岁月不饶人,它赋予人无形之中一种沧桑感,使你在写作上倾向于朴素的情感。”(21) 此前,《逝川》、《亲亲土豆》、《雾月牛栏》、《白银那》中的人之“本性”可能蒙垢,但拂去尘埃依然是金子般的光芒。而现在,在巨大的毁坏面前,人性之善还能卫护我们的最后家园吗?对于这个问题,迟子建是游移的。而徘徊于“信”与“不信”,迟子建可能逼近幽微,走向深刻。作为在一个大变局的中国和世界生活和写作的作家,作为在一个对世界抱有信仰的作家,迟子建的焦虑、惘然、忧戚和伤怀可以成就“经典”或者作为“样本”。而我们的文学史准备怎样接纳迟子建呢?
换个角度看呢?如果我们仅仅把现在的文学史叙述作为进入历史的一种可能呢?事实上,从一开始,迟子建的写作就自有谱系。迟子建喜欢《金瓶梅》“对市井生活风情民俗和语言的那种老到、平白”。她认为:“现代小说这么发展,确实是一种倒退,不是进步。比如明清小说就是追求一种民间野史类的写法,但不同于现在的民间文学。那个时代的民间文学是很高雅的,看来琴棋书画行云流水非常舒缓。”(22) 而按照巴尔扎克的观点,作为风俗史的小说是与“公共生活”不同的东西,近乎中国的“民间野史”。他认为:“我对于经久的、日常的、隐秘或明显的事实,个人生活的行为,它们的起因和它们的原则的重视,同到现在为止历史家对各民族公共生活的重视一样。”(23) 如果从这个角度回到迟子建写作的起点,迟子建把她北极村的故事称为“童话”就是很有意思的了。按周作人说,“童话”“无一定的时地与人名,也不信为史实,只是讲了听得好玩的”,“现在用了日本输入的新名词称之曰童话,其实这并不是只有儿童要听的故事,尤其不是儿童读物,她的原意是‘希奇事儿’”(24)。“希奇事儿”的童话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其实和志怪、传奇、小说的“传奇性”是一路的货色。所以迟子建的小说要讲那么多幽灵、神迹、梦境的诡异,要说那么多悲欢离合、因果报应,甚至中国古典小说察人观世的那种“平白”,那种朴素的期许也被迟子建搜罗在册。而从这种意义上,二十多年的小说写作迟子建在别人获稻的时候,她却在拣拾弃置在收获的田野上的稗子。应该说,今天的小说家越来越意识到“小说稗类”的意义。而有一天“小说稗类”的文类意义被重新唤醒,迟子建是不是可以进入文学史了呢?至于迟子建,她所置身的世界不再是“黑白两色的人间”,不是明清,也不是十九世纪的巴黎、伦敦和俄罗斯,而是《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是《起舞》、是《额尔古纳河右岸》那个复杂、缠绕的“中国”。同样,如果她再讲述“小说稗类”,再写作为风俗史的小说,明清小说和巴尔扎克们肯定是不够用的。
“我相信生命是有去处的”
说到“小说稗类”、“民间野史”、“希奇事儿”的童话这些,我们可以把话题稍微展开。现代小说和“小说稗类”的中国小说传统比较,隐而不彰的东西还有许多,比如谈狐论鬼的癖好。在这方面,迟子建小说揭示了更深的沉默和更远的消逝。这些小说:
这时豁唇突然发现在雾间有一个斜斜的女人飞来飞去,她披散着乌发,肌肤光洁动人,她飞得恣意逍遥,比鸟的姿态还美。
——《逆行精灵》
她感到她和曲儿之间的那团红光已经慢慢地走出房子,穿过屋里的空地,穿过门,走向起风的空气中。风掀动着无层次的尘埃,一片茫茫无际的土黄色笼罩着世界。
——《遥渡相思》
走到桥头的时候,我忽然在黑压压的人群中发现了禾。我发现他完全因为走到桥头时心怦然一跳,接着我感觉到人群中有一个人的眼睛冷冷地亮了一下,他的身影就是这样被突出出来了。
——《炉火依然》
我已经是第三次来到河岸了。河岸上没有行人,远远近近都飘飞着轻盈的雪花,对岸的渔村因为苍茫而若隐若现。
——《九朵蝴蝶花》
我和玛利亚把血肉模糊的果格力抱回希楞柱的时候,妮浩回来了。她一进来就打了一个激灵,她看了看果格力,平静地对我们说,我知道,他是从树上摔下来的。妮浩哭着告诉我们,她离开营地的时候,就知道她如果救活了那个孩子,她自己就要失去一个孩子。我问她这是为什么,妮浩说,天要了那个孩子去,我把他留下来了,我的孩子就要顶替他去那里。
——《额尔古纳河右岸》
幽灵、神迹、梦境,迟子建的意义世界是有“神”的。《向着白夜旅行》写“我”与一个幽灵结伴出游北极村的故事。迟子建自己认为:“也许由于我生长在偏僻的漠北小镇的缘故,我对灵魂的有无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在那里,生命总是以两种形式存在,一种是活着,一种是死去后在活人的梦境和简朴的生活中频频出现。不止一个人跟我说他们遇到过鬼魂,这使我对暗夜充满了恐惧和一种神秘的激动。”(25) 一定意义上,这里的“神”之有无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而且涉及到世界观,涉及到我们如何建构我们的精神和意义世界,如何安顿我们的灵魂。可以从很多方面去讨论十九世纪以降乡土中国的巨变,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应该是我们不再像从前那样对鬼神充满敬畏之心,而迟子建的小说则沐浴着神灵的恩泽。“我在大兴安岭出生和长大,没有很厚的家学的底子,所以东北文化对我来说更多体现在小时候听历史传奇、乡里乡亲的神话鬼怪故事。”(26)“我的故乡因为遥远而人迹罕至,它容纳了太多的神话和传说。所以在我的记忆中房屋、牛栏、猪舍、菜园、坟茔、山川河流、日月星辰等等,无一不沾染它们的色彩和气韵。我笔下的人物显然也无法逃脱它们的笼罩。我所理解的活生生的人不是平常所指的按现实规律生活的人,而是被神灵之光包围的人。”(27) 有着这样的成长背景,我们自然不难理解迟子建经验的诡魅世界。
应该重新认识迟子建小说对“中国小说经验”的呈现。幽灵神迹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参与曾经是中国文学中最富有想象力的部分,同样也是迟子建小说中最为惊艳的部分。“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这可以作为迟子建小说的真实。这类似于卡尔维诺所说的“民间故事是真实的”。卡尔维诺在编辑《意大利童话》时意识到这样的真实,他认为:“似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生活,在现今处于停滞之中,而实际上任何事件都可能发生:蛇洞被打开,成了牛奶河;仁慈的君主却原来是暴虐蛮横的父亲;寂静无声、着了魔的王国突然复苏。我有这样一个印象:早已丧失的在民间故事里统治一切的法规,正在我所打开的魔箱里蹦出来。”不仅如此,卡尔维诺还认为:“本质平等的人类被任意分成帝王和平民;生活中常见的无辜者遭受迫害和随之而来的复仇;情人初遇不期,爱情刚刚萌发即失去;普通人受符咒支配的共同命运,或是让未知的力量左右个人的存在。这些复杂因素渗透整个人生,迫使人们为解放自己、为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斗争;同时,我只有解放他人才能解放自己,因为这是我们自身解放的必要条件。这需要对奋斗目标的忠诚,需要纯洁的心灵,它们是获得解放胜利的根本。此外,还必须有美,这种美有时会蒙上卑微和丑陋的蛙皮,但故事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是无穷无尽的变化和万物的统一:这包括人类、动植物和无机体。”(28) 如此看去,民间故事有着其与生俱来的逻辑。从这里出发,我们也许能够理解迟子建“简而直的善恶两分”世界的经验和想象。缘此,我们应该意识到当代中国文学对庶民史、地方志、风俗史、日常生活史意义上的书写的强调应该有更开放的“想象”包容。
想象力的匮乏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困境,这是一个带有追溯原罪意味的题目。讨论这个问题,一个预设的前提就是想象力是推动文学进步的核心动力。对于想象力和文学的关系,我们无意也无力在这里仔细清理和辨析。想象力的匮乏不只是一个技术和能力的问题,如果仅仅是这个问题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匠人式的习得获得想象力这种技术和能力。而从文学生态和作家精神状态来考察,我们其实发现,整个中国近现代一直到现在,甚至是更远的古典时代,是不利于想象力的生长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压抑多少文学想象。中国文学想象力的抑制,“乃是受到长期大一统的专制政治上的限制”。远的不说,如果我们就考察一百年的中国现代白话文学史,就会发现“定制”式的文学观一直左右着作家的文学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的标准化生产,从知识群体的定制生产一路滑向国家定制。因此,研究现当代中国作家,很容易识别出他们所依据的公共的、通用的生产尺度和标准。在“定制”式的文学观支配下,我们可能不缺少知识分子想象、国家想象、民族想象和现代性想象,但个人想象往往被压抑和钳制着。有研究者认为,中国社会,“人文的世界,是现世的,是中庸的,是与日常生活紧切关联在一起的世界。在此种文化背景、民族性格之下,文学家自然地不要作超现世的想象,不要作惨绝人寰,有如希腊悲剧的走向极端的想象。中国文学家生活于人文世界之中,只在人文世界中发现人生、安顿人生,所以也只在人文世界中发挥他们的想象力”(29)。但如果我们把“小说稗类”、“民间野史”作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这个判断可能就大有问题了。因而,作为风俗史的小说中国,或者扩大到对整个乡土中国的书写,不谈狐不论鬼将多么地了无生趣。在这方面,不仅仅是迟子建,苏童、莫言、阎连科、张炜、毕飞宇、阿来等都做了富有意味的探索。所以说,对于我们而言,当代文学其实同样存在着许多有待揭示的沉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上,《额尔古纳河右岸》是迟子建摆脱文学“定制”的一次自我想象远征。至今,无论是批评家还是迟子建自己,基本把《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解读放在行将消逝的文明的挽歌之上。而我倾向于《额尔古纳河右岸》是关于神灵的史诗。“最后的萨满”,这应该是这部小说最富魅力和想象力的地方。小说的叙述者,那个九十岁的鄂温克老妇人说:“我的身体是神灵给予的,我要在山里,把它还给神灵。”对于鄂温克人来说,能够交接神灵的是萨满。“尼都萨满是我父亲的哥哥,是我们乌力楞的族长,我叫他额格都阿玛,就是伯父的意思。我的记忆是由他开始的。”小说的结束则是:“妮浩就是在这个时候最后一次披挂上神衣、神帽、神裙,手持神鼓,开始了跳神求雨的”。“妮浩在雨中唱起了她生命中最后一支神歌。可她没有唱完那支神歌,就倒在雨水中——”
在人的颂歌时代,迟子建把最瑰丽的颂歌献给了神灵。
二○○八年十月-二○○九年四月
注释:
① 迟子建、郭力:《现代文明的伤怀者》,《南方文坛》2008年第1期。
② 迟子建、郭力:《现代文明的伤怀者》,《南方文坛》2008年第1期;迟子建:《心在千山外——在渤海大学的讲演》,《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
③ 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西方文论选》(下册),第16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④ 迟子建:《斯人独憔悴》,《北方的盐》,第188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
⑤ 查特吉:《关注底层》,《读书》2001年第8期。
⑥ 陈永球:《从解构到翻译:斯皮瓦克的底层人研究》,《从解构到全球化批判:斯皮瓦克读本·编者序》,第1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⑦ 斯皮瓦克:《从解构到全球化批判:斯皮瓦克读本·编者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⑧ 迟子建、郭力:《现代文明的伤怀者》,《南力文坛》2008年第1期。
⑨ 何平:《迟子建:为我们今天的文学时代持一盏简朴的灯》,《解放日报》2008年7月11日。
⑩ 迟子建:《年年依旧的菜园》,《北方的盐》,第52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
(11) 迟子建:《死亡的气息》,《北方的盐》,第282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
(12) 迟子建:《鲁镇的黑夜与白天》,《北方的盐》,第64-65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
(13) 迟子建、郭力:《现代文明的伤怀者》,《南方文坛》2008年第1期。
(14) 迟子建:《必要的丧失》,《北方的盐》,第176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
(15) 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西方文论选》(下册),第17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16) 迟子建:《心在千山外——在渤海大学的讲演》,《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
(17) 迟子建:《温情的力量》,张英:《文学的力量》,第295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18)(19) 迟子建:《秧歌·自序》,第1-2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
(20)(21) 迟子建、郭力:《现代文明的伤怀者》,《南方文坛》2008年第1期。
(22) 迟子建:《温情的力量》,张英:《文学的力量》,第295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23) 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西方文论选》(下册),第17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24) 周作人:《〈乌克兰民间故事〉凡例》,钟叔和编:《知堂序跋》,第535页,长沙,岳麓书社,1987。
(25) 迟子建:《秧歌·自序》,第1-2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
(26) 迟子建、周景雷:《文学的第三地》,《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
(27) 迟子建:《谁饮天河之水》,《北方的盐》,第238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
(28) 卡尔维诺:《意大利童话·序言·民间故事概观》,第7-8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29) 徐复观:《中国文学中的想象与真实》,《中国文学精神》,第74页,上海,上海书店,2004。
标签:迟子建论文; 小说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额尔古纳河右岸论文; 北极村童话论文; 雾月牛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