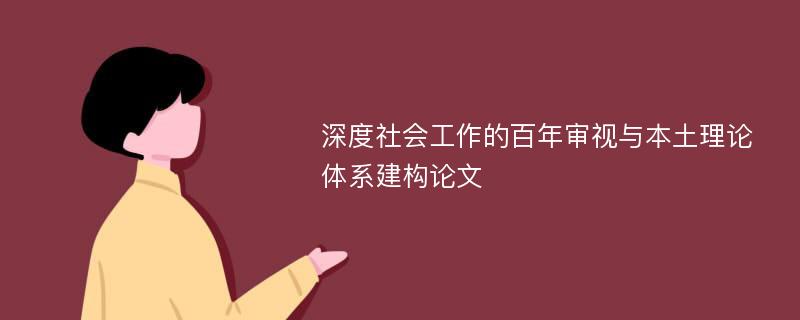
深度社会工作的百年审视与本土理论体系建构
童 敏,许嘉祥
(厦门大学 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西方社会工作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但是有关它的理论基础仍然认识不清,总是面临“浅显”的质疑。显然,对“深度”社会工作的探究不仅是理论发展的要求,而且对于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以及本土理论体系建构来说,更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通过对西方理论流派的百年历史考察发现: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从早期开始就一直处于“深度”的探究中,又无法摆脱“浅显”的质疑,尽管自20世纪60年代起从自然生活场景和历史社会场景两个维度抗争“浅显”的挑战,但仍然由于其一直站在个人的立场理解环境变化的原因,无法超越个人当下实践的经验。因此,需要提倡一种从环境立场出发的“深度”社会工作,在不断变动的场景实践中实现人们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深度自觉,提升人们的实践理性。这对于场景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社会工作来说,既是实践的要求,也是本土理论体系建构的核心,它为中国社会工作走向国际舞台提供了平等对话的空间。
关键词: 深度社会工作;社会工作理论;社会工作历史
一、问题的提出
对现象内在关联的深度分析和考察是每一个专业成熟的标志之一,社会工作也不例外。[1]尽管从里士满在1917年正式发表《社会诊断》一书算起[注] ① 作为社会工作的创始人,玛丽·里士满(Mary Richmond)也是社会工作理论的开山鼻祖,她在1917年出版的《社会诊断(Social Diagnosis)》一书被认为是第一本系统阐述社会工作服务逻辑的论著。 ,社会工作理论经历了整整一百年的探索,但是到目前为止,对社会工作理论基础的认识仍然众说纷纭。[2]在理论开创的早期,为了帮助社区贫困人群应对日常生活中的困难,社会工作就开始关注服务对象在生活中的问题解决的能力,并且把这样的能力视为社会工作理论建构的核心,特别是哈特曼提出自我可以独立于无意识的观点之后,更是把意识层面的自我作为社会工作理论逻辑建构的基础,认为社会工作理论只关注如何促进人们更好适应环境,是一种不涉及心理结构层面改变的支持性心理辅导(supportive psychology)。[3]这样的理论定位,在注重心理结构改变的心理治疗来看,自然是一种“浅显”的理论。[4]更为致命的“浅显”批评,来自于对社会工作学科基础的质疑,发现社会工作过分依赖心理治疗的理论,没有自己的理论基础,而一个没有自己理论基础靠模仿其他学科理论的学科,显然是走不远的,也不可能有自己的学科位置。[5]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察和分析,社会工作一直在寻找自己的专业理论基础,把社会因素引入到社会工作的逻辑框架中与心理因素结合起来,形成心理社会双重视角。[6]这样,社会工作似乎有了自己独特的理论基础,既区别于心理学,又不同于社会学,正好介于两者之间,是两者的结合。
然而,心理社会双重视角只是把庞杂的心理与社会因素连接在一起,并不意味着这样的连接就具有现象背后的深度分析和考察,导致社会工作要么依赖其他学科的深度分析,要么依赖日常的生活经验,无法让人们感受到社会工作专业的价值和作用,以及与其他专业的区别。尤其对于专业化和职业化快速发展的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来说,明确专业的价值和作用迫在眉睫。因此,有必要对社会工作的心理社会双重视角的理论基础进行重新审视,借助西方理论流派的百年历史考察和文献梳理,找到深度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和逻辑框架,为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理论的指引,也为理解西方社会工作的理论逻辑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
二、 自然生活场景中的“浅显”抗争
从20世纪20年代起一直到60年代,弗洛伊德的心理动力学派占据着社会工作的主导,几乎成了社会工作理论的代名词。[7]但是,到了60年代,由于种族冲突的加剧和民权运动的兴起,让人们看到专注于个人心理治疗的社会工作理论存在弊端,它不仅没有自己的理论基础,也无法承担起服务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工作宗旨和关注社会环境的要求。[8]因此,从60年代起,社会工作开始转向社会环境因素的探索,以对抗“浅显”社会工作的质疑。
李吉林在小学语文的教学领域提出 “运用情境教学,培养审美能力”的理念。文学艺术与音乐艺术是一脉相承的,儿童钢琴的学习也是以培养审美能力为主旨的。所以,情境教学的理念和方法可以移用于儿童钢琴教学中。
70年代初,结构视角[注] 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结构视角有两个取向:一个主张从现有的社会层面的因素理解个人的困扰;另一个主张对现有的社会制度采取批判的态度,主要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后来发展成批判社会工作。 正式向“浅显”社会工作提出挑战,认为以往的服务逻辑太关注个人心理因素的影响,而实际上,许多社会弱势群体的问题并不是由个人因素造成的,是因为社会环境缺乏必要的机会和条件,使得个人的成长要求无法得到满足,从而出现问题。如果社会工作只关注个人内部的心理因素,就会忽视外部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服务就会流于“浅显”的形式。而且,一旦社会工作强调这种问题的个人责任,就会不自觉地把问题中的社会责任转嫁给个人,根本无法使问题的讨论深入到问题背后的社会结构的分析。[9]尽管结构视角为社会工作引入了社会环境因素的分析,甚至还直接要求社会工作者从面临同样问题的人群或者因个人问题而关联在一起的社会支持网络等社会结构角度理解服务对象的问题,跳出从个人视角界定问题的局限,但是仅仅关注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显然,只是走了与个人心理治疗逻辑相反的分析线路,并没有摆脱心理与社会的二元分割,仍然继续沿用着“浅显”的类型化分析逻辑。
[2]D. Howe,A brief 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 theory .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p.3-6.
与系统视角相类似的是生态视角,它在80年代走进社会工作的服务领域,它也倡导循环逻辑,只是更注重个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转换,而且还把个人的成长改变要求也放入社会工作的理论逻辑框架中,[11]特别是到了90年代之后,它还通过生命历程概念的引入把个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个人成长改变的要求结合在一起。[12]可以说,生态视角是比系统视角更为复杂,也更有“深度”的理论,它揭示了生活困境中个人与环境相互影响的横向关系以及个人成长改变要求的纵向关系两个维度上的循环逻辑。
尽管系统和生态视角提出了与弗洛伊德心理动力学派因果分析逻辑完全不同的循环逻辑,把个人影响因素与环境影响因素结合在了一起,但是系统和生态视角采用的仍然是一种类型化的“客观”观察的逻辑,关注人的“客观”理性分析能力。这样的分析逻辑框架在弗洛伊德心理动力学派看来,是“浅显”的,因为无论人的“客观”理性分析多复杂,它只是人的意识层面的现象,而意识层面的现象就会受到人的内心更深层次的心理结构的影响。[13]显然,系统和生态视角并没有关注到人的“客观”理性分析的心理依据,它所要求的改变仍然只是支持性的,并不涉及心理结构层面的“深度”调整。
“综合材料艺术”的概念,最为直接的理解就是视觉艺术中混合运用多种材料进行艺术创作。综合材料的英文名称是Mixed media & material,又可以称为复合材料或综合媒介,强调材料多元、复合、兼容的特点。综合材料不一定是现成品,可以是制作作品的特殊材料。综合材料的“综合”二字,还有一个针对性,就是指不只是用单一、惯用的艺术材料,比如蛋清颜料、油质颜料或水墨等等,而是自由采用那些在既往艺术创作中不用或较少使用的多种生活材料、工业材料。综合材料在更多的时候体现为艺术创作的新的形式语言,而语言的变化往往使得
语文在我国基础教育体系中是一门重要的基础学科,语文具有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特征,新课程改革更加关注学生的人文性,突出了语文作为交际工具的这个特性。新课改的实施显得原有的高中语文教学方法落后,难以提高学生的语文学习水平。因此,教师要创新语文教学方法,灵活运用语文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三、 历史社会场景中的“浅显”抗争
[15]P. Parsloe, “Empowerment in social work practice”,In P. Parsloe (ed.),Pathways to empowerment (pp.1-10). Birmingham: Venture, 1996, p.8.
风味是酸奶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同时也是消费者考虑接受程度和偏好的重要因素。为了探究酸奶在发酵过程中风味物质的协同作用机理,国内外一些学者对其代谢途径和代谢调控方式开展大量的研究工作[10-12]。本文从酶活研究进展方面初步阐述酶活与酸奶风味的关系,以期为相关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由80年代第二代女性主义总结提出的“人际关联中的自我(self-in-relation)”的观点,对社会工作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7]依据这样的观点,人们的自觉意识就不是对自己生活状况的静态察觉,而是在人际动态关联中对自己生活状况的审视,是一种无法脱离周围他人影响的动态考察。这样的动态考察还有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权力关系的分析。在女性主义社会工作看来,人之间不是平等的,总是存在着权力关系的相互作用。[18]90年代兴起的批判视角则是继承了结构主义社会工作的社会结构分析的概念,认为人们之间的交往总是发生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内化为人们个人的价值标准。[19]因此,批判视角的社会工作提出批判思维(critical thinking)这个概念,强调社会工作不应走服务技术的线路,而应帮助人们在特定社会处境中对自己的社会处境进行批判性审视,改善主流意识中存在的社会歧视和社会排斥,提升人们在社会处境中的自觉意识。[20]90年代还出现了反压迫视角社会工作(anti-oppressive social work),[21]它是女性主义社会工作和批判社会工作的结合,并且在此基础上引入了社会位置(social position)和反身性(reflexivity)这两个重要概念,假设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不平等是多方面的,与人们所处的社会位置有关,当人们在确定自己的社会位置时,也就在影响其他人的社会位置。[22]这样,对自己所处社会位置的掌控就与周围他人以及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而人们需要把自己投入其中并且在与周围他人关联中审视自己的社会位置,这就是反压迫社会工作所倡导的反身性。如果说女性主义社会工作是把个人的自觉意识与周围他人连接在一起,那么批判社会工作则是把个人的自觉意识与社会结构结合在一起,而反压迫社会工作则是直接把个人的自觉意识与社会处境中的不同关联整合在一起,实现个人在特定社会处境中的“深度”的自觉意识,既涉及个人不同层面的关联(人际和社会结构),也涉及个人不同方面的整体关联。
80年代之后,由于全球化和国际化步伐的加快,种族矛盾和国际冲突不断加剧,如何摆脱以往单一的解释逻辑从多元的思维方式出发理解多元文化的交流,就成为社会工作关注的一个重要主题,由此出现了从多元文化角度解释社会工作的理论模式,以弥补社会工作一直以来对历史文化维度的忽视。其中影响最广的包括种族文化敏感的社会工作(the ethnic-sensitive social work)和多元文化社会工作(the multicultural social work)。[23]种族文化敏感的社会工作把种族文化的交流与权力关系的分析结合在一起,强调种族文化的交流总是伴随着主流文化的影响,而且两者之间存在着价值冲突,甚至歧视和排斥。这样,人们在多元文化交流中就需要借助种族文化敏感这个概念,才能够识别其中存在的社会歧视和排斥,保持文化自觉能力。[24]多元文化社会工作则直接把多元文化视为人们所处的社会场景的基本特征,认为在这样的场景中只有通过历史成长经验和社会处境经验的自我反思,人们才能超越特定历史社会的局限。[25]显然,无论种族文化敏感的社会工作还是多元文化社会工作,它们都把社会场景中另一重要的历史文化维度引入到社会工作服务中,这样,特定社会场景中的“深度”自觉意识也就有了文化价值反思和历史经验总结的要求,是特定历史社会处境的“深度”自觉。
显然,历史社会场景中自觉意识提升这种方式对个人心理的考察与弗洛伊德心理动力学派的无意识分析逻辑框架完全不同,它需要人们把自身放置到特定的历史社会处境中,通过对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的觉察提升理性把握环境的能力。[26]这样,个人的心理就不是脱离社会环境的内部心理结构,而是在特定的历史社会环境中的自觉意识,通过自觉意识的提升超越当下环境中个人的意识局限。可见,弗洛伊德心理动力学派追求的是抽离具体场景的普遍化的实证理性,它的“深度”来自于内部心理结构的深入分析,回答心理困扰是什么的问题。在这样的实证理性面前,注重问题解决的社会工作自然显得过于“直白”和“浅显”。实际上,社会工作追求的是一种在特定场景中如何有效行动的具体化的实践理性,它的“深度”来自于对自身所处的历史社会处境的深入洞察,回答场景中如何实践的问题。[27]
四、从“浅显”社会工作走向“深度”社会工作
尽管从20世纪60年代起,一方面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环境对个人生活的重要影响,把环境因素引入到社会工作的理论逻辑框架中,从生态环境的强调延伸到历史社会环境的讨论,不断深入挖掘环境对个人成长改变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又始终站在个人的位置上理解环境的作用,无法超越个人当下的生活经验理解环境的变化,环境成了个人意识中的环境。这样,无可避免地使社会工作理论出现内在的矛盾,不是社会工作的理论逻辑模糊不清,找不到一致的理论基础,有时偏向个人,有时又偏向环境,就是模仿其他学科的理论逻辑,无法深入挖掘场景背后的“深度”原因,最终也无法摆脱“浅显”的逻辑。显然,从“浅显”社会工作走向“深度”社会工作的关键就是转变观察立场,真正从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出发理解社会环境与人之间的复杂动态关联,超越个人自我经验的局限。
资料分析是确定技术方案的基础性工作,将各种资料中的有用信息充分合理地利用起来,可以使更新后的协议书及附图等成果资料内容更全面、权威,为乡级行政区域界线勘定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可靠的依据。
有意思的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有些社会工作学者已经发现,对个人理性盲目乐观并且认为可以无所不及的实证理性实际上忽视了环境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矛盾性,要求社会工作重新理解人与环境的关系;[29]甚至有些学者直接称社会工作为场景实践(contextual practice)的学科,强调这种学科首先需要关注的不是个人的理性,而是环境本身的特征,即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30]实际上,兴起于90年代中后期的正念治疗从21世纪初开始在社会工作领域流行,由于受到东方佛教正念(mindfulness)思想的影响,这一流派一改以往西方社会工作注重改变的服务逻辑,转而关注对当下生活中的矛盾方面的接纳,认为环境的改变总会超出人们的预期,如果仅仅关注如何改变,就会陷入“为了改变而改变”的怪圈中。[31]因此,人们首先需要做的是停下改变的脚步,学会开放自己,坦然面对即将面临的挑战,接受当下生活中的不确定性,[32]在场景化的经历中理解现实的本质。[33]
老父亲没有继续跟儿子争辩下去,而是让小儿子拿来一条锁链去把狗拴住。可是狗没犟几下就把铁链挣断了。父亲拾过铁链递到儿子手中,“你好好看看!”父亲语重心长地说道:“一条链子有几十个扣子,其中只锈坏了一个,而其他的完好,却仍然拴不住一条狗啊!”
显然,只有确立了从环境的立场理解环境与个人的关系时,社会工作才能真正放下实证理性的包袱,走进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挑起实践理性的责任,让人们能够勇敢面对生活场景中的意外挑战,并且通过与当下场景的对话审视自己意识的局限,延伸场景理解的广度和深度,逐渐从普遍化抽象化的“浅显”现象分析走向历史社会场景的“深度”实践探究。
五、“深度”社会工作的基本理论框架与中国本土理论体系的建构
正是在环境的立场上,“深度”社会工作有了自己的出发点,假设场景是复杂、多样、不确定的,它与以往“浅显”社会工作有了明显区别,两者之间存在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因此,对“深度”社会工作的考察也就需要以此为基础,重新审视人们在这种变动的场景中的实践逻辑,考察人们是如何在这种变动的场景实践中觉察自己的状况、选择自己的实践策略以及明确与场景的关联,即场景实践中针对个人自己的意识自觉、针对行动的实践自觉以及针对环境的场景自觉。[注]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以“变”为前提假设的逻辑在中国哲学的讨论中比比皆是,本文的讨论也受到中国哲学思维逻辑的影响。有关中国哲学思维逻辑的讨论,详细请参见蒙培元:《中国哲学主体思维》,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就个人自己的意识自觉而言,如果从环境的立场来理解人们的场景实践就会发现,此时的场景实践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场景的变动性,场景总会出现人们无法预料的情况。这样,场景的变动性就成为场景实践的基本假设。而面对一种不断变动的场景,人们首先要做的不是明确需要解决的问题或者希望达成的目标,而是学会接纳生活的不同方面和矛盾之处。这意味着原来处在意识之外或者意识边缘的内容,因为受到变动场景的挑战,让人们不得不关注它们的存在,转变成人们的自觉意识。可见,在变动的场景中人们的自觉意识不仅仅来自于对自己经验的反思和批判,这种意识层面的探索,同时还涉及直接面对意外挑战的勇气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无意识层面的探究,是两个层面的交错。它不同于弗洛伊德心理动力学派的逻辑,除了不再是一种心理结构的静态分析之外,同时还把个人回归到自己的生活中,与场景的变动紧密结合在一起,使无意识真正扎根于日常生活之中。
在这种变动的场景中,人们的行动就不只是涉及如何做这样的技术操作问题,而同时涉及如何回应变动场景提出的挑战,是如何确认变动场景中的真实需要并且将这些需要转变成现实的过程。可以说,是在特定场景中对真实的探究过程,是一种真实的实践。这样,作为社会工作者就无法站在生活之外,给服务对象技术的指导,而需要融入到服务对象的生活场景中,协助服务对象进行真实的探索。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场景处在不断的变化中,人们在真实的探究中还需要面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使得人们的行动同时具有了伦理的要求,是一种伦理的实践,需要承担起伦理的责任风险。因此,这种变动场景中的实践自觉也就具有了三个方面的要求:了解怎么做、事实是什么以及承担什么责任,将人们的行动与真实和伦理的探究结合在一起,不再像以往社会工作那样“各自为政”、相互割裂。
为此,文中提出采用AD8347与SI4133为核心的多频点射频模块的设计方案。该方案可以对现有多系统中的多个频点信号进行下变频;通过合理设计滤波器相关参数和接收机基带跟踪环路结构,实现单通道对L1,B1信号的同时处理、定位。文中主要阐述了通用射频模块的设计方案、微带线电感等设计经验,实现了多频点通用射频模块,最终通过测试验证结果。
就环境的场景自觉来说,在这种变动的场景中,人们通过意识自觉和实践自觉逐渐超越当下经验的限制,不断延伸场景理解的广度和深度,使个人的成长不仅能够与社会的改变紧密结合起来,而且还能够与历史的经验融汇在一起。这样,个人的成长就不只是个人的改变,它同时也是社会改变和历史发展的必要构成部分,是个人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的自觉。此外,在这种个人的成长中还涉及在地文化的审视,是个人对生命意义的文化探究,使个人拥有了文化责任的自觉。可见,场景自觉涉及个人对场景理解的延伸,它包括个人成长与社会责任、历史责任和文化责任三个方面的深度结合,可以弥补人本主义社会工作、存在主义社会工作以及灵性社会工作对个人成长和生命意义探究的不足,将个人成长和生命意义的探究融入到特定的场景实践中。
实际上,变动场景实践中的意识自觉、实践自觉和场景自觉三者是紧密关联的,它们一起构成具体场景的实践过程,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变化都会带来其他两个方面的改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场景实践的理性不同于实证理性,以实践自觉为主线,强调人是特定场景中回应场景要求和挑战的人,如果对个人自己进行审视,就是意识自觉;如果对环境进行审视,就是场景自觉,而人就是在这样的审视中不断超越当下场景实践经验的限制,延伸理性的光芒,实现心理和社会的深度融合。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在场景实践中探寻实践理性逻辑的“深度”社会工作给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因为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是在社区的场景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它与西方社会工作在机构服务的实证主义技术理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道路形成鲜明的对比,有着自己独特的因改革开放而出现的社区服务缺失的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契机。[34]正是在这样的独特历史社会处境中,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有了自身发展的现实条件和内在逻辑,它探寻的是场景实践中的实践理性。这既是中国本土社会工作实践要求的体现,也是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理论体系建构的核心,表明中国本土社会工作者的历史和社会自觉意识的提升。可见,“深度”社会工作不仅为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找到了现实发展的理论依据,而且也为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理论体系走向国际舞台创造了平等对话的空间。
壳聚糖酶应用广泛[25],最为重要的用途是生产壳寡糖。壳聚糖酶水解产生的壳寡糖分子量更易控制且条件温和,壳聚糖酶水解获得的壳寡糖分子量一般低于10 kDa,且更易溶于水,优于天然的壳寡糖。壳寡糖比壳聚糖有更好的生物功能,例如在生物医学领域对人体的免疫调节、抗肿瘤、降血脂、调节血糖、改善肝脏和心肺功能等。此外,壳寡糖在食品行业还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有助于改善肠道,从而促进人体吸收营养物质;可用于生产调味品,代替市场上一些如苯甲酸钠等化学添加剂;可用于生产饮料,具有减肥、美容养颜、调节免疫功能等作用;可用于蔬菜、水果的保鲜,且具有抗菌防腐的功效。
总之,对社会工作的“深度”强调是为了让社会工作从普遍化、抽象化的“浅显”讨论转向特定场景实践中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深度”考察,重新回归生活、回归实践理性这一生活中的成长改变的核心,真正实现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目标。
六、总结
通过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发展的历史回顾可以发现,尽管在理论发展的早期,社会工作就已经与弗洛伊德深度心理结构分析有所不同,关注服务对象生活中的问题解决,开始了自己的“深度”理论探索,提出心理社会双重视角,但是实际上,由于社会工作仍然沿用弗洛伊德心理动力学派的实证理性的“科学”逻辑,即使引入了系统和生态视角,也依然无法实现心理社会的“深度”结合。为此,社会工作还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把人放回到历史社会场景中,考察人们在历史社会场景中的实践理性,强调通过实践、反思和批判提升人们的社会场景、历史经验和文化价值的“深度”自觉意识,以便挑战“浅显”社会工作的批判。可惜,这样的历史社会处境考察依旧停留在个人意识的层面,把环境简化为个人意识中的环境。
显然,实现“深度”社会工作的关键是转变人们的观察视角,从环境立场出发,假设环境是复杂、变动、多样的,重建变动场景中的实践逻辑,围绕实践自觉这条主线,通过对特定场景中的场景要求和挑战的回应,以及对个人自己和环境的审视,将意识自觉、实践自觉和场景自觉三者紧密结合起来,不断超越变动场景实践中当下经验的限制,使个人的成长与社会的改变相互促进,真正实现心理社会的深度融合。值得一提的是,“深度”社会工作给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它推崇一种在社区场景实践中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道路,与西方建立在机构服务基础上的实证主义技术理性根本不同,倡导场景实践中的实践理性,这不仅构成了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理论体系的核心,而且也为这一理论体系建构找到了文化自信的精神资源。
[6]E. G. Goldstein, “The knowledge base of clinical social work”,Social Work , 1980, 23(3), pp.173-178.
[1]E. Greenwood, “Attributes of a Profession”,Social Work ,1957, 2 (3),pp.44-55.
就历史文化维度而言,这种强调以变为前提假设的中国文化注重的恰恰是生活场景中的实践,它关注的也是人们的实践理性,无论对“知行合一”的推崇,还是对生活背后“道”的体察以及生活境界的提升,都始终围绕着生活场景实践中的实践理性。[35]显然,在“深度”社会工作的理论框架下,中国文化成了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理论体系建构源源不断的精神资源,而这一精神资源也正是通过社会工作者的实践与反思深深扎根于现代社会的弱势人群的日常生活中,成为推动和保障改革深化的重要力量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深度”社会工作为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理论体系的建构找到了文化自信的精神根源。
在70年代,社会工作还引入了系统视角,它与结构视角不同,不是放弃个人心理因素的影响寻找社会环境因素的解释,而是把不同的影响因素通过系统这个概念连接起来,关注不同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转化。[10]这样,个人心理因素的影响与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就紧密结合在一起,不存在谁主导谁,而是一种崭新的相互影响的循环逻辑。借助系统视角的循环逻辑,社会工作就可以对人们生活困境中的不同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找到表面现象背后的循环逻辑,做出“深度”的介入,使社会工作既可以避免因只关注心理影响因素而导致的“浅显”质疑,也可以找到对复杂社会现象进行“深度”分析的理论依据。
花叶型,新叶产生褪绿斑点,并有明脉,逐渐扩展成大块褪绿或呈花叶,疱斑状,瓜长不大,表面长有环状斑或绿色斑驳;黄化皱缩型,上部叶片叶脉周围失绿,具有黄绿斑点,发展至整个叶片黄化,向下卷曲、皱缩、坏死,甚至全株枯死,未死的病秧有的不能结瓜,或结瓜很小,瓜面产生许多小瘤或隆起皱褶;混合型,为害严重,常成片死秧,造成减产或绝收。
[3][7]E. G. Goldstein,Ego psychology and social work practice (2nd ed .).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5, pp.8-9,39.
[4]M. E. Woods & F. Hollis,Casework :A psychosocial theory (4th eds .). New York: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mpany, 1990, p.85.
[5]J. Taft, “The function of a mental hygienist in a children’s agency”,I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f Social Work (pp.396-40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7, p.396.
h1=∑wiai=0.698561*0.6+0.725445*0.3+0.802354*0.1=0.764811
注释:
[8]H. Specht,New directions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 .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88, pp.42-43.
[9]R. Middleman & G. Goldberg,Social service delivery :A structural approach to practice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p.11.
[10]A. Pincus & A. Minahan,Social work practice :Model and method . Itasca, IL: Peacock Publishers, 1973, p.3.
再次,要有底线。中国共产党从民主革命时期走到现在,经历了各种艰难困苦,特别是在和平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使一些不良思想有一定抬头,这就要求思想的坚定和政治信仰的坚定就非常重要了。所以,这就意味着每一名党员必须要牢固树立底线意识,作为青年学生,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我始终坚守底线,要有自己的原则,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要立志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11]C.B. Germain & A. Gitterman, “The life model of social work practice revisited”,In J. Turner (ed.),Social work treatment :Interlocking theoretical approaches (pp.618-644).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6, p.619.
[12]A. Gitterman & C. B. Germain,The life model of social work practice :Advanc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3rd eds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2008, p.57.
[13]E. G. Goldstein, “Issues in developing systemic research and theory”, In Diana Waldfogel, and Aron Rosenblatt (eds.),Handbook of clinical social work (pp.5-25).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83, p.24.
[14][26]L. Dominelli, “Anti-oppressive practice in context”,In R. Adams, L. Dominelli, & M. Payne (2nd eds.),Social work :Themes ,issues and critical debates (pp.3-19). New York: Palgrave, 2002, p.4.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种族冲突中发展出来的增能视角,可以说开启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工作思维逻辑和理论发展取向,这一理论视角改变了以往社会工作把服务对象作为被动的帮助对象的想法,把服务对象作为自己生活的主角,认为增能不是他人给予的,而是自己给自己的,为此,还提出自觉意识(self-awareness)的概念,它是指人们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生活状况的自我觉察。[14]这样,社会工作的理论关注焦点就从服务对象的问题分析和指导转向了服务对象自觉意识的培养,而整个理论的逻辑就是围绕着如何提高服务对象在特定社会生活场景中的自觉能力,即增能视角所说的增能过程(empowerment)。[15]与此相对应,在对社会生活环境的理解方面,增能视角第一次尝试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人们的社会生活状况,把权力和资源分配不公等社会环境的特点引入到社会工作中。[16]这样,社会工作的理论探索从此走向了与系统和生态视角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发展取向:历史社会场景中的自觉意识提升。
[16]J. A. B. Lee,The empowerment approach to social work practice :Building the beloved community (2nd ed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34.
[17]D. Miehls, “Relational theory and social work”,In Francis J. Turner (5th ed.),Social work treatment :Interlocking theoretical approaches (pp.401-412).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404.
[18]C. Weedon,Feminist practice and post structuralist theory . Oxford: Blackwell, 1987, p.108.
[19]J. Fook,Social work :Critical theory and practice . London: Sage, 2002, p.70.
[20][28]K. Healy,Social work theories in context :Creating frameworks for practice (2nd edn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2,217.
这样,环境就不是个人意识中的环境,也无法完全由个人的意识来把握。尽管批判视角和反压迫视角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它们仍然认为,人是不可能跳出自己的生活经验站在“客观”的立场审视自己面临的困扰的,而需要通过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或者意识提升(consciousness-raising)等手段揭示主流描述中所隐藏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提升人们的自觉意识。[28]但是,实际上,环境之所以成为环境,它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总是超出人们的预计和经验。如果转到环境来理解就会发现,人们在场景中首先需要面对的不是反思或者审视自身的经验,而是学会面对和接纳场景中出现的意外。人们如何面对场景中的意外,如何开放自己,也就意味着人们站在什么位置反思或者审视自身的经验。而人们对自身的反思和审视与对未来的开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关注自身的反思和审视必然导致“为了反思而反思”,并不能够帮助人们超越当下场景中的个人经验的局限。
[21]T. Okitikpi & C. Aymer,Key concepts in anti -discriminatory social work . London: Sage, 2010, p.61.
[22]D. Clifford & B. Burke,Anti -oppressive ethics and values in social work .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14.
[23]M. Gray & S. A. Webb,Social work theories and methods . London: Sage, 2009, p.104.
[24]W. Devore & E. G. Schlesinger,Ethnic -sensitive social work practice (fifth eds.).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99, p.27.
[25]P. Sundar, “Multiculturalism”,In M. Gray and S. A. Webb (eds.),Social work theories and methods (pp.98-108). London: Sage, 2009, p.99.
赵仙童脸上露出一点笑容,连声道,听你的听你的,亲爱的,来,咱们总结今天你被打的经验,你最好能写到纸上,我们好好地讨论讨论。
[27]J. Fook,Social work :Critical theory and practice (3rd ed .). London: Sage, 2015, p.84.
[29]J. Gorman, “Postmodernism and the conduct of inquiry in social work”,Affilia ,1993, 8(3),pp.247-264.
[30]J. Fook, “Challenges and directions for critical social work”,in S. Hick, J. Fook and R. Pozzuto (eds.),Social work :A critical turn (pp.231-237). Toronto: Thompson Educational Publishing, Inc., 2005, p.233.
[31]J. Compson & L. Monteiro, “Still exploring the middle path: A response to commentaries”,Mindfulness , 2016,7(5),pp.548-564.
[32]S. F. Hick, “Cultivating therapeutic relationships: The role of mindfulness”,In S. F. Hick and T. Bien (eds.),Mindfulness and the therapeutic relationship (pp.3-18).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08, p.4.
2016年10月15日,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的武汉高等学校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高校要进一步转变理念,做到“四个回归”(分别是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1]。之后,在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等多次会议、谈话中,陈宝生部长都反复强调了高校(或高等教育)要做到(或推进)“四个回归”。“四个回归”以质朴的语言点醒了身处改革发展浪潮之中的中国高校,及时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敲响了警钟,也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提供了基本遵循。学习领会、贯彻推进“四个回归”在全国高等教育领域蔚然成风。
[33]R. D. Siegel, C. K. Germer & A. Olendzki, “Mindfulness: What is it? Wheredid it come from?”,In F. Didonna (Ed.),Clinical handbook of mindfulness (pp. 17-35). New York: Springer, 2009, p.34.
[34]童敏、史天琪:《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本土框架和理论依据——一项本土专业服务场域的动态分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35]杜维明、黄万盛:《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意义》,《求是学刊》 2005年第4期。
Deep Social Work :Revisiting the Theoretical Base of a Century of Social Work
TONG Min, XU Jia-xia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Social Work,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How to carry out deep social work is not only a practical problem, but also a theoretical topic, reflecting the widespread recognition of the profession. Although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y on social work has been going on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we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before reaching a consensus on the theoretical base of social work and often face challenges in terms of its depths of analysis. Thus, it is imperative to discuss how to carry out deep social work, especially in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Chinese social work.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a)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Western social work also faced the challenge of how to carry out deep social work; (b) since the 1960s, Western social work gradually has formed two schools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of how to carry out deep social work: one is to adopt ecological and systemic perspective, and the one is to use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 but they still suffer from limitations because of their personal stance; and (c) deep social work focuses on the promotion of individuals’ sense of practical reason, which is to raise self-consciousness in specific contextual practice. The conclusion provides a new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Western social work the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al work.
Keywords :deep social work, social work theory, social work history
中图分类号: C91-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8-0460( 2019) 03-0113-08
收稿日期: 2018-06-1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的场景实践与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理论体系建设”(18BSH151)
作者简介: 童敏,男,浙江永康人,厦门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许嘉祥,男,福建厦门人,厦门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社会工作实务研究助理。
[责任编辑:陈双燕]
标签:深度社会工作论文; 社会工作理论论文; 社会工作历史论文; 厦门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