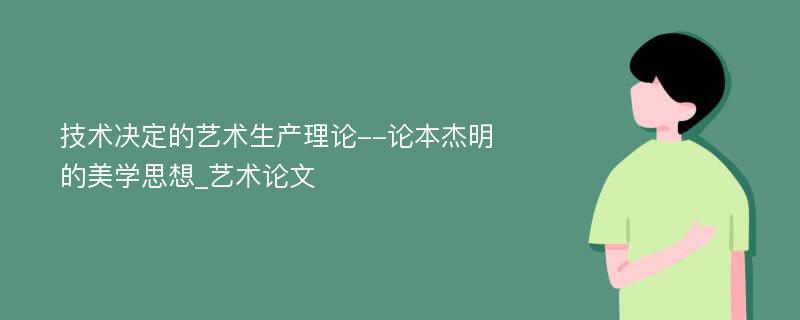
技术决定的艺术生产论——论本雅明的美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思想论文,艺术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 83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162(2007)06—0018—05
本雅明与其他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家一样,对现代资本主义文化持鲜明的批判态度,但他对工具理性的重视却使他的美学思想显得与其他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家有些不同,可以说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家中,只有他对现代科技以及与之相关的大众艺术给予了热情的肯定,这也使得他的理论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
众所周知,生产方式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概念。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著作中,是把生产方式当作分析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不同社会的重要尺度。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还曾从生产方式——即从艺术生产最终是受物质生产关系支配的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出发,对古今艺术的差异作过极富启发的著名分析。尽管如此,经典马克思主义在使用生产方式这一概念时,还是主要把它运用于物质生产范畴内的,只是偶尔地运用这一范畴来考察艺术的生产。可以说,真正有意识地把生产方式的概念创造性地运用于艺术领域的,本雅明应该说是第一人。本雅明与主张艺术自律的阿多诺与马尔库塞不同,他是主张艺术必须具有政治倾向的。在《作者作为生产者》(1937)一文中,本雅明不同意将政治倾向与艺术倾向相分离的见解,他说:“作品正确的政治倾向包含了它的文学质量,因为它包括了其文学倾向。”[1](P919) 本雅明的特点还在于,他所说的政治的倾向不仅是指思想的倾向,而且包含着更丰富的内容。正如本雅明指出的:“社会环境是由生产环境决定的”,因此,唯物主义的美学批评就应该考虑艺术作品与时代特有的生产方式有着怎样的联系,这种联系在他看来也是有着进步与落后的关联的。这就显示出了他与阿多诺等人的差异:阿多诺是贬低工具理性的,本雅明却不但不反对工具理性,而且他的思想中还明显地存在着技术决定论的倾向。这也使他在考察艺术生产的时候,独具慧眼地指出艺术的问题不仅关涉着内容与形式的问题,而且还有着技术的问题。在本雅明看来,具有文化含量的技术不仅是艺术生产的手段,而且本身还带有政治意味,它在特定社会关系中是带有着进步或落后的因素的。本雅明所说的技术(Ttchnik)中文中也有时被人译为“技巧”,从本雅明使用这个词的具体情况看,这个词确实具有汉语中“技术”与“技巧”的双重含义,具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
至于技巧的概念……它必须能使文学产品直接被社会的因而也唯物主义的分析所理解。同时,技巧的概念提供了一个辩证法的出发点,由此可以超越形式与内容的徒劳对立。再者,技巧这一概念,正确地表明倾向与质量谁决定谁的问题……所以,如前面我们说一部作品正确政治倾向因为它包括了其文学倾向也就包括了它的文学质量,我们现在就可以更确切地表明这一点,因为我们认为这种文学倾向在文学技巧上既司包含进步也可包含倒退。[1](P920)
在本雅明看来,在艺术生产中技术的因素是极为重要的。从一定意义上讲,艺术的技术因素可以说是艺术生产的生产力,它具有着改变艺术的形式功能,所以,本雅明才把这种技术进步的获得视作衡量艺术作品革命功能的标准。这样一来,艺术的政治倾向就不再只是一个政治观点的问题,还应包括着采用何种技术的问题了。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生产方式或关系是与生产力的变革紧密联系着的,在本雅明看来,技术的更新对艺术生产也是有着革命意义的,所以他强调“技术的更新应该受到重视”。这种对技术的重视是本雅明美学思想的重要特征,也正是这种对技术因素的重视,才使得本雅明对以现代技术为基础的现代艺术(摄影、电影等)采取了一种欢迎与开放的态度。
同样,正是因为对技术的高度重视,才使得本雅明对艺术生产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视界与认识。如果说艺术是生产,那么就不难发现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一样有个生产的流程,这个流程在本雅明看来就是由生产与消费、生产者、产品与消费者等多种要素所共同构成的,因而艺术生产本身,在他看来,同样是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制约。本雅明指出,在艺术生产过程中,艺术家就是生产者,读者观众就是消费者;艺术创作是生产,艺术欣赏就是消费,而艺术创作的技术则代表着一定的艺术发展水平。与物质生产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类似,本雅明指出,艺术技术构成了艺术生产的艺术生产力,而艺术生产中的生产与消费关系即艺术家与观赏者的关系,则构成了艺术生产关系。本雅明还根据马克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认为在人类的艺术生产活动中,艺术生产关系也一般地决定于生产力即技术,当艺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生矛盾时,也就是技术革命的出现的时刻——新的艺术技术产生了,艺术生产就必然要打破原有的生产关系,从而使艺术生产发生变革。所以,本雅明认为:“如果这个工具能使更多的消费者转变成生产者,即把读者和观察者转变成创作的合作者,这个工具就越佳。”[1](P924)
艺术生产的技术论可以说是本雅明美学思想的核心,他的许多美学论著都或显或隐地体现出这样的一种思路或精神。如果我们把本雅明的三篇论文《讲故事的人》(1936)、《论波德尔的几个主题》(1939)、《机械复制时期的艺术作品》(1936)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就不难发现艺术生产的技术决定论是如何地影响着本雅明对艺术生产与发展的见解。在这三篇论文中,本雅明把艺术家当作生产者,读者观众当作消费者,并以艺术生产中的技术因素为参照系,为人们勾画了人类艺术生产的重大变迁:首先是以乡村为特征的古代农业社会,这里存在着的是一种“手工劳动的关系”,由于还没有技术媒介的介入,艺术只能靠人的口头来传播,当时最具代表性的艺术样式就是史诗,史诗所传达的是集体的经验;而在以城市为特征的近代工业社会,艺术则以印刷为传播媒介,叙事艺术受到了重视,得到了发展,这时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就是有“近代史诗”之称的小说;而到了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传播的方式则主要转换成了机械复制,这时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则就变为了电影,于是经验的内容被经历的内容所代替。以上本雅明所勾画的带有宏观性质的艺术变迁图,无疑是以技术因素为主要参照系的,或者说本雅明充分地注意到了技术因素对艺术生产与转型所起到的关键性的作用,体现出了他的艺术生产与社会环境紧密关联的美学观念。这也是本雅明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美学家在一些问题上见解不一的原因。譬如阿多诺就不同意本雅明把艺术电影作为现代艺术来肯定,而更推崇卡夫卡等人的创作,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现代艺术,阿多诺显然是不同意把艺术生产的技术因素当作衡量现代艺术的参照系的。
我以为,要更好地理解本雅明技术决定的艺术生产论,就不能不重视他的代表作《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这篇被本雅明反复修改的论文在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本雅明美学思想的总结。在这篇论文中,本雅明从他的艺术生产技术决定论出发,对古代艺术的衰败与现代艺术的兴起作了极富启发性的独到研究。
本雅明敏锐地发现,西方文化发展到了当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艺术生产也随之产生了巨大的变革,他从他的技术决定论出发把当代称之为“机械复制时代”,并认为随着机械复制时代的到来,传统艺术正在让位给现代艺术,而这其中的最重要的表征就在于传统艺术所具有的韵味在现代艺术中萎谢了。需要指出的是,韵味(Aura;或译作“光晕”)这个概念在本雅明那里是一个含义复杂而模糊的概念,它同疏离感、膜拜价值、本真性、自律性、独一无二性等都具有着联系,本雅明用它来泛指传统艺术的审美特征。这也就是说传统艺术是一种有韵味的艺术,而在机械复制的艺术崛起后,传统艺术的韵味消失了,于是传统艺术开始让位给了现代艺术。
从上面的基本观点出发,本雅明对传统艺术与机械复制的艺术之间的不同作了敏锐的洞察与深刻的分析:他认为由于人造出的东西都是可以伪造的,所以从原则上讲,艺术作品就都是可以复制的,但是,当代的机械复制与传统的手工复制的性质却是明显不同的,当代的机械复制可以比传统的复制更“独立于原作”,因而这就使得它不必再把原作放在中心的地位。譬如,由于机械复制,音乐厅中的乐曲在卧室中也能听到了。其次,传统的艺术品还具有一种因独一无二而产生的本真性,但机械复制却可以把艺术摹本带到原作所根本无法到达的地方,因而原作的本真性也就变得不再具有太多意义了。譬如电影的拷贝,我们不必说哪个更为本真。正是由于这两个原因,就使得欣赏艺术就不必再像传统欣赏艺术那样要受制于种种时空条件的限制,而这就必然要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本雅明认为,正是因为传统艺术与机械复制艺术的上述两个重要不同,才导致了传统艺术的历史性的崩溃:
复制技术把所复制的东西从传统领域中解脱了出来,由于它制造了许许多多的复制品,因而它就用众多的复制物取代了独一无二的存在。由于它使复制品能为接受者在其自身的环境中加以观赏,因而它就赋予了所复制对象以现实原活力,这两方面的进程导致了传统的大崩溃——作为与现代危机对应的人类继往开来的传统大崩溃,它们都与现代社会的群众运动密切相联,其最有力的工具就是电影的社会意义即使在它的积极形式中也都具有着破坏性、宣泄性的一面,即扫荡文化遗产的传统价值。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2](P628)
在本雅明看来,传统艺术是有韵味的,也可以说韵味就是传统艺术的审美特征。但是,由于机械复制艺术的大量出现,即用先进的技术、机械手段进行大量复制的现代艺术品的出现,使得传统艺术消亡了,本雅明深刻地指出:“机械复制的时代凋谢的东西就是作品的韵味。”[2](P628) 而且,他还从四个方面对现代艺术中韵味消失的表征作了分析:首先,由于艺术可以大规模地复制了,传统艺术的独一无二的本真性消失了,原作的权威性被复制的无差别性取代了,而艺术传播的时空范围也前所未有地被扩大了。韵味本来是与艺术独一无二的本真性紧密相关的,这样一来,传统艺术的韵味就被机械复制的现代艺术品取代了。其次,表现在艺术的膜拜价值与展示价值的变化上。本雅明认为,传统艺术具有一种膜拜价值。艺术生产最初就是为膜拜服务的。如原始的巫术艺术,它们作为礼仪的存在价值显然是重于被观赏的价值的。而在机械复制艺术那里,膜拜价值却让位给了展示价值,这样艺术才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艺术品从它对礼仪的寄生中解放出来,使展示价值获得了主导地位,即艺术作品的价值转变为被展示与被观照,它们与受众形成了一种互动的关系。在这种艺术品的膜拜价值让位给展示价值的进程中,传统艺术的韵味随之凋谢了。再次,随着膜拜价值与展示价值的转换,艺术的全部功能都被倒置过来了。膜拜价值需要观者对作品有一种崇敬与神秘的感受,需要观者凝神观照沉湎于其中,这也就是说观众要被艺术品吸引,并在接受中唤起移情作用,达到净化的目的。而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不再建立在礼仪基础之上,而开始建立在另一种“实践——政治”的基础之上,它的观照方式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展示价值的消遣性接受方式代替了传统的接受方式。大众超然于艺术品,不再是移情于作品而是把作品吸收过来,如电影的接受就是通过片断的零散的镜头以及画面的蒙太奇转换,来打破观众常态的视觉过程的整体感,从而引起惊颤的心理效应,来实现激励公众的政治功能。第四,传统艺术追求的是一种永恒价值的形态,因为这样的作品是一次性的,不可复制的,如古希腊的雕塑就是如此。而当代艺术却不是这样,它是可以复制也是可以修改的,所以本雅明认为,雕塑艺术的消亡是必然的。在本雅明看来,机械复制的时代是一个“艺术裂变的时代”。随着诸如摄影、电影这些机械复制艺术的兴盛,传统艺术的衰败消亡是必然的,作为传统艺术审美特征的韵味也必然随着传统艺术的消亡而凋谢。本雅明本人对电影艺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认为作为现代艺术的电影,它并非面对观众表演,而是面对镜头表演,它展示给人们的是一个异样的世界和视觉无意识,它丰富了人们的观照世界的方式;它对现实的表现是通过强烈的机械手段,实现了现实中非机械的层面,现代人要求的正是艺术品展现现实中的这种非机械性层面,这个层面蕴含着现实中非异化的、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活动和变化。也正因如此,本雅明认为电影的出现是人类艺术活动中的一次革命。
这里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机械复制使得作为传统艺术审美特征的韵味凋谢了,那么,现代艺术的美学特征又是什么呢?本雅明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现代艺术以“惊颤”代替了韵味,这也就是说惊颤与韵味的对立所体现的也正是现代艺术与传统艺术的根本区别。作为一个美学概念的“惊颤”(Schocker fahrung),是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评论波德莱尔的诗作时提出来的。在本雅明看来,波德莱尔的诗是具有强烈的惊颤效果,以致“气息的光晕在惊颤经验中四散。他为赞叹它的消散而付出了高价——但这是他的诗和法则。”[3](P168) 那么,作为现代艺术审美特征的惊颤有哪些特点呢?结合本雅明对布莱希特与波德莱尔作品的评论,我们可以发现疏离性与费解性正是惊颤的两个重要特点。本雅明在评好友布莱希特的史诗戏时指出,布莱希特戏剧与传统的自然主义戏剧不同,后者是在千方百计地与观众亲近,不惜造出一种真实的幻觉,而布莱希特却使观众对戏剧“不是亲近的,而是疏离”,他引导观众跳出幻觉,而以极大的惊奇心情来看到剧情的真实,并以清醒的理性来反思剧情,这就使得剧作的意义“不是一开始,而是最后”才可以被理解。所以,本雅明把布莱希特的史诗剧说成“是姿态的”,是一种行动中静态的片断,而这种对行动打断是史诗剧的重要特征,这也就是所谓的间离技巧——它用陌生化的手法迫使观众对戏剧事件采取批判的间距的态度,而不是一味移情地认同,而是让观众意识到戏剧的存在,这也就是说,布莱希特的戏剧不是让观众得到传统式的被动的娱乐,而是要使他们成为评判者,就如布莱希特所说,“戏院里都是行家”,观众应该成为戏剧的二度创作者,而这种疏离性也就自然地增加了布莱希特戏剧的费解性。本雅明在评论法国象征主义大师波德莱尔时,对波德莱尔的抒情诗与传统单纯的抒情诗的不同也作了分析,他认为这位象征派大师在他的诗中加入了“反思性”,并使这种反思性上升到了诗的主导地位,从而增加了人们的阅读难度。本雅明指出,这种反思性也是惊颤的重要内容。因为读者在感受到作品惊颤效果的同时还必须对它加以更多地思考才能消化惊颤。在本雅明看来,惊颤与体验有关,就像经验与传统艺术有关。“惊颤的因素在特殊印象中所占的成分愈大,意识也就越坚定地成为防备刺激的挡板,它的这种变化越充分,那些印象进入经验的机会就越少,并倾向于滞留在人生体验的某一时刻的范围里,这种防范惊颤的功能在于它能指出某个事变在意识中的确切时间,代价则是丧失意识的完整性;……这是理智的一个最高成就;它能把事变转化为一个曾经体验过的瞬间。”[3](P133) 他还借助弗罗依德的理论来分析惊颤,认为消化惊颤的途径就是人们在先被激起的惊颤体验之后又去抵御现实的惊颤,所以惊颤因素的特点给人的印象越强烈,意识就越意识地成为反抗刺激的敏感屏障,因而在本雅明看来“消化惊颤是一个比获得惊颤更为重要的任务”,而这实际上也就是指波德莱尔的诗作具有着反思性或费解性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本雅明还指出,波德莱尔的诗作中的惊颤效果是与现代城市生活中人们的惊颤体验相仿佛的,是与马克思描绘过的现代大机器生产下工人的心理体验相对应。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使劳动者接受机械的训练而日趋机械化,工人的机械行为实际就是一种惊颤的反应,而本雅明认为现代艺术的惊颤“与工人在机器旁的经验是一致的”。本雅明正是通过了对上述两位艺术家作品的审美特征的分析,来揭示了作为现代艺术审美特征的惊颤的基本特点:就其艺术形式上言,它是以费解性与疏离性为其特点的,就其内容言,惊颤中则隐含着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深刻的批判。尽管本雅明与阿多诺等人对何为现代艺术上的见解有异,但对现代艺术惊颤的审美特征的看法,却又是与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批判精神完全一致的。
正像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本雅明的思想中是充满了矛盾的,他关注政治(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却不废神秘(受犹太教影响),他为技术进步大唱赞歌却又有浓重的恋旧情结(他对韵味的分析中就隐含这种复杂的心情)……这些矛盾在他的美学思想中都是有所体现的。但是本雅明的技术决定的艺术生产理论,我以为更多地体现出了马克思生产方式的思想对他的影响,可以说他的技术决定的艺术生产理论正是在这种影响下形成的,它的理论价值无疑是值得人们充分重视与研究的:首先,他的技术决定的艺术生产论把马克思有关生产方式的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艺术生产领域,他的艺术生产理论对人们宏观地把握艺术生产无疑是具有开创意义的。本雅明无论在论述古典艺术的终结还是现代艺术的费解方面,都注意考察造成文艺现象变化背后的时代、社会条件和阶级斗争状况,努力寻找其终极经济根源,试图把唯物史观贯彻到自己的论述中去。这是难能可贵的。这可以说是本雅明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个突出贡献。其次,本雅明用他的艺术生产理论考察人类艺术的变化发展,他运用的方法与一些结论也同样具有理论的启发性,特别是他对传统艺术韵味的消失、对机械复制时代艺术特点的分析都算得上既宏观而又敏锐、深刻。再次,本雅明从他的技术决定的艺术生产论出发,对机械复制时代艺术(电影等)的分析,使得他在法兰克福学派中显示出了一种独特性,这主要表现在对待大众文化的态度上。我们知道,阿多诺与马尔库塞都是坚决反对以现代技术为手段的大众文化的,他们所推崇的现代艺术实际上是指卡夫卡们的先锋派或先锋艺术。阿多诺就曾批评本雅明,说以现代技术为手段的电影所体现的恰恰不是韵味的消失,而是使韵味更浓了,而真正没有韵味的是卡夫卡们的作品,卡夫卡们的作品才是真正的现代艺术。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家中,只有本雅明对包括电影在内的现代大众文化给予了积极的支持,这一方面与他本人的技术决定论有关,一方面也表现出了他对现代的艺术生产与发展的深刻洞察与高度敏感。事实上,他提出的诸如“作者作为生产者”、“观众作为消费者”、“复制”、“韵味的凋谢”等美学概念,无不深刻准确地揭示了现代大众文化的基本特征,因而这也使得一些学者坚称本雅明才是后现代的真正鼻祖,而这也正说明了本雅明美学思想中潜藏着的理论活力[4]。
[收稿日期]2007—06—12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世纪西方美学史”(06SJD720008)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