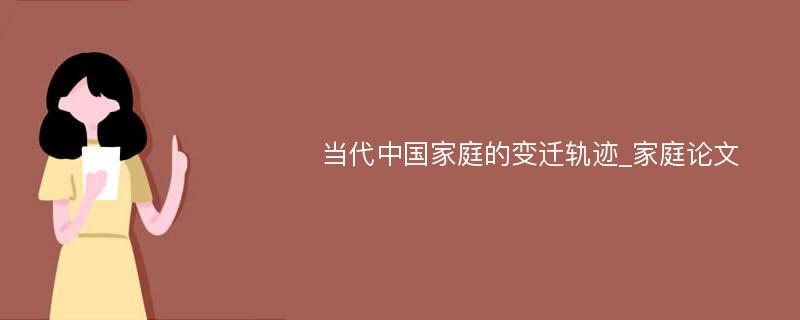
当代中国家庭的变动轨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中国论文,变动论文,轨迹论文,家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制度变迁的快慢基本上是与社会变迁的快慢相吻合的。当代中国的家庭经历了时急时缓的波浪式发展轨迹。1950年《婚姻法》的颁布促使大多数包办婚姻解体,提倡婚姻自主。但在随后的时间内,从整体上看,人们的家庭观念和婚姻行为并没有多大的改观。80年代以后,急速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促使当代中国家庭无论是在实体方面还是在观念方面都处在巨大的变动之中。
一、家庭结构由紧到松、由单一到多元
从量上看,外显为家庭规模的逐渐缩小。
一是户均人口数下降。
从20世纪初到40年代末,根据官方统计的家庭平均户规模大致保持在5.17~5.38人左右(注:参见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解放以来,家庭平均户规模经历了一个小——大——小的发展过程。50年代初由于家庭户的迅速增加(分居另过、立户为主),导致家庭人口规模下降。1953年户均人口数为4.33人,与1947年相比下降了19.07%。随后逐年增多,除去“大跃进”这段特殊时期,家庭人口规模的扩大态势一直保持到70年代,1974年户均人口发展到了4.78人(注: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年)》。)。70年代末到80年代以后,计划生育政策发挥了效果,人口自然增长率不断下降,小家庭的比重逐渐上升,使得户均人口数逐年下降,1998年降为3.63人(注: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总体上基本维持在2~4人之间。
二是家庭结构核心化。
累世同居是传统的理想家庭模式,直系大家庭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动力作用下,伴着家长制的削弱与瓦解,联合家庭已失去了存在的现实基础而逐渐趋于消失。主干家庭则保持着相对稳定,基本保持在20%左右,并有下降趋势,1990年人口普查结果表明,全国城市家庭三代户占15.4%。农村的比例相对要略高一些。而核心家庭则逐步得到巩固和扩大。50年代核心家庭占各类家庭总数的比重为50%,70年代上升为58%,1987年上升至71.34%,1990年则达到77.12%(注:张建、陈一筠主编:《家庭与社会保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页。)。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小型化已成趋势。
三是家庭类型的多样化。
1.“联合国”式的家庭增多。在1978年前后,中国的跨国婚姻完全是凭领导的开明来解决的,数量很少,1979年涉外婚姻及我国内地与港澳台结婚数仅为8460对。跨国婚姻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社会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择偶的范围相应扩大,跨国婚姻发展速度飞快。1982年上升为14193对,1990年为23762对,1997年已达50733对(注:资料来源:民政部《婚姻登记情况》。)。通婚圈已扩大到53个国家和地区。一般而言,这些“联合国”式的家庭具有以下特点:(1)通婚范围以亚洲为中心向欧洲扩展;(2)通婚方式外嫁多娶进少;(3)通婚目的由功利型向感情型过渡;(4)通婚年龄差距渐小,平均年龄差已降到5~6岁。
2.丁克家庭有所上升。双收入、无子女的家庭不是中国家庭的主要形式,一直保持着较低的比例。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竞争的加剧以及婚姻观念的更新,丁克家庭的比例逐年上升。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当时夫妻家庭仅占全国总户数的4.78%;在1990年的人口普查中,一对夫妇户占6.5%。以上海为例,1979~1989年期间结婚的113万对夫妻中,大约有16万对夫妇没有生育孩子,占结婚数的14.3%。减去其中一些再婚不生育的、由于生理原因不能生育的人数,具有生育能力而不愿生育的夫妇占全市家庭夫妇总数的3%。进入90年代以来,这样的夫妇人数有增无减。
3.单身家庭降中有升。随着婚姻被重新定义,人们已不再需要在社会压力之下,在找到真正合适的人之前就去结婚,“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把结婚看作是人生任务的传统观念,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摒弃,婚姻已成为一种可选择的生活方式。90年代以来随着年轻一代自立程度和女性就业期望值的提高以及婚姻消费的膨胀,平均初婚年龄呈推迟趋势,“单身贵族”已在一批高学历、高收入、高职位的青年中蔓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女性。
4.空巢家庭增多。社会老龄化和家庭规模的缩小,以及独门独户的居住方式导致了“空巢家庭”的大量增加。据1992年中国老龄科研中心对全国12个省市的一份调查,老人中一代户的比例,城市达到41%,农村达到43%(注: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汇编》,华龄出版社1994年版。)。调查表明子女与老人分居的倾向加大,老年夫妇家庭增加,空巢家庭愈来愈多已是不争的事实。
此外,非婚生育的单亲家庭、未婚同居家庭、一人独居家庭、再婚家庭等都有增多的趋势,家庭形式将由核心化向多样化的趋势发展。
从质上看,内化为家庭关系由不平等向平等过渡。
首先,在代际层面上的父子平等、母女平等。社会变迁的加快,导致文化的继承机制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同喻文化”和“前喻文化”取代了“后喻式继承”,长者在财产和能力方面不再具有绝对的优势,子女对父母的依赖性逐渐减弱,因而尽管父母对子女(尤其是未成年子女)的生活发挥着相当的作用,但已不再充当拥有绝对权威的角色,这主要表现为:在婚姻决定权上,包办婚姻已没有市场,婚姻自主已深入人心,越是年轻,由亲友介绍和自己结识的比例越高,父母的影响力大为减弱;在对待子女的教育上相对宽松,孩子们的行动自由度加大;在对待长辈的态度上,一味地迁就、顺从已成历史,亲子关系日趋平等,家庭气氛也趋于民主。据1997年对京沪510位13~19岁青少年的调查,50.5%的青少年认为父母比较尊重自己的意见。
其次,在性别层面上的夫妻平等。社会的构成、体制和文化观念的变化导致了婚姻观念、婚姻状态的变化,改变了家庭内部的夫妻关系,家庭中的权力逐渐从男性集权向夫妻平权过渡,主要体现为:(1)家务分工的公平性。现今“甩手丈夫”越来越少,夫妻之间逐步趋向合理化分工。(2)家庭决策的协商性。家庭中,在重大礼仪活动的操办、大宗消费品的购买、馈赠礼品、家庭投资、住房的选择、子女入学和职业选择等事务上,夫妻共同商量、共同决定的比重为最高。(3)家庭经济的民主化。家庭日常经济支出的管理不再是妻子享有的特权,由丈夫管理或共同管理的人数逐渐增多。夫妻双方消费支出基本持平。妻子经济相对独立,甚至有些家庭出现了AA制、婚前财产公证的现象。(4)闲暇生活的独立性。随着家务劳动逐步社会化、科学化,家务对于女性来说不再是“西西弗斯”的折磨,女性逐步从操持家务的羁绊中解脱出来,夫妻双方特别是年轻夫妇之间平等地享受闲暇时间,女性也得以在家庭中发展自己的兴趣。
二、家庭功能由家庭走向社会
传统中国的家庭作为社会的中心,承担了大部分的社会功能,如经济、宗教、教育、娱乐等等。然而,近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变革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家庭功能的重大变化。
1.生育功能逐步退化。中国传统的宗法观念和“多子多福”的信仰带来的是生育功能的强化。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凭借其所拥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资源,来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从而使生育不再仅仅是家庭的私事,而具有了社会性。
1954年国家曾提出节制生育的口号,但并未真正把人口再生产纳入国家计划而加以控制,生育习惯仍得以维持和发展,导致人口出现波浪式的增长,50年代和60年代分别出现了两个生育高峰,1965年人口出生率高达37.88‰,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高达28.38‰(注: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4年)》。)。
70年代末,国家在全社会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正式将人口再生产列入国家计划,家庭的生育功能不断削弱,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由1987年的19.68‰降至1998年9.53‰的平均水平(注: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年)》。)。在城市,新婚夫妇生育第一胎后基本上都领取了独生子女证,甚至婚后不要子女的家庭也日趋增多,1998年城市人口出生率为13.67‰,自然增长率为8.36‰(注: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在农村,人口出生率也有缓慢的变动,生一孩的家庭越来越多,1998年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0.04‰(注: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年)》。)。人口生育率的下降,预示着家庭生育功能的退化。
2.生产功能从丧失到恢复。传统的“男耕女织”点明了传统家庭是一个经济生产单位,家庭的生产功能占有统治地位。从50年代开始,公有化把生产功能从家庭转移到社会,中国传统家庭的生产功能基本上丧失殆尽。
70年代末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90年代的城镇私有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家庭生产功能的恢复。但是,这种恢复并不是简单的重复。首先,具有生产功能的家庭毕竟数量有限,截至1998年,个体企业数为603.38万个,占企业单位总数的一半,产值为20372亿元,仅占工业总产值的15%左右(注: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其次,这种生产是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归家庭所有的社会化大生产,家庭的生产职能越来越社会化了。以上海为例,到1990年,上海郊区各乡已全部建立专业的或综合性的农副业服务公司,80%的村建立了综合服务组织,传统单一的小农经济已逐步向多种经营、集约化和产业化过渡,家庭生产功能的发挥越来越离不开社会的协调和支持。
3.消费功能由平均到多元。家庭是一个基本的经济消费单位。建国后30年间,在“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下,从生产、分配到消费都由国家统一调配,而且计划消费的范围在总体上一直扩大。据上海市商业一局系统统计,1972年凭证供应的日用工业品多达87种,人们普遍过着有保障但不富裕的生活,到1978年,全国居民的食品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高达60%。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的持续发展,收入的不断增加大大提高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总体上进入温饱阶段,并向小康生活迈进。与此同时,消费层次迅速提升,由生存型向质量型转变,消费结构日趋合理,消费热点层出不穷,消费行为更趋理性。据1999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居民用于吃、穿、住的消费比重为63.8%,比1995年降低11个百分点;恩格尔系数由1997年的46.4%下降到44.5%;非消费性支出高速增长,1998年人均支出987元,比上年增长30.6%,其中购房与建房支出额高达411元,占实际支出的7.7%;享受与发展资料需求逐年增长,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成为消费热点(注:参见《中国物价及城镇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统计年鉴(1999)》。)。虽然消费方式的多元化得到了空前发展,但对于大多数城镇家庭而言,量入为出、勤俭持家仍是家庭消费的基调。而对于大多数农村家庭来说,仍存在着消费不足的经济矛盾,近八成的农村居民年生活消费支出还不足2000元。
4.赡养功能弱化。在传统中国,赡养老人既是一种传统,也是一种制度。但在现代化的推进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过程中,家庭养老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传统共居”模式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家庭的赡养功能。在城市,有分居子女者占老人总体的50.67%,占有子女者老人的51.36%;在农村,有分居子女者占老人总体的48.66%,占有子女者老人的49.88%(注: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汇编》,华龄出版社1994年版。),因此,传统意义上的养老将发生瓦解和分化,养老越来越具有社会意义,养老功能在家庭和社会之间的转移、互补将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5.教育功能分化。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家庭是子女社会化的重要场所,虽然有“私塾”和家庭教师,但基本教育是由家庭来承担的。建国后,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发展,削弱了家庭的教育功能,使之逐步走向社会化。然而,80年代以来,家庭规模小型化使独生子女逐渐普遍化,造成了家庭重心的下移,第三代日益成为现代家庭的关注焦点,“子女优先”和“子女偏重”的观念开始左右家庭关系,家长对子女的成长倾注了全部心血,从胎教开始到家教的出现,无不体现家长对子女教育的关心和重视。因此,虽然教育更多地是在社会中完成的,但家庭辅助教育作为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补充,将要延续相当长的时间。
三、家庭观念由浓转淡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成员的价值观念开始更多地向个人倾斜,家庭观念从“家本位”向“人本位”转移,由“家庭至上”逐步向“社会至上”过渡。
1.择偶观的变迁。择偶观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晴雨表。
1949年以前“门当户对”、“亲上加亲”是主要的择偶标准。50~60年代,人们往往重视职业的社会政治地位,政治面貌、家庭出身及社会关系成了择偶首要考虑的标准,“工农兵”一度走俏。到了70年代,人们开始注意物质条件,海外关系、房子等成为重要的考虑因素。80年代初,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下,个人学识曾经成为人们择偶的主要标准。但是随着经济的选择越来越占据重要位置,择偶标准出现了向传统回潮的现象,女性关注于男性的职业和地位,而男性则偏向于女性的漂亮、温柔等特征。到了90年代以后,随着人们的物质生活不断改善,婚姻开始由追求功利向追求婚姻质量转变,择偶标准也是多元标准,虽然“物”化因素仍占据重要地位,但在择偶过程中更多地体现出了“人本”精神,越来越注重人的情感、品质及能力。“谈得来”、“情投意合”,是90年代青年的口头弹。
2.生育观的更新。在自然经济时代,子女是一种财富,也是一种保障,在“传宗接代”、“养儿防老”观念的支配下,人们普遍多生,而且由于遵循男性继嗣的原则,往往重男轻女。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孩子不再是经济财富,多子多福的观念逐渐淡化,“少生、优生、优育”及“生男生女都一样”的观念为大多数家庭所接受。同时,现代避孕技术和避孕药物的引进和发展,使生育成为可供选择的行为,性与生育的相分离,也使计划生育成为可能,促使传统的“传宗接代”的生育观大为改观,目前,中国已婚妇女的避孕率达83%,有的地区达到90%以上,无生育的婚姻数量逐年增加。
3.孝道的重新诠释。现代意义上的家庭伦理是对传统伦理价值的扬弃。孝道在经历了众多波折之后被赋予了新的涵义,处在不断地完善与完备之中。首先是孝顺父母、尊敬长辈被继承了下来。2000年在天津完成的一项调查表明,90%以上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已不同程度地继承了孝顺长辈的传统,主要表现为:一是将自己每月收入的一部分固定用于老人消费;二是在日常生活中主动替父母分忧;三是尊重老人权利,对老人丧偶后再婚持开明态度。其次是顺从父母,但不盲从。崇老文化的转变,为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养老方式开辟了道路。
4.性观念的多元。谈性色变将成为历史,当代人的性观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对性越轨行为的宽容度增加。90年代初全国两万人的性文明调查资料显示,男大学生有性伴侣的占全部男生的12.5%;女大学生有性伴侣的占全部女生的6.03%。在被调查的622名大学生中,454名男大学生中有性伴侣的占52.4%,女大学生中有性伴侣的占48.2%。近几年婚前性行为更是有增无减。1997年进行的《全国大学生异性交往》的调查中,有过性行为的占78.2%。而且,据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表明,有64.8%的人对婚前性行为持肯定态度。此外,近年来,社会环境趋于宽松,人们对婚外恋的态度也渐趋宽容。
5.离婚观的改变。1949年以后,政治解放带来了婚姻和妇女的解放以及家庭的革新。1950年的《婚姻法》以法律为依据保障离婚自由,随后引起了一阵离婚浪潮,1955年申请离婚的夫妇人数猛增到507777对。如果说50年代的离婚更多的是肃清封建遗毒的话,那么,文革期间出现的离婚浪潮则隐含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原因多数属于“划清界限”或“反戈一击”。
尽管如此,在建国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离婚率是相当低的,这并不是因为婚姻质量高,而是离婚存在着一定的障碍:一是政治的干预。在传统观念中,离婚问题更多地被视为道德问题,高离婚率被当作是资本主义社会腐朽性和家庭崩溃的象征,因而离婚往往被视为是一种不道德不光彩的行为。二是责任的压力。在人们的观念中,孩子是脆弱的,是依存于父母的,一旦父母婚姻破裂,子女必然会遭受不幸,因而不少人为了子女而维持着失败的婚姻。
从80年代开始,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对婚姻问题的认识也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从一而终”的传统观念受到了严重的冲击。1981年新婚姻法实施以后,为解除“死亡婚姻”而导致的离婚比例逐步上升,传统的家庭平衡被打破了,离婚成了那些感情不和的夫妻追求自由、获取幸福的一种方式。较之过去,无错的离婚增多,因爱情转移的离婚增多。从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数量来看,1990年为81万多件;1991年为86万多件;1994年为103万多件;1997年为124万多件;1998年后呈略降趋势。在离婚案中呈现以下特点:一是离婚人口低龄化和中老年人的离婚增多同时并存。二是离婚中的家庭压力和社会责任约束逐渐减弱。三是农村离婚势头上升。四是协议离婚比例增加。
家庭在合乎规律地变动着,这种变动既有程度上的不同,又有方向上的差异。但是,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落后地区的家庭变革将缩短与前导趋向的差距,最终推动着中国的家庭变革沿着富裕、健康、和谐、贡献的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