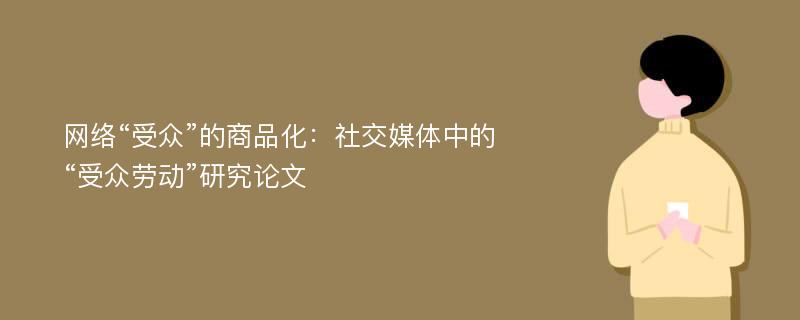
网络“受众”的商品化:社交媒体中的“受众劳动”研究
徐 颖,范和生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 要: 新媒体时代里,资本剥削的逻辑从现实物理空间延伸到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互联网产业,越来越多的网络受众成为推动互联网产业发展的“商品”与“免费劳工”。从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后现代社会学理论角度,揭示社交平台上受众参与、受众注意力投放、受众需求管理的劳动形式及其商品化中的资本剥削本质,思考与审视受众劳动与受众商品化背后映射的家庭与社会的工厂化、时间的殖民化、受众主体性弱化的现实困境,以提高受众对数字资本主义渗透的警惕。
关键词: 网络受众;社交媒体;资本;受众劳动;受众商品化
伴随着web2.0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不同媒介文化样态以及受众形态的变化推动数字劳动与互联网产业的兴起与发展,社交媒体成为资本产业扩大再生产与网络受众劳动实践的场域,受众劳动和受众商品成为新的劳动形式与商品形式及普遍化的社会经济现象。基于社交媒体平台的数字劳动对受众劳动的转化,一方面促进信息资源在社会范围内的实时共享,最大限度激发个体用户的积极性、创造性,开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空间,另一方面社交媒体的不断升级成功地将网民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转化为具有数字资本增殖效用的舞台表演。网民在社交平台上消耗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的传播与互动成为一种具有潜在商业价值的劳动形式,其无酬生产的视频、图片等媒介内容被平台资本产业转化成用于出售与交易的数据商品,受众的劳动剥削问题日益凸显。在这种现实背景下,亟需厘清受众劳动与商品化中的资本生产逻辑及受众面临的现实处境。
一、相关文献回顾
数字化时代里,移动终端、网络化大数据改变了传统的劳动形态,使得劳动分工趋向多元化。[1]有关劳动属性、劳动异化、劳动剥削等议题学术界早有研究。首先,劳动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核心概念以及理论基础,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下,劳动被认为是人和自然之间接触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为中介,调整和控制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的过程。[2]马克思理论框架中的劳动始终是基于自然空间的物质生产性活动。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电视、电影等传播媒介的兴起与发展,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W Smyth)最先提出“受众劳动”(Audience Labor)的概念,指出欧洲马克思主义研究存在的“盲点”,即没有对传播体系的经济作用给予足够的关注,忽略了传播产业尤其是受广告支持的传播媒体所产生的一种特殊商品—受众。斯麦兹认为在闲暇时间收看电视、阅读报纸的“受众”实际在为广告商工作,大众媒体主要目的是生产学习消费的观众。[3]斯麦兹受众理论的提出极大推动了劳动议题研究角度的多元化。随后,文森特·曼泽罗尔(Vincent Mineral)在斯迈兹受众理论的基础上揭示大众传播媒介是工业资本主义系统性的产物,具有生产商品价值的工具型属性。[4]比利文特(Bill Levant)、萨特·杰哈里(Sat Halley)以及米汉(Meehan)以有关马克思研究的“盲点之争”为出发点,在传统媒介的时代背景下围绕劳动议题展开讨论,[5]由此奠定了劳动研究的起步阶段。
互联网传媒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传统劳动行为和劳动类型发生巨大的变化,与互联网相关的劳动形态相继出场。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学者特拉诺瓦首次提出“数字劳动”的概念,他指出,受众的免费劳动在数字经济的环境下已经从文化知识消费转化成生产性行为,即数字劳动。近年来,数字劳动、免费劳工等议题成为学界尤其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热点。国内对劳动议题的研究主要从传播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劳动观角度探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劳动剥削、数字劳动、受众商品化问题,汪金汉从思想史角度出发,揭示商品经济交换的逻辑到数字资本剥削问题的劳动议题的发展脉络,[5]刘皓琰、李明指出网络生产力下新型经济模式对劳动关系的影响与数字劳动的本质。[6]通过国内外文献梳理发现,对于劳动议题研究角度主要集中于传媒、经济和政治,研究角度比较单一化。因此,在以往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基础上,利用后现代社会学理论视角,有助于分析和透视社交媒体中的受众劳动问题。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正确的思想才能引导人们进行积极的行动。要切实体现思想文化的重要性,让其成为引领工作的旗帜与标杆,应该按照从实际中来到生产中去的原则,用思想教育进一步密切干群关系,不断提升工作作风,切实在接地气、流汗中与员工打成一片,成为履职尽责“真干事、干成事、会干事”的员工贴心人。
1978年至今,广东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6%,比同期全国平均增速快3.1%,比世界平均增速快9.7%,经济总量连续29年位居全国第一。[15]2017年,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9879.23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81089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36倍。[16]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广东也积累了区域发展非均衡这一突出的问题。
二、社交媒体中受众劳动的表现形式
众多年轻用户在微博、微信、抖音等社交平台上分享心情、表现自我、管理人际关系的微劳动被纳入生产消费的经济链条中去,在这个经济链条中,受众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受众本身是价值的代表,社交媒体平台利用受众与广告商做潜在的价值交换,双方基于受众劳动的“价值网”与媒介用户关系的商品化获取经营性利益创收。同时,社交媒体平台上强关系与弱关系连接的使用价值,进一步强化受众与媒体的关系结构与用户黏性,构成资本价值传输与价值生产的一部分。
(一)“积极受众”的参与
新的媒介技术打破现实物理空间的阻隔,在互联网的“关系赋权”下建构网民身体缺场的公共话语空间,在参与式文化背景下网络受众摆脱传统意义上的媒介消费者及被动的信息接受者的身份定位,自由创作与传播各种形式的媒介内容。斯麦兹将媒介视为由特定生产关系组成的生产场域,媒介使用者则是媒介生产场域中的劳动实践者,媒介在受众劳动与资本市场的融合中起到重要的连接作用。[7]社交媒体既为受众提供参与互动与表演的多元化舞台,又为个体的情绪释放、才能发挥及沟通交流带来巨大的便捷,极大调动受众参与的热情与快感体验。受众在物理空间内的一切感知通过社交平台转化成虚拟主体性建构的表现形式。(浏览或创作在线视频、更新用户个人主页、发布文贴)平台化的运营模式很大程度上依靠受众参与来实现劳动力的释放与转化,受众越是积极参与,媒体平台获得用户的爱好、社交兴趣取向等数据或劳动性成果越多,用于与广告商进行市场交易的价值份额越高。
(二)受众注意力的投放
克里斯蒂纳·富克斯(Christian Fuchs)将“数字劳工”的剥削形式分为三种,其一,强迫性:网络化、数字化的信息社会背景下,受众不得不接触与使用互联网。其二,异化:互联网产业通过用户信息机制掌握用户数据,并将其转化成数据商品。其三,生产者和使用者的双重商品化:使用者本身沦为商品,其生产的信息同样沦为商品。[11]用户尤其是网红或明星在社交平台上的衣服穿搭、美妆示范、身材皮肤管理、才艺展示、好物推荐等私人经验的暴露与生产性劳动为资本的积累提供价值增长点。“口红一哥”李佳琦在具有7亿用户数量的抖音平台上拍摄上传关于各类品牌口红的上妆效果及购买推荐的短视频而吸引大量受众观看,并迅速爆红,其粉丝数量已达两千多万,成功吸引了不少美妆广告主。广告商正是通过赞助社交平台,购买用户在线使用的流量和内容的监控、私人经验的大量转载而将采集的用户数据进行技术分类和处理,从而获得用户行动的大致依据,以便于广告向特定受众群体的投放或直接引导受众自主推广,形成整套闭环式营销模式。
(三)受众的需求管理
经过渡电阻接地是指短路点与地之间短路电阻数值较大,如图1.2。常见的有经超高树木放电接地等。经过渡电阻接地时故障点的边界条件需要引入等效的过渡电阻[1]。
网民被网络技术赋权了操控社会传播资源的能力,社交媒体必须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和心理宣泄需求才能建立稳定的资本生产关系。新媒体技术的加持和信息共享的媒介环境使得受众可以自由选择在社交平台上发布各种图片、视频、文本等媒介内容,传播与互动的即时体验效果刺激受众不断产生新的交往需求与下一轮的自觉劳动实践。[9]需求管理(Demand Management)是受众产生的真正劳动力,受众生产的对象分为生产劳动力与生产需求,生产需求依赖受众在媒体空间里的参与及观看行为,媒介资本将受众观看的能力和观看时间引入资本流通和生产过程。受众基于UGC(用户生成模式)将身边的人或事拍摄并上传,获得点赞和转发,以满足“被关注”的自我认同与自我成就感。因此,受众的好奇心、追求个性等特定的心理需求不可避免地被纳入资本价值创造的象征性指标体系中,通过商品经济逻辑的中介效应将需求操作化为有意识消费的参与行动与劳动实践。
三、社交媒体中受众的商品化
在各类社交媒体平台上,网络受众不仅是观看者,同时也是媒介内容的生产者与传播者。受众的观看行为被数字资本转换成信息,日常生活中积累的私人经验在福柯笔下的“全景敞视主义”的结构中成为可规模化生产的商品,即量产式“二手经验”。以具有强互动性与社交属性的抖音、快手等社交平台为例,首先基于用户的性别、年龄、爱好、地域等个人信息的同意授权而赋予用户平台号的身份代码,随后依据用户活跃度、搜索内容与浏览的兴趣意向等数据指标,对受众进行暂时分类以方便向受众推送符合其爱好的内容,为受众私人经验的传输提供基本可能。
身处于福建教案漩涡中心的艾儒略,是继利玛窦之后,最为著名的耶稣会传教士,他在福建传教事业的成功不仅应当归功于耶稣会的“合儒”政策和其过人的学识及宗教献身精神,更应当功于福建官员和大量底层知识分子和教徒的支持[注]艾儒略在闽交往的人物达到200多人。林金水:《艾儒略与福建士大夫交游表》,《中外关系史论丛》1996年第5辑,第182—203页。。
(一)用户私人经验的商品化
当下,众多社交媒体采用UGC(用户生成模式)与PGC(专业生产内容模式)结合的模式,以提升受众对平台的关注度和扩大“受众商品”的生产。各种知识和艺术创作被资本市场赋予交换价值。[10]基于此,社交平台上受众的私人经验、情感投入及社会关系在媒介资本的营销技巧中走向商品化。
詹姆斯·韦伯斯特(James Webster)将受众、内容提供者、测量提供者建构成注意力市场,新媒体时代非线性的产消模式代替传统的线性传受模式,网络平台上免费劳动的实践依赖于受众注意力的吸纳。[8]互联网时代受众注意力的碎片化与部落化使得各类社交平台为增强受众注意力,往往通过“价值共创”、建立以用户为中心的客户关系和受众共同体的构建来吸引受众的网络化参与的劳动。微信朋友圈内三天或半年可见的权限设置、表情包更新、“跳一跳”等小程序的推陈出新以及网红或明星的刷屏广告、某个热点事件的讨论等都,不同程度地吸引受众的注意力。社交媒体作为资本剥削的重要工具与基础设施,将收集到的受众注意力转化为用于交换的信息商品,受众注意力投放的劳动形式及其网络化生存状态潜移默化地固化受众与社交媒体之间的资本价值联系与关系结构,网民的日常社会性时间最大限度地被网络资本吸纳,以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促使网络受众积极主动前往社交平台参与分享个人的生活场景、话题讨论、商品体验与消费。
(二)情感投入的商品化
传统共同体纽带的断裂、现实人际关系的空间移植,受众徘徊于不同媒介类型中。正如亨利·詹金斯所言,受众已变成媒介文化空间里的游牧民、“大规模平行文化”中的文本盗猎者。[13]资本的逐利性驱使其与广告商联手对网络社会里“产消合一”的受众采取各种营销技巧,将现实社会中“硬广告”的投入与网络空间中“软广告”的隐蔽投放同时进行。在掌握受众行为取向的统计数据基础上,将美妆、服饰、食品、旅游等领域的广告植入受众的朋友圈动态中,增添他人对广告的视觉印象,减少了商品流通的时间及库存成本,潜在培养受众及其交际圈内人群的消费动机。另外,根据受众的多元化的心理需求,刺激受众自觉在微信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平台转发广告、积攒点赞量。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转发即是一种劳动实践,受众在转发过程中完成自身的欲望需求与广告商传达的意识形态的统一,即经济过程和价值创造过程的一致性。
用户在扩大人际交往范围、输出情感劳动的过程其实质为劳动与商品化过程,只有用户之间相互合作,数字劳动才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受众在活动参与中培养的工具性情感纽带促进网络圈群的产生,集群化的网络社区相比零散的受众更有规律创造商业价值,如明星粉丝社群。媒介平台利用受众参与式社交的快感体验、情感满足等表象遮蔽数字资本对受众互动行为劳动化、商品化及无偿剥削的事实性存在。网络受众劳动的异化加速其情感投入的商品化,情感异化为商品,服务于商品价值的转换。
(三)社会关系的商品化
网络受众的精力、接受和传递信息的内容随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变得更加碎片化,互联网时代的技术驱动力有效满足受众的身份认同渴求、碎片化的情绪释放和话语表达。另外,身体缺场的特殊交往形态、人声画实时互动及交往时间的随意更换,促进网络受众主体性和情感性两方面体验高度达成,同时也为网络受众情感的商品化提供资本增殖的契机。以部分社交平台中的网络直播为例,观看直播的受众基于家庭、职场、生活、社会热点话题的在线交流与主播产生情感共鸣,并通过弹幕和礼物赠送强化其社交互动,主播根据受众个性化需求采取深层表演(Deep performance)代替真实表达的情感管理策略实现有效的在线沟通,主播作为情感服务生产者,在关注、点赞、提问的符号互动中即时进行情感消费。同时,受众在参与式消费实践中以数字劳动形式回馈主播的情感支持。[12]伴随着互动双方情感能量的积累,受众的时间与经济资本投入往往成正比,由此推动形成以受众娱乐与粉丝情感为重要生产力的以“粉丝经济”和“共享经济”。
在Web2.0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承担经济型生产工具和社会型生产工具的双重属性,依托受众劳动的价值实践,形成了以平台为中心的用户数据生产的非线性产消模式。社交平台上积极受众的参与、受众注意力投放、受众的需求管理构成一种可以获取利益的劳动形式,作用于资本价值的生产与流通等环节。
四、“网络受众”商品化的社会性困境
(一)家庭与社会的工厂化
数字资本主义的扩张不仅依靠现实物理空间的建构与生产,也需要网络社会关系空间的支撑与扩展。网络受众的商品化凸显家庭与工作场所界限的模糊,家庭和社会成为受众劳动的日常场所与非实体形态的工厂,并以受众商品和受众劳动为核心产品,传统社会的物质生产转化为思想意识生产,平台化的运营模式依靠各种媒介,以散点形式向家庭和社会的关系网络逐层侵入与渗透。根据鲍德里亚“内爆”(implosion)的观点,“内爆”指事物边界的消退和各式各样的事物崩溃(collapse)混杂在一起。[14]资本生产的逻辑向没有实体边界的家庭和社会扩散,其结果导致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身份界限在数字媒体时代变得模糊,消费者在家庭场所登录社交平台制作与发布图片或视频、习惯性发表个人评论、点赞,无意识地为资本市场价值增值做无偿劳动与贡献。数字资本根据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将家庭和社会作为其基本的生产单位,并以媒介平台为工具和手段,无偿占有受众的集体劳动与集体智慧,受众劳动越来越像日常生活那样,以惯例的方式存在和发生。表面上,受众拥有极大的自由、平等的话语权力,实际上,仍然无法真正摆脱当下数字资本的集体剥削。
(二)时间的殖民化
依托于信息技术革命的网络社会的发展颠覆了人们传统的时空观念,空间的时间属性发生了巨大变化,成为卡斯特笔下的“流动的空间”及哈维提出的“压缩的空间”,哈贝马斯将原本属于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的非市场和非商品化活动定义为日常生活的殖民化,信息化生存方式下受众形成对网络信息的依赖从空间和时间的维度渗透个体的日常生活领域。[15]互联网产业通过权力话语的构建提高受众的技术使用粘性和时间的空间化迁移,用户在线的时间即为创造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媒介资本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往往体现在对网民劳动时间的集约化剥削。马克思将劳动时间分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及剩余劳动时间,排除网民正常拿薪工作的时间外,网民剩余的休闲时间在很大程度上遭受媒介资本的占有与剥削。网民摆脱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任何剩余休闲时间进入各类媒体平台,尤其是参与各类媒介内容的制作,意味着受众进入信息生产的免费劳动阶段,受众能动主体的生产能力、自主、无酬的生产行为驱动资本产业以更加隐蔽和日常化的方式延长受众的在线劳动时间加速资本积累的广度和深度。
(三)受众主体性的弱化
基于身体隐性在场的媒介技术创造带给个体前所未有的参与式体验,个体化进程的日益加深,现实人际交往带来的压抑、孤独和冷漠迫使个体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付诸于社交媒体平台,网络受众更多关注自身的现实利益与关系,而缺少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受众在日常生活领域抽离化与数字劳动实践过程中陷入主体性的弱化的困境。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认为资本家为赚取高额利润,会将原本属于资本的享受、娱乐等需要强加给消费者,通过广告宣传不断挑起人们的购买欲望,使他们忽视衣食住行等真实的需求,变成被技术支配的、只追求享乐而不会批判与反抗的单向度的人。[16]在资本逻辑与媒介意识形态的牵涉下,受众信息获取的自主性被无限放大与生产、自主性的需求越来越取决于外部力量的作用,资本市场通过增加生产与消费等环节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灵活度扩大剥削面积,实现更大范围的殖民。受众在不知不觉中被引导和被利用,变成“透明人”的存在,而缺乏对自身主体性弱化的思考。
借口公务,我曾荒疏了好几年写作。2000年把中篇《试用期》寄给《十月》的时候,心里惴惴的,像第一次投稿。不久就收到主编王占军的回信,信不长,对稿子的评论只有一个词:扎实。是否真“扎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词在这里是作为正面肯定使用的。
综上所述,网络社会的崛起与发展,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互联网产业依靠网络受众参与、受众注意力投放、受众的需求管理的无酬劳动实践,形成以受众劳动为核心的资本经济循环模式。社交平台中受众从“参与者”到“免费劳工”的角色转变凸显受众的私人经验、情感投入及社会关系的商品化进程及其现实性困境。伴随着资本剥削的手段日益隐蔽与日常化,受众的媒介行为处在互联网资本的潜在剥削与监控下而不自知,阶级意识的觉醒受到阻碍。因此,必须加强对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受众劳动、受众商品等新生事物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受众必须在资本价值逻辑中确立自身,重新思考和警惕数字资本主义渗透下的劳动异化与剥削问题。
参考文献:
[1]孔令全.浅析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劳动研究的价值意蕴[J].沈阳干部学刊,2017,(06):22-23.
[2]吴鼎铭.网络“受众”的劳工化: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网络“受众”的产业地位研究[J].国际新闻界,2017,(06):125-136.
[3]邱海平,赵敏.受众劳动理论研究述评[J].经济学动态,2017,(04):101-110.
[4]蔡润芳.“积极受众”的价值生产——论传播政治经济学“受众观”与Web2.0“受众劳动论”之争[J].国际新闻界,2018,(03):116-130.
[5] 汪金汉.“劳动”如何成为传播?——从“受众商品”到“数字劳工”的范式转变与理论逻辑[J].新闻界,2018,(10):56-64.
[6]刘皓琰,李明.网络生产力下经济模式的劳动关系变化探析[J].经济学家,2017,(12):33-40.
[7]蔡润芳.平台资本主义的垄断与剥削逻辑——论游戏产业的“平台化”与“玩工”的“劳动化”[J].新闻界,2018,(02):75-79.
[8]刘燕南.数字时代的受众分析:注意力市场的解读与思考[J].国际新闻界,2017,(03):170-174.
[9]潘霁.恢复人与技术的“活”关系:对“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反思[J].国际新闻界,2016,(09):79-84.
[10]罗纳德·贝蒂格.圈地赛博空间:商品化、集中化与商业化[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02):83.
[11]吴鼎铭,石义杉.社交媒体“Feed 广告”与网络受众的四重商品化[J].媒介经营与管理,2015,(06):106-109.
[12]余富强,胡鹏辉.拟真、身体与情感:消费社会中的网络直播探析[J].中国青年研究,2018,(07):6-11.
[13]陶东风.粉丝文化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0.
[14]张天勇.社会符号化——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鲍德里亚后期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84.
[15]谢立中,阮新邦.现代性、后现代性社会理论:诠释与评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563.
[16]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116.
Commercialization of Network "Audience ":Research on "Audience Labor "in Social Media
XU Ying,FAN He-sheng
(School of Society and Politics, Anhui University, Anhui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In the new media era, the logic of capital exploitation extends from the physical space of reality to the Internet industry represented by social media. More and more online audiences become "commodities" and "free labo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industry. From the spread of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the theory of postmodern sociology Angle, reveals the social platform in the audience, the audience's attention, the audience demand management form and its commercial exploitation of capital essence of labor, ministry of labor and the audience to think and look at the audience behind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mapping of family and society's factory, the colonization of time, the audience of subjectivity, the weakening of permeability to digital capitalism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udience.
Key words :network audience; social media; capital; audience labor; audience commercialization.
收稿日期: 2019-05-07
作者简介: 徐颖(1993—),女,在读硕士。主要从事社会学研究。范和生(1961-)男,教授,硕士。主要从事政治社会学与社会治理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网络化时代的社会认同分化与整合机制研究(13BSH036)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638(2019)07-0028-04
(责任编辑 马 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