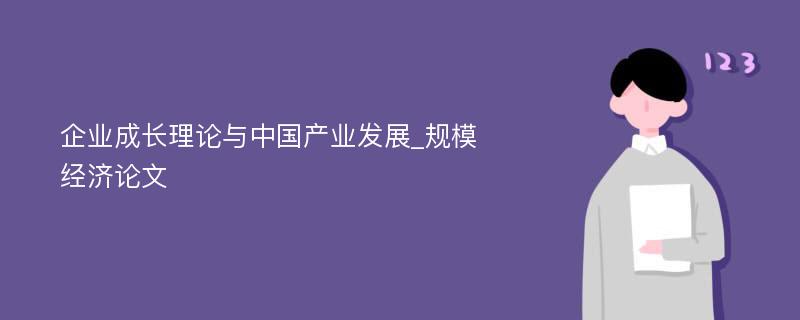
企业成长理论与中国工业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工业发展论文,理论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未竟的工业化对规模经济的呼唤
对于中国未竟的工业化,其中心任务是什么?是总量吗?总量的提高当然仍是重要的,但从许多产品的产量来看,我国工业(至少传统重工业)已达空前规模。同时,相对平淡的需求市场供给较多,“过剩经济”开始困扰中国的工业发展。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96年全国94种主要工业品中61种生产能力过剩,开工严重不足,其中35种开工率不足50%。这么多的产品过剩,过分强调总量扩张没有道理。
生产过剩的原因除了总需求不足外,一个重要原因被认为是缺乏规模经济。由于企业规模小、生产能力分散,因此造成了质次价高,与消费需求脱节(典型如汽车产业),在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矛盾日益突出。由此导致提高规模经济的呼声高涨。如国家计委课题组旗帜鲜明地提出,发展大型企业集团是“九五”时期到2010年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结合部,是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突破口,今后15年我国改革与发展重要战略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以这一时期我国大型企业集团的健康发展为标志,紧紧抓住企业集团的工作,有效地实施大公司、大集团的战略,就抓住了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其重要依据是规模经济理论。即认为发展大型企业集团可以充分利用好规模经济效益,只有在规模经济基础上运作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才有可能制订长期的开发计划、进行长期的持续投资,我国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历史任务将具体化在一批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的成长上,只有大企业和企业集团的发展壮大,形成一批国家级和世界级的主力舰队,我国新一代支柱产业才有可能有竞争力,才可能在国际竞争中站住脚,大型企业集团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国家经济实力的基础,是产业技术进步的策源地,是现代化管理的推进者,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组织形式,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依托,等等。
二、美国人的否证:大的是有效的吗?
发展大企业、视规模经济为未竟的中国工业化主要努力方向的第一问题就是:大的是有效的吗?
大规模经济的生产体制始于美国,相比其他各国,美国人自认有“偌大主义”的嗜好,“大而不是最好一向是美国的特征”(Thomas J.Peters,1988)。然而,规模经济能否产生“预期效果”,即使在崇尚“诺大主义”的美国也是长期被怀疑的,尤其是在第三次浪潮兴起以后的80年代,可以说遭到了一次彻底的清算。
早在30年代,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艾尔弗雷德·斯隆就曾进行过反思:“在差不多我们的全部活动中,我们看来正受规模过大的惰性之苦……把某项新办法付诸实施涉及的人如此众多,需付出极大努力才行,使新主意相形之下可能被认为毫无意义,因为代价太大,……,我几乎被迫作出结论:通用公司这么大,惰性也这么大,我们要当好领导是不可能的。”1986年,Walter Adams和James Brock 在《大型综合症》一书中,通过对数百份研究的评议,否认了大企业更效率、更有创新精神、更愿意从事基础性和风险性研究项目等诸如此类的传统说法,并得出“无可置疑”的结论:“大肆宣传的规模经济从来没有完全达到当初认为可以达到的效果”。1988年,美国著名管理学家Thomas J.peters 推出畅销书《乱中求胜——美国管理革命通鉴》,更是彻底否定了“大就是好”的思想,“美国经济备受崇拜之点,或者说美国人的心理特征确实是——大就是好;更大则更好;最大为最好已不再是真理了。而且,过去不曾是真理,将来也肯定不会是真理。”他认为处于美国经济制度核心部位的两种假设现在正引起无穷的祸害,而“越大越好,最大的最好”正是够得上引起无穷祸害的第一种假设。“统计质量控制及日本质量革命之父”爱德华·戴明则以汽车为例指出了“大就是好”的假设错误原因之所在:“享利·福特作过巨大的贡献,但他制造的T 型汽车并非优质车。”对此,美国道化学公司副总裁小欧文·斯奈德博士在一篇题为《质量革命——我们的基因中没有它》的讲话中进一步谈到:“由我们的先辈们按照祖先的传统经营起来的美国工业,变得庞大、强有力,要无休止地膨胀下去。我们建立了一些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厂、最大的炼油厂、最大的化工厂、最大的汽车装配线和最大的熔炉。好家伙,我们倒底能生产东西了,我们生产的东西并不总是最佳的,但我们能以最低的价格制造出大部分产品,美国工业于是就成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典范。我们曾是规模、生产率和效率上的典范,但并不一定是质量上的典范。我们把专门化、高质量的那部分市场让给了别人,而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大规模、大批量、大型生产的经济性……然而,到了60年代,我们开始感受到来自外国制造厂家的某些竞争,并非仅仅是因为他们生产得更快,产品更便宜,还因为产品质量,看在上帝的份上,也比我们的好。”
也许对规模经济以及“大规模生产体制”最具权威性的批判还数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生产力委员会”。为检讨80年代美国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明显衰退,麻省理工学院院长保罗·格雷等16位教授组成了“生产力委员会”,对各工业部门逐一进行了研究, 其主要研究结果见之于1989年《美国制造业的衰退及对策:夺回生产优势》一书。书中痛陈,在美国主流的作法中有两个战略已成为妨碍美国继续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因而属“过时的战略”,其中第一个战略便是“对标准商品进行大规模生产”。“生产力委员会”承认这一生产方式20世纪曾在美国取得伟大成功,其原因在于能以非常低廉的成本制造出大量的货物。但是这一优势的发挥是以庞大的美国国内市场为前提的。以汽车工业为例,只要能不断提供比较便宜,车型变化不大的产品,就能满足需求,并获取高额利润。因此重要的是价格竞争,也不必太重视改进产品的质量和设计。因此,工作简单化、工种专业化、梯级晋升制度、技术革新以改进机器和工具为方向,与供化单位和客户保持一定的距离,就成为这一生产方式的重要特征。
然而,正如该院迈克尔·皮奥里和查里斯·萨贝尔在《第二次工业分水岭》中提出的,大市场已经“解体”、“分裂”、“离析”,“市场细分化”已经进入到了“市场的碎化”,在变化了的市场上“特殊化需求”成为主流。其他国家看到了这一点,且因为不象美国人那样有“诺大主义”,因此在借鉴美国成功经验的同时,不照搬其大规模生产体制的做法,而是加以创新。例如,“日本轿车工业的成功就是基于一种与底特律的大规模生产体制几乎在各个方面都不相同的体制上”。日本人使用了一些新的产品开发方法,改进了车间组织形式,从而减少了生产数量,提高了将新产品推向市场的速度,并通过向不同的市场领域提供不同的产品取得了成功。
对规模经济清算的最终结论便是,从长远来看,市场力量、顾客爱好和技术机会的汇合可能会导致“完全灵活”的生产系统,“在这种系统里,那种通过定做产品来满足各个顾客的需要和爱好的工匠时代的传统将同现代生产技术的威力、精密性及节省的特点结合起来。在这样的世界上,战略目标就变成以大规模生产的价格提供适合于每个顾客的高质量的产品。”
三、理论比较:规模经济与成长经济
1.大企业何以生成:企业成长理论的观点
美国人主要从市场裂分、灵活应变等角度批判了“大规模生产体制”,笔者认为,这一批判还可以从理论上继续深化,本文在这是主要引用的是西方“企业成长经济理论”。与此同时,发展大企业、视规模经济为未竟的中国工业化主要努力方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大企业是如何生成的?是不是将几个国有企业堆在一起就行了呢?这也将涉及到企业成长经济理论。
企业成长理论起源于对大规模生产规律的研究,因而可以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是起源于规模经济理论。但企业成长理论并没有局限于规模经济的认识,而是有相当大的、本质性的发展,并广泛地涉及到企业行为、成长、组织结构以及管理问题等规模经济理论未曾涉及的内涵,因此被认为是适用于“现代企业”的核心理论,而规模经济理论则是适用于“工厂时代”的理论。企业成长理论的鼻祖是英国人Edith.T.Penrose,她于1959年发表的《企业成长理论》一书,首创从企业内部来解释企业的成长,从而成为企业成长理论的开山之作。
Penrose认为, “企业成长理念的内核可以非常简单地加以表述”。在她看来,企业无非是“建立在一管理性框架内的各类资源的集合体”,其功能则是“获取和组织人力与非人力资源以赢利性地向市场提供产品或有服务”,“企业的成长则主要取决于能否更为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Penrose,1997)。
谈到资源,最基本的当然是人、财、物三种物质资源。然而,除此之外,还有人们易于忽视的技术、经营决窍、商标、信誉、企业的营销网络、其与用户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关系等或许可统称为“无形资产”的非物质资源。由于下述原因,企业总是存在着未利用的资源:(1 )资源的不可分割性。即资源由于特殊的物理特性而难于分割,因而企业无法将多余的资源及时销入市场。尤其是人力资源更是难以分割,因此人们经常看到企业中无论何时总存在着一些人的专业能力没有被充分利用的情形。(2)资源间的永不平衡。 即在任何时候和任何规模的企业中总会存在一些资源利用得较为充分,而另一些资源则仅被部分利用的情形。(3)理性和能力的有限性。 企业资源利用的可能性和效率依赖于企业成员的知识,但企业成员尤其是经营者的知识是不完全的,因而其对资源的运用也不可能是完全的,“企业的人力资源既是企业扩张的引致性因素又是扩张速度的限制性因素(Penrose,1997)”。
企业的成长便是不断地挖掘未利用资源的无限过程,大企业不过是企业自然成长的结果而已。企业要想更完全、更充分地利用现有资源,通常可以选择两条途径:一是扩大生产规模,二是搞多角化经营。显然两者都能使未利用的资源更充分的利用,从而导致企业成长,并因此获成长经济。但是,企业成长后,不仅不可能完全消除资源未充分利用的情形,往往还会产生出新的未被利用的资源,因此导致企业新的成长过程。因此,企业内部无限存在的未利用资源导致企业持续成长,由于企业内未被利用资源的存在是无限的,因而企业的成长也是无限的。
2.规模经济与成长经济的比较
规模经济(包含工厂意义与公司意义两种),指的是在既定的(不变的)技术条件下,生产1单位单一或复合产品, 在某一区间生产的平均成本递减(或递增)的情形。通俗而言,就是大规模的生产导致长期平均费用的递减,从而创造出比小规模生产时更好的生产效果。“成长经济,是指有利于企业向特定方向扩张的,各个企业可能享受到的内部经济性。其是从企业内可能利用的生产性使用价值的独特集合中挖掘出来的,可以使该企业在投入新产品或增产原有新产品时,比其他企业处于比较优势的地位的东西”(杨杜,1996)。
规模经济与成长经济的最大区别与联系在于:“成长是一个过程、规模是一种状态(Penrose,1997,第88页)”。 即仅从资源的一定时点以及经济的、数量的角度来讨论企业成长,涉及的是规模经济的概念;排除时点限制,讨论“企业资源持续不断地扩大”这一动态过程,涉及的便是成长经济的概念。
然而,两者不具等量齐观的意义。“规模只不过是过程的副产品”,因而仅具相对意义。在技术条件变化的情形下,数量意义上的所谓最优规模实际上并不存在,因为规模经济得以实现的前提是“既定不变的技术条件”——这一点很重要却常常被忽视。设想不同地区间存在着不同的生产要素的比价——如一些国家和地区资金和有技术的工人以及懂管理的人相对另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特别稀缺,其大规模生产所需设备完全依赖于进口,其大规模运输的成本更高,规模经济就要大打折扣,甚至被新增成本所完全抵销。这就是为什么Penrose 早年倾向于认为任何一种规模都可能是经济的,晚年则进一步相信不顾企业条件盲目扩大规模一定会导致规模不经济,以及斯蒂格勒要用“生存法”来考察某一特定产业在特定时期的“最优规模”,而不原笼统地谈论什么“最优规模”原因所在(斯蒂格勒,1992)。
限制成长经济的因素也是有的,如技术革新、市场扩张、资源积累和企业经营者支配自由度以及企业家精神等等缺位或“残缺”,都会阻碍甚至窒息企业成长。但相比规模经济,成长经济更具绝对意义,因为在具备独立经营的企业主体和竞争性市场的情况下,只要资源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企业的成长就是绝对的——至今人们尚看不到何处是最大的企业的界限。Penrose因此指出,对于富有事业心的企业, 由于具有不断扩张的刺激,并不存在任何绝对的障碍。
从资源有效利用的角度看,企业规模的扩大一定与成长经济有关,而成长经济的获得却不必与企业规模相关。这是因为成长经济强调的是企业内部资源的经济利用,而不强调大企业和大量生产。任一特定企业不论其规模、大小如何,只要在一定条件下,能以较其他企业低的平均费用向市场推出追加商品,就可以说其中存在成长经济,而不论是否存在规模经济。因此,不可能所有产业都存在规模经济,但可能所有产业都存在成长经济。许多中小企业虽然不存在规模经济,但发展迅速,其原因便在于享受到了成长经济。反之,一个已经享有规模经济的大企业,一旦停止了扩张和创新,就不能享受到成长经济。
规模经济理论的要点是,大企业只凭借其规模大,就可以比中小企业更高效地从事生产、销售等经营活动。因此,在生产体制上,规模经济理论强调专业化单一品种而不屑于多样化多品种;在资源利用上,规模经济理论强调物和财的资源而忽视人和信息资源。然而,规模经济理论无法解释一些能用成长经济理论进行解释的现象,从而显示出理论的局限性。
四、政策含义及进一步讨论
本文不否认目前过于分散的经济具有走向规模经济的趋势,但不同意将其作为中国工业化来的主题。尤其在如何形成规模经济的方式和途径上,反对那种没有成长经济概念,为了获得规模经济不惜损害市场经济原则的行政干预的做法。笔者相信,追求规模只是追求成长的一个特殊阶段,就象巴比仑空中花园看起来是很美,但是最终不过是底座的自然延伸而已,而且绝不是美丽的终结。根据“成长经济理论”,可得出有关政策含义如下。
1.观念更新:中国的企业应以企业成长为目标,而不再以扩张规模为目标
受计划经济思想影响,过去我们发展企业时总希望一开始就达到“最优规模”,从而享受到规模经济的效益,虽然为此作出了很多努力,至今也还在“不懈努力”,但效果却不令人满意。其原因就在于忽视了不管多大规模的企业,设立后照样有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而这个成长过程对于企业而言比规模还要重要。因此我们如果真的想要实现两个转变,要有成长经济的概念,就不应不再去刻意追求什么最优规模,而要让企业在持续不断的成长过程中实现成长经济。这样做虽然短期内有可能“损失”一部分规模经济,然而企业的成长最终会带来规模经济——这是一种真正符合企业成长所需的规模经济,因而能比单纯追求规模经济创造出更好的效益。中国工业发展只有首先转变观念,才能顺顺利利的发展。
2.积极创造实现“成长经济”的内外部条件:一是加快培育市场经营主体,二是致力于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成长经济对企业自我经营能力和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的要求很高。因此,为创造“成长经济”得以实现的内外部条件,一是要致力于使中国企业应该成为真正的经营主体。为此,一方面应继续鼓励多种所有制成分的企业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特别是在大中型企业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二是必须加快市场化改革,以让不同所有制的市场竞争主体都能做到充分、公平、公正的竞争。
有人认为,中国企业自然成长的道路在对外开放环境下不复存在,因而通过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干预、尽快形成规模经济,以同发达国家相抗衡是必要的,为此可以不惜扭曲公平竞争的市场制度。其实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这样做常常是得不偿失的。原因在于,通过国家干预资金的倾斜分配、优惠税收等一系列外部措施来达到所谓的规模经济的目的,必定会产生对其他企业的不公平,从而具有负的外部性。然而,成长经济之所以实现,是通过对企业内未被利用资源的利用、以及利用不足的资源被更有效率的运用,因而不会出现对其他企业的外部性(相反其经验和作法有正的外部性)。除外部性的问题外,国家对企业的扶持,还会对被扶持的企业产生“负激励”,即使被扶持的企业产生依赖国家、不思进取的心理——总想一次扩张到位,然后维持简单再生产,而视追求成长经济为无意义,这样的企业根本达不到与国外企业相抗衡的目的。
3.经营者至上:要承认企业家的独特作用,精心爱护企业家、加紧培育中国的企业家
我国的国有企业经过20年的改革,至今未取得突破,原因当然很我,但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从未承认过企业家的地位。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至今不能被称为企业家,只能被称做“企业领导”,其任命仍然取决于主管部门的好恶,其激励靠所谓的“骂人机制”和“乌纱帽机制”,一旦收入高于工人若干倍被认为不应该。可想而知,在这样的制度下,谁去关心更有效率地运作国有企业的内部资源呢?“企业领导”还不如器着喊着让国家投资,上点“规模”来得轻松,谁人不知花钱(投资)比赚钱(运用内部资源)痛快得多。根据成长经济的逻辑,笔者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形成企业家机制,并相信未来能够运作的得有效率的国有大企业的模式只能是一种类似于“管理者资本主义”的“管理者社会主义”的模式。
4.“寸有所长、尺有所短”:重新认识中小企业的优势并给其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成长经济理论告诉我们,大企业有大企业的优势,中小企业也有中小企业的优势,各者完全可以各擅其长,因此,中小企业不仅能在大企业的缝隙中成长,还必然在更广的范围内发展。1998年,由于宏观经济启动乏力,中国人开始想到中小企业,政府开始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些条件。这都是值得赞许的好事,但如果不能在理论上从“规模经济”转入“成长经济”,认识不到中小企业的成长经济优势,只是一时着眼于其对劳动力吸收以及产值增长的贡献,一旦“规模经济”论者发难,政府大企业大集团战略成为主导,中小企业极又可能被再次抛到一边。朴正熙政府发布的第一个法案便是关于扶植和发展中小企业的,但结果却不由自主地走上了大企业为主导的道路(赵晓,1998),前车之辙并不遥远。对于那些骨子里既看不起中小企业,也不相信中小企业能在市场的海洋里长大的人,不妨多多玩味一家“小”汽车公司的广告语:“另看我小,长大了就是卡迪拉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