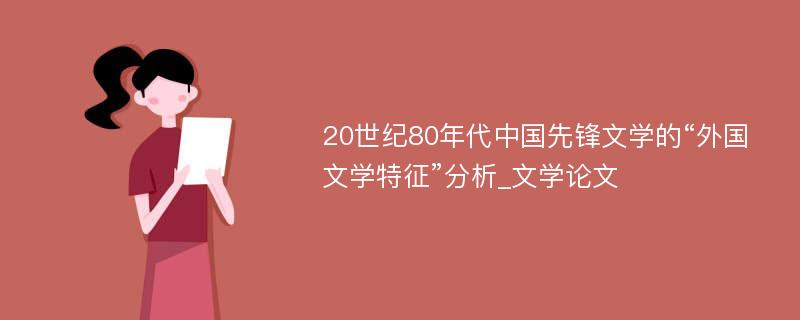
八十年代中国先锋文学的“外国文学特征”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锋论文,探析论文,外国文学论文,中国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没有一个年份能够和1985年相比。这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那年异质性的作品开始出现,文学多元化成为现实;寻根文学亮出旗帜,《爸爸爸》、《西藏,隐秘岁月》问世。先锋文学已渐成气候,小说《你别无选择》、《无主题变奏》、《山上的小屋》、《冈底斯的诱惑》、《透明的红萝卜》等的发表,标志着文学的裂变在加速,此后几年,莫言、马原、余华、残雪、格非、孙甘露等作家相继写出了自己重要的作品。毫无疑问的是,先锋作家是以欧美文学为圭臬的。而韩少功、阿城、郑万隆等寻根派作家祭起文化的大旗,表面上是在强调本土经验,实际上与马尔克斯为代表的拉美文学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对世界文学的理解上,先锋文学和寻根文学虽然不一致,但是,焦虑感是同样强烈的,二者都是借助外国文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借助拉美文学寻根与借助欧美文学先锋,其实质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先锋与寻根,二者秉持的文化逻辑是一致的。因此,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最具有活力的探索或者实验潮流,无论是回归传统还是先锋探索,实际上都和外国文学有着紧密的联系。如果仔细辨识80年代中后期产生的那些经典文本会发现,它们大都有着鲜明的“外国文学特征”,文本从形式到内容没有松弛感,焦虑感十足,颇像一个在十字路口彷徨的现代人:紧张、迟疑、敏感、焦虑。 这种“外国文学特征”比较突出的表征之一是文本的互文性。关于互文性,菲力普·索莱尔斯认为,“每一篇文本都联系着若干篇文本,并且对这些文本起着复读、强调、浓缩、转移和深化的作用。”①文本的互文性,在具有先锋意识的作家中,徐星较为典型。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过《无主题变奏》的互文性写作特征,这是较为典型的“外国文学影响焦虑症”:小说三次提到了纪德的小说《伪币制造者》。“我”极为欣赏《伪币制造者》中那个与虚伪的人生彻底决裂的斐奈尔。这是“我”对自己角色的主动认同。作为一篇虚构作品,究竟是“谁”在说话?是“我”在向读者讲述自己的经历,还是斐奈尔在和“我”探讨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我”在这篇作品中倾听到了来自异域的多重声音,有骂骂咧咧的霍尔顿、冷漠的莫尔索、一脸茫然的等待者、与虚伪的人生彻底决裂的斐奈尔、愤世嫉俗与放浪形骸的狄恩,他们都汇聚到“我”的名下,争相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和谐,有时还自相矛盾。值得追问的是,在众声喧哗中,作为小说主人公的“我”的声音又在哪里?在异域形象的主宰下,“我”的身份又是如何确认呢?② 我们可以在许多先锋作家的作品中辨识出这种异域的形象和声音。洪峰的小说《奔丧》,尤其是其开头部分,明显回荡着加缪的《局外人》的声音。余华在20世纪80年代出的许多小说,都有法国新小说家罗伯格里耶的客观、冷静、不动声色的写作方式。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岁月》,其叙事方式以及传奇内容,有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浓重投影。当然,在文本中向伟大的外国作家作品致敬也未尝不可,但是如果在人物语言、情节模式、叙述语调等方面过分倚重于异域文本,其原创性则是大打折扣的。需要说明的是,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这种“外国文学特征”随着先锋的转向已经式微,以往对西方现代主义经典作家的崇拜也渐渐消失。特别是莫言获奖以后,自80年代以来一直困扰中国作家的“诺奖情结”终于释然,那些敏感、紧张、焦虑的文学青年终于获得了自信,于是飘飘然大谈特谈“中国经验”、“中国故事”,仿佛要为世界贡献中国的“文学法则”了。在此,笔者想讨论的是,为什么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文学具有这么鲜明的“外国文学特征”?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它带给我们什么启示? 也许和新文学“五四”草创期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自“五四”时期诞生的中国现代文学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产生的。诸种文学体裁,小说、诗歌、散文、戏剧,都是在参照西方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算起来,新文学也就百来年,相对于悠久的中国古典文学来说,只不过是小小的片段。迄至1949年,中国现代文学已经产生了鲁迅、沈从文、老舍、曹禺等堪称一流的文学大师,并且将传统与现代结合得比较圆熟。这些作家将西方文学化用在自己的作品里,因而他们的作品没有散发出“食洋不化”的味道,我们反倒很容易辨识其中所蕴含的浓郁的中国情调与中国韵味。虽然战争、饥饿、杀戮、灾难这些20世纪流行的宏大词汇几乎把这些写作者的身体压垮,却并未对他们坚守的文学精神有过实质性的伤害。他们中绝大多数充分汲取过西学的营养,但是,西方的文学思潮只是作为他们创作的参照系而存在。 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文学的一次重要的“文艺复兴”,从政治八股的“‘文革’文学”、“十七年文学”中走出来,其难度之大,堪与“五四”新文学从古典走向现代的难度相比。但奇怪的是,与“五四”文学不同,80年代文学带有强烈的“外国文学焦虑症”,特别是在被指认为“现代主义”、“先锋”、“探索”的作家那里,从文学语言、文学形象和叙述格调,都有明显的外国文学的影子。这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如前所述,在新文学的诞生期,无论是鲁迅,还是周作人、胡适,虽然在阅读外国文学的基础上写作,但是他们的作品里洋溢着鲜明的中国文学的特色。看来,“文革”后对外国文学的接受,特别是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接受,还是很值得研究和反思的。中国文学和翻译文学之间,远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拿来”那么简单。 中国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外国文学特征”,显示出外国文学已经成为塑造本土文学的最基本的动力。对于“文革”后文学来说,相对于外国文学,尤其是蔚为大观的西方现代文学来说,中国短暂的现代文学三十年所能提供的可资借鉴的文学资源实在是太少了。而借鉴外国文学,便成为当时的第一选择。但是,这种对外国文学的接受,却由于当时各种条件的限制,存在着鲜明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妨碍了中国作家对于外国文学的吸收、转化,进而创造出具有鲜明中国风格的文学作品。笔者认为,形成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的“外国文学特征”的原因如下: 其一,从创作主体来看,作家在学养上的先天不足,会严重制约创作水平的发挥。当然,并不是说,作家的学养愈好,创作才能愈高,有的作家,如沈从文、莫言,并没有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一样成为大师。但是,一般说来,学养和写作才能兼备,往往会成为大作家。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茅盾、老舍、穆旦等许多耳熟能详的名字,可谓学贯中西,他们的写作,并不仅仅靠才气,还有伴随学识而来的眼光和见地。他们的外语较好,有人甚至能用外语写作,可以说具有国际视野。1949年以后依靠行政力量大力扶持的工农兵作家,所写的作品的水准自然是大打折扣的。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作家,多为知青一代,在革命年代,不少人学业荒废,学养先天不足,虽然经过后天弥补,但是就整体素质而言,与“五四”作家相差何止一点!囿于外语水平的限制,绝大多数作家没有能力阅读原文,只能阅读翻译文学,这样一来,对于翻译文学的接受,不可能做到原汁原味,所学多为皮相。王蒙曾在80年代呼吁中国作家的学者化,其实是很有见地的。 其二,20世纪80年代思想文化场域的制约。在80年代思想场域中,起建构作用的主要包含三种权力话语资源: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主流话语形态、西方18、19世纪启蒙主义话语形态、20世纪西方非理性主义话语。这三者之间的摩擦、妥协和交锋,很大程度上构成了80年代的文化思想地形图。在80年代理性主义复归、人道主义复苏的“五四”式环境里,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是个异类。如果承认传统存在着变动不居的文化内涵的话,经过“五四”的洗礼,西方的启蒙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构成了我们的传统,近百年来,不断有学者呼吁回到“五四”,实际上是回到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的启蒙传统。而意志主义、直觉主义、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等20世纪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则很难构成我们的传统,而这些哲学流派,则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哲学基础。西方非理性主义进入80年代思想场域,被挪用、误读,以迎合中国社会重建理性的时代诉求。流行一时的“萨特热”、“弗洛伊德热”、“尼采热”,就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青年对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热烈回应。但是,由于80年代的思想解放与思想限制(进行社会主义“纯化”)是同时进行的,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干预下,这些西方现代哲学更多地以被误读、肢解、改造的形式被片面接受③。而中国作家对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大多进行了功利性的误读。比如,作家谌容接触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写出的小说《杨月月萨特之研究》,只是顺应社会流行观念,浅层次地把萨特的学说理解为一种人生哲学,根本谈不上对人性的伟大洞察和对人类灵魂的深刻表现,而这,则是萨特的小说所着力表现的内容。由此可见,80年代中国先锋作家无法在知识谱系上将西方现代哲学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纳入自己的世界观,在这种情形下比照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写作,难免会出现只得皮毛的照猫画虎之作,落了个“伪现代派”的名称。正是80年代思想文化场域的制约,使得这些先锋文学既缺少真正的现代哲学根基的支撑,又远离了本土传统,如此一来,我们就很容易辨识出80年代中国文学里面的“外国文学”因素了。 其三,文学生态环境的制约。众所周知,1949年后的文学生态环境是高度政治化的,20世纪80年代以前是讲究文学的阶级归属,近20年虽然淡化了阶级归属,但是依然强调文学的“中国特色”,讲究意识形态特征。“文革”后的文学在突破禁区的欢呼声中一路高歌猛进,譬如朦胧诗从地下走向公开,进而进入主流诗坛;现代主义写作从被视为“异端”到受到追捧,等等。但是,无论怎样突破,底线是始终存在的,写作的禁区如同军事禁区一样横在作家面前。在这个文学生态环境中,从文艺政策、文艺体制、文艺组织,到文艺生产、发表、传播、批评研究等诸多环节,均受到律令的制约。而80年代的“清污”运动,一直在提醒这个“禁区”的存在感和不可冒犯性。在这个具有严格清规戒律的文学场域中产生的中国文学作品,整体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种缺憾。众所周知,中国80年代的先锋文学直接受到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而西方现代派文学从本质上说,是从属于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在对世界的认知方面,以反思、批判为主,是对启蒙理性、工具理性颠覆性的反动。这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所崇尚的带有浓厚的威权色彩的理性主义存在着激烈的冲突。因此,中国文学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接受,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话语妥协的结果。中国文学侧重于对西方现代主义表现形式的接受,而对其具体的精神内核,则作了毫不客气的“扬弃”。这是一种技巧层面的“仿制”与“试验”。我们往往从这种“中国式的现代主义”中,辨识出“意识流”、“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存在主义”等西方现代主义特征,当然这是一种极为表面化的特征,标签化的特色极为明显,和现代主义的真正内涵,可谓有云泥之别。 其四,稀薄的传统。如果说,通过对古典的断裂,诞生了“五四”文学,那么,显然,“文革”后,中国作家与传统的断裂更为明显。就年轻一代而言,多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从教育经历上看,早已完成了对传统文化的清算,甚至已经完成了对“五四”以降、以启蒙为底色的新文化的清算。老作家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在80年代初发表时有横空出世的感觉,面对这样的作品,我们仿佛看到,时间凝滞了,好像历次把中国搅得天翻地覆的革命运动不存在一样,悠久的中国传统复活了,当然那里面也有现代气息,但那现代气息却是高度中国化的。而知青一代的作家,却鲜有这种整合传统文化的能力,传统在他们的作品中,只是为了作为与现代相对照而存在。中国作家患上了强烈的“现代性”焦虑,在骨子里是想将传统剔除出去的。寻根文学被认为是知青文学为了摆脱对西方文学的过分倚重所发起的本土文学写作运动,从传统文化(主要是地域文化)中寻找精神支撑,但是其结果并未激活传统,反而强化了“现代”的存在。在这里,读者容易读出与拉美文学的关联来。韩少功的小说《爸爸爸》,虽然目的是在从楚文化中寻找民族的文化根基和精神内核,但是,象征主义、魔幻、荒诞、变形、超现实主义等西方现代派表现方式均不同程度地透射进文本,使得这部作品像一部文化寓言、文化隐喻,在貌似传统的外壳中,包裹着西方文学的内核。于是,我们看到,在80年代以外国文学为参照的写作实践中,传统的弱化或者说传统文化的缺失,使中国文学的本土特色弱化,从而凸显了外国文学或翻译文学的特征。 也许,与“五四”新文学相比,我们更能看清“传统”在文学发展中究竟有着怎样的威力。同样是参照外国文学进行写作,“五四”和20世纪80年代就有鲜明的不同。可以说,“五四”文学让我们想起了“创造”,鲁迅的《狂人日记》、郭沫若的《女神》一经推出,便振聋发聩。虽然鲁迅、郭沫若对现代小说形式、现代诗歌形式的创造稍显稚嫩,但毫无疑问是带有极大的“原创性”,是个性鲜明的本土文学。究其原因,新文学是从旧文学的基础上蜕变出来的。这种蜕变自晚清即已开始,传统给予了新文学以强有力的支撑。新文学的作家大都受过严格的私塾教育,饱读过四书五经,他们的作品中的现代性是根植于传统之中的。而80年代文学则不同,让我们想起了“模仿”,原创性不足。这一点在带有探索性的先锋文学那里最为突出。在80年代,“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是一个不断遭到质疑、抛弃的传统,“五四”文学有限的传统一时也不能得到全面的继承,可以说从一开始,80年代文学就处于一种无根的状态中。如果说,新文学是在传统基础上的蜕变,80年代文学则是在与传统断裂的地带产生的。对外国文学的倚重,大约是自中国新文学诞生以来最为突出的。80年代的作家,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仪的诸多外国文学作家,在此情形下,自然地,外国文学就构成了我们的重要传统。我们的文学,不可能没有浓厚的“外国文学特征”。 其五,走向西方文学的“幻觉”。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冲动,在80年代尤为突出。极端的封闭导致了极端的崇洋媚外,当国门打开,西方文化在各个领域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堪称是一场激烈的文化地震。在改革开放的宏大国家叙事的背景下,文学走出僵化的“文革文学”模式,向西方文学靠拢的愿望十分强烈。在“五四”时期,胡适等人就持一种“文学进化论”的观点,认为欧美文学代表着文学的最高水准,作为落后的中国文学理应和古代文学断裂,全面学习西洋文学。新时期自然又是一个以西学为主的氛围。一方面,大量重印西方启蒙主义时期的古典名著,以期恢复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另一方面,为了跟上西方文学的步伐,冲破阻力译介了不少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同时催生了中国本土的现代主义式的探索写作。西方古典名著所蕴含的启蒙理性,对于本土现实主义写作的恢复和深化,特别是对于清除“文革”造成的蒙昧,起了重要的作用。而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译介,对于中国文学来说,更是在文学观念上引起了一场文学地震。对于一贯推崇理性、倡导反映现实人生的主流文学来说,现代派是如此的一个“异端”:非理性、神秘主义、非逻辑、偶然性、意识流、自动写作、魔幻现实、荒诞、异化……而在80年代的先锋作家看来,这就是当时最新的世界文学潮流,而传统的现实主义已经过时。探索实验的风气成为一时的文学时尚,求新变革的愿望,几乎是当时的主旋律。黄子平有句名言,大意是说小说家们“被创新的狗追得连撒尿的功夫也没有”。之所以如此,就是被这样一个共识所驱使:创新性的先锋写作,才是代表了世界文学发展的方向。而从左翼文学以来一直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文学是文学的最高发展形态,在80年代遭到了根本性的质疑。茅盾在《夜读偶记》里曾经质疑过的“文学进化论”、“欧洲中心主义”,在此时已经毫无疑问地被确立起来了。这种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接轨的渴望,体现了强烈的对外国文学的“崇拜”心理。“十七年文学”崇拜的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80年代崇拜的是西方现代主义,走向西方文学,尤其是走向西方现代派文学,成为中国作家写作的一个潜在的背景。在这样的一种焦虑心态下,以西方文学作为镜像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没有主体性的写作。其所呈现出的外国文学特征,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中国文学的这种“外国文学特征”,主要是指带有先锋意识的探索、试验特色的文学而言。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文学,从整体上看,还是以传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为主。而这种“外国文学特征”,到了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文学那里达到了高潮。这时的先锋文学比80年代初更为内在,不仅局限于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写作技艺的具体追摹,如反讽、时空悬置、零度叙述、叙述圈套、元小说技巧等,更体现在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艺术本质的深层摹写上,譬如非逻辑、对偶然性的强调、深层隐喻的运用、神秘主义,等等。毫无疑问,现代主义已经向更深处发展,取得了不可小觑的成就,并产生了一批经典文本。但是,其暴露出的问题更为突出。如果说,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文学的现代主义还只是对意识流、存在主义、黑色幽默等具体潮流的借鉴,而80年代中后期则变为对西方具体作家的借鉴、摹写。譬如,残雪之于卡夫卡,扎西达娃、莫言之于马尔克斯,余华之于法国新小说,马原、孙甘露之于博尔赫斯,等等。自然,中国作家出众的才华使得他们在比照西方作家写作时,进行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创造,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此时他们创作出的文本,“外国文学特征”更为容易指认。譬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经典开头:“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仿照这个开头,以及那种向后叙述的方式和语气的小说,在当时极为流行,直至新世纪也仍有不少作家采用这种叙述方式。莫言的《生死疲劳》、范稳的“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百年孤独》的味道仍很浓郁。我认为,90年代初先锋的转向,与这种“过分的外国文学化”有着根本的关联,也许,作家们已经意识到这种写作的危险性,担心会沦为对方的“拷贝”。以往我们往往把这种转向归因于时代氛围、政治意识形态、作家心态、市场经济的崛起等原因,未免过于简单了,看来,来自文学内部的原因更值得重视。 形成中国文学的“外国文学特征”的原因比较复杂,并不是简单罗列几个因素就能解释清楚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代文学的“外国文学特征”也许是中国文学发展难以避免的。 自先锋文学兴起至今,已经过去了30年,而我们今天的诸多文学观念,大多还是来自于那个文学实验的时代。尤其是80年代文学所推崇的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观念,在今天仍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今天许多作家的创作观念的根基与底色。譬如,在对现实的理解上,不仅存在着对现实的反映,还存在着对现实的“变形”、“隐喻”,还有非现实的“荒诞”、“魔幻”等。譬如对时间的理解,不仅存在着线性的时间,还有圆形的时间,过去、现在与未来相互交织的时间,等等。又如,陈焜先生在80年代初由西方现代派谈到文学的复杂性。他敏锐地意识到,简单已经不是评价文学的标准了,“无论对外国文学还是对中国文学”,“复杂性”“都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一般地讲,这种复杂化不是歪曲而是更加接近了生活的真实。”“到底怎么理解现实?我们对现实的那些解释是否真的把握了现实的复杂性?我们的审美意识是否复杂到能够再现世界的复杂性?”具体到如何表现人物,他认为,“人已经非英雄化了,散文化了,他不是一个纯粹的英雄,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歹徒,而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④陈焜是从西方现代派入手来谈对文学的看法的,他对文学作品如何把握世界,如何写人物的理解,显然是很超前的。即使放在今天,也是富有启示意义的。90年代文学、新世纪文学,仍然离不开这些文学观念,可以说一直在印证这些观念的正确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其实还在80年代,我们还是笼罩在外国文学之中,尤其是置身于西方现代派文学为我们提供的思想资源之中。因此,80年代先锋文学的“外国文学特征”虽然意味着中国文学的不成熟,但同时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一种幸运,因为中国文学可以通过借鉴外国文学,摆脱封闭与僵化,进而开创具有真正文学性、实现文学内在价值的新天地。 注释: ①转引自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页。 ②王德领:《影响的焦虑:互文性写作中的文化身份的迷失——重读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南方文坛》,2011年第6期。 ③20世纪80年代对西方现代哲学的接受有着鲜明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譬如,对存在主义的接受。对人生观的讨论和关注,是80年代初期一个最为范围广泛的热点问题。在剧烈变动的时代,青年人对人生问题产生了苦闷与疑惑,对萨特的接受,往往从“人生哲学”的角度切入。在一定意义上说,萨特等现代西方哲学家扮演了后“文革”时代的青年“精神导师”的角色。 ④陈焜:《漫评西方现代派文学》,《春风译丛》1981年第4期。标签:文学论文; 先锋文学论文; 外国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文化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外国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百年孤独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