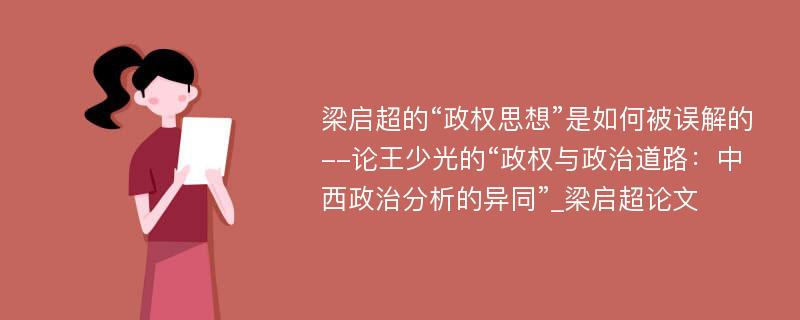
梁启超的“政体思维”是怎样被误解的——评王绍光的《政体与政道:中西政治分析的异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体论文,异同论文,是怎样论文,中西论文,误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政体与政道:中西政治分析的异同》一文中,王绍光致力于摧毁长期以来支配政治分析的西式“政体思维”,并重新挖掘与寻找中国式政治分析的范式和理论思路,从而为解释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与变迁开拓出一条新路。这一新的范式和思路的核心,就是用“政道思维”来取代“政体思维”。对于“政体思维”和“政道思维”这两个新的概念,王先生作出了一些界定与论说。他认为:“西式政体思维重政体”,按照这一思维,“一切问题都与政体相关,诸如经济增长、社会公平、腐败、幸福等等,不一而足。政体好,其他都会好;政体不好,其他都好不了。欧美、印度的政体好,因此,那里不管存在什么问题,长远来讲,它们的问题都可解决;中国的政体不好,因此,不管取得了多少成就,长远来讲,都是靠不住的,迟早必须转换跑道。这种思维方式叫政体思维;它往往导致政体决定论。”这种政体思维甚至隐含着一个未加言明的根本假设,即“政权的形式决定政权的实质”。而且,政体思维在进行政治分析时,“关注的只是政治秩序的形式”[1](p.75、76、86、119)。由此看来,王绍光所定义的“政体思维”,大约是指追求乃至极力执著于“政体解决”的那种政治思想观念和政治分析方式,即“政体思维”高度重视政体,认为政体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或者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前提,甚至以为“政权的形式决定政权的实质”。简单地说,“政体思维”其实就是“政体决定论”①。
而“政道思维”则以中国的“政道”概念而非西方的“政体”的概念为灵魂,它探求的是“政治体制的目标与途径”,其“着眼点是政治秩序的实质”。所谓“政道”,包括“治道”和“治术”两个部分:“治道”指治国的理念,是政治的最高目的或“政治体制的目标”;“治术”指治国的方式或实现政治目标的途径,如各种制度(包含政体)、措施、方针、政策、方法等等。虽然“政道”之中也有制度,制度之中亦包含政体,“但制度只是政道的一部分。因此,中式的政道思维不会陷入制度决定论,更不会陷入政体决定论”。在王绍光看来,以“政体思维”进行政治分析,显然存在着不少弊端,甚至根本上是不对的。职是之故,“摒弃狭隘政体思维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吗?”用王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进行政治分析时,应当“把西式政体的视角换为中式政道的视角”[1](P.76、89-91、119)。
王绍光的这一尝试,的确立意高远,而且发人之所未发,催人反思和追问。其端正学心、拯救学理、教诲学人和嘉惠学术的急切心情,也跃然纸上。②但是,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提出的不少观点以及对一些材料的处理,就不免显得有些匆忙。
例如,王绍光在论文的“结语”部分中认为,从近代开始,尽管政体思维已传入中国,但中国本土的一些政治思想家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运用政道思维来思考问题”。其中,梁启超就是摒弃其“政体思维”并转向“政道思维”的一个重要典范:在梁启超政体思想的演变过程中,已经出现了从“政体思维”到“政道思维”的根本性转变。对此,王先生在两页多的篇幅中作出了一个总体性的论断和论证:“梁启超是最早把政体思维引入中国的思想家,但他最终转入政道思维”[1](p.114)。这一论断和论证概括性很强,并勾画出了梁启超政体思想的生长与演变历程。而王先生正是以梁启超这个从“政体思维”到“政道思维”转向的典型,为自己倡导的“政道思维”张目。
但是,对这个总体性的论断和论证,无疑需要进一步追问:一方面,的确是梁启超最早把“政体思维”引入到中国的吗?另一方面,他是否最终又背离其“政体思维”而转入了“政道思维”?
本文试图对上述第二个问题进行辨析。笔者将从两个方面予以展开:(1)简要阐明梁启超的“政体思维”是什么?(2)王绍光所谓梁启超最终从“政体思维”转入“政道思维”的论判,是否能够成立?不过,本文的目的并不是完全重现梁启超政体思想的基本问题框架与演变轨迹,而是主要紧随王绍光的行文与逻辑,以及其所涉及的材料和论述进程,看一看他怎样解读特别是怎样误解梁启超的“政体思维”,从而澄清和还原梁先生政体思想的一些本来意旨。为此,本文不可避免的作法,是将梁启超的原著及其关键段落与王绍光的引证、判断进行比较,并讨论相关的语境和文献。
一、梁启超的“政体思维”
梁启超对政体问题的论说,大约始于1896年的《古议院考》。在这篇自称为“游戏之作”的论文中,梁先生认为议院之意在于“君权与民权合,则情易通。议法与行法分,则事易就。二者斯强矣。”但梁先生一方面将这种议院视为西方诸国强国之本,另一方面却又说中国因风气未开、民智未成而不宜马上开议院,故“今日而开议院,取乱之道也”[2](P.61-62)。其后的《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1897年)、《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1899年)、《各国宪法异同论》(1899年)等,则主要是介绍政体学说、政体分类及其嬗变,以及一些国家的宪法对于政体的设定,也未明确谈及对政体的褒贬取舍。所以,王绍光论断梁氏的“政体思维”,主要以其1901至1902年的论著为材料。
那么,梁启超的“政体思维”又是怎样的一种政治分析方式?王绍光谈到了梁先生运用政体概念进行政治分析时所提出的三个观点:一是颂扬“自由民政者,世界上最神圣荣贵之政体也”[3](P.462)。二是说中国数千年“至今不能组织一个合式有机完全秩序顺理发达”的良好政府,原因在于“无政治能力”,而“无政治能力”的原因在于专制政体,即“吾国民以久困专制政体之故,虽有政治能力不能发达”[4](P.729)。③三是认为:“然则为国民者,当视专制政体为大众之公敌”[5](P.794),必欲除之而后快。
这三个观点(后两个观点实为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外乎是指出:自由民主政体是非常优良的,而(中国的)专制政体是非常罪恶的。它们都属于梁启超对不同政体的功能、意义所作的评价,并由此彰显对自由民主政体的偏爱与选择。如果这是王绍光所定论的梁启超的“政体思维”,那大概是指梁先生的上述三个观点,其实就是认为“一切问题都与政体相关”,所以,为了解决中国的各种问题,特别是通过变换政治以挽救时局的大问题,根本上就必须首先解决“政体问题”。王先生根据上述材料将梁启超早期的政体思想归结为“政体思维”,显然是符合其对“政体思维”所作的界说的。
实际上,王绍光谈到的上述三个观点,甚至还不足以完全代表梁启超早期的“政体思维”。因为仅仅这三个观点,还未能真正彰显出梁氏“政体解决”的思维方式,亦即梁先生要用“新政体”来取代旧的专制政体的整个思想体系及其良苦用心。由“新政体”取代“专制政体”,其实是梁启超政体思想的总纲领。而他围绕这一总纲领而展开的所有政体思想,主要解决五个基本问题:(l)作为旧政体的“专制政体”是什么?(2)为何要用“新政体”将“专制政体”取而代之?(3)“新政体”又应该或可能是哪种政体?(4)怎样从“专制政体”到达“新政体”?(5)如何定型、巩固和维持“新政体”?在思考这五个问题时,梁先生都贯通了带有“政体决定论”色彩的“政体思维”。
对梁启超的政体思想作系统的论述和讨论,显然不是本文的主要任务。但是,这里可以根据梁先生1900至1902年及稍晚的论作,为王绍光的论判再增添一些重要材料,从而更详明地呈现出梁先生早期的“政体思维”。例如,梁先生认为,作为旧政体的“专制政体”,是中国一切问题的罪恶之源。因此,他对其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揭露和痛批。他在《新民说》中指出,中国的专制政体,是中国人的政治能力“隐伏而不能发达”、“发达而旋复摧夷”的罪魁祸首:“专制之国,其民无可以用政治能力之余地,苟有用之者,则必将为强者所蹂躏,使之归于劣败之数。而不复得传其种于后者也。”因而,“专制政体为直接以摧锄政治能力之武器,”“而中国之专制,全为政治能力之贼也”。[4](P.729-730)在《论专制政体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一文中,梁启超也断言,中国破家亡国的总根源,在于长期以来实行的专制政体:“今民间稍有知识者,莫不痛心疾首于专制政体。其恶之也,殆以此为吾害也。……专制政体者,实数千年来破家亡国之总根原也。”“若是乎,吾中国数千年脓血之历史,果无一事焉而非专制政体贻之毒也。”[5](P.788-790)④至于为何要用“新政体”将“专制政体”取而代之,上述判断,其实已从根本上回答了这个问题。既然专制政体是一切问题的“总根源”,那么,理所当然地要对这一政体进行一个救危亡求进步的“总解决”,即“必取数千年来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4](P.688)。所以,梁启超认为:“专制政体之不能生存于今世界,此理势所必至也。以人力而欲兴与势为御,譬犹以卵投石,以螳当车,多见其不知量而已。故吾国民终必有脱离专制苦海之一日,吾敢信之吾敢言之。”[5](P.794)将一切问题归咎于专制政体,进而认定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齑粉这个专制政体,这当然是典型的“政体思维”。而足以胜任“总解决”之职责的“新政体”,又应该或可能是哪种政体呢?对此,此一时期的梁启超有些游离。他有时主张立宪政体,这在1900年的《立宪法议》中作了明确的阐述:“中国彼昏日醉,陵夷衰微,情见势绌,至今而极矣。……故中国究竟必与地球文明国同归于立宪,无可疑也。特今日而立之,则国民之蒙福更早,而诸先辈尸其功,今日而沮之,则国家之进步稍迟,而后起者为其难,如斯而已。……故采定政体,决行立宪,实维新开宗明义第一事,而不容稍缓者也。”[6](p.407)有时他又主张民主制,他说:“吾以为民主制度,天下之公理。凡公理所在,不必以古人曾行与否为轻重也。”[3](P.461)不过,“立宪政体”这一问题,一直贯穿于梁启超的政治思考。梁先生终其一生,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与时代潮流之中,都在对其进行种种的设想与追问。
二、梁启超是否最终从“政体思维”转入了“政道思维”?
粗略地看,王绍光将梁启超从政体思维到政道思维的转换过程,大体分成了三个阶段。但笔者认为,在他所分析的每一个阶段中,其判断都有不少且不小的疏漏。
(一)王绍光认为,第一个阶段,梁启超开始怀疑政体思维方式,觉得运用这一方式“思考现实问题难以行得通”[1](p.114)。
王绍光所据材料之一,是梁启超1903年去美国考察时所撰写的《新大陆游记》。王先生认为,通过这次实地考察,梁启超对美国这个“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大失所望,所以指出:“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意即美国共和政体“美非不美”,但是并不适合于我中国。
就文献而言,王绍光注为“‘新大陆游记’(1903),《梁启超全集》第4卷,第1125-1229页”[1](p.114)。但是,《梁启超全集》中,实际上题为《新大陆游记节录》。在1936年的《饮冰室合集》(《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二)中,也是《新大陆游记(节录)》(1903)。(当然,梁启超在一些文章曾自称《新大陆游记》。)另外,《梁启超全集》将时间错为1902年,王先生按《饮冰室合集》注为1903年,但实际上1904年2月正式刊行于《新民丛报临时增刊》。王先生所引文字的确切页码是第1188页。
梁启超对美国共和政体的失望之心,在《新大陆游记节录》中多有所记,如说:“夫美国争总统之弊,岂直此而已。其他种种黑暗情状,不可枚举,吾游美国而深叹共和政体实不如君主立宪者之流弊少而运用灵也。”[7](p.1158)又说:“美国政治家之贪黩,此地球万国所共闻也。……而其最腐败者莫如市政。”如纽约等城市,“常为黑暗政治之渊薮”[7](1196-1197)。但是,梁启超并非仅仅批评、揭露美国政治的黑暗,而是同时平心、客观地肯定其不少的优点。所以,他特别说明:“以上所论,言美国民主政治之缺点居多。虽然,以赫赫之美国,岂其政治上无特别善良之处而能致有今日者,其所长者多多,固不待问。余亦稍有所心得,……”[7](p.1198)
而梁启超断言共和立宪政体“其如于我不适何”的那段文字,是他归纳中国人“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这一缺点时讲的。在观察、比较美国的华人社区以及国内诸多社会组织的运作情形之后,梁启超指出,中国人有四大缺点:“一曰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二曰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三曰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四曰无高尚之目的”,即“其所营营者只在一身,其所孳孳者只在现在”[7](p.1187-1188)。其中,他对第三个缺点描述尤其细致入微,也有不少比较的材料,甚至还引用了一位乡人对他说的话:“旧金山华人,惟前此左庚氏任领事时,最为安谧。人无敢挟刀寻仇者,无敢聚众滋事者,无敢游手闲行者。各秘密结社,皆敛迹屏息。夜户无惊,民孜孜务就职业。盖左氏授意彼市警吏严缉之而重罚之也。及左氏去后,而故态依然。此实专制安而自由危,专制利而自由害之明证也。”[7](p.1187)最后,梁先生总归而言之曰:
夫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是多数政体之总称也。而中国之多数、大多数、最大多数,如是如是。故吾今若采多数政体,是无以异于自杀其国也。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吾今其毋眩空华,吾今其勿圆好梦,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吾祝吾祷,吾讴吾思,吾惟祝祷讴思我国得如管子、商君、来喀瓦士、克林威尔其人者生于今日,雷厉风行,以铁以火,陶冶锻炼吾国民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五十年,夫然后与之读卢梭之书,夫然后与之谈华盛顿之事[7](P.1188)。
就此段结论而言,丝毫也无法说明梁启超就认为“政体”不那么重要,或者偏离了他前期的所谓“政体思维”。梁先生认为,共和立宪政体在当时于我中国不适。所以他才说:共和立宪政体,“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这犹如说:“西施云,昭君云,貂婵云,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看到美得让人绝望的美女(或许有痘痘),但是却搞不到手,自然不仅是要令人心痒痒然,而且要令人“大失所望”了。然而却不能说,这意味着梁先生觉得那些美女不美。否则,何来“美非不美”的论评?
为什么“美非不美”的共和立宪政体,却不适于那时的中国呢?梁先生说,从国民性和国民能力(例如他揭发的“四大缺点”)来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这正是他认为中国不能马上植入共和立宪政体的主要原因。“故吾今若采多数政体,是无以异于自杀其国也。”不过,梁先生并未决然否定共和立宪政体在中国的可行性,只是认为要经过一些强权人物(类似于管仲、商鞅、克伦威尔)运用强力对国民进行三、五十年的“陶冶锻炼”之后,才可以让共和立宪政体成功地通行于中国。正是这样的一种观察和判断,为随后的《开明专制论》倡导“开明专制”埋下了伏笔。而王绍光据此认为梁启超开始对“政体思维”有所怀疑,恐怕不符合梁先生的本意。如果说梁先生有什么怀疑的话,那也是怀疑在彼时的中国实行共和立宪政体的可能性,而不是怀疑一切政体的重要性以及“政体解决”的基本思路。我们从上述引语中看到,梁先生不是在期待着与经过几十年“陶冶锻炼”的中国国民一起“读卢梭之书”,以及“谈华盛顿之事”吗?
王绍光所据材料之二,是梁启超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1903年)一文。他引证说,梁启超坦承:“吾醉心共和政体也有年”,“吾今读伯立波两博士之所论,不禁冷水浇背。一旦尽失其所据,皇皇然不知何途之从而可也”。在王先生看来,这“也就是说,为了探求在中国建立‘有机之一统与有力之秩序’的途径,梁启超开始认识到,政体未必有决定性的作用,并把视线转向影响实际政治的其他因素”[1](P.115)。
首先要指出,王绍光此处根据《梁启超全集》所作的引用,有两处错误(也可能是印刷所致):一是“吾醉心”实为“吾心醉”。二是“伯立波两博士”实为“伯波两博士”,“伯”博士指出生于瑞士的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J.K.Bluntschli,1808-1881),“波”博士即著有《国家论》的德国柏林大学教授波伦哈克(Conrad Bornhak,1861-1944)。
梁启超为什么读了伯、波两博士的政治学著作之后,感到“尽失其所据”,而“皇皇然不知何途之从而可”,进而“不禁冷水浇背”?这得从梁启超“心醉共和政体也有年”说起。他自言其十年来“醉共和梦共和,歌舞共和,尸祝共和”。其想望中国实行共和政体的热切之心,表露无遗。但是,伯、波两博士的政治学说,给梁启超对于共和政体所怀抱的醉意美梦,当头泼了一大瓢冷水。事实上,梁先生早就关注到了伯伦知理,他在《清议报》(1899年)上就曾译介过伯氏的国家理论。1902年,广智书局还出版了梁先生所译伯氏的《国家学纲领》。1903年5月25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32号上也发表过《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的短篇文章。但从美国考察归来之后,梁先生却对伯氏(以及波氏)的思想,别有一番运用和思考,因而重新撰写了同题文章《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并刊发于《新民丛报》第38-39号(1903年10月4日)。梁启超解释说:“此题已见本报第32号中,以其所叙尚简略也,且夫作者之所感触别有所在也,故不避骈枝之诮,再撰此篇。”对于所谓“作者之所感触别有所在”,他写下了一段较长的自白:
吾心醉共和政体也有年。国中爱国踸踔之士之一部分,其与吾相印契而心醉共和政体者,亦既有年。吾今读伯波两博士之所论,不禁冷水浇背。一旦尽失其所据,皇皇然不知何途之从而可也。如两博士所述,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我同胞虽一不具,且历史上遗传性习,适与彼成反比例,此吾党所不能为讳者也。今吾强欲行之,无论其行而不至也,即至矣,吾将学法兰西乎?吾将学南美诸国乎?彼历史之告我者,抑何其森严而可畏也!岂惟历史,即理论,吾其能逃难耶?吾党之醉共和梦共和,歌舞共和,尸祝共和,岂有他哉?为幸福耳,为自由耳。而孰意稽之历史,乃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征诸理论,乃将不得自由而得专制。然则吾于共和何求哉,何乐哉?……呜呼痛哉!吾十年来所醉所梦所歌舞所尸祝之共和,竟绝我耶!吾与君别,吾涕滂沱!……吾与汝长别矣!问者曰:然则子主张君主立宪者矣?答曰:不然。吾之思想退步,不可思议,吾亦不自知其何以锐退如此其疾也!吾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者也。吾知昔之与吾同友共和者,其将唾余[8](P.1074-1075)。
这段论述,是梁启超介绍伯、波氏“论民主政治之本相及其价值”一节中最后的“译者曰”,它将梁先生的心迹剖白得清晰明了,很值得玩味和思忖。它主要表达了梁先生的几层心思:
(1)宣称十年来心醉于共和政体,热衷于共和政体,其目的,是为了幸福和自由。
(2)如果在中国因实行共和而断送了幸福和自由,则宁可与共和痛别。梁启超指出:在国民条件不具备之时实行共和,历史教训已经告诉人们,“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而伯、波两博士的政治理论也已阐明,“将不得自由而得专制”。他特别感到痛惜的是,在阅读伯、波两博士的政治学说后,发现我同胞不仅不具备“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反而由历史遗传下来的性习“适与彼成反比例”。这一让中国许多学者和政治家纠结、困扰一百多年的“国民资格”与“人民程度”问题,当年也让梁启超认识到,在中国绝不能强行建造“共和政体”。因此,梁先生对共和政体在中国的即时适用,已经感到绝望:“呜呼痛哉!吾十年来所醉所梦所歌舞所尸祝之共和,竟绝我耶!”而一连三句“吾涕滂沱”,足见梁启超对中国不能即行共和政体充满了怎样的悲痛欲绝之情。这也正好承续了他在《新大陆游记节录》中共和政体“其如于我不适何”的沉重感叹。如果说对美国的考察让事实粉碎了梁先生的中国共和梦,那么伯、波两博士则在理论上让梁先生与共和梦“长别”了。
(3)不能实行共和政体,是否可以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呢?“答曰:不然。”此时的梁启超,连“君主立宪政体”的主张,也觉得不合时宜和超前了。对这一大不同于从前的态度,他自称其“思想退步”的速度,“如此其疾”,简直令人不知其故和“不可思议”。
(4)既然如此,剩下的路又是什么呢?梁启超的回答也很干脆:“吾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者也。”即考察了美国,不梦美国,反而梦俄罗斯。这个“俄罗斯”,乃是“开明专制”的代名词。对此,《开明专制论》就很明确地指出过:俄国“迨大彼得一度开明专制,遂骧首于中原,以迄今日。……自大彼得后,野蛮专制频仍,至最近世,复渐进于开明专制。”[9](P.1465)
那么,梁启超因忧心于国民程度幼稚问题,从醉梦“共和”,一至“君主立宪”,再至“开明专制”,在其政体思想的演变上,到底意味着什么?易言之,“开明专制论”属于“政体思维”,还是“政道思维”?这就必须如同王绍光所作的那样,进入到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
(二)王绍光认为,第二个阶段,1906年的《开明专制论》标志着梁启超“正从政体思维转换到政道思维”[1](P.116)。⑤
王绍光介绍了梁启超对“专制”与“非专制”的定义及其分类,认为梁先生所讲的“专制”,有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而“这里的‘专制’实际上与‘政体’是同义词,而不是政体的一类”。他说梁先生讲的“专制”,就是指“纯粹政体”。“非专制”有君主、贵族、人民合体;君主、人民合体;人民这三类,其实是指“混合政体”。⑥在王绍光看来,梁先生的分类,当然与亚里士多德等西方理论家多有不同。而他之所以这样重新划分,是因为发现西方理论家的政体类型学“实多刺谬”,如“专求诸形式”,而忽略了“精神”这个评判政体“良”与“不良”的标杆[1](p.115-116)。对这个“精神”,梁先生有一段论述,说不论政体形式是什么,是“专制政体”还是“非专制政体”,都可分“开明制”与“野蛮制”,即“良”与“不良”。而这种区别的标准,就在于“国家立制之精神”的不同。请看梁启超是怎么说的:
发表其权力于形式,以束缚人一部分之自由,谓之制。据此定义,更进而研究其所发表之形式,则良焉者谓之开明制,不良焉者谓之野蛮制。由专断而以不良的形式发表其权力,谓之野蛮专制。由专断而以良的形式发表其权力,谓之开明专制。(附注)开明制,野蛮制,不惟专制的国家有之而已。以公意发表良形式者,谓之开明的非专制,以公意发表不良之形式者,谓之野蛮的非专制。如美国当南北战争以前之奴隶制度,即所谓野蛮的非专制也。然则何所据以鉴定其形式之良不良,实续起之一最要问题也。欲解决此问题,则不能专求诸形式,而当求诸形式所自出之精神。国家所贵乎有制者,以其内之可以调和竞争,外之可以助长竞争也。二者实相因为用,故可以一贯之,而命之曰国家立制之精神。其所发表之形式,遵此精神者,谓之良;其所发表之形式,反此精神者,谓之不良。……如是者谓之良,反是者谓之不良。于专制国有然,于非专制国亦有然[9](p.1455)。
对这段论述和王绍光的解读,有四个问题需要讨论:
其一,梁启超说西方理论家的政体分类“实多刺谬”,其中之一是王绍光所归结的忽略了“国家立制之精神”吗?我们来看梁先生自己是如何解释的。梁氏针对其新的分类,在“附注”中说:“国家之分类,泰西学者,历数千年,迄无定论。亚里士多德分为君主国、贵族国、民主国,孟德斯鸠分为公治国、君主国、专主国(名称依严译《法意》),皆其最有名者也。而近世学者,述近世国家之分类,大率分为专制君主国、立宪君主国、立宪民主国,吾以为此分类甚不正确。何以故?专制者不独君主国,而民主国亦有非立宪者。(有立宪之名,无立宪之实,则等于非立宪也。)故以论理学律之,实多刺谬也。吾之分类法,与前此东西学者之分类,皆有异同。”[9](P.1453)显而易见,梁先生在这里只是为其将国家分为“专制”与“非专制”两类作一合理性的论证。在他看来,“克林威尔时代,大拿破仑为执政官、小拿破仑为大统领时代,所以命之曰‘民主的专制者’,以其得任意蹂躏宪法也。专制与非专制一以宪法之有无为断。”[9](P.1453)而他认为,近世的西方学者,恰恰就忽视了民主国也同样有“非立宪”(即“专制”)这一历史事实。所以,他们的政体类型学,“以论理学律之,实多刺谬也”。西方政体类型学之所以“甚不正确”,梁启超在此指明的原因,仅此而已,而没有涉及王绍光所指出的对“国家立制之精神”的忽略。而且,毫无疑问的是,梁启超对国家所作的新的分类,虽然因其划分标准不同而与其他的政体类型学“皆有异同”,但它无疑也是一种政体类型学,而绝非否认、消解政体的分类学。这是王绍光也予以承认的。
其二,梁启超谈到了政治及其制度的“良”与“不良”,这代表梁先生偏离其“政体思维”而偏向了“政道思维”吗?其实,梁先生在此表达的意思很清楚:“国家立制之精神”,当然是政体这个形式“所自出之精神”,因此,政体形式的良与不良,不能“专求诸形式”,是指既要“求诸形式”,又要“求诸精神”。即使梁先生是指只能“求诸精神”,而不能“求诸形式”,那么,这个精神也是“形式所自出之精神”,而不是脱离政体或在政体之外的王绍光那个“政道”领域中的精神。换句话说,对梁启超而言,强调“求诸精神”并不超出解决政体(形式)问题的范围,所以,它并非意味着梁先生在思考不同于政体问题的所谓“政道”问题。应当看到,梁先生对“国家立制之精神”的追问,仍然是渊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包含“目的论”或“价值论”的政体理论。所以,梁启超对政制“良”与“不良”的分析,也属于他的政体理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对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材料,可以佐证王绍光的理解有不确之处。这个材料就是梁启超在1906年发表的《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一文(1906年3月9日《新民丛报》第76号)。该文认为:“立宪有两种:一曰君主立宪,二曰共和立宪。”对“共和立宪”的概念,梁先生有一个明确的解释。他指出:“吾示有界说二:(一)共和立宪制,其根本精神,不可不采卢梭之国民总意说。盖一切立法行政,苟非原本于国民总意,不足为纯粹的共和也。(二)共和立宪制,其统治形式,不可不采孟德斯鸠之三权分立论。盖非三权分立,遂不免于一机关之专制也。以上二端,精神形式,结合为一,遂成一共和立宪之概念。此概念谅为言共和立宪者所能承认也[10](p.1645)。这段话中所说的“精神形式,结合为一,遂成一共和立宪之概念”,显然是与上述《开明专制论》的论断同为一调且同为一脉的。
其三,梁启超对“专制”与“非专制”的优劣,是否有比较之论?作为阐明“开明专制”之重要意义以及论证中国应该实行“开明专制”的经典论著,《开明专制论》写道:“准是以谈,则国家所最希望者,在其制之开明而非野蛮耳。诚为开明,则专与非专,固可勿问。何也?其所受之结果无差别也。”[9](p.1456)这是说,只要为政的制度、法制(形式)是开明的、“良”的,其是否为专制,则可以不予究诘。该文还指出:“然则开明专制政体与非专制政体,究孰优?曰:是难言也。以主观论,则非专制之优于专制,似可一言而决。以客观论,则决其不若是之易易也。”[9](1462)这似乎反映了梁启超的某种“政道思维”。但是,梁先生同时也认为,无可置疑,在完全的专制国与完全的非专制国之间,显然也有着明显的优劣长短之别,即“非专制国优于专制国”。他说:一方面,从权原上看,“专制者,虽有极良之形式,一旦破坏之,而被制者无如何也。虽有极不良之形式,继续保守之,而被制者无如何也。”而非专制者则与此相反,被制者对破坏“极良之形式”的行为必定进行制约与追究,对“极不良之形式”也必定推动其废止或改良。另一方面,从“良”与“不良”的得、失上言:“非专制的国家,其得开明制也易,既得而失之也难;专制的国家,其得开明制也难,既得而失之也易。”[9](p.1454、1456)这一“非专制国优于专制国”的论说,隐约显现出梁启超对非专制的优良政制的期待,而非仅仅止步于“开明专制”。这就引出了下面第四个问题。
其四,梁启超倡议“开明专制”的良苦用心是什么?亦即其最终的目标是什么?这个目标,在梁先生那里其实也是十分明确的,就是追求和实现(君主)立宪政体。⑦在《开明专制论》的“著者识”中,梁先生自陈:“本篇虽主张开明专制,然与立宪主义不相矛盾,读至终篇自可见其用意之所在。”[9](P.1451)他虽然断言其时的中国“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但他更明确认定:“国家又非可以专制终也,则所余者,惟有君主立宪之一途。”所以,“君主立宪,固吾党所标政纲,蕲必得之而后已者也”。这种“立宪制之纲领不一端,而议院之开设,当其最重要之一也。”只是“今日尚未能行”而已[9](P.1483)。1903年,梁先生的美国梦破碎,结果去“梦俄罗斯”。如今,“梦俄罗斯”的用意,其实又在于达成(君主)立宪政体,而并非最终只成就一个“俄罗斯”。梁先生之所以倡议“开明专制”,正是因为在他看来,凡是普通国家,必须经过开明专制时代,然后才能“进于立宪,此国家进步之顺序也”。如若不得已而发生革命,“革命之后,再经一度开明专制,乃进于立宪”。总而言之,“开明专制者,实立宪之过渡也,立宪之预备也。”[9](1464)中国当然也不能例外,梁启超说:“今日中国当以开明专制为立宪制之预备。”[9](P.1470)⑧而这岂不表明,梁先生的《开明专制论》所孜孜以求的,正是中国政体问题的根本解决吗?可以说,在梁启超看来,(君主)立宪政体是原则和方向,“开明专制”则为实现(君主)立宪政体的手段和途径。如果不紧扣这一经“开明专制”到(君主)立宪政体的谋划,显然会错解梁先生“开明专制论”的苦心孤诣。
既然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所“怀抱之意见”,正如他在“著者识”中所言,乃是阐发“欲救中国必用开明专制”的种种理由,而其最终的主旨,又在于通过“开明专制”的预备与过渡,以解决中国的立宪主义政体建设问题,而不是想用“政道”来取代“政体”,那么,王绍光关于该文表明梁启超“正从政体思维转换到政道思维”的看法,无疑值得再推敲了。
不仅如此,梁先生是把“开明专制”视为“立宪之过渡”的,这就有必要考察一下《开明专制论》之后的梁先生,是否仍在继续发挥其“政体思维”?或者是否“转换到政道思维”?从王绍光所述的时间分期及其分析思路来看,“越往后”,包括1906至1909年,应属于梁启超延续《开明专制论》所开辟的方向而转向“政道思维”的一段时光。如其不然,则一方面意味着王绍光所说梁先生正在上述“转换”的途中,即使已经真切出现,但随后就戛然而止了,另一方面,说梁先生辛亥革命前后最终转入了“政道思维”这一结局,当然也缺乏思想历程上的过渡与积淀。
众所周知,1906至1911年的六年间,正是清室诏谕“仿行宪政”并掀动预备立宪的热闹岁月。而作为立宪派一巨子的梁启超,自然不可能缺席这一宪政运动。仅就其1906至1909年对“(君主)立宪政体”的倡导与讨论而言,梁启超对“政体思维”的坚持,是清晰可观的。如他在《政治与人民》(1907年10月)一文中认为,不论政治的目的是什么,“要之,无论从何种方面观之,而凡人民之生死荣瘁,盖无一不系命于政治。”所以,要救国救民,从根本上就必须改良政治。但怎样才能改良政治呢?梁先生指出:关键是建立良好的政体。
故欲求政治之能良,莫急于有监督机关以与执行机关相对立。执行机关者何?政府是也。监督机关者何?国会是也。故国会者,良政治之源泉也。今世立宪国,惟知此义也。……由此言之,则凡无国会之国,其政治决无术以进于良;凡有国会之国,其政治亦决无术以堕于不良,何以故?以政治之良否,恒因监督之者之有无故,而监督政治之实,非国会莫能举然则人民而欲求得良政治也,亦曰求得国会焉而己矣[11](p.1708-1709)。
同年10月,梁先生更是在《政闻社宣言书》中层层剖析,论断“政体解决”为拯救中国的根本大道。第一层,他说中国的危亡,恶根在于政府,亦当通过“改造政府”而拔除这一恶根:“今日之中国,殆哉岌岌乎!……问中国当由何道而可以必免于亡,遍国中几罔知所以为对也。夫此问题亦何难解决之与有,今日之恶果,皆政府艺之,改造政府,则恶根拔而恶果遂取次以消除矣。”[12](p.1711)第二层,认为“改造政府”,就是建成立宪政治:“夫所谓改造政府,所谓反对专制,申言之,则不外求立宪政治之成立而已。”[12](p.1713)第三层,他具体列明“改造政府”的四大纲领,即“一曰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二曰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三曰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四曰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总而论之,“以上所举虽寥寥四纲,窃谓中国前途之安危存亡,盖系于是矣。若夫对于军事上,对于财政上、对于教育上、对于国民经济上,吾党盖亦皆薄有所主张焉,然此皆国会开设后责任政府成立后之问题。在现政府之下,一切无所着手,言之犹空言也,故急其所急,外此暂勿及也。”[12](p.1714-1715)这即是说,要解决军事、财政、教育、国民经济上的问题,首先必须解决政体问题。这正是王绍光所说“政体思维”的基本见解。
1908年,梁启超等人又说:“立宪政体为富强之源”,“立宪政体之精神,在设立议决机关,以与行政机关相维系”。而“此诚致治之本,而举国臣民所欢抃以迎者也。”[13](528)他们又期待:“今中国当预备立宪时代,苟能正定资政院之权限,立责任内阁,使大臣对于资政院而负责任,则郅治之隆,亦可计日而待矣。”[13](p.544)这显然是把立宪政体视为致治之本,并把立宪政体视为中国达成郅治之隆的决定性前提。
(三)王绍光认为,第三个阶段,辛亥前后,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梁启超越来越重视“政体以外的因素”[1](p.116)。
对这一阶段的起始与终点,王绍光并未明言,从他所谈到的材料来看,早至梁先生1910年3月的《立宪政体与政治道德》,晚至其1915年的《政治之基础与言论家之指针》。所以,他所谓“辛亥前后”,大概是指1910至1915年之间的五、六年时间。
从时间顺序出发,我们先来看王绍光提到的《立宪政体与政治道德》(1910年3月)一文。他没有引用该文中的任何一段论述,但通过在注释中加以提及,意在表明梁启超此时已在“最终转向政道思维”。梁先生在该文中强调,正如法与人不可偏废一样,政体与人也不可偏废,尤其是为政者,必须具备良好的政治道德。对此,他引述孟德斯鸠曰:“凡一国之立,必有所恃。专制政体之国恃威力,少数政体之国恃名誉,而立宪政体所恃以立国者则道德也。”就此而言,梁先生的确认为政体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相反,政体的运行还必须依赖于有道德的为政之人。但是,梁先生实际上已经把“为政在人”的意义,置于现代政体之下来阐释,而与孔子的原意已经相去一段距离了。他还谈到,立宪政体的得人之道,要优越于其他政体:“立宪政体之为政者,其于得人之道,则较易焉耳”[14](p.2066)。这即是说,一方面,立宪政体的维持要恃凭政治道德;另一方面,为政者的政治道德在立宪政体之下较为易得。总之,政治道德并非脱离立宪政体而存在。况且,无论如何,强调为政者的政治道德和公民的公共精神,恐怕不能完全等同于王绍光所说的“政道思维”吧?
应当看到,1910至1911年,梁启超的“政体思维”不仅未见消散,反而屡次大放光亮。如他在《立宪九年筹备案恭跋》(1910年2月)中断言:“宪政之能成立与否,则数千年国家之存亡、数万国民之生死系之。”[15](560)又如,《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1910年11月)一文宣告:立宪政体是中国振兴实业之母。他认为,中国欲振兴实业,其首要的必由之路,在于有善良政治,即改良国会和政府,从而确立立宪的、法治的政体。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他说:
然则中国欲振兴实业,其道何由?曰:首须确定立宪政体,举法治国之实,使国民咸安习于法律状态。次则立教育方针,养成国民公德,使责任心日以发达。次则将企业必需之机关,一一整备之无使缺。次则用种种方法,随时掖进国民企业能力。四者有一不举,而哓哓然言振兴实业,皆梦呓之言也。然养公德、整机关、奖能力之三事,皆非借善良之政治不能为功,故前一事又为后三事之母也。昔有人问拿破仑以战胜之术,拿破仑答之,一则曰金,再则曰金,三则亦曰金。试有人问我以中国振兴实业之第一义从何下手,吾必答曰改良政治组织;然则第二义从何下手,吾亦答曰改良政治组织;然则第三义从何下手,吾亦惟答曰改良政治组织。盖政治组织诚能改良,则一切应举者自相次毕举。政治组织不能改良,则多举一事即多丛一弊。与其举之也,不如其废之也。然则所谓改良政治组织者奈何?曰:国会而已矣,责任内阁而已矣[16](P.1979)。
到了1911年,梁先生也持有同样的“政体思维”。例如,他在《敬告国人之误解宪政者》(1911年2月)一文中,针对清政府摧残“在立宪政体下为万不可缺”的资政院(国会)这一违法行径时说:“吾侪若谓中国自今以往可以毋立宪也,夫复何言?若信中国非立宪不足以救亡,则此未离襁褓之资政院,宜如何深惜调护,其忍自为牛羊以牧此萌蘖蕊也!”[17](p.2418)其后又在《〈法政杂志〉序》(1911年3月)中言道:“盖以中国今日,殆儳然不可以俄顷即安。苟非政治现象大有所变,则国且不纲,而凡百更安所丽!朝野达识热诚之士,日以宪政相呼号,皆为是也。”[18](p.562)
所以,王绍光认定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前就转向了“政道思维”,恐怕于其学术史实不完全相符。
那么,辛亥革命之后,梁启超的政体思想又是怎样呢?王绍光为了支持其转向“政道思维”的识判,引用了1912年《宪法之三大精神》⑨中所说的一段话:“政在一人者,遇尧舜则治,遇桀纣则乱。政在民众者,遇好善之民则治,遇好暴之民则乱。”在王先生看来,这意味着梁启超强调,为政致治的好坏不能光看政体,比政体“更重要的是道德”。
这里有两个问题:
第一、该段文字出自梁启超讨论“国权与民权调和”问题的那一部分论述之中,梁先生说:
自民权说之昌,而欧西政治,日以改良,论者辄以此为民权易于致治之显证,殊不知政治无绝对之美,政在一人者,遇尧舜则治,遇桀纣则乱,政在民众者,遇好善之民则治,遇好暴之民则乱。其理正同,若必谓以众为政,斯长治久安即可操券,则天下岂复有乱危之国哉。且极端之民权说,其不适用于政治实际者,尚有多端,……夫各种政制,各有所短,而从众较为近正,此义诚无以为难也。然必谓惟此为至善之符,则一反诘而且穷于应。……谓从众必能善治,此百年前欧洲学者所构之幻想也,及其后累积经验,而事实恒适得其反,故近世学者,于此种政制,类多失望。……我中国今日俨然共和矣,民权之论,洋洋盈耳,诚不忧其夭阏,所患者,甚嚣尘上,钝国权之作用,不获整齐于内竞胜于外耳[19](p.2563-2564)。
有鉴于此,梁先生主张,在今日的中国,制定宪法,应当“稍畸重国权主义以济民权主义之穷”,作为宪法所宜采纳的精神之一[19](p.2564)。故而,王绍光引用那一句所在的这一段论述,其主旨并非论证“道德比政体更重要”这一问题,而是阐述“极端民权之说”的不合理之处,从而说明今日之所以要“稍畸重国权主义以济民权主义之穷”的道理。即使那一句话有“强调道德”的意味,但也是不同政体之下的问题,即“政在一人”、“政在民众”两种政体下统治者和民众的素质好坏问题,以说明“政治无绝对之美”。所以,梁先生才说:“各种政制,各有所短”。而这决定了十分有必要在宪法中调和国权主义与民权主义。梁启超在该文中,原本就是分析宪法的三大调和精神,即“国权与民权调和”、“立法权与行政权调和”、“中央权与地方权调和”,这其中的任何一项,都属于或者至少牵涉到政体的设置问题。
第二、尤为重要的是,就在王绍光征引的这篇文章中,梁启超十分清楚地表达了他一贯的“政体思维”,也就是强调改良政治,其“枢机恒在政体”,并对解决中国的政体问题抱有很高的期盼,认为若能解决,则是“不朽之盛业”,而且“将永为世界模范”,因而要致力于从学理上探讨这一至关重大的问题。他在“著者识”中写道:
以吾平昔之所信,总以为国体与政体绝不相蒙,而政象之能否止于至善,其枢机则恒在政体而不在国体。无论在何种国体之下,皆可以从事于政体之选择,国体为简单的具象,政体则为复杂的抽象,故国体只有两极端,凡国必丽于其一,政体其参伍错综,千差万别,各国虽相效,而终不能尽从同也。而形式标毫厘之异,即精神生千里之殊,善谋国者,外揆时势,内审国情,而求建设一与己国现时最适之政体,所谓不朽之盛业,于是乎在矣。若此者,管其枢,植其基,其惟宪法乎,夫以广土众民之国,而欲行完全之立宪政体,非独共和国体以为艰也,即君主国体亦固不易。……夫专制之不能生存于今日,又岂待问?若中国终不能向专制政体以外讨生活,则国尚有自存之道耶?故我国此次新政之建设,若克底于成,则岂惟一新国命而已。且将永为世界模范。何也?大共和国大立宪国试验成功与否,实将于我国焉决之也[19](p.2560-2561)。
在这里,梁启超的“政体思维”就更是昭彰显著了。其中,“国体与政体绝不相蒙,而政象之能否止于至善,其枢机则恒在政体而不在国体”,这一“平昔之所信”的观点,不正是梁启超“政体思维”的典型告白吗?而在该文中,并未见他对此有深刻的检讨和重大的修正,可见此时的梁先生依然信奉这一“平昔之所信”。与此同时,梁先生说“大共和国大立宪国试验成功与否”,实际上将取决于中国的共和立宪的新政体,亦可见他赋予中国共和立宪政体建设以超乎寻常的重要意义。
王绍光引证的另一段材料,是《政治之基础与言论家之指针》(1915年)中的论述。在民初,关于“联邦制之利病,国会制之得失”的争论很激烈,针对这些争论,梁启超指出:
吾凡欲以证明此种种者,皆治具,而非制治清浊之原。我国人试思之,彼帝制也,共和也,单一也,联邦也,独裁也,多决也,此各种政制中,任举其一,皆尝有国焉行之而善其治者。我国则此数年中,此各种政治,已一一经尝试而无所遗,曷为善治终不可得睹?则治本必有存乎政制之外者,从可推矣。盖无论帝制共和单一联邦独裁多决,而运用之者皆此时代之中国人耳。钧是人也,谓运用甲制度不能致治者,易以乙制度,即能致治,吾之愚顽,实不识其解。……我国民当思十余年之政制,曷为维持焉不能善治,破坏焉亦不能善治,破坏维持,循环数度,终不能善治,则知其病因必有在政制之外者,不剔其病因而疗药之,则或维持至数十年,或破坏至十数度,其不能善治如故也。则夫政制论之辨争,其亦可以小休矣[20](p.2796)。
这是梁启超在历经民初政制屡遭变故致使政局激荡之后所发出的感慨,特别是他揭示出一个深层的问题:“治本必有存乎政制之外者”;或者之所以不能善治,其“病因必有在政制之外者”。这使得王先生认为,梁启超在这里表达的意思很清楚:“改变政治的关键不在于改变政体;政体并非政治之本。”[1](P.116)
但是,问题在于,依据梁启超表达的“治本”及政乱的病因“必有存乎政制之外者”,就可以认定梁先生转向了“政道思维”吗?
其实,在对梁先生这个第三阶段的所谓政治思想变化所作的描述中,王绍光无意之间(他自己也可能未察觉到)作了一个使人迷惑的转换。这个转换是什么呢?他在前面说梁启超在1897至1902年期间形成了“政体思维”,1903年开始怀疑“政体思维”,其后又认定1906年的《开明专制论》标志着梁先生“正从政体思维转换到政道思维”。按照这个历史脉络的必然进程,紧接着就应该是论证梁先生什么时候或在哪篇论著中完成了向“政道思维”的“最终转入”。可是,王绍光并未作这样的考察与论证。他进一步分析的,却是梁先生在思考政治问题时,并不认为政体是改变政治的关键,政体并非政治之本,而是越来越重视“政体以外的因素”。这就很自然地生发出一个颇为关键的问题:即使梁启超指出政体不是改变政治的关键,这就意味着他认为“政道”是关键吗?他认为政体并非政治之本,也就等于说“政道”是政治之本吗?亦即越来越重视“政体以外的因素”,就等于“政道思维”吗?总而言之,“政体以外的因素”全都属于“政道”,从而凡是对“政体以外的因素”进行的政治分析,即为“政道思维”吗?王绍光的确是按照这样的思路来处理的。但是,从王先生对“政道”概念所作的界说来看,却无法得出这样肯定的结论。譬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和政体,政治和政体都同属于经济所决定的上层建筑,政治与政体当然互相关联、互相影响,但是,在思考政治问题或进行政治分析时,必须看到,经济关系无疑是比政体重要得多的决定性因素。然而,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分析范式,这种重视从政体以外的经济因素和阶级本质因素来思考政治问题的立场和方式,也是一种“政道思维”吗?
由于以上这个让人无法理解的问题与论域的转换,即使王绍光根据《政治之基础与言论家之指针》那段论述所归纳出来的梁启超的那个“意思”,完全是准确无误的,但却不能由此证明梁先生“最终转入政道思维”。为什么呢?因为《政治之基础与言论家之方针》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政治基础在于社会耶?抑社会基础系于政治耶?更申言之,必先有良政治然后有良社会耶?抑先有良社会然后有良政治耶?此二义者,盖各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对这两种观点,梁启超赞同“政治基础在社会之说。”[20](p.2793)正是根据这一学说,他才发表了上述那段感慨,认为“政制论之辨争,其亦可以小休矣。”在此时梁启超的思虑之中,没有什么比“社会”这个政治的基础更重要的问题。那么,如何来建设“社会”这个政治基础呢?梁先生的答案是从事“社会教育”、进行“社会事业”的建设。他说:运用现代政治的一系列必要条件(梁先生在文中列举了八个必要条件),只能由“社会教育”、“社会事业”来奠定和准备。不然的话,“则舍社会教育外,更有何途可致者?此真孟子所谓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蓄,终身不得,虽曰辽缓,将安所避?”他又说:“吾以为惟当乘今日政象小康之际,合全国聪智勇毅之士,共戮力于社会事业,或遂能树若干之基础,他日虽有意外之变乱,犹足以支。而非然者,缫演十年来失败之迹,而国家元气,且屡斫而不可复矣。”[20](p.2796、2797)十分明显,梁启超在这里讨论的,虽然是政体以外非常重要的“教育”因素、“社会”因素,然而并非是王绍光所界定的那个“政道”。所以,王先生或许误解了梁启超“作此论之微意”[20](p.2797)。
对梁启超在民初是否真的“对政体决定论更加怀疑,认定政治之根本不在政体”[1](P.116),因而从“政体思维”转向了“政道思维”,如果进一步往后延伸来看梁先生的一些论著,也同样不能支持王绍光的论断。例如,梁先生在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1915年8月)中,自称“平生只问政体不问国体如鄙人者”[21](p.2906),并说:“吾侪平昔持论,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故以为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国体与政体,本截然不相蒙。”[21](p.2902)这个“平昔持论”,与上文所引《宪法之三大精神》一文中所说的“平昔之所信”,完全同调。随后,梁启超撰写的《国民浅训》(1916年),分列专章解释“国体”和“立宪”(政体),同样申明“政体解决”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他说:世界各国,“自从近百年来,相率改专制为立宪,使全国人民,皆有机会与闻国事。官吏权限严明,无从作弊,因此政务渐渐改良,遂有今日。”依据这一通例来衡断,则“我国若要转贫为富转弱为强,亦须从此着手。当前清光绪末年,已经许多人渐明此理,当时亦并非一定不要皇帝。但使政体真能立宪,则国体为君主为共和,原无所不可。”他认为:“夫共和必与立宪相缘。”中国人民“真有爱国之诚,共趋立宪之轨,庶乎国体可以不坠,而国家可以日兴也。”或者,“如此则政治安得不一新,而国家安得不渐强。”[22](p.2837)这些论述表明,“政体”问题在民初的梁启超心目中仍然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其早期以来形成并逐步凝结、一以贯之的“政体思维”,又是何等的顽固绵长。
①王绍光在另外的文章中,也直接把“政体思维”归结为“政体决定论”,如“中国民主政治之道”,载《人民论坛》2011年第1期;“中式政道思维还是西式政体思维”,载《人民论坛》2012年第12期。
②公元2011年8月6-7日,“中国文化论坛第七届(2011)年会”在北京大学召开。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绍光教授,在会议上报告了他的新作“政体与政道:中西政治分析的异同”。该论文的主要观点,先前已发表于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和韩毓海合著并由韩毓海执笔的《人间正道》(中国人民大学2011年7月版)一书的“中国民主政治之道”部分。该部分的内容,同时又以“政体重要,还是政道重要”为题,摘录发表于《民主与科学》2011年第4期(8月)。其后,该文收入上述年会的论文集,题为《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王绍光主编),三联书店2012年7月版。王绍光为该论文集所作的“序”,也进一步论述了其论文中的基本观点。而该“序”的精华部分,亦以“两个关键词”为题,发表于《读书》杂志2012年第10期。
③《新民说》各节发表的时间不一,从1902年2月8日《新民丛报》第1号至1906年1月9日第72号陆续刊载完毕。本段引文出自其“论政治能力”一节,发表于1904年6月28日《新民丛报》第49号。《梁启超年谱长编》也说:1904年,梁启超“关于政论方面,有《论政治能力》一文,……”(丁文江、赵丰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7页)。《梁启超全集》将其全部记为1902年,王绍光亦据此而注为1902年,本文尾注同样依此处理。但若据1904年,王绍光将这段论述视为早期梁启超“政体思维”的表达,而认为1903年之后梁先生开始怀疑“政体思维”,则难免有矛盾之处。
④梁启超在1902年下半年还发出《拟讨专制政体檄》,严厉指控专制政体:“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大仇也!……使我数千年历史以脓血充塞者谁乎?专制政体也。使我数万里土地为虎狼窟穴者谁乎?专制政体也。使我数百兆人民向地狱过活者谁乎?专制政体也。”又具体声讨专制政体的十大罪状,声言与专制政体势不两立:“我辈实不可复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我辈实不忍复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有专制则无我辈,有我辈则无专制。我不愿与之共立,我宁愿与之偕亡!”并要“誓翦灭此而后朝食”。(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0页)此外,陈书良选编的《梁启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也收录了该文。
⑤王绍光根据《梁启超全集》,说《开明专制论》出版于1905年,但实际上,该文发表于1906年1至3月的《新民丛报》。
⑥按梁启超新的分类,国家可分为“专制的国家”和“非专制的国家”。“专制的国家”包括“君主的专制国家”(中国、土耳其、俄罗斯等)、“贵族的专制国家”(斯巴达、寡人政治等)、“民主的专制国家”(如克伦威尔时代的英国、罗伯斯庇尔及大拿破仑任执政官时代等),而“非专制的国家”包括“君主贵族人民合体的非专制国家”、“君主人民合体的非专制国家”、“人民的非专制国家”(民主共和国家)。载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5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3页。
⑦萧公权论断说,《开明专制论》“全篇宗旨在为君主立宪张目”,参见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498页。
⑧梁启超在《1906年致蒋观云》中亦解释说:“弟所谓开明专制,实则祖述笕克彦氏之说,谓立宪过渡民选议院未成立之时代云尔。日本太政官时代之政体,即弟所谓开明专制,而公所谓宪胚非有二物也。弟之用此名则有所激而言,弟持论每喜走极端,以刺激一般人之脑识,此亦其惯技耳。”参见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20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949页。
⑨王绍光将该文发表的时间注为1911年,《梁启超全集》和《梁启超法学文集》都记为1912年。该文注明为“元年除夕”,实际上发表于1913年《庸言》第1卷第4、6号(1月16日、2月16日)。
标签:梁启超论文; 王绍光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共和时代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梁启超全集论文; 开明专制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