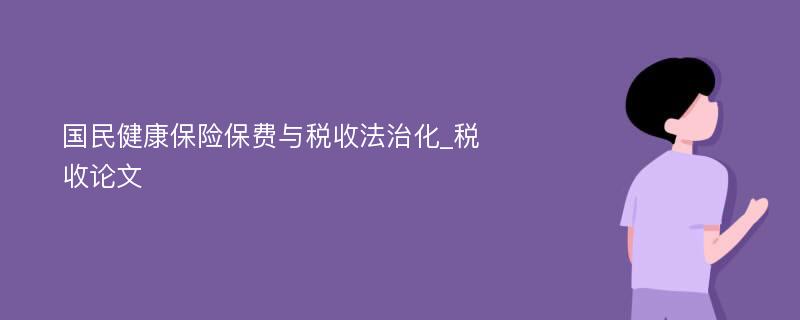
国民健康保险费和税收法律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险费论文,国民论文,主义论文,税收法律论文,健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2-6274(2007)02-010-10
日本的最高法院在平成18(2006)年3月1日,围绕着国民健康保险费是否符合实质意义的税收做出了最高院(大法庭)判决。本文的目的是介绍与此判决相关的各种法学原理并评论此判决是否恰当。
为了正确理解此判决的意图,有必要理解作为日本社会保险制度核心的国民健康保险制度。因此,我想在介绍判决之前,先对社会保障、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的概念以及国民健康保险制度进行说明。
一、社会保障
何谓社会保障,根据论述者依据的立场不同,有多种定义。然而,合乎标准的定义大概是社会保障制度审议会在昭和25(1950)年颁布的劝告中提出的:“所谓社会保障制度,就是对疾病、负伤、生育、残障、死亡、老龄、失业、多子女及其他原因造成的贫困,通过保险的方法或国家直接负担的方式提供经济上的保障;对陷入生活困境者,通过国家扶助给予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与此同时,努力增进公共卫生和社会福利,以期全体国民都能切实享有有文化的社会成员应当享有的生活。”
据此定义,社会保障按照两种方法实施。第一种是保险的方法,第二种是国家直接负担的方法。今天议论的只是按照第一种方法来实施社会保障这一情形。
二、社会保险
(一)社会保险的含义
所谓保险的方法,是指为了将商法中规定的“保险”健全运营下去,而利用开发的诸多技术来实施社会保障的方法。
所谓商法上的保险,以此类保险典型的损害保险为例,它是根据“当事人一方约定补偿对方因偶然的一定事故所发生的损害,对方缴纳费用(商法第629条)”而成立的,它被认为是营业性商行为。如果仅个别地如此缔结契约,商行为不成立。然而如果在作为营业而进行的场合成立,商行为就可以适用商法。因为甚至连商行为性都认可了,所以当然保险费与保险给付之间存在对价性。也就是说,支付愈多的保险费,在遭遇事故时,会得到愈多的保险给付。这种商法上的保险制度与通常的商行为不同,只依赖商人的直觉和经验的形式不能进行营业。把像所谓的大数法则成立那样极大的人群集团作为对象,运用统计的方法进行商品开发时,作为最初的健全的商行为可以成立。为了把如此之大的集团作为对象而进行健全的营业活动,开发各种特殊的技术是必要的。
在社会保障方面,也往往把在可以完全成立大数法则那样的极大的人群集团作为对象。在这种场合,为了健全地运营,作为商行为的保险事业借用各种各样开发的保险技术进行社会保障事业,称为社会保险。也就是说,把在前述社会保障的概念中论及到的各种生活上的困难作为保险事故,以与此相关的保险给付的形式在经济上保障国民生活为目的的制度,称为社会保险。
(二)社会保险的特征
与国家扶助相对比的社会保险,有两大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多以向特定的人征收保险费作为保险给付的全部或一部分的原始基金。被征收保险费的人,通常大多是通过社会保险接受保障。这种情形可以称为原始基金的分担。然而,也有向不接受直接保障的人征收的情形。例如,在把雇员作为对象的医疗保险(职业保险)中,除了作为保障对象的雇员,也要向企业主课以一定的负担。这种企业主负担就是典型。
不过,保险费征收制度的存在,不是社会保险的必须要素。这是因为存在以公费来负担基金全额,但却利用社会保险的形式处理的情况。因社会福利充实而有名的瑞典等国的社会保障在以公费作为原始基金的同时,也以保险的形式处理。而且在日本,例如无缴费制国民年金①,在内容上虽然是直接公费负担的制度,但也利用与给付相适应的保险形式。这是因为,久经商业磨练的保险制度,即使作为给付方式评价,也存在优越的技术性。
第二个特征是,与保险给付相适应,不需要进行资力调查(ミ—ンズテスト②)。要把作为社会保障的公费发放给个人(如生活保护),为决定给付额有必要进行资力调查。这当然是需要时间和费用的。但是,在采用保险形式的情况下,在可以认定发生了一定保险事故时,会自动地进行一定金额的保险给付。因此,可以减轻领受人方及行政方双方的负担。
(三)社会保险的对象
受到上述保险的特征的限定,可以成为社会保险对象的:第一,必须是在统计上达到大数法则成立这一程度的极大的人群集团发生了贫困;第二,必须是不需进行资力调查而可进行统一的处理。
所有国民共同遭遇的生活上的困难,基本上把如成立大数法则般极大的人群集团作为基础,同时,因为保险事故本身容易定型化,所以容易采用保险的方法。具体而言,对医疗、年金、失业以及灾害的社会保障,因为是任何国民共同遭遇的问题,所以容易以保险形式来处理。与此相对,仅仅是国民中个别人遭遇的社会困难是难以以保险形式来处理。原因是,社会保障必需的困难性,因每个国民的情况不同,大数法则不能成立。并且,给付必需的程度也因人而异。因此,通过行政厅进行的个别的资力调查变得十分必要。于是,通过国家直接负担来对待也变得普遍起来。具体说来,因为贫困、身心的障害只是对于特定的国民才发生的问题,所以可以以生活保障或身心障害者保护制度来处理。
(四)伴随保险费征收的社会保险的特征
如上所述,对社会保险来说,保险费的征收不是必需的要素。然而,在日本,社会保险向受益者集团征收保险费却极为普遍。
伴随保险费征收的社会保险制度,具有“二重特性”。二重特性的第一个叫做“保险原理”,它是因借助商事保险技术而产生的特性,它要求保险事故发生的概率(称为“危险”)以及依其进行的保险给付的范围,与受益者缴纳的分担金的范围应该存在严格的比例关系,即对价性③。第二个称为“扶养原理”或者“扶助原理”。它是为了满足救济社会上的经济上的弱者的社会要求,可以不考虑与分担金的关系而进行必要的保险给付,是从作为社会保障的机能中引发的原理。
如今,日本存在多种社会保险制度,而且即使在同一社会保险制度中,在对象、保险费的征收方法、保险给付的实施方法等的关系上,这两个原理的表现方式也未必相同。说到与本报告的题目关系,若保险原理具有优势的话,保险费的实质意义上的税收性则易被否定;若扶养原理具有优势的话,则易被肯定④。在作为保险原理充分具有优势的结果、承认符合实质意义的税收的情况下,即使使用“保险费”这一词汇,对其决定征收,也要求适用税收法律主义,符合法律规定的课税条件等所有内容(对地方标准的问题适用条例)⑤。
因此,不用说仅通过使用“保险”这个词就单纯地承认对价性,是错误的,对缴费制的社会保险直接说保险费与保险给付之间存在对价性,也是错误的。与此决定相适应,详细地理解与各个制度相关的保险原理与扶养原理的优劣关系是必要的。
首先要先介绍几个与之相关的词语:
1.强制加入
在日本,例如关于医疗保险,自昭和36(1961)年以来,推行了国民皆保险制度。结果是,以职业等为标准,所有的国民被强制加入其中任何一种保险。所以,如今不用说参不参加医疗保险的选择权,连参加国家医疗保险中的哪种保险的选择权,也不承认个人享有。
依据判例,强制加入制度是保险原理的要求使然。也就是说,在被当作是国民健康保险的强制参加者不缴纳保险费而发生争议的初期案件⑥中,第一审判决断言“强制加入原则是基于在提高国民健康保险的公共性的同时,防止逆选择进行危险分散的技术性考虑”⑦。最高法院也阐述:“国民健康保险,是遵照相扶共济的精神,对国民的疾病、负伤、生育或死亡,以支付保险金为目的的制度,其保持、增进国民的健康,使他们生活安定,增进公共福利的目的已十分明确,所以,接受保险给付的被保险人理所当然地是可能会发生保险事故的人的全部,并且,在相扶共济的保险性质上参加者应相互地分担因保险事故而产生的个人经济上的损害,这些自不待言⑧。也就是说,虽然不比一审判决更明确,但是基本上提出了把强制加入和相扶共济这一保险基础概念联系起来,这是受支持的(以下称此判决为“强制加入最高法院判决”)。这里最高法院提出了以保险原理为基础来理解医疗保险的观点,对其后的判例产生极大影响⑨。
2.逆选择
上述一审判决中存在“逆选择”这个词。这是保险技术上的语言,它意味着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一方对其选择加入的保险进行肯定。商业上的保险,是以保险参加者中不特定但仅一定比例的人遭遇保险事故为前提,向多数人征收少额保险费而同时对遭遇保险事故的少数人进行大额保险给付这一商品设计的产物。所以,不能允许逆选择。因为如果允许逆选择,作为被保险人,缴纳少额保险费就可以直接地领受极多的保险给付,这样作为合理制度的保险就存在破绽。把保险作为商行为来运行是不可能的。这是在商业上的保险中禁止逆选择的理由。
然而,从逆选择防止这一保险技术上的理由看,如果必然地引入强制加入,这样一来,以任意加入为基础的商法上的保险就不可能作为商行为成立,必然会导致这样的非逻辑的结论。不能不说判例所运用的逻辑显然自相矛盾,存在破绽。
事实上,逆选择的防止意味着,在医疗保险作为商法上的保险来实施时,只允许实际上并未患病、并且是年轻人等在患病危险相对较低的阶段选择保险加入。与此相对,对于所有的地域居民,强制加入意味着对在那时患病危险已非常高的人,当然也对业已患病的人强制加入保险。结果,业已患病的人加入后甚至是在一点也没缴纳保险费的阶段也可立即受领保险给付。因此,强制加入是与逆选择完全对立的、基于扶养原理的价值观而设立的制度。也就是说,强制加入制度的存在明显地表明医疗保险的保险费具有税收的性质。
强制加入中引入的扶养原理的性质,可以说不只在医疗保险中,在伴随强制加入的所有社会保险制度中都是相通的。
三、医疗保险
(一)概要
以保障国民因疾病或伤残的医疗费为目的的社会保障,总称为医疗保险。
日本最早的健康保险制度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大正11(1922)年制定,并于昭和2(1927)年施行。这项制度本来是以从事矿山劳动等危险性事业的工人为对象,后来渐渐地扩大了对象范围。昭和36 (1961)年,通过修改,将剩下的农民等自营业者作为被保险人,完善了国民健康保险制度,实现了国民皆保险,即全体国民都参加了某种形式的医疗保险。
由于日本的医疗保险历史悠久,所以它并不是单一的制度,而是由七种医疗保险立法构成的制度。
根据被保险人是不是雇员,日本的医疗保险大体上可分为雇员保险和居民保险。雇员保险可分为以一般民间雇员为对象的健康保险法[大正11(1922)年法70]和以日工为对象的日工健康保险法[昭和28 (1953)年法192]。此外,加上医疗保险,年金部门的综合性立法还有船员保险法[昭和14(1941)年法 73]、国家公务员互助法[昭和33(1958)年法128]、地方公务员互助法[昭和37(1962)年法152]、私立学校教职工互助法[昭和28(1953)年法245]。居民保险,即为本稿所称的国民健康保险法。
(二)国民健康保险
国民健康保险事业的主体有同行业的自营业者 (医生、牙科医生、药剂师等)的组合和市町村。在此,仅对市町村为主体这一情形进行说明。
在市町村的区域内拥有住所并且没有参加其他医疗保险的人,除正在接受生活保护的人外,全民不管意思如何均自动地参加所在市町村的国民健康保险(《国民健康保险法》第5条、第6条),也就是前面所述的强制加入。虽然叫做“国民”健康保险,外国人如果办理了登记并取得了在留资格,原则上也成为被保险人。
在国民健康保险中,作为保险人的市町村,必须向户主等征收保险费(《国民健康保险法》第76条)。但是,征收国民健康保险税(《地方税法》第703条第4款)的不在此限,换言之,各市町村可以选择是以保险费形式征收还是以保险税形式征收。
保险费和保险税,除名称不同外,在实质性效果这一点上几乎没有差异。但是,在征收决定的期间限制、消灭时效、滞纳处分的优先权的顺序、对规避行为的制裁措施等方面,由于采取税的方式,通常会发生与地方税同样的处理结果和强制力,所以压倒性多数的市町村采用了保险税方式⑩。不过,在秋田市国民健康保险税诉讼中,仙台高等法院秋田支部的判决,做出了其违反税收法律主义并违宪的判决(以下称为“秋田市健康保险税判决”)。结果,许多市町村修改为保险费的征收方式。于是,关于保险费,焦点集中在它与税收法律主义的关系这一点上。本案判决解决的正是这一问题。
各市町村要确定向各参加户征收的国民健康保险税额,就要先计算标准课税总额(11),再根据一定的课税方式向各参加户分配该标准课税总额。此课税方式规定,以所得比例额、资产比例额(两者合称为“应能比例额”)、被保险人均等比例额、户别平等比例额(两者合称为“应益比例额”)这四要素作为课税要素并以此为基础。虽然承认市町村关于采用哪种要素决定课税额有一定范围的选择权(12),但无论采用哪种方式,最终必须达成应能比例额50%、应益比例额 50%的比例。应能比例额可以认为是以财产为基础的定律法,与之相反,应益比例额显然是定额法。因此,与职域保险不同,地域保险由定律法和定额法两要素构成。
在采用国民健康保险费为征收方式的确定方法基本上也没有变化。
四、旭川国民健康保险费诉讼
我想在此简单地说明在日本关于国民健康保险费存在的论点、与此相关的判例和学说,同时,介绍本案判决,并阐述对此的批判。
(一)实质意义的税收概念
本诉讼的第一个论点是宪法上的税收概念。关于这一点,迄今为止还不存在可称为先例的判例。本案是第一次把它作为论点的案件。
关于上文提到的秋田市国民健康保险税案,在形式上,它明显的是税收。与之相对,本案的保险费在形式上不是税收。因此,如果不能被认为实质意义的税收的话,说到底不能适用税收法律主义。
1.学说的状况
《宪法》第84条规定的税收法律主义是实质意义的税收概念,但在形式上限定为法律所称的税收,所以不能适用,这无论在宪法学上还是在税法学上基本上没有异议。
问题在于怎样定义实质意义的税收概念。以往宪法学界的通说,关于实质意义的税收概念,有“通过国家权力对国民单方面征收的金钱债务”(以下称为“广义A说”)(13)的观点,有“虽然在形式上不叫税收,但实质上与税收相同,它不依国民的自由意志决定征收”(以下称为“广义B说”)(14)的观点。特别是广义B说,如今在宪法学会仍是多数说(辻村美代子(15)、浦部法穗(16))。
与此相对,德国税法(Abgabenordnung)第3条规定:“所谓税收,不是作为对特定给付的反向给付,而是为取得收入,公法上的团体对法律上负有给付义务的全体人员征收的金钱给付。”(17)按此规定来理解实质意义的税收概念,这可以说是税法学会的通说(18)。
而且,如今,在宪法学界也有人认为只在符合税收定义的场合适用《宪法》第84条(伊藤正己(19)、户波江二(20)等)、对有对价性的手续费否定其税收性(芦部信喜(21)、佐藤幸治(22)等)、肯定国家法定专营事业的税收性,但否定事实上的专营事业的税收性(阪本昌成(23)等)。这些观点与历来的通说相比,狭义地进行理解的观点增多起来。
2.本案判决
本案判决是日本对实质意义的税收概念进行争议并到达最高法院的第一案。也就是说,本案最高法院判决的最大意义在于确定了实质意义的税收概念。即:“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基于课税权、为了筹集充当经费的资金、不支付对特别给付的反向给付、对符合一定要件的全体成员征收的金钱给付,不管形式如何,都应当比照《宪法》第84条规定的税收征收。”
最高法院早就在所谓的工薪人员税金诉讼(24)中阐述过与此相同的内容。然而,在工薪人员税金诉讼案中,成为焦点的是所得税这种典型的税收。也就是说,实质意义的税收只不过是作为次要点被阐述的。在这个意义上本案是重要的。对这一点,本判决做如下阐述:“与税收不同,市町村实行的国民健康保险保险费是对被保险人取得的保险给付征收的反向给付。如上所述,被上诉人市町村的国民健康保险事业需要的经费的2/3是通过国家资金来维持,因此,不能切断保险费和取得保险给付的地位之间的牵连性。另外,强制加入国民健康保险、强制征收保险费,是源于国民健康保险的目的及性质,即国民健康保险是将接受保险给付的被保险人作为尽可能引起保险事故的人的全部、并且加入者相互分担因保险事故产生的经济上的损害的社会保险。因此,上述保险费不可以直接适用《宪法》第84条的规定(国民健康保险税虽然是目的税,是作为反向给付进行征收,但既然形式上是税,就可以适用《宪法》第84条的规定)。
3.评释
依照德国税法做出的税收定义,对于本案就断定反向给付性维持着国民健康保险费这一点,我认为不妥当。按照判例本身所承认的存在达到经费的2/3的公费负担,表明了它基本上处于扶养原理的支配下。
的确,因为如果支付愈多的保险费就会接受愈多的保险给付的话,在此限度内可以承认保险原理的支配,所以,或许可以说因为公费负担的存在,所以“不能切断保险费与取得保险给付的地位之间的牵连性”。然而,在作为保险费确定基础的诸要素上难以承认保险原理。这也就是说,加入户发生疾病或伤残的比例越高,保险给付就越多。与此相对,保险费因市町村不同而不同,但基本上都根据所得比例额、资产比例额、被保险人均等比例额、户别平等比例额这四要素来计算。所得比例额意味着户的所得越多,应缴保险费就越多。资产比例额意味着户的资产评价额越高,应缴保险费就越多。然而,说到与所得和资产相对应,疾病发生率也会上升,这是不可能的。相反的是,所得和资产越多的户,日常生活水平也越高,居住环境也越好,反倒是疾病率会下降。也即:只要应能比例额占保险费额的50%,就可以切断保险费与取得保险给付之间的牵连性。构成应益比例额的两要素中,被保险人均等比例额是除以被保险人人数的比例。假定无论是谁疾病率都不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肯定牵连性。与之相对,户别平等比例额,是指与户的人数无关(也就是说,一户一人和一户十人是相同的),向每户平等的征收相同的金额。如果认为被保险人均等比例额反映保险原理,那么可以直接说,户别平等保险比例额,体现的是扶养原理而非保险原理。也就是说,有可能在构成保险费的四要素中三个反映扶养原理而只有一个反映保险原理。
当然,是否全部使用这四种要素,是各市町村裁量的问题。这里,作为具体争议对象的旭川市,《国民健康保险条例》规定如下:该《条例》第9条规定,保险费征收额中涉及一般被保险人的基础征收额是:对该户的一般被保险人计算的所得比例额和被保险人均等比例额的合算额的总额,以及对该户计算的户别平等比例额(一般被保险人和退休被保险人等属于同一户时,把该户视为一般被保险人的户计算户别平等比例额)的合计额。也就是说,根据四要素中除了唯一有可能反映保险原理的被保险人均等比例额外的三要素来计算保险费。即,旭川市的保险费的算定有可能100%根据扶养原理计算。因此,不列举特别的理由,断定为存在牵连性这一点是明显不对的。
另外,“强制征收保险费是源于……作为社会保险的国民健康保险的目的及性质”的说明,是盲目遵从先前介绍的逻辑上完全错误地强制加入最高法院判决。自然不能说是恰当的。
从上文来看,旭川市的国民健康保险费因为是 100%处于扶养原理的支配下,所以应当断定为符合实质意义的税收。因此,我不赞同该判决。
另外,本文的括号书对判例也是重要的。即明确表示了关于没有实质意义税收性的形式意义上的税收也适用税收法律主义。如前所述,在秋田市健康保险税判决中,国民健康保险费是税。然而,如果本判决是正确的话,它就不是实质意义上的税收。因此,对形式意义的税收通过适用《宪法》第84条和以括号文的形式解释,确保了判例的统一性。如果不这样的话,在采用保险税方式的市町村,很可能再次引发诉讼。
(二)税收法律主义与课税要件明确主义
1.学说及判例的状况
本文第二个论点是税收法律主义的概念内容。关于这一点,最高法院(大法庭)于昭和37(1962)年2月21日做出的判决可称为先例。“这些规定将根据法律确定纳税人的范围、纳税对象、税率及征税方法为宗旨。”(25)
根据该判决,可以明确所谓税收法律主义,即为课税要件法律主义(以下称为“课税要件法律主义最高法院判决”)。
宪法学界也基本接受上述观点。问题是,在采用前文介绍的广义说的情况下,作为现实问题在狭义税收领域之外,照字面运用该定义是不合理的。因此,便通过“可以适用本条原则”(广义A说)、“应与税收同样对待”(广义B说)之类模糊的表达来回避这一问题。但是,至今仍无人论述这种暧昧性的具体所指。总而言之,什么是原则的适用,在学说上尚未明确。对此提供了一种回答是本判决的第二大意义所在。
本文第三个论点是课税要件明确主义。论及此点的判例有很多,但明确论述该点的是阐述国民健康保险税与税收法律(条例)主义的关系的秋田市健康保险税判决。
首先,该判决就课税要件明确主义做如下论述:
“课税要件法律(条例)主义,以排除行政权的恣意课税为目的,理所当然应包含全部课税要件和税收征收程序必须根据法律(条例)规定的课税要件,法定 (条例)主义和在此法律(条例)上对课税要件的规定必须是尽可能地以一种意思明确表达的课税要件明确主义”。
其次,该判决关于课税要件法定主义进行如下论述:
“尽管在课税要件明确主义之下,关于课税要件的规定要求尽可能以一种意思明确。关于课税要件的规定使用不确定概念是不可避免时,即使在相应场合也不能立刻断定是否违反课税要件明确主义;在其他情况下依照各事项,不确定概念的使用对于税收法律主义的实现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因此,为了谋求税收的公平负担,特别是为了禁止不当的税收回避行为,只要不违背禁止恣意征税的税收法律(条例)主义基本精神,关于课税要件的规定,应该留有使用不确定概念的余地。但是,以立法技术上的困难为由,使用不确定,不明确的概念是当然不被允许的。另外,可以使用的不确定概念必须是依据法律宗旨进行解释能够得出具体含义的概念;在课税要件的规定中使用即使通过解释也不能明确其具体意义的不确定不明确概念,因其无法否定课税权人对征税的恣意介入,而导致忽视税收法律(条例)主义的基本精神,所以不被允许。”
总之,至此论述了税收要件明确主义与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之间的关系。通过该判决要关注的是,追求课税要件明确主义的理由在于,消除“课税权人对征税的恣意干涉”,本判决也支持这个理由。
2.本案判决
本案件的原审法院(札幌高等法院)并没有给出实质意义上的税收概念。虽然保险费不是税收,但是税收法律主义也可类推适用于保险费。最高法院将税收法律主义的适用范围扩大到税收之外,表达了对作为宪法学上历来为通说的广义说的尊敬。
“《宪法》第(84)条规定,对国民设定义务限制权利需要有法律根据,故对于税收应该以严格的形式明文规定。因此,即使是国家、地方公共团体征收税目之外的杂税,也应该遵守按照其性质在法律及法律范围内制定的条例及规则;而仅以杂税不是《宪法》第 84条所规定的内容为由,就不适用上述法律原则是不恰当的。其次,即使是税收之外的杂税,在征税的强制程度等方面有类似于税收的性质,关于这一点也应认为是体现了《宪法》第84条的宗旨。”但是,因为只是限于体现了宪法的宗旨,在具体适用上与纯粹的税收法律主义有所不同。即:“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税收以外的杂税与税收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此外,依照征税目的,杂税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应该综合考虑该杂税的性质、征税目的与强制程度等,来判断法律及条例应以何种程度明确规定征税要件的规则。”因此,应将税收法律主义变化的内容、程度作为下一个问题来解释。如果可以适用税收法律主义,则保险费也当然适用课税要件明确主义。原告自第一审以来始终主张“作为保险费决定基础的征税总额的内容意义不被征收保险费人了解,就不可能检验出其被征收的保险费是否正确”。并且还主张“被告在保险费计算过程中,加入了种种裁量,因此使本案条例的意味很不明确”。总之,整理归纳此两点可以看出,宪法规定是不明确的。
关于这一点最高法院做如下叙述:
“市町村实施的国民健康保险,虽然是以征收保险费的方式,但因在强制加入、强制征收保险费、征收的强制程度上有类似于税收的性质,对此应理解为体现了《宪法》第84条的宗旨;从另一方面来看,保险费仅作为国民健康保险事业需要的费用。因此,基于《宪法》第81条的授权,在《条例》中应如何规定征收要件,除征收的强制程度外,还应综合考虑作为社会保险的国民健康保险的目的、特征等。”
根据前文所述,社会保险因为具有保险原理和扶养原理的双重特性,所以明确性这一概念本身与纯粹的税收有所不同。关于明确性最高法院做出如下认定:
“本案件依《条例》第8条规定,保险费征收总额是以该条第1款规定金额的估算额减去该条第2款规定金额的估算额所得出的金额为标准计算出来的。该条第1款规定金额的估算额,是国民健康保险事业的运营需要的各种费用合算额的估算额;该条第2款规定金额的估算额是,与国民健康保险事业相关收入(保险费除外)合算额的估算额。因为国民健康保险的保险费是作为国民健康保险事业需要的费用而征收的(法第76条原文),以该年度费用减去收入(保险费除外)得出的不足额度的合理估算额为基础计算出征收总额,并按户分担。这一点遵循了征收国民健康保险保险费相互扶助的宗旨及目的。本案也以此为前提。其次,本条例第8条各款明确地规定了可以成为该费用及收入的估算额的对象的详细内容。”
“此外,本案依《条例》第8条规定,保险费征收总额并不是指该条第1款规定金额的估算额减去该条第2款规定金额的估算额所得出的额度,而是以该额度‘为基准计算出的金额’。这一点可以理解为,按照前文所述的保险费征收的宗旨和目的,可预见的征收不足的保险费额度也可以通过保险费收入提供。因此,对照征收总额的计算,通过保险费预定收纳率可以退还一部分前文所述的费用与收入的差额。这样一来就可明确上述该条之规定。”(26)
对此,最高法院论述到:在一审中,原告的问题在于没有客观明确性。换言之,要求课税要件明确主义的根据是秋田市健康保险税判决中阐述的“以排除行政权的恣意征税为目的”。如果不存在恣意征税的可能性,就能确保明确性。因此,即使秋田市在保险费计算过程中加入种种裁量而导致“本条例的意味不明确”,也能够确保保险费的明确性。
3.评释
通常,与行政厅的恣意征税并存,确保纳税人的预见可能性是税收法律主义的根据。(27)换言之,最高法院删掉了在不直接适用税收法律主义的前提下根据税收法律主义的意味确保预见可能性这一点。而如前所述,我认为国民健康保险费符合实质意义的税收概念,所以必然反对这种逻辑。
但是关于书面规定的手续费等方面,与原判决内容相同,该判决与设置防止行政恣意征税的机构组织这一现实是相吻合的。今后在谈到适用《宪法》第84条原则或对其进行类推适用时,就其具体内容而言,我认为该判决可能成为支配性学说。
(三)下位规范的授权界限
1.学说及判例
本文第四个论点是,在课税要件法定主义之下的下位规范的授权界限。关于这一点最高法院认为在“只不过是将部分义务内容的细则授权给国家行政命令规定”(28),这并没有违宪。并且,上述秋田健康保险判决在下文中对此做了更详细的论述:“虽说是课税要件法定(条例)主义,必须在法律(条例)本身中规定全部课税要件,但也不是说关于课税要件都不允许法律授权给行政厅进行命令(规则),但是这种授权命令 (规则)立法,与其他情况相比,要求特别应当限定在最小限度内。”但是,最小限度这种模糊的表达,很难判断出其具体界限。在这层意义上,最近学术界所关注的是东京高等法院平成7(1995)年11月28日的判决。该判决接受上述昭和37(1962)年最高法院的判决,内容如下所述(以下本判决称为“下位规范授权界限东京高等法院判决”):“从这样的宪法宗旨来看,征税细则或其他个别情形允许法律授权给相关税收政令以下的法令规定,但是不得损害税收法律主义的本质。即,假设要规定程序的课税要件,作为课税要件的程序性事项本身由法律规定,在此基础上可以将成为课税要件的程序细节内容授权给政令以下的法令规定。〈中略〉其次,根据税收法律主义解释税收法规时,在是否把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某项事项追加为课税要件时,通常应解释为该事项不是课税要件。且不说上述内容,以‘根据政令的规定’这种抽象的授权语言为根据,通过解释追加某事项为课税要件、并通过政令以下的法令规定其细节内容作为税收关系法律的解释,也是不允许的。”(29)但是,即使是在该判决中也并未论及单方授权给告示是否符合宪法。
关于以上各论点的判断,因审级的不同而不一致,这一点是本案例意味最深的地方。下面在简单说明各个判决的基础上来研究一下最高法院的判决。
2.本案判决
关于该点本案的第一审判决做如下所述:
“所谓告示是指国家机关将其决定的事项等正式广泛地公布于众的行为,并不具有法规的性质。在本案中,被告市长只是将内部决定的保险费率做单方面的告知。”
最高法院并没有像第一审法院那样把告示是否具有法规性质的形式化作为问题,而是进行如下论述:
“这样,本案根据条例明确规定了作为保险费率计算基础的征收总额的计算基准,在此基础上,该计算必需的、与上述费用及收入的各种估算额及估计预定收纳率所需专门技术相关的事项,委托给被上诉人市长进行合理的选择;并且,关于上述估算额等的推算,通过国民健康保险事业特别会计的预算及决算的审议实现了议会的民主统治。”
这样一来,本案根据条例在第8条规定了成为保险费率计算基础的征收总额的计算基准之后,在第 12条第3款规定对于被上诉人市长以该标准为基础决定保险费率,并将决定的保险费率以告示的形式公示,没有违反《国民健康保险法》第81条的规定,并且,也没有违背《宪法》第84条的宗旨。
也就是说,授权下位规范规定事项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本该由法律(条例)本身规定的事项实际上却存在着授权给行政权恣意规定的可能性。但是,通过预算、决算的审议而达到民主统治的情形下,可以避免恣意的征税,所以在此限度内可以允许授权给下位规范规定。并且,告示也只不过是用来公布行政权决定事项的一种公示手段而已。
3.评释
法治主义(《宪法》第41条)以权力分立制为前提,要求公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的行使,必须根据法律进行。《宪法》第84条规定的税收法律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税法相关内容的确认。但是,因为税收征收中不存在对价性这种理论的界限,而且依照纳税能力为征收税收也存在风险,所以税收征收的全部程序都必须依据法律规定。
另外,为了确保国民的预见可能性,课税要件必须在法律标准上以一种意思明确规定(课税要件明确主义),即,不允许行政厅的自由裁量。
下面说说课税要件法定主义。一般认为它比通常的法治主义的情形有更严格的要件。因此,像在第 41条的情形下,必须限制对行政厅有发布执行命令、委任命令的权限。但是,也不能只理解为都不允许法律对下位规范授权。前面介绍过的下位规范授权界限以东京高等法院判决作为界限,理应受到关注,即,“假设要规定程序的课税要件,作为课税要件的程序性事项本身由法律规定,在此基础上可以将成为课税要件的程序细节内容授权给政令以下的法令规定”。即应理解为,禁止无法律根据而通过政令等重新制定课税要件(课税要件法律保留原则)。
第一审判决认为告示不是法的形式,而是向公众公示的手段。因此,制定应当公之于众的法规的权限是否承认应根据课税要件保留原则,是应该论述一下的。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应该支持本判决的逻辑。但是我不支持认为国民健康保险费属于实质意义上的税收,而授予市长过大的权限。
综上,要是没有最高法院的判例,即使明知存在争论点,日本的宪法学者也很少有加深论述的倾向。在此意义上,此次最高法院的判例对日本的宪法学界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事情。在中国今后的公法学发展中,本判决的介绍如果可以被作为他山之石来参考,我就感到很幸运了。
注释:
①在昭和36(1961)年4月1日国民年金制度开始实施时,已经50岁的人[明治44(1911)年4月1日以前出生的人]即使加入缴费年金,保险费缴纳的期间也过短,而且又考虑到那时已经是身体障害者或成为母子家庭的人,虽然他们没有缴纳保险费,也因全部金额由国家负担而发给他们年金(福利年金)。这称为无缴费制年金。
②ミ—ンズテスト(means test)直译为资力调查,是依靠行政厅进行的资产以及收入等的调查的意思,即在采用直接的公费负担制度的情况下,有必要依靠负责的行政厅对社会保障对象人是否具备领受资格进行个别的调查。
③“对价性”这个词在讨论税收概念时被使用。可以说使用“对价性”这个词来说明保险原理,是由于承认保险费与保险给付之间的对价性。
④我在扶养原理优越的场合,承认保险费的实质意义的税收性,因为它是以非对价性、非选择性以及收入目的性这三要素为必要的前提而成立的(参见拙著:《财政法规与宪法原理》八千代出版1996年刊,第225页以下)。根据只要有非选择性,保险费就属于实质意义的税收的广义说的理解,应该不必个别地讨论而可以承认所有的国家社会保险费的税收性。从这个立场出发,明确表示一切社会保险费都属于税收的观点 (参照北野弘久著:《税法学原论》(第5版),青林书院2003年刊,第29页)。
⑤税收法律主义意味着课税要件法定主义,这是长久以来最高法院判例明确说明的。即《宪法》第30条、第84条中的“规定应该理解为,是以不仅有必要根据法律确定纳税人的范围、纳税的对象、税率等,而且征税的方法也要依据法律”。
⑥ 在九州佐贺县小城町发生的强制加入的合宪性争议事件,如下所述。在日本尚未引入国民保险制度的昭和23(1948)年之时,佐贺县小城町基于同年颁布的国民健康保险法第8条第12款“市町村实行国民健康保险之时必须制定关于国民健康保险法的条例”,制定了健康保险条例。而且,以该法第8条第14款“实行国民健康保险的市町村的被保险人是其区域内的户主及其家属”的规定为根据,此条例规定同町的居民都作为强制参加人。对此,拒绝加入以及受到保险费滞纳处分的居民主张“原来国民健康保险制度虽然包含了许多的不完备和缺欠,但并未要求居民必须加入的性质,但是小城町条例强制居民加入,而且以保险费的名义侵害国民的财产权,因此该条例违反《宪法》第19条、第29条第1款、第98条”的规定,其合宪性受到质疑。
⑦关于引用的判决文,参照佐贺县地方法院昭和29(1954)年3月13日行政事件裁判判例集5卷3号第640页。又及,在本文中并未引用,但高等法院判决也登载于判例集中(福冈高裁昭和29(1954)年3月13日行政事件裁判例集5卷3号第805页)。
⑧关于引用的判决文,参照最高法院昭和33(1958)年2月12日最高法院民事判例集12卷2号第190页。
⑨例如,关于这次提起的最高法院判决的原审法院札幌高等法院平成11年12月21日判决,该判决引用上文所述的最高法院判决,否定不是实质意义的税收。又及,拙稿《规定以保险费维持国民健康保险财政的条例与税收法律主义》,参照《平成12年度重要判例解说》ジュリスト 1202号第22页。
⑩关于国民健康保险费和国民健康保险税两制度的异同的详细内容参见:厚生省保险局国民健康保险科主编《逐条详解国民健康保险法》第311条以下。
(11)国民健康保险税的标准课税总额是:在本年度的第一天从支付一般被保险人的疗养给付、特定疗养费以及疗养费所需要的费用的估算额中,扣除掉关于急用给付的一部分负担金总额的估算额后其剩余金额的75%,以及,从缴纳老人保健医疗费筹集金所需费用的金额中扣除掉该费用的国家负担金的估算额以后所得的金额的合计金额(地方税法第703条第4款第2项)。此标准课税总额占到国民健康保险制度总医疗费的四成。
(12)关于市町村可以选择的课税方式,法律上规定了如下三种方法(地方税法第703条第4款第3项)。即,(1)按所得比例额40%、资金比例额10%、被保险人均等比例额35%、户别平等比例额15%的比例四要素全部使用的计算方式;(2)按所得比例额50%、被保险人均等比例额 35%、户别平等比例额15%的比例,由三要素计算的方式;(3)按所得比例额50%、户别平等比例额50%的比例,只有两要素计算的方式。现在,全国3257个市町村中,选择(1)方式的有3014个(92.5%)、选择(2)方式的有199个(6.1%)、选择(3)方式的有42个(1.3%)(参见:漆博雄著《国民健康保险及老人保健制度的财源问题》,载社会保障研究所编:《社会保障的财源政策》,东京大学出版会1994年刊,第145页以下)。通过所谓的平成大合并,多数的市町村合并了。合并后的状况还没有掌握。
(13)参照宫泽俊义著、芦部信喜修订《日本国宪法》,日本评论社刊,第710页以下。准确地说,宫泽俊义所做的定义本身是采用了德国税法的定义方式。而且,论述了“关于不属于固有的‘税收’而完全根据国家权力单方面赋课、征收的金钱,也应适用本条的规定”。也就是说,在带有强制征收性质的场合下,负担金、手续费等等,不管名称如何,都可适用本条的规定。
(14)引自清宫四郎著《宪法Ⅰ》,有斐阁昭和32年刊,第211页。作为这里所提到的符合定义的具体事例,列举了特许费等的课征金、烟草的价格、铁路费用,特别是还不加说明的引用了《财政法》第3条,印认为“法律上或事实上属于国家专营事业的专卖价格或者事业基金”也包含于税收。
(15)辻村美代子在其所著的《宪法》日本评论社2000年刊第520页中,在定义上采用了德国税法的定义方式,其在第522页论述《适用范围》时,进行了如下论述:“《宪法》第84条所称的‘税收’,除了如上述定义的‘固有意义的税收’外,还包含实质上和税收同样强制征收的负担金(城市计划负担金、道路负担金、河川负担金等)、手续费(许可手续费、考试手续费等)、国家专营事业基金(邮政基金等)。而且,与其他学说相对比,此学说最后被称为多数说。
(16)浦部法穗在其著作《宪法学教室〔全订第2版〕》,日本评论社2006刊第552页中,依然采用德国税法的形式做出了税收定义,同时阐述了“要对国民单方面、强制的征收金钱给付就必须依照国会制定的法律”这一宗旨,并把《财税法》第3条作为规定这一宗旨的法律。而且,也称此学说为通说。
(17)《德国税法》第3条的翻译,引自畠山《税收法》第6页。
(18)作为代表性的见解,参见田中二郎《税收法》有斐阁法律学会集11,昭和43年刊,第1页以下。
(19)伊藤正己其著作《宪法〔第3版〕》,弘文堂1995年刊第468页有如下阐述:“从基于财政民主主义、广义上承认国家财政受国会的调控的宗旨来看,负担金(例如道路占用费)、特权费(如特许费)、公法上的手续费(如营业许可手续费、考试手续费)、国家专营事业基金(如邮政基金)等都包含于‘税收’里,这可以说是在国会的意思之下制定的,但对于将其视为宪法的要求是有疑问的。如果按照税收考虑的话,它们都有补偿的性质,例如,消费税含有税收的性质,也含有超过单纯补偿以外的性质(当时国家专营的烟草专卖价格等就含有这种性质),补偿以外的性质不是宪法的要求,而是财税法根据宪法的宗旨以及在法律规定的宪法要求之外的财政国会中心主义的要求”。
(20)户波江二在其著作《宪法〔新版〕》平成10(1998)年刊第468页,在论述了“即使必须在法律上规定负担金、手续费、专卖价格等,这也不是根据《宪法》第84条,而更应当说是根据《宪法》第83条的原则”后,又进行了如下论述:“专卖价格和专营事业基金,通过《宪法》第83条接受国会的调控,但最好是,国会仅保留有关基本的事项的决定权,详细内容可以委托主管大臣决定。”
(21)芦部信喜在其著作《宪法〔新版〕》岩波书店1997年刊第323页如下论述:“在和《宪法》第83条的关系上需要‘国会的决议’,但认为上述费用全部包含于《宪法》第84条所称的‘税收’也是不妥当的。由于税收不具有对特别给付予以反向给付的性质,所以应当把它与上述费用区别开来。”
(22)佐藤幸治确实对以清宫为代表的通说(多数说)的税收概念做了批判,但因为批判内容模糊不清,很难抓住要点。在其著作《宪法〔第3版〕》第179页以下做了如下论述:“广义上日本宪法上的‘税收’,包含负担金、手续费、专卖物资的价格、国家专营事业基金等(广义说),作为宪法学说是达成共识的。《财政法》第3条规定了‘除税收外,关于国家基于国家权力缴纳的课征金,以及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属于国家专营事业的专卖价格或者事业基金,也必须完全根据法律或者国会的决议决定’,根据广义说的话,此规定确认了宪法的要求。〈中略〉确切地说,不管名称如何,有可能必须对手续费等以‘税收’标准对待,广义说所称的‘税收’概念过于宽泛了。”
(23)阪本昌成的观点一方面与芦部等的观点基本上相似,但同时也表示了若干不同的见解。对其在其所著《宪法理论Ⅰ〔第3版〕》(成文堂 2000年刊第304页)中所述内容简单地进行归纳,“在法律上作为国家专营的事业,对国民在法律上强制征收的基金、对价或负担(负担强制)”也包含在“税收”里,“关于除此之外的缴纳金,不是根据《宪法》第84条而是根据《宪法》第83条的基本原则管制的,法律规定的事项没有必要进行实体的规定(费用和它的计算标准),关于费用等的确定手续只要明确表示了国会的意思就可以了”。
(24)参见最高法院大法庭(上诉审)昭和60(1985)年3月27日民集39卷2号第247页(Lex-DB22000380):
该诉讼原告是私立大学教授,因其没有进行所得税的确定申告,而受到主管税务署长的课税处分,该课税处分的根据是所得税法(昭和40 (1965)年修改前)关于薪金收入的规定。以对薪金收入者和其他收入者之间的不公平对待为由,主张它违反了《宪法》第14条第1款平等权,请求取消课税处分的案件。判决认为,在税法领域以收入性质的不同为由而在对待上亦有所区别,其立法目的是正当的,同时,只要该立法具体采用的区别情形,在与该目的的关联上没有明显的不合理,就不能否定它的合理性,不能认为它违反了《宪法》第14条第1款的规定。
(25)参见最高法院(大法庭)昭和37(1962)年2月21日判决、刑集16卷2号第107页(LEX-DB21015861)。
(26)为便于参考,下文为《旭川市国民健康保险条例》第8条第4款(判决中所称的第8条为第8条第4款的错误)(与一般被保险人相关的基础征收总额)。即:
第8条第4款 关于保险费规定的国民健康保险法(昭和33(1958)年法律第192号。以下称为“法”)。
第8条第2款规定的被保险人(以下称为“退休被保险人等”)以外的被保险人(以下称为“一般被保险人”)相关的基础征收额(根据第17条的规定在削减基础征收额的情况下,包含削减后所得金额)的总额(以下称为“基础征收总额”)是以第1项规定金额的预算额扣除第2项规定金额的预算额后所得金额为基础计算出的金额。
(1)本年度疗养给付需要的费用(限于与一般被保险人相关的费用)扣除与该给付相关的一部分负担金相等的金额以后所得金额,支付住院伙食疗养费、特定疗养费、访问护理费、特别疗养费、疗养费、移送费以及支付高额疗养费需要的金额(限于与一般被保险人相关的费用),根据老人保健法的规定交纳医疗费筹集金需要的费用金额扣除《国民健康保险法》第70条第1款第2项所规定的负担调整前老人保健医疗费筹集金的等量金额乘以该号规定的退休被保险入等的参加比率得出的金额以后所得出的金额,保险事业需要的费用的金额以及其他国民健康保险事业需要的费用{除去国民保险事务[含有关于老人保健筹集金以及护理交付金(护理保险法(平成9年法律123号)的规定所交付的金额。下同]的交付的事务。下同}的执行所需的费用的金额(与退休被保险人等相关的疗养给付需要的费用金额中扣除与该支付相关的部分负担金相等的金额以后得出的金额,支付与退休被保险人等有关的住院伙食疗养费、特定疗养费、疗养费、访问护理疗养费、特别疗养费、移送费以及高额疗养费需要的费用金额以及交付护理交付金需要的费用金额。)的合计额。
(2)根据该年度《国民健康保险法》第70条的规定的负担金(与交付护理交付金需要的费用相关的费用除外),《国民健康保险法》第72条规定的调整交付金(与交付护理交付金需要的费用相关的费用除外),《国民健康保险法》第72条第2款规定的都道府县调整交付金(与交付护理交付金需要的费用相关的费用除外),《国民健康保险法》第72条第3款第1项规定的转入金,第74条以及第75条规定的补助金(与交付护理交付金需要的费用相关的费用除外),同条规定的贷款(与交付护理交付金需要的费用相关的费用除外),基于其他国民健康保险事业需要的费用(执行国民健康保险事务需要的费用以及支付护理支付金需要的费用除外)而得来的收入(该法第72条第2款第1项规定的转入金以及第72条第4款规定的疗养费等交付金除外)金额的合计额。
(27)在宪法学者的著作中,因为专业限制,没有找到叙述税收法律主义根据的例子。而在税法学者的著作中,一般说来都会提到本文所述之事。例如,北野弘久做如下论述,“基于传统观念所确立的税收法律主义原则,若用一句话来规定税收法律主义,是为确保税收领域中法的安定性、法的可能预测性的法律手段”(参见北野:《税法学原论[第五版]》青林书院2003年刊第98页)。
(28)参见最高法院(大法庭)昭和33(1958)年7月9日判决=刑集12卷11号2407页(LEX-DB=21010311)。
(29)参见东京高等法院平成7(1995)年11月28日判决,判例时报1570号57页(LEX-DB=22008571):
本案是这样的:与税收特别措施法[平成4(1992)年法律14号修改前]第78条、第3条第1款相关的本法实行令以及实施规则,为了接受使用减轻税率所进行的登记,对登记程序的细节进行规定有重大意义。但不能理解为是为了适用减轻税率而对课税要件做出的有效规定。因此,与本案登记相关的税率是根据减轻税率在登记时自动确定的。本案中的差额是错误缴纳的,且国家没有持有该差额的法律上的原因,因此承认错误付款的退还请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