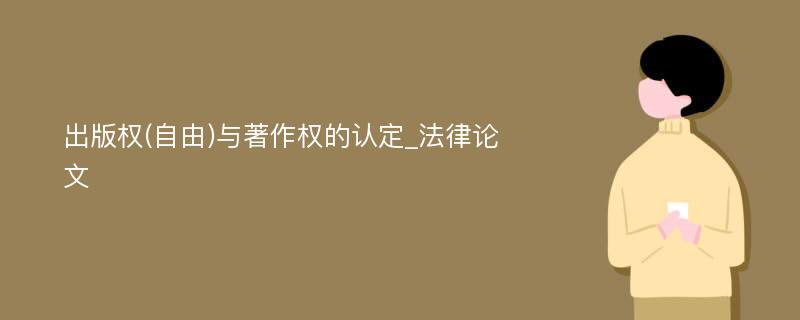
出版(自由)权与著作权辨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著作权论文,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公民权利体系角度看,出版(自由)权和著作权分属于不同的范畴,但是,由于这两个概念都与作品的复制、传播有关,因而有着密切的联系。目前,在理论上探讨两者的区别与联系的著述较少见,在实践中,对两者的混淆和误解却经常发生。前些年在北京审理的“侵犯《周作人散文集》著作权纠纷案”中,被告(一家出版社)就提出了一种有悖法理的观点:周作人已被剥夺政治权利[其中包括出版(自由)权],因而不再享有著作权,对其作品的使用不存在侵权问题①。本文试图通过对两者的历史起源和内涵的分析,使人们更准确地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
出版(自由)权和著作权(版权)的概念,都出现在 17和18世纪的欧洲。从起源上看,两者的产生都与现代印刷产业的发展息息相关。15世纪中期,德国人谷登堡 (Johannes Gutenberg)经多年探索发明了手工平压式活字印刷机,并立刻将其用于图书的复制,这样“印本”图书很快在欧洲各国取代手抄本图书,这标志着欧洲图书出版史上“印本”时代的到来。这种纯技术、纯经济性质的社会进步引发的却是新的权利斗争和利益冲突。
一方面,图书出版业的发展使图书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传播新思想的媒介。为了压制新思想的传播,统治者建立了最早的书报检查制度。而正是针对这种书报检查制度,人们发出了争取“出版自由权”的第一声呐喊。英国诗人、思想家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于1644年向议会所作的《论出版自由》的演讲,最早提出了言论、出版自由的著名论点,猛烈地抨击了书报检查制度。由于言论出版自由的口号,适应了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斗争的需要,符合历史发展的进步要求,因此它很快变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普遍口号。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和奋斗,出版权或出版自由终于被写入1793年的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这一宪法性文件,并逐渐在世界各国成为受宪法保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
另一方面,现代印刷业的发展使图书成为有利可图的大众消费品,一件作品一旦公之于世,任何拥有印刷技术手段的人都可以通过复制它,为自己赚取钱财。因此,要求保护作者权益的呼声越来越高,1690年英国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在其《政府论两篇》中提出,作者在其作品上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与其他劳动者的劳动是一样的,因此应与其他劳动者一样取得应有的报酬②。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保障作品创作者以及该作品的首家出版商的利益,便提上了立法日程。1709年,英国颁布规范出版行为的《安娜法令》,被看做是世界上第一部著作权法。而法国的著作权法则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几乎与包含“出版自由权”内容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同时诞生。
二
通过对出版(自由)权和著作权历史起源的简要回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出版(自由)权和著作权概念的产生都与现代印刷技术革新引发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相关,出版(自由)权和著作权是从不同角度规范出版行为的规则:出版(自由)权是一种调整国家与公民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规范,是一种源自于公法的权利;著作权则是一种调整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规范,是一种源自私法的权利。
1.两种权利之间的区别
首先,二者的取得方式不同。我国《宪法》第二章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宪法》第三十三条开宗明义地指出:“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2004年《宪法修正案》在本条下又增加了第三款:“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一方面,可以宏观地说,《宪法》第二章所列举的公民基本权利,是以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资格为前提条件的。也就是说,只要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资格的一切自然人,都不加区别地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按照我国最新的宪法理论的分类,基本权利可分为三个部分:人权,公民权及特定人的权利③20。“基本权利中的公民权,只能由公民享有。有的国家宪法规定由国民享有。不具有一国国籍的人,在其他国家只享有人权,但不享有公民权。”③20政治权利是最典型的公民权。一个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外国人或无国籍人,是不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范围内享有出版 (自由)权的。而著作权则不同,它是一种特殊的民事权利。作为一项民事权利,著作权并不像出版(自由)权那样在一定国度内被每一个公民所享有,创作并拥有自己的作品这一民事行为是取得这项权利的前提。并且,在实行“注册保护原则”的国家中,创作并拥有自己作品的民事主体,还必须履行一定的法律手续,才能取得这项权利。
其次,二者的功能不同。一项宪法性权利,主要调整的是“国家权力与公民基本权利之间的关系,不调整私人之间的关系。国家的行为受宪法的限制,私人之间的行为受普通法律的限制,这是法治国家的一个基本原则”③43。出版(自由)权的直接约束力只限于立法机关。因为“无论是国家机关还是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公民个人都不能侵犯宪法所确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宪法规定基本权利的主要功能在于“对作为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做出指示,让其制定完备的法律,保护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④而作为一般民事权利的著作权,其调整的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其约束力直接针对可以成为民事主体的所有自然人和组织。国家公权组织则可以以平等民事主体的身份成为其约束对象。
正因为如此,由宪法确认的出版(自由)权只是一种法律原则,在一般情况下,并不具有直接的法律适用性。“只有在缺乏适当的低位阶法律规范可以适用时,才得适用宪法规范裁判具体的个案。”③43而著作权则是由《著作权法》规定的一项具体的民事权利,它具有直接的法律适用性。著作权规范是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直接依据。
此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运用刑罚手段对著作权加以保护。比如,我国《刑法》第三章“侵犯知识产权罪”一节中规定的“侵犯著作权罪”(第二百一十七条)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第二百一十八条),就是著作权刑事保护的规定。也有很多国家将侵犯著作权犯罪处罚纳入在著作权法中,以“罚则”或“刑事规定”等方式加以规定⑤。但是,通观各国刑事法律规定,却很少有哪个国家将公民政治权利,特别是出版(自由)权,也纳入刑事保护的范围,确定一些相关的罪名。这难道说明出版(自由)权的重要性低于著作权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笔者认为,这与我们前面阐述过的出版(自由)权的特性有关。从出版(自由)权的起源来看,对出版(自由)权的威胁主要来自公权力,而不是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因此,宪法规定出版(自由)权主要针对的是国家立法机关,即为国家立法行为确定原则。出版(自由)权和著作权都是授权性规范,所不同的是:前种授权性规范的义务人是特定的,即国家和国家行为,而后一种授权性规范的义务人是不特定的。国家不可能成为刑事犯罪的主体。因此,运用刑罚手段为出版(自由)权提供保护,与这种宪法权利的性质不相切合,对出版(自由)权最恰当的保护形式是违宪审查制度。
2.两种权利之间的联系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国家一切法律的立法依据。我国《宪法》不仅在第三十五条规定了公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权,并且在第四十七条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公民的著作权和其他民事权利都是基于《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产生的。如果公民没有言论、出版(自由)权,不能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学、艺术作品便不会产生,有关这些作品的著作权也就不会存在了。另一方面,《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只有通过各种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加以保护,通过相应的民事法律加以具体化,才能得到实现。著作权中核心的权利就是发表权,它既是著作人身权的重要内容,又是著作财产权产生的基础。发表权是指作者决定是否、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将自己的作品公之于众的权利。如果法律没有规定这项民事权利,公民不能自主地决定自己作品的命运,那么公民的出版(自由)权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因此,从整体上看,出版(自由)权是著作权的前提和保证,而著作权则是出版(自由)权得以落实和具体化的私法手段。
就个体而言,两者的联系却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一般情况下,一个公民如果被剥夺了出版(自由)权或其出版(自由)权受到限制,那么他便无法正常地行使自己的著作权。但对特殊的民事主体而言,并不一定非要拥有作为政治权利的出版(自由)权,才能行使著作权。比如,外国人不是我国公民,在我国并不享有中国公民才享有的政治权利,但却可以在我国境内行使其著作权。我国《著作权法》第二条规定:“外国人的作品首先在中国境内发表的,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外国人在中国境外发表的作品,根据其所属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享有的著作权,受本法保护。”当一个作品的著作权属于一个法人时,情况也类似,也就是说,该法人虽不拥有作为自然人的公民才享有的政治权利,但却可以依法行使自己的著作权。然而,这种没有出版(自由)权做依托的著作权是有缺陷的:当著作权受到私权的侵害时,权利人仅可以依据民事法律规范来寻求救济;当其著作权中的发表权的行使因公权措施的干预而受到阻碍时,当事人则无法依据与出版(自由)权相关的法律规范来寻求救济。举例说,一个美国人的作品,未经其许可,就被我国的出版单位出版了,这便构成了侵权。这个美国人可以依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要求我国的司法机关追究侵权者的法律责任。另外一种情形是:这个美国人的作品中包含着我国法律禁止出版的内容,我国相关机构可以禁止该作品在我国的出版。在这样的情形下,这个当事人不仅无法在我国行使自己作品的发表权,而且没有相应的救济手段。
三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到,出版(自由)权对著作权有较强的制约作用。下面,本文着重讨论一下,当前者受到限制时对后者产生的影响。
在我国,涉及出版(自由)权的限制措施主要有两个:
第一,刑事法律措施。我国《刑法》第三章“刑罚”规定了三种附加刑,即罚金、剥夺政治权利及没收财产⑥。对于某些犯罪分子,司法机关在判处其主刑的同时,可以适用附加刑;在某些情形下,也可对犯罪分子独立适用附加刑。我国《刑法》第五十四条明确规定:“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下列权利:(一)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三)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四)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第五十八条又规定:“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监督管理的规定,服从监督;不得行使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各项权利。”⑦
第二,行政法律措施。目前,1997年国务院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是我国唯一一部全国性的出版管理法规,《条例》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任何出版物不得含有下列内容:(一)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二)危害国家的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三)危害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四)煽动民族分裂,侵害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破坏民族团结的;(五)泄露国家秘密的;(六)宣传淫秽、迷信或者渲染暴力,危害社会公德和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七)侮辱或者诽谤他人的;(八)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对于含有上述内容的作品,我国出版行政管理机关——新闻出版总署可以依法禁止其出版。另外,我国《著作权法》第四条规定:“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本法保护。”这就是说,对于这样的作品,其作者不得主张自己的著作权。从《著作权法》这条规定的内容看,这种民事法律措施,是同行政法律措施相配套的,它本身并没有独立的意义。
刑事法律措施和行政法律措施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和意义。刑事法律措施是一种刑罚,强调的是对当事人的惩罚,并不一定具有限制其作品传播,以免危害社会的目的,其指向的对象是人而不是作品。剥夺政治权利属于资格刑。资格刑一般具有两个基本功能:第一,剥夺或限制罪犯再犯能力的功能;第二,通过权利享有方面的差别待遇,表达一种国家法律对犯罪行为及其实施者的否定性评价,以达到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双重目的。总体上看,我国《刑法》规定的剥夺政治权利这种刑罚的功能侧重于第二个方面。剥夺出版(自由)权这种刑罚表达的是对犯罪行为及其罪犯人格的整体否定,重点不在于防止犯罪分子再次犯罪,更不考虑潜在出版物的内容如何。
行政法律措施的主要功能是通过限制特定作品的出版,以避免产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与剥夺公民出版(自由)权的刑事法律措施的效果不同的是,一个公民的某个作品被禁止出版,并不影响该公民出版自己其他没有问题的作品。行政法律措施对公民出版(自由)权的限制是特定的,而不是全面的。
上述两种措施的共同点是均对当事人出版(自由)权构成了限制,但应该强调的是,剥夺或限制当事人出版 (自由)权并不等于剥夺或限制当事人的著作权。从纯法理的角度分析,剥夺或限制当事人出版(自由)权,对其作为著作权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没有丝毫的触动,而只是造成了著作权人民事行为能力的衰减,也就是说,上述两种措施造成了其民事行为能力(或客观权利)与民事权利能力(或主观权利)的分裂,虽然该主体民事权利能力并未被剥夺,但其却丧失或部分丧失了以自己的行为行使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能力。这就如同一个正在服刑的罪犯,其许多民事权利并未因判刑而被剥夺,但其却因丧失人身自由而无法实际地从事那些民事活动。总之,一个公民以某种方式丧失出版(自由)权,决不意味着其同时也丧失了相应的著作权。也就是说,出版(自由)权受到限制导致的著作权行使障碍并不表现为“被终止”:
第一,受到妨碍的只是著作权中的某些权利,如发表权及相关权利。
第二,这种限制具有一定的时间性。例如,依据《刑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只在被剥夺政治权利期间,无法对自己作品行使著作权中的一些权利。即使是在“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情形下,在著作权人身故后50年内,其作品仍未进入“公有领域”,其继承人仍可依法行使著作权。
第三,限制对象具有一定的特定性。正如上面已经谈到的,依据《出版管理条例》及相关法规,禁止某作品出版,意味着仅就该作品限制著作权人行使其著作权,这并不妨碍其对自己的其他作品行使著作权。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本文开头提到的前些年在北京审理的“侵犯《周作人散文集》著作权纠纷案”中,被告(一家出版社)提出的周作人已被剥夺政治权利[其中包括出版(自由)权],因而不再享有著作权,对其作品的使用不存在侵权问题的申诉是站不住脚的。出版(自由)权与著作权具有完全不同的权利属性,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其中一个被剥夺决不意味另一个也被剥夺。另外,这种说法的荒谬之处还在于:如果一个人被剥夺了出版(自由)权,其著作权就不再受保护,这将意味着著作权人本人无法行使的著作权,其他人却反而可以毫无顾忌地进行侵权。特别是,当侵权行为涉及的是该著作权人在被剥夺或限制出版(自由)权之前已经出版的作品时,就显得更加荒谬了。因此,人们只有在区别和联系的整体关联中理解和把握二者的关系,才能避免误解。
注释:
①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北京知识产权判例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74.
②中国版权研究会.版权研究文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117.
③周伟.宪法基本权利司法救济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3.
④刘志刚.宪法拘束与立法自由.宪政论丛(第4卷).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128.
⑤杜国强,廖梅,王明星.侵犯知识产权罪比较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76.
⑥我国有学者对我国(刑法)规定剥夺政治权利的附加刑提出不同意见,主要认为像这样的宪法性权利是不能剥夺的,除非宪法中有可以剥夺的明确规定,参见曲新久著:《刑法的精神与规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0-351页。
⑦肖扬.中国新刑法学.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749-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