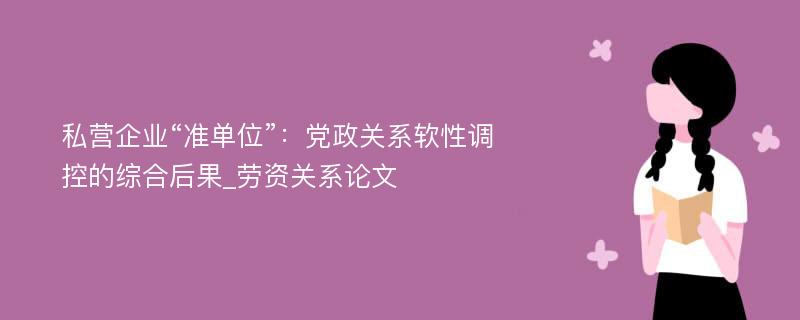
私营企业“类单位化”:党和政府软性调控劳资关系的一种综合性后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软性论文,劳资论文,私营企业论文,党和政府论文,综合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概念界定与问题的提出 虽然不同的理论视角对国家(政府)是否应该调控劳资关系①以及应该如何调控劳资关系的看法各不相同,但实际上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所有国家(政府)都会对本国的劳资关系进行调控,我国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②对我国的劳资关系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控,其最终结果之一,是把城市中的就业场所改造成了“单位”。典型形态的单位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党和国家的机构、合法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机构等;二是所谓不创造物质财富的国营机构,如研究所、各种教育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和文化团体等;三是所谓创造物质财富的机构,即各类国营企业。这三类单位分别被简称为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路风,2003)。 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人们之所以把自己就业于其中的社会组织或机构统称为“单位”,是因为“我国的各种社会组织都具有一种超出其各自社会分工性质之上的共同性质——‘单位性质’”(路风,1989)。近20多年来,一些学者,如路风(1989,2003)、李汉林(1993)、李猛等(1996)、刘建军(2000:43-51)等,曾从不同的研究角度论述过这种“单位性质”或单位组织的基本特征。从党和政府调控劳资关系的角度来看,以国营企业③单位为例,这种“单位性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在党和政府与国营企业的关系上,主要体现为二者密不可分、融为一体。当党和政府把企业组织改造成为具有“单位性质”的国营企业之后,党和政府不但实际上变成了国营企业的用工主体,成为了国营企业职工的雇主,而且,国营企业本身也不再只是一种经济组织,它还是党的组织系统和国家行政系统的延伸,也即兼具“行政”属性(路风,1989;李培林等,1992:95-96)。这是“单位性质”的本质特征,或者说,这是我国的单位组织与西方市场经济中的企业组织之间的本质区别。(2)在国营企业与职工的关系上,主要体现为国营企业不只是要给职工提供合适的劳动条件,它还要以集体福利的形式为职工提供生活、文化等设施,如提供住房、食堂、浴室、理发店、托儿所、子弟学校、卫生所(医院)、俱乐部等设施。这使得每个国营企业就像社会的缩影,变成了“小社会”(李培林等,1992:96-97)。(3)在国营企业领导干部与普通职工(工人)的关系上,主流意识形态强调彼此之间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不存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别,也不存在根本利益上的冲突,因此,工人无需成立工会。即使成立了工会,其基本职责或中心任务也不是为了代表并维护工人的正当权益,而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如开展劳动竞赛、文化体育等方面的活动。本文把就业场所(尤其是国营企业)具备这些“单位性质”的过程称为“单位化”。 自1980年代末期以来,对单位组织与单位体制的研究一直是社会学关注的一个热点,其中一个课题是:随着国有企业的衰落、单位组织之“单位性质”的弱化以及非单位组织的兴起,“单位性质”有没有在非单位组织(尤其是新兴的非单位组织)再生?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答案是肯定的。毛丹(2000)、肖立辉(2002)、李培林(2004:43-52)、包路芳(2010)、郭圣莉、王兴(2011)、朱逸、纪晓岚(2012)和黄淑瑶(2013)等的研究表明,一些村庄(尤其是集体经济强大的村庄)出现了“单位化”现象,变成了“单位化村庄”;赵定东、王洲(2013)发现,在城乡一体新社区建设过程中出现了单位制回归现象,他们称这种现象为“新单位化”;张朝林、侯喜春(2009)认为,我国民间组织的“单位制”追求很强烈,出现了“类单位制”现象。遗憾的是,除了18年以前弗朗西斯(Francis,1996)④做过一些研究之外,对出现在私营企业的类似现象几乎没有学者深入研究过。 1950年代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我国内地的私营企业及其劳资关系就不复存在,一直到1979年以后才重新出现。近30余年来,我国的私营企业⑤从无到有,异军突起。据统计,截至2012年底,全国内资企业实有1322.54万户(含分支机构),其中私营企业达1085.72万户⑥,即82.1%的内资企业都是私营企业。从前面的叙述可知,典型形态的单位都归国家所有,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私营企业并不属于单位的范畴。然而,近几年来,笔者在浙江省诸暨市等地调查时发现,不少私营企业,尤其是那些规模较大的制造企业,也已具备了类似“单位性质”的特征。本文把这种现象称为私营企业“类单位化”。 本文以诸暨市的调查为基础,试图探讨以下两个基本问题:(1)私营企业“类单位化”现象是如何形成的?(2)私营企业“类单位化”现象的出现具有哪些重要意义?本文的基本论点是: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2003年以来党和政府采取软性调控措施调控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的发展而形成的一种综合性后果;充分认识这种现象,至少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理解与之两个相关问题。 私营企业“类单位化”的基本历程 私营企业“类单位化”的基本历程,与党和政府软性调控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的基本历程是一致的。1979年以后,随着私营企业的重新出现,各级党委和政府重启了调控私营企业及其劳资关系发展的进程。我们可以把这个调控过程大致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1)从1979年到1991年:对私营企业的重新出现,党和政府采取了从默许到公开放行的政策,但尚未出台健全的、有力的调控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的政策措施。(2)从1992年到2002年: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尤其是中共十四大以后,我国的私营经济迅速转入由各级党委和政府大力推动的发展阶段,私营企业异军突起。从1993年到2002年,登记的私营企业户数由23.8万户增加到243.5万户,从业人数由372.6万人增加到3409.3万人(张厚义、刘平青,2003)。与此同时,一大批私营企业主迅速成长起来,他们日益受到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关怀和重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有关维护私营企业工人的合法权益、协调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的问题却并没有引起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足够重视,致使劳资关系日益紧张。(3)2003年以后:私营企业仍然保持了快速发展的势头,与此同时,党和政府加大了调控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的力度,纷纷出台了调控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的政策措施。之所以如此,除了劳资关系日益紧张的原因,还有另外两个重要因素:一是一些私营企业主财大气粗、肆意妄为,这不但影响了企业劳资关系的和谐,也影响了党和政府对经济、社会等的宏观调控。二是在沿海地区出现了“民工荒”现象,影响了一些企业的正常生产,各级党委和政府不得不进行相关的调控或干预。 党和政府的调控措施可以大致分为硬性调控措施与软性调控措施两种类型。所谓硬性调控,通常是指出台并严格执行具有强制性的相关法律(也包括强制性的行政措施)。如果不考虑中间过渡类型,那么,硬性调控之外的所有调控都属于软性调控。不过,在本文,软性调控专指各级党委和政府通过出台有关的文件来调控。这些文件(俗称“红头文件”)往往以“关于……的通知”和“关于……的意见”的形式出现,其调控手段以积极引导、正面激励为主,而很少直接采取强制和惩罚的手段。软性调控又大致可以分为直接的软性调控与间接的软性调控两种类型。直接的软性调控指直接针对企业主及其代理者、雇员及其代表或整个企业的调控,其基本做法是通过下发“红头文件”开展有关的活动,它需要企业有关人员直接配合、参与或做出回应。或者说,这种调控意味着党和政府的力量直接深入企业内部。间接的软性调控则指其他的软性调控手段。本文所说的“软性调控”主要是指直接的软性调控。下面将以浙江省诸暨市(县级市)⑦的调查为基础,简要论述这些直接的软性调控措施。⑧ (一)将党组织逐渐融入私营企业 考虑到党组织与私营企业(或曰非公有制企业)之间原本缺乏制度性的联系,要想将党组织逐渐融入私营企业必须解决以下三个依次递进的焦点问题:一是私营企业主(企业出资者)能否入党;二是成立党组织之后,党员私营企业主能否担任党组织书记;三是成立党组织之后,是否使党组织成为经营管理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发挥作用。只有全部解决了以上三个焦点问题,党组织才算融入了私营企业。 1989年8月中共中央出台的《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曾规定“不能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不过,当时人们对这个规定的看法并不一致,实际上,它也并未得到很好的落实。此后,相关政策逐渐放宽,2000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的《关于在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加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已默许私营企业主入党,200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及2002年中共十六大对党章的修改,则将党的大门正式向私营企业主打开,前述第一个焦点问题得以顺利解决。约十年后,201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该《意见》明确提出要“注意培养发展符合条件的企业出资人入党”,并强调要“加强党员教育培训,注重把党员培养成生产经营骨干,把生产经营骨干培养成党员”。这势必使生产经营骨干中党员的比重逐渐提高,或者说,势必使生产经营骨干逐渐党员化,从而逐渐使党员与生产经营骨干融为一体。对于党组织书记的选配,该《意见》规定:“党组织书记一般从企业内部选举产生,注意从生产、经营、管理骨干中推荐人选,……规模大、党员数量多的企业主要出资人担任党组织书记的,应配备专职副书记。提倡不是企业出资人的党组织书记、副书记通过法定程序兼任工会主席、副主席;也可以由党员工会主席通过法定程序担任党组织书记、副书记。”这项规定体现出两重含义:一是默许甚至鼓励企业出资人尤其是“规模大、党员数量多的企业主要出资人”担任党组织书记;二是要求党组织书记、副书记与工会主席高度融合。该《意见》还强调要加强经费保障,规定:“将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工作经费纳入企业管理费用,建立并落实税前列支制度。”这项规定实际上是将党组织视为企业管理机构的组成部分。可以认为,该《意见》的出台标志着在制度设计上彻底解决了前面提及的第二个和第三个焦点问题。至此,至少从制度设计上讲,党组织已融入私营企业。 截至2010年底,全国符合组建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99.6%建立了党组织,规模以上非公有制企业96%建立了党组织(李源潮,2012)。具体到浙江省,截至2012年9月,在全省326435家非公有制企业中,292170家已建立了党组织,组建率达89.50%。其中,有党员的非公有制企业(共292170家)已全部建立了党组织;有3名以上正式党员、条件成熟的非公企业(共35288家)已全部单独建立了党组织(中共浙江省委新经济与新社会组织工作委员会,2012)。将肩负着众多职责的党组织融入私营企业,这本身就是对私营企业的一种改造。不仅如此,从浙江省诸暨市的实际进程来看,党组织逐渐融入私营企业的过程,其实也是地方各级党委相继出台有关文件从而试图进一步对私营企业进行改造的过程。党组织融入私营企业之后,不但改变了私营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而且在党与私营企业之间建立了一种党内的组织关系,从而迈出了私营企业“类单位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步。 (二)建立起地方政府与私营企业互动的平台 地方政府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与私营企业互动,或者说,地方政府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将自己作用和影响渗入私营企业,其中,一项重要的举措是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网络延伸到私营企业(或曰民营企业),也即在私营(民营)企业里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简称“综治”)工作。浙江省开展这项活动始于2005年在平湖市的试点。2006年5月,浙江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出台了《关于大力推进企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意见》。该《意见》提出了推进企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六项内容,并提出了四项保障措施,其中包括:将企业治安综合治理情况与企业升级、信誉评估等综合性资质资格认定联系起来,与企业家的各种荣誉和实际利益挂起钩来;规模企业应设立企业综治工作室(站)负责综治日常工作;乡镇(街道)综治工作中心要加强与企业综治工作组织的联系与衔接,建立企业与政府及社会之间的联系枢纽和互动平台。截至2011年9月,浙江省已有96%的规模以上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建立了综治工作室(站)(中共浙江省委、省人民政府:2011)。这意味着,除了前面所说的将党组织融入非公有制企业之外,又建立了一个乡镇(街道)与规模以上企业互动的平台。这个平台的建立,意味着将地方行政系统延伸到了非公有制企业。通过这个平台,地方党委和政府可以将治安防控、矛盾化解等调控措施直接送入企业。 (三)引导私营企业强化职工生活后勤保障 所谓强化职工生活后勤保障,主要是指改善企业职工就餐、居住和文化体育活动等方面的条件。在诸暨市,这种“强化”工作始于2002年开展的“十佳职工食堂”评比活动。这种评比活动每年都搞,并从2005年起增设了“十佳职工宿舍”的评比,其主办单位为诸暨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诸暨市卫生局和诸暨市总工会。2007年9月,浙江省总工会出台了《关于开展以“强保障、促和谐”为主题的职工生活后勤保障推进活动的意见》,决定在全省企业开展以“强化生活后勤保障、促进劳动关系和谐”为主题的职工生活后勤保障推进活动。这些旨在引导、激励资方改善职工生活后勤保障的做法强化了企业的社会功能。 (四)开展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活动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活动(简称“创建活动”)始于2005年。其基本做法是: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首先成立由党、政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创建活动领导小组,并出台创建标准,然后,评选、表彰劳动关系和谐企业。根据行政层级,劳动关系和谐企业一般分为四个等级,即全国级、省(部)级、地区(地级市)级和县(县级市)级。开展这种创建活动的基本宗旨在于引导、激励、督促资方及其代理者遵守有关的法律法规并落实相关政策,从而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 (五)对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进行政治安排与综合评价 对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政治安排主要是把他们“安排”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代会代表以及在有关人民团体如青联、工商联、侨联中担任领导职务。对私营企业主个人来讲,要想获得这种政治安排,需要满足党和政府提出的多方面的要求,其中之一是必须接受由统战部门牵头开展的“综合评价”。这种综合评价始于2005年的局部试点,其评价内容涉及思想政治表现、诚信守法状况、企业经营状况和履行社会责任情况。具体到诸暨市,至今已搞过两次综合评价,第一次是在2007年,第二次是在2010年。据诸暨市委统战部提供的资料:第二次确定的评价对象为514人,其中486人接受了评价,其评价结果是:60.3%的人被评为“优秀”等级,各有18.1%的人分别被评为“合格”和“基本合格”等级,另外3.5%的人则被评为“不合格”等级。这种综合评价以及政治安排的基本作用在于直接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按党和政府所希望的那样健康成长。 (六)在私营企业里组建由党领导的工会 前面介绍的五项软性调控措施基本上都是针对资方及其代理者的。其实,党和政府对劳方及其代表也采取了一系列的调控措施,其中,最有力度的调控莫过于在私营企业里组建由党领导的工会,并要求工会共谋企业发展。 对私营企业工会组建工作的高度重视始于2000年11月在浙江省宁波市召开的“全国新建企业工会组建工作会议”。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的尉健行(2009:163)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强调:“必须明确,不论企业所有制性质如何、企业规模大小、职工人数多少,只要开业投产就要依法建立工会组织。”尉健行(2009:166)还提出:“实现新建企业工会组建工作的突破,必须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各方配合的工作格局。”此后,马上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新建企业工会组建运动。这场运动的效果十分明显,至少从统计数字来看是如此。截至2008年6月,全国工会基层组织数已达到170.2万个,工会会员总数已达到20867.5万人(全国总工会研究室,2008)。2011年初,全国总工会进一步出台了《2011-2013年推动企业普遍建立工会组织工作规划》。根据这个《规划》的要求,浙江省总工会马上出台了《浙江省工会推动企业普遍建立工会组织三年工作规划(2011-2013)》,并分解提出了全省各市企业工会组建目标和发展会员目标。紧接着,绍兴市总工会和诸暨市总工会也相继出台了“推动企业普遍建立工会组织”的积极应对措施。 在私营企业里建立工会只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建立工会之后让工会干什么?其实,早在1950年代,经过召开三次全国总工会党组扩大会议,就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即确定了工会的中心任务——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游正林,2012)。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善党对工会、共青团、妇联工作领导的通知》,重申“工会、共青团、妇联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遵循党的基本路线,围绕党在每个时期的中心任务进行工作”。后来,全国总工会常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来概括中共中央对工会的这种要求,并把这种要求体现在有关文件之中。比如,2005年出台的《关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的决议》从七个方面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的基本内涵,其中,第三个方面的内涵是“坚持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强调“要自觉坚持在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下行动,把工会工作放到大局中去思考和部署”。在这种情势下,我们有理由相信,各级地方工会会自觉坚持在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工作大局下行动,为当地工作大局服务。具体到每个企业,企业工会也会自觉坚持在企业党组织和企业行政的工作大局下行动,共谋企业发展。⑨从诸暨市的实际情况来看,也确实如此。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的经济体制等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可是,我国工会的领导体制与运作模式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在私营企业里组建主要由同级党组织领导的工会并要求工会共谋企业发展,这实际上是沿用了国营企业工会的领导体制与运作模式。工会领导体制与运作模式的这种沿用既是私营企业“类单位化”现象得以出现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私营企业“类单位化”现象的重要表现。 党和政府软性调控私营企业劳资关系发展的措施当然不只以上这些,比如,还进一步采取了多种措施来预防、化解劳资纠纷。 我们虽然很难知道每项软性调控措施的具体效果如何,但从诸暨市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些软性调控措施经过较长时间的共同作用之后已经产生了多种相对稳定的综合性效果(参见游正林,2014:第十一章),其中之一,就是使不少私营企业,尤其是那些规模较大的制造企业,已具备了类似“单位性质”的特征。具体表现为:(1)党和政府的作用和影响已深入私营企业内部,党和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的互动越来越便利,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私营企业已成为党的组织系统和政府行政系统的延伸。(2)在私营企业内部,食堂、宿舍、卫生所、书报阅览室等设施越来越多,私营企业承担的社会功能越来越多,它们越来越像“小社会”。(3)在私营企业内部,已普遍成立了由党领导的工会,这种工会的基本任务是共谋企业发展,并努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而不像某些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工会那样承担着牵制甚至对抗资方(管理方)权威的功能。⑩因此,可以认为,私营企业“类单位化”现象的出现主要是2003年以来党和政府采取软性调控措施调控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的发展而形成的一种综合性后果。 以上结论虽然是基于对诸暨市的调查,但从前面的论述可知,那些软性调控措施并非诸暨市独有,实际上,它们都是在浙江省甚至全国范围内从上往下逐级推行的。即使是产生于诸暨市或浙江省的调控经验,也往往已被推广至全国其他地区。因此,可以认为,前面提及的那些软性调控措施具有全国性,私营企业“类单位化”也是一种全国性现象。当然,在不同地区,其程度可能并不相同。 私营企业“类单位化”的基本意义 考虑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发生的社会转型是在政体连续、权力连续和主导性意识形态连续的背景下以渐进的方式进行的(孙立平,2005),私营企业“类单位化”现象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充分认识这种现象,至少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理解以下两个相关问题。 (一)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单位以及单位体制的成因 自1980年代末期以来,已有一些学者探讨过我国单位以及单位体制的成因。路风认为,单位以及单位体制是中国从落后状态中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在组织上的反映(路风,1989)。单位体制是现代中国在经历了一场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并由这个夺取了政权的党运用国家行政力量对社会进行大规模重新组织之后形成的。单位体制产生的基本原因是国家用行政手段来组织人民(路风,2003)。刘建军(2000:59-64)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面临的一种特殊情况是社会资源总量的不足,这迫使我国进行有组织的现代化战略,即通过权威对资源的强制性提取和再分配来满足现代化的要求。单位的形成是这一战略设计的一个重要产物。或者说,单位的生成与单位制的建构,是中国社会资源总量不足的必然产物。田毅鹏、刘杰(2010)认为,如果从“长时段”的角度,将“单位社会”的起源、形成及发展置于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危机”和“重建”的高度来认识,那么,单位社会是作为中国社会精英为解决社会总体危机、重建社会的根本性措施而出现的结果。这些观点虽然各有千秋,但都强调单位以及单位体制不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而是(或主要是)党和政府(或国家)追求某个宏大目标(如迅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解决社会总体危机)的产物。对这一点,笔者也表示认同。不过,笔者进一步认为,从“类单位化”的形成过程来看,我们还可以更为具体地从以下两个角度来思考单位以及单位体制尤其是企业组织之“单位性质”的成因:(1)从党和政府调控劳资关系的角度来思考。毋庸置疑,企业组织的基本功能是基于社会分工而形成的经济功能或生产功能。在企业组织内部,其基本关系是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或资方与劳方之间的关系。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所有国家(政府)都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对本国企业的劳资关系进行调控,急于实现工业化的我国更不例外。大体而言,我国党和政府之所以要调控企业的劳资关系,旨在追求两个相互关联的主要目标:一是追求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二是追求企业劳动秩序的和谐稳定。其中,前者又主要表现为追求充分调动职工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或者说,追求充分发挥职工群众的主人翁精神,使职工群众忘我地、自觉地努力劳动。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两个主要目标的追求促使企业组织日益具备了“单位性质”。(2)从“过程”的角度来思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和政府会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而采取不同的措施来调控企业的劳资关系,企业组织的“单位性质”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或者说,“单位性质”主要是党和政府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范围之内采取众多措施来调控企业的劳资关系而形成的一种综合性后果。这个综合性后果可能并不是经过事先周密设计而出现的一个意料之中的结果。 (二)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我国的劳动秩序乃至社会秩序是如何实现的 本迪克斯(Bendix,1956:434,436)认为,在工业化早期都会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伴随着工业化,会产生一个非农业劳动力队伍,这个非农业劳动力队伍通常被迫承受因为巨大的社会与经济位置的改变而导致的后果。那种社会与经济位置的巨大改变终止了前工业社会中“下层阶级”的传统隶属关系,导致“下层阶级”被剥夺了他们在社会中被承认的位置。因此,所有正在进行工业化的社会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对被新创造出来的工业劳动力进行公民的再整合(civic reintegration)。本迪克斯因此而进一步发问:一个正在进行工业化的社会将在什么条件下在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共同体内部解决新招聘的工业劳动力的吸纳问题?这个问题吸引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劳资关系研究的许多奠基者,他们都热衷于解决因工业化而产生的劳工问题(labor problems),支持创建调控劳资冲突、把工业人口整合进入自由民主的社会的新制度(Heery et al.,2008)。大体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一直到1970年代,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美国)调控劳资关系或解决劳工问题的重点是整合工人阶级,或者说吸纳工人运动,其基本做法之一是立法支持工人自由组建和加入工会,并与资方就工作报酬、工作时间以及其他雇佣条件进行集体谈判。新中国成立以后,同样面临一个如何整合工人阶级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在企业层次上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精神或充分调动工人阶级的劳动积极性和如何维持良好的劳动秩序的问题。从实际过程和效果来看,党和政府采取了完全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曾经采用过的基本做法,即不是立法支持工人自由组建和加入工会并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而主要是采取一系列的调控措施,逐渐把企业整合进入党的组织系统和国家行政系统、把工人整合进入企业之中,从而导致了单位以及单位体制的形成。 在“类单位化”时期,党和政府同样面临如何在企业层次上调动员工的劳动积极性与维持良好的劳动秩序的问题。鉴于私营企业的财产属于私有,私营企业主(出资者)自然会考虑如何调动员工的劳动积极性的问题,党和政府考虑的重点问题是如何维持良好的劳动秩序。从实际过程和效果来看,党和政府继续采取了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曾经采用过的基本做法,即不是立法支持工人自由组建和加入工会并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而主要是对私营企业劳资关系进行软性调控。从前面的论述可知,软性调控的重点是私营企业主(出资者及其代理者),而不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员工。之所以如此,原因主要有三:首先,至少从党的意识形态来讲,私营企业主阶层的重新出现属于异军突起,面对这个突起的“异军”,为了缓解他们对现行体制的冲击与挑战,党和政府对他们加以调控是理所当然的事。其次,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私有制和资产阶级被消灭、工人阶级被确立为领导阶级并实现了党对工会的领导,党和政府也就基本上完成了对工人阶级的整合,并随之形成了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包括建立单位体制)。私营企业雇工的重新出现并不对早已形成的制度安排构成明显的冲击与挑战。再次,如果党和政府直接整合私营企业员工,将至少遇到两个难题:一是由于存在户籍管理制度,难以将以农民工为主体的私营企业员工整合进入企业所在的城市(或地区)管理体制。二是由于政治体制不同,不可能像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那样开展劳资集体谈判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比较明智的选择就是引导、激励私营企业主及其代理者遵守有关的法律法规并落实相关政策、善待处于弱势地位的员工。这种做法不但促进了私营企业“类单位化”,也使得私营企业员工可以通过生存于企业而生存于企业所在的城市(或地区)。 在浙江省诸暨市调查期间(2010年11月至2013年11月),笔者得到了诸暨市总工会主席戚志军先生、副主席叶淑秀女士、权益保障部部长楼伟广先生等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表谢意。 ①劳资关系是指因雇佣行为而产生的雇主及其代理者(经营管理者)与雇员及其代表(如工会)之间的关系。 ②鉴于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以及党、政不分的国情,在以下论述中,一般把党和政府视为一个整体,不再具体地区分哪些是党的调控、哪些是政府的调控。 ③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国营企业被称为国有企业。 ④弗朗西斯发现,在北京海淀区高科技领域,工作组织“再生”了某些单位制度特征,如:员工的某些基本生活需要(如住房)需要依赖工作组织来解决,工作组织需要承担一些公共职能,工作组织需要扮演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介。 ⑤私营企业有时被称为民营企业或非公有制企业,本文不对这三个概念做严格的区分,而基本上视它们为同义词。 ⑥参见《全国市场主体发展总体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网站,http://www.saic.gov.cn/zwgk/tjzl/zxtjzl/xxzx/201301/P020130110600723719125.pdf。 ⑦诸暨市拥有袜业、珍珠、铜加工及新型材料、机电装备制造、纺织服装等工业产业集群,拥有规模以上企业3000多家(都是非公有制企业)、上市企业13家,综合经济实力位居浙江省前列。 ⑧对这些软性调控措施的详细论述,参见游正林(2014)。 ⑨2006年12月,全国总工会出台的《企业工会工作条例》规定:“企业工会接受同级党组织和上级工会双重领导,以同级党组织领导为主。”“企业工会与企业行政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平等合作,共谋企业发展。” ⑩有学者(如Alexander,1975)认为,美国的工会就承担着这样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