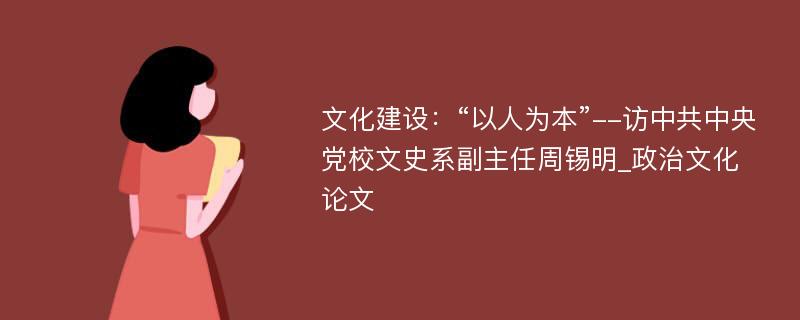
文化建设:“以百姓之心为心”——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副主任周熙明访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心论文,副主任论文,文化建设论文,文史论文,百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政治和心灵的同步崛起
记者:似乎从1840年以来,我们一直都这样,搞经济建设、制度革新,到后来是文化建设。
周熙明:回顾一下中国这一百多年以来,从经济到政治制度变革,再到所谓思想、文化的反省,这个过程确实已经重复了好几回了。这十几年又开始越来越密集地谈论文化,和过往的近代史进程实际上是有某种同构性的。我们19世纪下半叶的时候开始搞洋务运动,实际上是谈经济问题;然后百日维新谈政治问题,维新末端已经提出很多文化问题,后来到了“五四”就全面爆发,开始反省我们整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
记者:可是,在近代中国,我们过往的过程算不上成功,也没有真正完成过一次。
周熙明:在这一点上,我喜欢跟我们的近邻日本比,近代以来,日本已经完成了两次崛起,两次现代化,而我们依然在现代化的途中。原因是什么?我觉得伊藤博文有段话很有参考价值,伊藤博文代表他们的政治精英,当然也是知识精英,他当时就说,一个国家的崛起要有经济的崛起、政治制度的崛起,还要有心灵的崛起。
我们中国人当然不应该不明白这样的道理,但让人困惑的是,在近代中国,我们从来没能同时关注经济、政治和心灵的同步崛起,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样的过程:从一味重视器物层面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开始,直到经济发展无法继续了,才被迫把目光投到政治制度的革新上;等到制度革新走到山穷水尽了,又被迫把主要精力放到思想文化的更新上。
但是,生活总是整体的,真理也是整体的。在日本,经济、政治、心灵的崛起是同时展开的一个过程,它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今天说GDP成长的同时,也在追求政治制度上脱亚入欧,以及思想文化上的脱亚入欧,它是一个同时进行的均衡推进的过程。我们恰恰好几回都是只片面追求一个目标,到最后必须停摆。这可能是一个我们还在途中,日本已经两次崛起的秘密所在。就像一个人的发育,10岁已经长到1.80米了,你的骨骼如果不发育,我把这个骨骼比喻成政治,政治制度如果没有发育,你再这样长下去肯定要出问题的。骨骼发育了,肌肉也长起来了,但你的心智如果没有跟上,那最后成为一个傻乎乎的傻大个肯定也不行。
所以均衡的推进看上去好像是慢一点,但同时考虑肌肉、骨骼和心灵的问题,最后它完成一种均衡的推进,反倒是快速的现代化。我们过往的现代化历史,往往太急于求成,搞经济就忘了制度,谈制度的时候又忽略心灵。
1871年的时候,德国那个铁血宰相俾斯麦就说过一句话:中日两国,一个天朝大国、一个岛国,未来30年如有竞争或者战争,必是小胜大输。人家问他理由,他说中国人到我们欧洲来就谈生意,买枪炮、买战舰,买完拉倒就走;而日本人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翻译他们的典籍、学他们的典章制度。光是买这样的看得见的、有价值的东西,这样的国家能不败吗?
后来甲午战争果然中国失败了。
我们启动现代化比日本早,一百多年却总是半途而废。我们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头痛医脚、脚痛医头。这一次要真正持续进行,不要半途而废的话,必须把这个根本性的短板补起来。唯有文化的关怀是整体的生存状态的关怀,如果没这条很危险。
我们的文化危机是圣贤失语了
记者:那么共产党所致力的文化建设,跟百年来的轮回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周熙明:共产党的历史使命,用我们最近30年的话语方式来说是“社会主义改革”;用60年的话来说,要完成“革命党向建设党、执政党转变”种种这样的表达,但事实上,从文化意义上来说,最终还是要克服中国1840年以后逐渐深重的文化危机。
我们原来的圣贤一方面给所有的民众提供精神居所,所谓的精神家园;另一方面,它作为一种公共的产品提供给大家用,就是公共的价值,我们用惯了,几乎2000多年不需要变,这个建筑非常牢固。但是欧风美雨的强劲到来,使我们这个精神居所,使我们的精神家园突然处于风雨飘摇当中,用另一种话来说,我们的圣贤失语了。
如果说孔孟是我们老的圣贤,德国的马克思则是中华民族新的圣贤。我们引入马克思主义,在缺乏物质文化条件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是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一种应急的机制、应急的体制来缓解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危机。我们用一套革命的方式、用一种把生活中的一切进行简单二分的战场思维的方式,来应对我们所遇到的危机,有效地缓解了我们的文化危机。
但是到了今天,危机时刻已经过去,我们已由非常态的生活转变到常态的生活,我们这种革命的体制也要随之转化为日常的体制。过去那一套革命的政治意识形态不能完全充当今天常态社会的文化价值系统,充当不了了。为什么呢?我愿意把它表达为文化的几个“无”,文化无根、文化无魂、文化无序、文化无声、文化无力、文化无信。我们中国人今天文化上的几“无”和一种普遍的、各个阶层的文化焦虑,我们站在一个十字路口,迷路了,这种危机是难以看见的真正的文化危机。
从以圣人之心为心,到“以百姓之心为心”
记者:执政党的文化建设,对于整个国家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周熙明:就是从一种应急性的体制,到一种常态的体制;从造反思维、革命思维到执政思维,从战场思维到日常思维,从纯粹的政治思维,到一种广阔的文明思维,甚至也可以说是从以圣人之心为心,到“以百姓之心为心”。中国过去从来都是以圣人之心为心,老的圣人是孔孟,按照他们的概念、学说来规范我们的生活,新的圣人是马克思、毛泽东,以他们的心来教导众人之心,但真正的常态思维,尤其是谈文化,就应像老子说的一样,“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对于我们中国共产党来说,我觉得要完成这样一个转变。
记者:未来的文化建设是建设一种精英的文化,知识分子的文化,还是劳苦大众的文化呢?党的十七大报告里关于文化建设的最后一句话也说:“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当中的主体作用”,人民群众有成为主体的可能性吗?
周熙明:这句话说得很简单、很朴素,实际上是意味深长的。但说实话,我自己也没有想好。至于我们未来文化的发展,你说不应该是精英的文化,也不应是知识分子的文化,这个要改一下——不应光是他们的文化。
文化在各个历史阶段也不一样,在古典社会里面,的确文化主要就是为少数社会精英所享用。我们不能设想2000多年以来没有孔子这种社会精英、知识精英,社会就是分成先得道、后得道,先觉醒、后觉醒,就是这样各方面都分阶层的。
当然当人类进入了现代社会,情况就很不一样。现代文化为什么会发展?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根据自己幸福的标准,用自己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的幸福,它的副产品就是精神文化的繁荣。在这个时代,由精英以任何方式发动的政治运动、文化运动、新生活运动等等,都只是表达少数人的一种愿望而已。
真的,不管你是怎么说的,只要进入现代性生存,一个最主要的标志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理解的幸福的标准,和他实现幸福的特殊途径。只要是不触犯法律,不触犯一些基本的道德,他做什么事情都是可以的,这是文化繁荣的一个前提。要让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享受已经创造出来的文化,而且更有权利和义务自己创造文化。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人民群众是文化建设的主体的内涵。
文化问题不是数学题
记者:这场文明转型能够兼容多种文明吗?
周熙明:至少我们应该去努力推动三个层面的兼容:内外兼容;上下兼容;古今兼容。前一段时间不是老在讨论西方发达国家的普世价值的问题吗?我们不是照本宣科来谈它的价值,任何一种普世的东西到了一个具体的地方,又变成特殊的;没有纯粹抽象的普遍,即便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在今天的中国,它表达的形式也会不一样。普世价值跟水一样,放到这个杯子里它成为这么一个形状,赋之以形的总是具体的历史,具体的现实,具体国家的传统。
内外兼容,我们不是要照本宣科说他们的那一套,但是要兼容。世界上190多个国家,大部分国家都认可的价值,你什么时候都去批判它,你干吗?这是要兼容,是一种兼容的关系。
另外要上下兼容,不能上层建筑,作为中央文件,老百姓完全不关心,完全是另外一套语词,那叫不兼容。不是生长于普通人的人心之上的那些东西,必然游离于生活,生活是所有文化、道德、价值、信仰生长的唯一的土壤,游离于生活之外,花一定会变成是纸花、塑料花,尽管也鲜艳,但是没有生命、没有香气,不可能有香味的,所以要上下兼容。
还有一个,古今兼容,我们是中国人的后代,文化上所谓一以贯之、薪火相传,传的是什么?传的就是我们古人就信仰的那些东西。如果跟我们古人,我们的经典都不兼容,提倡的价值一定是离开历史土壤的。
我们说文化实际上就是一部民族在历史当中,一代一代人活出来的,花开花落、叶发叶落,逐渐积累起来成为一种肥沃未来的腐殖质土壤。
记者:构建一套如您所畅想的什么都兼容的文化体系,是不是有点太乌托邦了?要有一套什么样的价值体系才能满足您这样美好的设想呢?
周熙明:我们谈文化就不能完全进行逻辑的切割、规整,以为文化问题是跟数学题一样推导出来的,这就没法进入真正的文化问题。今天我们有些人就是犯了一个毛病,又想找一群理论家到某个地方关起门来搞一个月,用数学式的方法推导出一套善的价值来公之于众,发给全国民众。这样做有好处吗?至少有个坏处,浪费很多纸张,破坏了自然生态。
人们说出来的大都是向善的,没有哪个社会、哪个政党说大家要做贼、大家要为恶、大家要喜欢丑,没有,世界上没有的。最重要的是你说的要有人信,真信。没有人信的任何完整的系统的描述,都轻如鸿毛,没有任何用处。任何一个社会、一个团体、一个企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所谓的核心价值体系,我们一定要追问,它主要是靠人们活出来的,还是靠说出来的?显然主要是靠活出来的。
我们谈文化、道德、价值、信仰,如果没有准备一套生命意志、行动意志去张扬、去担待、去践行这些价值的话,那这些表达为语词的东西,无论多么美好,都是二维空间生存的苍白的概念,或者也可以说只是一种向善的愿望,说得严重一点,这是一种意淫式的自我精神安慰,它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造成社会进一步的道德流失,乃至于崩溃式的流失,还会造成普遍的社会的人格分裂。我们的社会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假话、大话、空话、套话?那么多的言不及义和言不由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一种语词崇拜,就是我们常常缺乏行动主体和行动意志。
反省“愿望”文化
记者:今天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是说得太多,做得太少。
周熙明:是的,近代以来,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愿望”文化。动不动要什么,全在那儿表达,把好的东西说成你全要。但是现代性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则是什么?除了目标以外,要有目标和现实之间的中介,所谓工具,就是要找到途径,要有对途径的描述。要过河,是用船、游泳还是修桥?我们都没有这种中介,都是诉诸一种意淫式的自我安慰的幻念。
记者: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能从这个困境中走出来吗?
周熙明:一定能!如果缺乏信心,或者先就认定了走不出来,那我们还去讨论它干吗?我们敢于进行深刻的文化反省,指出生活中存在令人烦恼甚至痛心的问题,恰恰表明我们对未来有一种乐观的信念和克服任何困难的勇气。相反,那些不敢正视问题或面对危机却若无其事的人,才是真正的悲观者、胆怯者、逃避者和对党对国家对历史不负责任的人。
怎么办?首先应该让代表真善美的价值成为制度的灵魂,当然要有人进行理论的表达,但理念之光如果没有落实为一种制度的灵魂,它作为大观念很快就会像天上的浮云一样随风飘散,无影无踪。
先是赋之以形,就是让价值理念进入制度,成为制度的灵魂。然后付之于行,也就是让价值理念成为社会成员尤其是社会精英的实践理性,也就是让价值理念找到前面说的那个生命的行动意志的支撑。最后,制度成为了习惯,理念成为了文化基因,核心价值体系自然就成为了国家、民族和社会的灵魂,天地之心就立起来了。
记者:靠什么付之于行呢?
周熙明:所有在现代史上后发的国家,社会的三类精英在文化再造当中起着特殊的作用,就是知识精英、财富精英和政治精英,他们要首先付之于行,就是首先要用行动、意志去担待这种价值,给民众树立榜样,让这种价值由对大众的制度的要求、普照一切的概念之光,变成由一个个血肉之躯、行动意志张扬开来的东西。
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以近处的说,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为什么会搅动整个地球、全世界?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凯歌行进?固然是马克思、恩格斯这些天才说得好;但是最重要的是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准备用自己的整个青春、生命、家庭去担待它,我拿我的血肉之躯去喂养这个概念,能不把概念喂养成一种坚强的、强大存在吗?
你想想,现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肯定要比当时(多数革命者都读不到《资本论》)好得多,理论上说得比原来不知道要周全多少。理论研究从纯粹学术来说的话,比原来的水平高多了。可是为什么遭遇危机?是因为缺少血肉之躯生命意志去张扬马克思所倡导的价值。
远的例子是儒学,儒家学说2000多年来为什么在中国的精神里面,占这么大的空间,占领这么长的时间?固然是孔孟圣人们说得好。但说得好的人多得很,为什么一旦选取了它以后,它能这么持久地占领中国的精神空间,长期成为不倒的精神居所,是因为几十代以来的儒者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生命意志去张扬孔子所倡导的价值。
你看看方孝孺可以用700多口人的性命,来捍卫他所信仰的儒家真理,当然也有人怪他太残忍了,但是我们要看到一点,他为了弘扬这个道,什么都能奉献,这是何等决绝的生命意志。
近年来,儒学传播很有复兴态势,于丹先生他们口才都很好,在传播我们传统思想、情操、价值方面做了很大贡献。但是如果认为这样儒家学说就可以成为我们未来新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话,那就错了。
没有儒者的儒家学说,只是学说而已,是文献式的、文本式的存在。儒学原本就不是作为一个纯粹的西方式的学问存在的。今天,这里成立国学院,那里成立国学院,可是国学院里有儒者吗?没有儒者的国学院等于太监谈恋爱,只有形式没有内容,没有那种来自宇宙深处的我们也许永远不理解的生命意志的冲动,任何说得好的学说都等于零。
从儒学到马克思主义,说这两个例子,只是想说明,今天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要靠社会精英们活出来的,绝不是单靠说出来的。
一切政治公共品都是文化公共品
记者:文化的重建可能是一个漫长历史过程,那么,作为这一代人,我们眼前要做的、能做的又有哪些事情呢?
周熙明:在我们现在这么一个梦幻色的、因众生喧哗而过度喧嚣的社会里面,我们最急于需要的是一个文化公共品,也就是天天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最长的特殊民族、特殊国家的唯一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提供的政治公共品、文化公共品。
中国不是一个简单的源自西欧那种民族国家,我们既是一个民族国家,又还是一个文明体。中国共产党在这样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文明体里面执政,提供的一切政治公共品同时也是文化公共品。作为公共品,至少要有两个特征,一是人们愿意消费,第二是人人都可以消费。
文化一旦只是作为GDP发展的策略,它就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物化了,就不再是文化了。近代以来,中华文化中所谓关乎心灵的东西,始终未能受到真正的关注,文化成为经济的奴仆,这是最为悲剧的命运。我们应该吸取这样的教训,尽力避免宿命重来。
记者:那我们从哪里汲取资源和能量来避免宿命重来?
周熙明:必须启动各个阶层,越来越多的社会个体去进行自己的精神创造,在追求物质幸福的同时,也追求精神升华、精神生活质量的提高。政府的职责是要提供一种宽松氛围,一种创新的环境,使每个人的生命能量、创新的潜能都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当每个人的生命能量、创新的潜能都能得到充分发挥的时候,作为一个社会的整体效应,这个社会就必然成为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创新型的社会。下一步中国的文化要发展,整个现代化要持续推进的舌,首先是每一个个体的尊严、价值、创新的潜能要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
记者:创新的口号我们已经提了太多了,我却发现多数是创而不新,文化要怎么创新呢?
周熙明:返本方能开新。我们文化上要创新,就要尊重自己的历史,尊重文化上的祖宗,回到自己的原典。一个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怀着轻薄态度的社会,是不会有创新的智慧的。现在国学应该说要重新诠释我们在诸子百家大争鸣时代的那些原典,这是对的,面对真实的现实问题,重新向文化轴心时代的那些先贤们讨教,与他们切磋对话,必能让我们获得开拓未来之路的勇气和智慧。
反本开新,另外一个“本”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典;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典进行重新的解读,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完成现代化,完成国家的崛起,完成整个中华文明的复兴,走出资本逻辑带来的现代性困境,甚至是绝境。如果能敝到这些,我们的文化重建还是大有希望的。终有一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能够真正锻造出自己的独特制度、秩序和提供自己独特的思想、文化、价值、信仰,从而为整个人类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新的独特的贡献。
标签:政治文化论文; 精英主义论文; 周熙明论文; 精英文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论文; 精英阶层论文; 中共中央党校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