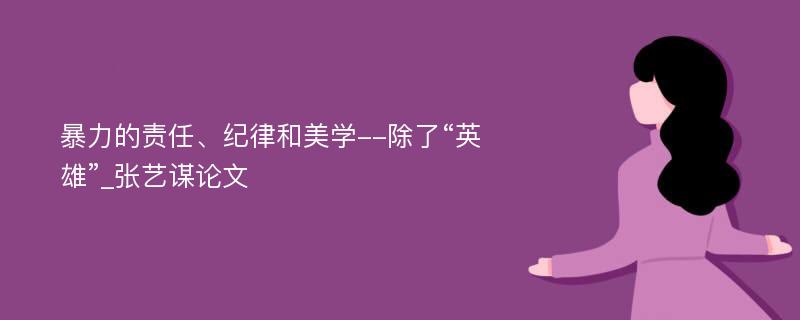
责任、规训与暴力美学——再说《英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暴力论文,英雄论文,责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2年上映的《英雄》迄今已经过去4年,当时人们怀有的那种情绪现在已经平静,回过来看看张艺谋的这部大片可能会有非常不同的感受,在当时被遮蔽的不少问题也会水落石出。
谈论张艺谋在当今中国已经很难有单纯的艺术的和学理的讨论,张艺谋既象征着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成就,也表征着中国电影在艺术追寻与市场化定位之间所遭遇的最深刻的尴尬,面对这种尴尬状况,中国观众异乎寻常地吝惜了他们的同情和怜悯。这与中国当下日益增长的酷评不无关系,对于文化现象,特别是那些巨大的文化现象,中国观众(和读者)就等着看笑话,没有人会真正认真地对待这些现象,平心静气给予恰当的探讨和批评。嘲笑与谩骂已经不幸成为当代中国文化传播的主要风格,这是媒体为吸引眼球而培养起来的风格,其深层时代精神则是一种威权压抑和社会不公正的心理变态反应。人民对占据了社会巨大资源的群体深怀不满,这些群体的大多数深藏不露,而这些明星名人们则要在媒体出现,他们在充当人民崇拜的偶像的同时,也要承担人民发泄愤懑的情绪。2006年的今天,人们对此已有更深切的感受。
张艺谋的那些大片在电影院放映完之后也就引发了一阵疑问和责难,随后就被迅速淡忘,这使学术界也不太敢染指张艺谋,似乎这是个烫手的山芋,谁沾着都不会很轻松。因此,这里试图再次探讨一下张艺谋《英雄》中所包含的一些矛盾状况,那就是影片的思想意识与他的艺术表达之间构成的复杂关系。期望不会被归入“倒张”的阵营,也不会被列入“保张”的行列。
如果说《英雄》有什么主题思想,“天下”二字无疑是其点题之词。影片反复提到“天下”,无名、残剑、飞雪、秦王之间的深仇大恨,都在“天下”二字前化解。影片的内在转折也是依靠这两个字。影片的后半部分主要是在烘托这两个字或者说这个主题的出现。“天下”的意蕴就在于表明:为了天下的和平既要放弃恐怖主义式的暴力谋杀,又要容忍甚至支持强权武力征服世界。这两方面看似矛盾的思想内容统一于“和平”的意愿上。刺客放弃刺杀而支持强权征服是为了和平,而强权自我确认的正义也是为了和平,和平成为化解一切暴力的最高正义。张艺谋的《英雄》上映之时,正值美国“9·11”事件过去一年,如果说张艺谋拍摄这部电影是直接回应“9·11”事件,那有点过分,但影片的拍摄和制作过程肯定会受到“9·11”一定的影响。“9·11”事件不过是冷战后国际冲突的升级,在此之前地区冲突和恐怖事件就充斥了电视的新闻内容,张艺谋制作《英雄》不可能不考虑这样的现实背景,它表达的内容也明显是在与后冷战时期建构国际新秩序的艰难现实对话。张艺谋试图思考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在遭遇恐怖主义时的走向,他也试图调动中国的思想文化资源为这个时期的历史抉择提供一种参照。作为影片的主导思想——“天下”就是要调和中国本土的传统政治与现代国际政治的关系,做出现实的直接回应。当然,电影是一种艺术作品,我们有必要去理解和分析,如此重大的主题在张艺谋的电影思想中具有何种意义?它在《英雄》中又是如何展开的?这个思想主题的呈现与其艺术表现构成何种紧张关系?这就是本文试图加以探讨的内容。
一、天下:面向新国际的规训
天下,在中国古代主要指中国范围内的全部土地,其意为全国。《书·大禹谟》:“奄有四海,为天下君。”《论语·宪问》:“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但“天下”也可指全世界。“天下”是中国政治家和古代士大夫以及现代知识分子最经常提到的词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的名句几乎是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口头禅。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是现代中国政治家的标准口号,至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则是激动了中国现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的座右铭。很显然,“天下”观念也是张艺谋这代知识分子或艺术家所熟知的概念,这已经不只是中国传统儒家士大夫式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还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理想信念。经历过“文革”,政治理念并没有削弱,整个80年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正是满腔热血,报国有门,他们也理所当然地把自己看成是推进中华民族改革兴盛的动力。90年代,中国社会的政治色彩有所减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社会的专业化程度的提高,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热情普遍下降,如柏林墙倒塌后,福山(F·Fukuyama)所说的“历史终结”那样,以政治来支配社会和人们的精神的那种意识形态也已经终结。
90年代是张艺谋崛起的真正时代,就当代电影而言,这是一个张艺谋的时代。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张艺谋最早也最成功地领悟到了中国电影如何走向国际,如何在当今多元化的国际文化语境中找到中国话语的存在方式。正因为此,张艺谋的电影在90年代对中国的表现不是现实主义式的直接呈现,而是历史寓言化式的隐喻表达。它在西方的电影界是以“他者”文化的形象出现,它是来自第三世界的压抑性的怪戾的文化。对于中国的历史主体来说,对于主流的中国现实来说,它也是一种边缘性的、非现实的,它是被剥离的历史碎片。80年代,张艺谋以《红高粱》一鸣惊人,这部影片包含着强烈的时代情绪,那种野性的恢复民族生存力量的渴求表达了当时中国人普遍的生存愿望。但转向90年代张艺谋面临着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选择,他对思想情绪的捕捉就低调得多,那是自觉他者化和边缘化的选择。《菊豆》那是一种压抑的乱伦,灰暗色的电影语汇表达的是压抑与绝望的情绪,多少也反映了90年代中国的历史无意识。《大红灯笼高高挂》写出中国女性在传统社会最后的历史情境中的命运,其文化特征的怪癖和畸形无疑是刻意的自我塑造,强调的依然是他者化的品性。《秋菊打官司》像是反映中国底层妇女的遭遇和个性,其现实性似乎相当充分,但放在中国现实语境中,秋菊的形象只是弱者的勉强呼喊,而她怪模怪样的特征与其说连接中国当下的农村与现代意识的关系,不如说她的诉求对象依然是国际电影市场。至于《一个都不能少》和《幸福时光》,张艺谋还真是想对中国现实发言,但并不是很成功,而且张艺谋习惯了处在边缘来思考,他的底层小人物的自我意识被压制到最简单的状况,张艺谋已经习惯作为一个文化的“他者”在主流文化之侧徘徊。但是他的这种“他者”并不是与历史主体(以威权政治为中心的历史支配力量)形成对抗关系的他者,而只是一个自觉远离历史主体位置的他者,依然是那种第三世界的寓言化叙事使他去表现那些无助的处于生存困境中的被同情的小人物。很显然,在思想上,在电影人物的精神品格上,张艺谋一直处于一种“弱势状态”,他的影片所表达的思想,或者他的人物所承载的思想,并不具有当下中国历史的深刻性和时代的鲜明性特征。也就是说,在现实潜在的矛盾冲突意义上和官方自我塑造的主流话语层面上,张艺谋都并不有意识地参与其中。
很显然,《英雄》是一部大片,与张艺谋过去的影片很不相同,可谓气势磅礴,意境深远,尤其是影片试图站在历史主体的位置上,表达具有历史深刻性和现实针对性的思想——“天下”就这样成为影片的主导思想。这是张艺谋一直在内心渴望的一种表达激情,摆脱思想意识边缘化和弱者化的状况的一种努力。那是《红高粱》的狂野放纵,暴力与欲望,革命与祭祀的复活和重建。“天下”就这样现身了,张艺谋真有一种酣畅淋漓的痛快感觉,要不然那些剑拔弩张不会那么飘逸舒展而无所顾忌。作为对现实的回应,张艺谋仿佛又找回80年代的感觉,那就是中国知识分子重新承担了历史责任的感觉,也是再次与国家意识形态能够契合一致的感觉。进入21世纪的中国,在经济上创造的高速发展的神话,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也以一个大国的形象周旋于东西方之间,可以说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引人注目。特别是反对恐怖主义,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具有了更多的共同利益,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国家,其国际地位显得日益重要。关于“和平崛起”、“和为贵”以及关于“和平发展”的种种国际政治话语,使中国在当今国际政治语境中找到了一种进退自如游刃有余的路径,尤为重要的,那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与当下的国家形象重建融合在一起,颇为巧妙地抹去了意识形态色彩,这是现实的遮蔽与历史的跨越所获得的崭新的形象。因此,可以说,张艺谋的“天下”既是他本人的思想在新世纪之初的表达,也是携带着中国民族-国家本位意识对新的国际政治面临的挑战所作的应答。
二、天下:暴力与艺术的超越境界
“天下”作为一个电影叙事话语在影片中被点出都是在重要的场景中。
“天下”第一次出场是在残剑劝阻无名刺秦王未果时,残剑在黄土漫漫的大地上用剑写下这两个字。那是在空旷的野外,沙土飞扬,在道上,残剑的劝阻无效,无名对残剑说:“你气力已衰,不能再挡住我了。”无名迈步告辞,残剑的眼神格外忧伤深沉,但深沉的目光却不看无名,残剑望着手中断剑说:“此剑,为侠者所传。”残剑说:“我若辜负它,便再不是剑客。”残剑说:“我最后以残剑剑法,送你两个字!”残剑郑重举剑,剑指沙土,一笔一画,书写下他的嘱托。无名在一旁凝神看残剑书写。残剑写完,低头守在字前。观众看不清这两个字,但无名看清了,风刮起,卷过黄沙,抚平了地上的字迹。但这两个字却使无名若有所思,铭记心中。这是影片第一次郑重其事写下“天下”,不是以直接说出的形式,而是以书写的形式,“天下”是以剑法书写下的大义。为了这两个字的出场,影片做足了气氛。
这样重要的主题思想,电影叙事当然不会轻易说出,张艺谋不用说深谙此道。这个“天下”主题思想在影片中通过各种氛围的铺垫再次出场;在影片中人物那里则是通过对“剑”字的领悟而得到的。无名要见到残剑、飞雪,他以求字为名,求的就是残剑写的“剑”字。而残剑的剑法,就源于一幅字①。残剑和飞雪一同迁到书馆,以期从侯嬴的书法《天下论》中悟出绝世剑法。残剑于是努力悟字悟剑。残剑练成了一套剑法,写成了一个字:“剑”!“剑”字挂在墙上。残剑独自面壁,体味字中奥妙!影片反复呈现那个用朱砂写就的大红的“剑”字,那本是后来无名向残剑求的字,在影片中也奇怪地被当成是当年残剑面壁领悟的“剑”字。按李冯剧本小说的说法:书法精义,在于人字合一,剑法也如此,讲求人剑合一,于是,残剑慢慢地领悟到剑法的至高境界了。残剑当时从“剑”字中悟出的至高境界中,就是不能杀秦王的道理。当时残剑自己都不敢相信!可以设想——按李冯的剧本小说,残剑岂止不敢相信,还很震惊!残剑震惊之余又感到痛苦!但残剑当然是想通了,悟出的不只是剑法,而是天下的道理。是历史的意愿,是人民的意愿。残剑悟剑的过程,也是悟天下道理,要胸怀天下,才能胸中有剑!残剑说,书馆悟剑那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日子。残剑还悟到,剑虽不能平定天下,但可以帮助具体的人,可以帮助天下,这是剑法真谛!残剑身为剑客、侠士,就不能违背侠士精神、剑客信仰!
残剑从书中,从书法中悟到什么道呢?那就是:秦王不能杀!这是残剑从书法中悟出的道理。这倒是一个奇妙的辩证法,剑是武器,那是用于杀人的,而残剑练剑,悟剑法,就是为了刺秦王。而他对“剑”字的领悟,也就是对写下的文字,对书法的领悟却是得出剑法,而这个剑法的最高境界,是反“剑”,是对剑的消解。一个事物包含着消解自己的存在的内在性,而且是其最高的也是最根本的内在性,反-剑就是“剑”的本质——“剑”字蕴藏的是“天下”的玄机。张艺谋这里当然又是在搞东方神秘主义,书法里面居然可以蕴含剑法,艺术与暴力就这样被合为一体。
这个“天下”不是空旷的天和大地的概念,而是人的生存世界,而是历史和社会,人民的愿望。影片随后就赋予“天下”以实际内容。残剑说,天下本来是统一的,没有战争,人们过得和睦,生活在和平中。慢慢天下就分裂了,分裂成许多小诸侯国,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连年交战,人民如同被置于水火。战争已持续了七百年。百姓做了七百年噩梦,结束噩梦,就要结束战争。如果天下不统一,战乱不会止歇。谁来结束战乱?再强的剑客也做不到。剑只能消灭具体的人,不能消灭战争。有一个人能做到:秦王。对照李冯的剧本小说,其中这样写道:残剑以为唯有秦王能平定六国,结束战乱!所有诸侯国被秦王统一,那会是痛苦的过程。可痛苦过后,人民可能就不会痛,是阵痛。阵痛比永痛好,长痛不如短痛!这是痛苦的推理。残剑领悟出来后感到痛苦!但一个人的痛与天下之痛比,那就不算痛了!甚至赵国对秦王的仇恨,也无足轻重!赵国能比天下重吗?由此可见,“天下”的概念在这里,就是一个“中国统一、获得和平”的概念,就是拯救万民、顺应民意的概念。
秦始皇统一中国,功过是非一直是史学界争议的话题,其争议主要是落在秦始皇的“暴君”身份上,秦始皇的残暴不仁与他统一中国的功劳自然是两个不同的方面,也不可二者简单做一个加减。他的残暴是事实,他统一中国也是事实。而在那样的年代,按照主流史学界的说法,统一中国就必定要采取残暴强硬的手段。因此,与统一比起来,秦始皇的残暴也就可以理解、赦免了。问题在于,在那样的年代,统一就一定要采取残暴的手段吗?比如史称“焚书坑儒”,一定就是统一的必然手段吗?② 但不管如何,秦始皇统一中国还是在中国历史上得到正面评价,特别是在1950年后的中国得到积极的肯定。这当然有某种历史与现实的对应关系在起作用。仅仅从歌颂暴君这点来批评这部影片的思想主旨并不恰当,根本的问题在于,这部影片表达的思想主旨——亦即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意义——并没有什么新意,并无独到之处,它不过是中国史家或褒或贬的陈词滥调,也是当代史学的主流观点。如果停留在这一层面上,那么对这部作品表达的思想意义理解就很不全面。作为一部与当代国际政治语境对话的影片,其思想主旨当然不是落在这么老套的话题上。
从刺秦到不刺秦,这在残剑和无名都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这是对秦统一中国的可能性的愿望,而这个天下愿望的背后更深刻的愿望,则是人类对和平生活的渴望。历史发展到今天,大一统被质疑的可能性要远大于被赞同的可能性。但和平这个同样老套甚至更古老的话题,在今天却是当代世界性的主题,也正因为这样的一个当今“天下”的愿望,当今在国际政治中最基本的和根本的共识,《英雄》才敢于在那么老套的秦统一中国的意义上做文章。
把“和平”作为主题,这在张艺谋当然没有问题,他对当下国际形势的回应无疑是及时的,这是他要尽的一份责任,也是他能给予国际政治新秩序建构的规训。但这只是张艺谋对当今“天下”的理解,而未必是秦始皇对他所处的时代的理解。秦始皇想的不过是统一霸业,不过是帝王统治的伟大梦想,秦王当然也有责任,但他的责任是帝王霸业的责任,如果把他的责任愿望置换成“天下和平”,那就是失之毫厘,谬之千里。统一霸业就是帝王的霸业,而和平则是当今“天下”的愿望。残剑所思与秦王所想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从影片对残剑作为一个士所抱负的胸怀来看,残剑寄望于秦王统一中国,结束七百年的战乱以求得天下太平;这是残剑作为一个民间的士可能具有的民本主义思想(这无疑也是虚构,但其可能性还是合乎历史逻辑)。但古往今来的帝王则是为了称帝,为了帝王霸业而征战,平息战乱也是为了巩固王朝,而征战则是扩大帝王的版图。和平只能是,也始终是帝王霸业的副产品,也永远是人民愿望的不可能性(或部分实现的有限可能性)。
影片描写了秦王与残剑所达到的那种沟通。在大殿上,秦王低声问无名:“残剑给你送了哪两个字?”无名凝视秦王,两个字的说出仿佛有千钧重,影片配着隐约的风声,仿佛残剑嘱托时的情形。无名终于慢慢地把那两个字说出来:“天下!”秦王微微一震:“哦,天下!”无名对秦王继续说道:“残剑告诉我,天下七国连年混战,使人民受苦,可唯有秦王才能结束战乱。残剑希望我为了天下放弃!他要我明白,一个人的痛苦与天下人比便不是痛苦;赵国与秦国的仇恨放到天下,也不再是仇恨!”秦王明显被震撼了!这位威震海内的君王竟不知不觉热泪盈眶。影片这时几乎达到高潮,秦王透过泪水,凝望大殿之外,越过黑压压的群臣,遥看远方。他已不再冷酷,仿佛已经动容。秦王说道:“没想到天下最了解寡人的竟然是寡人通缉的刺客!”李冯的剧本小说写道:一代豪君,一生金戈铁马,睥视六国,却承担不了残剑的两个字!短短的两个字,然而对于秦王,却重过世间任何事。英雄相惜,秦王饱含热泪,放纵自己内心情感。在电影里,这时的秦王已经是心潮澎湃:“十年来,寡人孤独一人,忍受多少责难、多少暗算!没有人明白,我要给百姓一个统一的疆土,给他们有同一个国家!就连我秦国满朝文武,也怪寡人与天下为敌!只有残剑,才真正懂得寡人!才真正与寡人心意相通!”这就是影片真正的高潮了:风穿过大殿,秦王长喟:“寡人得到这样一个知己,心中无憾!”在责任中他们达成了共识,他们获得了默契。
话说到这一步,秦王已经被感动得一塌糊涂,他立在残剑书写的巨幅丝帛下,看着那“剑”字。秦王说:“寡人能有残剑大侠这样的知己,便是死,此生也已知足。你为天下,决定这一剑吧!寡人也如残剑大侠一样,刺与不刺,交于无名!”说完,秦王竟转过身去,把剑扔给无名,他让无名决定刺与不刺。就在无名举剑要刺时,秦王却突然悟到剑法,秦王对无名说:“难怪你悟不出,残剑这幅字,本来就不是剑法,而是他用心在写!寡人不如残剑,你我都不如残剑!”一边是悟字,另一边无名在举剑,但秦王却沉醉在对剑字的领悟中。秦王继续说:“残剑写给你这两个字,便是说,刺与不刺,已不重要!秦将统一六国,势在必行,大势已成。一个人的生死,改变不了天下。天下大势,残剑早已看透!可天下是什么?它是百姓所盼,民心所向!”天下现在不是秦王的天下,而是百姓的天下,秦王在这里与残剑达成共识:“那便是不杀,便是和平了!”秦王变成了一个向往和平的人,变成一个与民间的刺客或侠士一样的人。秦王看出,比王更重要的是天下,天下大势,无人可以左右,就算秦王自己死了,另一个新的王,仍然会统一天下,因为天下需要统一,需要安宁——秦王被这个发现震惊!秦王这才觉得自己也悟出了王者真谛。无名最终还是使出了他的十步绝杀。但剑缩在无名手里,没有真正刺秦王。无名对秦王说:“天下!请大王记住这两个字!”刺杀于是终结。记住“天下”,就是历史之终结,就是新纪元之开始——这就是以民为本的和平观。这是说给秦王听的,是秦王悟出的,也是说给当今新国际听的。
在这里,根本被混淆的是帝王统一霸业与人民的和平愿望。秦王的历史面目被彻底更换,一个哀婉动容、仁义慈爱的秦王,一个爱好和平事业的秦王,替换了历史上的野心勃勃、残暴不仁的秦始皇。作为艺术作品,这样虚构未尝不可,我们的理解不是去质疑这种虚构的合法性,而是去追问这种虚构的合理性和可能性。这样的裂痕并不只是作为一个历史记载的秦始皇和作为一个电影叙事的秦始皇的区别,更重要的在于,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与人民的愿望之间的巨大裂痕,这种裂痕如何在那样的瞬间,在面对一幅字时就领悟到了?在这样的瞬间,完成了一切的和解、信任、期望和嘱托。这是参禅?是佛教的顿悟?这个巨大的历史的和阶级的裂痕,却是通过神秘主义式的感悟做出的,这实在是差强人意,这是虚构中的虚构,是一个不可能的虚构,这是虚构的不能性。说到底,这种强行的虚构背后的动机就是为了说出“天下”,就是为了重建当今“天下”新国际的秩序。
当然,无名是最终的英雄。长空是英雄,残剑是英雄,无名是最后的英雄。他们都是为人民的利益,为天下的和平而不杀秦王。长空、残剑与无名之间的友情和信任都因为对“天下”的责任而升华,这个本来是要描写友情和信任的故事,实在是因为当今“天下”的巨大阴影而转向了责任,为“和平”的责任。如果是关于责任、信任和友情的书写,这部电影可能真的会有惊人之处,但这一切都因为面向新国际的当下规训的需要,而要让无名与秦王达成一致,这就使统一的(在叙事的意义上)需要压倒了影片的深化。电影叙事设法使最不能弥合的鸿沟——秦王与刺客达成共识,这都是为“天下”的责任考虑。无名最终未刺死秦王,而是嘱托他:“记住天下。”刺客们其实毫无把握,他们何以能信任秦王为天下着想呢?实际上,他们的“天下”根本不同,秦王的“天下”就是帝王的统一霸业,而刺客们的“天下”是和平。而这种责任、理想和抱负,既不可能也显得无比虚构化,秦王站在大殿上,看着没有刺死他的无名走去,双眼饱含着泪水,一个仁慈的君主,也就是一个软弱无力的帝王。此时呼声四起,杀死他,杀死他,那是秦国将士的呼声,那也是人民的呼声,那也是民意——也是人民的责任。什么是民意?古典时代的民意不幸早就被国族、阶级、法、责任、权利所分解。乱箭杀死无名,那是秦国的法在起作用,铁面的法之下,是不可弥合的古典时代的国族冤仇。最终能给统一赋予荣光的依然是强权,强权完成统一,而不是和平愿望,和平只是强权的副产品,和平只是暴力的有限补偿。秦王结果是真正的英雄,如果秦王没有完成统一结束战乱,那刺客们的期望就全部落空,不杀秦王就不会是一项义举,只是一件蠢事。秦王完成了统一霸业,把和平带给人民,他就成就了无名们的英雄美名,也成就了自己的英雄封号③。
三、暴力美学的依据和托辞
对于张艺谋来说,“天下”的观念只是一个概念,一个巨大的能指,它是宽泛的,模糊的,无法确定确切的内涵。一旦具体化,无名与秦王的共识就不能重合。但张艺谋需要这样一个巨大的概念,既能回到中国的历史中,又能应对当下世界性的难题,这就是侠士,就是一个中国式的“艺术侠士”。不同的是,无名们用的是剑——这个古典时代的冷兵器;而他们用的是电影艺术——一种汇集了思想智慧和高科技的现代媒体。张艺谋从90年代的思想困顿中解脱出来,因此能站在时代的前沿,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化英雄”而发言。这不只是张艺谋渴望自我建构的新的主体形象,也是他的美学寻求转换和变化的一个向导。“天下”作为影片中的思想意识,一个巨大的难以被真正具体化的思想意识,张艺谋因此可以获得一个美学表现的宏大叙事的背景。“天下”所表达的巨大的精神关怀,因为其模糊和不确定性,因为它空旷无边,因为它贯穿古今,它在美学上显示的表现风格也同样是无限大的。这就像《哈利·波特》和《指环王》之类的魔法片一样,其思想意识属于灵异世界,如果要现实化,那也是民族-国家,人类的灾难和自我拯救之类的巨大寓言。思想意识与艺术作品的叙事方法风格之间构成的关系,一直是文艺理论的盲区,本文当然也不想陷到这个疑难重重的区域。我只是想表达,“天下”观念的巨大空泛特征,乃是张艺谋要寻求的空灵大象的艺术手法和美学风格需要的精神依托。
张艺谋90年代的那些成功之作,大都是在压抑性的氛围下展开电影叙事,怪戾病态式的东方文化标识始终为人所诟病。而张艺谋的本性并非如此,他的成名作《红高粱》就是明朗热烈的作品。现在,张艺谋终于找到一个契机,一个能反映他浮出压抑的历史地表的巨型能指——天下。还有什么比“天下”与“英雄”更具有昂然挺立的主题呢?有这样的主题思想作背景,广延与高远的场面就有尽情挥洒的余地。因此,张艺谋惯用的大块的色彩,空旷的构图,点线艺术的随意穿梭都获得了形式主义的自由余地。在这个意义上,《英雄》就具有了张艺谋一直追求的唯美主义风格。
但是,《英雄》的唯美是巨型的唯美,这个巨大的唯美只具有形式的意义,而不具有唯美的内涵。唯美主义的经典形式是精细柔弱,其内涵则是颓废病态,但《英雄》则是充满昂扬之气,这与他的“天下”思想意识相对称。但张艺谋还是试图强调他的唯美,但那不是唯美美学的自主性的表达,而是“天下”的形式外壳。作为一部巨片,《英雄》不只具有思想主题之宏大,而且还具有电影语言之“宏大”。总是广角设置的巨大的背景,从远到近,或从近到远,大块的色彩,黑压压的人群,巨型的物体,辽阔的战场……,长空、无名、残剑、飞雪、如月等人,就都在这些巨大的背景和场景中舞枪弄剑。看得出来,张艺谋追寻的是一种空灵的东方美学。但张艺谋从整体上来说,偏爱青灰色的色调,它的空旷就不是真正的空灵和空无,而是有一种内在焦虑,有一种始终摆脱不了的压抑感。那个空无中藏着它的逻各斯,那就是一个始终在场的实有的“天下”。对于“天下”这个思想本身来说,它是空洞暧昧的,但对于空旷的电影表现形式来说,它却是一个实有,是剧中人物始终要迫近的意念。在美学与思想之间,虚与实之间,在超脱与目的之间,电影的叙事话语始终包含着“天下”的情怀。
“天下”不仅是巨型美学的前提,也是暴力美学的基础。因为对“天下”和平的关怀,暴力的充分展示就有了充分的理由。所有的美学都是在暴力行为中展现,美学是关于暴力的美学,是关于暴力如何展示得更完美、更刺激、更富有东方情调而设计。这不管是无名与长空的搏杀,还是与飞雪和残剑的比拼,或者飞雪与如月的绝杀,每一个场景都是被设计成形式主义的审美场景,那是东方式的空旷、点线、空白、变异的高度概括。令人惊异的是,每一个搏杀的场景都有“文化”在场,无名第一次遭遇长空就有一个老者弹琴,悲怆的琴声中这个暴力的场景被表现得如歌如诉。无名在书馆与残剑的拼杀,那是以书简作为背景的暴力展现,那是关于文明与暴力的搏杀,同时也是具有文化蕴含的搏杀。这样的搏杀是与“书”沟通的,是在书中的搏杀,是书启示下的搏杀,是为了文明的进步的搏杀。飞雪与如月的那一场绝杀安排在一片血红的樱花树下,纷纷扬扬的樱花使暴力与死亡变得华丽鲜艳,妩媚动人。影片反复出现的那个巨幅的鲜红的“剑”字,那是残剑、无名和秦王共同从中领会的意蕴,在这里,书法之美与剑法的境界被融为一体。剑法的最高境界也是暴力达到的审美境界,其意蕴则是“无”,则是对剑的消解,对暴力的解构。暴力的最高的境界就是美,美的最高境界就是暴力的消除。而它们最终都有一个实在的所指——“天下”。
“剑”字作为暴力与美学的统一体,它是始终在场的逻各斯,它是一个神符,是一个伟大的启示录,是一部开启的神学词典,它被反复书写,被残剑和飞雪以情爱的形式反复书写,那也是反复的膜拜。影片中他们俩共同在沙盘上临摹,那会心的相视一笑,是情爱对暴力的消解。暴力与美学的最终统一就是“天下”,暴力美学的最高的和最终的境界就是“天下”。“剑”字原来就是“天下”的在场,就是“天下”的存在-神学。因为胸怀“天下”,长空、无名、残剑、飞雪演绎着暴力的所有场景,那是美学的场景,是“天下”使暴力具有了美学的含义,也是因为要抵达“天下”的神学,要不断地展现暴力的美学。只要胸怀“天下”,渲染暴力就具有美学的意味,或者说,在对暴力的美学追寻中,领悟到了“天下”的真谛。张艺谋把暴力展现得美轮美奂,这是为了“天下”,这也是无意间的抵达吗?残剑是在日复一日的书写剑字、感悟剑字中蕴藏的剑法而领悟到“天下”的。“天下”是一个预谋的逻各斯,还是一个意外的副产品?对于残剑来说,那是后者,而对于张艺谋来说,那肯定是前者。只是蕴藏于暴力美学中的“天下”不再那么纯粹,不再那么真诚。就像秦王突然转过来说的那样,“寡人悟到了!”那是让观众吓了一跳的时刻,那个暴力与美学最高的和最终的统一时刻,不幸地是一个略显滑稽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瞬间。《英雄》说到底玩的是暴力美学,“天下”终究不过是一个突然感悟的逻各斯,只有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在生死的关头,秦王突然感悟到了。这不是一个去蔽的时刻,这是一个怪诞的时刻,那是一个明显的预谋的逻各斯。
张艺谋既要怀着巨大的美学冲动,又要怀着面对新国际说话的愿望,这二者都在“天下”那里获得支撑。然而,“天下”并不能统合这两方面的需要,作为宏大美学的基础,“天下”让张艺谋如愿以偿;作为向新国际说话的依据,“天下”并不能恰如其分。在当今新国际的舞台上,谁是秦王?谁是无名?没有人可以对得上号。张艺谋本来也没有指望对上号,只是那种似是而非的隐喻,故作高深的格调好像要给天下大势指明一条未来之路。这样的隐喻和比拟被历史阻隔而不再能重合,这是巨大的现代性创伤,是哈特和内格尔式的“新帝国”时代的挫折④。古典时代的“天下”本来就是帝王的天下,因为王权而具有统一的本质。当今的天下早已是四分五裂,冷战后并没有迎来一个和平的新秩序,而是更加剧烈的文明间(宗教间)的冲突。新国际的刺客们有了新的封号,那就是恐怖分子。这是追问谁的“天下”的时代,这是打破强人统治“天下”的时代。《英雄》的“天下”只是一个重返古典时代的自欺欺人的梦想,是一个哀悼和祭祀,是一个不自量力的历史规训,然而,作为一个蓄谋已久的美学托辞,它是暴力美学合法的家园。
注解:
①《英雄》电影播映的同时,由编剧之一的李冯根据剧本脚本整理而成剧本小说出版。实际上就是电影剧本,剧本小说中的人物台词与电影并无区别,只是电影镜头语言换成了描写性的语言。本文所引人物语言,参照李冯剧本小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2002年。据李冯剧本小说所写,传给残剑的字的主人,叫侯嬴。侯嬴原来是游侠,后来做了隐士,隐居在魏国,为了激励朋友信陵君和朱亥援救赵国,侯嬴慷慨自刎!侯嬴传下了一柄断剑和一篇文章。剑和文章都传到残剑手里。文章的题目叫《天下论》,是侯嬴亲手书写,据说剑法就化在字意里。影片的“天下”概念按其情节设计主要来自侯嬴的《天下论》,其开篇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士为知己者死,担天下之兴亡……”中国古代把士看成是一种特殊的人,侠客也是士,也叫做侠士。剧本小说里说:比剑更高的境界就是侠。所以,残剑若想成为绝世剑客,并完成刺杀秦王的刺客使命,就必须努力悟通侠的涵义,先做一名侠客、侠士。刺杀秦王,本来就被天下人视为侠义之举!侯嬴的故事在《战国策》中有记载,后世不断改编的“窃符救赵”说的就是信陵君与他的故事,但没有关于侯写有《天下论》的记载,这是电影编剧所虚构。
②据史书记载秦始皇焚书坑儒杀害460人,其中大多数是道家方士,儒生只在少数。这其中的冲突起因恐怕相当复杂,史家称是由道家方士诽谤秦始皇引起的。
③有史书称,秦统一六国后,把兵器收缴进国库,铸为大鼎。这似乎是应了刺客们期盼的和平,秦王果然统一天下,并放下屠刀。但事实上,秦王完成霸业也就是完成他对天下的统治,天下归顺,从此和平。但前提是对他的绝对的服从。那些兵器收缴后,人民不准有任何怨言,有任何造反行径格杀勿论。秦统一后的残暴不仁,最终导致农民起义,推翻秦帝国。秦王的天下是他的天下,是一种驯服在帝王(和帝国)脚下的和平。这样的和平掩盖的是帝王对人民的压迫,只不过是把过去四处涌动的暴力集中起来,暴力的特权控制在帝王手中。天下只是帝王行使暴力特权的天下,由此或许可以说客观上带来和平,但电影《英雄》却解释秦王为天下谋和平的强烈的主观意愿,正是在这一点,无名与秦王在大殿上达到一致,这是张艺谋无法缝合的叙事裂痕。
④这里是指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尔(Michael Hardt & Antonio Negri)合著的《帝国》(Empire)一书中表达的“帝国”,2000,publish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中文版,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