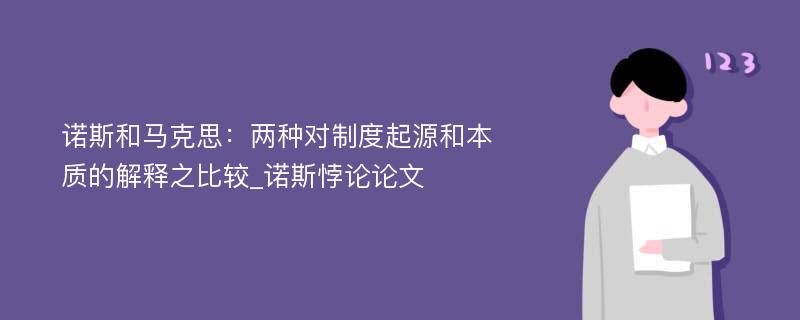
诺斯与马克思:关于制度的起源和本质的两种解释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两种论文,起源论文,诺斯论文,本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被恩格斯称为马克思毕生的两个重大发现之一。因建立了一套与新古典经济学接轨的社会制度变迁理论而得了经济学诺贝尔奖的诺斯教授,则宣称自己超越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对社会制度变迁做出了更令人信服的解释,尽管他曾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框架是“对长期制度变革的最有力的论述”(诺斯,1993)。比较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与诺斯的社会变迁理论,对于澄清一系列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是非,是大有助益的。这种比较涉及社会制度的起源与本质、社会发展或制度变迁的动力、社会发展的道路或制度变迁的“路径”等重要问题,不是一篇文章所能包揽无遗的。本文拟仅就制度的起源和本质这一个问题对马克思和诺斯进行比较。需要事先申明的是,这里要做的比较,不是要把马克思和诺斯这两种理论中的一种理论,当作真理的标准来检验另一种理论,而是要对两种理论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和它们与历史事实的相符性进行验证,并以此判别二者的优劣。
一、对社会制度起源和本质的两种解释
先让我们来看一看诺斯对社会制度所下的定义:“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入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包括“正规约束”(例如规章和法律)和“非正规约束”(例如习惯、行为准则、伦理规范),以及这些约束的“实施特性”(诺斯,1994)。在诺斯看来,制度的主要功能就在于通过内部和外部两种强制力来约束人的行为,防止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以减少交易后果的不确定性,帮助交易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从而减少交易费用。总之,诺斯是以个人之间的市场交易行为为背景,从法律和道德规范这一个层面来理解制度的。
与诺斯不同,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制度最初来自物质生产条件,过了很久以后才上升为法律。在马克思看来,制度不能仅仅归结为表现为社会普遍意志的法律和伦理范畴。在他的理论中,完整的社会制度是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个相互联系的层次组成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个层次之间,既具有原生和派生的关系,又具有互动的关系,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对社会制度进行研究,首先要分析作为整个社会制度经济基础的生产力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然后才能对耸立在这个基础上的道德和法律等上层建筑的性质做出合理的说明。可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规范,诺斯所说的制度,只是作为全部社会制度一个层次的上层建筑中的法定权利、政治秩序和道德准则。
马克思和诺斯的制度概念的不同,与二者对制度起源和形成的不同解释有关。
诺斯的解释:
像所有信奉个人主义的西方经济学者一样,诺斯是从亘古不变的抽象人性出发来解释社会制度的起源的。这种人性,就是被威廉姆森(O.E. Williamson , 1999 )称为新制度主义的“关键性好主意”(keygood ideas)之一的关于人类行为特征的假设,即人的自利性和认知能力的有限性(the condition of cognition and self-interestedness)。在诺斯之类新制度主义者看来,由于人总是要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同时由于认知能力有限又总是处在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的环境中,于是在交易中就会发生欺诈、偷懒、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使人与人之间发生利益冲突和磨擦,增加交易费用和交易后果的不确定性,最终损害自己的福利,而制度就是人们为防止机会主义而缔结的契约。这是制度起源的一种契约论解说。一贯倡导新古典主义的诺斯,希望通过这种解释,将一向作为新古典的经济分析的外在前提的制度,“内生化”到以自利个人的成本—收益为基本范式的新古典分析框架中来。
一些新制度主义者,如安德鲁·斯考特(Adrew Schotter,1981,1983)和罗伯特·埃科赛罗德(Robert Axelrod,1986),还用博弈论来图解这种解说。他们假定人类社会一开始处于一种机会主义盛行、利益相互冲突的“霍布斯状态”或“自然状态”,但这种状态不会持久,因为缔约即建立制度可以产生一种“合作收益”或“合作剩余”,即大于不缔约时各方总收益的增量;这个增量开始是潜在的,人们经过多次博弈会发现这个增量,从而缔结合约,形成私有产权制度,跳出“霍布斯状态”。许多新制度主义者不仅用这种过程来说明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初起源,而且依据它来解释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制度的一切后续的发展。
如果暂时撇开“自然状态”的假设是否与历史事实相符的问题不论,这样一种图解要想成立还需要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利益冲突的各个孤立的个人具备离开他人独立生存的能力,换句话说,自然状态下的个人凭借自身的能力,至少能够获得维持自身生存所必须的收益;第二,“做交易”确实如亚当·斯密所说,是人类天生的倾向,自有人类以后就有市场交易。缺少这两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前述博弈过程都无从发生。原始的初民社会是否满足这两个条件,要由历史学和考古学的证据来检验。此外,市场交易本身就是一种制度现象,对它的起源也必须做出说明。而自利这一关于人性的基本假设,显然顶多是交易制度发生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将需要说明的东西当作前提,这不能不说是诺斯等新制度主义者逻辑上的一个大疏漏。
熊彼特说过,“任何社会制度的运行都不能只以(法律上的)平等签约双方的自由契约(其中每个人被假定只受他自身短期功利目标的引导)为基础。”(熊彼特,1990)如果按照熊彼特的这个思路进一步深究下去,私人产权或某种排他的专一所有权的存在,又是自愿交易制度成立的前提。而新制度主义者往往用自愿“做交易”性质的博弈来说明私有产权,其逻辑上的循环论证是显而易见的。卢瑟福在评论对诺斯理论的博弈论解释时指出,“为了解释诺斯所讨论的那种合作性互动,仍然有必要假定存在一组事前给定的共同信念和行为规范。博弈论不可能将所有这些内容成功地归结为只受自利驱使的个人互动的结果。合同论文献里也有类似的问题。这里,某些基本的立宪规则应当来自(非制度化)的理性个人的自愿安排。问题是,经考察发现,这些个人原来已经接受了文明言行的最基本规范。”(卢瑟福,1999)以“囚犯两难”博弈为例:合作解的出现离不开交易的多次重复,这就要求博弈双方不能退出交易或使对方遭受灾难性损失而不遭报复;然而,正如阿费尔德所说,这意味着至少已经假定了事先存在“非背叛的互动的总体结构”,即在交易之前已经存在能够使之重复下去的、交易双方都不能不置身于其中的某种制度安排;否则,就没有理由假定博弈的策略空间中不包括可以导致交易破裂或中止的退出、报复以及消灭对方的行为(Alexander Field,1984)。
诺斯意识到了这种逻辑上的问题。于是他又用“国家理论”来“补充”产权理论,说产权是由作为具有强制力或暴力的政治组织的国家规定的。而这样一来,产权这一重要的经济制度现象的产生,似乎又成了与经济活动即个体间的市场交易无关的东西了。而且,诺斯也未能提供一种关于国家这样一种极其重要的制度现象的起源的令人信服的解说。他认为,国家起源于某种“暴力潜力”在公民中的分配。若“暴力潜力”的分配是平等的,则国家起源于契约,反之则起源于掠夺。但是,“暴力潜力”的不同分配格局是如何产生的,他并无明确的说明。而在其“新古典国家”理论中,作为游戏规则制定者和维护者的国家,自己也成了效用最大化目标(追求租税的最大化)支配下的游戏者——它既是裁判,又是运动员(诺斯,1993)。此即所谓“诺斯悖论”。事实上,国家理论的提出,意味着诺斯将制度的形成内生化于新古典分析框架之内的企图已经失败。
除此之外,诺斯的制度形成,还需要有“意识形态理论”或“文化理论”的补充。也就是说,信仰、道德、习惯等对于克服“搭便车”所必须的“非正式制度”,也不能由前面那个基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博弈过程来说明。事实上,某种关于社会正义的观念,如果一旦形成,就具有不可侵犯和不容交换的心理特性,它绝对排斥功利主义,因而正义等价值标准是难以纳入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算计过程的。从私有财产制度形成以来,似乎还找不出小偷通过诺斯等人所说的那种博弈,改变了“盗窃不道德”这一社会正义观念的事例。但按照前述博弈论的逻辑,这种事情不但有可能而且必然会发生。但这是违背常识的,于是就只好请出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意识形态来保驾护航。显然,意识形态是诺斯对历史的新古典解释的又一个外生变量,而这又一次说明了他的那种内生化尝试的失败。事实上,如果不引入意识形态、文化、认知模式以至于基于两性生理需要的人口自然增长,诺斯那个基于不变的人类理性的契约论模型是任何社会变迁都解释不了的。道理很简单:既然自利的人性是亘古不变的,那么基于这种人性的社会制度也应该是亘古不变的,但为什么又会发生作为诺斯研究对象的制度变迁,而这种变迁所造成的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制度又有如此显而易见的巨大差异?
诺斯的博弈过程还包含着更为深刻逻辑上的悖论。他的制度分析所遵循的基本方法论原则是个人主义。因此,制度的形成,只能归结为个人的选择和行动,而社会既不选择也不行动。因此,作为制度形成过程的博弈,是由个人的成本—收益计算推动的。而作为这种计算根据的个人效用函数,又难以加总为社会效用函数。所以,社会的成本和收益也就是不存在或不真实的。但是,制度却是社会的,是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其成本和收益都只能是社会的。事实上,心理学对集体行动中的个体无理性的研究,以及福利经济学的加总问题和阿罗不可能定理,都已经证明要从自利人的个体选择引出社会选择,在逻辑推理中会碰到无法克服的困难。哈耶克根据自己的进化论得出的结论是,群体中的整个行为秩序“大于个人行为中可以观察到的规律性的总和,前者不可能全部归结为后者”;“作为整体的秩序”,“不可能完全从部分的相互作用中得到说明”(F.A.Hayek,1976)。 克拉夫茨在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写的“经济史”词条中,谈到诺斯的新经济史时也指出,作为“公共产品”的制度无法通过个人的功利主义计算得到充分的供给,而诺斯和他的合作者托马斯的理论恰恰缺少制度这种“公共产品”的供给函数,因而是不成功的。
总之,要想从诺斯的有关论述中理出一个前后一致的逻辑发展线索,相当困难。克拉夫茨在上引词条中不无讽刺意味地说,诺斯和他的合作者托马斯试图将历史塞进新古典的经济理论框架,“如果这不是一个反面教训,至少也是我们已经吸取的一个重要教训。”(克拉夫茨,1987)
马克思的解释:
马克思是反对用鲁宾孙式的孤立个人之间的自由契约来解释社会制度的起源的。他认为,人的独立性以及通过契约建立的独立主体之间的自由交易,是历史的结果而不是历史的起点。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来说,才表现为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最发达的社会关系的时代。而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形态中,人与人的关系是以血缘、宗法和人身依附为基础,个人并没有“市民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中那种所谓契约自由。而在马克思看来,即使是市场交易形式的契约自由成为经济生活中普遍现象的资本主义社会,其最基本的制度特征,也无法仅仅用自由契约来解释。因为,对于靠工资生活的劳动者来说,虽然有选择受雇于哪一个老板的自由,但并无不受雇于某个老板的自由。这后一方面的社会强制,与自由契约的“天赋人权乐园”无关。
马克思认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杜撰。按照他的理论,在人类社会产生之初,由于个人抗御和利用自然、获取生存资料的能力十分低下,为维持生存、延续种群,原始先民不能不在血缘联系基础上,以氏族、部落和公社的形式结合为共同体。在这种社会形态中,共同体的存在是个人生存的前提,生产活动采取集体劳动的方式,因而个体与群体的利益是同一的,资源分配必然采取公共所有的制度形式。只是随着生产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生产力水平提高,才有了超过生存需要的剩余产品,逐渐形成了个人脱离共同体而独立的条件,发生了社会分工以及市场交易,导致共同体内部发生利益分化,产生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形成在社会分工体系中处于不同地位、对经济资源具有不同的支配和占有权力的个人、集团以至阶级之间的利益差别和冲突。在社会分工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的集团或阶级,为了在与其他集团和阶级的矛盾和冲突中,维护有利于自身的既定利益分配格局,依靠自己在资源占有上的优势,建立起了被称为政府或国家的强力组织和法律制度,同时通过各种形式的资源投入巩固和发展相应的意识形态。
总之,在解释制度的起源时,马克思从人类与自然界的矛盾出发,从生产力的发展导出了第一个层次的制度的起源,即社会生产关系的形成过程;进而又从社会生产关系中不同集团和阶级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出发,从社会生产关系中导出第二个层次的制度的起源,即包括政治、法律、道德规范等等在内的上层建筑。
对马克思的上述理论,诺斯等新自由主义者的一个常见的批评,是说它缺少个体行为的基础。比如,诺斯就多次批评马克思未能将搭便车之类机会主义行为方式纳入制度分析。其实,对于为什么不从个体行为出发来解释制度的形成和演进,马克思是有过解释的。他说过,“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社会发展是由无数个体的选择汇合而成的。但是,个人的选择并不完全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因为,现实中的个人是在一定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而个人所面对的既存的界限、前提和条件就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生产力状况。人不能自由地选择生产力,因而也就不能自由地选择由既存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以及相应的法律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因此,不是先有了某种由先验的人性决定的个人偏好,然后人们在各自偏好的驱使下自由地缔结社会契约,从而形成社会制度,相反,是与既存的生产力相适应的制度——其中最根本的是现存的生产资料占有关系,规定着个人的经济权利、价值取向和选择空间。举例来说,美国内战前南方的奴隶市场上的某个庄园主可以根据个人的偏好,对高矮胖瘦不同的奴隶进行充分自由的选择,并自由地与奴隶贩子缔结买卖契约;但这种自由的交易,以奴隶制度在南方的存在为前提,不可能发生在禁止奴隶交易的北方各州。同时,那些被当作货物交易的黑奴们是谈不上有什么自由缔约的权利的。
至于个人的“搭便车”行为这个被诺斯视为阻碍制度变迁中集体行动的难题,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对于新制度代替旧制度的大变革,不过是无足轻重的鸡毛蒜皮。因为,属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社会集团和阶级的多数个人,在社会实践中最终会认识到,只有改变自己所从属的那个社会集团或阶级在既存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由旧制度注定的个人的不幸命运;这时,集团或阶级的整体行动就会不可阻挡地发生,而且这种集体行动往往带有英雄主义史诗的风采,尽管也难免有一些畏首畏尾的胆小鬼躲在一旁等着分一杯胜利之羹。而代表先进生产力阶级在摧毁旧制度后,其政治上的代表就会凭借自己所掌握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权力,巩固和健全与新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法律准则和社会规范。而这种新制度的确立过程,往往伴随血腥的暴力,而决不是靠谈判桌上缔结的反机会主义的自愿契约来解决问题的。就私有产权制度的确立而言,汉莫拉比法典这一类古代立法,为了使私人产权不可侵犯的观念成为普遍的社会行为准则,消除随意取用他人物品(这是诺斯心目中的“搭便车”行为)等原始公社公有制遗风而设立的令今人发指的残酷惩罚条款,为此提供了有文字记录的确凿历史证据。
人们可以不同意上述马克思社会制度的起源或形成的解释,也可以批评马克思叙述其理论的方式带有所谓“黑格尔遗风”,但就逻辑的严整性而言,马克思的解释是诺斯所不能望其项背的。马克思将社会制度的演进置于生产力进步这个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首要的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层次分明地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社会制度演进过程,纳入一个有机统一的理论体系。相形之下,诺斯的理论则明显地具有多元论的倾向,令人失望地支离破碎,在逻辑上缺少起码的内在一致性。当然,形式逻辑的严谨并不能保证一个理论的正确,更重要的是要看这个理论是否与历史事实相符。下面,让我们着重从有关社会制度形成的基本假设和社会制度的本质两个方面,用历史学和考古学提供的事实,对马克思和诺斯对制度起源和形成的不同解释作一检验。
二、理论与历史
从前面对诺斯和马克思理论的概述可以看出,在人类社会制度如何形成这个问题上,诺斯与马克思的分歧集中在两点上。一是制度形成的某本假设,即理论展开的出发点方面的分歧:诺斯的出发点是自利和机会主义等先验的人类行为特征;而马克思的出发点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首要的实践活动即发展生产力。二是对制度的本质的认识上分歧:诺斯等新制度主义者认为制度是通过孤立个人之间的平等交易形成的,其本质是自由契约;而马克思则从生产这一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出发,将一定制度的形成,归结为一定生产关系,以及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并维护这种生产关系的社会机构和规则确立的过程,认为制度的本质就是在社会分工协作体系中不同集团、阶层和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
首先,关于社会制度的形成的基本假设。就这个问题,我们列举历史学、人类学和考古学提供的如下有关的事实。
第一,至少目前还没有考古证据证实原始人采取非群居的独立生活方式。对我国大量史前人类遗址的考察,无可辩驳地说明,原始先民采取的是群居方式,人类一开始就是一种“社会动物”。原始人的居住方式、生产方式、食物摄取内容等,都有进化论上的根据和必然的生理基础。人由猿进化而来,原始人自然继承了类人猿的群居生活方式。人属于中小型动物,要抗御大型动物尤其是猛兽的侵害,以及通过狩猎获取足够的肉食,都必须有群体的合作(奇波拉,1993)。将初民们描写为独自谋生的孤立个人,处于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显然与考古证据不符。
第二,许多比较人类学家和生物学家,通过考察非洲、美洲和澳洲等地的原始部落和高级动物群体发现,越是在个体独立生存能力低下的群体中,群体行为的本质越是利他主义而不是利己主义。在生存需要的压迫下,个体本能地采取利他主义的行为方式而很少有机会主义行为。而随着群体中个体独立生存能力的提高,各种争斗和利益矛盾发生的频率也提高(普罗格、巴茨,1988;谢苗诺夫,1984)。由此可以推断,利己主义和机会主义是生产率提高,剩余产品出现,个体独立生存能力提高的产物,并不是亘古不变的人类行为特征。将其当作解释制度起源的基本假设,实在不是什么“关键性好主意”,而是个“关键性馊主意”。
第三,古生物学家对原始人骨骼化学成分的分析表明,原始人群经常面临饥馑,必要的营养成分的摄取严重不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4中译本;C.Clark and M.Hasnell,1967)。 这说明最初的人类社会生产水平十分低下,包括所谓“合作剩余”在内的整个群体的总收益仅能使每个群体成员维持生存。离开群体,个人只有死路一条,因而所谓“霍布斯状态”肯定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的机会主义也根本就不具备发生的物质基础。须知,对于原始先民来说,基于利己心的机会主义是非理性的,因为它会导致群体的瓦解,而这又意味着个人自身的毁灭。
第四,大量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资料表明,在人类社会制度的第一个形态即原始公社制度条件下,共同体内部不同成员间并不存在市场交易关系。只是随着社会分工的发达,剩余产品的出现,才发生了部落之间交换。至于个人之间的交易,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行为规范和权利观念(交易双方基于各自的自由意志的平等权利、交易的等价性等等),那是在私有财产制度产生,共同体濒于解体的时期才发生和流行起来的。
第五,卷帙浩繁的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成果提供了对马克思的理论极为有利的证据。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仅引证两个并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类学家的论述。
美国学者摩尔根依据在美洲印第安人中的多年调查以及大量历史文献,研究了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财产继承法的演化,即由氏族成员共同继承到子女继承的变化。他得出的关于财产制度发展的结论是:“关于财产的最早观念,是与生活资料的获得密切相关的,而生活资料的获得则是基本的需要。物品的享有,将自然地随着在连续的各文化时代中与生活方法所依赖的那些技术的增加而增加。因之,财产的发展,将与文明及发现的进步同时并进。每一文化时期,都较其前一时期显示着更显著的进步,不只在发明的数量上是如此,就是在由发明数量的增加上所产生的财产的种类与数量的增加上,亦是如此。随着财产的增加,关于财产享有及继承的法律,亦必因之而发展。这些财产所有权及其继承的法律所依据的风俗,是由社会组织的状况及进步所决定和制限的。”(摩尔根,1972)显然,摩尔根的结论与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状况决定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的理论是一致的,他对有关事实的整理和归纳,是对马克思的经济制度起源和形成理论的一次有力的印证。
再让我们看一看俄国学者M·科瓦列夫斯基的论述, “假如我们想知道那逼迫我们的原始祖先及现代未开化人保持多少明显地表现着的共产主义的原因时,那么我们便特别应该知道原始的生产方式。因为财富的分配方式应该为财富的生产方式所决定。……在澳洲,猎取袋鼠就是由几十个甚或几百个土人的武装队伍来进行的。在北方的国度中,在猎取鹿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无疑的,人不能孤独地维持自己的生存;他需要援助和帮助,而联合十倍地加强他的力量……这样,我们就看到了在社会开始时的社会生产及作为它的必然和天然结果的社会消费。人种学上证明这点的事实异常丰富。”他还指出,私有财产观念的产生并非来自“个人的自我意识”(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就是“理性”),而是来自生产方式:“原始人的达到关于个人占有用作武器之尖石或用以遮身之兽皮的思想……是因为在物件的生产上应用了个人的力量”;“个人劳动的使用,因之也便逻辑地产生个人的占有。”集体狩猎中兽肉归集体分享而兽皮归最后射倒猎物或箭射得离猎物心脏最近的人之类的原始惯例,即源于此。“所有这些,为印度的法律,南部斯拉夫人、顿河哥萨克人或古代爱尔兰人的习惯法所同等地证实。”另一个例子是,在处于原始阶段的爱斯基摩人社会,作为集体劳动工具的大捕鲸船是公有财产,而作个人或家庭日常生活之用的小船是私人财产,可见“生产组织继续影响占有方式到何种程度。”农业出现之后,氏族(“血缘联合”)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怎样解释它的起源呢?科瓦列夫斯基说:“我们以为,原因就在那个在某个时候引起了占有大部分动产的社会生产中。”(M.Kovalevsky,1890)
类似的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证据俯拾即是。这些证据在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假设提供坚实的支持的同时,显然否定了诺斯的新古典假设。
其次,关于社会制度的本质。诺斯等新制度主义者将独立个人之间的自由契约看作是一切社会制度共同的本质规定,因而在任何制度下,社会分层、阶级剥削、阶级压迫、阶级冲突等与人类文明史相伴随的重要制度现象是没有理由存在的。但是历史证明,这种在自由契约论者看来不应发生的事情就发生了。
第一,考古学家对分布在中国、中美洲等地区的200 多座古代墓葬的研究发现,这些墓葬中存在墓主人和殉葬者的明显社会分层。墓主人的身高平均比殉葬者高出7至8公分。而且,根据对二者骨骼中的含锶量的化验结果,墓主人骨骼的含锶量大大低于殉葬者,这表明前者的肉食量大大高于后者。而这又意味着食物分配上悬殊的社会分层。对玛雅文明遗址和中东一些古代遗址的考察还发现,在生产工具特别是制备食物的工具的占有上,社会分层现象也是明显的。
第二,考古学家在一些古代建筑遗址的考古中发现,这些建筑不仅是防止外来侵犯的设施,具有防止内部暴乱的功能。遗址中社会上层人物的住宅一般建造在保护圈中,而且它住宅本身也有防御设施,其功能是对付内部的暴乱。据考古学家分析,在圣罗伦索的奥尔梅古遗址中存留的大量被蓄意破坏的石碑等古物表明,该文明毁灭的原因就是社会内部不同集团的冲突(哈斯,1988)。
上述历史事实显然是无法纳入新制度主义那个基于自由契约的“合作世界”的。对此,某些新制度主义者也有所感觉,承认他们用来说明制度形成的合作性博弈,无法确定“合作剩余”的分配解。例如,罗伯特·考特和托马斯·优伦说:“对策行为引起博弈论中许多非常复杂的问题。经济学通常假定人们理性行事并寻求他们之间的均衡。然而,经济学尚未成功地找到一个建立在理性之上的谈判问题的解。理性自身并不能决定如何分配合作剩余。”(考特、尤伦,1994)事实上,作为个人间博弈结果的“合作剩余”的分配方式,取决于双方的“谈判力量”,而“谈判力量”并不是来自个人的利己理性。个人的“谈判力量”其实来自于他所置身于其中的特定社会集团或社会阶层对经济资源的支配权力,来自于个人在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试问,一个自身生死操之于他人之手的奴隶,除了接受牛马般的生存条件,同时将生产出来的所有剩余奉献给主人,难道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将“谈判力量”对比悬殊的不同社会阶层、集团和阶级的关系描述成自由、平等的市场交易,将社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归结为一部精于算计的自利者的生意经(对交易成本的算计),可以说是诺斯之类新经济史家以至整个新制度主义的“最深刻的浅薄”之处。而这种浅薄又使得新制度主义的某些弄潮儿,已堕落到肆无忌惮地伪造历史的地步。
在诺斯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就可以看到将连农民的“死魂灵”都可以买卖的农奴制,被说成是农奴用劳役换取封建庄园主保护的自愿契约(诺斯,1993)。一个叫R·S·西伯里的新经济史家,在研究美国南方的奴隶制度时,竟然认为奴隶与奴隶主之间存在着“提供劳务与授予一方关心与保护”的“隐契约”,并且在这种契约形成过程中,奴隶有选择的自由,即有选择生与死的自由。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奴隶逃跑是一种背约行为,即违背了自己的“隐契约”(转引自:霍奇逊,1993)。如此“高论”,足以骇人听闻。许多西方学者也不同意这种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的理论。阿卡迪斯·卡亨在详细研究农奴制后指出,农奴受领主的束缚,其行为和活动受其地位的严格制约,不存在自愿的协议;用现代契约观分析封建时代的农奴—领主关系,是强加给人们一种使人误入歧途的现代观念(Acadius Kahan,1973)。
克拉夫茨曾批评诺斯缺少解释冲突的理论(克拉夫茨,1989)。的确,我们不知道诺斯将如何回答初学历史的中小学生都有可能提出的这样一些问题:中国的陈胜、吴广为什么要揭竿而起?古罗马的斯巴达克为什么要造罗马共和国的反?法国的“第三等级”为什么要发动民众攻打巴士底狱并把国王和贵族送上断头台?既然奴隶制度是自由契约的产物,美国人进行南北战争岂不是发疯?……这类举不胜举的历史事实,都是社会制度通过自由契约的途径形成的理论所无法解释的:陈胜、斯巴达克、罗伯斯比尔、林肯们竟然没有遵循诺斯等人的教导,在新古典经济理性的引导下,打起算盘来计算交易费用,与秦二世、克拉苏、路易十六、罗伯特·李们轻松有趣地博弈一番,达成个皆大欢喜的自由契约,而非要拼个你死我活。由其个人主义和自由契约的基本假设所决定,诺斯的理论注定解释不了历史发展长河中的这类巨大社会冲突,以及由这种冲突所导致的社会基本宪法制度的革命。当然,这不是说诺斯的理论解释不了任何制度的形成和起源。在以市场交易已成为最普遍的经济关系形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框架内,对于一些表层的制度现象(例如诺斯早期研究过的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制度原因),诺斯的理论还是可以提供某种能够自圆其说的解释的。但是,它肯定无法解释社会基本制度的根本变革。硬将这种理论的适用范围推广到全部人类社会制度的变迁史,那是要闹笑话的。这大概就是克拉夫茨将诺斯归入“没有认识到过去与现在不同的经济学家”之列的原因。
根据马克思对制度形成过程的说明,上述冲突却可以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作为全部社会制度基础的生产关系的本质,就是在社会分工体系中处于不同地位、对经济资源具有不同支配权力的各种社会集团、阶层、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人类文明史上连绵不绝的巨大社会冲突,正是一定社会制度的内在利益矛盾激化的结果。而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冲破旧制度桎梏的条件下,这种社会冲突往往成为新制度取代旧制度的契机。这就已经涉及到社会发展或制度变迁的动力问题了。在这个问题上诺斯与马克思的观点也是大相径庭的。但这是需要用另一篇文章来探讨的问题。
标签:诺斯悖论论文; 新制度主义理论论文; 诺斯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合作博弈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法律论文; 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