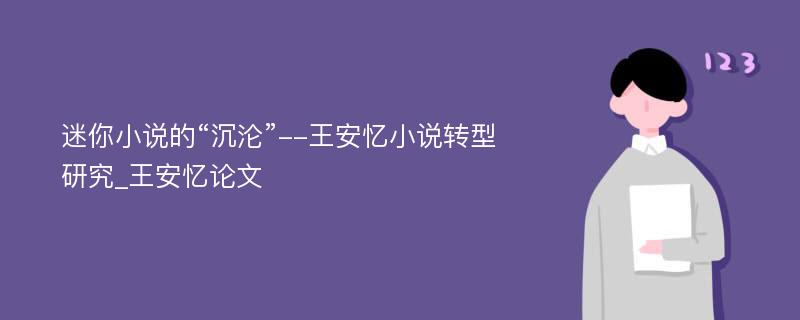
“米尼”们的“沉沦”——王安忆小说转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安忆论文,小说论文,米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安忆在近年来与张新颖回顾整体创作的对谈中谈到《米尼》①在她创作中的重要地位:“事实上《米尼》对我的写作来讲,蛮重要的,因为是我第一次写一个十万字规模的东西……我觉得十万字的东西挺适合我的表达。”“这个长篇……开始摆脱我惯常的长篇结构上编年的方法,不是依赖时间的自然长度来填充篇幅,它是写事情的。”“时间可以允许有不那么严格的情形出现,故事却要求逻辑的严谨。《米尼》对我作用蛮大的。”②时至今日,我们重新来检阅王安忆的创作历程和创作评论,《米尼》这部在八、九十年代之交书写普通市民生活的作品,明显不同于王安忆80年代的“思潮化”创作,而又与90年代的《文革轶事》、《长恨歌》、《妹头》、《富萍》等作品似乎有着一脉相承的隐蔽联系,它的出现正如王安忆所说的具有叙述结构、叙述方式革新上的意义。然而《米尼》的出现是否会与王安忆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创作转型有着深层的联系?《米尼》是否是标志王安忆创作转型的一部重要作品?对这些问题的清理,或许会使我们对王安忆的创作历程获得一些新的认识。
一 王安忆的“身份归属”
“身份归属”在作家的创作中一直处于重要的地位,甚至决定了其创作的主题与倾向。佛克马指出:“人类不能离开身份而生活。”“个人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社会群体或是一个人归属或希望归属的那个群体的成规所构成的。”“缺乏自我将会使一个人不能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用流行的说法就是,他或她将只会是风中的一根草,风把它吹向何方它也就飘向何方。”③因此,对于一个作家而言,对自身“身份”所归属的“社会群体”的认同显得尤为重要,它直接影响到作家的创作方向与创作成果。王安忆在当代作家的创作群体当中,身份特征却一直较为特殊。
王安忆既有知青的经历,又是出生后移居上海,是上海市民中的一分子,同时还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庭的后代,是社会主义的接班人。王安忆的多重身份特征,给其80年代初的创作带来了很多尴尬。王安忆虽然有过知青上山下乡的经历,但在插队的两年半中,一直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与知青群体没有过多的交在④。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流逝》等虽带有“伤痕文学”、“知青文学”的印记,也终究是以其不熟悉知青群体的生活,没有更深刻的“文革”伤痕体验,而跟“伤痕文学”、“知青文学”打了个“擦边球”,仅仅是站在“上海”“眺望”一下“伤痕”、“知青”的影子。王安忆又很难说得上是上海本土的作家,其“外来户”的心理影响一直到她成为知名作家也难以消除。在王安忆的上海“文化寻根”时期,她很难找到与上海文化相关联的文化符号,相反,在《我的来历》中,王安忆倒是把自己母系、父系的来历追溯到江浙一带和更远的域外南洋。而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后代的王安忆,在80年代“去政治化”的文艺创作环境中,显然也不愿意使用这一政治化身份进行文学创作。
王安忆的这种多重身份与难以归属的难题,间接造成了她创作主体的游移与群体归属的模糊,因此面对80年代热闹的文坛,王安忆的身份也一直在各种文学思潮背后的作家群体身份中漂移。批评界更多地把王安忆归结为“思潮型”作家,而王安忆在80年代纷至沓来的文学思潮中所能依仗的创作资源其实一直只有她自身的“成长史”与青春期在文工团六年的生活经历。
“身份”的“归属”问题深刻地影响到作家的创作资源与创作走向,同样也会影响到作家的创作态度与创作立场。王安忆“飘忽不定”的“身份归属”使她显得有点无所适从。作为知青返城潮中一员的王安忆,在其初登文坛时,使她首先遭遇到作为“外来人”闯入上海的那种“在而不属于”的尴尬。虽然王安忆从小在上海的“市民堆”中长大,在上海这个城市里上学,有自己的一帮要好的同学,学会了说上海话,懂得上海人的诸多人情世故等等,甚至在《庸常之辈》、《流逝》等作品的人物对话中,刻意地使用上海地道的方言俚语,但在这些自我的“上海化”背后,王安忆又常常不自觉地流露出一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眼光,挑剔地看着上海弄堂中的各种小市民的庸俗、自私、冷漠和斤斤计较,如《鸠雀一战》、《好姆妈、谢伯伯、妮妮和小妹阿姨》、《逐鹿中街》等作品当中,王安忆对这些上海普通市民居高临下的审视态度,传达的更多是对上海市民文化与生存价值观的不信任和鄙夷。
在1988年一篇谈论上海文化与北京文化的文章当中,王安忆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上海人及上海文化的“粗鄙”:“很多人,尤其是上海人自己以为,上海是一个优雅的城市:法租界的洋房和林荫道,外滩沿江的古典风格大楼,还远俱乐部的爵士乐,咖啡馆着洋装说洋文的侍者……这些欧洲的风味的确是给上海增添了格调。然而,暂且不说这仅是表面的装饰,就是这些货真价实的欧美人,在我们源远流长的北京人眼里,则已是够粗鄙的了。”“欧美的文化锣声落在粗鄙的江湖之中,得到一种奇妙的结合。”“切莫以为上海曾经聚集过一批优秀的文人,而就以为上海有了文化。”“一个暴发户的故事远没有一个怀旧的故事富有人性与格调。”⑤王安忆面对上海这些“粗鄙”的文化形态,本能地选择了北京的文化而抛弃上海的文化:“我们的文化人,包括作家、读者和批评家,其实全是为一种文化,也就是士大夫的儒学的文化所养育而产生,我们本能地选择了北京的、正统的、我们所习惯的、已拥有了批评标准的文化,而抵触着上海的那一种粗俗的、新兴阶级的、没有历史感的、没有文化的文化。”“解放以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革以及公共道德的强调,使得这两个城市的文化又出现了更加复杂的情况。上海人的小康心理更削减了人文艺术的想像力与气质,而天下为公的理想,且具有伟大的道德感与使命感,也富有浪漫的激情。这种情况使我们更加困惑,却也更坚定了立场,而使上海更加抛荒了。”⑥从上述言论中,我们不难看出在一些更为正式的场合上,王安忆本能地选择了“无产阶级接班人”这样的一种身份特征对上海残存资产阶级“市民文化”的排斥,因而我们也不难理解,在1983年至1988年间大多数涉及到上海市民文化的作品中,王安忆为什么会一以贯之地采用嘲讽、挖苦等口吻去描画上海市民的众生世相。
然而,有意思的是,在《“上海味”和“北京味”》发表一年后的《好婆与李同志》中,我们看到了王安忆对上海普通市民及其市民文化的另一种态度。在《好婆与李同志》中,“好婆”与“李同志”分别代表了上海的“市民文化”与外来的(或者说是“北京的”)“革命文化”两种文化形态。“好婆”作为“繁华看尽”的上海底层市民一直在捍卫着上海的“市民文化”,在生活细节上极尽资产阶级生活的“优雅”形态;“李同志”作为革命的胜利者在1949年后以“城市改造者”的身份进入了上海,“爱穿一身灰色的双排扣的列宁装”,即便是“穿了西装,样样都好,只可惜脚上那双玻璃丝袜大概是穿得匆忙了,后脚跟的缝没有对齐,歪到一边去了,倒还不如穿长裤整齐体面了”⑦。“好婆”与“李同志”这两种文化形态的差异在现实中既是相互亲近,又显得格格不入。与已往勾勒上海小市民的作品不同的是,王安忆在《好婆与李同志》这篇作品中,第一次没有使用批判式的语调对庸俗、琐碎的“市民气”进行抨击,相反却处处显示出她对“小市民”生活方式的维护:“这个小说想写的不仅是友谊,而且是新市民和旧市民的相互抵触。”“对老市民来说,(上海)是他们苦心经营建立的成果,因而李同志的进入就很有一点占山为王的架势。他们的对抗显然在无数细微的事情上,不断提醒李这个外来者,她并不懂得上海。”⑧
而作为革命胜利者进入上海的“李同志”,最后却又悄然地退出上海,特别是王安忆把“李同志”的退出置于“好婆”这样一个上海小市民的观察视角时,“李同志”的退出就显得有点意味深长了。程光炜在《王安忆与文学史》一文中指出:“1989年,发表在《文汇月刊》第12期的小说《好婆与李同志》是一个大变。”“王安忆的创作为什么突然有了这个一个‘急转弯’?这当然与1990年代后中国社会的变化有关,但更深层次上是否也牵涉到作者自己‘人生观’的某种微妙调整?”⑨在“市民文化”与“革命文化”两种此消彼长的文化对抗中,王安忆通过“李同志”对上海“市民文化”的选择,可谓是隐晦地透露出王安忆人生观的“微妙调整”。在“好婆”眼中,“李同志”的彻底“上海化”可以看出上海市民文化的强大同化作用:“上海将人改变得那么厉害啊!什么样的人到了上海都彻头彻尾地变个样。上海虽说不再是昔日的上海,可是它的威力还在,上海还在。”⑩而李同志面对生活细节上的“上海化”,她的自我解嘲式的辩解更显得耐人寻味:“她有时候会带了一些歉疚地问自己:是不是不应当忘记那些以往的日子?再一想:共产主义就是要使人生活得越来越美好,心里就坦然了。”(11)在这里,市民文化不再是“粗鄙的”、“没有历史感的”、“没有文化”的文化。王安忆把上海的“市民文化”与“革命文化”通过多项生活细节上的并置对比,通过“李同志”生活观的转化,显出上海的“市民文化”对“革命文化”强大的同化效应,也显出上海市民生活中的优雅、精致和处处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王安忆这种市民“生活观”的“微妙调整”,透露出其对市民生活、市民文化认识的重大变化,“李同志”对市民生活“自我解嘲”式的认同,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王安忆对市民生活“自我解嘲”的认同,而在这种“自我解嘲”的认同背后,我们不难看出王安忆对其“市民”身份的“解嘲式”认同。有社会学家指出:“人们在接受一个新的社会身份认同时,往往经过和自身历史文化的复杂互动过程。”(12)王安忆这种“解嘲式”认同的过程,也正是她在80年代末接受新的社会身份前所要经历的“复杂互动过程”。《好婆与李同志》中所透露出王安忆对“市民”身份的“认同”与“归属”,必将极大地影响其后的创作。紧接着《好婆与李同志》之后出现的长篇小说《米尼》,则让我们看到王安忆在“解嘲式”地归属“市民”身份后如何以同情与理解的眼光一次次深刻地影响着市民的生活命运。
《米尼》是王安忆1989年6月采访白茅岭女子监狱后,根据部分采访材料创作而成的“一个走向深渊的故事”,叙述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上海插队女知青米尼回城后如何一步步走向卖淫堕落的故事。在《白茅岭采访》后记中,王安忆这样给我们描述《米尼》诞生的过程:“很长久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个女人(插队女知青)的故事。那长江轮上的邂逅,越来越像是一次从此岸到彼岸的航渡。一个女孩,从这一个世界渡到那一个世界,其间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那一个世界,究竟是怎样的面目,快乐还是不快乐?米尼的到来,就是为了帮助我回答这些问题的。”
值得注意的是,米尼与王安忆知青身份的重合与她早期经历的相似,使得《米尼》这部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王安忆的早期精神自传,也正是这种身份上的重合,让我们看到王安忆终于破除了对上海市民身份的成见,自觉地把自己也归入到米尼的生活历程当中:上海长大-插队下乡-回城。在这一系列的叙述当中,王安忆不着痕迹地重构了她与上海内在的“血缘关系”。王安忆这种“市民”身份的认同与归属,使得她在安排作品主人公的命运时,不自觉地站在“同情与理解”的立场上去构建人物的命运。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面对米尼的一次次走向堕落的越轨行为,王安忆都有理由为其开脱,直到最后米尼已经行走在道德、良知泯灭的边缘,王安忆依然能用米尼的一次人性道德良知的觉醒把她从堕落的深渊拉了回来。王安忆对“米尼”的“怜惜”可谓是对城市女性犯下的各种错误的最大宽容与理解,也正是80年代末王安忆市民生活价值观的转变与“市民”身份归属的发生,才使得《米尼》这部书写灰色人生的小说处处充满了温暖的亮色。
二 城市变革与“米尼”们的“沉沦”
如果说王安忆80年代后期“市民”身份的归属使其获得了一副“同情与理解”的眼光,客观、冷静而充满温情地关注市民生活中的各种悲欢离合,那么对普通市民悲剧命运的进一步探索,则使王安忆有可能获得一个总结社会、历史现状的超然视角。在《采访后记》的末尾,王安忆明确地交代了《米尼》创作的动机和目的:“我想知道米尼为什么那么执着地要走向彼岸,是因为此岸世界排斥她,还是人性深处总是向往彼岸。我还想知道:当一个人决定走向彼岸的时候,他是否有选择的可能,就是说,他有无可能那样而不这样走,这些可能性又是由什么来限定的。人的一生中究竟有多少可能性!”(13)王安忆对“米尼”“沉沦”的各种“可能性”的探讨,构成了全篇的结构框架与故事逻辑演进的推动力,也成为王安忆剖析市民生活与社会变革的切入点。
在米尼回顾她前半生的经历时,她一直把她“沉沦”的原因归结为个人的“宿命”,这一“宿命”便是在一次返程途中意外地遇到阿康:
“阿康,你为什么不从临淮关上车?”
阿康说,“我们要在蚌埠玩一天。”
“蚌埠有什么好玩的!”米尼笑道。
阿康说:“蚌埠是很好玩的。”(14)
米尼与阿康的“对白”在后来的十几年里,“前后加起来足有几十次”。“有时候,米尼觉得阿康不从临淮关上车是一桩幸事;有时候,米尼觉得阿康不从临淮关上车是一桩不幸的事。觉得幸和不幸的时候是一样多。”在米尼的观念中,阿康若是从临淮关上火车,就不会遇到米尼,也就不会引诱米尼走上“堕落”的道路。米尼的这种“宿命观”成了她个人无法把握自我命运的“注脚”,直到入狱后,米尼也无法分辨出遇到阿康是幸运的事还是不幸的事,因为阿康在带给她巨大欢乐的同时也带给了她巨大的痛苦。
米尼遭遇阿康显然不是她最后自甘堕落命运的“注脚”和“宿命”,在王安忆对米尼故事的叙述中,米尼遭遇阿康是故事的起点,却并非是米尼命运的转折点。阿康过去虽然有种种劣迹,却也并非无药可救,阿康与米尼之间奇异而真挚的爱情,甚至使两人过了一段平静而温馨的普通人生活,若非经历大的时代变动,这种充满“温情”的“小日子”还将一直持续下去。王安忆显然不会简单地认同米尼的这种“宿命论”判断,而是从米尼自身精神轨迹的蜕变与复杂的社会、历史环境等因素挖掘出促使米尼走向堕落的各种“可能性”。在王安忆对米尼命运的探索中,王安忆细心地注意到了促使米尼命运转折的三大重要事件:
首先是1977-1978年的“知青大返城”事件。1977年末,米尼与阿康这样有过犯罪前科的插队知青,借助“知青大返城”的风潮从上海周边的小镇回到了熟悉的上海,并且两人都获得了稳定而体面的工作,成为极少数拥有“铁饭碗”的幸运人。然而,米尼与阿康的幸福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却意外地因为阿康“婚外情”的曝光而使两人离异。米尼与阿康的返城、离异,使他们原本趋于稳定、封闭的生活,因时代的发展和所处的环境不同,而获得了极易受到各种外界因素影响的不确定性。
其次是米尼与阿康在1986年的意外重逢。米尼与阿康在离异多年后,又在1986年重逢并重归于好,使米尼又重新燃起了对阿康爱情的期待。米尼虽然还是原来的“米尼”,阿康却非昔日温情脉脉的“阿康”,他早已重操旧业并成为一个熟练的“皮条客”了。米尼与阿康的重逢,使米尼重新进入到阿康的生活轨道中,并不设防地掉入了阿康设置的情欲“陷阱”,米尼自此陷入到“堕落”的边缘。
再次则是米尼与阿康、平头等人合伙南下卖淫。米尼在自甘堕落地报复了阿康以后,自身也便在堕落的轨道上不可逆转地向着更邪恶的深渊滑行。米尼与阿康、平头们合伙到南方卖淫,已经成为他们寻求生活刺激的又一种方式,米尼原本残存心底的一点精神依恋和对无望爱情的期待,也因这一次大胆的举动而彻底被毁灭。米尼从曾经朝气蓬勃的知青、温柔善良的家庭主妇,彻底沦为了隐匿于烟花柳巷中出卖肉体的“卖淫女”。
这三大事件环环相扣,层层推进。没有知青的回城风潮,也就没有米尼与阿康在回城后遭遇婚姻的危机;没有米尼与阿康的离异,就不会有多年后重逢米尼掉入阿康设计的情欲陷阱中;没有米尼自甘堕落的爱情报复,就不会有米尼与阿康、平头们南下合伙卖淫,使得米尼最终走上一条不归路。在这三大事件中,王安忆注意到米尼爱情生活的蜕变无疑是促使她精神堕落的重要因素:回城后家庭的裂变,破镜重圆的可能性与期待,不慎落入情欲的陷阱,因爱成恨的报复,由被动变为主动的卖淫行为等等,米尼正是在这一期待爱情到幻想破灭的轨道上,才滑向了不可自拔的堕落深渊。
然而,王安忆在对米尼精神轨迹探索的同时还注意到一些更为隐蔽的社会因素,如80年代初期僵化社会秩序的打破,使阿康有了“婚外情”的可能,阿康婚外情的曝光又进一步促使阿康回复到以前不劳而获的生活当中。又如1985年后上海城市改革的展开,使阿康、平头们有了重操旧业的条件,而阿康、平头们在经济改革开放年代对金钱与享乐的不断攫取,又使与阿康重逢后的米尼不可避免地被推到他们攫取金钱的风口浪尖上,沦为赚钱的工具。
可以说,正是对这些复杂的社会因素的深入探索,王安忆逐步理清了米尼的堕落与80年代城市变革之间的深层联系。王安忆对米尼堕落各种可能性的探讨,正是建立在“城市改革”的背景和基础上一步步展开的。米尼与阿康的返城,正是城市改革的前奏。1977年是中国的政治、经济领域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年,“四人帮”的垮台,改革开放的倡导,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重新确立等等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措施的实行,都给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也给个人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巨大的机遇。1977年对许多普通百姓而言是“苦尽甘来”日子的开端,然而对米尼与阿康这样有过犯罪前科的人来说,在享受“苦尽甘来”的同时也会暗藏着凶险的祸端。1977年后中国整体的环境从封闭走向开放,个体在挣脱国家意识形态的束缚后,个体的自由也将变得无所依傍,其发展也必然充满着各种不确定性。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王安忆对时代发展的机遇与暗藏的危机把握得相当准确,王安忆冷静地看到了米尼与阿康“平静”生活表面下的“暗流”:
他们这两个小小的懵懂的人物,在飘泊游离了多年之后,终于被纳入正常的社会秩序。这秩序好比是一架庞大的机器,一旦进入其间,便身不由己,在轨道上运行。如要强行脱离,须有非凡的破坏力。这破坏力就是在这机器上造成了创伤,要就是两败俱伤,最不济的则是单单将自己粉身碎骨……他们因为是最没有教育,最无理智,最无觉悟,最无自知之明和自控能力的人,他们的破坏力恰恰正够破坏他们自己,将他们自己破坏殆尽,于是,灭亡的命运便不可避免了。(15)
米尼与阿康离婚多年后的重逢,正是上海的城市改革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1984年经济改革的重心已经由农村经济改革逐步转移到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上来了。1984年4月30日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明确提出在四个经济特区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等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上海也初步制定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题纲》,可以说1986年前后的上海已经稳步向自由、开放的社会迈进了。离婚多年后的米尼与阿康在1986年前后重逢,双方都无法抵御物质的冲击而发生了更大的精神扭曲。1986年的上海街头早已经充斥着音乐茶座、酒店、舞厅等各种新兴的市民消费公共娱乐场所。在这看似“闲笔”的对时代变化的“勾勒”中,王安忆充分注意到米尼内心的“波澜”。米尼的“寒伧”、“苍老”和“拘谨”都显得她与这座迈向现代生活的城市格格不入,而上海暗藏的“繁华”、“魅力”与阿康、平头等人的“洒脱”、“游刃有余”却是相得益彰,这对于常年在固定而沉闷的“工场间”劳作的米尼来说,无异经历了一番精神上的“震荡”。米尼在这繁华的物质之都面前一下子显得束手无策,甚至现出强烈的心理自卑,这也为米尼最后为什么甘心受控于阿康、平头这样的皮条客埋下了伏笔。米尼在挣脱了“社会秩序”的束缚后,却保持了与阿康“藕断丝连”的关系,并最终陷入阿康设置的性欲圈套中,米尼的命运便不可遏止地向阿康的方向滑落了。而此后米尼与阿康、平头们合伙去南方“卖淫”则是在城市改革纵深发展的过程中的一种普遍性行为。在金钱与物质的刺激下,米尼终于自己打碎了所有的道德戒律,成为了彻头彻尾的堕落者。
在米尼走向堕落的各种“可能性”的“关节点”中,王安忆充分注意到促成米尼堕落的各种主客观要素:知青返城风潮,改革开放的时代机遇,城市经济的发展,社会风气的转向,米尼因爱成恨的“纵欲”等等,这些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米尼堕落的“可能性”。在这些要素当中,我们可以看出,王安忆把米尼命运的“拐点”放到了改革开放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当中。米尼走向堕落的各种“可能性”因素,也形成了80年代城市女性游离“社会秩序”后的一种悲剧命运,在米尼“选择”与“被选择”的过程中,始终是米尼背后隐藏的“城市改革”的“要素”在发生作用。
王安忆对“米尼”们不断走向“沉沦”的各种可能性因素的探讨,使她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对自身浑浑噩噩的小市民生活做出符合历史社会发展规律的解释。王安忆把人物命运置身于改革图景中的实践,重新激活了她笔下人物的精神世界,从而也为王安忆开拓更大的写作空间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和途径。
三 “世俗生活”的重新发现
市民的“世俗生活”一直是王安忆创作的题材和背景,在80年代初、中期的《流逝》、《话说老秉》等作品中可以看出王安忆对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细致关注。《流逝》开篇描写的场景是作为资产阶级少奶奶的欧阳端丽一大早在菜市场排队买肉的情景,而《流逝》中也存在着用大量篇幅描写上海的资产阶级家庭陷入困顿生活环境的细碎场景。这些扎实、细致的世俗生活场面铺叙显示了王安忆对上海市民生活环境的熟悉,也显示了王安忆最初的创作兴奋点。上海小市民的生活故事在现当代文学史上众多作家的笔下都有所表现,三四十年代的张爱玲、苏青等海派作家更是书写市民生活故事的个中高手。而在80年代,书写上海市民生活的作品却不多见。王安忆在其后的《鸠雀一战》、《好姆妈、谢伯伯、妮妮和小妹阿姨》、《逐鹿中街》等作品中,对上海市民生活中悲欢离合故事的持续关注,把上海市民生活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冲突很好地结合了起来。
王安忆笔下的市民生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无产阶级接管上海后的“新市民”生活,另一类则是三四十年代“老上海”影响下的“旧市民”生活,也可以说是带有“老上海”遗风的旧市民生活。书写这两种生活方式的冲突是王安忆常见的主题,如《流逝》中无产阶级生活方式与恢复后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冲突,《逐鹿中街》中新老生活观念的冲突等等。然而不能不看到的是,在80年代中前期的作品中,王安忆却是一直以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眼光去观察这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在《流逝》、《鸠雀一战》等作品中,王安忆不自觉地运用夸张、漫画化的方式去勾勒受打压的资产阶级儿女的孱弱、无能,“老上海”的生活方式就是吃喝玩乐和沾满金钱腥味的生活,而“新市民”的生活显得健康、质朴而富于活力。王安忆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并置对比理解方式多少会使她与所叙述的对象产生一些隔膜。而80年代末的《好婆与李同志》中透露出王安忆市民生活观的“微妙调整”,又让我们看到王安忆对上海市民生活的探索将会呈现出一种新的特质。
客观地说,在创作《米尼》之前,王安忆很少会用大量篇幅细致地、不厌其烦地叙述带有“老上海”遗风的本土市民生活史,并把它作为正面的叙述对象。在《好婆与李同志》中初步显示出王安忆对“老上海”市民生活方式的关注和肯定。“上海将人改变得那么厉害啊!什么样的人到了上海都彻头彻尾地变个样。上海虽说不再是昔日的上海,可是它的威力还在,上海还在。”(16)“李同志”被“老上海”生活观念同化,就很能说明“老上海”生活方式在本土市民生活观念当中根深蒂固的地位,而“好婆”对“老上海”的发现,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王安忆对“老上海”的重新发现。“老上海”不再是庸俗的、充满金钱味的生活的代表,而摇身一变成为“好婆”意义上的“精致”、“优雅”和“富有人情味”的生活。王安忆这种市民生活观的转变,为她从“老上海”遗风的市民生活角度打开如“米尼”这样的上海普通小市民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做了充分的准备。也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我们看到了紧接着《好婆与李同志》之后的长篇《米尼》与王安忆已往作品很大的区别。
《米尼》中充满了琐碎的生活叙事,书中两个主人公“米尼”与“阿康”的成长生活史,几乎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二篇幅,而真正写到米尼与阿康走上“卖淫女”与“皮条客”的道路却只占有很小的篇幅。在琐碎的叙述中,米尼与阿康的日常生活叙事占了主导的地位。米尼年幼时家庭的变故,结识阿康后米尼与阿康父母的交往,米尼在婚后独居生活时为生活所迫而被迫行窃等生活事件构成了米尼生活经历的完整叙事,而对米尼在下乡插队前与阿婆为生活费的斤斤计较更能看出在细碎的生活表层下所蕴藏的小市民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在这茫茫人世上,唯一可使她感到安全的就是这些燕子衔泥一样积蓄起来的钱了。钱一点点积多了,她反而觉得不够了,她积钱的热情日益高涨。孙子在农场,自己的工资足够养活自己了;大孙女一月十八元时,她并不说什么,待到第二年拿到二十三元了,她便让她每月交五元做饭钱。哥哥本来就忌讳香港来的钱,盼望自食其力;姐姐由于麻木,对什么都浑然不觉;米尼却将端倪看得很清,经常生出一些小诡计,迫使阿婆用钱。阿婆越是肉痛,她越是想方设法挖阿婆的钱。看见阿婆脸皱成一团,她心里高兴得要命,脸上却十分认真,殷殷地期待阿婆的答复。阿婆说:“给你一个月十块。”其实她心里想的是十五块,出口却成了十块。米尼以这样的逻辑推断出了十五块这个数字,又加上五块:“每月二十块。”她说。阿婆就笑了:“你不要吓唬我啊,二十块一个月?到乡下劳动,又不是去吃酒。”米尼就说:“那也不是命该你们吃肉,我吃菜的。”她的话总比阿婆狠一着,最后阿婆只得让了半步,答应每月十七元。(17)
金钱对于生活拮据的小市民而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米尼、阿婆、阿康以及阿康父母正是在对金钱花费锱铢必较的基础上来建立各自的生计问题的。阿康幼年时也正是对零花钱的渴望,才使他走上了扒窃的道路,而米尼在婚后也是因为生计所迫,才重蹈了阿康当年的覆辙。在对米尼命运的探索中,王安忆正是在对小市民生活、生计等问题的深入挖掘上,把平凡、琐碎的世俗生活推向了人物叙事中前台的位置,从而颠覆了已往以观念冲突为主的意识形态化的叙事特征。王安忆对普通市民世俗生活的叙述,在其90年代以来的作品中不断发展,在《长恨歌》、《妹头》、《富萍》等作品当中,王安忆甚至把这种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哲学上升到诗学的高度,对生计的兴趣和执著甚至成为王琦瑶们躲过一次次“文革”灾难冲击的唯一方式。
“世俗生活”在《米尼》中不仅仅是人物生存的背景,更是故事发展必须具备的坚实基础,甚至能改变个人发展的命运。王安忆不断地把“小市民生活”的主体内容放置于“大上海”这样一个“世俗生活”的历史环境中,让人物本身在外界因素的刺激下呈现其必然命运,而“老上海”这样的世俗生活内容重新出现时就承担了这样一种叙事功能。80年代随着上海城市改革的展开,以三四十年代为代表的“老上海”生活的回归使生活其间的普通市民兴奋异常、奔走相告。有几则材料可以反映1985年前后的城市改革给上海带来日新月异的变化:
本市目前最高的大楼——上海宾馆,昨天全部完成土建施工……这幢坐落在华山路乌鲁木齐路附近的宾馆,总建筑面积四万四千五百平方米。主楼地下一层,地上二十九层,总高度为九十一米。四至二十二层是客房层,设有客房六百套,每间客房有十件中国式家具、冷暖空调设施及呼唤装置。二十三层是宴会厅,设有中国式、欧美式、日本式三个餐厅,旅客用餐时可俯瞰市容。(18)
上海宾馆“芳园”餐厅七月十二日起对外举办音乐茶座,开放时间为每天下午二时半至四时半,每位收费二元五角,其中包括饮料和西点。晚上还将播放彩色投影电视。(19)
1985年,上海共有52家舞厅和迪斯科舞厅,到1994年已超过了1000家。(20)
豪华的酒店设计和舒适的用餐,“额外”的“音乐茶座”及其娱乐节目,呈级数增长的歌厅、舞厅等新老生活方式的出现无疑极大地改变着人们对生活的认识,厕身其间的米尼第一次领略到“老上海”醉人的生活方式时,不免产生梦幻般的感觉:
平头的摩托在南京路东亚大饭店门前停住了,她就随了他上楼,有了穿制服的年轻朋友给他们开门。电子音乐如旋风一般袭来,灯光变幻着颜色,光影如水,有红男绿女在舞蹈。米尼茫茫地跟在平头后面,绕过舞池,她感觉到灯光在她身上五彩地流淌过去……窗外是一条静河般的南京路,路灯平和地照耀着,梧桐的树影显得神秘而动人。米尼惊异地发现,上海原来还有这样魅力的图画,她在此度过了三十余年却刚刚领略。(21)
王安忆对“老上海”的发现也正如米尼对“老上海”梦幻般生活的发现一样,惊讶而震撼。在这之前,“老上海”的生活方式一直作为受批判的对象而在小说、话剧中出现,“老上海”的生活方式也一直与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而成为把人引向“堕落”的“罪恶之源”。“老上海”生活方式的出现对米尼而言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甚至在米尼与平头们合伙下南方卖淫前也曾设想过以后过上“老上海”一般优雅的生活。米尼的迅速堕落除了有其诸多的主观因素以外,对“老上海”所代表的生活方式的向往未尝不是米尼走向堕落的一个原因。
王安忆对“老上海”世俗生活方式的重新发现,不仅仅使米尼的生活与命运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更重要的是,“老上海”去意识形态化的展示激发了王安忆更多的想象空间。摒弃意识形态视角的“老上海”所代表的是上海本来充满活力的生活画面,在多重生活空间的对照下,人物本身所呈现的命运形式就显得跌宕多姿。王安忆正是从对“老上海”的想象与描述当中,重建了她对市民生活本身的形式感和现实感。由《米尼》而引起的对市民生活现实感与形式感的重建,在以后的《我爱比尔》、《妙妙》、《妹头》、《长恨歌》、《富萍》等作品中也不断重现。王安忆在《米尼》中所发现的多重生活空间对人物的冲击,使得她与上海市民普通的生活越走越近,最终融为一体。80年代末王安忆一大批回忆上海童年生活与青春岁月的散文,使得她不自觉地融入了现实与虚构的市民生活世界。而“老上海”市民所代表的价值观与“新上海”市民价值观之间无形的冲突,使得普通的市民生活背后总有“老上海”的影子,使普通的故事本身就具有饱满的张力。王安忆由“米尼”们的“沉沦”而发现的“老上海”,使她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故事资源,并最终在90年代以来形成其独特的叙事方式。
四 结语
文学创作转型是很多作家在其创作中都会存在的现象。促使作家创作转型可以说有各种各样的因素,每个作家所面临的创作问题不一样,其选择的方式和转型的方向也不同。通常作家的转型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被动的转型,一种是主动的转型。在被动的转型中,时代转变的因素和作家创作资源濒临枯竭的因素会占很大的成分;在主动的转型中,则大多是因为作家对自身的创作不满,或是为了寻找更好的创作资源等,才会促使作家对生活或对自身创作优势进行重新的检视。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作家创作的转型因为时代和自身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两种转型都曾频频发生。
王安忆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转型,无疑是属于主动型的创作转型。王安忆对市民身份的自觉归属,对城市改革与市民命运的重新探索,以及对“老上海”的重新发现等等,都透视出王安忆对创作的努力探索。《米尼》正是王安忆诸多文学创作探索中起步最早的一部,《米尼》无疑实践了王安忆多种文学观念与写作方式的“可能性”。正是对《米尼》这一文本的深入探索,才使得我们对王安忆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创作的转型有了更多的认识。
注释:
①《米尼》初名《米妮》,江苏文艺出版社1990年8月版,后来又发表在《芙蓉》1991年第3期。
②王安忆:《谈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③[荷]佛克马、[荷]蚁布思:《文化研究与文化参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8页。
④王安忆:《插队后记》,《独语》,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⑤⑥王安忆:《“上海味”与“北京味”》,《北京文学》1988年第6期。
⑦王安忆:《米妮》,江苏文艺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232页。
⑧王安忆:《我做作家,是要获得虚构的权力——与台湾作家张灼祥对话》,《王安忆说》,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⑨程光炜:《王安忆与文学史》,《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3期。
⑩(11)王安忆:《好婆与李同志》,《文汇月刊》1989年第12期。
(12)(13)参见张静主编《身份认同研究——观念、态度、理据》,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4)王安忆:《米妮》,江苏文艺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8页。
(15)王安忆:《米妮》,江苏文艺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122页。
(16)王安忆:《好婆与李同志》,《文汇月刊》1989年第12期。
(17)王安忆:《米妮》,江苏文艺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28页。
(18)《文汇报》,1983年1月1日。
(19)《解放日报》,1984年7月12日。
(20)戴慧思、卢汉龙译著:《导论:一场消费革命》,第3页,《中国城市的消费革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21)王安忆:《米妮》,江苏文艺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1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