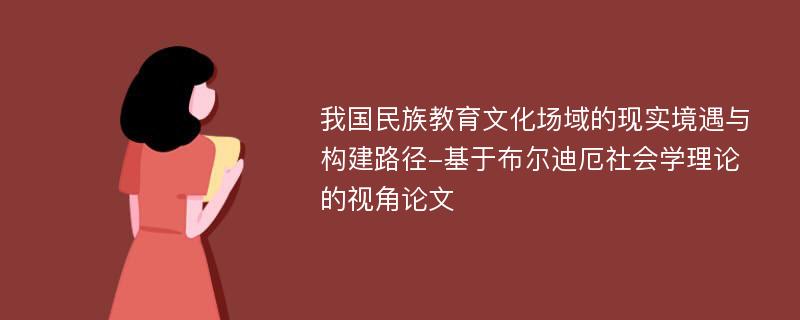
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的现实境遇与构建路径
——基于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的视角
戴 妍,陈佳薇
(陕西师范大学民族教育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摘 要] 民族教育与民族文化相互依存、相济而生。民族教育文化场域是我国各民族文化实现传承、交流、创新与发展的重要空间,但在其内也存在多元文化相冲突、文化资本不对等、教育话语权不均衡和实践逻辑不一致等问题。构建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应以“和而不同”为价值理念,培养多元文化共生惯习;以“立德树人”为价值定位,开发文化融合课程;以“公平均衡”为价值要求,构建多元教育话语;以“文化再生”为价值目标,调适教育主体关系等方面着手,以期释放我国民族文化活力,进而推动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关键词] 民族教育;文化场域;现实境遇;构建路径
场域(field)是将诸种客观力量调整定型的体系,是被赋予了特定引力的关系构型,也是一个充满着冲突与竞争的空间。[1]16该范畴对于认识与理解教育活动及其教育现象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并被教育社会学研究领域中越来越多的学者所使用,正如教育场域,它是指在各教育主体间(如教育者、受教育者等)所形成的一种客观关系网络(network),该场域依托于知识的生产、传承、传播与消费,并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2]所以,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是指在我国少数民族教育内各种少数民族教育要素和少数民族文化要素所占据位置之间形成的以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交流、创新与发展为依托,以少数民族教育主体的全面发展为旨归的客观关系网络。该场域蕴含着我国少数民族教育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相互依存、相济而生的紧密联系,是我国各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交流、创新与发展的重要空间,它不仅促进着我国各少数民族文化间的和谐与交融,在维护中华文化多样性与统一性的过程中也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本文基于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考察了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的现实境遇,探寻了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构建路径,以期释放我国民族教育中的文化活力,借我国民族教育之力发展我国少数民族文化,进而推动中华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一、民族教育文化场域的构成要素
惯习、资本和权力是由场域中的主体(或称行动者)在实践过程中所统一于场域之中的。研究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的构成要素应以布尔迪厄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和核心概念作为理论前提和重要切入点。由于民族教育文化场域是场域的下属概念,其重心落在文化场域,在构成要素方面既具有场域的一般特性,又具有自身文化和教育特性,其主要由文化惯习、文化资本、文化权力和教育主体四个要素构成。
(一)文化惯习
惯习是一种结构形塑机制,其运作来自于行动者内部;它还是一种生成策略的原则,且行动者能够运用这种原则去应付未被预知、不断变化的各种情景。或者说,惯习是一套持久存在的、可变更的性情倾向系统。[1]18它是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生成的,在体现人类主观性的同时,也必然是社会化的客观结果,是具有主观性的客观社会化结果。它有利于把场域构建成一个充满感觉、价值和意义的世界,一个你愿意投入精力的世界。[1]158所以,文化惯习是指场域的主体(行动者)在场域内的文化实践活动中所生成的既持久存在又可变更的一套性情倾向系统,它是场域的主体被社会化了的主观性体现,能使场域的主体去应付各种各样的文化情景。而且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活动,对于民族教育文化场域来说,文化惯习是该场域内惯习的主要形式,它是教育主体在持有特定教育目的,并以民族文化为载体的民族教育的长期文化实践活动中所逐渐生成的、较为稳定的性情倾向系统。它体现着教育主体的能动性、创造性,是他们习得和传承其民族文化的重要辅助力量,是民族教育文化场域内民族文化传承、交流、创新与发展的重要载体。
(二)文化资本
场域是一个围绕特定的资本获取加以组合和分类的结构化空间。“资本”是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它是一种以物质化与身体化的形式所累积而成的劳动,体现着一种生成性,蕴含着一种潜在的、生产利润的能力,且这是一种通过等量或增加的方式来不断生产自身的能力。文化资本作为资本的重要形式之一,它是指在不同的教育行动中所传递出的文化物品,并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布尔迪厄之所以使用文化资本的概念,最初就是为了解释“尽管大家拥有着同样的教育机会,为什么仍会存在教育成就的差异”这一现象。文化资本通过影响学术成就来实现和参与社会再生产,且其再生产主要依赖于学前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两种方式而实现。在教育场域内,文化资本界定着该场域的基本资本形态,是教育场域的媒介资本。民族教育文化场域作为教育场域的衍生概念,其基本资本形态和媒介资本同样是文化资本,这是该场域得以区别于其他场域的关键要素。在民族教育文化场域内,文化资本的再生产主要依赖于家庭教育文化场域和学校教育文化场域而实现。
(三)文化权力
场域是一个包含着多种力量的空间,是持有不同利益需求的主体为控制有价值的资本而进行争夺的领域,是一场权力的博弈。每一个场域内都充满着各种力量的冲突与对抗,且场域内的个体是以其权力利益为依据而展开竞争的。[1]17权力是以资本为基础的,其支配场域的力量是资本所赋予的;而且,权力确保场域正常运作并从中获取利润,也要受益于资本。[1]127场域内的文化权力与文化资本是相对应的,它是指不同活动主体在场域内的文化实践活动中所分配而得的权力,并具体性地呈现着文化的支配性与文化霸权。[3]在民族教育文化场域内,文化权力是指权力层面上的文化支配与霸权,它以话语权力为表现形态,具体表现为文化管理权力、文化施教权力和文化受教权力,它们使得该场域得以产生或再生产,并在该场域中被概括为“教育话语权”。由此可见,文化权力是民族教育文化场域中教育话语建构的权力中轴,是该场域内文化再生产的重要推动力量。
Cloumn-Bot是一种集成了环境检测、灾情预警、故障追踪与远程控制等功能的工业用智能化机器人,将各功能作为单一模块集成至机器人壳体,采用总线将各模块连接,实现控制器与模块的双向数据流.
(四)教育主体
在场域中,主体亦称为“行动者”,他们是场域内实践活动的践行者,是场域内惯习、资本和权力的组织者,需要遵循一种复杂的实践逻辑。这种实践逻辑是自在逻辑,它“既无有意识的反思又无逻辑的控制”。[4]也就是说,场域的主体在实践活动所要遵循的是一种无意识的自在逻辑。因此,场域内的教育主体其实是指在场域内的教育实践活动中,遵循某种无意识的、自在的实践逻辑的教育行动者。而场域内的教育实践,它指的是教育主体在教育的文化实践活动中积累、整合和内化其文化经验,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其文化惯习、掌握相应文化资本的一系列教育活动。可以说,教育实践就是教育主体在文化惯习的影响下,根据其已有的文化资本,在教育场域中所发生的策略行为。由此可见,教育主体是场域内教育实践的关键要素,他们在场域内的教育实践活动中将文化惯习、文化资本等要素组织起来。在民族教育文化场域内,教育主体是指使该场域内的文化惯习、文化资本和文化权力作用于民族教育文化场域内文化实践活动的重要行动者,主要包括该场域内文化实践活动中的教育行政者、校长、家长、教师和学生等。这些教育主体在民族教育文化场域内的文化实践活动中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文化惯习,获取和习得了相应的文化资本,并在该场域中发生了一系列的文化实践行为。
二、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的现实境遇
文化资本在多种资本形式中是最具影响力的,其中,作为文化资本之一的课程,也是极有价值的。多元文化课程能够满足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学习需求,并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多元文化氛围、提供平等的文化学习机会,它有助于推进多元文化的交融与互鉴,从而实现多元文化间的传播、发展与融合。[11]在构建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的过程中,为了缩小该场域内的文化资本不对等,尽可能地保证我国每一少数民族教育主体获得相对平等的文化资本,要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价值定位,为该场域内的少数民族教育主体们积极开发文化融合课程。要在丰富文化资本的同时,努力保证和实现我国不同少数民族教育主体所获取的文化资本是相对平等的。具体来说,可以通过以下三种途径来开发文化融合课程:第一,应做好文化融合课程设计,不仅包括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外来文化的融合,也包括了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尤其要积极地开发较为缺乏的文化融合课程资源,如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古建筑、礼仪、史诗等;第二,要做好顶层设计,保护我国濒危的、被边缘化的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将其与我国主流文化、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以及外来文化相融合,在融合中实现创新,从而开发出开设科学、合理、可行的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课程;第三,要发现和挖掘我国各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课程中的闪光点,找到它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课程之间的连接点和融合处。
(一)场域内多元文化相冲突
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是一个由少数民族文化惯习、文化资本、文化权力以及教育主体所构建而成的客观关系网络。要解决当前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中存在的问题,我们需依据当下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的应然价值取向,尝试性地提出构建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的主要路径,具体如下:
(二)场域内文化资本不对等
我国民族教育公平是我国社会公平在民族教育领域的延伸,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基础,有利于维护社会主义和谐稳定和推动国家发展。教育目的分为教育过程之内的目的与教育过程之外的目的两大类。而恰恰是教育过程之外的目的,即社会和经济等外在因素,主导着教育场域内话语构建的支配关系。由于社会和经济等外在因素的不均衡发展,导致了教育场域内的文化资本分配不公,且不同教育主体所掌握的教育话语权日益失衡,从而有损于教育公平的实现。在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内,受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该场域内的文化资本在不同少数民族教育主体间的分配是存在差异的,这会导致他们对文化权力的掌握是不均衡的,或者说其所掌握的教育话语权的不均衡,而这种不均衡在学校教育文化场域中甚至会进一步扩大,这不利于我国民族教育公平的健康发展。具体而言,在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内,少数民族学生在话语构建中所掌握的教育话语权与其在该场域中所获取和占据的文化资本是相对应的,其所占据的文化资本越多,所掌握的教育话语权也越多。而且,该场域内的少数民族教师也会以学生所掌握教育话语权的多少为依据去分配教育资源,这进一步加深了少数民族教育不公。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的教育目的要始终以“公平均衡”为价值要求,应尽可能地满足我国少数民族教育主体的文化需要,使我国各少数民族文化在该场域中得到公平地传承、交流、创新与发展,要尽可能地保证我国不同少数民族教育主体所掌握的文化权力和教育话语权是相对公平和均衡的,以该场域内文化权力和教育话语权的公平去推进我国少数民族教育公平的发展与前进。
选择与3.3节中相同的条件,基于Lambert-Beer定律,计算三种辐射波在平流雾和辐射雾中的透过率TLB,并与Monte Carlo仿真的透过率TMC进行比较,结果如图8所示.
(三)场域内教育话语权不均衡
场域是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网络或图式[5],是一个围绕特定的资本获取加以组合和分类的结构化空间,在这一空间里,知识话语、权力话语等相关话语权得以构建和分配。[6]269在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内,特定的文化资本产生特定的文化权力,该场域内的少数民族教育主体在获取知识并建构其教育话语的过程中,不是凭借其已有的才能,更多地依赖着其上层文化资本。这里所说的“上层文化资本”,指的是少数民族学生在家庭背景、社会出身和经济实力三种主要因素的影响下所获取到的文化资本。所以,不同少数民族教育主体在其教育话语的建构过程中所依赖的上层文化资本是不对等的,且差别甚至在逐渐扩大。长此以往,我国少数民族教育就呈现出一种不均衡、不公平的发展态势,这会相应地导致我国少数民族教育主体在少数民族学校这种中介性场所中所掌握的教育话语权也是不均衡、不公平的,进而演变成其所获取到的知识和社会资源同样是不均衡、不公平的。也就是说,在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内,由于不同少数民族教育主体间文化资本的分配存在差异,从而导致其所掌握的教育话语权是不均衡的。例如,少数民族学生在构建其教育话语的过程中,占据文化资本多的学生相应地会掌握更多的教育话语权,而少数民族教师也会以学生话语权的多少为依据去分配教育资源,那么该学生会进一步掌握更多的文化资本和教育话语权,这会在少数民族学生群体之中形成一种隐性的层级建构,从而有损于我国少数民族教育公平的发展。
(四)场域内实践逻辑不一致
各种位置与立场的场域与场域内行动者的实践之间是密不可分。[1]131实践决定认识,认识反过来又影响着实践。场域内每一主体所遵循的实践逻辑都是在其所从事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是在主体的日常生活经验与生命体验的实践活动中获得的;反过来,科学合理的实践逻辑指导和推进着主体在实践活动中的进一步发展。在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内,无论是少数民族的家庭教育文化场域和学校教育文化场域,还是经济和政治等场域,每个场域都有着自身特定的实践逻辑,且该实践逻辑是各场域主体在其所参与的各种实践活动中生成和获得的。尤其对于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内的家庭教育文化场域和学校教育文化场域来说,它们的文化实践背景、文化实践方式和文化实践行为各有特点,其少数民族教育主体都有着自身特定的实践逻辑,且彼此间存在差异。所以,我国少数民族学生在家庭教育文化场域所遵循的实践逻辑会与其在学校教育文化场域所遵循的实践逻辑相冲突。例如,在我国少数民族家庭教育文化场域内,其实践逻辑规定着该场域内的价值规范,不仅会对少数民族学生的个体惯习产生较为稳定和持久的影响,也会对该学生未来的学校生活产生潜在的影响,甚至有些是消极影响,这会导致少数民族学生的内部价值冲突与混乱,其原因是少数民族家庭教育文化场域与学校教育文化场域之间的实践逻辑不一致。
教育既关乎国计,又涉及民生。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不仅继续把优先发展教育作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中心任务,同时也把教育问题作为改善民生与社会建设的首要问题。这既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现,也是进一步尊重人民对于美好教育和美丽中国的期盼。
三、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构建的价值取向
民族教育的“根”在于民族文化。我国少数民族群体如何才能将自己的民族特色、民族优势与其民族文化相结合,是我国民族教育中的核心问题。教育的相对独立性是其价值取向发生的前提,就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而言,该场域的相对独立性也是其构建过程中价值取向发生的重要前提。针对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的现实境遇,构建新时代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需坚持并遵循以下价值取向:
(一)“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
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形态是确立我国民族教育价值取向的现实基础。[7]我国社会文化的多元化要求我国民族教育要尊重和维护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要努力实现我国少数民族教育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协同共生,要始终遵循“文化共生”的价值理念。“文化共生”是指“不同民族文化间异质共存、交流互鉴、兼容并包的一种文化形态”[8],它突出的是多元文化异质共存理念,即“和而不同”理念。在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内,多个少数民族文化小场域是同时存在的,它们都有着各自的文化价值观、文化逻辑体系、文化特征以及文化内核等,在相互接触过程中会产生矛盾,进而引发该场域内的多元文化冲突。为了消除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内的多元文化冲突,要始终坚持“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促进该场域内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异质共存、相互交流和兼容并蓄。在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内,要借民族教育之力去协调与处理好各少数民族文化间的关系,尤其要注重协调好三方面的少数民族文化关系:首先是本民族在对待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间相互关系方面的态度取向;其次是本民族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少数民族文化选择和文化适应;最后是不同少数民族教育文化场域内的少数民族教育主体对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适应与认同,从而推动各少数民族文化间的和谐与交融。[9]
(二)“立德树人”的价值定位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和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其中,“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育人之本,就在于立德铸魂。可以说,“立德树人”是发展我国教育事业必须始终牢牢抓住的灵魂。我国民族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必须始终牢牢抓住“立德树人”的教育灵魂。因此,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从本质上来说是“育人的文化场域”,该场域内的每一少数民族教育主体正是在习得和传递其少数民族文化中获得价值感和归属感,并进而实现了自身的情感升华、道德提升和生命成长。但是,在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内,不同少数民族教育主体由于受到该场域内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影响和制约,如家庭背景、社会出身、经济实力等,其获取文化资本的差别与不对等在逐渐扩大,这种功利性倾向会妨碍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的健康发展,使其偏离“立德树人”的根本价值与目标。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理应是一个遵循育人价值标准与规范,尊重人的个性,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文化场域,或者说,我国所要构建的民族教育文化场域是一个能够促进每一少数民族教育主体全面发展与健康成长的文化场域。尽管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内共存着多个少数民族文化小场域,且各有差异,但这些文化小场域首要的都是把“立德树人”作为最根本的价值定位,遵循共同的育人价值标准和规范,尽可能地保证每一少数民族教育主体获得相对平等的文化资本,以促进其身心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三)“公平均衡”的价值要求
在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内,文化资本并非只来自学校教育文化场域,还来自于家庭教育文化场域。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内的家庭教育文化场域,一方面是我国少数民族儿童获取和传递文化资本的重要空间;另一方面,它也是文化资本再生产的重要场域。我国少数民族儿童在接受正式学校教育之前,就已经有了早期社会化的迹象,具体而言,少数民族家庭成员的受教育水平、对于传统民族文化的代际传承方式、对于少数民族地方性知识的接受程度、少数民族地区内大众传媒所传播知识的深度与广度等,这些社会因素都影响着少数民族儿童获取文化资本的数量与类型。即使是进入学校教育文化场域后,我国少数民族学生所获取到的文化资本还会受到少数民族地区内学校地理位置、物力资源、财力资源、教师资源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进一步扩大了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内的文化资本不对等。也就是说,我国少数民族儿童所获取的文化资本会因个体、地域、经济、政治等因素形成一定的差别,即文化资本是不对等的,这体现着不同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群体间的“区隔”,即区分和隔离着不同的少数民族阶层。而且我国少数民族儿童即使在进入学校教育文化场域后,仍然要受到多种非教育因素的影响,其中主要包括个人的家庭收入、社会出身、经济基础三种因素,它们是影响少数民族儿童获取文化资本的重要因素。概括来说,在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内,不同少数民族教育主体由于受到该场域内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影响和制约,其获取文化资本的差别与不对等甚至在逐渐扩大。
(四)“文化再生”的价值目标
惯习是一种依靠行动者自身努力或经由他人灌输而来的行动的产物,它通过个体或者集体的生活史被身体化与内在化。[10]惯习具有传承性、稳定性、开放性和能动性等特点,是影响场域重塑的重要因素。在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内,不同少数民族教育主体的态度、思想、价值观等在其民族文化的变迁与整合过程中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进而导致了不同少数民族文化小场域间出现某些多元文化冲突。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内多元文化冲突的存在,是不同少数民族教育主体在生命成长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惯习”的差异所致。在构建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的过程中,为了消除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内的多元文化冲突,要从该场域内的文化惯习入手,始终坚持“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培养我国少数民族教育主体们的多元文化共生惯习。具体来说,一方面,要尊重我国不同少数民族教育主体的个体生活经验,正视他们之间个性化惯习差异的客观存在,关注不同少数民族教育主体间的个性发展差异在我国少数民族教育及其文化中的适切性,努力使少数民族学生的个体化发展与群体化“惯习”相契合;另一方面,要努力培养我国少数民族教育主体们的多元文化共生惯习,尽可能地为他们的生命成长提供共同的、丰富的文化情境体验和文化主题实践活动,从而推进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文化建设与发展,促进该场域内的多元文化融合与共生。
四、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构建的路径
场域是一个多种力量相互争夺的空间,在这个争夺空间中,既有隐而未发的力量,也有正在活动的力量。[1]128这体现并说明了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存在着冲突论色彩。场域内的惯习差异,场域的资本、权力之间的纠结与冲突是场域运作和转变的原动力。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是一个富含多元文化的场域,它包含着多个少数民族文化小场域,该场域中的各少数民族文化是共存的。场域形塑惯习,不同的文化惯习是在不同场域中所形成的,即由于不同场域的文化基因序列是有差异的,从而导致场域文化冲突,这是产生场域文化冲突的内在逻辑。对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内的少数民族文化小场域而言,它们各自不同的少数民族教育主体在其生命成长和文化实践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惯习”各不相同,且每一个少数民族文化小场域都有一套自身独特的文化价值观和逻辑体系,内含其独有的文化特征与内核,因此,它们之间的接触和交流必然会产生矛盾和冲突。所以说,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内存在着多元文化冲突是必然的,其具体表现为不同少数民族文化小场域间的文化认同冲突,各少数民族教育主体间的文化心理冲突,以及各少数民族文化在同一时间轴和空间轴上的文化共生冲突等。
(一)消除文化冲突,培养多元文化共生惯习
在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中,十分重视场域内社会实践和社会经验的重要性,并强调社会实践是场域内文化再生的重要手段与途径。就教育而言,“教育实践,不仅能传递文化资本,还可以推动教育文化资源的再生产”[6]270,“文化再生”应是所有教育实践活动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就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内的家庭教育文化场域和学校教育文化场域而言,由于它们的文化实践背景、实践方式和实践行为各有特点,各场域内的少数民族教育主体都有着自身特定的实践逻辑,这会导致彼此间的矛盾与冲突,从而不利于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群体共同致力于“文化再生”。因此,在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内,应以“文化再生”为价值目标,重视我国少数民族教育中文化活动的实践性,要在少数民族教育的文化实践活动过程中促使文化再生产,尽可能地发挥该场域内各少数民族教育主体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参与性,释放该场域的应有文化活力。在重视“文化再生”价值目标的同时也应重视“人际关系环境”的场域观念,需打破狭窄的场域观,认识到“人际关系环境”在该场域中的重要性,而不是将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仅仅局限于少数民族学校和课堂之内,要借我国民族教育的社会力量为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营造和维持良好、多元、平等的人际关系环境。这是因为,人际关系环境是我国民族教育中文化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内文化再生的重要空间。
(二)坚持立德树人,开发文化融合课程
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是我国民族教育与各民族文化相互交织、协同共生的重要场域,体现着我国的多民族文化特性,它是一个动态系统。该场域内的多重矛盾是其运行和发展的动力,且场域内的少数民族文化惯习、文化资本、文化权力以及少数民族教育主体是生成多重矛盾的重要因素。以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入手,并结合以上构成要素的分析,以此观之,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主要处于以下现实境遇:
一般意义上的“启蒙”指的是一种态度或过程,它只承认自由个体的权威,而不承认其它的权威。这个意义上的启蒙没有日期来标示其开始或结束,因而不能指一个阶段的启蒙。不论何时,只要能摆脱不加怀疑的接受并学会批判性分析,那么就可以说是获得了启蒙。
(三)破解权力构架,构建多元教育话语
在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内,特定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本产生其特定的文化权力。在构建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的过程中,由于我国不同少数民族教育主体所获取的文化资本存在差异与不对等,从而导致了不同少数民族教育主体所掌握的教育话语权存在一定的“区隔”,形成一种隐性的等级结构,这与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所遵循的“公平均衡”的价值理念是相违背的。在该场域内的教育实践过程中,教育话语所传递给学生的教育内容往往是符合统治阶级价值观和利益的,而这种教育话语已经具有了一种文化和权力专断之嫌。[12]也就是说,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内的教育话语是以统治阶级价值观和利益为主导的,它在某种程度上暗含着文化权力的“专断”。而且,这种文化权力的“专断”会使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整体话语发生失衡,进而使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内的某种教育话语权影响了各少数民族文化小场域内的教育话语权,从而诱导了每一文化小场域内少数民族教育主体们的话语表达。在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的构建过程中,为了尽可能地消解文化权力的专断,努力满足“公平均衡”的价值要求,要破解该场域内固有的文化权力构架,构建多元教育话语。具体来说,一方面,要推进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内的各少数民族文化小场域的教育话语的创新,不断地用新的教育话语取代传统的教育话语,从而实现该场域内的少数民族教育话语权的公平配置;另一方面,我国少数民族教育文化场域应保持相对独立、客观和自由的少数民族教育话语,在相对独立的教育话语空间中生成多元教育话语,要在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领导下努力发展其应有的生存空间。在我国民族教育的文化实践活动中,要努力建构多元化、民主化、相对自由化的少数民族教育话语,以消解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构建过程中教育话语权的专断。
(四)立足教育实践,调适教育主体关系
教育实践,是促使文化再生产的重要途径;教育实践活动中的行动者要遵循一种特定的、复杂的实践逻辑。教育实践活动中的行动者,即我们常说的“教育主体”。在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内,其实践活动的行动者指的是“我国少数民族教育主体”,如少数民族教师、少数民族学生和少数民族家长等。在构建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的过程中,为努力消解该场域内的实践逻辑冲突,要尊重我国少数民族教育主体们的生命成长规律,关注其文化情感需求及成长愿望,坚持以“文化再生”为价值目标,以形成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的整体育人实践体系,调适好场域内不同少数民族教育主体间的关系。具体来说,一方面,要始终坚持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的实践性,关注和重视各少数民族教育主体的教育与文化实践活动,要在这些文化实践活动中去调适我国少数民族教育主体间的关系,如家长—教师、教师—学生、学生—学生的关系等;要建立并营造尊重、民主、平等的我国少数民族师生关系及氛围,重视少数民族的家庭参与,充分认识到少数民族家长是我国少数民族学生健康成长与否的关键影响力量,积极处理好少数民族家长与教师、少数民族教师与学生等关系。另一方面,要在尊重我国各少数民族教育主体的个体惯习的基础上,重建我国少数民族教育中的文化实践方式与途径,尊重我国少数民族教育主体们的日常文化体验及经验,尽可能地满足其文化情感需求和成长需要。
(12)前瞻性考核:将步骤(1)~(8)所产生的数据按7∶3随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作为训练集用于建立判定亚组的模型,另一部分作为考核数据集用于前瞻性考核,按步骤(10)~(11)分别计算出符合率和模型判对率。
总之,构建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民族团结教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发展进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未来我国民族教育文化场域的构建应以培养多元文化共生惯习,开发文化融合课程,构建多元教育话语,调适教育主体关系等方面着手,以期借我国民族教育之力去传承、交流、创新和发展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在传承、交流、创新和发展之中,使我国各少数民族文化在“文化之林”重焕生机,进而实现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引导学生:让学生认识到,实际生活中解决问题可以有多种方法,只要言之有理即可。以此让学生大胆思考,不怕犯错,不怕与众不同。
[参考文献]
[1][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美]华康德.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康,李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2]刘生全.论教育场域[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1):78—91.
[3]娜拉.场域视角下民族教育文化相关性解读[J].湖北社会科学,2012,(11):183—185.
[4][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实践感[M].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131.
[5][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M].陶东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36.
[6]谢益民.论教育场域中的文化资本与话语构建:以学生为视角[J].湖南社会科学,2013,(6).
[7]王鉴.论我国民族教育的价值取向问题[J].贵州民族研究,1996,(1):99—104.
[8]孙杰远.文化共生视域下民族教育发展走向[J].教育研究,2011,32(12):64—67.
[9]祁进玉.国家认同与公民身份的生成场域:学校教育的衍生功能[J].民族教育研究,2008,19(6):38—42.
[10]张祥兰.班级文化场域建构:价值选择与关系调适[J].中国教育学刊,2016,(8):51—54.
[11]张增田,靳玉乐.多元文化课程的内涵与特点[J].当代教育科学,2006,(9):23—24.
[12]牛海彬,白媛媛.我国教育场域的话语批判与重构[J].教育与职业,2012,(17):162—163.
The Realistic Situations and Construction Pathways of China's Cultural Field of Ethnic Education——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Bourdieu's Sociological Theory
DAI Yan,CHEN Jia-wei
(School of Ethnic Education,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062,China)
Abstract :Ethnic education and ethnic culture are interdependent and mutually beneficial.The cultural field of ethnic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space for the inheritance,communication,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various ethnic cultures in China.However,there are also some problems in it,such as the conflict of multiculture,the inequality of cultural capital,the imbalance of discourse power in education and the inconsistency of practical logic.In order to construct China's cultural field of ethnic education in lin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era,we should cultivate multicultural symbiotic rituals with taking"harmony in diversity"as the value idea develop cultural integration courses with taking"morality and nurturing"as the value orientation construct the multivariate educational discourse with taking"fair and balanced"as the value requirement adju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in subject of education with taking"cultural regeneration"as the value goal.The aims of them are to release the vitality of Chinese ethnic cultures and promote the great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Ethnic education;Cultural field;Realistic situations;Construction pathways
[中图分类号] G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215(2019)03-0036-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精准扶贫战略下西北民族地区教育扶贫机制与监测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6BMZ058);陕西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项目“民族地区卓越教师培养计划研究”(项目编号:JSJY2019013)。
[作者简介] 戴妍,陕西师范大学民族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与民族教育研究;陈佳薇,陕西师范大学民族教育学院民族教育专业201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族教育。
[责任编辑 齐金国]
标签:民族教育论文; 文化场域论文; 现实境遇论文; 构建路径论文; 陕西师范大学民族教育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