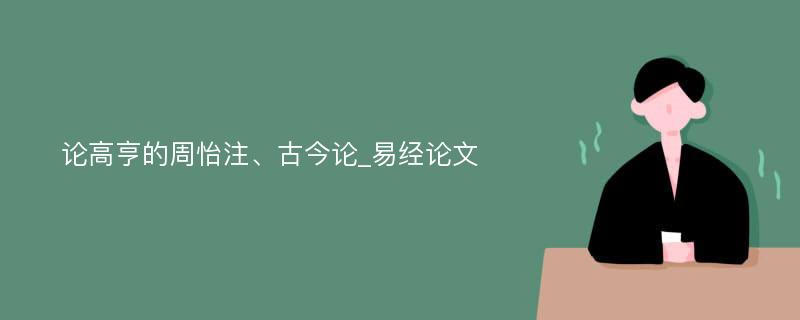
高亨《周易古經今注》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易论文,古經今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易經》自漢以後被視爲“六經”之首,雖稱難讀,但由于兩千年間易學家的不懈努力,已經基本可通,其中深旨奥義亦足啓迪人生,嘉惠世人。然自辛亥革命後廢除尊孔讀經,經學傳承由此斷裂,此後學人號稱以史學代經學,將前代經師所作之經典詮釋一切推倒,重起爐灶,欲以訓詁學之小識小慧重解經典。而所立之論,表面看似有訓詁學之根據,實則以文字訓詁爲包裝,而作光怪陸離之論。高亨的《周易古經今注》①就是這樣一部著作。
傳統易學分爲兩大派:即漢儒的象數派和宋儒的義理派。漢儒象數派根據卦象來解釋卦、爻辭,由于本卦的卦象比較單一,往往不足以解釋卦、爻辭的意思,象數學家便發明旁通、飛伏等方法,由一卦變出其他卦,再用新變出之卦的卦象來解釋本卦的卦、爻辭。此類方法就是後人所批評的“象外之象”。其方法不僅繁複,而且甚不合理。因爲你所解釋的是本卦,卻用其他卦的卦象來注解,不足以令人信服。當然也有少數卦的卦、爻辭只需用本卦卦象就可以解釋得很好,而不須借用其他卦的卦象來解釋。但這樣的例子比較少,因而漢儒象數派對《易經》的大部份解釋,顯得牽强附會。
宋儒義理派對于《易經》的解釋,强調以卦名作爲一卦的中心思想,將一卦看作一個整體,他們一般不反對用卦象解釋卦、爻辭,但反對漢儒那種“象外求象”的方法。他們解《易》更看重爻位、正應等關係。以爲自然、社會中有等級、相應等關係,《易經》作爲對自然、社會的反映和模擬,也有同樣的關係,這些關係正是通過《易經》的爻位、正應等方式來體現的。由卦、爻辭與這些爻位、正應等關係相結合,來表達和闡釋種種人間的道理,是義理派易學的基本思路。
入清以後,學界出現一種反宋學思潮,起初只批判宋學中的理學思想,到了清中期以後,學者又開始反對宋儒以義理解經的方法。戴震倡導“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的解經方法,爲學人所推崇。但當時在易學上有成就的學者並未采用此方法來解釋《易經》,如惠棟的《易漢學》、《周易述》;張惠言的《虞氏易禮》等采用的是漢儒象數易學的方法。而真正采取“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的方法來解釋《易經》的,或由現代高亨的《周易古經今注》開其端。然高亨治學之時,早已不是乾嘉時代,而是一個批判傳統、以顛覆傳統經學爲能事的時代。
高亨治《易》,不講象數,也不講義理,有人說他“開創了我國現代《周易》‘義理派’的研究新方法”,非其實也。如將高亨歸爲易學某一派,不妨稱之爲“現代易學訓詁派”。此派人物非止高亨一人,而高亨實爲此派之宗主。
《周易古經今注》一書既不像漢儒那樣以卦象來解釋卦、爻辭,也不像宋儒那樣用爻位、正應等關係來解釋卦、爻辭,這就大大增加了卦、爻辭的解釋難度。因而高亨采用文字、音韻、訓詁的方法來改字解經。改字解經,一向爲解經之大忌。采用這種方法,似乎某卦叫什麼卦名並不重要;卦爻辭與卦名之間没有了意義的聯繫;爻辭與爻位之間也變得毫無關係,似乎某一爻辭寫在任何爻位上都可以;這就使得爻辭與爻辭之間的聯繫變得鬆散,看不到爻辭之間的內在聯繫,有時甚至使得單條卦、爻辭的文句也變得毫不連貫,只是不同占筮記錄的拼湊而已。因此,由高亨筆下注出的《易經》,不惟毫無義理之可言,簡直就是一堆占卜迷信的垃圾。
近數十年來,向學之士繩繩不絕,有求學《易經》者,欲遠離江湖術士之易學,而求學術界傳統之易學,苦無門徑,而多藉現代學者注《易》之書,然而現代學者系統注《易》之書本來少之又少,高亨素享盛名,其《周易古經今注》遂成學者學《易》入門書的上上之選。加之學《易》者又多有“先入爲主”的心理習性。所以,此書貽誤來學,其過非小。
高亨(1900-1986),吉林雙陽人。早年曾在清華國學院讀書,師從王國維、梁啓超,長于訓詁考據,一生著述甚多。《周易古經今注》寫成于1940年,即高亨四十一歲之時。1960年代加以重訂。高亨治《周易》,將《易經》與《易傳》分開,改變前人“以傳解經”的舊習,誠爲卓見。但他完全忽視前人解《易》成就,自出胸臆,僅從自己的文字訓詁知識出發,通解《易經》,而所得極少,所失極大。
今不恤冒犯前輩之嫌,特對其書中的若干問題提出商榷意見,以求教于方家。
一、對于卦名的輕忽
高亨易學方法的最大失誤,首在輕忽《易經》之卦名。他認爲,《易經》之初,僅有六十四卦卦形作爲區別,而無卦名之稱。後人依據卦爻辭(高亨稱之爲“筮辭”)而追題卦名。他說:
《周易》六十四卦,卦各有名,先有卦名乎?先有筮辭乎?吾不敢確言也。但古人著書,率不名篇,篇名大都爲後人所追題,如《書》與《詩》皆是也。《周易》之卦名,猶《詩》、《書》之篇名,疑筮辭在先,卦名在後,其初僅有六十四卦形以爲別,而無六十四卦名以爲稱,依筮辭而題卦名,亦後人之所爲也。②
《易經》之初,是先有卦名,還是先有卦爻辭?以現在我們所掌握的資料(無論是傳世文獻,還是考古文獻)而言,我們都無法證明。高亨的觀點完全建立在一種推論的基礎之上。如依高亨的意見,“其初僅有六十四卦形以爲別”,而無卦名作稱謂,一人與另一人交流,必指一卦形給另一人看,方可溝通意見。若六十四卦爲占筮之用,當筮得某一卦時,也不能向人說筮得某某卦,以其無卦名可供稱述也。顯然,高亨的意見是說不通的。
若言“依筮辭而題卦名,亦後人之所爲”,如《蒙》卦卦、爻辭多言“蒙”字,其卦題名爲“蒙”,自然允當。但同樣的情况,《乾》卦多言“龍”,且“用九”言“群龍無首”,顯指六陽爻而言,其卦何以不題名爲“龍”而題名爲“乾”?《姤》卦爻辭三言“包”字,僅一言“姤”字,其卦何以不題名爲“包”而題名爲“姤”?《漸》卦六爻均出現“鴻漸”字,何以不名其卦其爲“鴻”或“鴻漸”,而名其卦爲“漸”?《噬嗑》卦多言“噬”字,並無“嗑”字,若依前例,題一“噬”字即可,又何必增一“嗑”字?《大壯》卦多言“壯”字,並無“大”字,若依前例,題一“壯”字即可,又何必增一“大”字?而《坤》、《小畜》、《泰》、《大有》、《中孚》等卦中並無卦名之字,何以獨選其字以名卦?等等。像這些問題作者自己也認爲是不能由“依筮辭而題卦名”的理論作出解釋的,但高亨還是勉强立說,標新立异。
高亨又提出,《易經》之卦名,並無意義,他說:
《周易》卦名,疑爲後人追題,原無意義。《十翼》釋卦名,亦多與筮辭不合。如《遯》卦筮辭之“遯”皆爲“豚”,而《序卦》、《雜卦》並訓卦名之“遯”爲“退”。《蹇》卦筮辭之“蹇”皆爲“謇”,而《彖》、《序卦》、《雜卦》並訓爲“難”。《夬》卦筮辭之夬爲赽,而《彖》、《序卦》、《雜卦》並訓卦名之“夬”爲“决”。此皆大違經旨。其例甚多,茲不歷舉。本書不釋卦名,但釋筮辭中與卦名相同之字而已。③
高亨所舉之例,並不能證明他的觀點,而恰成反證。
先看《遯》卦,《周易》原典《遯》卦卦、爻辭皆寫作“遯”,《經典釋文》稱“字又作遯,又作遁,同隱退也。匿迹避時,奉身退隱之謂也。鄭云‘逃去之名’。《序卦》云:遯者退也。”《序卦》、《雜卦》解“遯”爲“退”,本合訓詁。高亨以己意將原典之“遯”改作“豚”,反說《遯》卦筮辭之“遯”皆爲“豚”,外人讀之,以爲其有所本,實則逞臆亂說也。至于說到“經旨”,按傳統的理解,《遯》卦全卦是講隱遯退避,當遯之時,晦迹潜光,以遠小人。因此,將“遯”理解爲“退避”,並不“大違經旨”,而是正合“經旨”。因爲《周易》教人,並不一味强調進取,在特定的政治境遇下,有時隱退反而是更明智的選擇。高亨將本卦所有的“遯”字皆釋爲“豚”,即小豬,全卦皆圍繞此“小豬”說事,不知聖人設此卦有何教誡意義?此高亨一味迷信訓詁之卑陋也。
再看《夬》卦,《周易》原典《夬》卦爻辭皆寫作“夬”,《經典釋文》稱:“古快反。决也。”《彖》、《序卦》、《雜卦》並訓卦名之“夬”爲“决”,本合訓詁。高亨以己意妄改原典“夬”字爲“趹”或“赽”,反說《夬》卦筮辭之夬皆爲“赽”,實則逞臆改經。無本之言,不足爲訓。按傳統的解釋,《夬》卦之經旨有二:一是教人在不同的境遇下都能做出正確的决策;二是在君子决去小人的鬥争中,要克己從義,不要依違不决。高亨將本卦所有的“夬”字皆釋爲“趹”或“赽”,認爲是行疾之貌,猶今語之“快”,不僅此卦名無甚意義,整個《夬》卦亦無任何教誡意義之可言,則聖人何以繫此卦爻辭,豈不是太無聊嗎!
再看《蹇》卦。高亨《周易古經今注》說:“蹇借爲謇。《一切經音義》十引本卦名作‘謇’。又六二云‘王臣蹇蹇,非躬之故’。《楚辭·離騷》王注、《後漢書·楊震傳》李注、《三國志·陳群傳》裴注、《文選·辨亡論》李注並引‘蹇蹇’作‘謇謇’。此本卦‘蹇’字古本有均作‘謇’字者之證。”今按:《楚辭·離騷》“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王逸注:“謇謇,忠貞貌也。《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文選注》卷五十三《辨亡論上》:“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李善注“謇”字曰:“《周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三國志》卷二十二《陳群傳》,裴松之注中引“袁子曰:或云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見人主之非,則勃然怒而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也。豈非所謂‘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者歟?”這些材料確實可以說明,當時或有《周易》文本將“王臣蹇蹇”寫作“王臣謇謇”,並且將“謇謇”解釋爲“忠貞”或“忠言”的。然而宋初徐鉉校定《說文解字》時已經指出,《周易·蹇卦》“蹇”爲正字,“謇”爲俗字。他說:“‘王臣蹇蹇’。俗作‘謇’,非。”
《後漢書》卷八十四《楊震傳》謂:“先公道而後身名,可謂懷王臣之節。”李賢注:“《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但同書卷七十三《朱暉傳》謂:“俗吏苟合,阿意面從,進無謇謇之志,郤無退思之念。”李賢注:“《易,蹇卦》艮下坎上,艮爲山,坎爲水,山上有水,蹇難之象也。六二爻上應于五,五爲君位,二宜爲臣也。居險難之時,履當其位,不以五在難,私身遠害。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謇與蹇通。”李賢依據卦象對《蹇》卦卦義及對六二爻辭作了精準的解釋。同書卷七十五《袁安傳》謂:“引義雅正,可謂王臣之烈。”李賢注:“《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烈,業也。”這足以證明李賢所看到的《周易》文本《蹇》卦就寫作“蹇”,偶引“王臣謇蹇”,只是以爲“謇”、“蹇”可通而已。
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周易》是目前我們所看到的最古的《周易》文本,其中《蹇》卦的“蹇”字從“足”而非從“言”,這一新的考古文獻足證高亨妄改經文之非。
高亨還說:
總之,六十四卦卦名,當皆爲後人所追題。大多數卦名,不能代表卦象之意義,僅有若干卦名可以體現其卦筮辭之要旨而已。吾人研究《周易》,不必深究其卦名。而《易·十翼》之作者不明乎此,往往講論卦名,輕下定義,以致陷于紕繆。④
這裏高亨封堵了研究《周易》卦名的途徑。其實,《周易》卦名皆與卦象有關,但高亨完全不講象數,自然不能發現卦象與卦名之間的聯繫,正如他在《述例》第四條中所說:“象數之說不知起于何時,晚周人已常言之。後人推衍,益爲迷離……本書悉擯而弗錄,可云無一語及于象數也。”⑤後世《周易》象數學的確有許多牽强附會的東西,但這不等于《周易》原無象數方面的內容,高亨于象數“悉擯而弗錄”的治學態度,導致他對《周易》卦象缺乏起碼的研究和理解,以致得出“大多數卦名,不能代表卦象之意義”的草率結論。
高亨在《述例》第五條中說:“《周易》某卦爲何繫某種卦辭,某爻爲何繫某種爻辭,某卦之爲休爲咎,其故安在,某爻之爲休爲咎,其故安在,均難得正確之理解。《十翼》所言,似有義例,而不融通。後儒之解,穿鑿附會,名滋人惑。本書于此略而弗論,但釋其筮辭而已。”⑥這是高亨《周易古經今注》一書的要害所在,因爲你不知道“《周易》某卦爲何繫某種卦辭,某爻爲何繫某種爻辭”,那《周易》的卦辭和爻辭豈不是可以亂繫嗎?若《乾》卦的卦辭可以繫于《坤》卦,初爻的爻辭可以繫于上爻,那六十四卦的形式就成了隨人擺放東西的“寄存處”了。“《十翼》所言,似有義例,而不融通”。《易傅》所講的爻位說、相應說等義例,正是解《易》者所當重視者,至于某些卦不符合其例,即不能完全“融通”,也應研究其不能“融通”之故。義例乃解經之指路明燈,不知義例,只靠訓詁解經,不免南轅北轍。此如學外語而不知語法,雖字詞皆識,而不明句意。實則一卦之卦名,正是一卦之要旨,得此要旨,“《周易》某卦爲何繫某種卦辭,某爻爲何繫某種爻辭”即可迎刃而解。先秦《易傳》(《十翼》)中如《彖傳》、《大象傳》、《序卦》、《雜卦》皆釋卦名之意義,雖所釋互有參差,但都認爲卦名自有其意義,至宋儒時,則更明確地指出卦名乃一卦之本質,如郭雍說:“自一卦論之,原始要終,上下不遺,爲一卦之質也。卦名之義,名其質而已。如《乾》之爲‘乾’也,原始要終,知《乾》之質爲健,故名其卦曰‘乾’,至于潜、見、飛、躍,則非質也。六爻之義,剛、柔、動、靜、吉、凶、悔、吝之不同,各從其時與物之异而已,是則潜、見、飛、躍之謂也。此卦爻之義不能一也。”⑦高亨不講一卦之主旨,只講訓詁之末流,是捨大方而趨小道也。在這一點上,晚年的李鏡池倒是頗有所悟,他說:“由于易文簡古,不易解釋,故對卦名和卦、爻辭的聯繫有許多没有看出來,最近寫《周易通義》一書,纔明白卦名和卦、爻辭全有關聯。其中多數,每卦有一個中心思想,卦名是它的標題。”⑧
二、對于卦、爻辭的怪誕解釋
經學本是一門講究傳承、積累的學問,譬如積薪,後來者居上。這就是說,學者對于前人的解經成就,應該給予積極的肯定,並加以繼承,在此基礎上再圖有所發現,有所發明。然而,“五四”以後的學界認爲經學是傳統文化中“一團最濃最重的迷霧”⑨,必要摧陷而廓清之。因而此後出現的解經著作,完全摒棄固有的經學傳統,另闢蹊徑,往往以所謂的民俗學、訓詁學知識重解經典,而所提出之觀念,雖有時不乏新穎之見,但其大多數見解不免光怪陸離、離題萬里。高亨的《周易古經今注》中就有許多這樣的例子。下舉數例。
(一)解“亢龍”爲“沆澤之龍”
《乾》卦上九爻辭“亢龍有悔”,“亢”之義爲極高、盈滿,《周易》多有戒人驕盈之意。所以《小象傳》說:“盈不可久。”謂上九在最上盈滿之位,盈則難久,所謂“物極必變”。不惟《乾》卦如此,各卦上爻皆含此義,故易家稱上爻爲“亢悔之地”。以是,歷史上易學諸家于“亢”字皆讀本字。而高亨以爲“亢”疑借爲“沆”,意謂大澤。他對“沆澤”作了冗長的考證,最後得出結論說:“亢龍者,爲池澤之龍也。池澤水淺而幅員或小,草多而泥淖或深。龍處其中,爲境所困之象也。人爲境所困,是爲有悔,故曰‘亢龍有悔’。”⑩按爻位之說,由初爻至上爻,本是步步升高,《乾》卦九五爻辭已說“飛龍在天”,不應天位之上更有“沆澤”!高亨不明爻位之說,也不信爻位之說,故有此種解釋。
(二)解“直方”爲“持方舟”
《坤》卦六二爻辭:“直,方,大,無不利。”按傳統的解釋,《坤》卦六二爻辭用來讚美大地之道至善至美的德行。大地之道,被概括爲三個字:“直,方,大。”直,可通于天;方,有法可循,大,無所不載。“不習無不利”,謂自然而然,莫之爲而爲,無往而不利。高亨斷句爲“直方,大不習,無不利”,釋“直”爲“持”,爲操,釋“方”爲“並舟”,“直方”爲“操方舟”。“方舟以渡,不易傾覆,雖甚不習于操舟之術,亦不致有隕越之虞”。(11)
(三)解“包蒙”爲“庖人矇”
《蒙》卦九二爻辭:“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按傳統的解釋,《蒙》卦九二之爻爲治“蒙”之主,面對初爻、三爻、四爻、五爻衆多陰爻,倫類不齊,而皆能包容之。故曰“包蒙”。九二以剛接柔,故曰“納婦”。此卦二至五爻互體有震,震爲長子,故曰“子克家”。高亨以“包蒙吉”之“吉”爲衍文。謂“庖人矇則厨事廢,爲子娶婦,則中饋有主,子亦有室,故曰包蒙,納婦吉,子克家”。(12)
(四)解“見金”爲“見奩金”
《蒙》卦六三爻辭:“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無攸利。”按傳統的解釋,六三陰爻爲蒙昧的“失位”女性,看見有錢的男人,不能自持,而失身于他。這樣的女人還是不娶爲好。在政治上,比喻不以正道進取,趨炎附勢,無操守之可言,引用這種人,對家、對國都没有好處。而高亨將此句斷爲“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無攸利”。他解釋說,筮遇此爻,不可娶女。娶女則但見奩金,而女之夫將有喪身之禍,無所利。高亨所謂之“奩金”,指女方所帶來的嫁妝資產,爲什麼夫婿見到這些“奩金”,就會有“喪身之禍”呢?殊無道理。
(五)解“幹父之蠱”爲匡正其父淫邪之妾
《蠱》卦初六爻辭說:“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按傳統的解釋,“幹”爲“矯正”、“革治”之義。“蠱”,物有蠹弊之謂。除蠹補弊,謂之“幹蠱”。亡父曰“考”。先父所定制度歷久而弊端叢生,子承家道,對蠹弊加于“矯正”、“革治”,可使先父無咎遇之責。高亨釋“蠱”爲女惑男。謂“幹父之蠱”,爲子匡正其父淫邪之妾。《蠱》卦九二爻辭中又有“幹母之蠱,不可貞”的話,高亨則謂子不可干涉其生母閨房之事。就是說,其父淫邪之妾可以匡正之,而自己的生母若有淫邪之行則不能匡正之。這如何又能說“有子,考無咎”呢?(13)
(六)解《咸》卦之“咸”爲以大斧斬物
《咸》卦卦辭:“咸,亨。利貞。取女吉。”按傳統的解釋,此卦爲男女相感之卦。咸,感也。其各爻爻辭中有“咸其拇”、“咸其腓”、“咸其股”、“咸其脢”、咸其輔、頰、舌”之語,謂男女愛悅相感,由淺而至深。高亨以爲,咸從戊從口。戊爲大斧,口爲物,以戊斬物爲咸。故《咸》卦六“咸”字皆作“斬傷”義。但《咸》九五爻辭:“咸其脢,無悔。”脢是背脊肉,爲什麼被斬背脊肉而無悔?上六爻辭:“咸其輔頰舌。”高亨改“舌”爲“吉”,爲什麼被斬面頰而吉?(14)
(七)解“明夷”作“鳴雉”
《易經》中有《明夷》卦,按傳統的說法,此卦坤上離下,離爲明,坤爲地,明入地下,是謂“明夷”,此卦六五爻辭說:“箕子之明夷,利貞。”是說箕子自晦其明以事商紂王,而內守貞正之道。高亨把“明夷”解釋成“鳴雉”,一種善于鳴叫的野雞,說箕子上山捕獲了一隻“鳴雉”。這種解釋不免太過離譜。(15)
三、對于兩個重要字的解釋
《周易》長期以來一直被看作占筮之書,故而當秦始皇實行“焚書坑儒”政策時,並未被置于焚禁之列。職是之故,《周易》的傳承在歷史上從未中斷。雖然後世儒者因學派不同,所傳之文本及章句或有异同,但在總體上各家《易經》文本有極大的趨同性,而對其中一些關鍵字的理解和解釋,也並未有很大的差异。比如對于《易經》中出現較多的“亨”字,除在個別語境下作“享祀”解外,在絕大多數的語境下作“亨通”之義解。至高亨則提出《易經》中的所有“亨”字,皆作“享祀”之義解。《易經》中的“孚”字在傳統的易學中皆作“誠信”之義解,而高亨則將大部份之“孚”字或作“俘虜”之義解,或作浮(罰)之義解。由于“亨”、“孚”在《易經》出現的次數頗多,所以影響了對整部《易經》的解釋。茲略述如下:
(一)關于“亨”字的解釋
《易經》中“亨”字甚多,傳統經學多以“亨通”解之。高亨提出,《易經》中所有“亨”字,皆作“享祀”解。據高亨統計,《易經》中有“元亨”字十一條,其中一條是《比》卦卦辭:“吉,原筮,元永貞無咎。”高亨以爲“元”下當有“亨”字,故也算一條。按:此屬增字解經,並無實據。今上海博物館所藏楚竹書《周易·比》卦卦辭:“備筮(16),元羕貞,亡咎。不寧方逨,後夫凶。”可證先秦古本《周易·比》卦卦辭“元”下並没有“亨”字。是《易經》中實有“元亨”字共十條。高亨解釋,元亨,猶云大享,凡云“元亨”,皆記古人大享之祭,或謂筮遇此卦可以舉行大享之祭。另有“小亨”字兩條,高亨解釋,小亨,猶云小享,凡云“小亨”,乃記古人舉行小享之祭,或謂可以舉行小享之祭。其餘單書一“亨”字者,共三十一條,其中三條繫于爻辭中,二十八條繫于卦辭中。高亨解釋,以上三十一條,亨字皆即享字,乃即古人舉行享祀,或謂可以舉行享祀。
按照高亨的說法,《易經》六十四卦中已經有四十一卦(除去繫于爻辭的三條)即三分之二的卦都被筮人判定可以舉行享祀了。那麼《易經》的整理者爲什麼要保留這樣一些記錄在《易經》中呢?高亨解說:
《周易》中言“亨”(或享)與“元亨”、“小亨”者甚多,以余觀之,皆記當時享祀之事。蓋古人尚迷信,敬鬼神,重祭祀。祭祀必筮(或卜),得吉而後行之。祭祀之前,筮得某卦爻,既得吉矣;祭祀之後,事實果無不吉矣。筮人從而記錄于當時所遇卦爻之下,即成爲卦爻辭之文句。《周易》中之亨字(或享字),其來歷蓋皆如此。(17)
古亨字,有亨、享、烹三義。高亨將《易經》中的“亨”字皆作“享祀”解,不免拘于一隅之見。《萃》卦“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卦辭兩言“亨”字,高亨解釋說:“古有王者,筮遇此卦,以舉行享祀,而至于廟,故記之曰亨……更有古人舉行享祀,筮遇此卦,故再記之曰亨。”(18)如果真像高亨所說的那樣,《易經》各卦中的“亨”字是古人享祀得吉的記錄,那無非表示後人當祭祀之時筮遇此卦,可以放心進行享祀活動。那在一卦中標示一次“亨”字已足,何必要標示兩次呢?《易經》文辭本甚簡古,此卦卦辭何以如此繁複?更何况將“亨”皆釋爲“享”,多有扞格不通之處。如《履》卦“履虎尾,不咥人,亨”。前言“履虎尾,不咥人”,後接“古人舉行享祀”,前後兩句,意思毫無關係,有似癡人說夢!又如《同人》卦“同人于野,亨”。高亨先釋“同人于野”爲田獵之事,田獵必在其野地。又說:“亨即享字,古人舉行享祀,曾筮遇此卦,故記之曰亨。”(19)既是田獵之事,怎麼又無端扯進享祀!又如,《否》卦初六,“拔茅茹以其匯。貞吉。亨”;“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凶。亨”;“六三,包羞”。高亨認爲,初六之“亨”當接六二之“包承”,釋爲“享包脀”;六二之“亨”當接六三之“包羞”,釋爲“享包羞”。(20)《大過》卦辭:“棟橈,利有攸往,亨。”高亨認爲,此“亨”字當在下文初六字之下,傳寫之誤。(21)高亨爲了將自己“亨”即“享祀”的意見說得圓通,不惜改經以就己說,凡此之類,乃爲解經之大忌。
(二)關于“孚”字的解釋
《易經》中“孚”字甚多,傳統經學皆作“誠信”解。高亨認爲,《易經》中僅《萃》卦六二爻辭“孚乃利用禴”、《升》卦九二爻辭“孚乃利用禴”、《兌》卦九二爻辭“孚兌吉”、《中孚》卦卦辭“中孚,豚魚吉”四處之“孚”爲“信”之義。其餘“孚”字,或作“俘”解,或作“浮”(“罰”)解。
今舉其釋“孚”爲“俘”之例:《比》卦初六爻辭:“有孚。比之無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按傳統的解釋,“比”的意思是親近。水與地親密無間,故名此卦爲“比”。此卦六爻中,唯九五爲陽爻,餘皆爲陰爻。衆陰爻多求欲九五親近。初六雖居位最下、最遠,亦求與九五親近。“有孚比之,無咎”,“孚”爲誠信之意。親比之道,原以誠信爲本。“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缶”爲樸素之器,不假文飾。“有孚盈缶”謂樸素之人,誠信充實于內,最終會使外人受到感動,而來找他,給他帶來好運氣。高亨認爲,“孚”即“俘”字,第一句,“有俘”,謂軍隊虜得敵方之人員財物。是“有孚”(通俘)專指一事。第二句,將“比”釋爲輔佐,臣輔其君,無咎。此又指一事。第三句,“有孚盈缶”,謂虜得敵方器物滿于盆中。第四句,“終來有它,吉”,高亨釋“來”作“未”,謂終無意外之患,故吉。爻辭中兩“孚”字既然皆作“俘”字解,卻又岔開作兩事說,那《易經》豈不是語無倫次嗎?(22)
《觀》卦卦辭:“盥而不薦,有孚顒若。”按傳統解釋,“盥”謂古代宗廟祭祀之始,盥手酌鬯郁于地以降神,其禮簡略,人皆盡其至誠之心、恭肅之意。薦爲獻牲之禮,禮數繁縟,人易生倦怠。《論語》載孔子之言曰:“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孚”爲誠信,“顒”爲虔敬。“有孚顒若”形容行盥禮者之虔誠莊嚴。“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喻王者居上臨民,當如宗廟祭祀行盥禮之時,盡其誠敬之心,以爲天下觀法。高亨將“孚”解釋爲“俘”。謂虜獲敵方之人員。顒,大貌。謂其人之大。祭不薦牲,乃因有俘,可殺之以代牲。高亨解《易經》之“孚”(俘)多有此類血腥味者。(23)
《易經》中的“孚”字有時與“心”字直接聯繫,表“誠信”之意甚爲明顯,高亨于此則將“心”字改爲“之”字。如《坎》卦卦辭,高亨釋讀如下:“習(疑衍)坎。有孚(俘)維心(之)。亨(享)。行有尚(賞)。”一個十字的卦辭,竟擬改五字之多!並說:《益》卦九五卦辭“有孚惠心”,“心”字亦“之”字之訛,可以互證。(24)亦彼之錯改,來證此之錯改,其方法亦令人驚愕!
再舉高亨釋“孚”爲“浮”(“罰”)之例:《泰》卦九三爻辭中有“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之語,按傳統的解釋,謂不恤一己之利害,盡誠信以輔君,其于食禄則有福益。高亨釋“孚”爲“浮”,再轉爲“罰”。謂筮遇此爻,勿憂其罰,乃在祭祀之時,受飲祭神餘酒之罰也。(25)然既是“祭祀之時受飲祭神餘酒”,怎麼又會稱“罰”呢?
近年傳統文化熱、儒學熱、國學熱大興,其中尤爲人們所熱衷者,乃在《周易》。而港臺新近又流行“八卦”一語,如“八卦新聞”之類,乃將“八卦”看作“亂說”之同義語,隱謂講《周易》者多胡說亂道也。考今之易學,無非兩類:一類爲江湖易學,一類爲學者易學。昔吾曾認爲,胡說亂道者,江湖易學也。學者易學,非胡說亂道者,學《易》當學學者之《易》。今讀高亨《周易古經今注》,豈非另一類之胡說亂道嗎?經學久廢,大道湮厄。吾批評高亨,非批評其一人,乃在批評此種誣經之學風,亦望學人重返經學之正途。此如孟子所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注释:
①高亨:《周易古經今注》(重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②《周易古經今注》,第24頁。
③《周易古經今注》,第10~11頁。
④《周易古經今注》,第45頁。
⑤同上,第10頁。
⑥同上。
⑦郭雍:《郭氏傳家易說》卷八,四庫全書本。
⑧李鏡池:《周易探源》,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第291頁。
⑨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古史辨》第一册,第80頁。
⑩高亨:《周易古經今注》,第164頁。
(11)同上,第167頁。
(12)同上,第174頁。
(13)參見高亨:《周易古經今注》,第215頁。
(14)同上,第249~251頁。
(15)同上,第263~267頁。
(16)以上參見《周易古經今注》,第110~111頁。
(17)《周易古經今注》,第48頁。
(18)同上,第288頁。
(19)同上,第200頁。
(20)參見《周易古經今注》,第196~197頁。
(21)參見《周易古經今注》,第239頁。
(22)同上,第184頁。
(23)同上,第219頁。
(24)同上,第242、281頁。
(25)同上,第193~19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