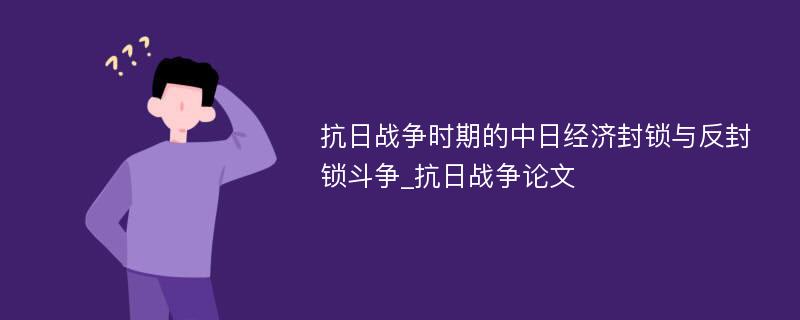
抗战时期中日经济封锁与反封锁斗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中日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现代战争中,对敌经济封锁和反封锁是壮大自己、削弱敌人的有利武器。抗日战争中,中日双方都实施了经济封锁与反封锁,各阶段策略互有变化,笔者拟对此做一些探讨。
一
日本对中国的封锁,经历了一个由武力到物资,由物资倾销到物资封锁的过程。
“八·一三”事变后,日驻上海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于8 月25日发表所谓“遮断航行”宣言,宣布封锁上海至华北沿海。9月5日,日海军部又宣布封锁我国全部海岸。1939年5月26日, 日海军部发言人宣称:“第三国在中国沿海之航行,一律实行封锁。”(注:常奥定《经济封锁与反封锁》,重庆1943年,第9—10页。)中国沿海交通断绝。
战争初期,日军迅速占领中国大片领土,日商异常兴奋,认为发财致富的大好时机到来,它们以三井、三菱为头领,组织“奥地取引组合”(内地出入商人联合会),在沦陷各地设立所谓“实业百货店”、“物资交换所”和“物资通济处”等机构,专门贩卖日货(注:张群《战地政治经济》,1940年,第51页。)。
随着中国沦陷区域的扩大,日寇在中国建立了五大走私据点:上海、天津、汉口、徐州和广州(注:陈介生《抗战以来敌寇对我经济侵略概况》,1940年,第42—43页。)。其余具体的走私据点,据报仅在沿海就有700处以上(注:顾翊群《经济封锁》, 《中央训练团讲词选录》第三册,国民党中执委训练委员会1941年印行,第419页。)。 日寇勾结奸商,从这些据点大肆向国统区走私日货。内运的日货可分为十类:1.纺织品类:棉纱、布匹、人造丝织品、呢绒等;2.食品类:面粉、米、谷、盐、碱、糖、海味等;3.日用品类:毛巾、牙刷、牙膏、肥皂、火柴、煤油、蜡烛、伞、瓷器、颜料等;4.文化用品类:钢笔、铅笔、油墨、橡皮、纸张等;5.消费品类:香烟、酒、玩具、照相器材、化妆品、滋补品等;6.五金百货类;7.工业用品类:机器零件、胶轮车胎、电器材料、电池、汽油等;8.肥料类;9.药品类;10.毒品类:鸦片、 吗啡、海洛因、红丸,高根等(注:参考陈介生《抗战以来敌寇对我经济侵略概况》第43页;中央调查统计局特种经济调查处(以下简称中统特调处)编《四年之倭寇经济侵略》,1941年,第145页; 《第五年之倭寇经济侵略》,1943年,第73页;何存厚《本省(福建)走私情况实录》(手稿),1939年;《陇海战区走私调查报告》(油印本),1941年;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湘桂办事处编《湘桂两省走私调查报告》(复写本),1942年;贸委会广东办事处编《广东省走私调查报告》(手稿),1942年;中统特调处编《甘宁绥三省走私概况》(油印本),1941年。)。日寇倾销的货物应有尽有,无所不包,但其中以奢侈消费品为大宗,民生必需品较少,工用和军用品更为罕见。
内运日货大多经过改头换面。为利倾销,日寇把大量货物廉价出售。尤为恶劣的是,日寇对倾销毒品更是不遗余力,贩毒成为日军的一项公共营业。走私商人每推销1两鸦片, 日寇便给数十元“奖励”(注:《闽南的走私问题》(湖南《开明日报》被扣稿件),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编《走私专辑》(中)(油印本)。)。日寇除明目张胆地贩毒以外,还以出售香烟为名,行贩卖毒品之实(注:顾翊群《经济封锁》,《中央训练团讲词选录》第三册,国民党中执委训练委员会1941年印行,第420页。)。更令人发指的是, 日人还以“帮助”中国人戒毒为幌子,大肆贩卖替代毒品。日东兴公司于1939年2月, 一次就向中国内地贩运进名为“东光剂”的“戒毒剂”(其一半成份为吗啡)1 万公斤,换取铜、铁、铝、钨、桐油等军用物资数千吨(注:钟山译《抗战时期日本以毒品换取中国内地战略物资史料》,《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4期。)。日寇的毒化政策由沦陷区延伸到了国统区。
这一阶段日本封锁中国沿海交通,走私倾销其廉价商品的目的在于,一方面阻止中国与第三国的贸易往来,妄图把中国变成它的独占市场,发展其本国工商业,实现其“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计划,阻碍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使中国在经济上成为它的附庸;另一方面,以其大量廉价的过剩商品向中国内地倾销,换取法币,以便向国统区诱购它所急需的战略物资,或把法币集中运往上海,在外汇黑市上套取法币外汇基金,再向英美等国购买军事物资,打击中国抗日力量。
面对日寇的经济掠夺,国民政府决定对敌实施经济封锁。
首先,颁布战时经济封锁法令。1938年1月20日, 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发布《国民经济绝交办法》,规定各地凡“八·一三”以后购买的日货,概予充公没收,作慰劳和救济用品,此后有再购日货或改充他国货者,以通敌论罪(注:千家驹《论经济反封锁》,《理论与实践》创刊号,1939年 4月。)。10月27日,国民政府颁布《查禁敌货条例》,规定敌货一律禁止进口及运销国内(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四编《战时建设》(三),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8年版,第379页。)。1939年6月23日,颁行《战时查获敌货处置及奖励办法》,规定查获的敌货分别予以拍卖、呈缴或焚毁,并规定各项奖励办法(注:浙江省政府及浙江国民抗敌自卫团总司令部行署编《对敌经济封锁法令汇编》,1940年,第63—64页。)。8月7日,颁布《防止水陆空私运特别物品进出口办法》,规定海关对于船、车、飞机及其它交通工具所载的特别物品的进出口,应按照禁运法令,分别查禁验放(注:国防最高委员会对敌经济封锁委员会编《现行有关对敌经济封锁法令汇编》,1941年,第4—7页。)。以上法令的颁行,使对敌经济封锁工作有法可依。
其次,健全对敌经济封锁机构。1940年1月, 财政部筹设各战区货运稽查处,分广东、广西,湘鄂、苏皖赣、闽浙、冀鲁豫、晋陕、甘宁绥等八区,由货运稽查处负责查缉私货运入工作。后为统一缉私起见,于1942年1月,将各区货运稽查处裁撤,改由海关接办。同月, 财政部设立缉私处,统一筹办全国缉私事宜。次年6月,改处为署, 下设编练、查缉、值讯、经理、总务、医务等6处,会计、统计2室,另设督察若干员,派赴各省。各省分处或办事处改称缉私处,于各走私要冲据点及各省缉私处驻在地设查缉处,到1942年底共设立129所,设分所404所(注:财政部缉私署编《十年之缉私》,中央信托局1943年版,第11页;童蒙正《关税概论》,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93页。)。
最后,国民政府不但严密地对敌实行经济封锁,还采取积极行动,打击日寇的毒化政策,令各战区所属部队及游击队,深入敌后,铲除罂粟。1942年,各部队在山东境内铲除840余亩,在安徽铲除20 余亩(注:曹骏《禁烟与抗战之关系》,健康日报社1942年版,第4—5页。)。
二
1941年后,日寇更侧重于经济封锁。2月, 日华北派遣军下达“长期战现地战略指导”,规定“在经济对策上要加强对敌经济封锁,制止有利于敌方的经济活动,破坏敌方的经济力量”。6月11日, 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命令日军要“加强对敌封锁,力图消耗敌战斗力”(注:日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7页。)。标志着日本开始放弃倾销政策, 对国统区厉行经济封锁。
1941年7月,英美相继宣布冻结中日资金, 日利用倾销商品换取法币套购外汇的方法失去效用。在此情势下,它的经济封锁政策更加强化。在华北,日寇配合所谓“治安肃正战”,通过华北“昭和16年度经济封锁并确保资源要领”,在其方针中明确规定:“调整经济封锁机构,发挥日华军队之综合力量,封锁境内山岳地带之匪区,防遏一切利敌物资之流出,以消灭敌人战斗力。”并规定了套购物资的原则,如第17条规定:“努力套购非占领区域之重要国防资源,但如由购买而获得时,则向敌区流出之交换物资,务须不致减低封锁效力。”第18条又规定:“交换物资尽量利用鸦片、化装品、果子酒、人造丝绢等不能增加敌战斗力及生活力之商品。”(注:中统特调处编《华北敌伪对我经济封锁概况》(油印本),1942年。)在都市和平原地带,日寇禁止下列物资流出:武器弹药、硫磺、印刷机、金属及其制品、医药品及其它有关军需物资。在山区,除上述物品外,电池、棉花、棉纱、米、麦、杂粮,织布、制丝等机器及印刷颜料也在禁止之列(注:国民党中执委训练委员会编《中国战时经济问题》,1943年,第125页。)。 日寇还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在天津,面粉、大米、小麦、大豆、玉米、香油、花生油、白糖、红糖、咸菜头、煤球、硬煤、烟煤、木炭、劈柴、煤油、火柴、蜡烛、布匹、棉花、鞋袜、肥皂、碱、毛巾、食盐、茶叶等27种日用品都实行配给。每人每天配给面粉1斤(儿童减半)、食盐每月14两, 煤油每户每日4 两(注:中统特调处编《华北敌伪对我经济封锁概况》(油印本),1942年。)。
在华中和东南地区,日伪组织所谓“清乡委员会”,负责经济封锁。日伪确定的禁运物资包括矿苗及金属材料制品、机械、棉、麻、茧、皮毛、漆、空瓶、蛋品、猪鬃、羽毛、肠衣、桐油、茶、煤等(注:刘耀荣《中日经济战》,新建设出版社1941年版,第61页。)。1943年3月11日,汪伪通过“战时物资移动取缔暂行条例”,规定苏、皖、 浙三省及宁沪二特别市,一切物品禁止运往“匪区”。下列物品的移动,需征得伪全国商业统制总会的许可。1.各种汽车及其零件;2.汽车用汽油及石油类;3.各种机械类;4.通信器具、材料(包括零件)及电池;5.金属(包括银元原材料、非铁金属及其制品);6.医药品(指医疗及工业用者,中药除外)及染料;7.橡皮及其制品;8.棉纱、布及其制品;9.蜡烛(包括原料);10.火柴;11.糖(注:汪伪物资统制审议总会编《物资统制法规》,1944年,第5—6页。)。9月18日, 日汪通过“扬子江下流清乡地域米粮封锁暂行办法”,规定供给敌方米粮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注:胡菊蓉等编《日汪的清乡》,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78页。)。
在日伪的封锁下,国统区物资供应遇到极大的困难。为应付这种局面,国民政府的对敌经济政策做了大幅度调整。1940年3月18日, 财政部、经济部联合颁布《进出口物品禁运准运项目及办法清表》,规定粮食、棉花、棉纱、棉布、钢铁、五金材料、机械工具、交通通讯电工器材、水泥、汽油、柴油、润滑油、医药及治疗器材、化学原料、农业除虫药剂、食盐、酒精、文化教育用品等,不问其来处,一律照普通货物验明,以奖励进口(注:国防最高委员会对敌经济封锁委员会编《现行有关对敌经济封锁法令汇编》,1941年,第42页。)。同年10月,经济部厘定特许进口物品14类,除上述物品外,增加麻袋,也不问来自何国何地,一律准予进口(注:常奥定《经济封锁与反封锁》,重庆1943年,第21—22页。)。1942年5月11日,财、 经两部拟定《战时管理进口出口贸易条例》,较前更为放宽,进口货物,不复以敌友为取舍标准,凡属军需用品、日用必需品及以前禁运的蚕丝、织品、呢料、印刷用纸、普通食物用具等,均予弛禁。但生活奢侈品、毒品和淫秽物品,绝对禁止进口(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二史馆)藏国民政府财政部档案309—重192。)。
国民政府还通过一系列法令,鼓励商人从敌占区抢运物资。1942年6月,行政院颁布了《战时争取物资办法大纲》, 规定公司行号抢运物资入后方,除汇兑、运输、沿途安全由国家及地方金融机关、运输统制局以及沿途军警予以种种便利外,并由中央信托局承保兵险,主管机关给予奖金(注:吴大明等主编《中国贸易年鉴》,1948年,第29页。)。还制定《奖励商人抢购办法》,规定做到下列之一者,给予奖励:1.所购物资属于经济部指定的抢购种类,有利于国防、军需或后方生产者;2.购运困难、风险很大者;3.在一定期间,购运价值达到规定奖励标准者;4.在一定时期内,购运数量达到规定标准者;5.供给情报,有功于经济作战者(注:《财政年鉴》三编(下),1948年,《物资》第54页。)。
为了切实加强抢运工作,国民政府于1943年4 月成立了货运管理局,掌管争取战时物资事宜,由戴笠负责领导。油类、机器、钢铁、五金、通讯器材、交通器材、化学原料、棉麻、毛织品、米谷粮食等21种物资,风险较大,利润较薄,商民抢运困难,由货运管理局组织抢运,其它物资由商民抢运。抢运最成功的物资为纱布,在长江下游,发动接近宁沪杭三角地带的商民,以土产、药材、桐油、柏油等换取沦陷区的纱布,总值不下20亿元。1944年衡阳之战后,东南各省与后方关系隔绝,货运管理局于10月抢购上海纱布6万匹。商行通济公司的抢购也很得力, 共抢购棉布5万余匹,棉纱600余件,基本解决了东南民众的穿衣问题(注:吴大明等主编《中国贸易年鉴》,1948年,第55—56页。)。
三
日本是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抗战爆发后,日本为支持战争,除加强对沦陷区的物资掠夺外,还千方百计地从国统区套购物资。每当新谷上市,日寇就“重价收购”(注:二史馆藏缉私署档案145—21841 (3),《财政部安徽缉私处代电快邮》(1943年9月24日)。), 用超过国统区4 倍以上的商价到处收购猪鬃(注:《中原的经济漏洞》(重庆《新蜀报》被扣稿件),《专私专辑》(上)。)。对于硬通货和法币,日寇也着力收买。
总之,日寇极注意吸纳各地物产,除粮食、油、牲畜、木材、炭薪、茶叶、药材、漆、蔗糖、樟脑、筍干、瓷器、苎麻、羽毛等生活必需品、各地特产,金银、法币等硬通货和货币外,钨、锡、锑、汞、铅、硝等特矿产品,铜元、废铜铁、棉花、桐油、猪鬃等战略物资,日寇都竭力诱购,对粮食、桐油、特矿产品更为注重(注:《第五年之倭寇经济侵略》,第73—77页。)。
为了遏制日寇套购物资,国民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法令。1938年8 月,修正公布《惩治汉奸条例》,规定凡通谋敌国,供给、贩卖或为敌购办运输军用品、粮食者,供给金钱资敌者,都以汉奸罪论,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注:常奥定《经济封锁与反封锁》,重庆1943年,第30页。)。10月6日,国民政府颁行《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 凡图利己或第三人,以原料和物品供给敌人者,或意图得利而向敌人泄露企业秘密者,处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注:常奥定《经济封锁与反封锁》,重庆1943年,第30页。)。10月27日,颁行《禁运资敌物品条例》,规定凡是国内物品足以增加敌人实力者,一律禁止运往敌国或其委任统治地;或已被敌人暴力控制的地区(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四编《战时建设》(三),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8年版,第382页。)。12月13日,发布《禁运资敌物品表》,禁运物品共计80余种,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可供军需使用的物资,如煤、盐、矿产等;一类是可供输出换取外汇的物资,如桐油、皮革、豆类等(注:吴大明等主编《中国贸易年鉴》,1948年,第28页。)。8月19日,颁布《禁运资敌物品区域表》,所有当时我国沦陷各地,均列为禁运资敌地区(注:浙江省政府及浙江国民抗敌自卫团总司令部行署编《对敌经济封锁法令汇编》,1940年,第76—78页。)。9月8日,通过《封锁敌区交通办法》,限制人民通过敌区,封锁区(线),严厉取缔禁运资敌物品外逸(注:国防最高委员会对敌经济封锁委员会编《现行有关对敌经济封锁法令汇编》,1941年,第122—124页。)。对敌禁运执行至1942年5月后有所松动,对敌裨益无多的物品可以运出, 以换取物资。
为图统一领导,切实加强对敌物资封锁起见,1940年2月24日, 国防最高委员会饬令成立对敌经济封锁委员会,擘划全面对敌经济封锁工作。该会严密监视走私资敌行径,在1942年的工作计划中,确定其调查目标包括各地的走私情形,如物品、种类、数量、路线、人物等,以谋对策(注:二史馆藏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43—292, 《对敌经济封锁委员会31年度工作计划》(1942年1月1日)。)。该会还在各地设立分会,为堵截物资外流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国民政府不仅查禁物资资敌,防止敌人套购,还组织人力积极抢购游击区物资,以防被敌利用。农本局负责抢运各种农产品,主要是粮食和棉花。贸易委员会的抢购范围更加广泛,江苏的丝茧,浙江的茶叶、桐油、丝茧、棉花、羊毛、蛋品,福建的茶、纸、水烟、糖,安徽的茶叶、桐油、苎麻、羽毛、猪鬃,江西的桐油、茶叶,湖南的桐油、猪鬃、茶叶,湖北的桐油、羊皮,河南的牛羊皮、桐油、蛋品,都在贸委会的抢购范围之内(注:张群《战地政治经济》,1940年,第75—76页。)。货运管理局的抢购范围则不仅仅局限于农产品,他们抢购豫皖区的交通器材,纱布、颜料、五金,广西区的橡胶、汽车、五金器材,广东区的颜料、橡胶、车胎、化学原料、五金,苏浙皖边区的花纱布、汽油、颜料、日用必需品、机器,福建区的五金、橡胶、汽车、燃料及日用品,湖北的棉花、土纱、 土布等(注: 吴大明等主编《中国贸易年鉴》,1948年,第55页。)。这些抢购行动抢回了大量物资,阻止了敌人的抢购势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统区的生活困难。
四
国民政府的对日经济封锁与反封锁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抗战前期,由于厉行查禁敌货工作,1938、1939两年国统区自日输入商品价值只占整个国统区进口价值的0.2%,1940、1941两年更下降到不足0.05%,1942年也仅占1.3%。国民政府实行进口不复以敌友为标准的政策后,日本向国统区的输出才逐渐回升,1943、1944两年分别占22.8%、14.4%(注: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171、191页。)。抗战后期的抢购工作也卓有成效,以货运管理局为例,该局从1943年4月成立,到1945年3月撤销为止,共抢购价值100亿元的物资, 商民抢购数量更数倍于此(注:《财政年鉴》三编(下),1948年,《物资》第54页。)。缉私工作也取得一定成绩,缉私署于1942年共缉获走私案件24748件,1943年上半年缉获22870件(注:《十年之缉私》,第23、21页。)。
但是,国民政府的对日本经济封锁和反封锁工作还存在着重大纰漏。抗战前期虽然自日进口值表面上下降,但日货走私一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止,据国防最高委员会致军事委员会函称,1939年度敌货输入超过3亿元(注:1940年4月29日《大公报》。)。而时人据可靠情报估计,更不止此数。在抗战前后的二三年内,日寇由平绥路以及黄河各渡口走私到察、绥、晋、陕、甘、宁等西北各省的货物,每年价值约3600万元。从广州湾、北海走私于华南的敌货,仅麻章、遂溪一路,每天就高达40万元,每年计约1.4亿元。此外从陇海路东段,宁沪路、 沪杭路与长江水道分散走私到苏、浙、鲁、皖、湘、赣等省,以及从广州、汕头、厦门分散走运至粤、桂、闽等省的敌货,合计年约2亿元。 综合以上各路敌货走私倾销的总额,每年在4 亿元以上(注:常奥定《经济封锁与反封锁》,重庆1943年,第32页。)。抗战后期日寇严禁民用必需品和军需工用品输入国统区,代之以人造丝织品,酒类,特别是其“特别优待之毒品”(注:《第五年之倭寇经济侵略》,第73页。),这些物品体积小,价值大,估计走私总额仍能维持前期的水平。
日寇自国统区套购的物资数量也极为惊人。1939年,在国统区出口的80万箱茶叶中,估计有1/4是走私出去的。桐油出口价值在1937年为8990万元,1938年骤减至3920万元,1939年更进一步下降到3360万元,造成出口大幅度下降的原因之一就是大量桐油被日寇套购(注:顾翊群《经济封锁》,《中央训练团讲词选录》第三册,国民党中执委训练委员会1941年印行,第423页。)。用以换取外汇的重要特矿产品钨、 锡、汞、锑等,据保守估计,八年抗战当中分别被敌套购钨2000 吨、 锡20190吨、汞410吨、锑7417吨,共价值3128万多美元(汞因国际市价不明未计在内)(注:唐凌《抗战时期的特矿走私》, 《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粮食、棉花、猪鬃等物资流失数量更为巨大, 难以估计。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在经济上困死中国抵抗力量,它封锁中国海岸,大肆贩卖毒品,煽起国统区奸商走私的狂潮,无不从此目的出发。日寇是走私套购的发动源。同时,国民政府自身存在的弱点,也是这种局面难以扭转的重要原因。它虽然颁布了许多对敌经济封锁与反封锁的法令,但往往徒具空文,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不能传达到社会的基层。具体操作上缺乏弹性,在抗战前期,对敌货采取一刀切的政策,一律不准进品,主要是担心敌人售货结款套取外汇,但同时却又顾及英美利益,在上海无谓地维持外汇黑市,拿大量宝贵的外汇填黑市这个无底洞,给日伪以可乘之机。据估计,从1938年6 月至1940年5月,日寇套取的法币外汇在2亿元左右(注:寒芷《战后上海的金融》,香港金融出版社1941年版,第14页。)。巨额的物资和外汇给敌人起了“输血”的作用,延长了日寇负隅顽抗的时间。等到宣布不限有利于抗战的敌伪物资输入,为时已晚,日伪已抢先一步,对国统区实行经济封锁,给后期的抗战造成很大的困难。
大量敌货,特别是奢侈品和毒品渗入国统区,以及大量战略物资从国统区运到沦陷区,与国民政府公职人员的腐败是分不开的。连蒋介石都承认,“凡是在财政、金融、交通、经济各界服务的,一般社会人士,……总以为我们是官僚,是贪污的”(注:蒋介石《抗战建国中交通财政经济金融人员之职责》,国民党中央秘书处文化驿站部管理处1943年印行,第7页。)。执法人员知法犯法,护私、包私、运私, 甚至亲自参与走私,连为国家柱石的军队也操起走私的营生,这在当时是普遍的现象、公开的秘密。走私屡禁不止,国府公职人员是难辞其咎的,也必然会使对日经济封锁与反封锁的效力大打折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