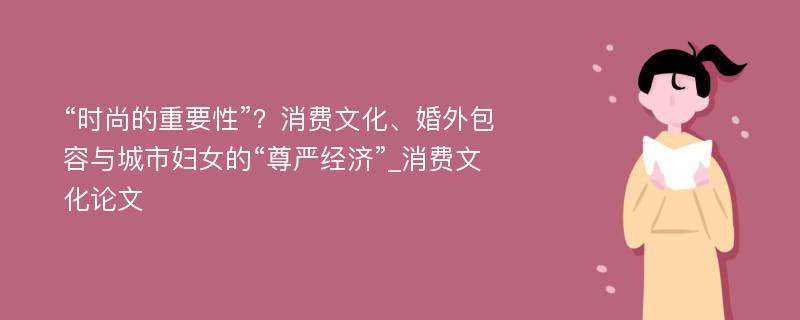
“时尚的重要性”?——消费文化、婚外包养与都市女性的“尊严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包养论文,重要性论文,尊严论文,都市女性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15)05-0029-10 广州初夏一个闷热的下午,我和Lucy相约一起做头发。等我大汗淋漓地赶到美发店,Lucy已经等得快不耐烦了。我跟她解释说公交车不准点,她用带着浓重广东口音的普通话“教育”我:“我叫你打车的嘛。看你出这么多汗,很没样子,省这点小钱做什么呢?”我抱歉地笑笑,拉着她一起讨论发型。她准备将大波浪拉直,留了三个多月了,想换造型,建议我烫成小卷——时下最流行的发型。听到我在260元的韩国烫发水和150元的国产烫发水之间选了后者,Lucy立马和发型师插话说:“不要,给她用韩国的。”接着转过头来继续“教育”我:“你怎么会选那个(国产的烫发水)呢?没省多少钱,但是对你的头发不好。”我没有坚持,尽管对这两种烫发水到底会有多大的差别心存怀疑,但到埋单的时候,我只需要付国产烫发水的价钱,而Lucy分文未付。看我疑惑不解,Lucy向我解释,美发店老板是她的前男友,他们分手之后还是朋友。 Lucy,26岁,广州本地人。三年前与一位香港已婚的建筑师在一起后便不再工作,由男友供养,成为人们通常所说的“二奶”。她在广州的日子看起来光鲜惬意,在市中心租住了一套一居室,出门就打车;用雅诗兰黛和迪奥的化妆品,背LV包包,挂Gucci的手机链;每日与朋友们出入咖啡厅和酒吧,定期去香港购物,到各地旅游。 Lucy是我访谈的处于包养关系中的广州本地女性中的一例。和Lucy一样,她们大多时尚靓丽,追求有品位高消费的生活。通过深描和分析城市女性进入、维系(以及计划离开)包养关系的过程与策略,本文将探讨她们对时尚消费和亲密感情追求中的矛盾和冲突,并进一步阐释消费文化、本土性别观念和社会网络如何互相交织,形塑她们的身份认同、群体归属与亲密关系选择。 市场改革以来,中国的城市社会经历了一场消费革命,各种此前闻所未闻、甚至无从想象的商品和服务都被引入国内市场[1]。在大众传媒、公司广告的推动下,消费文化日益兴起,重新建构着关于现代生活方式和社会身份的想象。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帮助新兴的中产阶级自我定位为全球资本主义空间中老练的“公民—消费者”[2]。昂贵的奢侈品和休闲活动向市场改革中崛起的经济精英们推销着一种值得渴望的生活方式,并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3][4][5]。社会地位较低的低收入群体也不遗余力地按照新标准消费。一些研究表明,消费为那些在新的社会秩序中对自身的位置缺乏安全感的群体,如农民工,提供了一种融入城市文化并获得现代身份的感受①[6][7][8]。 正如社会学家指出,消费除了满足个体的需求之外,有着重要的社会和情感意义,对于消费行为的理解必须放到具体的社会文化情境中进行理解。一些学者指出,消费往往是一种寻求竞争性身份地位的行为,比如托斯丹·邦德·凡勃伦(Thorstein B.Veblen)在关于“炫耀性消费”的经典阐述中谈到,人们消费特定的物品是为了显示出“高人一等”的地位,从而获得他人的艳羡或重视[9]。消费不仅是一种“区隔人群”的重要形式,同时也是建立人际纽带的途径。人们往往通过为他人购买和赠送商品来表达关心和爱意,从而建立和维系社会关系[10]。在消费主义日益兴盛的今天,情感的表达已经越来越被市场所主导,已经形成某种高度依赖于商品的“爱的物质文化”[11][12]。一些新近的研究指出,消费日益成为在社会群体中确立成员身份、获得认可和归属的重要方式。很多时候,人们购买特定的物品或服务与其说为了获得让令人艳羡的优越感,不如说更多为了获得他人的承认和尊重,以享有社会交往的平等机会。比如,社会学家阿里森·普赫(Allison Pugh)通过对儿童消费文化的研究提出“尊严经济”(economy of dignity)的概念,意指确认个体是否有资格参与群体活动并从中获得认可和归属感的社会意义系统。普赫发现,流行的玩具和消费经验构成了儿童之间社会交往的重要话题,即儿童“尊严经济”的重要筹码,如果缺乏被群体认可的消费经验,就容易被排除在群体生活之外,难以获得同伴的认可和群体归属感[13]。 本文借鉴普赫的“尊严经济”的概念,强调消费行为与个体尊严和群体归属之间的重要关联,着重阐述时尚消费对城市女性的身份认同和社会生活的形塑,并分析在剧烈的社会流动中维持特定的身份和群体归属对这些女性的特殊意义。文章还将深入描绘女性消费文化与亲密关系的勾连,并嵌入中国市场转型期的性别秩序中展开讨论。市场改革以来,本质主义的性别文化兴起,男女之间性别分工和差异的“自然化”得到了空前的强调,女性的身体、外貌和角色在消费文化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被视为一种不可多得的资源,使女性身体走向商品化、客体化的消费时尚[14],消费女性也成为新贵群体进行成员选择和结盟的重要手段[15]。与商业化的性消费相比,拥有情人则更能彰显男人魅力和社会地位,因为“不用直接和赤裸裸的付钱而能吸引到漂亮女人的能力无疑是对其男人味和社会地位的终极证明”[16]。与此同时,在亲密关系中,性别分化也进一步彰显。一方面,由于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性别歧视,使得女性作为一个群体在市场中往往缺乏获得物质资源的平等机会,很多女性的消费能力要高度依赖亲密关系中男伴的经济水平;另一方面,男性对于女性的供养被建构成情感表达的重要因素,在亲密关系中男性满足女性的物质要求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荣耀的。在消费文化和性别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对于缺乏市场机会、来自中下阶层家庭的城市女性而言,与有钱男性的婚外亲密关系不仅使她们能够实现心神向往的现代都市女性身份,而且帮助她们获得和维系有尊严的社会生活。 本文的分析主要基于笔者于2005年9月至2006年8月以及2007年6月、8月在广州和宁波进行的关于婚外包养的田野调查。笔者对婚外包养的界定采取“社会生成”的方式,即由知情者给我介绍他们认为的处于婚外包养关系的当事人,然后分析这些关系的特点,由此总结婚外包养的通常理解。本研究收集到的个案具有三方面的相似性:(1)相对长期的同居关系,往往有固定的共同居所;(2)同居关系中一方为已婚男性;(3)另一方为男方合法配偶外的女性,并在经济上由男方供养。笔者对16位在包养关系中的女性(即俗称的“二奶”)进行了多次深度访谈,到受访者家串门,并参加她们的日常娱乐和社交活动(比如朋友聚会、泡吧、唱卡拉OK、逛街、美容美发)。其中7人是广州本地人,多数为初中或高中学历,她们的男伴多为生意人或高级白领,其余9位是外地女性,为寻求工作机会来到广州或宁波。本文的分析以广州本地女性的生活经历为主②。为保护受访者,文中出现的人名均为化名③。笔者从受访者主体视角出发,通过情景化(contexualized)的方式阐释婚外包养关系对城市中下层女性的意义,将其个体选择嵌入具体的社会情境中进行分析,透视城市女性的亲密关系与其人生轨迹和社会生活的勾连④。为了更好地展示社会情境对个体生命的影响,下文将深描Lucy的案例并辅以来自其他受访者的材料,来对相关议题进行阐释和分析。 二、通过消费维系自我认同和群体归属 Lucy生长在一个工薪阶层的家庭,父母在她上小学的时候离异,她跟母亲和外祖母一起生活。18岁时,Lucy交了第一个男朋友,比她大两岁,是做生意的,两人感情发展顺利,并有结婚打算。在交往的五年多里,Lucy不再工作,由男友供养。后来男友生意失败,提出分手。“他觉得我会拖累他……那个时候他也认识了另外一个女孩子。”回忆往事,Lucy依旧感到委屈。 分手后,Lucy去了深圳,在朋友的帮助下开了一个饰品店,但生意不好,不得不继续依靠朋友给她介绍的追求者所提供的经济支持来维持生活。直到半年后遇到她的现任男友——一个已婚的香港建筑师。“我不喜欢他”,Lucy坦言,“但我需要有人照顾我”。关系确立后,Lucy关了店铺,回到广州,男友给的每月10000块钱左右的生活费,够她基本的日常开销,包括租房、打车、和朋友外出吃饭、泡酒吧和咖啡店。 这三年间,Lucy也曾尝试找过一些工作,她有高中文化,学过一些平面设计,朋友给她介绍一些办公室文员的工作,月薪在2000元-2500元,但每份工作都干不过一个月,用她朋友的话说:“一个月挣的还不够她逛街一次花的呢。” 作为时尚美女,Lucy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她说:“对女生来说,样子是最重要的。好的样子让你感觉很好。”对她而言,“美丽的女性形象”首先意味着通过消费生产出白皙的皮肤、精致的妆容和性感的身材。为此她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每天出门前化妆1-2个小时,每周做一次美容,每年至少换两三次发型;她还花了1万块钱隆鼻,并考虑去做个腹部抽脂手术。正如女性主义学者苏珊·波多(Susan Bordo)指出,受市场利益驱动的各种流行广告和商业形象已经重新定义了女性身体的“正常状态”,并通过建构女性的主体性来发挥作用[17]。在市场改革时期的中国,外貌被认为是“自然”的女性特质,构成了女性“自我认同”的重要部分[18]。美容产业的兴起极力向大众传达了这样一种文化信息:美丽的外表并不是那些天生丽质的人所独有的,相反,任何一个认真对待并尽力表现其女性魅力的人都可以获得。其次,“美丽的女性形象”也是一种通过消费对自身社会地位和文化品位的展现。Lucy相信名牌,对此知之甚多。她相信使用名牌可以使人看起来更“高级”,也更“漂亮”。因此,对品牌和时尚的了如指掌和恰当使用也是她保持理想外表的关键。为了跟上最新的时尚动态,Lucy会定期(一般每月一次)去香港逛街,并经常更新衣柜和化妆品。 身体是Lucy需要进行投资的一项资产,以保持对男人的吸引力。她越是性感时尚,就有越多的男性追求,得到男人们的喜爱和追求是其女性魅力的重要体现。与此同时,保持对男性的吸引力也有工具性的意义,便于建立亲密关系以获得经济上的资助。 更为重要的是,时尚的物品和生活方式是Lucy维系自己在朋友圈子里的身份地位的重要凭证。Lucy的闺蜜们是一群在广州土生土长(或小时候就随家人搬来广州)的女孩子。她们年轻漂亮,装扮新潮,在一起只说粤语。Lucy与她们相识很久,有几个一起长大,有几个是上学时候的朋友,还有几个通过彼此的朋友相识。她们中除了个别自己做生意,大多依赖男友供养(一些是正牌男友,另一些则跟Lucy的情况类似)。Lucy告诉我,与闺蜜们相比,她算“过得很惨”了。她们中有人在二沙岛(广州最昂贵的居住区之一)拥有一套别墅,有人开雷克萨斯或奔驰,还有人把刚过季的普拉达(Prada)手提包送给家里的保姆了。和女友们在一起聊天的最主要话题就是美容、新款的名牌包、衣服、化妆品以及男人。Lucy说:“如果你什么都不懂,她们会觉得你很没意思,懒得理你了。”Lucy还记得一次一个朋友背了个当地品牌的手提包去聚会,被女伴们奚落了好一阵,“大家问她是不是刚从农村回来”。 换而言之,在Lucy生活的成人世界里,时尚消费是其“尊严经济”——确认个体是否有资格参与群体活动并获得认可的社会意义系统[13]——的重要筹码,用以维系社交活动和群体认可。对Lucy而言,使用品牌化妆品、奢侈品牌的包包以及参加各种昂贵的消费服务与其说是为了彰显“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不如说更多地是为了获得同伴的认可和接纳,维系在原有社会网络中的成员身份,避免被朋友圈子边缘化或排斥⑤。在市场改革带来的阶层结构的巨大变迁中,消费已经成为人群分化的重要标志。社会阶层的剧烈分化使得人们对自身地位产生了高度不确定和不安全感。通过消费跟上主流推崇的生活方式,维系与原有社会群体的连接与其说是为了获得向上流动,不如说是为了避免遭遇向下流动的尴尬境地。Lucy极力避免因经济匮乏而无法维系原有的生活方式,因“消费不足”而与原有的社会网络脱节——这将使她陷入向下社会流动的危机体验⑥。 与Lucy相似,受访的其他广州本地女性进入包养关系多是长期由男性提供经济支持的一个延续。这些女性大多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从20岁左右就开始没有固定工作,成为全职女友或者全职太太,他们在恋爱或者婚姻关系破裂的时候可能短期从事比如服务员之类的工作,但是很快会进入另外一段关系,继续由男性供养。对这些女性而言,进入稳定的、有婚姻期待的两性关系是最佳选择。然而,随着社会分层的加剧,并不是每个(单身)男性都有能力供养并支持她们的消费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与经济稳定的、已婚男性的亲密关系只是她们连续性的、由男伴供养的恋爱关系中的一段,是未能遇到结婚对象时“退而求其次”的权宜之计。 一些受访者也曾梦想自己赚钱过上好日子,如阿菲,“我想找赚钱的工作,没学历啊。我想做生意,没钱投资啊”。这些广州本地女性没有人拥有高中以上学历,她们本身的家庭也不富裕。尽管与许多我访谈的外地打工妹相比,她们可以依赖社会关系找到更高收入的工作,但远远无法支持她们为维系原有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所需要的消费水平。 三、包养关系中的交易与尊严 在当地盛行的性别观念中,亲密关系中男性对女性的供养备受鼓励和推崇:男人供养女人不仅是自然的,甚至是合理的。受访女性身边的不少女性朋友、亲戚和熟人都是靠男人养活的,不一定作为二奶,而是正牌的妻子或女朋友。对于这些女性而言,被男人养着没有什么问题,差别只是在于是否(有可能)结婚,而能不能遇到理想的结婚对象很大程度上倚赖“命数”。比如阿雪的妹妹嫁了一个本地人,妹夫近年来生意越做越好,钱赚得越来越多;因而妹妹过上了闲适的生活,每天喝茶、逛街、打麻将。对比妹妹的“好命”,阿雪说:“我的命不好,我的第一个(男人)是嗨药(即吸毒)的。”然而,与受法律和社会习俗保护的婚姻关系不同,婚外包养关系对于男性的行为几乎没有社会约束,而女性需要运用各种策略如甜言蜜语、额外的“情感劳动”等实现自己的需求。 凭借男友每月给她的生活费,Lucy在广州的日子还不错,但对于她想要购买的奢侈品而言,这些钱是不够的。因此,Lucy需要想办法向男友讨要更多财物。她说: 香港人很虚伪的,你接触多了就了解了,嘴巴上很好听的,但是不会去做的。他说:我很爱你啊,我想给很多的钱你啊。但是,我现在很穷啊,没钱啊,我没能力啊。其实他有钱的,就是不想给,还装出可怜的样子。(怎么知道他有钱?)他过几天就给自己买东西了,什么枪啊,衣服啊。 Lucy从男友处得到的金钱数额并不是严格固定的。男友每次来找她的时候都会给她几千元,具体数额同Lucy的需求有关,因此,找到让男友觉得合理的理由很关键。相处三年来,Lucy发现,相比于购买奢侈品,男友更愿意为一些实际的需求买单,如安装和更换家庭设施、支付医疗费用以及给家人购买生日礼物。因此,Lucy会编些故事来向她的男友要钱,比如亲戚过生日或家里某个电器坏了。“但这种借口不能用多了”,她说,“他会怀疑的”。而节假日、生日以及周年纪念日则是Lucy向男友讨要贵重礼物——尤其是她想要的奢侈品——的重要时机。 对于男友口头表达的爱意,Lucy并不全然相信;甜言蜜语仅仅是为了得到她的忠诚,但她借机向他提出各种物质方面的要求,以作为爱的证明。为了向男友表明她的要求是合理的,她常常向他展示女友们从男友处获赠的礼物,Lucy说道:“我跟他说贝贝生日的时候,她老公送了她一辆雷克萨斯。我说我知道你钱没那么多,你给我买个浪琴的手表好不好?”Lucy深谙“爱的物质文化”[12],通过强调礼物交换的情感意义和圈内行情,Lucy促使男友用物质来“兑现”他的爱;对照那些更为富有的朋友,她将自己的物质诉求表述得合情合理。 不仅如此,Lucy还通过付出额外的情感劳动“挣得”物质回馈。在婚外包养关系中,被包养的女性一般来说都会从事大量的情感劳动,忍受情绪暴力、压抑负面情绪或迎合对方需求,以使男友在家中感到放松、受到遵从并获得良好的自我感觉[19]。然而,当Lucy期待得到一份昂贵的礼物时,她会花费额外的力气来讨好男友。例如,在她生日的前一个月,Lucy向我多次抱怨男友最近如何恶劣地对待她。她说:“要不是他答应给我买LV包包做生日礼物,我才不忍他呢!” 与其他处于包养关系中的女性(尤其外地打工妹)相比,Lucy对自身感情的工具性使用最为纯熟。一次我同Lucy一起吃火锅闲聊,她向我列数了近期她从男友处得到的昂贵礼物。正为自己的聪明和伎俩得意之时,她突然说道:“大家都有付出嘛,其实我付出的更多。他付出的是钱,我付出的是青春啊。虽然他管不到我,但是每个月要见两三次的,要陪他。” Lucy试图用这种公平交易的逻辑告诉我,她得到的是对其付出的合理回报。她既不是不劳而获,也不是靠色相骗取男人钱财的女人,她仅仅是亲密关系游戏中的一个诚实玩家。公平交易逻辑帮助Lucy合理化了她目前的亲密关系处境:男友从她这里获得身体和情感上的愉悦,她以此换得经济上的实利。在很大程度上,她有意识地商品化了身体和感情,将它们当作通过投资能够产生经济利益的“资本”。但为此她也不得不付出不小的代价,比如失去对情绪的掌控能力。Lucy说:“我以前脾气还可以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坏了,Betty她们也这么说,很容易着急,生气,都是被他害的。我有的时候真的是很气啊,这里很难受(捂胸口),闷得厉害,还要忍他。” 尽管Lucy有意识地通过情感上的付出获得经济上的补偿,但她拒绝一味隐忍受气,并积极捍卫自己作为“女朋友”的情感底线和权利。当男友表现得过分粗鲁或不可理喻的时候,她会作出反击。比如,有天晚上,Lucy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大家玩得正高兴,Lucy的男友打电话过来,得知女友在酒吧后,开始发脾气。Lucy下楼哄了他40多分钟,对方依旧不依不饶,Lucy决定不再忍受: 他跟我说:我很不喜欢我的女朋友泡吧;我很不喜欢我的女朋友喝酒;我很不喜欢我的女朋友喝醉;我很不喜欢我的女朋友跟其他男仔玩。我说:这就是我喜欢的生活方式啊。他说:那说明我们两个不合适在一起。我说:是啊。他气得要命。后来我就跟他讲: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要进去了,他们在等我了,就把电话给盖(挂)了。他气死了。 “我不是他的佣人”,Lucy解释道,“他说他喜欢我,很爱我,那他怎么会这么对我呢?”Lucy的爆发不仅意在提醒她的男友,他在情感上所求过多付出太少,并再次强调了他们之间亲密关系的界限,其中包含了一定程度的彼此尊重和情感上的相互付出。虽然很多时候为了维持这段关系,Lucy不得不在事后为自己的“冲动”而向男友道歉,但也有时候她的“反击”则帮助她成功地把握了关系的主动权——包括那次在酒吧挂了男友电话。几天后,她的男友打电话向她道歉,并提出送她一盒高档化妆品以表达歉意。成功的反击不仅使Lucy填补了情感赤字,还给她带来了物质利益。对此,Lucy如此认识,“男人很贱的,他们觉得太容易得到了,就没有兴趣了”。 除此之外,Lucy还要求男友对她保持忠诚,不能约会其他女性,只要发现他勾搭女生的蛛丝马迹,她就会提出抗议。一次,男友来广州看望她时,一个深圳女人给他打了很多电话,发了很多短信。Lucy怀疑两人有瓜葛,于是生气地对她男友说,如果他爱她,那就不要和其他女人通电话。尽管男友并不心甘情愿,但为了证明他的忠诚和体贴,还是照做了。 在分享了击退潜在竞争者的成功经验后,Lucy提醒我说:“我不是因为我喜欢他而生气,而是我觉得我配他多了,还要啃他(忍受他),他还扣女(泡妞)。”Lucy将男友对她的忠诚视为自我价值的一种确认:作为年轻漂亮的都市女性,她在亲密关系市场中具有较高价值,爱和忠诚是亲密关系中地位较低的一方给予地位较高的一方的回报。与此同时,积极要求男友在情感和性关系上的忠诚也是Lucy将自己所处的亲密关系与交易性性关系区分开来的重要方式,帮助她确认和维护自己在这段不受法律和社会习俗保护的关系中的权利和地位。 在受访的广州本地女性中,Lucy是其中最善于在亲密关系中争取经济和情感“利益”的一位,对待亲密关系更类似于在进行一场公平交易的市场游戏。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Lucy对其男友的浪漫情感的投入是最少的。其他受访女性与男伴的情感依恋程度各有不同,但也会采取各种不同的议价策略,比如,每月应该得到的金钱数额,应得的礼物,男友陪伴她们的时间以及情感付出。这些城市女性对于如何在亲密关系中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表现得积极而富于策略,她们在亲密关系中的谈判优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们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而有效的支持网络对城市女性在包养关系中占据主动是至关重要的。 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女性处于单纯的市场契约和家庭契约之外的亲密关系中⑦,在矛盾冲突的性话语和性伦理中建构自身生活的意义。对于包养关系中的城市女性而言,她们对于包养关系的总体性认知趋于类婚姻/恋爱关系,以区分于单纯的钱色交易。男性提供的金钱和物质被赋予了重要的情感意义:男伴提供共同的居所代表了一种稳定关系的承诺,每月的供给是对她们的生活照顾,礼物则是表达爱意的重要符号;她们也就男性的情感付出有所要求,寻求经济供给与情感付出之间的相对平衡。与此同时,一些女性也借用“公平交易”和“个体选择”的市场逻辑,一定程度上将包养关系工具化和去感情化,摆脱家庭伦理对她们性/情感忠贞的束缚,在缺乏制度性保护、地位不对等的包养关系中寻求更多的主动性和安全感。 四、包养关系之外的社会支持网络 因为男友一般每月只过来两个周末,Lucy有大把的时间自己打发。她的一天通常是这样度过的:睡到中午,随便在家吃个午饭,比如下碗方面便,然后打一圈电话,约上几个闺蜜购物或做美容,之后再去咖啡店小坐聊天。傍晚和朋友们相约晚饭,晚饭后,再和另一群朋友一起去酒吧或卡拉OK。 在与闺蜜们的下午聚会中,她们分享各种最新的时尚资讯以及美容小诀窍。比如,一个朋友告诉Lucy,用蓝色睫毛膏可以使眼睛看起来更明亮动人。如果有人刚去过日本或香港的话,则会将她们了解到的信息广而告之。她们还互相交流对付男人的经验和技巧,比如,如何保持对男人的吸引力,如何让男人出钱给她们买她们想要的昂贵商品,男人的某些行为代表什么,等等。 除了交流各种技巧诀窍,Lucy还从女友们那里得到情感支持,比如,当她和男友吵架、受气的时候,她最好的朋友会安慰她。此外,她的不少女友——尤其是那些同样要在经济上依赖男人的朋友——往往也需要对她们的男友进行“情感劳动”,忍气吞声或刻意讨好。她们聚在一起时,会纷纷抱怨她们的男友,并为彼此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鸣不平。她们会用贬损的语言来称呼她们的男友,比如把他叫做“傻閪(hai)”(即“傻B”“白痴”),抖露男友的丑事,炫耀自己背着他“扣仔”(“找其他男人”),以此宣示自己对男友的某种象征性胜利。通过这种“集体泄愤”的仪式,Lucy释放了她在情感付出上不对等的包养关系中遭受的某些苦痛和委屈。 除了闺蜜圈,Lucy在广州还有很多朋友和熟人,其中大部分也都是广州本地人。她每天出入各种咖啡馆、餐厅、酒吧和夜总会,进一步拓展了她的社交圈,为她的生存提供了重要保障。每当她与男友吵架,男友暂时中断对她的经济支持的时候,她可以向朋友们借钱或通过朋友介绍工作来维持生活⑧。 其他六位广州本地女性也都有类似的支持网络。和Lucy一样,她们通常都有一群闺蜜以及从小建立起来的社交关系网,这是她们物质和情感支持的重要来源。住在广州市郊的四位离异妇女在十几岁时便成了朋友,十多年来她们依然通过不同的方式互相支持。在调研期间,这四位女性都由已婚男人供养。她们几乎每天呆在一起,搓麻将、购物、吃饭、去酒吧、去卡拉OK唱歌,还一起外出旅游。阿菲每天醒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阿雪讨论那一天她们想要做什么。当她为同男友的关系感到烦恼的时候,她就会打电话给其他三人来寻求安慰或建议。她说:“跟她们说也没什么用,心理感觉好点。” 这些住在广州市郊的女人们也都受益于一个由亲戚和熟人所构成的社会关系网。阿婉是这四个二奶中经济来源最不稳定的一个,她的男友是当地一家建筑公司的工头。由于只有在工程结束后才能拿钱,有时他会没钱给阿婉。在缺钱的时候,阿婉就会请亲戚朋友给她介绍工作,在男友挣到钱后,她再把工作辞掉。我在广州做调研的那一年中,阿婉做过两份临时工,其中的一份工作是在她朋友开的夜总会里当部长,另一份工作则是她阿姨介绍的,在广东本地的一家流行服饰店做收银员,但每份工作她都没干满两个月。 这些广州本地女性所建立和维系的社会关系网给她们带来了应急的物质资源,给予她们情感和精神上的支持,帮助她们度过亲密关系中的“不稳定期”。这些女性所积累的社会资本也使她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在某个时刻决定是否要中断这段关系。 五、对未来的打算:向往婚姻 一天晚上,我陪Lucy回她的公寓去拿两本她向我推荐的书。知道我研究亲密关系,她建议我读一下张小娴的书,这位香港作家对两性关系有着深刻的洞见。在开门前,她提醒我房间很乱,因为她已经有好几天没有打扫了。她将堆放在米色长沙发上的衣服推至一边,给我腾出坐的地方,然后快速清理了茶几上的一个吃剩的面碗。“中午吃的,我懒得收拾”,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你是个女的,所以被你看见也没关系”。 她给我拿来了张小娴的书,大声地朗读了其中她最喜欢的一篇文章《将来的那个人》: 想知道自己是否爱一个人,只要想象一下,当他年老,卧病在床的时候,你愿意照顾他吗?想到他老病的时候,你已经有些沮丧,那么,他决不是能够跟你厮守的人……当你年老,病在床上的时候,你也愿意由他来照顾你吗?只要他在,你就放心了。那么,他是你寻觅的人。你只希望他是来探病的朋友,而不是夜里抱你上厕所的人呢,那么,你要找的人,不是他。在最软弱的时候,你会想念的那个人;在那个人最软弱的时候,你会怜惜的,你们才是彼此将来的那个人。 Lucy似乎就是用这篇文章的观点来检视她对男人的真实感受的。她向我袒露了之前有一位条件不错的追求者,而且单身,“我不喜欢他,就是拿他解闷的,一起玩。但是他要是生病了,我肯定马上就会逃开;如果我老了,我也不会愿意是他抱我去上厕所。所以我觉得自己肯定不喜欢他,后来就分手了”。 Lucy26岁了,家人已经开始催促她快点结婚稳定下来。她向家人隐瞒了她同香港男人的关系,只是告诉他们交了一个男朋友,但不够结婚对象的条件。为了安抚家人同时避免成为剩女,Lucy设定了一个目标,要在28岁之前结婚。问及对另一半的要求,她说了三条:合眼缘/有感觉、对她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Lucy说:“我要求很低的,有房有车,每个月可以收两万就可以了。”2005年,广州城市居民的人均年收入是18287元,这个“很低”的要求超过了90%的广州人的收入水平。 作为漂亮女生,Lucy在朋友们的派对上遇到过不少追求者,但迄今没有一个开花结果。此外,Lucy还上交友网站寻觅结婚对象,收到了很多男性的询问和关注,从中等收入的白领到商人和企业家。然而Lucy所面对的困境在于,她很难找到一个既认真对她又有良好经济基础的男人。对一些认真的追求者,Lucy不满意他们的经济实力;讽刺的是,她对那些拥有良好经济基础的追求者常抱着不信任的态度。例如,Lucy如此评价她曾经约会过的一个男人,这个男人35岁,在广州有一家公司:“条件这么好的男人怎么还单身呢?他肯定和我男朋友一样就是玩玩的。”她的包养经历着实让她很容易怀疑男人的意图。 谈及对未来的打算,所有的受访广州本地女性都和Lucy一样,希望找到一个有感情又有经济基础的男人结婚,安定下来。Jamie跟现在的男友——一个已婚的4S店老板已经五年有余,感觉“离不开他”了,她希望男友离婚娶她,但不知道愿望何时能够实现。为了保障自己的地位,她计划怀孕——她相信孩子可以稳固她同男友的关系;将来,即便男友对她失去兴趣,还是会承担起父亲的责任。其他五位都和Lucy一样,认为目前的关系只是权宜之计。尽管她们对男友抱有不同程度的感情,但并没有打算永远跟随这个男人。她们积极寻找机会,利用身处资源丰富的社会网络的优势,结识新的男伴以便缔结有婚姻可能的恋爱关系(即使是痴情的Jamie,在和男友认识的最初两年当中也曾不时地约会其他男人)。 受劳动市场的性别结构、原生家庭和教育水平的限制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女性在没有找到理想的男性建立婚姻关系以获得经济支持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寻求已婚男性的包养关系作为临时替代。但是,她们大多希望从一段不受法律和社会习俗保护、充满不确定性的婚外包养回到“正轨”——进入符合社会习俗的婚内供养,并在这个更替中维持特定的生活方式和群体归属。 女性主义学者指出,婚外性关系往往是男性性特权的一种表现,是男权制(抑或男性对女性的支配性统治)的一个组成部分[20][21]。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寻求或经历婚外性关系,这与男性(尤其是精英男性)占有更多的经济社会资源、拥有更多的社会交往机会等密切关联[22][23][24][25]。在以性别分工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生产体系中,女性群体被结构性地剥夺了进入市场平等获取物质资源的权利,她们的生活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人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而更大程度上在于她们选择的男性伴侣的市场位置[26]。因此,对于在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女性而言,通过男性伴侣获得经济保障,甚至“退而求其次”,愿意接受已婚男性的包养,维系“体面”的消费生活,不失为一种策略。 本文进一步指出,一些城市女性通过已婚男性的物质供给参与时尚的生活方式,不仅仅是个体物质欲求和向上流动的企图,更是她们参与群体生活,获得社会归属的重要方式。而这正与中国社会剧烈的阶层分化、消费文化对社会生活的“绑架”以及推崇男性供养的性别文化的“复兴”有着密切关联。对一些城市女性而言,成为“二奶”不受法律保护,背离主流道德,甚至比包养她们的男性受到更多的舆论谴责。然而,这一定程度上帮助她们免于陷入另一种“危机”,即被原有的朋友圈子抛弃以及由此带来的向下流动的失落与恐惧。在快速的社会变迁中,在市场化大潮的冲击下,传统的性别观念与新兴的消费主义交织在一起,深深地影响着年轻女性的人生选择与生命体验。 ①然而,正如潘毅指出的,尽管农民工试图通过参与消费来使自己成为城市的一份子,但由于收入微薄,他们的消费行为实际上强化了其在城市中的弱势地位,凸显了他们的农村背景,参见Ngai Pun.Subsumption or Consumption? The Phantom of Consumer Revolution in "Globalizing" China,Cultural Anthropology,2003,18(4)。 ②笔者在别处展开论述了外地打工妹在包养关系中的经验,可参见肖索未:《“双重边缘”:婚外包养与打工妹的情感体验》,《中国青年研究》2014年第5期;肖索未:《“今天不知明天事”:婚外包养与打工妹的情感困境》,《中国研究》2010年春秋季合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③一些城市女性喜欢用英文名称呼自己,本文中也用英文化名替代。取“洋名”也是这些女性时尚都市身份的一种体现。 ④对于受访女性个体而言,进入包养关系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种个体行动的逻辑是在特定的、“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框架下形成的。也正因如此,笔者“同情地”(empathetically)理解受访者的亲密关系选择,但并不意味着认同包养关系本身。 ⑤笔者曾要求Lucy介绍我认识她最有钱的两个女朋友,她犹豫片刻后拒绝了:“她们不爱说普通话,而且她们很年轻很骄傲的,肯定跟你聊不来。”在广州调研时,笔者作为在美国留学的博士生身份所承载的文化资本曾经帮笔者突破了很多的壁垒,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但是缺乏身体资本和时尚消费经验,使得笔者难以接触最“高端”的研究对象,这也从侧面说明时尚消费对于维系Lucy在其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成员身份的重要性。 ⑥维系资源丰富的社会网络对Lucy而言还有很多实质性的好处,可以帮助她在亲密关系中获得更多的主动权。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在之后关于“社会支持网络”的探讨中具体展开。 ⑦关于亲密关系的市场契约和家庭契约的论述,请参见宋少鹏:《性的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的性别奥秘——从2014年“东莞扫黄”引发的论争说起》,《开放时代》2014年第5期。 ⑧Lucy很少找家里要钱。作为离异家庭的孩子,她的父母各自有了新的家庭,她感到自己不属于这两个家庭中的任何一个;她还表示,自己成年以后还依赖父母是件羞耻的事,她不希望家人为她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