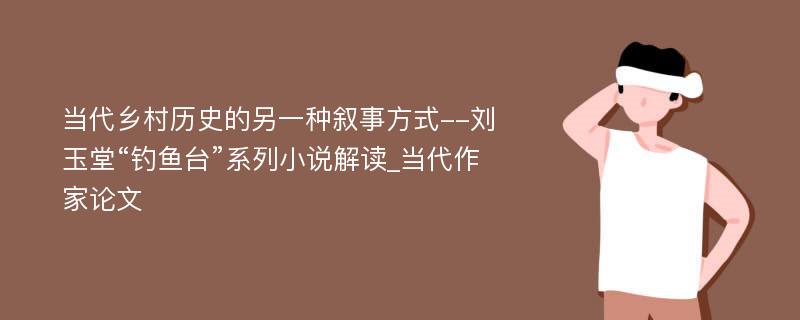
当代农村历史的别一种叙述方式——读刘玉堂“钓鱼台”系列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钓鱼台论文,当代论文,农村论文,方式论文,系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4年,山东作家刘玉堂有一篇《钓鱼台纪事》在刊物上发表。作品通过沂蒙山区一个村庄里几位颇具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的描述,勾勒了革命老区从40年代到80年代的历史演进过程。那文体中体现出的幽默调侃式叙事风格,在小说创作反思历史的一片沉闷严肃的氛围中,使读者体验到一股轻快的审美感受,因而引起了文艺界的广泛注意。近两年,刘玉堂又在《上海文学》和《时代文学》等刊物上连发表《温暖的冬天》、《冬天的错误》、《最后一个生产队》和《本乡本土》等中篇小说,重新选择钓鱼台40至90年代几个历史转折时期进行断面式的艺术展示。细读这些作品,使人进一步感受到作家有意识地将沉重的历史释解为幽默轻松的文本叙事,其叙述风格之中,体现着对过往生活的别具情态的审美观照。从创造主体的美学视角上说,作品摆脱了农村小说单一的社会政治观照模式,用时代文化中生发的机智聪慧去透视生活的具象和历史的记忆,从而形成一种传统文化与当代意识双向复合的叙事形态。体现在具体的话语操作过程中,创作主体善于使生活的经验和感受按照极富时代智慧的审美思维线索组合成象,其幽默风趣的文体特征,可谓使当代农村小说增强了新的审美格调。
我国农村的当代发展历史,比其他任何领域都充满着一种悲剧色彩。广大农民为求生存而进行的一切努力,无论表现为徒劳后的痛苦还是满足时的欢乐,都与党在农村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紧密连在一起。这种由政治直接制导的生活发展现象,为文学创作奠定了神圣的审美基调。在17年的以政治为文本建构中心的小说作品里,农村生活经过路线和阶级斗争意识的过滤变得异常严肃。“文化大革命”10年自不必说,即使进入了历史新时期,小说创作在反思农村历史的时候,以批判极左的政治为建构意向,展示在读者面前的叙事文本,依然没有摆脱既定的神圣意味和严肃面孔、审美过程中的沉闷、滞重之感,从根本上限制了读者自身的艺术扩展能力。久而甚者,一些作品远离了生活自身的鲜活性和丰富性,那煞有介事、故弄玄虚的叙事情态使广大读者望而却步。小说创作面临的危机告诉人们:面对同一个历史时期的生活现象,如果我们的作家不能发现区别于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新东西,而是用不同的形式去释解在政治文体中已经存在的思想观念和历史观点,这种创作就难以在读者中站住脚。作家的职能与政治、历史学家的最大区别,即是“扩展读者对生活的理解,从而使读者获得只有作家才能给予他们的”①。生活本身是丰富多彩的,我们只要超越政治决定论的观照视点,就能看到生活万花筒式的原态。取独具自我特点的审美角度,让人们在愉悦中感受生活、反思历史,理应是文学的本份。特别是在生活本身已经带给人们太多的紧张、烦累的时候,到文学中寻求反例的调节,已成为不容忽视的时代审美期待。令人不能满意的现象是,我们的新时期小说创作,在增强文学思考色彩的同时,往往把文本有意无意地变成了累人的读本。这对于作家来说,起码表现出了一种创作指导思想上的错位。通俗轻快的审美客体,与深刻独到的审美思考不但不矛盾,而且是文学吸引力的一个必要条件。高晓声运用轻喜剧的形式刻画过一个极具典型意义的陈奂生形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兴趣,从其思想的深度来说,它对农民劣根性的挖掘,反而高出好多题材范畴的作品。可惜的是,检视新时期的小说创作,这种寓严肃于轻快、寓深刻于通俗的作品实为鲜见。正是在这种前提下,刘玉堂的别具情态的创作,才显出了非同一般的意义。
在谈到创作的追求,刘玉堂说自己“十分注意将小说写得十分生活化”②。这里,作家用了两个“十分”来强调他对作品生活化的追求。读“钓鱼台”系列作品,也使我们感受到他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不是玩弄笔墨的结果,而是对生活真实性执著追求的表现。如同塞利安说过的:“作家的风格的成熟部分地取决于他对生活的诚实的表现,独创性意味着作家的诚实。由于作家的诚实,才鞭策他去探索恰切的语言来表现生活和他对生活的感受。”③刘玉堂小说的幽默调侃风格,不是表现在具象形态的滑稽效果上,也不滞囿于善恶伦理的戏谑讽剌中,它是创造主体在观照生活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审美机智,是作家面对复杂的历史所采取的极富策略性的叙事风度。用作家自己的话说,“生活需要摄影师的术语:‘笑一笑’。笑过了,再难受它一小会儿。”④《温暖的冬天》所写的,是钓鱼台胜利农业社因试验和推广胜利百号大地瓜有功,上级奖给该社双轮双铧犁一副和无线电一台所引起的种种喜剧式场景。作为革命老区,那些翻身不久又置身互助合作运动的干部和群众,与一般农村相比,对党的指示和上级的精神有着更强的亲切感和信任感。因而作家没有像过去的作品那样描写坏人破坏或保守落后势力的抵触等政治层面上的情节,他着力揭示的是为人忽视的另一面,即我们的干部和群众的理论水平、理解能力和局限性所造成的喜剧色彩。带着私有观念长期养成的显摆、迎合和自以为是,钓鱼台农民以小农经验为资本参与着一场从未经受过的社会变革实践。面对社会主义革命初期的生活情景,他们仰仗着朴实的想象和本能的感悟,不无盲目地应付着不断到来的新问题。这便使一场巨大的历史变革运动中不时演化出许多小聪明式的令人笑中有涩的喜剧场景。从为使上级满意而自编落后材料的刘日庆,到为使材料过关而引导基层干部说假话的杨秘书,我们已初步看到当时的主人公们为达目的而不惜违背客观实际的趋时心态。而到了《秋天的错误》里描写的那场空前的跃进场景,这种心态便膨胀性地发展为社会风气。一个“三天之内实现独轮车轴承化,五天之内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随意性添油加醋的电话,便引发了钓鱼台60名青年男女临界共产主义的种种盲目行为。他们冒大雨连夜出发,在瓜棚提前实现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生活。直到后来砸钢珠、造水磨、炼钢铁以至刘玉华、王德室受伤住院等等,都愈益明显地展示出了钓鱼台人在虚妄的幻想对客观现实的戏弄中如何推波助澜地充当着主要角色。从美学意义上说,“假”战胜了“真”(客观规律性)而一时赢得上风,表现在现实实践中便会呈现出喜剧性形式。然而这种喜剧形式的深层,却蕴含着历史的悲剧因素。在作品幽默调侃的叙述中,我们已然体察出作家这种深厚的历史意识。正是农民自身的民族劣根性,使当时违反客观规律的空想集聚为狂想式大合唱,造成了大跃进的每个实践环节,都因实践者的随意起哄而更具荒诞色彩。虽然在若干年后刘玉华等人回想起来,承认当时玩了一次“大家家”,但当时他们确实没有半点开玩笑的意思。正是喜居形式中所含蕴的善良和真诚的因素,使这们的笑含着苦涩的意味。所谓“笑过了之后,再难受一会儿。”
农业合作化道路的曲折历史,从社会基础上延缓了老区人民战争年代思想意识的变化更新。物质贫乏和生活的穷困,使他们不得不到既往的革命精神中为社会主义寻找理论根据,在造精神寄托维持心理平衡的苦中作乐的社会生活中,自觉不自觉地养成了多方面的崇旧性的依恋意识。《最后一个生产队》正是以独特的叙事笔法,揭示了农村经济变革初始期典型人物的依恋心态中所含蕴的复杂的社会因素。何永公等人之所以坚守着“集体的道路地久天长”的理论,皆因为他们与集体化之间埋藏着种种难以抽脱的情感导线。集体生活、集体劳动对他们来说,之所以一时难以割舍,因为它是青春、爱情和生命价值的见证;恋旧心态直接造成了他们从过往生活中寻求自我价值的后视性思维特征。钓鱼台人在战争年代形成的道德观念,在解放后只重精神不重物质发展的集体化生活中得到了进一步加固。所以当历史真正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变化时,一种貌似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便成了阻碍他们大胆起步的精神负担。主人公们以惯熟的理论水平和理解能力作为抵制生活变革的武器,便会形成由意识错位而生发的种种喜剧性。正是他们那种振振有词的真理在我的严肃态度中所包藏的滞后性思维观念,造成了作品笑中带涩、啼笑皆非的艺术审美效果。当然,历史不会随人的意愿而逆转,尽管刘日庆们一时难以超越感情局限,他们还是要追踪社会的发展,只不过走的是一个曲折艰难的历程。《本乡本土》可谓从更广阔的视角上进行艺术观照,进一步揭示了钓鱼台人在新形势下的困窘、醒悟的变化过程。在老一代积极分子看来,革命就要有自我牺牲精神,革命和吃苦分不开。多少年来,他们饿着肚子关心外边的形势,牺牲自我利益而迎合上级的精神。如果说这种思想表现在政治意识上还有令人崇敬的成份的话,由此而演化出的把革命与自我视为水火不容,为了老区的面子,饿着肚子为自身挨饿辩护,就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了。《本乡本土》的叙事时空较之前风篇作品大大扩展,即是想通过处在先进文化氛围的人物的视角,审视钓鱼台先进思想中的落后性。事实上,钓鱼台也正是在刘玉霄代表的激进思想的冲击下,才逐步放下了革命老区的架子,放下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实事求是地面对世界,开始了真正的发展。到这里,几部中篇连接成了一部当代农村历史。革命老区钓鱼台,为什么解放后反而成了比其他农村更为穷困落后的地方?这似乎是作家想要揭示的一个中心问题。我们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失误,特别是极左路线的破坏,自然是重要的原因。而这些被别的小说反复揭示了的思想,已不是刘玉堂艺术思考的重点,他的审美观照点在钓鱼台人自身。我们从小说中看到,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历史观念和道德观念的冲突,在钓鱼台这个典型环境里,演化成人物的内心意识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表现出来,往往以道德价值观念为中心,形成一种文化心理的平衡。而协调这种平衡,似乎组成了钓鱼台人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主要生活内容。这使得钓鱼台几十年貌似前进而实则在原地打转。在这一过程中,由于觉悟水平和理解能力的历史局限性,人们在内心协调和社会协调过程中的意识行为,包括一些合理或不合理的自我想象,共同组合成了一桩桩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从总体上说,钓鱼台人正是在这种充满喜剧色彩的平衡心态的追求过程中失却了许多发展的机会。因此,我们带着笑意读完刘玉堂幽默味十足的故事叙述之后,内心却不能不有一种沉重感。
善于以喜剧形式揭示民族性格中的弱点,是刘玉堂钓鱼台系列人物描写上的特点。作品本身的调侃色彩,往往生发于对人物自足性意识在开放环境中的困窘状态的描写过程。我们这个民族有一种本能的自我调节能力,为了整体的和谐及心理的平衡,民族的智慧每每被撕裂为能将痛苦幻化成即时性满足的小聪明。钓鱼台系列正是以这种意识为审美创造基点,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下巧妙地选取透视人物的审美视角,进而为审视人物性格创造了充分的文本空间。在对曹文慧、刘玉贞、李进荣、刘日庆、刘乃厚等不同历史阶段主要人物形象的描写中,作家善于将他们的历史故事叙述作为现实生活的深远背景,叠映在对笔下人物描写的过程中,从而造成文本叙述的历史空间感。使读者清楚地了解到,钓鱼台人是带着对过去的回忆眷恋,背负着先进的包袱,进行现实事务操作的。这就很难使他们在历史转折过程中表现出种种相背相离而又极富合理性的举动。因为他们在历史上的种种业绩甚至牺牲,显示出来的绝大成分是农民式的伦理正义感。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传统道德观念,而且这种观念也成为解放后支撑他们带头走集体化道路的主要成分。所以,他们在每一个关键时刻的自我选择,都很难摆脱这种心理积淀。刘玉贞在高级社时愤然辞职,既带有看不惯一些领导人工作作风的执拗,也与自己当了劳模而使刘日庆背了黑锅所造成的心理不平衡有关系。同时,也是忠孝不能两全的遗憾心理的一次痛苦移位(弃忠尽孝:把弟弟抚养成人,完成父母之命的婚姻结合),这种带有生命本能感受的历史选择,我们很难用对或错来武断地评论,它带着生活自身的复杂性。但在这一选择中仍然是农民传统的伦理思想在起着作用,却是基本的事实。再如刘日庆,大跃进大炼钢铁时他出于一个农民的本能的正义感,曾拒绝收缴社员的铜盆、铁锅和门鼻儿,也设法抵制过深翻土地一米八的瞎指挥风,还因此被视为思想右倾受到撤职处分。但当1980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根本上纠正农村极左的路线和政策时,他却站在顶着不干的行列里,并以先进典型作资本来对抗工作组。这使我们认识到,在农村几十年使人失望的现实生活中,钓鱼台人特别是带头人是靠历史的辉煌作资本赢得心理平衡的,用回顾过去来填充现实的空虚,不但使人的锐气日渐减弱,在面对新的选择时,那美好的记忆也往往成为难以超越的感情障碍。钓鱼台人的这种感情障碍是明显的。这一点,作者在《本乡本土》中,以超越了钓鱼台情感局限的刘玉霄所处的先进文化视角看自己的故乡,有过明显的省察;也在《最后一个生产队》中让刘来顺的大哥从别一种角度上进行过一针见血的揭示。虽然他们的观点不能说没有偏激的成分,但毕竟是超越了钓鱼台人的生活局限,因而对其群体心态和性格弱点的认识,也就更为透彻。以老解放区的革命传统,光荣历史来遮掩贫穷落后的现实,几十年安着贫困大唱赞歌,这固然有极左路线统治和上层各级领导人的责任,而作为钓鱼台人自身,何以能够平心静气、心安理得?归根结底,症结还在于固有的文化道德观念,低层的生存状态限制了文化的发展,传统的道德观替代着历史观来作为理解社会生活的准绳,在调节自我和社会的距离时,便会生出可笑、可悲、令人慨叹的举动:韩富裕为寻求感情上的失落而采取的种种行动,刘乃厚为迎合形势而给自己的金牙编出的一套啃排骨的谎话,还有刘玉华的套话高调等等,这些钓鱼台人的性格中所表现出来的亦困惑亦清醒的双重特征,使我们不得不联想到作品中那位清末秀才杨尚文。曹文慧在钓鱼台办识字班的时候,跟他学过一个“糁”字,并了解了这是一种稻米和肉合而煎之的好吃的东西。40年后,曹文慧又来到钓鱼台,遇上这位忽儿清醒忽儿糊涂,一辈子就会写、解一个字的神经秀才,看到他终生不忘的“糁”,竟是地瓜面加蛤蟆肉煮的糊粥,作家为什么写这位百岁不死却糊涂不醒的人物,我们不好硬性比附,但这个形象的描写使我们能想到很多很多,他的难以说清道明的生命现象自然也会对我们认识钓鱼台人的性格复杂性富有启示意义。
刘玉堂在谈到创作时曾认为:“有许多小说靠味儿赢人,不全指望深刻。”而“有了自己的语言,文章也就有了味儿。”⑤“钓鱼台”系列小说的创作,不以内容叙事的深度取胜,也不强求情节的酷似真实,而是靠场面描写和语言叙述中的独特的“味儿”来赢得读者。整体来看,“钓鱼台”系列选取的是几个极富历史性转折意义的时间断面,通过同一地点的人物具体行为和语言所组成的种种生活场景,使读者在身临其境的艺术体验中感受极富时空跨度而又具持续性的农村生活律动。作家把传统小说的再现生活与富有现代审美特点的显现型叙述结合起来,在文本中制造出一个个戏剧性的生活场面,进而靠这种生活场面凝聚成的整体氛围(味儿)创造审美的效果。具体说,也就是追求一种阅读过程后的自我深化。从语言上讲,作品的叙事过程与那种“陌生化”文本有本质区别,它注重的是极富生活原生态的语境制造,不论是叙述语言还是人物自身的语言显现出生活本来的面目都是其操作中的艺术追求,靠动作性拓展艺术表现空间。所谓动作化,首先表现为语句叙述的生活流状态,作家不追求语句本身的深刻含义,因为这样往往会使语言脱离现实农村生活甚至有时变得生涩。作品的叙事遵守着山村农村说话的那种多向流动的自然生活状态,围绕一件事、一个人、一句话题,大家东拉西扯,为展示自我而作即时发挥,往往形成多方位的空间语义场。语句中带着生活本身的杂质灰尘和主体的生活逻辑意味。特别是以陈旧的思维方式来表述对新鲜事物的理解,滞后的语式里夹杂着时髦的词句,共同形成了极富幽默调侃效果的语言环境。譬如刘乃厚见了县委办公室主任袁宝贵所说的一系列问话:“当前的形势是怎么个精神?”“蒋介石和李承晚没动静了吧?”“艾森豪不为儿打朝鲜了吧?”(把艾森豪威尔误听为艾森豪为儿)以及他自己不是党员却自告奋勇介绍别人加入共产党的言语等等。在极具生活困窘的语境中,作者让人物刻意摹仿上级领导人来表述崇高严肃的主题,从而使语言本身自然生发出一种戏剧式的诙谐感。它所留下的苦涩余味,使我们为由地会想起黑格尔关于喜剧人物的深刻表述:“在意志、思想以及在对自己的看法等方面,都自认为有一种独立自足性。但是通过他们自己和他们内外两方面的依存性,这种独立自足性马上就被消灭了。”⑥
塞米利安在《现代小说美学》中谈到语言时曾指出:“优秀的小说语言并不是把读者的注意力不适当地吸引到语言本身,也不是集中在作家身上,不管作家的语言如何具有个人特点,它的任务是使读者的思想集中在故事上,集中在事件上和小说发生的一切上。”⑦刘玉堂小说语言的动作性,即表现在它对生活场景的显示功能。文本中的人物语言,不是单线思维的语义展现,而含在着说话人的神气、动作。它与受话者的感应和行为形成一种交流互动的推进作用,照作者自己的说法是“骂张三的时候,顺便把李四也捎带上。”这种语言的语义指向不是直接供读者接收,而是形成生活的动态画面后才吸引读者的感受,所以它是以调动读者的审美感受域为目的的。像《最后一个生产队》里开始的一段描述,钓鱼台刚实行分田到户,坚持“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集体的道路地久天长”的几户农民与工作组辩论,作家按照他们所具有的各自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水平”,逐一把其语言不加任何评议的呈现于读者面前。虽然作品没有描写工作组的任何行为,但我们从刘日庆等人的语句中已能看到辩论的场景。像公家嫂子李玉芹说的,“当脱产干部几年了?说你呢?五年?五年还不懂唯、唯物主义啊?一点灵活性也不讲,政策一变你怎么办?耷拉着脑袋写检查啊?写检查也写不出好哲学!”何永公、刘日庆、刘玉华、刘来顺等等,他们你丢我拾,从不同的角度来表述着自己的看法和态度,语言本身与受话人所形成的互动关系十分明显。读着这些语言,头脑里便可随之浮现出生动的生活画面。因此,在人物语言中,读者不但能了解说话者的历史身份和思想个性,同时也通过其语气中所显示的动作因素扩充着小说的审美空间。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本语言的生活化和动作化,是作家对生活进行审美观照过程中的极富艺术智慧的表现。
注释:
①利昂·塞米利安:《现代小说美学》第3页,陕西人民出版社。
②《文学评论家》1988年5期。
③《现代小说美学》第231页。
④《山东文学》1985年3期。
⑤《文学评论家》1988年第5期。
⑥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239页。
⑦《现代小说美学》第2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