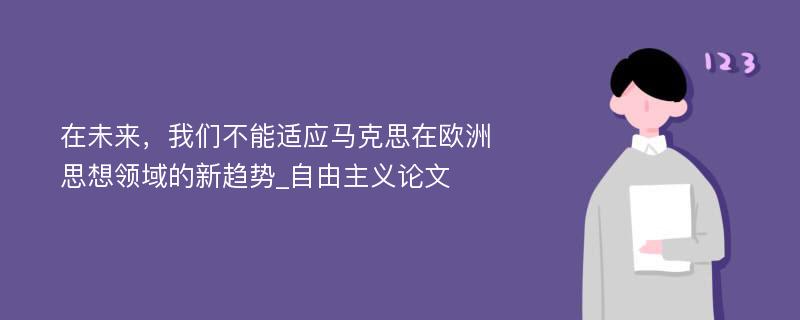
未来不能没有马克思 欧洲思想界的新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思想界论文,欧洲论文,新趋势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九十年代欧洲思想界的新趋势,不仅同“冷战的终结”有关,而且同“历史的终结”这样的说法联系在一起。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造成这种联系的是一个美国人,他就是作为美国国务院官员和美国政府智囊兰德公司顾问的日裔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 )。在1989年夏季,福山以“历史的终结”为题作了一系列讲演并发表了一篇文章,后来又于1992年以《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为题出了专著(同一年至少还出了该书的法文版)。另一个美国人,哈佛的亨廷顿教授,近年来也发表了一个惊世之论:冷战以后的世界的主要冲突将是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尤其是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的结合——之间进行。但不知为什么,据笔者的印象,欧洲人对亨廷顿的高论不怎么感兴趣。相比之下,福山在欧洲要更走运一些;1989年以后欧洲政治哲学方面的文章、论著中不提福山的名字的很少。尽管福山的黑格尔主义出发点、宗教术语和美国官方背景在不少人看来有些滑稽,但那么多人谈论他、批评他甚至讥讽他,这本身就说明一些问题。尽管一位叫尼特哈默尔(Lutz Niethammer)的德国人也在1989 年发表的一本题为《后历史:历史到了终点了吗?》的著作,研究本世纪上半期不少同法西斯主义有思想联系的法国和德国哲学家的历史终结论,而且据说学术价值比福山的高得多,但能流行一时的观点不一定就是有深度的观点:重要的是像意大利学者鲁克斯(Steven Lukes)在评论福山时说的那样,“大胆,清晰,抓住我们时代的普遍心态”。
初听上去,“历史终结论”的调子颇为悲观。欧洲思想史上曾出现过不少“终结论”,包括尼特哈默尔研究的那些“历史终结论”,是同人们对“进步”这个启蒙时代流行的乐观主义观念的怀疑、放弃有关的。这种对继续进步、继续创新的可能性的悲观主义态度、怀疑主义态度或保守主义的态度,在1989年以后的欧洲人文思想界也可以看到。英国这几年关于“回到基本”的争论内涵之一,就是在道德、文化价值方面能不能像科学、技术和经济方面那样不断进步、不断创新、不断抛弃旧的、传统的东西。英国的这场争论也涉及对现代先锋艺术的估价的问题,但对于在艺术领域的无休止的“现代”、“先锋”、“实验”的厌倦情绪表现得最强烈的,是在曾经对它们最欣赏、最陶醉的法国。“为什么新的就一定是好的”,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在10 多年前一次包括艺术家和艺术史家在内的多学科讨论会上提出这个问题,但显然未引起共鸣。现在,像法国Esprit(《精神》)杂志的多麦克(Jean—Philippe Domecq)这样的主流艺术评论家, 也对现代艺术的“求新癖”提出质疑。以前外行们不知所云的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现代艺术,现在连艺术专家们也觉得是“胡闹”对当代先锋艺术,人们的态度现在就像安徒生童话中那个小男孩一样:人们终于喊出了“皇帝没穿衣服!”
但进步的观念的复杂之处在于它不仅包含“创新”的含义,而且预设的“目的”的含义。关于“某某东西的终结”的议论,可以是出于对无休止创新的厌倦或绝望,也可以是出于对某一个目的之实现的满足与自得。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主要属于这后一个范畴。福山之所以提出这个命题,主要是为了概括在二十世纪上半期的悲观主义(两次世界大战等等)之后出现的、尤其是在最近几年来出现的乐观局面自由民主制度的决定性胜利:
“在过去的几年里,在全世界出现了对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政府制度的合法性的了不起的共识……”“自由民主制可能是‘人类的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是‘人类政府的最后形式’,因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现在的有些国家有可能无法实现稳定的民主,另一些则有可能倒退到其它的、更原始的像神权政治和军人独裁,但自由民主制的理想已经不能再作完善了。”
如果说自由民主制度是自由和平等的原则在政治领域的体现的话,那么,自由市场经济则是这两个原则在经济领域的体现。所以,全面地说,“历史的终结”这个命题的根据是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在这几年的决定性胜利。我们或许可以说,这是自由主义的“乌托邦”的实现。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在欧洲引起了各个方面的反响,叫好的不少, 批评的更多。 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批评性反应是:右翼的格雷(John Gray),中间的达伦道夫(Ralf Dahrendorf),和左翼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历史的终结”还是“自由主义的终结?”
——来自右翼的反应
在福山于1989年夏发表他的文章《历史的终结》后没有几个月,格雷就写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还是自由主义的终结?”的书评,指出在自由主义困境重重的今天,福山兴高采烈地宣布自由主义的民主制度的决定性胜利,是笑得太早了。
首先,自由主义虽然在英美学术界占主流地位,但自由主义从来也未能成功地证明,对于正义和人类的善来说,只有自由民主制度是必不可少的。格雷认为,近年来自由主义在西方学术界、尤其是北美学术界受到社群主义的猛烈攻击,是咎由自取,因为自由主义者没有看到存在着在许多种政府形式下,例如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英国的君主制,明治时期的日本,甚至像韩国和新加坡这样的东亚社会,人们曾经过得很好、将来也可以过得很好。自由主义是想把一种特定的立宪民主的历史传统(即美国的传统)普遍化。
其次,格雷认为,即使福山的依据不是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而是把自由民主制度看作是历史之目的的历史哲学,他的观点也只有这样理解才是合理的,即把自由主义的核心理解为市民社会,而不是立宪民主制度。以法治和私人活动自由为宗旨的市民社会是市场经济的母体,而历史和理论都证明市场经济是现代世界上繁荣和自由的前提。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有西欧北美的那种市民社会;相反,市民社会有许多存在形式、类型,并在各种不同的政权下面蓬勃发展。
最后,格雷认为,美国本身的情况表明在美国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是市民社会的敌人,而不是市民社会的朋友。当它以女权主义和对少数人群的惠助行动政策的形式出现时,自由主义支持了对私人权利的侵犯,对结社自由的限制和对契约自由的损害。由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加于市民社会之上的这些破坏,美国实际上已经变得比其它任何现代民主国家都更科层化、更条条框框化,更不宽容,更不团结,更是一个国家主义的社会。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是建立在它的市民社会基础上的,而现在这份历史遗产正被白白浪费。
“历史的终结”还是“乌托邦的终结?”
——来自中间派的反应
在写于1990年的《东欧革命反思》一书里,英国著名学者兼社会活动家达伦道夫显然对福山1989年夏天的文章和一系列演讲的学术价值评价不高,但也花了一些篇幅来讨论他的观点。
达伦道夫说他主张立宪自由主义,但与一般的立宪自由主义者不同的是,他一方面像他们一样在“构成性政治”(按:在英语中,“构成”与“宪法”为同一个词:constitution)方面主张立宪自由主义,另一方面,在“常规政治”领域主张激进改革。所以,达伦道夫虽然像福山一样主张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但对西方社会的现状却不像后者那样乐观。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哲学上赋予自由民主的地位不同。在达伦道夫看来,福山像许多别的西方人、甚至东欧人一样,把1989年以前的四十年看做是西方的民主资本主义和东方的国家社会主义之间的两大制度之间的斗争,而这个观点他认为是错误的。西方社会的特点并不是某一种特定的制度,而是对各种制度进行选择的一种方法——一种自由的、尝试性的、可以通过消除错误而在制度选择方面进行学习的方法。达伦道夫用波普尔的一个著名术语,把具有这种特点的西方社会称作“开放社会”,而把1989年以前的四十年叫做“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之间斗争的时期。从原则上讲,这种开放社会是对任何制度开放的;它唯一排斥的是只允许一种制度、只允许一种官方意识形态存在的“封闭社会”。1989年的意义不在于一种特定的制度战胜另一种特定的制度,而在于“开放社会”战胜“封闭社会”。而这同时也意味着“开放社会”战胜“乌托邦”,因为“乌托邦”和“封闭社会”之间有内在的联系:乌托邦是一个无所不包的选择项,因而它必然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它或许只存在于‘乌有之乡’,但它常被看作是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各种现实相对立的一种反面谋划(counter—project)。在达伦道夫看来,即使是一个仁慈的乌托邦,也必然走向反面。理由有二。第一,建立一个总体性的乌托邦必须要把现实世界的画布变成一张白纸,以便去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在他看来太残酷。第二,建立这样一个新世界免不了会犯错误,从而有必要经历一个实行独裁或专政的“过渡时期”,但问题是掌权者没有放弃其权力的习惯,所以我们就只好一直过渡下去。
因此,乌托邦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它“可望不可及”;它的问题主要在于它不仅不可及,而且不可望——不仅“及”不了,而且“望”不得。
“历史的终结”还是“一种历史观的终结?”
——来自左翼的反应
英国最著名的左派理论家之一汤普森(E.P.Thompson)在一篇书评中说,达伦道夫的书值得一读,因为他讨论了我们时代的一些非常困难的问题,而且他的讨论是诚实的。但是汤普森对达伦道夫的反乌托邦主义作了激烈批评。汤普森说,达伦道夫的论证没有什么新意;自由主义者多少年来一直在借口反乌托邦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但达伦道夫肯定误解了乌托邦主义到底是什么。在汤普森看来,乌托邦的实质是一种想像能力和批判能力:“乌托邦主义并不是一种政治,并不是一种政治纲领。它是想像能力的政治表现。它更接近于诗,而不是更接近于计算。要推进任何一种社会变化,人们都必须首先想像别的可能选择;乌托邦主义想像什么东西或许可作为批判现实的手段。”
汤普森在捍卫作为乌托邦的社会主义的时候没有提到福山,但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在1994年上半年的《新左派评论》上发表的长文,是在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评论中捍卫并阐发他的乌托邦思想的。
德里达的这篇文章的基础是他在1993年作的一系列讲演,题为“马克思的幽灵”。显然,这个题目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开头关于“共产主义的幽灵”的那段话受的启发。1989年以后重提《宣言》的重要西欧思想家不止德里达一个;在哈贝马斯写于1990年的反思1989年的重要文章中,他也大段引用《宣言》,作为其分析这个历史事件的一个重要依据。但德里达对《宣言》的主要兴趣不在于对过去的解释,而在于对未来的展望。在德里达看来,这个未来不能没有马克思的幽灵(spectres of Marx)。
这里有好几层意思。
首先,未来不能没有马克思;当代社会的许多问题,涉及人类命运的许多问题,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启发,是不可能解决的。在五十年代中后期,在苏共二十大和匈牙利事件以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同样处于严重困境(虽然不像现在那么严重)时,当时法国最著名的哲学家萨特出语惊人地断言:“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现在,同样是目前法国最著名哲学家的德里达也说:“没有马克思就没有未来,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和继承,就没有未来。无论如何,没有对于某一个马克思、对于他的天才、至少是对于他的许多精神中的一个的记忆和继承,就没有未来。”
但为什么说“马克思的幽灵”呢?对于不反对马克思主义本身而只反对它的苏东版本的人来说,现在谈论马克思的幽灵,有这样的意思:在全新情况下重提“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终结,就像历史并没有终结一样。几年来在西方世界的大众传媒炒得很热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哲学的终结”一样,早就不知道有过多少个版本。在经历了一个德里达所说的哲学和政治的双重“解构”过程之后,再重复这种先知预言,是令人厌倦的“年代错误”。但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有必要对它们作重新的认识。把马克思主义叫做一个“幽灵”,是因为“幽灵”总是同逝去的先人有关的,而在1989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确实同时具有哀悼者的心情和继承者的心情。把马克思主义看做一个“幽灵”的另一层意思,是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某种确定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是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性质。就像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写《宣言》时共产主义的境况一样,马克思主义现在也使欧洲的统治势力感到威胁,但谁也不知道这威胁到底在哪里:幽灵之所以为幽灵,就是因为它或它们的存在形式与众不同:既存在,又不存在,既属于过去,又属于未来。这些势力想要搞清楚到底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幻的。甚至马克思本人,至少他的“一部分”,也希望消除现实与虚幻之间的这种令人不安的模糊不清,他希望通过实现乌托邦来消除乌托邦。显然,马克思的精神中的这个部分,德里达是不想继承的。
最后,与马克思、恩格斯讲到“共产主义”时用的“幽灵”一词不同,德里达讲的“幽灵”是复数的、而非单数的:马克思的幽灵不止一个,而有多个。因此有必要进行选择、因此没有必要强求统一。
以上还只是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他还进一步用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当前具有极其重要的一个问题:对当代社会的“统治性话语”或“文化霸权”的分析。在德里达看来,一种统治性话语支配着当代社会的三个领域:政治文化、大众传媒文化和学术文化,而且这三个领域之间由电子传媒时代的同一些装置空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况对民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在德里达看来,前几年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在西方思想文化界的走红,正是这种统治性话语的一个典型表现。
德里达指出,福山为了证明自由民主制度是已经实现了的历史目的,在对其论点有利时大量引用经验事实,尤其是这个世纪的下半叶中发生的许多事件,但面对同样是大量的相反事实时,则强调他所说的作为历史之目的的自由民主是一种理念、理想,因而自由民主制度在事实上的不普遍和不完善并不妨碍他——福山——说自由民主已经赢得决战。
但德里达认为福山的书的成功也正在这里:它之所以一下子成为西方超级市场上十分抢手的传媒小玩艺(人们对它的态度就像家庭妇女一听到打仗的谣言便抢购物品一样),是因为它满足市场上的一种特殊需要:那些为自由资本主义的胜利欢呼的人,觉得有必要向自己隐瞒自由资本主义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脆弱、都危险,在某些方面甚至灾难重重这个事实,有必要向自己隐瞒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原则或“精神”(亦可译为“精灵”)的潜力。
马克思的幽灵的一个重要作用是有助于德里达提出他的“新国际”(The New International)设想。在国际范围而不是在一国范围、 甚至也不仅仅在西方世界范围内为乌托邦辩护、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辩护,这是1989年以后的欧洲左翼知识分子的相当明显的共同特点。有的左翼学者,看来并不属于托洛斯基那个传统,甚至还怀疑是不是真如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范围内取得胜利。但1989年以后谁也没有像德里达那样热情地呼唤、构思继承《共产党宣言》作者及其事业之遗志(也就是“幽灵”)的“新国际”。它要求对国际法、对它的概念、对它的干预范围作深刻的转变。理由不是别的,而是由无数个单个受难现场构成的这个触目惊心事实:任何程度的进步都不允许我们否认,就绝对数字而言,地球上从来没有那么多男人、女人和儿童,像现在这样被压迫、受饥饿或者遭灭绝。
当然,现实的考虑和德里达的浪漫气质都不允许他按以前几个国际和目前的社会党国际那样构思他所谓的“新的国际”的组织结构。这种为乌托邦而奋斗的“国际”,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乌托邦:没有地位,没有头衔,没有党,没有国家,没有民族社团,没有共同公民身份,没有共同的阶级归属,而只是一种人类同舟共济的感情纽带和希望之光……
结论
在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实验失败以后,福山、格雷和达伦道夫以不同方式表示: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名为科学,实际却不过是乌托邦。然而,德里达的观点却与众不同:“如果有一种我永远也不准备放弃的马克思主义的的精神,那么它不仅仅是批判的精神和质问的态度……它毋宁说是某种对于解放和获救的肯定,是某种许诺我们可以设法摆脱任何独断观念、甚至摆脱任何形上—宗教的预定、摆脱任何救世福音的体验。”
在目前的情况下,在福山们、格雷们、达伦道夫们以不同形式宣告社会主义破产的时候,德里达仍然想捍卫和发展社会主义,这很好。但是,把社会主义归结为乌托邦,这样的“捍卫”能行吗?
然而,德里达的观点虽是惊世骇俗,却也发人深省。很大程度上德里达是以比较极端的说法表达了当今欧美其他许多左翼人士(包括前面提到的汤普森)的共同想法。这种想法确实很成问题,但它可以启发我们对“科学”和“乌托邦”这两个概念本身,对它们之间的关系,对这和关系在历史现实中的投射,作新的思考。
标签:自由主义论文; 德里达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马克思的幽灵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宣言论文; 幽灵论文; 乌托邦论文; 自由民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