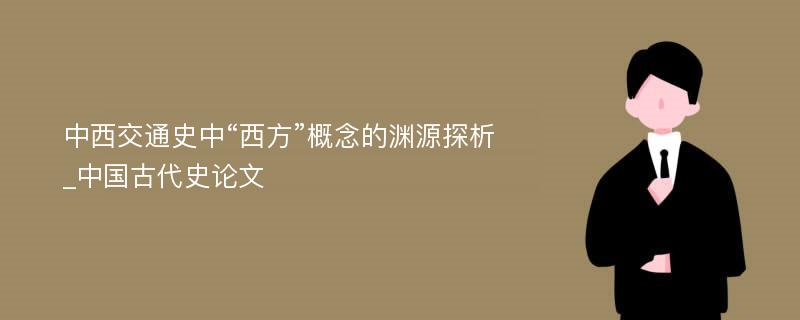
中西交通史上的“西方”概念之探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上论文,中西论文,概念论文,交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在中国历史地理学上是一个含混而不确定的名称,它与历史上的中西交通密切相联,这一名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变迁、演变过程。要理解中国人的“西方”观念,首先要从追溯中国历史上与这个概念相联的两个地域名称说起,即汉唐时期的“西域”和宋元明时期的“西洋”。探讨历史上从“西域”、“西洋”到“西方”的名称转换过程,可以看出中国人的西方观念之变迁。 一 “西域”的含义及范围 中原通西域始自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张骞出使西域。司马迁所作《史记·大宛列传》详记张骞出使事迹,文中出现了“西域”一词:“是岁汉遣骠骑破匈奴西域数万人,至祁连山。”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有“匈奴西域王”之称,也使用了该词。可见,“西域”之名在汉武帝时期已使用,其所指并不明确,将“匈奴西域”并联在一起,说明西域为匈奴之地或匈奴统辖之区域。 对“西域”一名的范围明确做出界定的是《汉书·西域传》,称:“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阸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余太山先生认为:“这一关于‘西域’的定义可能形成于西汉开展西域经营之前,亦即上述地区被匈奴统治时期。据《汉书·匈奴传上》,公元前176年(文帝前元四年)冒顿单于遗汉书中提到匈奴征服了‘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这‘二十六国’显然是‘三十六国’之误。也就是说,由于冒顿发动的战争,‘三十六国’成了匈奴的势力范围。正是这一范围,被匈奴称为‘西域’。”①余氏这一看法,与我上述对《史记·大宛列传》中的“匈奴西域”一词解析相一致。即西域最早是指匈奴统治的区域,但西域之名是否为匈奴所命名,还是汉人之称呼,仍有待考证,从语义上说,“西域”初义应指西部化外之域,这应是汉人对西部的指称。 《汉书·西域传》实际所涉范围要大,该传述及当时的中西交通:“自玉门关、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今吐鲁番)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今喀什),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黑海、咸海间)焉。”这就是当时西域的范围。现今论者一般认为,“‘西域’有广狭二义。广义的‘西域’,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狭义的‘西域’主要指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围地区”②。《汉书·西域传》实际介绍的是广义的“西域”。 随着中西交通范围的拓展,东汉的“西域”范围也随之增大,由于东罗马帝国与东汉通使,欧洲开始进入中国的文献记载。《后汉书·西域传》称:“西域内属诸国,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极玉门、阳关,西至葱岭。其东、北与匈奴、乌孙相接。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所载范围包括大秦(东罗马帝国)、天竺(印度)、安息(波斯)等国,可见当时“西域”范围之广,远超《汉书·西域传》。“具体而言,将意大利半岛和地中海东岸、北岸也包括在内了。这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描述的‘西域’中范围最大的,以后各史‘西域传’实际描述的范围再也没有越出此传。”③当时中原与西域交通的情形与西汉似无大改,具体情形为:“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自伊吾北通车师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后部金满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门户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而西域通中亚、印度、地中海诸国的交通情形:“自鄯善逾葱领出西诸国,有两道。傍南山北,陂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领,则出大月氏、安息之国也。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陂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领,出大宛、康居、奄蔡焉。”④这些路线实际上就是当时的丝绸之路,故西域也是与丝绸之路紧密相联的一个历史地理概念。 有关魏晋南北朝正史著作,如《魏书》《南史》《北史》《新唐书》均设《西域传》,多取西域之广义。而《魏略》《晋书》《梁书》及后来的《旧唐书》则改设《西戎传》,其所述范围涵盖此前的西域。唐朝与西域的交通较此前更为发达,中原与西域的关系自然更为密切。其中《旧唐书·西戎传》中“拂菻”一条记“大秦”之事曰:“拂菻国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东南与波斯接。地方万余里,列城四百,邑居连属。”⑤《新唐书·西域传》记“拂菻”一条曰:“拂菻,古大秦也,居西海上,一曰海西国。去京师四万里,在苫西,北直突厥可萨部,西濒海,有迟散城,东南接波斯。”⑥显然,随着中国与中亚、西亚、欧洲的交通日益增多,中国对这一带地区诸国情形的了解越来越清晰。 与西域相联的一个名称是“西天”。印度古称“天竺”,古代中国通称印度为“西天”。其名可能出自有二:一是唐代佛教信徒玄奘前往“天竺”取经,俗称“西天取经”,这是就地理上而言,意指比西域更为遥远的西方。二是在佛教用语中,“西天”意为极乐净土、极乐世界。唐代皇甫曾《锡杖歌送明楚上人归佛川》诗曰:“上人远自西天至,头陀行遍南朝寺。”宋代晁冲之《以承宴墨赠僧法一》诗中有“王侯旧物人今得,更写西天贝叶书”之语。可见,唐宋时期“西天”一词已经流行。 《宋史》未再列《西域传》,而在卷四百九十列传第二百四十九《外国六》之下列“天竺”“于阗”“高昌”“回鹘”“大食”“層檀”“龟兹”“沙州”“拂菻”诸条。可见宋朝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元史》亦未再设《西域传》,甚至《外国传》,只是在卷十六《志第十二·地理志三》有“甘肃等处行中书省”涉及原辖西域之地区的介绍,这可能是元朝所辖之区域空前之广大,所谓“西域”和“外国”大多在其控制或相关汗国的统治区域内。《明史》在卷三百二十九至卷三百三十二设《西域传》,其所涉范围大致只是狭义上的“西域”了。而在“西域传”之前设有“外国传”,显示出明朝与西域微妙而复杂的关系,既不同于“外国”,又与内地有别,但“西域”作为中西交通的特殊区域或必经之地已失去原有的意义和价值。 二 “西洋”的最初含义及范围 “西洋”名称的出现相对较晚。如果说,“西域”一词与中西陆路交通紧密相联,那么,“西洋”的名称则是伴随中西海路交通兴起的产物。从“西域”到“西洋”,实为中西交通由陆路转向海路的飞跃。 “西洋”的名称可能最早见于五代。据刘迎胜先生考证,《西山杂志》记载,泉州蒲氏家族蒲有良至五代时“之占城,司西洋转运使”,宋末其族人蒲甲又“司占城西洋之转运使”。这里的“西洋”大体上指今马来半岛和印尼苏门答腊周围海域⑦。开封为宋代犹太人居住集中之地,开封犹太寺院中曾存四通碑文,其中《重建清真寺记》刻于明弘治二年(1489年),文称:“噫!教道相传,授受有自来矣。出自天竺,奉命而来,有李、俺、艾、高、穆、赵、金、周、张、石、黄、李、聂、金、张、左、白七十姓等,进贡西洋布于宋。帝曰:‘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⑧此处“进贡西洋布于宋”一语说明宋代已使用“西洋”一词。元代刘敏中所著《中庵集》之《不阿里神道碑》提到不阿里的远祖从西域的“哈剌哈底”徙居“西洋”,此处“西洋”意指印度东南海岸的马八尔国。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十余处使用“西洋”一词,如“西洋丝布”“出于西洋之第三港”“后西洋人”“舶往西洋”“舶往西洋者”“用西洋丝布”“舶往西洋”“国居西洋之后”“至西洋或百日之外”“亦西洋诸番之马头也”“界西洋之中峰”“西洋亦有路通”等⑨,足见元代“西洋”一词流布之广。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述及真腊国“服饰”时,称“往往以来自西洋者为上”⑩。周致中的《异域志》在“虎六母思”“西洋国”“黑暗国”条下三次提到“西洋国”或“西洋”(11)。 万明女士对“西洋”一词在元、明两代的演变作了梳理。她认为:“将‘西洋’作为一个区域来整体看待,并将这种称谓固定下来,被人们广泛地接受、采纳和统一应用,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的开端是在元代,而它的完成是在明初下西洋的时代。”她将明代“西洋”一词的演变分为两个阶段:洪武年间到永乐年间,《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年(1370年)出现有“西洋琐里”的国名。《明太宗实录》永乐元年(1402年)有“西洋剌泥回回哈只马哈没奇剌泥等来朝,贡方物”。随着郑和下西洋,马欢述“往西洋诸番”,费信“历览西洋诸番之国”,而巩珍所著书名《西洋番国志》则将下西洋所到国家和地区,包括占城、爪哇、旧港乃至榜葛拉国、忽鲁谟斯国、天方国,均列入西洋诸番国,从而扩展了“西洋”的范围(12)。纪录郑和下西洋的著作有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1434年)、黄省曾的《西洋朝贡典录》(1520年)。其中《西洋番国志》所载西洋二十番国为:占城、爪哇、旧港、暹罗、满剌加、哑噜、苏门答剌、那孤儿、黎代、南浡里、锡兰、小葛兰、柯枝、古里、溜山、祖法儿、阿丹、榜葛剌、忽鲁谟斯、天方(13)。《西洋朝贡典录》对《西洋番国志》的错误有所修正,所载西洋诸国增至二十三个:占城、真腊、爪哇、三佛齐、满剌加、浡泥、苏禄、彭亨、琉球、暹罗、阿鲁、苏门答腊、南浡里、溜山、锡兰山、榜葛剌、小葛兰、柯枝、古里、祖法儿、忽鲁谟斯、阿丹、天方(14)。这可以说是欧人来华前中国人的“西洋”范围。张燮所著《东西洋考》(1617年刻印)所载“西洋列国”只有交耻、占城、暹罗、下港、柬埔寨、大泥、旧港、麻六甲、哑齐、彭亨、柔佛、丁机宜、思吉港、文郎马神、迟闷。范围较《西洋番国志》《西洋朝贡典录》所述略小。“西洋”一词广泛运用于明代社会,出现了广、狭两义。狭义包括郑和所到的今天的东南亚、印度洋至波斯湾、北非红海一带;广义“是一个象征整合意义的西洋,有了引伸海外诸国、外国之义”(15)。也有学者根据《东西洋考》卷九《舟师考》中的“西洋针路”“东洋针路”之说,提出西洋与东洋最初并非地理之概念,而是航线概念,沿南海以东航行所经诸地为东洋,沿南海以西航线航行所经各处为西洋(16)。此说可备一说。 三 近代意义的地理概念——“西方” 不过,明代虽使用“西洋”之名,其所指范围并非限定欧洲,甚至不含欧洲,而是指东南亚、西亚、东非或印度洋周围国家。郑和下西洋中的“西洋”即是指其所经这些地区。接近近代地理概念上的“西方”是伴随欧洲传教士东来而出现的一个地域名词。对欧洲地理最早系统介绍的是意大利籍耶稣会士艾儒略(Giulio Aleni)的《职方外纪》,该书卷二介绍了欧洲诸国及其地理(17)。首次正式使用“西方”一词,且直指欧洲者可能是艾儒略的另一部不太为人们所提及的小册子——《西方答问》,此书开宗明义谓:“敝地总名为欧逻巴,在中国最西,故谓之太西、远西、极西。以海而名,则又谓之大西洋,距中国计程九万里云。”该书将世界分为五大洲:亚细亚、欧逻巴、利未亚(即非洲)、亚墨利加(即美洲)、墨瓦腊尼加(即大洋洲)。“自此最西一州,名欧逻巴,亦分多国,各自一统。敝邦在其东南,所谓意大利亚是也。此州去贵邦最远,古未相通,故不载耳。”(18)该著分上、下卷,上卷分国土、路程、海舶、海险、海贼、海奇、登岸、土产、制造、国王、官职、服饰、风俗、五伦、法度、谒馈、交易、饮食、医药、性情、济院、宫室、城池兵备、婚配、守贞、葬礼、丧服、送葬、祭祖,下卷分地图、历法、交蚀、星宿、年月、岁首、年号、西土诸节。其中在“路程”一节介绍了自欧洲来华的航行路线和时间。在“登岸”一节对欧洲与“回回”、天主教与“天竺浮屠”(印度佛教)作了区别。“问:贵邦到敝邦,从何省登岸?曰:极西海舶,不到贵国,只到小西洋而回。西客在小西换舟,到广东香山边,予辈亦乘客舟而至。”“问:有西方人从陕西进,三年一贡。亦有传道之僧从四川、云南而来者,不知与贵邦同否?曰:来自秦中皆回回之类,此与中国相连地,与敝邦相悬绝也。来自四川、云南者,天竺浮屠之类,与天主圣教又悬绝也。”(19) 随后由耶稣会士利类思(P.Louis Buglio)、安文思(P.Gabriel.de.Magalhaens)、南怀仁(P.Ferdinand Verbiest)编写的《西方要纪》,实为《西方答问》的增删本(20)。该书开首即称:“西洋总名为欧罗巴,在中国最西,故谓之大西。以海而名,则又谓之大西洋。距中国计程九万里云。”由于该书出自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三位传教士之手,故对西方之介绍带有相当正面的色彩。如“风俗”一节:“西洋风俗,道不拾遗。偶或有遗,得之者则悬垣壁,以便原主复取。”如“法度”一节:“西洋虽以德养民,亦有囹圄刑罚以惩已犯罪而儆未犯者,但不用箠楚耳。定罪必依国法,不敢参以私意。若不依法者,罪反归于有司矣。”如“性情”一节:“尚直重信,不敢用诈欺人,以爱人如己为道,有无相济。又尚志,难于忍辱。交处多情义,一国中少有不得其所者,即他邦之人至,尤不敢慢,更加礼焉。”如“教法”一节:“西方诸国奉教之后,千六百年,大安长治,人心风俗和善相安,家给人足,不争不夺,各乐其业。”(21)由此可见,“西方”作为一个地理名称明确指称欧罗巴洲,是由明末清初耶稣会士艾儒略撰著的《西方答问》和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编写的《西方要纪》两书确定下来的。有趣的是,张潮在将该书收入《昭代丛书》时,为该书作《跋》称:“西洋之可传者有三:一曰机器,一曰历法,一曰天文。三者亦有时相为表里。今观《西方要纪》所载,亦可得其大凡。然必与其国人之能文者相与往复问难,庶足以广见闻而资博识也。”将西洋可资学习者定格在“机器”“历法”“天文”三项,显示张潮对西学的了解尚较肤浅和片面,也反映了时人对西方认识的局限,但与近代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思想主张联系起来,它又不失为学习西方的先声。 与“西方”一词同时采用并广为流行的指称“欧罗巴”的同义词还有“泰西”“太西”“极西”“远西”。耶稣会士熊三拔(P.Sabbathin de Ursis)撰说、徐光启笔记、李之藻订正的《泰西水法》(1612年初刻)和耶稣会士邓玉函(Johnn Schreck)译述、毕拱辰润定的《泰西人身说概》(1643年刻)两书的书名即采用了“泰西”这一名词。此词一直到晚清仍然沿用,如晚清介绍西方的重要典籍,徐继畬所著《瀛寰志略》,魏源编撰的《海国图志》,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口译、蔡尔康笔录的《泰西新史揽要》,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mest Faber)撰写的《自西徂东》等书,即采用了“泰西”一名指称欧洲。“极西”“远西”常见于各种介绍西方学术书籍的作者署名前,如《修身西学》《齐家西学》两书作者署名为“极西高一志撰”,《超性学要》作者署名为“极西耶稣会士利类思译义”,《四末真论》作者署名为“远西耶稣会士柏应理撰”,《西方答问》作者署名为“远西艾儒略撰”。 “西洋”“西海”两词继续沿用,但其义由原来的泛指东南亚、西亚、东非一带,逐渐转向专指欧洲,这也许最能反映当时明末以后中西交通的实际。《四库全书》收入南怀仁撰写的《坤舆图说》,卷前介绍:“怀仁西洋人,康熙中官钦天监监正。是书上卷,自坤舆至人物,分十五条,皆言地之所生。下卷载海外诸国道里、山川、民风、物产,分为五大州,而终之以西洋七奇图说。”(22)这里的“西洋”系指称欧洲。“西海”则常见于来华西人撰译的各种书籍署名中,如1614年初刻于北京的《七克》,作者署名“西海耶稣会士庞迪我撰述”。1623年在杭州成书的《性学觕述》,署名“西海后学艾儒略著”。艾儒略所撰《职方外纪》卷二《欧罗巴总说》开首曰:“天下第二大州名曰欧逻巴。其地南起地中海,北极出地三十五度。北至冰海,出地八十余度,南北相距四十五度,径一万一千二百五十里。西起西海福岛初度,东至阿比河九十二度,径二万三千里。共七十余国。”(23)这里的“西海”即为大西洋。当时,人们对“洋”与“海”之区别并不甚在意或了解,故“西洋”与“西海”混用是常见的事。 与“西方”相联的还有一些词,如“西学”“西儒”“西医”“西历”“西国”等,几乎同时出现在介绍西方学术、医学、历法、地理的书籍里。最早使用“西学”一词的可能是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的《西学凡》(1623年初刻)。该书开首即称:“极西诸国,总名欧逻巴者,隔于中华九万里。文字语言经传书集,自有本国圣贤所纪。其科目考取虽国各有法,小异大同,要之尽于六科。一为文科,谓之勒铎理加;一为理科,谓之斐录所费亚;一为医科,谓之默第济纳;一为法科,谓之勒义斯;一为教科,谓之加诺搦斯;一为道科,谓之陡录日亚。”(24)第一次在中文世界系统介绍了西学。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P.Nicolas Trigault)撰述的《西儒耳目资》(1626年刻)较早使用了“西儒”一词。以“西学”命名刊刻、篇幅量较大的书籍当推意大利耶稣会士高一志(P.Alphonse Vagnoni)编撰的《修身西学》《齐家西学》《治平西学》三书。作为与中学相别的“西学”在明末的少数士大夫中开始传播。 晚清以降,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渐次扩大到军事、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地理范围也由欧洲扩展到美洲、澳洲。“西方”成为基督教文化圈的代名,并被赋予地理以外其他方面的内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出现所谓东西方冷战,这里的“西方”则是指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包括亚洲的日本,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它是一个意识形态共同体的指称,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被排除在“西方”以外。冷战结束以后,虽然苏联解体,取而代之的俄罗斯不为西方或欧共体所接受,俄罗斯仍是与西方并立的另一极,所谓“西方”当然也不包括俄罗斯和其他与俄罗斯关系密切的独联体国家。 从历史上看,古代西方文明主要是指古代希腊、古代罗马所涵盖的区域,它与东方文明国家(包括地处近东、中东、远东的四大文明古国,即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相对应,主要是一个地理概念。在近现代,随着西方国家意识形态色彩的加重,西方学者就认为:“西方文明首先可以近似定义为法治国家、民主、精神自由、理性批判、科学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经济。”(25)它显然带有排斥非“西方”文化或文明的意味。在这种背景下,当西方学者使用“西方”这一名称时,就不仅是一个地理指称,可能还带有某种程度的文化优越感,它与“西方中心主义”有着某种关联。有的西方学者区分了“旧西方”与“新西方”两个概念:“旧西方大约从凯撒开始,一直持续到法国大革命。旧西方是指一种欧洲文化秩序:它在哲学上以柏拉图为主导,在宗教上以希伯来圣经的伦理一神教为主导,在法律和社会组织上则以古罗马遗产为主导。拉丁基督教会是它的中心,也是它最持久的机构。现代批判性思维的兴起和启蒙运动深深地影响了旧西方,接着在19世纪,旧西方进入知识和工业快速发展的时期。”“新西方”是指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美国领导的西方,“新西方是某种类似于人类顶峰的事物,因为它是以第一批得到彻底解放的人的出现为标志的。这些人知道,他们自己是他们的世界观、知识体系、技术和价值的唯一创造者。他们的世界完全是属人的世俗的世界。他们的政治是自由民主的政治,他们的经济秩序是‘社会市场’或‘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他们的伦理首先是人道主义。”“在艺术和个性方面,西方人特别罗曼蒂克,他们坚持把他们自己看作是自己生活的创造者。他们热爱‘时尚’,表现自我。每个人都想成为他自己,用自己的‘生活方式’安排生活。”(26)按照这种区分,古代北京实际对应的是“旧西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才真正面临同以美国为首的“新西方”打交道。 梳理中国人的“西方”观念,从汉唐时期的“西域”到宋元明时期的“西洋”,最后到明末清初以后出现的“西方”“泰西”,可以看出中国人的“西方”观之演变是与中西交通密切相连的一个概念,中西交通伸向哪里,“西方”的意含就指向哪里,“西方”可以说是一个流动不居的历史地理概念。“西方”这一名称往往表现的是一种异域、异种情调,即为华夏文明之外的化外之域或非我族类的文化,从文明程度来看,“西方”文明经历了一个从异域文明到强势文明的演变过程,在这一演进过程中,它既受到了中国文化的排拒,又常常通过交流、融会,为华夏文明所吸收。近代欧美的崛起,亦即“西方”的崛起,与华夏文明形成新的对峙,也是中国最重要的参照系。作为新兴的强势文明,西方在与大清帝国的军事对决中胜出,其在宗教、科技、军事、经济、政治、法律方面的优势地位因此确立。在西方文明的强大冲刺下,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和社会—文明结构逐渐解体,中华民族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谋求建设一种适合自我生存的新文明,中国在与西方的冲突、交流、融合中开始艰难的社会转型和步入现代化的历程。 ①②余太山撰:《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0页。 ③余太山撰:《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第258页。 ④《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 ⑤《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拂菻》。 ⑥《新唐书》卷二二一《西域传·拂菻》。 ⑦刘迎胜:《东洋与西洋的由来》,《走向海洋的中国人》,海潮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135页。 ⑧《重建清真寺记》,李景文、张礼刚、刘百陆、赵光贵编校:《古代开封犹太人:中文文献辑要与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 ⑨汪大渊著,苏继癫校释:《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33、178、187、214、218、240、264、280、318、325、339、352页。 ⑩周达观著,夏鼐校注:《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6页。 (11)周致中著,陆峻岭校注:《异域志》,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3、30页。 (12)万明:《从“西域”到“西洋”——郑和远航与人类文明史的重大转折》,《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期。 (13)参见巩珍著,向达译:《西洋番国志》,中华书局2000年版。 (14)参见黄省曾著,谢方校注:《西洋朝贡典录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 (15)万明:《从“西域”到“西洋”——郑和远航与人类文明史的重大转折》,《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期。有关“西洋”概念的探讨,还可参见洪建新:《郑和航海前后东、西洋概念考》,《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1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沈福伟:《郑和时代的东西洋考》,《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2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陈佳荣:《郑和航海时期的东西洋》,《走向海洋的中国人》,海潮出版社1996年版,第136~147页。 (16)刘迎胜:《海路与陆路——中古时代东西交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页。 (17)参见艾儒略原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7~118页。 (18)(20)(21)黄兴涛、王国荣编:《明清之际西学文本:50种重要文献汇编》第2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736、829~838、834~837页。 (19)黄兴涛、王国荣编:《明清之际西学文本:50种重要文献汇编》第2册,第740页。有关对艾儒略《西方答问》的研究,参见Mish,John L.:Creating an Image of Europe for China:Aleni's Hisfang Ta-wen Introduction,Translation,and Notes.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Vol.XXⅢ(1964)《华裔学志》23卷(1964)。 (22)黄兴涛、王国荣编:《明清之际西学文本:50种重要文献汇编》第4册,第1732页。 (23)艾儒略原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7页。 (24)黄兴涛、王国荣编:《明清之际西学文本:50种重要文献汇编》第1册,第233页。 (25)菲利普·尼摩著,阎雪梅译:《什么是西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26)Don Cupitt:The Meaning of the West,London:SCM Press,2008.pp 1-2.中译文参见唐·库巴特著,王志成、灵海译:《西方的意义》,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