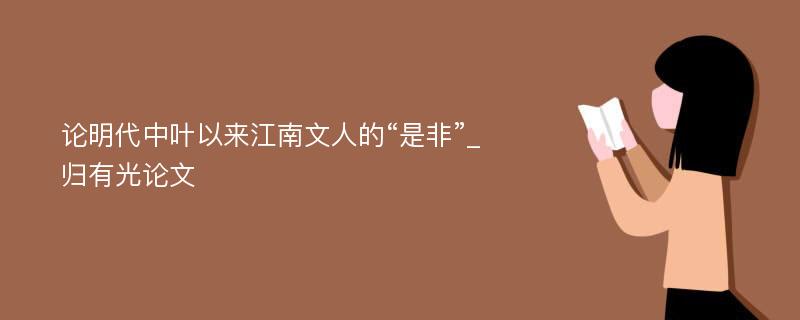
明中期以来江南学者的“是非”之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南论文,是非论文,学者论文,之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中期以来,即嘉靖、隆庆、万历至启、祯间,以至到清初,江南地区的一些学者如归有光、顾宪成、顾炎武和黄宗羲展开了“是非”问题的争论。本文试图对这一时期江南学者“是非”之论的发展演变,认识根源与社会根源,阶级实质,历史地位,提出初步看法,以期对明清之际批判专制主义思潮有更深入的认识。
一 “是非”之论的发展演变过程
江南学者的“是非”之论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由嘉靖、隆庆间昆山人归有光提出“国有大事必合天下之议”的廷议说开其端,经万历间无锡人顾宪成指出的东南地区出现了有别于“庙堂之是非”的“外人之是非”论,到明清之际昆山人顾炎武提出的“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议之”的清议说,和余姚人黄宗羲提出的“公其是非于学校天子不敢自为是非”的学校说,总结以往江南学者和思想家对是非问题的认识成果,而最终走上对“天子之是非”的批判。
归有光生活于嘉靖隆庆时,由于嘉靖以来吴中地区的社会变迁,他开始关心世务,是江南地区较早对是非问题进行争辩的学者。隆庆元年(1567),他代浙江乡试主考官拟定程策说:“国有大事必合天下之议……‘议,其尽天下之公乎?’……不专于一人,不询于一说,惟其当而已……汉制,大夫掌论议事,有疑未决,则合中朝之士而杂议之。自两府大臣,下至博士议郎,皆得尽其所见,而不嫌于以小臣与大臣抗衡,其道公矣”(注:《震川先生别集》卷之2上《隆庆元年浙江程策四道》。),这就是说国家大事应由“天下之议”来决定。
顾宪成生活于万历间,与他同时代且有交往和思想交流的王锡爵是太仓人。王锡爵曾给归有光写墓志铭,对归的学术和政治思想有相当的了解。万历12年(1583)王锡爵作为大学士,能参与机务,对神宗提出“辟横议”建议(注:《明史·王锡爵传》。)。万历14年,顾宪成到北京拜谒王锡爵,王告诉顾,北京有“异事”:“庙堂所是,外人必以为非;庙堂所非,外人必以为是”。顾也告诉王锡爵东南的“异事”:“外人所是,庙堂必以为非;外人所非,庙堂必以为是”。他们说完后,“相与笑而起”。他们决不是在搞文字游戏而是在谈论“庙堂”与“外人”两种对立的是非观。侯外庐先生指出“外人”隐指以顾宪成为首的反封建专制主义的一些在野势力(注: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第1110页,第1104页。);王锡爵和顾宪成对东南与朝廷在是非问题上的对立态度,是会心一笑。这说明万历时江南地区出现了有别于“庙堂之是非”的“外人之是非”;顾宪成说:“是非者,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注: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第1110页,第1104页。),表现了反对“朝廷之是非”而追求“天下之是非”的意愿。
明清之际黄宗羲提出“公其是非于学校天子不敢自为是非”的学校说,顾炎武提出“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议之”的清议说,把归有光、顾宪成对是非问题的争论推进了一步。黄宗羲赋予学校掌握政治是非标准的功能。他认为,古代,学校兼有设计治国方略任务,后代,“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天子荣之,则群趋以为是;天子辱之,则群挞以为非”:一切以朝廷的是非为是非实际造成了无是非的局面。书院曾一度掌握了天下是非权,和朝廷的是非发生了严重冲突,朝廷以武力和政治压制书院的是非,是非的标准又统一于朝廷,但天下随之而亡。他认为学校“必使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即学校不仅应养士而且应该掌握天下之公是非。在太学,选拔当世大儒或退休宰相为太学祭酒,其权威大于天子乃至宰相六卿,有权批评政治得失:“每朔日,天子临幸太学,宰相、六卿、谏议,皆从之。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郡县学,学官的权威大于郡县官,“郡县朔望,大会一邑之缙绅士子,学官讲学,郡县官就弟子列,北而再拜……郡县官政事缺失,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注:《明夷待访录·学校》。),他赋予学校以批评政治得失的功能。在政治是非问题上,顾炎武与黄宗羲有相通之处,他认为应该有“清议”以评论政治得失:“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然则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议之”,如子产不毁乡校,汉文帝止辇受言,唐宪宗以白居易乐府诗来观时事得失(注:《日知录》第19,“直言”。)。这种评论政治得失要靠皇帝接受人民劝谏、讽刺、议论来实现。
从归有光,到顾宪成、王锡爵,再到黄宗羲、顾炎武,对政治是非问题的争论过程基本如此。江南学者对是非问题的争论,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点。隆庆时江南学者要求对田赋、盐课、治河、边事等具体经济问题的发言权,如归有光就说“今庙堂方有郊社宗庙之议,而天下田赋未均,盐课折阅,历纪渐差授时之度,徐沛岁有治河之役,术良哈之属役翻为外应,受降城之故地弃为虏巢,则此数者,正今日之所宜考。毋谓汉卑而不足法,因是,而亦可以略追三代之遗文古义,而所谓法后王者,谓此也”(注:《震川先生别集》卷之2上《隆庆元年浙江程策四道》。)。这是提出应效法汉朝的廷议,来讨论、决定郊社宗庙和田赋、盐课、历法、治河、边事等国家大事的孰当孰否、孰是孰非。万历时,江南学者在要求对经济问题的发言权外,又发展为要求具体政治问题的发言权,表现为东林党人如顾宪成等人的“讽议朝政,裁量执政”(注:《明史·顾宪成传》。),谴责朝政的腐败黑暗,反对阉党及其爪牙的专权乱政,反对矿税,要求惠商恤民,减轻赋税等。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等对政治制度的大是大非问题展开批判。黄宗羲认为,明朝政治最大之“非”是明太祖罢宰相:“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宫奴掌握宰相之权;古代皇帝和臣只是一位之差,后世小儒神化君权,“天子之位始不列于卿大夫士之间”;汉唐宰相与皇帝坐而论道,宋朝宰相只能立谈,明废宰相而设廷杖,皇帝“遂谓百官之设所以事我,能事我者我贤之,不能事我者我否之”;应恢复汉唐宰相参与议政、批阅章奏的职权(注:《明夷待访录·置相》。),这具有限制皇权的用意。同时他们认为应扩大地方的权力,顾炎武提出“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即把辟官、莅政、理财、治军四权下放给郡县,使郡县既有其责又有其权(注:《日知录》卷9《守令》。)。自秦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以来,地方权力归于中央,归于皇帝,而他们提出恢复宰相制和扩大郡县政治经济军事等权力的主张,就是反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二 “是非”之论的根源
如历代封建皇朝一样,明朝的政治是非标准掌握在皇帝手中。明神宗说:“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虽各因时制宜,而与治同道,则较若划一”(注:《明会典·御制重修明会典序》,万有文库本。)。为什么明中期以来江南学者要起而争“是非”问题呢?我有许多原因。首先他们有独立的学术见解,关于顾炎武和黄宗羲的独立学术见解,学术界所论颇多,此不赘言。特别指出,归有光是明中期敢于反对以朱子之是非为是非的第一人。他认为朱子的传注有功于孔子,但真能符合孔子原意的不过十分之三四,六经非一人之说所能决定,朱熹以一人一时之见解,不能都符合孔子原意而无一言之悖(注:《震川先生集》卷10,《送王子敬之任建宁序》;卷9,《送何氏二子序》;卷10,《送许子云之任分宜序》;卷11,《赠张别驾序》。)。他批评“世儒果于信传,而不深惟经之本意,至于其不能必合者,则宁屈经以从传,而不肯背传以从经。规规焉守其一说,白首而不得其要者众矣”(注:《震川先生集》卷10,《送王子敬之任建宁序》;卷9,《送何氏二子序》;卷10,《送许子云之任分宜序》;卷11,《赠张别驾序》。),表达了反对经学上以朱子之是非为是非、以阳明之是非为是非的思想。这使他们敢于对一切是非问题进行重新认识。
其次,嘉靖以来苏松二府赋税之重和社会变迁使他们对赋税不均和吏治风俗变迁等民生利病、大是大非,进行议论批评。归有光说:“昔之为者非矣,而天下之民常安,田常均,而法常行;今之为者是矣,而天下之民常不安,田常不均,而法常不行,此可思其故”(注:《震川先生集》卷10,《送王子敬之任建宁序》;卷9,《送何氏二子序》;卷10,《送许子云之任分宜序》;卷11,《赠张别驾序》。);“吾县之人力耕以供赋贡……独于是非之实亦有不能昧者”(注:《震川先生集》卷10,《送王子敬之任建宁序》;卷9,《送何氏二子序》;卷10,《送许子云之任分宜序》;卷11,《赠张别驾序》。),要对“是非”、“是非之实”,进行“思其故”。他的朋友郑若曾认为苏松土壤条件是“水多而土淖,故田为第九等而下下”,但是“今日赋额之重惟苏松为最”,表示“愚不能无议”(注:郑若曾:《郑开阳杂著》卷11。)。东南学者特别重视赋税制度的沿革,归有光批评《一统志》和《明会典》没有反映各地山川原委、方物土贡、土壤等第,松江人何良俊批评《明实录》对典章制度记载失当,上海人王圻于万历间著成《续文献通考》。明亡后,顾炎武著《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重视典章制度是明中期以来吴中学者的共同学术特点,归有光、何良俊是较早倡议的,王圻是最有成就的,顾炎武和黄宗羲总结批判了专制主义经济制度的掠夺性和政治是非的独断性。由对江南重赋等民生利病问题的关注,到对记载经济政治是非的典章制度史的批判,再到对政治制度的总批判,表现了明中期以来江南学者由对东南民生利病的关注,到对典章制度史的不满,再到对社会制度的批判的曲折的认识历程。
再次,嘉、隆、万至启、祯间,江南人要求减免苏松赋税之意愿被苏松官员们嘲笑,而发展西北水利的建议和实践也被朝廷否定,使江南学者认识到争取政治是非决定权的重要性。嘉靖间,苏松官员“闻蠲赋之语往往相顾而笑”(注:《震川先生别集》卷之2上《隆庆元年浙江程策四道》。)而他们的三吴水利建议往往“格于因循积习之论”(注:《震川先生集》卷11,《送周御史序》;卷16,《常熟县赵段圩堤记》。),兴修西北水利以解决北京粮食供应的建议和实践最终也被朝廷否定。嘉靖19年归有光在南京乡试中提出西北水利建议,贵溪人徐贞明是西北水利的积极实行者。万历12年,长洲人申时行为首辅,歙县人许国为次辅,太仓人王锡爵兼文渊阁大学士,“三人皆南畿人,而锡爵与时行同举会试,且同郡,政府相得甚”(注:《明史·王锡爵传》。),他们支持徐贞明开畿内水田(注:《明史·申时行传》。)。徐贞明在京东地区开垦水利田39000余亩,而出身北方、占有大量荒地的宦官和官员担心水利修成会像江南一样纳税,于是在神宗面前反对这件事,徐贞明被迫退回家乡(注:《明史·徐贞明传》。)。这意味着江南人解决江南重赋问题的失败,归有光之子归予宁痛心地说:“徐公……开西北水利,诚百世之利,亦中止而不行。今东南民困已极……乃今西北之水田既废已久,而惟仰给东南一隅……予宁每怀杞人之忧”(注:归予宁:《论东南水利复沈广文》,《三吴水利录·附录》。),这使江南学者认识到政治是非的决定权比技术因素更重要。而明末东林党人的“是非”遭到朝廷压制的教训,更使复社中人黄宗羲认识到政治是非决定权的重要,他对以朝廷是非压制书院是非记忆犹新:“(书院)有所非也,则朝廷必以为是而荣之;有所是也,则朝廷必以为非而辱之”,于是禁伪学、毁书院。他认为“必欲以朝廷之权与之争胜”,使天下是非统一于朝廷,这“不特不能养士,且至于害士”。他痛心地指出镇压书院的是非权是明亡的原因:“使当日之在朝廷者,以其(学校)所非是为非是,将见盗贼奸邪慑心于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乃论者目之为衰世之事,不知其所以亡者,收捕党人,编管户口,正坐破坏学校所致,而反咎学校之人乎?”(注:《明夷待访录·学校》。)惨痛的教训使他更重视是非的决定权,因而赋予学校决定政治是非的功能。
最后,江南学者之间有学术和思想的交往和影响,归有光之于顾炎武,顾宪成之于黄宗羲,黄宗羲与顾炎武,都有间接或直接的影响。顾炎武与归有光同县,乡里相距不远,他与归有光之曾孙归庄是复社中同志好友,他们“入则读书作文,出则登山临水,间以觞咏,弥日竟昔,…归生与余无日不作诗,往来又日密,如是者又十年”(注:《顾炎武文》之《从叔父姆庵府君行状》。)。归庄编辑刊行了《震川先生集》,毫无疑问,顾炎武会受到归有光的影响。黄宗羲是复社中人,无疑受到东林党人的影响,他在《明夷待访录》中评论明朝政治、经济、军制等,其思想得到顾炎武的赞同。康熙15年(1676),顾炎武在蓟门致书黄宗羲:“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弊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炎武以管见为《日知录》一书,窃自幸其中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注:黄宗羲:《思旧录·顾炎武》。)日常交往或学术交流必然影响到思想。诸人的“是非”之论,虽然语言表达形式不同,但实质是一致的。
三 “是非”之论的实质及历史地位
归有光的廷议论,顾宪成的“外人之是非”论,顾炎武的庶人议政论,及黄宗羲的学校是非论,其实质是什么?他们果真认为政治是非应由全体人民决定吗?非也。他们其实是在要求江南富户对国家大事的决定权。归有光对苏松二府田赋之重和江以南赋税不均十分不满,他说:“江右田土不相悬,而税入多寡殊绝……苏州田不及淮安半,而吴赋十倍于淮阴;松江二县,粮与畿内八府十七县埒,其不均如此。”(注:《震川先生集》卷25,《通议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状》;卷9,《送县大夫杨侯序》;卷8,《昆山县倭寇始末书》。)他看到东南民力衰竭与国家赋税之矛盾,说:“东南之民何其疲也?以蕞尔之地,天下仰给焉……东南民力物产虽号殷盛,而耗屈已甚,非复囊昔。”(注:《震川先生集》卷25,《通议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状》;卷9,《送县大夫杨侯序》;卷8,《昆山县倭寇始末书》。)他认为吴中富民的破产是因为嘉靖以来苏松重赋,根本原因是国家取之东南用之西北,因此他提倡西北水利和东南水利,而又认为国家应该实行“安富之道”,保护“大户”富民的利益(注:《震川先生集》卷25,《通议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状》;卷9,《送县大夫杨侯序》;卷8,《昆山县倭寇始末书》。)。同时,昆山人郑若曾著《苏松浮赋议》,用具体数字论证明朝苏松二府田赋总额311万石,比宋元时100万石增加三倍,比湖广和福建两省赋税总额还多10万石,比直隶其他12府78县赋税总额165万石多近二倍;苏松赋重直接损害“有田者”的实际利益,“苏松……有田者为赋役所困,竟竟乎朝不保夕”(注:郑若曾:《郑开阳杂著》卷11。),他认为“天下惟东南民力最竭,而东南之民又惟有田者最苦”(注:郑若曾:《江南经略·凡例》。)。万历时武进人唐鹤征著《武进志》,对江南民田重赋表示不满。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写下《苏松二府田赋之重》专文,对“国家失累代之公田而小民乃代官佃纳无涯之租赋”,感到“事之不平,莫甚于此”,认为要改变富民的破产,应重新丈量土地、定其土壤等第、依等纳税(注:《日知录》卷12,《苏松二府田赋之重》。);黄宗羲认为每户应授田五十亩,其余土地听富民自占。同时他们都反对朝廷对东南的经济掠夺,归有光批评“天下之大而专仰给东南”、“取者无穷而民生日蹶”(注:《震川先生别集》卷之2上《嘉靖庚子科乡试对策》。),顾炎武批评“今之人君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注:《亭林文集》卷1《郡县论》。)的经济掠夺,*
宗羲对“江南之民竭于输挽,大府之金钱靡于河道”(注:《明夷待访录·建都》。)和“郡县之赋……解运之京师者十有九”(注:《明夷待访录·田制一》。)的赋税、漕运之制深为不满。他们关心江南民生利病,或者确切地说是关心江南“有田者”即富民的利益,而反对朝廷的无限权力,反对朝廷对东南富民的经济掠夺。因此其是非之论的实质,是要求江南富民对国家政治是非的议政权和决定权,是有其阶级和地域特色的。
明中期以来江南学者的是非之论,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封建社会判断政治是非,主要依据“上之是非”和“古之是非”,“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注:《墨子·尚同》。);“古之所是则谓之是,古之所非则谓之非”(注:李觏:《直讲李先生文集》卷29。)。这两条也就是皇帝的是非标准和孔子的是非标准。前者是政治的,法律的;后者是学术的而又为政治服务。君主专制统治有渐强之趋势,但明中期以来出现了反君主专制的思想,这种反对基本沿着两条线开展而又不是绝然分开。李贽是从学术方面坚决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思想家,他指出,汉唐宋千百余年间“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等于无是非,而提倡“今日之是非”(注:《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并用于历史评论中。归有光、顾宪成、顾炎武、黄宗羲是从政治经济方面反对“天子之是非”而提倡“天下之是非”的学者和思想家,他们的“是非”之论,具有明显的反专制主义的特点。对顾宪成、顾炎武、黄宗羲的反专制主义思想,不难理解。对归有光则需多说几句,他提出应效法汉朝的廷议,由廷议讨论、决定郊社宗庙和盐铁、历律、河渠、边事等重大问题孰当孰否、孰重孰轻、孰是孰非,这说明什么呢?汉朝的廷议制对皇权有制约,何兹全先生指出:“皇帝的废立、国家大事、立法、官爵封赠等,皆可由廷议提出意见或由廷议作出决定。廷议由皇帝诏令召集,意见由皇帝最后裁决。这种制度……对皇帝权力不无限制作用。”(注: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315—316页,河南人民出版社。)归有光提倡效法汉朝廷议,应该认为具有限制皇权不顾盐铁、治河、边事等有关民生利病国家安危问题,而一味讲究郊社宗庙的思想意识。尽管元人邓牧早已有民主思想,但那是他的“独鼓”之音(注:《伯牙琴·自序》。)。明中期以来江南学者的“是非”之论,不仅在当世有知音,而且在晚清有梁启超、谭嗣同这样的同调,对鼓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起了思想启蒙作用。
最后要强调的是,明中期以来江南学者的“是非”之论对明清之际批判专制主义思潮的产生有思想启发作用,因为尽管有明清更迭对顾炎武、黄宗羲的影响,但促使归有光、顾宪成等人起而争是非决定权的社会经济根源,即东南民生利病,不仅没有好转,而且在明末越发严重,成为广泛的“天下郡国利病”。由对江南重赋等东南民生利病问题的关注,发展为经济、政治是非标准的争论,通过对记载经济政治制度的典章制度史的不满、批评、研究之折射,最后走上对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总批判,这就是明中期以来江南学者基本的心路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