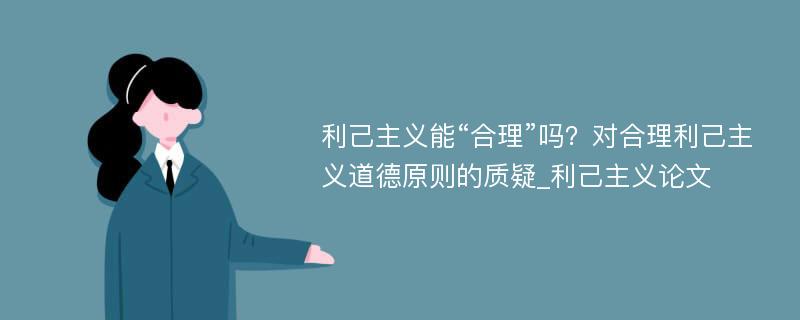
利己主义能够“合理”吗?——对合理利己主义道德原则的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利己主义论文,道德论文,原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究竟应该信奉怎样的道德原则,目前理论界尚存在诸多的争议。但与理论界的疑虑与争议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当今中国人的行为实践中,却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选择了合理利己主义的处世之道。一些人甚至认为这是适应市场经济的最合乎理性的道德选择,还有一些人则声称这一原则是超越集体主义和利己主义之上的一种全新的“第三种道德”。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本文拟就合理利己主义道德原则作一理论剖析。我们的分析将表明,合理利己主义恰恰是不合理的,因而它无法成为我们所应信奉的基本道德原则。
合理利己主义伦理原则的思想史考察
对人类思想史的考察表明,利己主义的伦理学说是建立在人类的所谓生存和发展的利己天性上的。这种理论认为,为了生存和发展,人就天性而论是利己的,这是人作为动物所有的一种自然本能特性。在古希腊伦理学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那里,便已论及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生物倾向性”。他认为人一方面是理性的政治动物,另一方面人又还总是自然界的一种生命存在,故总有利己的欲望和冲动。亚里士多德之后的中世纪宗教神学则使人性的探讨走向了异化。中世纪的伦理学家们承认了人有利己的天性,但认为这和神性相离,因而是应遭诅咒的“恶”之品性。但这种对利己倾向的诅咒,并未真正消灭人的天性中真实存在的利己欲望的骚动。相反,即使在宗教神职人员中,也正如《十日谈》中尖刻讽刺的那样,有相当多的人是一些道貌岸然的利己主义者。
所以,文艺复兴运动对中世纪的以神性压抑人性的异化现象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在人性问题上,一大批思想家们的观点惊人地一致,这就是承认人的利己天性的合理性。他们认为利己心是人固有的权利,道德应从这种现实的人性出发。这种思想经过启蒙思想家的论证和发展,到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那里得到了全面的阐述,并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所谓合理的利己主义思想。主张合理的利己主义的思想家们坚信,人就其本性来说是自私利己的。但人的群体性生存本性又决定了每个自我必须对这种自私利己之心有所克制,在追求个人幸福的时候要兼顾他人的存在。否则,利己的追求必然要受到他人的干扰和阻碍,最终势必危及利己心和自身幸福的实现。为此,费尔巴哈曾有过如下一段著名的说法:“为了自保为了享受幸福,与一些具有与他同样的欲望、同样厌恶的人同住在社会中。因此道德学将向他指明,为了使自己幸福,就必须为自己的幸福所需要的别人的幸福而工作;它将向他证明,在所有的东西中,人最需要的东西乃是人。”
由此可见,合理利己主义思想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必然产物。这种伦理道德原则把呻吟于中世纪神性压抑和专制下的人性解放出来,这无疑具有历史的进步性。而且,合理的利己主义理论还有一个可取之处,这就是它并没有只停留在自私利己的自然本性中认识人,而且还同时意识到人总处于与别人的社会关系之中。因此,我们暂且不论这种伦理主张在实践中是否可行,但至少在理论上它强调必须兼顾他人,自我节制地去追求个人的幸福的观点比之彻底的利己主义或极端个人主义无疑要合理一些。
合理利己主义的窘境与实质
然而,合理利己主义从根本上讲是不合理的,因为它不可避免地要在生活实践中使人陷于窘境。
我们知道,合理利己主义内含了一种最基本的逻辑:人是自私的。从人是自私的基本点出发,这种理论仅把自己视为目的,而他人只是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这一点无论是合理利己主义理论的倡导者,还是信奉者都明白无误地承认的。费尔巴哈就说:“爱别人,就是爱那些使我们自己幸福的手段,就是要求他们生存,他们幸福。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的幸福与此相联系。”爱尔维修则声称,“如果爱美德没有利益可得,那就决没有美德。”但是,显然所有的人都要把自己视为目的,而把他人作为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这样的结果是目的与目的、手段与手段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而且,冲突的最终结果又不可能做到合理地自我节制。因为合理的自我节制只是为了实现自我幸福这个利己目的的一个手段。如果这个利己目的也在节制中丧失了,那么,不仅自我节制的手段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失去目的手段本身也就不再可能存在了。
因此,合理的利己主义在实践中最终无非是两种结果:其一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行为的出现。因为手段要服从于目的,“合理”作为手段是为利己的目的服务的。当手段无法“合理”时,目的就会使得他放弃这种手段,采取极端自私的行为来实现利己的欲望和目的。这种由合理利己主义走向极端利己主义的情形,在历史和现实中都是屡见不鲜的。其二是利他主义与自我牺牲行为的出现。这是合理利己主义在实践中的另一个比较罕见的结果。也就是说,当“合理”的手段与“利己”的目的发生冲突时,行为主体能自觉或被迫地牺牲目的,以维持手段的合理性。而这必然或多或少地以自我的某种牺牲为代价。爱尔维修虽然竭力宣称“人都为利己的目的而存在着”,但他自己的一生却表明他并没有去追求这一目的。他在反对专制政府和天主教会的斗争过程中,在书被焚毁、人身遭到攻击迫害的情形下,依然著述不止。这正如狄德罗指出的那样,显然不是自私的目的所能解释的,而是一种追求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使然。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看,合理利己主义追求最终必然使行为主体陷于一种窘境。
或者是走向极端利己主义。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考察,合理的利己主义几乎从来未被真正实现过。这就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对多数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所给予的尊重,即使一般说来多些,也未必比奴隶制或农奴制所给予的多。”现代西方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普遍冷漠,正义感和热忱感的消失,如萨特等一大批哲学家所深刻揭示而又无力改变的“他人即地狱”境况的出现,都证明着追求合理利己主义道德理想的破灭。
或者是放弃利己主义,走向利他主义与自我牺牲。这是合理利己主义者的一种更改初衷的追求。这种追求必然以某种程度的自我牺牲作为代价,规范自我本能属性中的利己倾向,从而在这过程中造就完美的人性。但这种道德追求显然已不是什么合理利己主义所能解释的了。也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如下一段论述:“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理论上既不是从那感情的形式,也不是从那夸张的思想形式去领会这个对立……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因此,在利己主义和自我牺牲之间,从来不存在折衷的所谓合理利己主义。
我们认为,使合理的利己主义走向这种窘境的最根本的根源在于,合理利己主义的道德追求,实质上本身就是一种虚假的不合理的追求。即便从语义学的角度分析,合理的利己主义从实质上讲,依然是以利己主义作为基本出发点的,所谓的“合理”仅仅是附加的一个要求。我们知道,道德和法同作为人的行为规范,其不同之处就在于法是外在强制性的,而道德则是内在的自觉自愿。这样,只要以利己主义为目的并以此为目的准则去为人处事待人接物,那么一旦行为无法“合理”时,利己主义的目的便自然要抛弃“合理”的手段。至于那些能放弃利己主义而甘愿自我牺牲的人,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他们的确已不再是利己主义者了。所以,合理的利己主义依然是一种利己主义,其“合理”的手段因为利己主义的目的,几乎从来没有真正地被实现过。
合理利己主义原则的非道德性
不仅如此,合理利己主义的不合理性,还在于以合理利己主义作为人性的道德规范,从实质上讲,正是把人降低为动物存在的一种非道德的追求。道德之所以必要,恰恰因为道德是用以规范人的自然属性中那些类似于动物的自私、利己本能特性的。人就其自然的本能属性而言,的确存在极多的“利己”品性。所以,恩格斯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决定了人永远无法摆脱兽性,所以问题只能在于摆脱的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和人性在程度上的差异。”也许从这一点上讲,孟子提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的思想,并把人和动物之异归结为人有仁义礼智这些最基本道德规范的思想是深刻的。我们把道德理解为人性的自觉规范正是基于这个根本的出发点。如果我们依然只是以自私、利己和利己主义作为道德规范的基本原则和出发点,那么,道德的存在就没有必要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利己主义”是每个人从自然本能的特性上讲就存在的。而道德正是借助于自觉的理性和意志,对这些自然本能的属性进行自觉的规范,没有这些自觉规范,那么人就降低为一种只凭籍“生存竞争”的自然法则而生存的动物性存在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道德的自觉规范,对人显示了最重要的意义。这不是道德说教,而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规定。
所以,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承认人有“饮食男女”之类的自然本能的属性,我们暂且可以称之为“利己”的天性。但另一方面又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注定要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他总是自觉意识到自己与他人、与集体、与社会处于一种不可分离的联系之中。这样,尽管人有和动物一样的自私、利己的本能特性,但人却能够为维护一定的关系而自觉地以理性来规范这种本能属性。所以,人不可能像动物那样在生存竞争的搏杀和争斗中去实现自己的天性,而总是能依据一定的社会为其成员制定的行为规范和法则,去实现自己的各种人生理想追求。而这些行为规范与准则内化为每个人内心的信念,便是道德。也因此,人们习惯地把道德定义为依据人的内心信念调整人们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
可见,从道德本身的含义上讲,它恰恰具有利他主义的倾向。因为规范自己利己的天性,就意味着有某种程度的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的因素存在。而我们通常所谓的道德境界的高尚与否,无非也就是行为中具有多少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也因此,我们认为把合理利己主义奉为人生的一种道德原则,恰恰是非道德的,或者说这种追求正是对道德本质的否定。当然,道德对人利己的自然本性的规范不是泯灭人的自然性,而是以后天的德性去调整和节制自然本能方面的天性,使人在自己生存和发展的追求与满足中能合乎人性,亦即合乎人的社会性。这也就是中国古代哲人讲的以德性去改造天性,成为人性的过程。
弘扬真正的集体主义原则
既然合理利己主义追求丧失了其合理性,那么,我们就必须以一种真正合理的道德原则来取代这种实质上必然表现为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道德原则。在我们的理解看来,这个原则只能是真正的集体主义原则。我们在这里之所以特别强调“真正”的集体主义,那是为了区别以往“左”倾思潮影响下的那种集体主义说教。我们认为,既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所应信奉的道德基本原则依然是真正的集体主义原则。
其一,真正的集体主义原则超越了利己主义的藩篱。因为集体主义揭示的一个最基本事实是,任何个人利益的实现都有赖于整体利益的实现。这就如马克思说的:“我们知道个人是微弱的,但是我们知道整体就是力量。”而且,由于人永远处于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交织之中,只关注个人利益追求必然会破坏整体利益的实现,因而不为社会和集体所容忍,从而最终也无法实现个人利益的追求。
其二,真正的集体主义也摈弃了抽象的利他主义和片面的自我牺牲的道德说教。这种集体主义道德原则承认,人不仅从自然属性上有利己自私的“天性”,而且从后天德性培养中也同样必须承认人有个人利益的追求。这正如马克思所理解的那样,人的自我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永远应该成为目的。因此,“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所以,完全脱离个人利益,离开人的自身发展的利他主义、自我牺牲或者为利他而利他、为牺牲而牺牲的所谓道德理想追求都是一种不合理的道德说教。
其三,真正的集体主义道德原则恰恰是每个人自我实现的必要条件。关于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对于自我实现的必要性,前苏联著名的伦理学家季塔连柯曾这样归纳道:“首先,集体保证经常性的交往、合作和辩论,这些是使个人内心安宁,使个人理智和感情增长的需要;其次,巨大而宏伟的目标要求集体的努力来实现,就是在那些似乎纯粹是个人活动的领域里,也要求有集体主义的处世态度;第三,全面地发展个性,要求全面地去活动,要求多方面去掌握社会力量;第四,集体主义是强调所有人的自由发展,所以离开集体主义基础组织起来的社会,这种发展是不可思议的。”因此,那种认为集体主义抹杀个性的说法只是无稽之谈。恰恰相反,在我们看来,集体主义正是个性发展的一种最完美的形式。
基本的结论
归纳如上所述,我们也许可以得出如下两个基本的结论:
结论之一:合理利己主义原则决不是什么新的“第三种道德”。事实上,它是产生于近代西方社会的一个主流伦理思潮。尽管合理利己主义理论和实践在反封建专制的斗争中有过一定的启蒙意义,但是,把合理利己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的道德追求则是错误的。这个错误不在于承认了人的所谓自私利己的自然属性,而在于放任了这种自然属性。事实上,道德作为对人性自觉的规范,恰恰要对利己的自然属性进行真、善、美的规范。也因此,合理利己主义从来无法真正实现。所以,费尔巴哈在论述合理利己主义原则时一方面教导人们“对己以合理的节制,对人以爱,”但另一方面他不自觉地也意识到人们往往做不到这一点,故憧憬一种“新道德的出现”。
结论之二:道德的基础决不是合理利己主义,而是一种真正的集体主义。这是一种基于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相结合的行为规范。因为,人是个体的存在,故有个人利益;但人又是社会的人,故又有整体利益。个人利益的追求往往凭本能、天性便可获得,而整体利益的维护更多地要依靠道德的自觉规范。这也可以说是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社会本体论根据。普列汉诺夫曾非常深刻地指出过这一点:“实际上,道德的基础不是对个人幸福的追求,而是对整体的幸福,即对部落、民族、阶级、人类幸福的追求。这种愿望和利己主义毫无共同之点。相反地,它总是要以或多或少的自我牺牲为前提。”因此,道德对人性的自我规范往往要以某种程序的自我牺牲为代价。正是在这个自我牺牲中,我们感受到自己对他人,对社会的价值,我们有了自身的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实现。也正是在这个自我牺牲中,我们使自己变得完善和崇高,从而造就自己的理想人格。我们的时代呼唤这样一种理想人格;我们坚信,我们的时代也能够造就这样的理想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