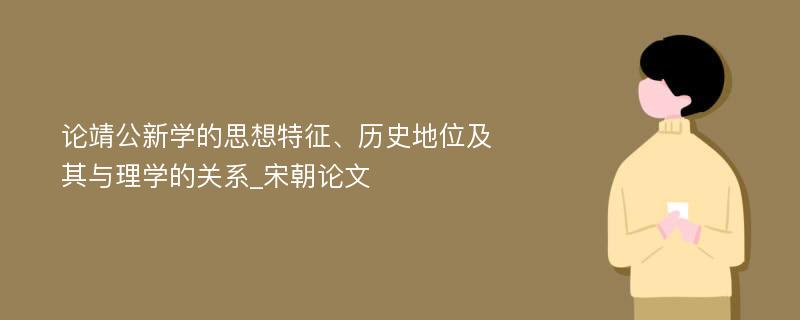
论荆公新学的思想特质、历史地位及其与理学之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学论文,特质论文,地位论文,思想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03)03-0086-06
一
王安石的学术与思想被后人称为“荆公新学”,是北宋中后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形态。梁启超在《王安石传》中,盛赞荆公之学术“内之在知命厉节,外之在经世致用,凡其所以立身行己与夫施于有政者,皆其学也。”(注:《王安石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第204页。)并讥讽程朱理学之所倚重者,“在身心性命,而经世致用之道,缺焉弗讲。”(注:《王安石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第204页。)是以王安石新学包举儒家内圣外王之道,而濂洛关闽之学不过“经述之一端”耳。但是,现代学术研究的深入拓展使人们逐渐认识到,王安石学说亦是以接续孔孟之道为己任,以内圣外王为基本框架,在恪守儒家本位的基础上,融通佛老,兼采诸子,其规模阔大宏伟,然其学术特征还是以道德性命之义理为主旨而展开的。“在北宋一代,对于儒家学说中有关道德性命的义蕴的阐释和发挥,前乎王安石者实无人能与之相比”,“应为北宋儒家学者中高踞首位的人物。”(注:邓广铭《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今天的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新学与理学这两种宋代思想史上最为著名的思想派别所存在的内在关联。徐洪兴在《思想的转型:理学发生过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中就有阐发。此外,对荆公新学及其与理学关系的探讨,马振铎《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的哲学思想》,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李祥俊《王安石学术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萧永明《北宋新学与理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为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三部成果。)的确,和任何思想的出现一样,新学的产生尽管有极为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但在理论形式上,它仍要以以往的思想资料作为出发点,其主张无论如何创新,总是依傍六经,从中找出立论的依据。新学所依傍的重要的儒家经典就是被誉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周易》在相当程度上模铸了荆公新学。
从宋初三先生开始,宋儒就对《周易》有浓厚兴趣。胡瑗、石介都有注《易》的著作传世。范仲淹之《易义》、欧阳修之《易童子问》、周敦颐之《通书》(又称《易通》),均重视《周易》研究,借《易》之内容发挥其本人的思想。程颐的《周易程氏传》更是踵其前武而过之。理学的实际开创者——北宋五子,都精于《易》。
正是在这种社会氛围和学术语境之中,王安石亦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将目光集中于先秦儒家的最高哲学典籍《周易》。其一生治《易》之得,早年有20卷的《易解》(今亡佚),此书比《东坡易传》与《周易程氏传》还早,是王安石学术思想基本形成的标志,是荆公新学的发端之作。中年有《易象论》、《大人论》、《易泛论》、《九卦论》、《卦名解》、《河图洛书义》等,是构成荆公新学主干之著作。王安石的易学实为新学的中心线索。
王安石的易学思想相当完备,他认为,自有生民以来,《周易》最为深邃:“自生民以来,为书以示后世学者,莫深于《易》”(注:《王文公文集》第七卷《答徐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在他的心目中,《周易》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易》之为书,圣人之道于是乎尽矣。”(注:《王文公文集》第二十九卷《大人论》。)儒家的微言大义全部包含在《周易》之中,“通天下之志在穷理,同天下之德,在尽性。穷理矣,故知所谓咎而弗受,知所谓德而锡之福;尽性矣,故能不虐茕独以为仁,不畏高明以为义。”(注:《王文公文集》第二十五卷《洪范传》。)易道可以统摄儒家穷理尽性之学,通晓易道,即可臻于仁义之境。
对性命之理的关注固为荆公易学之核心,也是新学与濂、洛、关、蜀、朔之学的相通之处。然而,内圣与外王并重,则是荆公新学的鲜明特征。在王安石看来,《周易》一书包举综核内圣外王工夫,“万物莫不有至理焉,能精其理,则圣人也。精其理之道,在乎致其一而已。致其一,则天下之物可以不思而得也。《易》曰:‘一致而百虑’,言百虑之归乎一也。苟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则可以入神矣。既入于神,则道之至也。”(注:《王文公文集》第二十九卷《致一论》。)致一乃内圣工夫,近乎孟子所云之尽心、知性、知天。《系辞》有言曰:“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荆公发挥道:“此言神之所为也。神之所为虽至而无所见于天下。仁而后著,用而后功。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及其仁济万物而不穷,用通万世而不倦也,则所谓圣矣。故神之所为,当在于盛德大业。”(注:《王文公文集》第二十九卷《大人论》。)
王安石认为致一工夫必进于致用方能显现其功用,“内圣”必须开拓出“外王”,“圣”与“王”之间存在着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圣”和所以成圣的心性本体是本质,理想的社会政治秩序是“王”者治理的结果。所以,“致用之效,始见乎安身。盖天下之物,莫亲乎吾之身,能利用以安吾之身,则无所往而不济也。”(注:《王文公文集》第二十九卷《大人论》。)
圣人乘天地正气,秉人间真运,以自己伟大的人格感召天下,从自然万物到芸芸众生,在这种力量的感召下各得其序,丰亨豫大的王道世界降临于人间。在内圣与外王并重的王安石看来,盛德大业往往比内蕴之仁更值得歌颂与称道,“夫身安德崇而又能致用于天下,则其事业可谓备也。”(注:《王文公文集》第二十九卷《大人论》。)荆公追求的是一种功利性的泛利天下的功业,这也是其变法理论的基石。
二
从思想史的角度审视,荆公新学是第一个成功地全面取代汉唐注经之学的义理之学。是真正居于思想界统治地位的新儒家学说。这点尤为重要。理学的发生要早于新学,且理学之特质也是以义理的获得为区别于以往儒学注经之学的理论形态。但直至南宋晚期,它一直或即或离于政治权力圈,从未真正成为思想界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事实上,荆公新学建立伊始,便以思想深邃博大以及特有的革新精神,震惊当时的思想界。后来苏轼在《王安石赠太傅敕》中这样评价王安石:
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注:《苏轼文集》第三十八卷,中华书局,1986年。)。
尽管有人说苏轼此言暗寓讥讽之意,但也道出荆公新学特有的革新精神。陆九渊的评语:
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注:《陆九渊全集》卷十九《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中国书店,1992年。)。
新学之精髓不仅蕴藉于荆公易学之中,其对经学之革新还可从作为新学建立标志之一的《洪范传》中考察得到。《洪范传》不同于汉儒章句训诂之学,它看重阐述《洪范》中圣人的“妙道至言”,并借此发挥荆公本人的哲学与政治思想,也就是东坡所言之“断以己意”。汉儒由于劬劬于章句训诂而置经典大义于不顾,因而既不能阐明经典中的思想,更不能发挥自己的观点。王安石对这种束缚思想的经学形式加以改革,使之成为借阐明经典大义而发挥自己思想的新经学,这就为思想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
全祖望续修的《宋元学案》卷九十八《荆公新学略》引刘静春云:“介甫不凭注疏,欲修圣人之经,不凭今之法令,欲新天下之法,可谓知务。”肯定了王安石在学术、政治方面破旧立新的变革精神。即以《洪范传》而论,其优胜于汉唐旧说者所在多多,晁公武云:
安石以刘向、董仲舒、伏生明灾异为蔽,而别为此《传》。以“庶征”所谓“若”者不当训“顺”,当训“如”,人君之五事,如天之雨、阳、寒、燠、风而已。大意言天人不相干,虽有变异,不足畏也(注:《郡斋读书志》卷一上《洪范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彻底否定了秦汉以来儒学中存在的神秘主义的天人合一说,消除了汉儒所加于“天”的妖妄荒诞的色彩,将“天”所发挥的作用限制在利益庶物,四时递行,万物资始的范围之内,为宋代寻“理”之风拓开了通途。荆公新学在学术史与政治史上所占有的地位,所打下的深刻烙印,是不容抹杀的客观事实。当元祐更化之际,新法遭到全面废除,但新学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地位。全祖望陈述道:
荆公《三经新义》至南渡而废弃。元祐时,不过曰“经义兼用注疏及诸家,不得专主王氏之解”。所禁者《字说》耳。独莆田黄隐作司业,竟焚其书,当时在廷诸公不以为然,弹章屡上。按《山堂考索》所载,元祐年十月癸丑,刘挚言:“国子司业黄隐学不足以教人,行不足以服众。故相王安石经训,视诸儒义说,得圣贤之意为多。故先帝立之于学,程式多士。……隐猥见安石政事多已更改,妄意迎合,欲废其学……”同时吕陶亦言:“经义之说,盖无古今新旧,惟贵其当。先儒之传注未必尽是,王氏之解未必尽非(注:《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九《记王荆公〈三经新义〉事附〈宋史经籍志〉》,四部丛刊本。)。
又,《宋史》卷三百一十五《韩维传》载:
执政欲废王安石新经义,维以当与先儒之说并行,论者服其平。
刘挚在学术、政治上属朔学、朔党,吕陶属蜀学,韩维与二程、吕公著等交往颇深,在政治上亦属保守派的阵营。此数人皆非王安石一派,其论新学如此,则是比较公平的。黄庭坚《赠晁无咎》诗云:“荆公六艺学,妙处端不朽。诸生用其短,颇复凿户牖。譬如学捧心,初不悟己丑。玉石恐俱焚,公为区别否?”(注:《山谷外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把荆公新学与末流区别开来,对荆公新学的评价甚高。南宋黄震尝言:“汉唐老师宿儒,泥于训诂,多不精义理”(注:《黄氏日抄》卷八十二,清乾隆三十二年重刻本。)。荆公新学不仅“脱去训诂”,而且在两宋理学所侈言的“道德性命之学”方面,荆公也是自开户牖,自树一帜的先驱。北宋晁说之尝云:“南方之学,异乎北方之学,古人辨之屡矣。大抵出于晋魏分据之后,其在隋唐间犹云尔者,不惟其地而惟其人也;盖南方北方之强,与夫商人齐人之音,其来远矣。今亦不可诬也。师先儒者,北方之学也,主新说者,南方之学也。”(注:《晁氏儒言》之《南北之学》,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在这里,我们当然不能机械地、片面地理解所谓的南方北方之学,但荆公新学之为南方之学中坚而成为11世纪出现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种新型的文化模式——“宋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几乎是毋庸置疑的。那么,荆公新学是通过什么途径取得思想界的统治地位的呢?
首先,王安石的思想与学术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承认。这一点,在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时代显得尤其重要,荆公要使自己的经术服务于世务,必须先得到皇帝的认可:
(熙宁)二年二月,拜参知政事。上曰:“人皆不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经术不可施于政务尔。”(注:《宋史》卷三百二十七《王安石传》,中华书局,1977年。)
为适应“所遭之变,所遇之势”,经常措置天下之政务,针对宋朝已积贫积弱的现实,提出了富国强兵的变法主张,这就深深地打动了年轻的急欲奋发有为的宋神宗的心灵,使君臣二人在政治见解上达到了惊人的一致,表现出一种牢不可破的团结,为王安石践履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张扬自己的学术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程就看清了这一点,曾道:
浮屠之术,最善化诱,故人多向之。然其术所以化众人也,故人亦有向有不向者。如介甫之学,他便只是去人主心术处加功,故今日靡然而同,无有异者,所谓一正君而国定也(注:《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下,《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50页。)。
专制时代,一种学说如要取得思想界的统治地位,非要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肯定和信奉不可。新学如此,后来的理学亦是如此。正是因为荆公新学专“去人主心术处加功”,并得到宋神宗的认同,它才取得了思想界的绝对主导地位。
其次,王安石把《三经新义》和《字说》颁行于学校。以经义作为取士之衡准,使新学成为每个士子必须掌握和信奉的思想,同时也就排挤了其他学说。事实很清楚,当学校中士子诵习的是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字说》时,当学者们著书立说,根据也是《三经新义》和《字说》时,天下“靡然而同,无有异者”就是一种顺理成章的结果了。元祐年间,荆公新学在思想界的统摄力一度有所下降,但绍圣之后,荆公新学重新统治思想界,而且过去不曾颁行于学校的新学其他著作,也“行于场屋”。据载:
介甫《三经新义》皆颁学官,独《易解》自谓少作未善,不专以取士。故绍圣后,复有龚原、耿南仲注《易》。三书偕行于场屋(注:《郡斋读书志》卷一上《洪范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论语解》十卷……王安石介甫撰。绍圣后,亦行于场屋(注:《郡斋读书志》卷一下。)。
介甫素喜《孟子》,自为之解。其子雱与其门人许允成,皆有注释。崇、观间,场屋举子宗之(注:《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二。)。
这种情况至南宋立国后学术抉择发生戾转才得以改变。新学“独行于世者六十年”。从当时对荆公新学与新法持激烈批评意见者的表述来看,新学在北宋中后期确实处于一种炙手可热的地位:
今之治经以应科举,则与古异矣。以阴阳性命为之说,以泛滥荒诞为之辞,徒诵熙宁所颁《新经》《字说》,而佐以庄、列、佛氏之书(注:刘挚《忠肃集》卷四《论取士并乞复贤良科疏》,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
钱景谌以为荆公新学:
至于教人之道,治人之术,经义文章,自名一家之学,而官人莅政皆去故旧而务新奇,天下靡然向风矣。乃以穿凿六经,入于虚无,牵合臆说,作为《字解》者,谓之时学,而《春秋》一王之法独废而不用。又以荒唐诞怪,非昔是今,无所统纪者,谓之时文。倾险趋利,残民而无耻者,谓之时官。驱天下之人务时学,以时文邀时官(注:《邵氏闻见录》卷十二,卷十五,中华书局,1983年。)。
钱景谌等人的愤懑之情乃是建基于正统儒学立场之上的一种道义评判,他们不能理解荆公新学所反映的北宋中期的时代要求,这种要求就是当时社会普遍兴起的改革要求,因此,“介甫今日亦不必诛杀,人人靡然自从。”(注:《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下,《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51页。)魏泰《东轩笔录》卷六载:“王荆公在中书,作新经义以授学者,故太学诸生几及三千人,以至包展锡庆院、朝集院,尚不能容。”其所掀起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化革人心”的巨大浪潮,几乎席卷北宋社会的一切领域。从思想史角度观察,荆公新学“独行于世者六十年”,指导了中国专制时代最大的一次改革运动,而这次改革运动及其余波末流,震动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的一些具体措施尽管在荆公身后逐渐归于消寂,但其影响一直持续整个中国专制社会后期。梁启超评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注:《王安石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第1页。)。也就是说,北宋以后历代王朝所实行的法度,是渗透着荆公新学的精神的。当然,有许多法度措施完全失去了王安石制定它们时的进步意义,成为统治者手中的枲剥工具,但那是另一个领域的问题。从来源考察,则不能否认荆公新学对后世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发生的巨大影响。即以科举考试而论,王安石改以往的诗赋取士为经义取士,对元、明、清三代科举制度的影响至为显著,所以皮锡瑞说“王安石所立墨义之法”,“元人因之,而制为四书五经义,明初用四书义,后乃改四书五经义。具破承原起之法,本于元王充耘《书义矜式》,义本于吕惠卿、王雱义”(注:《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第277-278页。)。王安石的以经义取士,几经演变,终于成为八股取士制度。
三
荆公新学主导北宋后期思想界的几十年里,正是理学形成时期。尽管周敦颐在王安石建立新学之前就构建了濂学思想体系,张载在王安石建立新学的同时构建了关学体系,但作为宋明理学真正奠基人的程颢和程颐,他们的学术活动则主要是在荆公新学统治思想界的时期进行的。荆公新学这一强大的、天下“靡然而同,无有异者”的统治思想,不可能不对形成中的理学发生影响。侯外庐说,“宋明理学应该于此(笔者按:指新学)寻源”(注:《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36页。)。因为正是荆公新学所关注的道德性命问题,逐渐变成了士人普遍感兴趣的问题,变成了学者们讨论的核心问题,才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与影响了理学主流的洛学的形成。侯外庐又说:“道德性命之学,为宋道学家所侈谈者,在安石的学术思想里,开别树一帜的‘先河’,也是事实。”(注:《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23页。)事实上,王安石变法改变了理学发展方向,理学也对新学的理论和实践提出责疑。
王安石变法之前,形成中的理学和荆公新学一样,同是庆历、嘉祐时期士大夫阶层普遍要求进行改革的思潮的反映。因此,这时的理学尚不能视之为新学之对立面,更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时的理学是一股政治上保守、思想上内倾的思潮。相反,此时的理学亦主张改革,二程也是提倡政治革新的。但是,王安石变法实施之后,普遍要求改革的士大夫阶层却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产生了动摇,进而坚定地站在了反对的一面。二程,尤其是程颢即是如此。程颢是较早意识到自己的学术主张与荆公有很大差异的学者,“一日议事不合,安石曰:‘公之学如上壁。’颢曰:‘参政之学如捕风’”(注:《宋史》卷四百二十七《程颢传》。)。程颐到后来更是视荆公新学为洪水猛兽:
今异教之害,道家之学则更没可辟,惟释氏之学衍蔓迷溺至深。今日是释氏盛而道家萧索。……然在今日,释氏却未消理会,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学(注:《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二程集》第38页。)。
二程觉得新法容易对付,“只消一日除了便没事”,但是新学却使他们感到棘手,“其学化革了人心,为害最甚,其如之何?”(注:《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下,《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50页。)佛教、道教的挑战均不在话下,“如今日,却要先整顿介甫之学,坏了后生学者”(注:《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二程集》第38页。)。二程的洛学,就是为整顿介甫之学而建立的。应该指出,不仅二程指斥新学,有相同思想倾向的学者亦然,陈次升入太学,习王安石《字说》,评曰:“丞相岂秦学邪?美商鞅之能行仁政,而为李斯解事,非秦学而何?”(注:《宋史》卷三百四十六《陈次升传》。)德高望重的富弼的言辞更为激烈:
臣窃观安石平居之间,则口笔丘、旦,有为之际,则身心管、商;至乃忽故事于祖宗,肆巧讥于中外。喜怒惟我,进退其人。待圣主为可欺,视同僚为不物。台谏官以兹切齿,谓社稷付在何人?士大夫罔不动心,以朝廷安用彼相(注:《挥麈录》后录余话卷一,中华书局,1961年。)。
富弼对荆公的抨击,既没有理性地剖析新法之弊害,也没有冷静地分析新学之缺失,而是相当情绪化地指斥荆公的政风与学风,这种做法,甚为不妥。在此之后,更有直接对荆公实行人身攻击者,程颢即曾说:“介甫性狠愎,众人以为不可,则执之愈坚。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争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注:《邵氏闻见录》卷十五,卷十五,中华书局,1983年。)但如果说洛学同人仅会作如此的抨击与谩骂,则是完全看低了洛学的水平,事实上,既然新学与洛学是两种对立的思想体系,则后者必然构成对前者有系统的非难。综而言之,新学与洛学之歧义,即在于本体与工夫之上。
洛学与新学的本质差异正落在本体论之上,换言之,洛学之“道”与新学之“道”存在着深刻的差异。二程认道为理,天理与道是同一的,道作为观念性的无形无声无嗅的宇宙本体,其内涵便是儒家宣扬之伦理规范。程颐曾言:“道之大本如何求?某告之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于此五者上行乐处便是”(注:《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187页。)。显然,道就是一种纲常彝伦性的精神本体。而新学之“道”则吸取了老子、王弼及元气论的思想,以本末论道,认为道是无与有、元气与冲气、自然与形器的统一。前者是道之本质,后者是道之作用。明显带有道家与玄学的痕迹,而没有以儒家之纲常伦理为道的主要内涵。正由于此,新学之道论就遭到二程的严厉批判:“介甫只是说道,云我知有个道,如此如此。只他说道时,已与道离,他不知道,只说道时,便不道也。”(注:《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二程集》第6页。)双方论“道”的不同就在于二程以儒家伦理作为道的内涵,道是天理的代名词;而王安石的“道”在本体上吸纳了道家、玄学的思想因子,道是元气,是无,是自然。双方思想的基本分歧都是从本体论上的歧异而发散开去的。有意思的是,在当时与后来,认为荆公不识“道”与“理”几乎成为守旧学者与官僚的共识。朱弁曾述熙丰变法时的一则小事:
介甫对裕陵(即神宗)论欧公文章,晚年殊不如少壮时。且曰:“惟识道理乃能老而不衰。”人多骇此语,予与韩秉则正言论此,秉则曰:“道理之妙当求于圣人之言,圣人之言具在六经,不可掩也。欧公识与不识,姑置不勿问,不知介甫所谓道理果安在?抑六经之外,别有道理乎?”……时坐客颇众,莫不以秉则之言为然(注:《曲洧旧闻》卷四,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
正因为二程及其同人认为荆公不识“道”“理”,所以,二程虽然从注重阐发经典之义理的角度肯定过王安石治《易》的方法,认为王安石同王弼、胡瑗一样,其易论有可取之处,但一旦涉及到纲常彝伦之理,则严厉批评,毫不宽贷:
王荆公云:“九三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大煞害事。使人臣常怀此心,大乱之道,亦自不识汤、武。“知至至之”,只是至其道也。(注:《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九,《二程集》第248页。)
或问:“王介甫有言,‘《乾》之九三,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如何?”子曰:“使人臣每怀此心,大乱之道也。且不识汤、武之事矣。”“然则谓何?”子曰:“知大人之道为可至,则学则至之。所谓‘始条理者智之事’也。”(注:《河南程氏粹言》卷一,《二程集》第1203-1204页。)
所谓“知至”就是体认“道”,“大人之道”,可“可学而至之”,这不过是“学以至圣人之道”诉求的翻版。两者的思路甚为不同,荆公“《乾》之九三,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强调的是《易》之变革精神,而程颐则株守彝伦之道,圣人之道可学而至,圣人之位则不可觊觎,在他看来,荆公之论道,“大煞害事”。
对于终极性本体“道”与“理”的理解既有不同,对于如何认识此一终极性的宇宙本体之方法亦归于歧异。工夫论上,二程与荆公也是对立的。
程颐与门人一段对话可充分说明这一点:
问:“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无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间,皆是理。”又问:“只穷一物,见此一物,还便见得诸理否?”曰:“须是遍求。虽颜子亦只能闻一知十,若到后来达理了,是亿万亦可通”。又问:“如荆公穷物,一部《字解》,多是推五行生成。如今穷理,亦只如此著工夫,如何?”曰:“荆公年平说话煞得,后来却自以为不是,晚年尽支离了。”(注:《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九,《二程集》第247页。)
这段对话,有三点值得研究,其一,就“格物”的内涵来说,程颐认为既有“外物”,又有“性分”中物。前者指主观之于客观自身固有之理的认识,后者则直指主体之所蕴藉而未被自身意识到的东西,问题是程颐实际上认为“格物”“穷理”之对象应以后者为主。其二,程颐认为“见得诸理”,“须是遍求”,这个方法是可以肯定的,问题是一旦“达理”是否就不需再“遍求”了,若作肯定的回答,则程颐对此问题的理解亦未出先验主义之局囿。其三,程颐对荆公“穷物”“穷理”的批判是着重指出其说到晚年归于支离。程门弟子吕大临称:“介甫之学,大抵支离。伯淳尝与杨时读了数篇,其后尽能推类以通之。”(注:《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二程集》第28页。)意思是说荆公之学“支离”而不“达理”,不能臻于“亿万亦可通”之境界,这实际从反面证明了荆公之学,理通义明,很少形上学之意味。二程之所谓“格物”“穷理”,是要通过对眼前事物的了解,以达到把握客体精神“理”的目的;他们的“理”,则是由法则而伦常而本体,是派生世界的根源。荆公则不然,其之“格物”“穷理”乃是通过对眼前事物的了解,以达到把握事物之发展法则的目的,以用于变法的实践。因此他不能强调“理”之纲常伦理内涵,不能像二程那样把现实的一切看成合理的存在。二程重义轻利的理学价值观与荆公重视事功的新学思想形成对照,而这种价值取向上的不同,是其深刻的认识论上的歧异决定了的。
综上所述,思想史的事实表明,思想是在相互对立中形成的。一种思想的形成,不但受思想倾向相同的前人思想的影响,而且还要受到思想倾向不同的对立面思想的影响与制约,使其采取与论敌相反的理论路径。这后一种情形实际上也是思想的影响与渗透,而且是比前一种更深刻的思想影响,证之于北宋中后期新学与理学之相互关系,可谓如影之随形。
[收稿日期]2002-10-20
标签:宋朝论文; 历史地位论文; 理学论文; 王安石传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二程集论文; 洪范传论文; 国学论文; 儒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