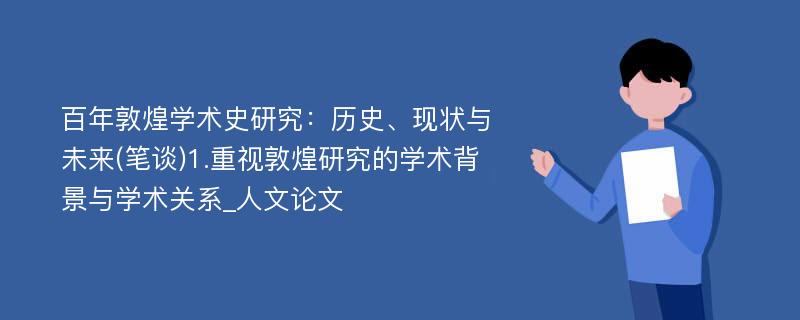
百年敦煌学学术史研究:历史、现状与未来(笔谈)——1.注重敦煌学的学术背景与学术关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论文,笔谈论文,敦煌学论文,史研究论文,注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G25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8)03-0201-15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重新面世已经108年。近百年来,随着藏经洞古代文献、文物的流散而兴起的“世界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已成为得到国际学术界普遍承认的“显学”。但是,敦煌学是否是一门真正经得起严格科学界定的独立学科,国内学界一直有不同的认识。对此,我曾经在《对敦煌学百年回顾中若干问题的认识》一文中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弄清该学科的构建与其学术背景、学术渊源的关系。敦煌学之所以能成为一门新学问,其学术渊源并不是单一的,它是在东西方学术文化的交汇之中逐渐形成的。对于外国学者来说,它应归属于“汉学”或“东方学”的范畴;而对于中国学者来讲,它又是西渐之新国学[1]。今天看来,这个认识并无不妥之处,但是尚缺乏对敦煌学的学术背景与学术关联的充分说明,有必要做进一步的阐述。
关于敦煌学的学术背景,过去讲得比较多的是20世纪初藏经洞文献被发现与流散的时代背景(或可称之为“近景”),而对于这些4-11世纪古代文献及石窟艺术品形成与保存的历史文化背景(或可称之为“远景”),则分析得较少。地处西北,原本水草丰茂、地广民稀的敦煌地区,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前后,屯垦筑城,列郡设关,经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及江汉地区大量移民迁徙至此,并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保护商旅、鼓励民族交融,到隋唐之际,已成为丝绸之路南、北、中三道必经的“咽喉”之地。据史籍和藏经洞所出文献记载,唐、五代、宋初的敦煌地区,尽管也有过短暂的战乱灾祸,而和平安定仍然一直是当地社会生活的主旋律,不仅保持了较长时期农、牧、商和寺院经济繁荣稳定,城有积贮,民有余粮,各民族居民和睦相处,而且儒家主流文化与各种外来文明融汇交流,佛、道、祆、摩尼等宗教兼容并蓄,各族人民信仰自由,郡县官学、私学及寺院学校共同构建了开放民主、不拘一格的教育体制,官府支持的民间岁时节日的文化、体育、宗教活动及艺术创作丰富多彩。这些,既是促进敦煌文化艺术发展繁荣的经济基础,也是形成以莫高窟彩塑与壁画及藏经洞文物为标志的灿烂辉煌的敦煌历史文化遗产的人文背景。
中国古代社会的“人文”观念,与欧洲不同,有自己的内涵和诠释。被后世尊为“十三经”的古代典籍中,只有《易经》(《周易》)明确地提及“人文”一词,其《上经·贲卦》说:“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古文字里的“止”,是一个形似足迹的象形字。因此,古人认为“人文”是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脚印,是可以教化天下、促进社会进步的东西,是包括礼仪、法律、道德、修养、教育等文化层面的“上层建筑”,属于“礼”的范畴。所以《晋书·礼志》曰:“经纬人文,化成天下。”《旧唐书·杨绾传》云:“人文兴则忠教有焉。”这与西方强调以人的自身权利为核心的“人文主义”是有区别的。但是,从另一角度看,参与文化艺术和体育活动,受教育、学礼法,也是人的基本权利,是“民本”思想的拓展,因此中西方之间也有可沟通之处。古代的敦煌,既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又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累代移居河西的世家著姓担负起传承儒家文化的主要任务,而往来不绝的各民族商旅、取经求法僧人,以及已经定居在此地的昭武九姓、吐蕃、回鹘、粟特人则起着传播、吸收与融合外来文明的关键作用。二者兼容相辅,并行不悖。熠熠生辉的石窟建筑、彩塑、壁画和包罗万象的藏经洞文献,正是长达千年的文明交汇、人文荟萃的硕果遗存。
我们今天探究敦煌学的学术背景,不能离开对古代敦煌地区独特的人文环境的认识。这样,我们才可以解释诸多大家饶有兴趣而又常常心生疑惑的问题。例如,为什么莫高窟同时并存了源自印度的毗诃罗式禅窟、支提式(中心塔柱)礼拜窟和中国特有的覆斗顶式庙堂?为什么在敦煌两千多身彩塑中既有清晰可辨的犍陀罗、马土拉风格,又有在魏晋时代风行一时的秀骨清像和在盛唐时期美似宫娃的丰腴菩萨?又为什么在四万五千平方米的绚丽夺目的壁画上,人们仿佛看到了张僧繇、曹仲达、展子虔、尉迟乙僧、阎立本、吴道子等高手的神来之笔?为什么在佛教寺院的洞窟里,除佛经之外还收藏着如此丰富的儒家典籍、道经写本、社会文书、文学作品、多民族文字抄卷等?又为什么这些珍贵宝藏能历经千年沧桑而保存至今?史籍上称敦煌是“华戎所交,一都会也”,我的理解是除了称颂其经济发达、商贸活跃、文化繁荣之外,更是强调了它因多种文明交汇而持续、稳定发展的特性。在“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的当今世界,有些国家的政治家、理论家鼓吹“文化一元化”,强调“文明的冲突”,其实都是不符合古往今来的历史事实与发展规律的。虽然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各种不同文明的碰撞不可避免,但其结果应该是文明的融汇与包容,在相互吸收中孕育出创新与发展的因素,共同前进。有些反映古代敦煌历史的文学、影视作品,过度渲染血与火的“外族入侵”、“宗教纷争”和“文明毁灭”,也是不符合敦煌地区的历史事实的。否则,将很难理解大量文化艺术珍品能在敦煌延续保存下来的事实。敦煌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文化艺术宝库,同时又是凝聚着国际文化交流心血智慧的结晶,属于全世界。20世纪初敦煌宝藏遭劫掠而毁损、流散的行为,理所当然地应该遭到国际舆论一致的谴责,但那只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必然会发生的短暂事件。近半个世纪来敦煌学的发展,证明了国际真诚的合作交流是推进学术发展的强大动力,而提高民众的人文素养才是保护研究、发扬光大文化遗产最有效的手段。
要使敦煌学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除了加强学科理论建设、注重本身的学术史研究外,还必须努力梳理厘清它和相关学科的内在关联,而不能只停留在“敦煌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或曰“交叉学科”)的笼统表述上。中国早期的一些著名学者在整理和研究藏经洞所出古AI写作本时,其实基本上都是在自己熟悉的学科范围内展开论述的,并没有将它们从文学、语言学、历史学、宗教学等等的学术领地里脱离出来另列门类,但后来可能便因材料的珍贵稀见与特别而冠之以“敦煌”名下,强调其为“学术新潮流”、“显学”而自立门户。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对“变文”写本的整理与研究。研究者先是为发现了中国文学史上“脱失”的环节而兴奋不已,随即便推及通俗诗、曲子词、歌辞、灵验记等,开始了相对独立集中的“敦煌俗文学”的研究,而后又逐渐形成了“敦煌文学”这个模糊概念。今天,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敦煌文学”研究者深感全面把握藏经洞所出文学材料,将其回归文学意义上的诗、词、赋、文、小说等,置于中国文学史的长河中做整体研究的必要性。其他门类亦是如此,均应在深入把握相应学科关联的基础上开展研究。
谈到学科关联,我们还应当特别关注与西域、中亚、印度密切相关的一些学问,如藏学、吐鲁番学、西夏学、于阗学、丝路学等。今天,已经有许多从事这些学问研究的学者,或投身到敦煌学的研究队伍中来,或注意加强与敦煌学界的联系,这也为我们探寻敦煌学和这些学科的内在关联创造了条件。真正的“综合性学问”或“交叉学科”,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区别于单科学问的学术体系、理论与方法。又如,目前我们国家正在兴起新一轮的“国学热”,而敦煌学与“传统国学”或“新国学”究竟有何关联?是否能占有“一席之地”?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思索的。我们认为,只有把握了学科间的内在关联,才能在分辨异同的基础上脱颖而出,真正达到“和而不同”的境界。因此,这样做的结果,非但不会“消灭”敦煌学,而且能为其先天不足的躯体补充丰富的营养,促进敦煌学学科自身的发展壮大,使其真正巍然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注释:
①本组百年敦煌学学术史笔谈的组稿、审稿,得到了南京师范大学刘进宝教授的大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