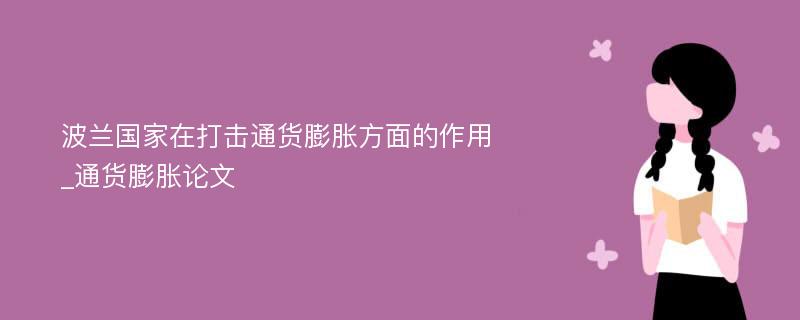
波兰国家在反通货膨胀中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波兰论文,通货膨胀论文,作用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始于九十年代初的波兰经济体制改革成就显著。但目前的经济增长尚不稳定,原因是深层的危机根源未被彻底根除:国民经济结构不合理、工农业生产低效率、保留甚至加大与西方在技术上的差距等等。而其中波兰的通货膨胀问题尤其令人瞩目。
造成通胀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预算短缺。94年国家预算缺口约29%,同时国家的内外债务上升近9%。95年负债总额占预算开支的17%以上。
91-94年贷款和金融政策的变动具有通胀性质,为的是扩大总需求。当时成功地控制了价格制定领域。不论从消费价格普遍放开的社会效果看,还是对供给生产的物质技术商品价格调整,成效显著。于是,国家依旧保留对国内价格体系的影响和作用力。保留此功能利弊兼得。在波兰这些措施虽然减缓了市场改革的速度,但却是制约通胀的因素。
应该说,新一轮超级通胀的可能依然存在。这使得通胀变成今后波兰经济发展的主要威胁和障碍。通胀的长期因素继续在活动,这和启用手段和货币金融政策无直接关系。克服通胀过程需要逐渐地和连贯地完善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和进一步改革整个经济体系。
众所周知,波兰成功地克服过短期因素引起的通货膨胀,当时采用的是从紧的货币信贷政策,最初是“休克疗法”。目前主要生产经济指数与通胀水平的明显不符,专家认为,与其说是不可能经受住94年和95年国家预算结定的通胀水平(94年的通胀率高出结定9%),不如说是当今经济政策的要求。该政策的宗旨是活跃生产和投资,刺激出口。作为手段政府选择了较为宽松的贷款政策,计划借此扩大内部的国民经济需求,促进始于94年的国外对波兰产品的需求。目标基本实现,但是以提高通胀水平作为代价。
近年波兰降低通胀进展甚微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预算缺口居高不下,波兰国家银行在资金供给中比重占优;另一方面国营企业对工资监管薄弱,由94年年中取消工资增长超标税引发的提高票面工资,加速了通货膨胀,首先是食品价格的上涨。正如保守派领袖维兹多夫斯基所说的“超计划的通胀是帕夫拉克内阁关税保护政策的结果。我们面临很危险的现象。政府把一小批生产者或外国康采恩的利益置于不得不购买更贵、质量更差或简直是在救济企业的波兰消费者利益之上”。
波兰通胀发展机制具有很强的惯性和自我再生特点。该机制的基础是价格对国营企业工资上涨的影响、兹罗提贬值速度和银行贷款的票面利率。这些变量对价格上涨的反应取决于对通胀的期望。减小通胀的措施之一是降低兹罗提贬值速度。
波兰的克服通胀纲要着重谈了货币行情和兹罗提内部兑换问题。曾经使用过固定货币行情模式,虽然固定机制在整个时期发生过变化。固定货币行情与从紧的反通胀措施一同实行(有时几乎与克服超级通胀和月均价格上涨指数单一的措施重合),同时实行的还有固定居民本国货币储蓄的高额正利率。结果出现了下列情况:在实行固定货币行情的1990年,国内价格上涨617.8,在降低兹罗提市价15%的1991年,价格上涨71.1%,1992年相应的指数变化是44%和42.2%,1993年为35.4%和35.3%,94年为12%和32.2%。这些措施促使人们脱手美元并提高了本国货币的吸引力。
从91年5月起波兰国家银行转而实行浮动货币行情,此行情由每月世界主要货币花盘所确定。随着国家银行经济状况的好转,出于经济政策的需要,如必须扩大或缩小货币储备,对贬值系数及其运作同期作了确定。有意思的是,兹罗提的贬值系数是相当有效的经济手段。其任何变化和预测都会引起传媒的激烈争论和财政部及国家银行的重大分歧。譬如,当决定把94年底1.4%的贬值系数降低到95年的1.2%时,对外经贸部作出强烈反应,公布波兰出口下降将导致波兰商品和劳务在外国市场比重下降的威胁通告。
推迟降低贬值系数是波兰国家银行的严重失算,为94年货币净储备的迅速增长创造了条件:增至113亿美元,93年为88亿美元。同时94年的国家预算结规定降低货币储备2500亿美元。波兰经济学家认为,货币储备超标准增长合加速通胀。波兰财政部认为,94年通胀的6至7个百分点是货币储备过于增长的结果。此外,国内货币贬值系数这一纯经济手段,在大选前的激烈斗争中具有政治色彩,是与反对派辩论的依据。
由此可见,波兰制止通胀的主要手段还是货币政策。其主要目的一开始不是短期刺激货币的需求,而是通过减缓通胀过程建立长期增长的健康基础。同时可以肯定,波兰国家银行手中控制着调整国内货币的主要杠杆,包括重新货款率水平、必须储备水平、货币行情政策和对证券市场炒作的起码监控。
“休克疗法”和整个货币金融政策的返通胀目的表明,无论在与通胀斗争领域,还是在其它改革领域,在波兰国家的作用日益增强。这是反分裂斗争的需要,是外部环境压力所致。
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波兰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改革伊始曾主张把国家逐出经济领域,希望市场自我调节,而实际部与想象相背离,主要的经济杠杆始终留在国家手中:货币、贷款和利率等等。正是国家在缺乏自我调节市场的情况下,挑起了拯救经济的担子,灵活地运用了手中现有的杠杆。
这个道理普遍存在于一切搞体制改革的国家。国家起主要作用的条件一是国营成分在经济中长期保持统治地位;二是,如果我们要较快地文明地走完资本积累过程并建成有效的市场关系体制,那么国家强大的调节作用必不可少。也就是说,要自觉地目标明确地建立新社会,建设主体只能是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改革的不仅是国家的功能,还有其组织制度形式。
但波兰独立经济学家指出,波兰改革过程中会出现94年那样的倒退。人们,包括国际金融组织在内,所担心的理由是国家预算再分配作用的增强。其作用的加大萌生了国内生产者和外国投资者的不信托,同时促使他们从事不符合财经纪律的活动。与此有关的还有无意义地推迟养老金和医疗保健制度的改革。左右议会的生产商强迫扩大保护国内市场的规模,这也是促使新一轮通货膨胀爆发的因素。
容忍国家分权的主要责任在统治集团身上。其中原因有得深入探究。类似情况,有的甚至以更尖锐形式出现在所有搞改革的后社会主义国家里,理应对所发生过程实质的产生条件作一番研究。解决这些问题与其说是靠政治经济决议,不如说是取决于经济改革彻底的程度。
据俄《社会科学和当代》96.2
房筱琴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