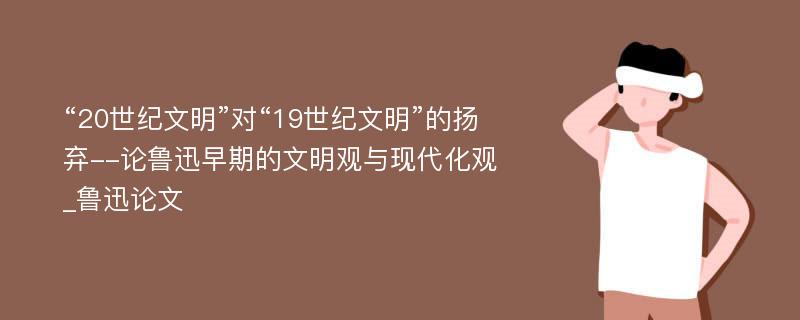
“二十世纪文明”对“十九世纪文明”的扬弃——论早期鲁迅的文明观与现代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1)05-0047-08
一 反对“十九世纪”:鲁迅世界观的完整画面
“鲁迅是谁?”这个后来的人们频频以概念的方式来进行判断的问题,对于1933年的瞿秋白却是一个难题,作为鲁迅的“知己”,他在《〈鲁迅杂感集〉序言》中的回答,仍需要借助一个神话的形象:“鲁迅是莱谟斯,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瞿秋白不仅在莱谟斯与鲁迅的身上看到了形象的类似,更重要的是,他发现了整个莱谟斯神话与鲁迅所生活的中国之间存在着一种隐喻的关系。因而这个神话有了一种新的讲述方式,东方文明的公主被帝国主义的战神强奸,产下了莱谟斯——鲁迅——及其孪生的兄长罗谟鲁斯——维新派、革命党与富国强兵的幻想家。这对孪生子在出生后就被抛弃,是一只母狼——人民群众——用奶汁哺育了他们。后来罗谟鲁斯创建了罗马城,并升上天做了和战神一样的军神,而莱谟斯则从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怀抱——
莱谟斯是永久没有忘记自己的乳母的,虽然他也很久的在“孤独的战斗”之中找寻着那回到“故乡”的道路。他憎恶着天神和公主的黑暗世界,他也不能够不轻蔑那虚伪的自欺的纸糊的罗马城,这样他一直到他回到“故乡”的荒野,在这里找着了群众的野兽性,找着了扫除奴才式的家畜性的铁扫帚,找着了真实的光明的建筑,——这不是什么可笑的猥琐的城墙,而是伟大的簇新的星球。[1](P.8-9)
这是一个伟大的隐喻。因为这个神话不仅描绘了鲁迅从“孤独的战斗”到“找着了群众”的历程,而且容纳了鲁迅时代中国思想斗争的场域与社会关系的总体。这个莱谟斯的形象,不仅是瞿秋白对于鲁迅的天才观察,而且根据冯雪峰的回忆,鲁迅对于《〈鲁迅杂感集〉序言》发生了非常深刻的感激情绪,尤其是关于自己早期思想上的缺点,他说瞿秋白的“分析是对的。以前就没有人这样的批评过”。[2](P.75)鲁迅对于莱谟斯形象的认同意味着他肯定了瞿秋白对于鲁迅“转变”的描述:他“从进化论最终的走到了阶级论,从进取的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1](P.18)
在瞿秋白的描述里,莱谟斯在“‘孤独的战斗’之中找寻着那回到‘故乡’的道路”。将这个隐喻还原为描述:当鲁迅“孤独的战斗”,他是一个尼采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者;而当他“回到‘故乡’的荒野”,这意味着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而进入了“伟大的斗争集体”。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这就是那条“回到‘故乡’的道路”,而在这条道路之上,所谓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的“转变”,并不是思想的断裂,而只是从一个环节到另一个环节的过渡。在瞿秋白看来,在鲁迅的个人主义之中,已经隐藏着对集体主义的寻求,而在集体主义之中,又包含着个人主义的真正实现。因此,在鲁迅的早期论文中,瞿秋白看到了尼采的“超人”所投下的厚重的影子——“鲁迅当时的思想基础,是尼采的‘重个人非物质’的学说”,但他认为“鲁迅在当时的倾向尼采主义,却反映着别一种社会关系”。尼采的学说是以“超人”的名义对集体和一切群众的拒绝,而鲁迅却要通过这个“超人”完成对群众的呼唤:“因为民众落后,所以更要解放个性,更要思想的自由,要有‘自觉的声音’,使它们‘每响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响’。”[1](PP.11-12)鲁迅的个人主义预设了“个人”对于“群众”的辩证克服,但这一克服的努力遭遇了失败,因此他颠倒了这一辩证关系的指向,转而用“群众”来克服“个人”,用他在《二心集·序言》中的说法即:“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3](P.195)鲁迅转向了集体主义,如同瞿秋白所说,他发现“只有同着新兴的社会主义的先进阶级前进”,“才能够在伟大的斗争集体之中达到真正的‘个性解放’”。[1](P.18)作为莱谟斯的鲁迅“回到‘故乡’的道路”包含着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辩证法,包含着尼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之间的辩证法。
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从尼采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所形成的并不是鲁迅的自我对立,恰恰相反,在此过渡之中,鲁迅向我们提供了他的世界观的完整画面。事实上,虽然尼采与马克思在思想上处于正相对立的位置,正如卢卡契在《理性的毁灭》之中所揭示的,“尼采的全部著作都是继续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虽然尼采绝没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他认为在社会主义那里他可以碰到活生生的社会的、历史的和道德上的敌人”。[4](PP.185,235)但如马歇尔·伯曼所说,“马克思和尼采的声音中有一种共同的东西”[5](P.25)。他们都生活在19世纪这个资产阶级或者说市民阶级的世纪,这个世纪所产生的“颓废”现象是他们共同的敌人①,或者说,市民阶级—基督教世界的衰落是他们共同的分析主题。他们都是19世纪这个他们自己的时代的产儿,他们也都在自身里面同这个时代进行了艰难的斗争:对于19世纪,他们分别展开了文化批判和阶级批判。他们都期待这个资产阶级世纪的终结,期待一个政治有不同含义的时代:一个由“超人”统治的等级社会,或者一个由“自由人”组成的联合体。② 19世纪及其终结,构成了尼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前提,而对于任何一个从尼采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思想者来说,这构成了一个可靠的历史中介与理论中介,同时,也正是通过这一中介,他的世界观仍然是一个完整的画面,他的思想仍然能被理解为一个内在整体。当鲁迅在1907年登上思想的历史舞台,虽然19世纪在纪元意义上已经结束,但按照霍布斯鲍姆的分界,一个历史意义上的“漫长的19世纪”仍然在延续③。就此而言,20世纪初的鲁迅,仍然是19世纪之子,而无论是在思想的开端处他对尼采主义的接受,还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都包含着同19世纪的斗争,同一个资产阶级世纪的斗争。虽然中国并没有为他提供一个资产阶级世纪的生活现实,但他通过尼采等哲学家却已经对这个资产阶级世纪有了批判的理解,对他来说,中国虽然没有参与19世纪资产阶级文明的上升,但却承担了19世纪资产阶级文明的后果:在资本主义的扩张中它被置于一个从属的地位。以中国的从属地位为代价,19世纪同样是鲁迅自己的时代,而他必须在自己思想的内部打破这一时代对他的限制。对于终结19世纪,鲁迅从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意识,在《文化偏至论》中,他将“十九世纪”理解成一种文明的类型——由“物质”与“众数”两个方面所构成的文明类型,并在与“十九世纪”正相反对的意义上,为“二十世纪文明”确定了“非物质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基本原则。因此在鲁迅思想中的反对19世纪的斗争,又表现为作为文明类型的“二十世纪”与“十九世纪”之间的斗争,对于鲁迅来说,虽然在纪元意义上20世纪已经开始,但是作为文明类型的“二十世纪”,还没有成为一个现实的存在。
二 反对“现代”或“跳过‘时代的限制’”
在鲁迅的描述中,个人主义有一个漫长的谱系,而尼采是“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其“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
尼采的“天才”有一个具体的榜样,那就是他视为自己的“教育者”的叔本华。他从叔本华那里不仅看到了对“人性”的渴望,而且看到了其“天才”产生的过程:
对强有力的本性的热望、对健康的和质朴的人性的热望,在他那里就是对自己本身的热望;而一旦他在自身中战胜了时代,他就必定以惊奇的目光在自身中发现天才。[6](P.273)
“天才”意味着“对健康的和质朴的人性”的肯定,而“天才”的获得来源于同“时代”的斗争。这种和“时代”斗争的姿态,在尼采那里属于叔本华,在鲁迅看来,它当然地也属于自称叔本华的“继承者”、“后裔和学生”[6](P.258)的尼采。同样,对于向鲁迅的作品投去目光的人来说,它必然也属于作为尼采主义者的鲁迅,在《〈鲁迅杂感集〉序言》中,瞿秋白写道:
不是伟大的天才,有敏锐的感觉和真正的世界的眼光,就不能够跳过“时代的限制”,就算只是容纳和接受外国的学说,也要有些容纳和接受的能力。[1](P.10)
“跳过‘时代的限制’”——瞿秋白对于鲁迅的评价仿佛在回应尼采对于哲学家的要求,他们甚至都遵循同一种修辞的方式,在《瓦格纳事件》的《前言》中尼采说:“一个哲学家对自己最初和最终要求什么?在自己身上克服他的时代,做到‘不受时代限制’。”[7](P.13)
如果说叔本华是尼采的“教育者”,尼采就是鲁迅的“教育者”。尼采之所以将叔本华作为“教育者”,因为在他看来,我们“能够通过叔本华教育自己来反对我们的时代——因为我们拥有有利条件,通过他来现实地认识这个时代”。[6](P.274)叔本华所“战胜”的“时代”也就是尼采所“反对”的“时代”,这一“时代”是被称作“现代”的时代,尤其是指他们都生活于其中的19世纪:在《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中,尼采把“现代人”称作“过于骄傲的19世纪欧洲人”。[6](P.216)对于尼采来说,“现代人”怀有的是既无生产能力也不快乐的“现代灵魂”,而叔本华正是“自己如此坚定地和健康地立足于自身,以至于还能够扶持和牵领另一个人的现代人类的医生”。[6](PP.252-253)
按照叔本华与尼采之间的“教育”模式,鲁迅追随着作为“教育者”的尼采,应该同样保持着对于“现代”(Modernity)的批判关系,或者说通过尼采“教育自己”来反对“现代”的“时代”。但日本的鲁迅研究者伊藤虎丸却从鲁迅对于尼采的接受和理解之中,把鲁迅归入“近代”(Modernity)④ 的世界。在《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1983)一书中,伊藤虎丸写道:
尼采对19世纪文明的批判,现在虽然被称为“反近代”思想,但曾是亚洲后进国的日本,却在尼采的第一次流行当中,从尼采那里接受了并非“反近代”的“近代”思想。鲁迅从尼采那里学到的也正是欧洲近代的精神……[8](P.31)
后来在此书的结束语中,伊藤虎丸把鲁迅对马克思的接受与对尼采的接受并列在一起,但伊藤看到的仍然是鲁迅对“近代”的汲取:
鲁迅从尼采和马克思,特别是尼采那里汲取了西方近代的“神髓”。不过,尼采和马克思在欧洲当然是批判近代的思想。[8](P.172)
“批判近代的思想”经过了“理论旅行”之后,颠倒了原有的思想的性质:对“近代”的批判变成了对“近代”的肯定。伊藤虎丸作出这一判断的根据在于:
鲁迅从尼采的个人主义那里所汲取的,是包括国家、道德和科学在内的处在欧洲近代文明根底上的东西,是其“神髓”。所以,诸如鲁迅对科学主义者的批判……实际上却不是对科学本身的批判,而是对不懂科学者精神的科学主义者的批判;他那里的文学艺术,是“真的人”之“精神界之战士”发出的“心声”和“内曜”,它们和科学、国家不是对立的,而是探寻其“根底”之“精神”并且滋养其“精神”的东西。而从这种“真的人”的立场出发,去寻求民族灵魂根底上的全面觉醒,就是鲁迅的文明批评。[8](P.34)
鲁迅从“反近代”思想中接受了并非“反近代”的“近代”思想,这是伊藤虎丸反复强调的主题。虽然尼采在伊藤虎丸的鲁迅论中是一个不可绕过的存在,但伊藤虎丸几乎没有在尼采的思想内部讨论过问题。对于伊藤虎丸来说,其基本的出发点是鲁迅所理解的尼采式的人物形象(除了尼采,还包括叔本华、易卜生以及《摩罗诗力说》中的“恶魔派”诗人)和日本的尼采形象之间的比较:在日本,尼采的形象经历了从“积极奋斗的人”到“本能主义者”的演变,鲁迅的尼采式人物和前者存在着相当的共性,而和后者有着决定性的区别。[8](P.33)由此,在跨越了东西方之间的界限之后,在尼采本人那里已失去合法性的“近代”,却通过尼采的形象,在亚洲获得了重建的先验基础;在西方通过尼采的批判而呈现出的“近代”之存在的危机,却通过尼采形象的差异,变成了亚洲内部关于“近代”之理解的危机:日本与鲁迅的中国,建构的是两种“近代”的类型。在《鲁迅与日本人》的序言里,伊藤虎丸描述二战之后日本的中国形象:“人们在中国近代当中找到了和日本不同的另一种近代,一种‘真正的近代’”。这个“真正的近代”也是伊藤虎丸本人的认识,在《鲁迅与终末论》的《解说·译后记》的最后,译者李冬木总结说,伊藤虎丸的真正用意在“个的自觉”(《鲁迅与终末论》)或者说“个的思想”(《鲁迅与日本人》),而“作者在鲁迅身上发现了这一思想,并且以这一思想为标志,鲁迅所代表的是真正的‘近代’”。[9](P.403)所谓“个的思想”,即“真正的个人主义”[10](P.31)——鲁迅在尼采那里所发现的“个人主义”,由此,在“真正的个人主义”与“真正的‘近代’”之间,形成了一种修辞上的同构关系。
“真正的个人主义”反对的是19世纪欧洲的“个人”形式,由此,它的“真正”与“真正的近代”的“真正”之间存在着一种语义的距离:与鲁迅所代表的中国之“真正的近代”相对立的是日本的“近代”——不妨称之为“虚假的近代”。所谓“真正的近代”,是指将自身作为“近代”的主体,在接受西方的“近代”的同时展开对“近代”的抵抗,或者说将“近代”作为自身内部的问题;与之相对,所谓“虚假的近代”,则是主动将自身作为“近代”的对象,无条件地承认西方“近代”的优越性和普遍性,放弃对西方的“近代”予以抵抗的契机。因此在伊藤虎丸看来,“虚假的近代”把西方的“近代”当作了惟一的普遍性,它自身是对这一普遍性的复制,而“真正的近代”,则在西方的“近代”之外,构成了一种新的普遍性,对于伊藤虎丸来说,这就是鲁迅的意义。在鲁迅的内心世界里,新与旧、东与西两种文化尖锐冲突、相互纠缠,而鲁迅“执著于民族=自己的最落后的部分”展开“抵抗”:
以这种抵抗为前提的对民族=自己最落后部分的彻底批判,和对西方近代的全面接受,其结果就是开辟了一条民族传统的全面再生之路,并且由东方产生出超越西方普遍主义的新的普遍主义。可以说,鲁迅文学的核心就在这个暗示当中。[8](P.179)
将鲁迅的文学当作一种普遍主义诉求,这充分体现了伊藤虎丸理论上的洞见和文化政治上的敏感:在“民族传统的全面再生”中同时产生出“新的普遍主义”,包含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法”。不过,他对新的普遍主义产生方式的描述却又并未摆脱暧昧的状态:“对西方近代的全面接受”能够加速“对民族=自己最落后部分的彻底批判”,但从“对西方近代的全面接受”之中如何能够直接产生出对西方普遍主义的超越?“真正的近代”不过是将“近代”从西方换到了东方的场域,又如何是一种“新的”普遍主义呢?实际上,“真正的个人主义”已然批判了“真正的近代”,它将“新的普遍主义”预约给了“二十世纪文明”。
三“二十世纪文明”:对“十九世纪文明”的扬弃
在20世纪初,作为一个中国人,鲁迅承受着一个历史的事实:欧洲的“十九世纪文明”早已经以武力的方式批判了中国的传统文明;作为一个思想者,鲁迅观察到一个思想的事实:在19世纪末叶的欧洲产生了对“十九世纪文明”的批判,而这种批判为即将到来的“二十世纪文明”提供了理论与精神的基础。因此,在鲁迅那里,传统文明、“十九世纪文明”与“二十世纪文明”分别作为“古文明”、“旧文明”与“新文明”,在不断递进的批判关系与时间关系中,构成了一个类型学序列。
在中国的传统文明与“二十世纪文明”之间,“十九世纪文明”处于一个中介的位置:相对于“二十世纪文明”,它作为“旧文明”而存在;但相对于中国的传统文明,它又获得了“新文明”的名义,而它也正作为“新文明”被接受与传播。对于鲁迅来说,这形成了一种连续的时代错乱:当欧洲凭借着“十九世纪文明”而从自己的内部描绘一个完整的世界图像时,中国却正在经历传统文明的最后衰落;当以尼采为至高代表的个人主义哲学在19世纪末叶推动了一个思潮的转变,欧洲由此来寻找向“二十世纪文明”转换的契机,中国的寻求变革的人们却正将欧洲的“十九世纪文明”当作自己的方案。如果说在前一个过程中,中国是在一种不自觉的状态里被欧洲视作一个落后的他者;那么在后一个过程中,中国则是主动地将自己转化为欧洲的过去。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关于德国的论断,只需要将国家的名称换作中国,呈现的就是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与《破恶声论》中所描述的中国的历史境遇与思想境遇:
它分担了这一发展的痛苦,而没有分享这一发展的快乐和局部的满足。……有朝一日,德国会在还没有处于欧洲解放的水平以前就处于欧洲瓦解的水平。[11](P.11)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从“传统文明”走向欧洲的“十九世纪文明”丝毫不意味着自我的更新,而只是一次对新文明的误认,是对于“已陈旧于殊方者,馨香顶礼”,或者站在欧洲的角度,这不过是欧洲已显现出危机的“十九世纪文明”通过在一个世界空间里的转移来延缓自己衰落的命运:
顾新者虽作,旧亦未僵,方遍满欧洲,冥通其地人民之呼吸,余力流衍,乃扰远东,使中国之人,由旧梦而入于新梦,冲决嚣叫,状犹狂酲。夫方贱古尊新,而所得既非新,又至偏而至伪,且复横决,浩乎难收,则一国之悲哀亦大矣。[12](P.51)
19世纪末叶从“十九世纪文明”批判中所产生的思想,还没有通过与人民的结合,转化成为欧洲的现实;而“十九世纪文明”作为一个掌握了欧洲与欧洲人民的社会实体,不仅在欧洲与“远东”之间形成了一种侵略的关系,而且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为自己确定了一种衍生的形式。正如竹内好在《何谓近代》中以鲁迅为线索所作的考察,“东洋的近代是欧洲强制的结果”,从而欧洲与东洋(“远东”)作为一组对立的概念,或者说作为一组差异性的时间与空间的范畴,形成了一个“前进—后退”的运动图式。但必须认识到,这个图式是在“十九世纪文明”的框架里形成的,在欧洲作为“十九世纪文明”向着“远东”“前进”的同时,“十九世纪文明”正在尼采等人批判思想的“前进”里一步一步地“后退”。因此,这是一个双重的“前进—后退”的图式,而鲁迅通过“古”、“旧”、“新”的时间关系指明,只有将这个双重的“前进—后退”的图式作为中国的认识框架,才能把握到一个真实的世界史,并在这个世界史的进程里为中国赢得一个真实的位置。
在鲁迅看来,欧洲与中国之间空间上的对立与时间上的差异必须消除,而消除的办法在于预先占有未来,即预先建构作为“新文明”的“二十世纪文明”。在“十九世纪文明”的框架中,中国作为征服的对象,只能被动地接受来自欧洲的历史指令。但在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转折时刻,“十九世纪文明”自身的危机,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改变被支配地位的可能,因为19世纪末思想的转变,或者说个人主义哲学的兴起,所提出的诉求是“十九世纪文明”的彻底瓦解:
十九世纪末思想之为变也……即以矫十九世纪文明而起者耳。盖五十年来,人智弥进,渐乃返观前此,得其通弊,察其黮暗,于是浡焉兴作,会为大潮,以反动破坏充其精神,以获新生为其希望,专向旧有之文明,而加之掊击扫荡焉。[12](P.50)
通过对“十九世纪文明”的批判,19世纪末叶的思想成为对一切“旧有之文明”的批判。由此,“传统文明”与“十九世纪文明”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一种质的分别,而只是量的或者说程度的差异:它们最终都将消失在个人主义“破坏”的“大潮”里。如同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重新忆及个人主义哲学家时所说,这是一种“轨道破坏”,也是一种“革新的破坏”,[12](P.204)因而在他们的否定之中包含着肯定,在他们的“掊击扫荡”之中孕育着“新生”:“以是为二十世纪文化始基,虽云早计,然其为将来新思想之朕兆,亦新生活之先驱,则按诸史实所昭垂,可不俟繁言而解者已。”[12](P.51)
“二十世纪文明”将是由“新思想”与“新生活”结合而成的一个实体,个人主义哲学是为这一文明所作的准备。但需要注意的是,它也仅仅是一个准备,并不能直接现实化为“二十世纪文明”,而只能作为“朕兆”与“先驱”,保持着一个等待的姿势。重新回到关于尼采的引文,在那里,尼采通过查拉图斯特拉等待未来的“苗裔”(孩子):
德人尼佉(Fr.Nietzsche)氏,则假察罗图斯德罗(Zarathustra)之言曰,吾行太远,孑然失其侣,返而观夫今之世,文明之邦国矣,斑斓之社会矣。特其为社会也,无确固之崇信;众庶之于知识也,无作始之性质。邦国如是,奚能淹留?吾见放于父母之邦矣!聊可望者,独苗裔耳。[12](P.50)
在这里,鲁迅以极为精简的方式,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二部中以“文化之国”为题的一整节内容[13](PP.134-137)改写成这样一小段文字。对于鲁迅来说,查拉图斯特拉就是尼采,这里所说的“文明之邦国”、“斑斓之社会”就是尼采对于“十九世纪文明”的描绘。社会所以呈现为“斑斓”的面貌,是因为累积了过去的色彩,而历史知识的重压,使人们失去了创造(“作始”)的能力。按照罗森在《启蒙的面具》一书中的说法,查拉图斯特拉将希望寄托于“苗裔”,也就是他的孩子们,就此而言他是一个预言者,而预言者同样“无法进入那将给人带来幸福欢乐的希望之乡”,因为他同样“知道得太多了而无法创造”,因而“他惟一能做的是代表着未来创造的承诺或梦想去摧毁”。[14](P.185)这也正是鲁迅的理解,紧接着上面这段引文,鲁迅评论道:“此其深思遐瞩,见近世文明之伪与偏,又无望于今之人,不得已而念来叶者也。”[12](P.50)
尼采在象征意义上所谈论的“苗裔”(孩子),被鲁迅在历史意义上转化成了“来叶”。在尼采的原文中,查拉图斯特拉声称“我要借助我的孩子们进行补救”,实际上的意思是“借助一切未来挽回——这个现在”[13](P.137),而鲁迅则通过“近世文明”——“十九世纪文明”与“来叶”的对比,将尼采的普遍的“一切未来”确定在具体的“二十世纪”。
对于鲁迅来说,“二十世纪”是一个能够属于中国的世纪,因为:(一)“二十世纪”虽然在公元纪年意义上已经开始,但在文明类型意义上却尚未确立,因而中国能够加入对“二十世纪文明”的定义与形式的争夺;(二)中国的传统文明在“十九世纪文明”的侵扰中已经彻底松动,在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瓦解的时刻,中国自身产生了迫切变革的要求;(三)“顾瞻百昌,审谛万物,若无不有灵觉妙义焉,此即诗歌也,即美妙也,今世冥通神閟之士之所归也,而中国已于四千载前有之矣”[15](P.30),鲁迅在《破恶声论》中的这一观察表明,中国的源始文明(传统文明的源头)与“新神思宗”哲学有着内在的通约关系,故而实践以“新神思宗”哲学为始基的“二十世纪文明”,既是一场自我的变革,同时也是一场朝向自身的回归。因此,鲁迅将尼采视为自己的“教育者”,将中国的“明哲之士”当作查拉图斯特拉的“苗裔”,一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将成为尼采所期待的“孩子们的国土”,亦即罗森所说的“幸福欢乐的希望之乡”:
中国在今,内密既发,四邻竞集而迫拶,情状自不能无所变迁。……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12](P.57)
这是鲁迅前期思想的一个核心表述,是鲁迅对中国“二十世纪文明”的设计。在这里,鲁迅一方面通过比较(“权衡校量”)的途径,将“二十世纪文明”放在“世界之大势”之中,从而确定“二十世纪文明”是一个历史的总体;另一方面通过“自觉至,个性张……转为人国”的表述,将“二十世纪文明”描述为由各个环节构成的一种精神运动,从而确定“二十世纪文明”是一个伦理的实体,因为所谓伦理,如黑格尔所说,就是“成为现存世界和自我意识本性的那种自由的概念”[16](P.164)。
“二十世纪文明”是批判“十九世纪文明”的产物,因而在鲁迅的描述之中,“二十世纪文明”与“十九世纪文明”之间形成了一种严格的对立关系。这种对立,是“客观”与“主观”的对立,而鲁迅同时又把它表述为“梦幻”与“觉醒”的对立。从“十九世纪文明”到“二十世纪文明”的发展,变成了这样的一个过程:“成然以觉,出客观梦幻之世界,而主观与自觉之生活,将由是而益张。”[12](P.57)“梦幻”与“觉醒”的隐喻是鲁迅经常使用的隐喻,但又总是和文明类型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前面的引文中,我们已经看到,从传统文明到“十九世纪文明”,鲁迅称之为“由旧梦而入于新梦”,而在这里,鲁迅把这个“新梦”之“新”落实到一个“客观”的层面。“客观”被看作“梦幻”,这意味着,在鲁迅看来,只有回到“主观与自觉”才意味着“觉醒”,才意味着真实。相对于“十九世纪”的“客观梦幻之世界”,“二十世纪文明”所组建的是一个“主观觉醒之世界”或者说“主观真实之世界”。
在鲁迅的描述中,“十九世纪文明”的构成包含着“物质”(文明)与“众数”(文明)两个方面,其客观性也正寄寓在“物质”与“众数”之中。“物质”本身已经意味着与“主观”和“精神”相对,而在“十九世纪”所出现的一个特殊情形是,由于在科学的支持下所获得的迅猛发展,“物质”被赋予了主动性的力量,它被“视若一切存在之本根,且将以之范围精神界所有事”[12](P.49)。“众数”在鲁迅那里指的是“十九世纪”所确立的民主政治制度,它把个人的意志集中为“众意”,又将“众意”表现为法律与国家,即作为公认的存在的权力,借用黑格尔的概念,在鲁迅所说的“众数”之中形成了一种“客观精神”。“客观之物质世界”斩断了“十九世纪文明”与“主观之内面精神”的关联,而“众数”作为“客观精神”在政治领域将“十九世纪文明”展现为以下的环节:人作为“国民”而成为真正的“人”,由作为“国民”的“人”组成了一个政治性的“社会”,而这个政治社会的中心则是“国家”。在“十九世纪”,“国家”居于绝对主体的地位,它将“人”指派为“国民”,并宣布“吾当与国民合其意志”,鲁迅引用施蒂纳的话批评说:此“亦一专制也”。[12](P.52)
相对于“十九世纪文明”中的“物质”与“众数”两个方面,“二十世纪文明”以“非物质主义”与“个人主义”作为构成原则。鲁迅以“非物质主义”颠倒了“十九世纪文明”中“物质”对“精神”的统治关系,他不仅确定了“主观之内面精神”相对于“客观之物质世界”的优越地位,而且“反省于内面者深”[12](PP.55-56),以“意志”(“意力”)为中心重建了“主观之内面”的形式。对于鲁迅来说,确定“意志”的地位,是树立“个人主义”的前提,而正是通过“意志”的力量,“十九世纪文明”中的“人”在“二十世纪文明”中变成了真正的“个人”。“个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作为“国民”的“人”以“国家”作为价值的标准,而“个人”将自身作为意义的源泉。“个人”的出现改变了政治领域的面貌与组织形式,“十九世纪文明”中的政治性的“社会”,在“二十世纪文明”中被改造为具有“大觉”的“群”;“十九世纪文明”中的“国家”,在“二十世纪文明”中被上升为“人国”。“国家”所确立的是“国民”对它的臣服关系,而“人国”则将自身展现为“个人”自由意志的充分表达。鲁迅认为:“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在这里,鲁迅将“自觉”作为“人国”创制的第一个前提,将“个性”作为“人国”创制的中间环节,由此,从“自觉”到“个性”再到“人国”构成了一个连续的运动过程。
“自觉”经过“个性”的中介最后汇聚入“人国”,这解释了为何鲁迅将全部的“二十世纪文明”都归结为“主观与自觉之生活”:在“二十世纪文明”这一伦理实体的内部,每一个环节都是“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恃意力以辟生路”[12](P.57)的结果。“二十世纪文明”不仅消除了“个人”与国家的界限,而且将“内面”与“外面”联合成了一个整体。在“二十世纪文明”所塑造的生活世界里,“意力”(“内面”、“精神”、“自觉”)、“个人”、“群”、“人国”内在地具有一种相互构成的关系。“二十世纪文明”废黜了“十九世纪文明”所存在的“国家”对“国民”的统治,克服了“十九世纪文明”在“物质”与“精神”之间所形成的断裂与对立,也因此颠覆了“十九世纪文明”所描绘的“客观梦幻之世界”。“二十世纪文明”驱使“客观”向“主观”臣服,将主客观的关系全部收回为“主观”内部的关系,从而将整个生活世界转化成了自我再现、自我表现与自我认识。由此可以明白,鲁迅在描述从“十九世纪文明”向“二十世纪文明”的变化时,“客观梦幻之世界”与“主观与自觉之生活”在语义上形成了完全对立的关系,但在修辞上没有采用严格对应的形式。对于前者来说,“客观”就是“梦幻”,对于后者而言,“主观”与“自觉”却不是同一的关系:“主观”界定了一个范围,“自觉”则表现为一个运动,“自觉”在“主观”的范围里不断运动。而在与“梦幻”相对的意义上说到“自觉”,这个“自觉”既指的是自我对自我的觉知——也就是认识的活动,又指的是自我所获得的觉醒的状态。从作为自我认识的“自觉”而至于“人国”,“二十世纪文明”所呈现的就是一个“主观真实之世界”;从作为自我觉醒的“自觉”而至于“人国”,“二十世纪文明”所展开的就是一个“主观觉醒之世界”。
收稿日期:2011-08-20
注释:
① 马克思与尼采不约而同地使用“颓废”(decay,decadence)一词。马克思宣布“……19世纪……显露出衰颓的征兆,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能情景”(《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774页),尼采则自承“我和瓦格纳一样,是这个时代的产儿,可说是颓废者[decadent];……一直让我伤透脑筋的,其实正是颓废[decadence]问题”(尼采《瓦格纳事件/尼采反瓦格纳》,卫茂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13页)。
② [匈]卢卡契《理性的毁灭》第三章《尼采——帝国主义时期的非理性主义的创始人》,[德]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的第四章《作为我们时代的哲学家和永恒的哲学家的尼采》,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第三讲《尼采(上):反历史主义的文化批判》虽然讨论的主角都是尼采,但都在尼采与马克思之间作了一番比较研究。
③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将1789-1914年,也就是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都划归“19世纪”,他称之为“漫长的19世纪”,并写有“漫长的19世纪”三部曲:《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和《帝国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4月)。
④ Modernity有“近代”与“现代”两个译名。这两个译名对于鲁迅 研究来说是一个直接的困扰,因为在现今的中国的语境中,Modernity一般被翻译为“现代”,而日本的鲁迅研究在被翻译为中文之后,保留了日语以“近代”翻译Modernity的方式。在《亚洲的“近代”与“现代”》一文中,伊藤虎丸描述了中文与日语之间的这种错位对应的关系:日语的“近代”对应着中文的“现代”,而日语中以“反近代”为指归的“现代”,表达的则是中文里“反现代”或“现代主义”的含义。
标签:鲁迅论文; 尼采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十九世纪论文; 新文明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现代文明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读书论文; 瞿秋白论文; 哲学家论文; 存在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