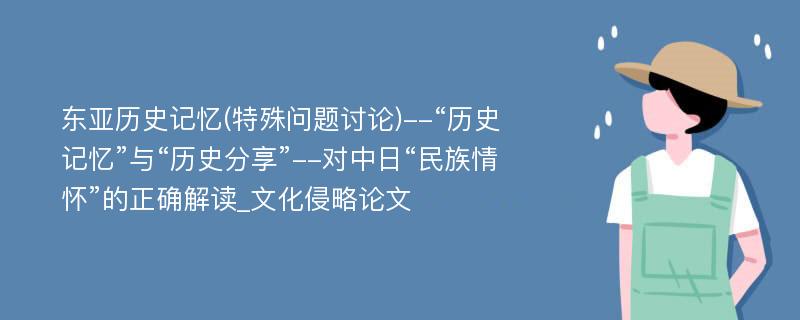
東亞歷史記憶(專題討論)——“歷史記憶”與“歷史共有”——中日“國民感情”的正確解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论文,感情论文,專題討論论文,東亞歷史記憶论文,正確解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日關係在東亞區域發展進程中佔據十分重要的地位。兩國之間的親疏既體現在政府層面的互訪,也體現在民衆之間的日常交流。如何看待近年來中日之間的“國民感情”,日本政府新近發佈了兩個數據:一是日本內閣府於2014年12月20日公佈的“外交輿論調查”,在受訪的近兩千名日本人中,對中國“無親近感”的比例達83.1%,創這項調查四十年來的新高。日本外務省表示,這一調查結果“反映了調查期間的‘國民感情’”。①二是日本文部科學省2015年2月彙總的統計資料顯示,2014年赴中國大陸留學的日本學生人數較上一年增加18%,達到2.11萬人。這是文部科學省自1983年開展調查以來,中國首次超過美國,成爲日本學生留學首選地。②另據中國國家旅遊局公佈的統計資料,2014年,中、日、韓三國旅遊交流規模從十年前的年1300萬人次躍升到2000萬人次,增長超過50%。其中,中日两國人員互訪達512萬人次,赴日中國遊客爲241萬人次,來華日本遊客爲271萬人次。③這前後兩組數據顯示的都是中日“國民感情”,但前者是極度“惡化”,後者卻是相當“熱化”;兩者都呈上升態勢,但方向卻正相反。人們不禁產生疑問:究竟是相信日本政府設計的“問卷投票”及其解讀呢?還是相信日本民衆自主自發來到中國的“行動投票”呢?顯然,後者要比前者可靠、可信,至少它可以讓人們對日本外務省的“官方結論”提出質疑。 一、“親近感”並不等同於“國民感情” 日本內閣府已延續四十年的這項“外交輿論調查”問卷設計的問題是:“對中國有無親近感?”關於“親近感”,日本《學研國語大詞典》釋義爲“親しみを持ち、近づきたぃと思ぅ気持ち”(感覺親密、想接近的心情),中國《現代漢語詞典》對“親近”一詞的釋義爲“親密而接近”。兩義基本相同。但需要注意的是,問卷題目中“有無親近感”的對象是“中國”,而非與日本“國民”對等的中國“國民”。這就意味着,受訪的每一位日本普通國民要回答的是:在中日兩個國家關係現狀下,作爲日本國民對於對方“國家”是否抱有“感覺親密而想接近的心情”。回答者的立場和標準自然明確:立場就是作爲日本國民的一員對對方國家取何種態度,標準就是本國與對方國現在關係的好壞。因爲,對於兩個國家之間的關係以及採取什麼外交政策,畢竟是由政府操作,普通國民不可能有深入、全面的瞭解,也與他們的日常生活沒有直接關係,他們衹能以所屬共同體——自己的國家爲立場。特別對於“團體性”很強的日本人來說,作爲“國民一員”,以本國政府的外交態度作爲對對象國採取“團體一致”態度的立場和標準,是理所當然的。因此,訪民回答問卷對於中國“有無親近感”,實則表達的是對當時本國與中國關係好壞的感受和心情。當然,不排除回答問卷時有人出於對兩國關係現狀的不滿與擔憂而選擇內心希望兩國“親近”的意向,作出與“團體主流”不同的表達,但多數訪民會順從“團體主流”立場及標準來作答。因此可以說,這一對中國“有無親近感”民調資料的升降變化,衹是反映了日本國民對調查時兩國關係好壞之下對中國“抽象形象(往往是由本國政府和媒體所勾畫)”的感受和心情。 回顧一下歷年來日本內閣府這項調查結果的變化,恰恰也是與兩國國家間關係的好壞直接相關。1983-1984年,因兩國領導人互訪及中國政府邀請三千名日本青年訪華,兩國關係熱絡,這一民調結果是,有親近感者分別爲72.5%和74.5%,佔絕對多數,無親近感者衹有19.8%和19.2%。此後幾年,有親近感者一直佔據多數。至1989年,中國發生“六四政治風波”、日本加入西方制裁陣營而使親近感下降,但有親近感者仍超過半數。此後,直至2003年,有無親近感者都基本持平。2004年,因中國公民登釣魚島被日方扣留及中國駐大阪總領館被日本右翼宣傳車衝撞事件等使兩國關係出現裂痕,無親近感者升至58.2%,明顯超過有親近感者的37.6%。此後,無親近感者一直佔多,且有所增加。直至2010年,日方在釣魚島海域抓扣中國漁民、漁船事件而使兩國關係裂痕加大,當年的調查結果是,無親近感者明顯上升至77.8%,有親近感者降至20%。2012年,因釣魚島爭端及歷史認識問題等使兩國關係緊張,無親近感者升至80%,有親近感者降至18%;2013年與此相近,直到2014年無親近感者升至83.1%,引起兩國媒體輿論驚呼爲“史上最惡”。④ 造成兩國關係變化的原因,既有因一時一事的摩擦帶來的短期影響,也有這一期間中日兩國經濟實力升降變化的長期效應。1980年代,日本經濟實力遠高於中國之上;進入1990年代後,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實力快速提升;至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首次超過日本而位居世界第二,日本經濟則陷入長期低迷。這對於自明治維新以來一百餘年間一直以亞洲頭號強國和先進國自居而俯視甚至蔑視中國(甚至由此發展爲發動侵華戰爭)的日本人來說,形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和實際壓力。兩國關係遂由1980年代的強弱上下縱向“攜手”關係,轉變爲兩強並立、相互競爭的橫向“對手”關係。反映到日本內閣府的這項歷年調查中,就表現爲日本國民對於中國的態度,由“攜手”關係時的“感覺親密而想接近”的“親近感”,向“對手”關係時“不感覺親密而想接近”的“不親近感”轉變。正因如此,在國際輿論熱議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而位居世界第二的2010年,日本內閣府的這項調查結果顯示,日本訪民對中國“無親近感”者由前一年的58.5%,陡然上升至77.8%,這應當是這種被超越的壓迫感和對抗感、加上兩國外交摩擦相互交織,在日本國民心理上引起的自然反應。 因此,日本內閣府的這項“外交輿論調查”,比較準確地說,反映的是作爲日本國民對於中日關係現狀下的對手國——中國,抱有怎樣的感受和態度;“不親近感”的上升,反映的是日本國民對中日競爭對手關係緊張度上升而形成“對抗感”強化的感受。也就是說,正如其名爲“外交輿論調查”那樣,這衹是一項日本國民對於兩國外交關係現狀感受如何的民意調查。 但是,對於這項調查結果,日本外務省作出的官方解讀卻是“反映了調查期間的(日本)國民感情”。這一“權威”解讀,又被日本內外媒體輿論廣爲接受並沿用,甚至又進一步地推演。於是,“國民感情”一詞成爲伴隨這項調查結果輿論議論的“熱詞”,並推演成了如下一些結論:“日本國民感情普遍厭華”,“對華厭惡感達史上最高”,“中日國民感情極度惡化”,“兩國九成國民彼此厭惡”等等,由此引發兩國輿論一片憂慮和悲歎,甚至引起兩國一些網民情緒化的隔空罵戰。 然而,與前述對日本內閣府這項輿論調查的本來意涵進行對照,就會對其結果反映日本“國民感情”的說法以及由此推演出的結論產生疑問:這種解讀是否準確?調查問卷中的問題“有無親近感”是否等同於“國民感情”?這裏所指的日本“國民感情”針對的對象爲誰?是對“中國”,還是對“中國國民”?需要加以具體分析。 “感情”一詞,中日文共用。《現代漢語詞典》解釋爲:“對人或事物關切、喜愛的心情。”《學研國語大詞典》有二義,一義爲:心中的憤怒、喜悅、悲傷、快樂、寂寞等感受;⑤另一義爲:對事物或人抱有的心情心態。⑥第二義與中國詞典釋義相近。據一般用詞規則,兩個對等相關項應彼此對應,即國家對國家、國民對國民。“國民感情”的主體是“國民”,而且具有一定的整體性,其對應的對象也應當是對等的他國“國民”,即他國的“國民感情”。因此,“國民感情”一詞似乎可以定義爲:指一個國家國民對其他國家國民所抱有的是否關切和喜愛的感情。事實上,作爲一個在談論中日關係時約定俗成的組合詞,“國民感情”的含義決非僅僅如字面上咬文嚼字的生硬解釋這樣簡單,而是具有中日兩國之間深厚而久遠的歷史文化連帶感及其積澱的內涵,並且爲雙方所共同理解。正因如此,這個詞成爲中日討論雙方關係時喜歡常用的“熱詞”,而在討論歷史文化關係不如中日深厚的中美、中歐關係時很少使用。這就提示人們,在談論中日之間的“國民感情”時,不能忽視其歷史文化內涵。 如果本着中日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澱來看待彼此的“國民感情”,對照前述日本官方對“外交輿論調查反映日本國民感情”的解讀,就會發現,日本外務省的“權威解讀”並不準確。 首先,從字面而言,調查問題是對中國“有無親近感”而非與日本“國民”主體對等的“中國人”或“中國國民”,因而日本訪民的回答衹是表達在中日國家間關係現狀下對“中國”的感受和態度,而並非對“中國國民的感情”,更不能代表中日兩國民衆之間的“國民感情”。 其次,就內涵而言,日本訪民在中日國家間關係現狀下對“中國”的感受和態度,並不能等同於日本國民基於兩國深厚歷史文化積澱而形成的對中國國民的“國民感情”。中日國家間關係一時的好壞變化,可能會引起兩國民衆對彼此國家、政府或領導人產生一時的喜厭好惡、有無親近感的變化,但作爲兩個一衣帶水、有着兩千年交往和深厚歷史積澱及文化淵源的鄰國之間的“國民感情”,決不是由一時一事、暫時國家關係的變化而完全決定的。 由此可見,日本官方對此項“外交輿論調查”反映日本“國民感情”的解讀是一種誤讀和曲解。這一誤讀通過媒體輿論形成進一步推演誇大的結論,進而對兩國民衆對於彼此“國民感情”的認知形成誤導,得出與事實不盡相符的認識,使得兩國“國民感情”受到一定損害。 日本官方的這項調查及其解讀,衹是形成這樣一種效應:將日本訪民對中日國家間關係陷入低谷現狀下對中國“無親近感”大幅上升達史上最高,解讀爲日本人對中國“國民感情”空前極度惡化,由此證明日本“國民感情”與日本政府現行對華強硬政策高度一致,進而表明日本現行對華政策代表了日本八成以上的普遍“民意”。如此一來,日本政府現在採取對華“強硬對抗”政策,就有了日本人普遍“極度厭華”的“國民感情”這一“民意”基礎和正當性。就這樣,日本民衆的“國民感情”被與日本政府的現行對華政策捆綁在一起,成爲其現行對華政策民意化、合理化的注腳。 二、“國民感情”與“歷史記憶” 中日民衆對於彼此的“國民感情”主要由兩種因素所決定:一是國家間關係的現實利害,二是兩國及國民關係的歷史積澱。前者是眼前利益,後者是深遠積累;後者是基礎,前者衹是在後者基礎之上的疊加,並將會隨着時間推移而成爲後者的一部分。由於中日兩國特殊的地緣關係及歷史文化淵源關係,特別是近代以來十分密切、恩怨交織的關係,使得“歷史積澱”在兩國“國民感情”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分量。正因如此,中日兩國的“國民感情”纔如此豐富而複雜、深厚而長久,並不是一朝一夕、一時一事所能決定和改變的。也正因如此,導致近年兩國關係摩擦而陷入低谷的兩大癥結:一是海島爭端,二是“歷史認識”問題,都與歷史有關。對於前者,兩國國民站在各自國家的立場而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這既需要兩國政府通過對話對之進行理性應對與把控,也需要兩國政治家和學者對這一爭議問題進行認真研究和真誠交流,以求趨近共識,化解爭端。對於後者,則牽涉的是“歷史認識”問題,它更深切地牽動着兩國的“國民感情”。 人們的“歷史認識”基於“歷史記憶”。作爲國民的“歷史記憶”,即民衆對以往歷史的體驗、見聞、記述、交流、傳承並通過一定載體而留存下來,被民衆廣爲接受並傳遞給後代的歷史形象及其解釋。中日兩國民衆雖然共同經歷了近代以來兩國緊密聯繫的歷史,但是由於分處兩個國家,特別是兩國還經歷了戰爭,戰後又有不同的社會環境,因而作爲兩國國民,對於以往歷史的體驗、見聞、記述、交流、傳承等內容有所不同,由一定的載體而留存下來的歷史形象及其解釋也有所不同。在一定意義上說,這也是難以避免的。但是,也正是兩國國民“歷史記憶”的差異,往往造成兩國“國民感情”的隔閡,甚至傷害。 如對於以往日本侵華戰爭的記憶與認識,作爲受害國中國民衆來說,無數的親人同胞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殺戮、殘害、欺壓、侵奪,或家破人亡,或背井離鄉,生者也長期生活在貧窮困苦、屈辱絕望、悲哀恐懼之中。這種遭受侵略的巨大傷害,不僅深深印在親身體驗這一苦難的一代人心裏,印在到處殘留着戰爭遺跡的廣闊土地上,也形成了“歷史記憶”而留存在後代人心間,令幾代人刻骨銘記。正是遭受侵略和戰爭的災難,教會了中國人要奮力自強,增強自衛能力,珍惜和平,警惕和反對侵略戰爭。對於曾經侵略中國、造成戰爭災難的日本,中國民衆則希望日本國民能反省侵略戰爭的罪行,瞭解中國民衆受害的歷史事實,充分理解與尊重中國民衆反對侵略戰爭的感情,使兩國人民達成反對侵略戰爭、維護永久和平、保持友好相處的共識。 然而,日本國民對於那段歷史的“歷史記憶”,則與中國民衆存在很大差異。由於日本是發動侵華戰爭的“加害者”一方,當時的日本國民從對華戰爭中體驗的大多是勝利、征服、掠奪、收穫等愉悅的“獲得感”。戰敗後的日本雖然被國際社會判定爲侵略戰爭的“加害國”,一些主要“戰犯”也受到國際法庭的審判,但由於戰爭的發動者、領導者的戰爭責任並沒有得到徹底清算,一些人還很快恢復了在日本政府內任職,使得日本政壇一直有不願承擔戰爭責任及掩飾、美化侵略戰爭的右傾勢力存在,他們與社會上的右翼勢力相互呼應,採取掩蓋侵略罪行、歪曲歷史事實、美化戰爭參與者、淡化戰爭記憶等手段,使得一些日本國民的“歷史記憶”狹隘缺失,偏離歷史真實,也偏離和平正義的普世價值。這種狀況特別到近年,親身經歷戰爭的一代逐漸離世,對於僅靠前代傳承而形成“歷史記憶”的當代日本人來說,這種偏離更加嚴重。 據日本《每日新聞》2014年12月報導,日本媒體與大學聯合調查結果顯示,現在日本人口中有八成是戰後出生,他們當中一半人沒有聽說過戰爭,其中20歲-30歲年輕人中約有六成從未聽說過戰爭。另據日本《讀賣新聞》2015年2月進行的輿論調查顯示,對於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衹有5%的受訪者表示“很清楚”,44%的受訪者表示“知道一些”,49%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或“完全不知道”;60%的受訪者表示,是通過學校教育和教科書瞭解戰爭的。⑦由此可見,在日本政府右傾勢力主導下對侵略戰爭掩飾、淡化的策略,對於塑造沒有戰爭體驗的當代日本人、特別是青少年一代“去戰爭化”和“去罪責化”的“歷史記憶”確有成效。日本國民特別是年輕一代“歷史記憶”的日漸偏失,與中國、韓國等戰爭受害國國民“歷史記憶”的差異愈漸拉大,勢必成爲兩國“國民感情”及兩國關係的障礙,也給未來的東亞和平埋下了隱患。 但是也要看到,自戰後至今,日本國民中一直有許多愛好和平、具有良知和正義感的人士,包括政界、學界、社會、媒體、律師、商界人士及普通民衆,自發地發表文章、著述,組織民間和平組織,舉辦集會、展覽等,開展各種反省戰爭、謀求和平的活動。他們頂着右翼勢力的壓力甚至威脅,揭露日本侵華戰爭期間犯下的毒氣戰、活體解剖、強征“慰安婦”、南京大屠殺等被日本政府及右翼極力掩蓋而不被日本民衆廣泛瞭解的罪行,敦促日本政府認真反省戰爭,承擔戰爭責任,反對日本政客掩飾、美化戰爭罪責的右傾化言行。⑧日本民間和平人士堅持不懈的和平努力一直持續,形成來自民間、以民間和平人士爲主導的反對美化戰爭、反省侵略罪行、謀求東亞和平的民間“歷史記憶”,以求矯正掩飾戰爭責任的右傾化“歷史記憶”的偏失,縮小與中、韓等受害鄰國“歷史記憶”的差異,以求得與中、韓等受害鄰國和平友好相處,共建亞洲和平國際關係。這股民間和平力量雖然在當今日本社會不佔主流,但也具有相當的影響力,而且他們堅持不懈,使得這股民間面向和平的“歷史記憶”具有持久頑強的生命力,代表着日本國民中理性、和平的力量,他們因而也得到受害國中國民衆的尊敬,成爲連接中日民間友好的紐帶。日本這些愛好和平人士,正在做着增進中日“國民感情”的事。 三、“歷史記憶”與“歷史共有” 雖然中日兩國民衆“歷史記憶”的差異導致兩國國民的“歷史認識”存在差異,但隨着時代的變化,這種狀況也在發生改變。在全球化浪潮衝擊下,中日兩個東亞鄰國的經濟聯繫愈加緊密,國家共同體與“東亞利益共同體”的重合度日益擴大。在此環境變化之下,中日兩國國民更需謀求消解“歷史認識”上的隔閡,尋求建設“共同歷史認識”,以鑄造兩國永久和平、友好相處的“國民感情”基礎。 “共同歷史認識”的基礎是“歷史共有”,即對“歷史事實”的共同確認和瞭解,以及“歷史記憶”的相互瞭解和共有。對此,中日兩國學者及各界人士多年來做了許多工作。在他們的推動下,已經取得不少進展。例如,2006年,安倍晉三首次出任日本首相時訪華,與中國政府達成協議,組織中日兩國權威歷史學者進行“中日共同歷史研究”,經過雙方多位學者長達三年的認真研究、反復研討、交換看法,於2009年底完成了第一階段研究成果報告並公佈於世。報告指出,雖然兩國學者對一些戰爭具體事實的認定上存在差異,但“在日本侵略中國的戰爭性質及戰爭暴行的問題上取得了共識”。⑨這是第一次由中日兩國學者依據兩國政府協議而進行的共同歷史研究,是兩國政、學兩界共同認可的權威性研究。它奠定了兩國“共同歷史認識”的基礎,也應當成爲兩國政治家和國民大衆的歷史認識基礎。2014年10月,由參與“共同歷史研究”的中日學者撰寫的報告《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報告》的中文、日文版在兩國同時交付出版,中日兩國民衆通過閱讀報告內容,會自主作出理性判斷,會對兩國學者共同研究達成的“權威歷史共識”抱有尊重和接受態度。這也是建構兩國國民“共同歷史認識”的基石。 “共同歷史認識”的前提是“歷史共有”,它既需要親身經歷者的如實陳述,文獻和遺跡的物化留存,以及後世學者的研究認定,並誠實地形之於書籍、影視及大衆讀物,還需要通過傳播、教育等傳承形式,形成國民世代傳承的“歷史記憶”。通過兩國國民“歷史記憶”的相互交流、瞭解和共有,向着“共同歷史認識”趨近。 兩國國民“歷史記憶”的相互瞭解與共有,是民衆通過自主行爲即可進行的有效方式。在中日民間交流交往日益擴大的今天,兩國愛好和平的學者、文化界、旅遊界人士,以及衆多去對方國家旅遊、觀光、工作、學習的人們,都可以以自己的行動做到。例如,每年超過500萬人次的兩國互訪遊客,在對方國家除了欣賞美景、參觀古跡、品嘗美食、選購特產之外,也應當去參觀遍佈各地的歷史博物館,特別是記錄近代中日歷史、兩國交往以及日本侵略戰爭的歷史博物館、紀念館、歷史遺址遺跡等,去看一看對方國民的“歷史記憶”怎樣,與本國的“歷史記憶”有何不同,並認真地回味思考一下“戰爭與和平”對於兩國人民的意義。兩國的學者、媒體人和文化界、旅遊界等人士,應當鼓勵和引導兩國遊客做這樣的“歷史游”、“文化遊”。這就是“歷史記憶”的相互瞭解與共有。 對於去日本的中國遊客而言,也應當到日本的歷史博物館、紀念館瞭解作爲戰爭“加害者”和“受害者”雙重身份的日本國民形成了怎樣的“歷史記憶”,思考如何縮小兩國國民“歷史記憶”的差異,增多歷史事實的共有內容。此外,日本各地還有不少記錄近代中日友好交往歷史的紀念館和遺跡。如孫中山領導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辛亥革命,是改變中國近代命運的重大事件,但對於孫中山及這場革命與日本的關係,一般的中國民衆瞭解不多。其實,日本是孫中山領導革命的首要基地——自1895年領導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後即避往日本,後於1905年在日本東京聯合黃興等一批留日學生、革命團體成立中國同盟會,開始進行推翻清朝、建立共和的革命活動;辛亥革命成功、建立民國後,又於1913-1916年間在日本組建中華革命黨,開展反袁獨裁鬥爭;直至逝世前數月的1924年冬,由廣州北上途經日本時,又停留10天。在孫中山長達三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總計進出日本14次,在日本居留時間累計達9年,約佔他流亡時間的一半,革命生涯的三分之一。據日本學者考證,孫中山結識、接觸、交往過的日本人,包括政、軍、財、文等各界人士約三百人,與孫中山及革命志士黃興、宋教仁、何天炯、戴季陶等有過交往及各種關係的日本各方面人士達千人以上。⑩因此,日本各地留存着不少孫中山及革命志士與日本人士交往的歷史遺物遺跡。日本友好人士對此倍加珍視,有些被精心保存下來。他們通過建立紀念館、設立歷史遺跡以及舉辦展覽、演講、集會等各種紀念活動,讓這些中日友好交往的歷史作爲國民的“歷史記憶”而固化。 這些與中國友好交往的歷史遺存及所承載的“歷史記憶”,是連結中日友好的紐帶,通過赴日旅遊參觀的中國人的瞭解,可以成爲中日兩國人民“共有的歷史記憶”。這些中日友好交往的“歷史記憶”,就是中日深厚的“國民感情”的基礎。衹要兩國國民以“自主”態度加強相互瞭解,從“歷史記憶”的相互瞭解和共有做起,不斷向“共同歷史認識”趨近,就能由“歷史共有”奠定中日世代友好的國民感情基礎。 注释: ①日本內閣府大臣官房政府広報室:“世論調查報告書”,http://survey.gov-online.go.jp ②齊旭:“五年內往來人員增千萬中韓VS日本:政冷經熱”,《新民晚報》2015-04-14。 ③中國旅遊局信息中心:“推動中日韓三國旅遊更便捷、更舒適、更安全”(2015-04-13),中國旅遊局官網。 ④日本內閣府大臣官房政府広報室:“世論調查報告書”,http://survey.gov-online.go.jp ⑤日文原文爲:心の中たぉてる、嬉しぃ·悲しぃ·樂しい·さびしぃとぃぅょぅな感じ。 ⑥日文與“感情”詞義相近的“気持”一詞釋義爲:ぁる物事·人などに對して起こる心の狀態。 ⑦趙松:“日媒調查:近五成日本受訪者不知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人民網,2015-02-25。 ⑧步平:《跨越戰後:日本的戰爭責任認識》(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⑨步平:《跨越戰後:日本的戰爭責任認識》;步平、[日]北岡伸一 主編:《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 ⑩[日]安井三吉:“解說”,《孫文·日本関係人名錄》(神戶:孫中山紀念会,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