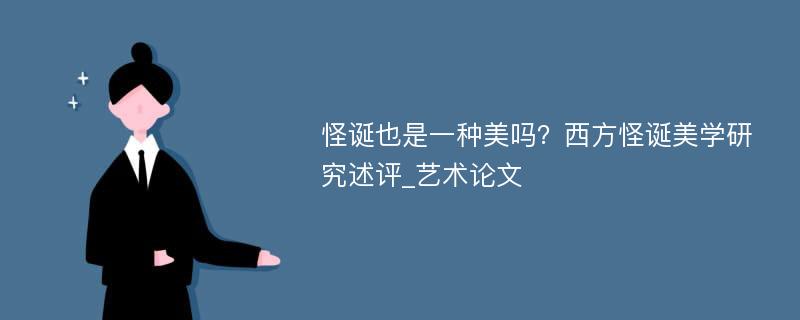
怪诞也是一种美吗?——西方怪诞美学研究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怪诞论文,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0)05-0088-05
一
怪诞(grotesque)是西方现代艺术中一个十分突出和普遍的审美现象。就像当代西方研究者哈普汉姆(G.H.Harpham)所注意到的:“尽管在20世纪的艺术中怪诞并非无所不在,但几乎没有哪位主要的艺术家与这一主题完全无关。”[1]462面对达利的《记忆的永恒》、德尔沃的《睡梦中的维纳斯》或者培根的《玛哈》这样的怪诞艺术作品,人们常感觉不能用简单的美丑来形容它们。上世纪初,一位首次参观怪诞艺术画展的观众如此表达了他的困惑:“在这个一流的画廊里,搞了些如此的失常绘画、疯狂色彩、说不清的奇思怪想,那些创作这些东西的人,如果不是玩的话,都应该送回学校里去。”[2]当时的诗人布伦特也批评道:“这个画展要么是一个糟糕的玩笑,要么是一场骗局。”[2]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小说、电影和音乐等其他艺术门类中。这些作品中似乎有某种既恐怖骇人又荒唐可笑的混合成分,它们在让人厌恶的同时却又有强烈的吸引力。这些现象说明,传统的审美尺度和审美范畴正在失去对这类作品的把握能力,现实的艺术和审美实践要求人们对这种新的审美现象作出解释。
于是从19世纪中期开始,西方越来越多的美学家逐渐把怪诞纳入到他们的研究视野。人们发现,怪诞不单是现代艺术所特有,从原始人的洞窟岩画到中世纪的哥特传奇,从拉伯雷的《巨人传》到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怪诞其实一直就存在艺术之中,只是被人们出于这样那样的审美误解或偏见而弃之不顾。今天人们已经认识到怪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审美现象,甚至有人认为:“作为一种复杂而带综合性质的艺术手法和审美途径,怪诞可以说是连接诸种感性学范畴——悲剧、喜剧、滑稽、丑与荒诞等——的元范畴。”[3]
但直至今日,我们国内对怪诞艺术的认识还相当不足。在近二十年出版的美学专著和教材中,要么对之避而不谈,要么把它与丑或荒诞混淆不分,而最大的谬误则是把它作为美的一个新形态,妄谈什么“怪诞美”①。因此,系统梳理一下西方近两个世纪以来的怪诞美学的发展历程,将会对我们国内的相关研究大有裨益。
二
《辞海》中对“怪诞”的解释为“离奇古怪”[4]。“怪”指奇特而异乎寻常的事物和现象;“诞”则指荒唐和不合情理。前者侧重外在形式,后者则更倾向内容。二者合在一起就基本构成怪诞的艺术风格。怪并不一定是完全背离通行准则,而是独特大胆甚至有些粗鲁地解释和运用这些准则。就像我们给小孩扮鬼脸一样,适度夸张怪异的表情可以让小孩感觉滑稽可笑,但如果把脸完全扭曲,则肯定会把小孩吓哭。因此,怪诞与庸俗和粗鄙不同,它虽然趣味特殊,但其中又包含着某种分寸感。艺术中的怪首先是指描绘现实中的怪事物、怪现象本身,以及对它们所做的不同凡响、有悖常规的解释,大胆运用新的出其不意的表现手法,来达到新奇效果。
艺术中的怪如果不能配合内容而成为目的本身,那么这样的怪也就失去了任何艺术上的审美价值,而仅仅成为一种噱头。美国研究者芬戈斯登(P.Fingesten)认为,怪诞必须同时体现在艺术表现的形式和内容上,“如果单是形式上的夸张、扭曲和暴力而使人想到怪诞这个描述性词汇,而主题却并非这样,或者说主题怪诞但形式却与怪诞毫不搭边(比如对怪诞的学术研究),那么我们所面对的就不能算是完全实现的怪诞艺术,只能算是类怪诞艺术(quasi-grotesque)。”[5]比如德国著名哥特艺术画家马蒂亚斯·格吕内瓦尔德(Matthias Grunewald)为伊森海姆祭坛所绘制的壁画,他用极度夸张骇人、甚至让人心生排斥的现实主义手法,描绘了基督受难时遭受的痛苦和折磨。但这样的艺术算不上是怪诞,因为其浓郁熟悉的宗教题材对基督徒来说既不“怪”也不“诞”。
有人常把怪诞看做是丑的一个类型,其实这是很不恰当的。怪诞的东西不一定丑,而只是怪。它并非完全与观者的审美情趣和审美期待相对抗,它引起的反应也并非厌恶、震惊或反感,而往往是混合了诧异、恐怖、趣味和愉悦的复杂情感。怪诞在英语、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中的表述都是“grotesque”,它们都源出于意大利语“grottesco”,这个词在意大利语中与“洞窟”(grotta)相关。最早在15世纪时人们用“grottesco”来指当时从洞窟中发现的原始绘画风格以及追随这种风格的装饰艺术,因其组合的怪异奇特而得名。后来由于怪诞艺术不断出现,人们才把它从单一的装饰风格扩展为一个美学范畴。而今天被人们公认的第一件真正意义上的怪诞艺术作品是1940年在法国拉斯科山洞发现的原始人绘制的野兽图案。它描绘了一头完全凭空想象的怪兽,狮身马首,肩背弯曲高耸,肚子因有孕在身而松弛下垂,前额还伸出一对长角,周身密布环形的神秘图案。它或许象征着动物的繁殖魔力。但另一方面,位于维也纳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艺术作品维纳斯石雕却不能算是怪诞,尽管她身上那些与生育有关的部位也得到了刻意强化。和丑一样,怪诞也总是与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相关。中国龙的形象在西方人眼里就是怪诞的。过去人们认为是怪诞的,今天却未必这么看,比如19世纪英国作家勃郎宁的作品。与他同时代的狄更斯在当时是现实主义作家的代表,可今天西方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倾向于把他看做怪诞作家。
荒诞与怪诞是更容易被混淆的一对范畴。但二者是有区别的,它们有着完全不同的词源。如前所述,怪诞最初用来指某种装饰绘画风格,以及追随这种风格的艺术。而荒诞则首先是个音乐术语,表示不和谐。二者都具有不合常规的特点,不同的是荒诞被冠之以“荒”,是荒唐性与反常性的结合。怪诞却冠之以“怪”,是怪异性与反常性的结合。美国学者汤姆森对这两个审美范畴的区分较有影响。一方面,他也承认“文学作品中(特别是戏剧作品中)荒诞的现代用法使其与怪诞颇为接近,因此荒诞戏剧甚至也可以称之为‘怪诞’戏剧。”[6]172但同时他又强调二者问有较大差别:“怪诞可以简化为一定的形式。而荒诞却无一定的形式,无一定的结构特征。人们只能感觉到荒诞是一种内容、一种特性、一种感觉或一种气氛、一种态度或世界观。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6]174也就是说,荒诞和怪诞都既表现在形式上也表现在内容上,但它们的侧重点却不一样。怪诞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要有明显的怪异性,而荒诞却主要是指内容的荒诞,在形式上却不一定有什么明确的荒谬或怪异性。
怪诞这种艺术样式早在远古时代就有了,比如前面讲到的拉斯科洞窟绘画。中国古代的《山海经》、《庄子》和一些志怪小说中也不乏怪诞形象描写。这些都主要是源于人类在社会生产力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对自然的恐惧、误解或者崇拜所造成。人们心目中的世界是怪诞的,故而他们艺术表现的世界也常常就是怪诞的。但直到19世纪之后的现代主义艺术中怪诞才真正成为艺术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像德国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所注意到的:“简要概括来说,我认为现代艺术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它已不再认同与悲剧或喜剧的范畴,……它视人生为一出悲喜剧,导致的结果便是怪诞成为最贴切的风格。”[1]465在曼看来,怪诞就是理性、道德和宗教信仰三重失落后西方世界的本相。英国学者斯泰伊格(Michael Steig)的话最能说明怪诞艺术家的心态:“生活在一个越来越像是梦魇的世界里,我们发现最能直接面对我们的处境的艺术就是这种艺术,在这里梦与现实不再清晰可分。”[7]253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在历经激烈动荡后,不少人心中不免又会生出一种迷茫、空虚、不安和困惑,人的主体意识似乎遭到前所未有的否定和压抑。正如李泽厚所说:
现代科技工艺和工具理性的泛滥化所带来的人性丧失,人的非理性的个体生存价值的遗忘、失落和沦落,作为感性个体的人被吞食、被同化、被搁置在无处不在的科技理性的形式结构中而不复存在,从当年希特勒的法西斯杀人机器到大公司的职业大军,从广告消费的奴役到人际关系的安排,一切都同质化、秩序化、结构化、均衡化……于是人不见了,人做了由自己所发现、掌握、扩大的形式力量和理性结构的奴隶[8]。
因此,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说,像以往那样崇尚模仿、追求完美的艺术已经不能适应现代艺术家的需求了,他们现在需要刺激、需要呐喊、需要尖叫、需要通过艺术来宣泄自己的困惑和不安,并用艺术来表现他们幻觉中的那个令人烦躁的世界。于是,各式各样的怪诞艺术也就应运而生了。
三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对怪诞艺术作出的最早评述来自于古罗马时代作家马库斯·维特鲁尼亚。面对当时出现的一种将人、动物和植物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的绘画风格,他表现了一般人常有的困惑:
……我们当今的艺术家用奇形怪状的东西装饰墙壁,而不再去再现我们现实世界的形象。他们不画圆柱,而画刻有凹槽、长着奇形怪状的叶子和盘蜗的树茎;不画山墙而搞蔓藤花纹。华柱和着了色的大建筑物亦是如此,山墙上精美的花朵从长袍里流展出来,其顶端莫名其妙的冒出许多长着人头或兽头的半身像。然而这样的东西过去不曾有过,现在不存在,将来也不会出现。……花茎怎能支撑起房顶,华柱怎能承担起山墙雕塑?嫩弱的枝芽怎会负得起人像,根须里怎会长出人体和花朵构成的奇异形状来[6]152?
19世纪英国学者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于1851年出版的艺术评论文集《威尼斯的石子》中专门用一章讨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怪诞艺术。他把怪诞分为好玩的(sportive)和可怕的(terrible)两种类型。前者主要由荒唐可笑的元素构成,后者则主要由恐怖骇人的元素构成。但他也指出,二者很少有单独存在的情形是,更常见的是它们混合搭配出现。在他的另一部著作《现代画家》中罗斯金还列出了怪诞引发的几种基本心理效用:一是“在闲暇时间内有益健康但不合理性的想象游戏”;二是“偶尔发生的对可怖事物或通常所谓恶的不合常规的冥想”;三是“想象力与它不能完全把握的真理的混合。”[7]254罗斯金对后人启发最大的就是他强调怪诞是可怖与可笑的混合物。
德国学者沃尔夫冈·凯泽尔(Wolfgang Kayser)于1957年出版的专著《艺术与文学中的怪诞》被公认为对怪诞作出了最全面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怪诞最根本的特点就是通过描绘一个时刻受魔怪之力摆布的世界从而在欣赏者内心唤起他对所处现实世界的异化感、疏离感和荒诞感。人们从怪异的形象中却能感受到一种“不相容领域的互相混合;静力规律的废除;本体丧失;对‘自然’形状的扭曲;种属差异不复存在;对人格的破坏和历史秩序的破碎。”[9]196人们欣赏了这样的艺术后,就会从心理上产生一种滑稽感和恐惧感,既会有一种苦涩的笑,又会引发一种对生活的恐惧。他说:“在那里,也只在那里,我们心中油然升起另一种情感。潜藏和埋伏在我们的世界里的黑暗势力使世界异化,给人们带来绝望和恐怖。尽管如此,真正的艺术描绘暗中产生了解放的效果。黑幕揭开了,凶恶的魔鬼暴露了,不可理解的势力受到了挑战。就这样,我们完成了对怪诞的最后解释:一种唤出并克服世界中凶恶性质的尝试。”[9]199
凯泽尔还将怪诞区别于纯粹的奇异幻想,比如神话故事。因为神话中的世界并未被疏离,那些人们熟悉的事物和规则并未显得怪异可怖。换句话说,在真正的怪诞艺术中,我们应时刻意识到那个异化世界与我们现实世界的关联。汤姆森也认为:“如果一个文学作品‘发生’在一个作家虚构的幻想世界里,根本就不想同现实世界有什么联系,那么也就不存在怪诞了,因为在一个封闭的幻想世界里,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读者一旦意识到他面临的是这样一个封闭的世界,便毫不惧怕地接受那最为奇怪的事情,因为并不要求他把这一切当真。”[6]164他还援引格哈特·门什英的话说:“怪诞的标志是可被人们意识到的虚幻和现实的混合。”[6]165
与凯泽尔几乎同时代的真宁斯(Lee Byron Jennings)也对怪诞作了较深入研究。他总结了怪诞的几条原则:第一,“怪诞的对象总是展现出可怖与可笑的混合质,或者更确切的说,它在观者心中同时唤起恐惧和着迷的反应。”这显然是继承了罗斯金的观点。第二,“这些看似矛盾的趋势是在现象本身中被结合到一起的,……而其结合的机制是理解怪诞的关键。”第三,“考虑到其中既有扰人心境的可怖趋势,同时又有滑稽搞笑缓解心情的趋势,我们便有理由作出这样的假设,即,有某种消解机制运作其中。可怖的形象从一出现便被喜剧的趋势所拦截,最终造成的对象便反映了这种对抗力量的交互作用。”[7]255
另一位研究者克莱默(Thomas Cramer)与真宁斯的观点相近,认为“怪诞就是被发挥到极致的喜剧手法所唤起的焦虑感。”[7]256而哈普汉姆则强调:“一个事物要成为怪诞的,它必须能唤起三个反应。笑与吃惊是其中两个;第三个要么是恶心要么是恐惧。”[1]463比如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曾有这么一段描写:
一股鲜血从门下流出,流过客厅,流出家门淌到街上,在高低不平的行道上一直向前流,流下台阶,漫上石栏,沿着土耳其人大街流去,先向左,再向右拐了个弯,接着朝布恩地亚家拐了个直角,从关闭的门下溜进去,为了不弄脏地毡,就挨着墙脚,穿过会客厅,又穿过一间屋,划了一个大弧线绕过了饭桌,急急地穿过海棠花长廊,从正在给奥雷良诺·霍塞上算术课的阿玛兰塔的椅子下偷偷地流过,渗进谷包,最后流到厨房里,那儿乌苏拉正预备打三十二只鸡蛋做面包[10]。
这段描写可谓是小说中怪诞场景的典范了。
四
一个经常困扰怪诞美学研究者的问题是:怪诞本身有审美价值吗?人们为什么会接受甚至喜欢这种艺术?怪诞的东西不美,这一点毫无疑问,因此如果有人说“怪诞美”,那就根本是一个不成立的自反式表述。有人把怪诞看做是美的一个形态,这是很不准确的。严格说来,怪诞和丑一样,只是一个审美范畴或审美现象,而非美的形态。能给人带来直接审美快感的审美范畴只有优美,其他的最多只能给人带来间接快感,甚至是恶心和反感。美国研究者卡尔郎(M.Kieran)对此所作的研究最具启发。
卡尔郎首先区分了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不同。他说:“如果一个对象仅在我们对它的观审中就能带来恰当的愉悦,那么它就具有内在的审美价值。”[11]383当然,适当的美学知识或艺术素养也经常是必需的。如此看来,怪诞和丑(尤其在现代艺术当中)就不可能有什么内在的审美价值,因为它们根本无法给人带来直接的审美快感。但卡尔郎强调,否认一件艺术品的审美价值绝不等于说它没有艺术价值,就像美的东西不一定是艺术,是艺术的东西不一定美一样。区分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是正确理解和评价怪诞艺术的关键。怪诞艺术不能带来审美快感,但却可以带来其他快感,比如认知的快感(cognitive delight)和怪异的快感(freakish delight),这些正是它的艺术价值所在。他说:“米开朗琪罗晚期作品中的怪诞风格受人重视,因为它们表达了人们在罗马教廷被毁后对世界宗教秩序的幻灭。怪诞、丑和非连贯性的艺术品的价值因其使我们探究自身的信仰、欲望和认知态度的方式而得到肯定。”[11]387比如当代著名的英国怪诞艺术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909-1992)以极度夸张、扭曲的手法描绘的人体,虽然一个个丑怪不堪,但却让人借以反思人生的境遇。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他那幅《玛哈》了,这样的作品单从审美层面上讲绝对是令人作呕的,但从认知的层面上,它的确又引人进入对道德、灵魂和肉欲形而上的思索。所以卡尔郎才说:“尽管缺少审美价值,这样的作品或许却有伟大的艺术价值。”[11]387
除了认知价值,怪诞艺术还有另外一种价值,即它的确在强烈吸引和满足着不少人对它的关注,能给人带去一种类似复仇或者自虐的快感。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曾经讲过这么一则故事:“阿格莱翁之子勒翁提俄斯从比雷埃夫斯进城去,路过北城墙下,发现刑场上躺着几具尸体,他感觉到想要看看但又害怕而嫌恶它们,他暂时耐住了,把头蒙了起来,但终于屈服于欲望的力量,他张大眼睛冲到尸体跟前骂自己的眼睛说:瞧吧,坏家伙,把这美景瞧个够吧!”[12]这说明,怪诞艺术对人的吸引力就源于其所呈现的怪诞形象与我们惯常熟悉的形象间的巨大差异。正是这种亲历所见与意识中原有知识储备的落差给人以强烈刺激。就像我们明知道某部电影恐怖异常,却非要忍不住去看一样。卡尔郎说:“那些引人厌恶的丑、不连贯和怪诞可以从本质上提供巨大的愉快,尽管我们并不认为它们值得期待。”[11]395现实经验告诉我们,人们的确常常从丑怪、混乱和疯狂中获取某种快感,要不然古代在处决犯人时不会引来那么多的旁观者,今天也不会有那么多人会对车祸现场那么感兴趣。
五
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一般把怪诞看做是艺术家个人放荡不羁的想象力的创造,是为了引人关注而耍弄的想象游戏,甚至会把它看做是艺术家病态心灵的征兆。但到了现代主义之后,怪诞却被视为是更能勘破现实的艺术途径,它再也不被看做仅仅是艺术家个人的畸形创造。所以哈普汉姆才会说:“在一个受炸弹统治的焦虑时代,被人们用最可靠的现实观测手法揭示的客观现实为怪诞艺术提供了刺激。”[1]463。现代艺术中的怪诞实际上是对病态社会现实的控诉,是人们对失去了的完美世界的呼喊。它们渴望以丑怪形象使人惊觉,发人深省。“用丑、怪诞或不连贯的艺术来面对观众或许可以有助于挑战我们关于健全、正常和美丽的舒舒服服的假设,以及那些我们用来理解世界的方式。”[11]397
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如果一个艺术家纯粹以怪诞为时髦,如蝇逐臭般片面追求新奇怪异的形象,以胡乱涂鸦替代艺术创作,这样的作品也就根本算不上是真正审美意义上的怪诞,而只能是粗制滥造的艺术垃圾。就像卡尔郎所说的:“那些一味培植我们最阴暗卑鄙的癖好的艺术是缺乏人性的坏艺术。”[11]397
收稿日期:2010-04-30
注释:
① 比如在王朝闻先生的《美学概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蒋孔阳先生的《美学新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朱立元先生的《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曾繁仁先生的《文艺美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以及叶朗先生的《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中,均没有关于怪诞艺术的讨论。在董学文先生的《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和蒋国忠先生的《审美艺术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中,存在将怪诞与丑和荒诞相混淆的嫌疑。另外,陈望衡先生在《当代关学原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中,则把怪诞和荒诞均视为丑的不同表现。相比之下,楼昔勇先生的《美学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和王杰先生的《关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对怪诞的研究较为全面,并将怪诞与丑和荒诞作了比较详细的区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