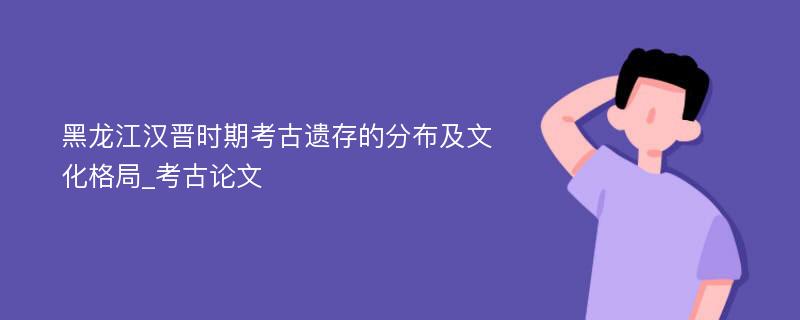
黑龙江汉晋时期考古学遗存的分布与文化格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遗存论文,考古学论文,黑龙江论文,格局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刚刚结束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是一次对不可移动文物资源全面的调查登录工作,普查所覆盖的范围和获取信息、数据的精度均非以往的文物调查工作所能与之相比,因此普查所获的信息和数据为科学的保护、管理与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平台。基于第三次文物普查的相关数据①,以下拟就汉晋时期考古遗存在黑龙江省域的空间分布状况及所反映的文化格局作一些分析,并就相关问题进行初步的讨论。
所谓汉晋时期大体指相当于中原王朝的西汉之始以迄东晋结束的历史阶段,绝对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06年至公元420年这样大约600余年的时间范围内。而按照考古学的观察,在黑龙江区域则大体可以将这一阶段相对年代的下限设定在所谓靺鞨文化的出现之前。当然考古学遗存所反映年代的上下限只能是相对年代的概念,因此存在着一定幅度的浮动或偏差当然也在情理之中。
考虑到黑龙江考古学研究基础还相对薄弱,考古学文化编年体系尚未得到很好的构建,而多数从事普查的基层工作人员对遗存时代的判断可能存在着一些难于把握的因素,加之统一的秦王朝本身也就历十余年的时间,所以在做统计时将那些标明为秦代的遗存也包括进来。另外较多调查对象所登录的年代信息可能比较宽泛或模糊,如存在着“商至汉”“秦至南北朝”“汉至南北朝”等年代信息,在现有条件下显然难以对此做更精确的判断,因此统计时采取了将调查对象所标示的年代信息中包含着汉、三国、晋或年代跨度覆盖了汉至晋的遗存都包含在内方法。
按照前述条件所作的初步统计,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在黑龙江省行政区域内发现的含有汉晋时期的不可移动文物遗存共计2270处②。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古遗址,其他仅为数量极少的墓葬(墓地)或遗物采集点。古遗址中名称明确标明为城址(或山城、堡寨等)的约有311处,根据笔者掌握的线索,普查登记中的所谓城址,情况并非如一,其中更多的是分布在丘陵山冈利用自然地势而简单加以人工掘壕堆土、构筑所形成的具有一定防御功能的堡寨,而真正成规模的能够围合的平原城址可能只是极少数。此外如果按照在七星河流域开展的全面考古勘查与测绘的成果③,这一时期的遗址中除去城址和普通居住址外,还有出于祭祀、瞭望以及设塞等功能而形成的特殊遗存。
按照自然地理的分区,现代黑龙江区域大致可以分作松嫩平原、三江平原、东南山地丘陵和大兴安岭山区、小兴安岭山区这样几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以及相互间的过渡地带。就三普发现或确认属于汉晋时期遗存所分布的地域考察,大致可以确认,在松嫩平原发现70处,三江平原1707处,东南山地456处,大、小兴安岭山地37处。上述遗存分布的统计主要是基于现行各县级行政区域汉晋遗存的发现所做的归纳,虽然存在着部分遗存的自然地理区划归属未必完全准确的可能,但总体应当能够反映当前调查登记汉晋遗存分布实际情况的基本态势。
通过分析,上述汉晋时期遗存在黑龙江区域所处地理位置的情形明显地反映出在地理分布上的不平衡性,即东南多而西北少,如属于东南部的三江平原和东南山地两者的汉晋遗存合计达2163处,占总数的95%强,而居于西部和北部的松嫩平原与大、小兴安岭山区却只有107处,尚不及总数的5%。之所以会在分布上出现如此强烈的反差,当然与调查中对遗存年代的判断或登记出现偏差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例如主要分布在松嫩平原西部的汉书文化在传统概念中被认为属于所谓的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④,因此在普查登记中调查者往往仅仅将其对应为中原王朝纪年的周代(含战国),而忽视了该文化年代的下限至少已进入西汉时期的情况,由此导致西部地区一些可能应当归属于汉晋时期遗存的年代下限判断偏早,最终影响到统计结果。然而即使是存在着年代判断不够精确、发现中的偶然性等因素的影响,仍应当承认汉晋时期人类活动遗存分布的密度在现代黑龙江省域的不同自然地理单元间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虽然根据普查登录的信息多数只能了解遗存的大致年代范围,而难以进一步掌握遗存的考古学文化属性,但是通过既往黑龙江区域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仍可以对不同区域汉晋时期遗存的文化属性作一些分析和了解。按照现有的知识,黑龙江区域属于汉晋阶段的考古学文化,根据地域的分布大致有如下几类。
松嫩平原:主要分布在嫩江中、下游流域的汉书文化;分布于松嫩平原东南部、干流松花江上游(也即松花江中游)的庆华遗存⑤;发现于嫩江中、上游的红马山文化⑥;发现于松嫩平原北部以望奎戚家围子墓群为代表的遗存⑦;此外在与吉长地区的接壤地带还有泡子沿类型遗存的存在⑧。
三江平原:广义上的三江平原大体以完达山为界,分作北部所谓的小三江平原和南部的兴凯-穆棱平原,其中在小三江平原的腹心地区汉晋时期的遗存主要有滚兔岭文化⑨、凤林文化⑩。而在北部边缘的三江沿岸还有所谓蜿蜒河类型的存在(11)。在兴凯-穆棱平原目前考古学文化的性质虽然尚不十分清楚,但如就穆棱四方台遗址的发现来看(12),至少穆棱河中上游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在总体面貌上应当更接近于团结文化。另在与松嫩平原以及东南山地交接的区域还发现有所谓的桥南文化(13)。
东南山地:发现有主要分布在绥芬河流域的团结文化(14)、分布于牡丹江中游的东康类型(15)、牡丹江下游的东兴类型(16)以及河口三期遗存等(17)。
大、小兴安岭山区汉晋时期考古学文化的面貌未详,相关考古学文化的属性也难以判断,如果就大兴安岭腹地的嘎仙洞发现来看(18),至少在大兴安岭地区可能会有早期鲜卑遗存的存在。另外通过嘉荫仁合古城所获陶器的线索分析(19),在小兴安岭北麓的黑龙江沿岸可能应当存在着与滚兔岭文化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类型。
尽管不能排除在黑龙江区域尚有未被学界发现、认识的相关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存在,但普查登记的汉晋时期遗存大体上应当多数能够被归属于上述文化之中。因此按照地理范围和文化面貌,大体可以将所知汉晋时期遗存在文化属性方面的分布以及所体现的文化格局作一基本的分析。
松嫩平原特别是嫩江中下游地区在西汉阶段应当依然是由战国以来当地的汉书文化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吉林通榆兴隆山发现的墓葬出土的西汉五铢清晰地表明了该文化年代的下限不会早于西汉(20),而在周边其他相关汉代遗存中所见到的陶鬲等因素,无疑应当来源于汉书文化。到了东汉阶段,红马山文化所体现的与大兴安岭西侧早期鲜卑文化的联系,表明了南下的拓跋鲜卑集团中还有向东挺进到嫩江流域的一支,类似的遗存发现的线索尚很少,反映了鲜卑的东进可能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扩张,但从远在三江平原腹地的凤林古城所出土的鲜卑式铜鍑来看(21),汉晋时期鲜卑集团对东方的影响仍不能小觑。汉书文化的终结很可能与鲜卑的东进南下存在着联系,除去红马山文化在大兴安岭东侧的出现外,以往在吉林大安渔场和后宝石等地的发现也能够透露一些端倪(22)。红马山文化之后出现了以戚家围子墓群所代表的遗存,虽然偶有一些因素体现着鲜卑陶器的风格,但似乎很难找到反映两者间承袭关系更多的证据,因此后者究竟是否属于鲜卑系统尚存在着疑问。戚家围子墓群的年代当在两晋时期,可能同辽西所谓的三燕文化或鸭绿江流域的高句丽存在着些许联系。戚家围子遗存目前也只是孤立的发现,进一步的认知显然还有待于更多地发现与研究。
松嫩平原东部的干流松花江上游分布着以宾县庆华遗址所代表的遗存,由于同一时期周边考古学文化分布的线索比较清楚,因此如果按照比较宽泛的界定基本可以将该遗存分布的地域限定在于流松花江以南、拉林河之北、蚂蜒河以西、京哈铁路之东这样一个大致范围内。庆华遗址存在着城墙与城壕,所以也有名之为“堡寨”或“城址”的,但根据发掘简报,城墙叠压着房址,所以城墙的年代究竟可以判定为什么时期尚存疑问。由房址等遗存出土的陶器分析,庆华遗存的年代可能主要属于汉代,其同西侧的汉书文化和吉长地区的泡子沿类型乃至东南山地的团结文化都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总体上更接近泡子沿类型,两者应当属于同一文化系统(23),从现有的线索分析,庆华遗存在当地没有生成的基础,因此很可能是吉长地区的泡子沿类型或其前身西团山文化向北扩张的结果。五常白旗遗址的发现表明泡子沿类型向东南方的扩张有可能已越过了拉林河,而同样来自吉长地区的影响在稍西一些的嫩江下游也有所表现,以往曾在肇源望海屯遗址发现过反映农安田家坨子遗址相关因素的遗存(24),而后者很可能是泡子沿类型的一种变体,是泡子沿类型在与汉书文化的交互影响下所形成的一种地域类型。
尽管存在着较多的类型或因素,但汉晋时期,至少是在东汉之前,黑龙江区域松嫩平原的考古学文化应当仍以汉书文化为主体,就目前所了解的线索,三普所登录的信息以及据此所得到的统计结果显然与该文化分布的真实状况尚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即松嫩平原汉晋时期的遗存当然不会只有六七十处左右,估计仅汉书文化遗存就当会不少于上百处。
三江平原北部,即所谓的小三江平原汉晋考古学文化类型相对简单,除去在北端的黑龙江沿岸有所发现的所谓蜿蜒河类型之外,基本是以乌苏里江西侧诸支流流域为分布核心区的滚兔岭文化和凤林文化,两支文化前后相接,并表现出具有一定的传承关系,但两者可能也并非简单的一脉相传,而应当是融入了其他文化因素所导致的重构。滚兔岭文化的年代大体相当于中原王朝的两汉阶段,以往在佳木斯桦南的小八浪遗址中曾发现有汉代的五铢(25),说明该遗址滚兔岭文化遗存年代的上限至少不会早于西汉早期。而凤林文化年代的下限则有可能已进入南北朝时期。滚兔岭文化陶器突出的特征之一是末端上翘的所谓角状把手(器耳),在罐、钵等器类上都有应用,调查工作中这一特征成为判断遗存年代的主要依据。凤林文化时期虽然角状把手依然存在,但已呈现衰退的趋势,而较之滚兔岭文化,陶豆则十分流行。由于角状把手和陶豆柄都具有比较坚固的特点,所以更容易得以保存,在调查中被发现的几率也就更高,因此如果以角状把手和陶豆分别为判断调查遗存文化属性的主要依据,则不难发现目前在三江平原北部所见的汉晋遗存实际上更多的应当属于滚兔岭文化或相当于滚兔岭文化的阶段,因为已知的各遗址往往会有角状把手的发现,而陶豆的发现则很少见。如在七星河流域调查勘测的遗存介绍之中,采集到角状把手的遗址(城址)有31处,而采集到陶豆者则仅有4处,由此大致可以了解两个阶段遗存的数量多寡的基本趋势。
所谓的蜿蜒河类型是三江平原北部汉晋时期的另一种考古学文化,通常认为其与俄罗斯一侧的波尔采文化属性相同,就目前所了解的情况,在中国一侧该类遗存主要发现于三江平原的北端,而在七星河等三江平原的腹地则很少有该类遗存的出现。在俄罗斯的波尔采文化中曾发现有类似于滚兔岭文化的角状把手罐,因此可知该文化的年代至少部分应与滚兔岭文化相当。按照俄罗斯方面的研究,波尔采文化可以分作三期,对比来看在三江平原的相关发现虽然也有角状把手的存在,但似乎部分遗存的年代可以稍晚一些,如就目前所见到的陶器特征来看,蜿蜒河遗址所出的部分陶罐和碗已颇具早期靺鞨的风格,因此估计其年代很可能至少已到了魏晋阶段。
桥南文化的情况稍显特殊,这种目前仅发现于干流松花江中游,地处松嫩、三江平原以及东南山地交接地带的考古学遗存被分作两期,早期由于没有铁器的发现而被视作青铜时代,而晚期则进入了汉代。器身箍多周附加堆纹的鼓腹罐是该类遗存陶器最具典型的特征之一,如就方正于家屯和依兰桥南两处遗址陶器的对比来看,可能该遗存两期之间衔接的还比较紧密,似乎并不会存在太大的隔阂或距离,所以是否真的存在着青铜与铁器两大历史生产形态阶段的差异,可能还需斟酌,没有铁器的发现并不意味着遗存就一定会早于所谓的铁器时代。在于家屯遗址出土了应当属于中原文化系统的铁钁和铁刀等,而且也有角状把手的存在(26),因此将其年代判断为汉代当不会有太大的出入。这里的角状把手具有一定的特色,表现出所谓的“柱(瘤)状耳”与角状把手相结合的特点,可能反映着分别受到滚兔岭文化和庆华遗存东西两方面影响的事实。由于东西两侧乃至南部均有同一历史阶段考古学文化的存在,而北部即为小兴安岭山地,因此桥南文化分布的范围可能也不会太大,其来龙去脉以及文化属性目前也不是十分的清楚,但总体而言仍可以视作东部考古学文化系统之一。
三江平原南部是穆棱-兴凯平原,由穆棱河冲积平原和兴凯湖湖积平原组成,大体以完达山为分水岭与北侧的小三江平原相界分。由于邻近绥芬河流域,所以在穆棱四方台发现的汉晋遗存面貌更接近团结文化,而估计到了穆棱河下游和兴凯湖以北的区域,汉晋时期遗存的文化属性或当比较接近滚兔岭或凤林文化。
黑龙江区域的东南主要是由张广材岭和老爷岭诸山脉构成的山地丘陵,牡丹江、绥芬河以及穆棱河穿行其间,形成了一些适合古代人类居住、生产的河谷盆地、冲积平原等。绥芬河作为独立的水系是黑龙江区域唯一流入日本海的河流,两汉时期这里是团结文化的分布区域。除去黑龙江的发现外,在同为流入日本海的吉林省图们江流域以及俄罗斯的滨海地区和朝鲜半岛的东北角也都属于该文化的分布区。团结文化在俄罗斯学术界被称作克罗乌诺夫卡文化,彼得大帝湾沿岸及纵深地区应当是该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在黑龙江区域团结文化在穆棱河上游也有分布,而文化的影响则可以深入到松嫩平原。按照林法先生既往的研究,团结-克罗乌诺夫卡文化的年代大体在春秋战国之交至东汉阶段,但如果就陶器特别是铁器所表现的样相而言,有关年代上限的认识似乎稍嫌偏早,估计可能主要是受到[14]C测年数据的影响。目前学术界多将团结文化视作中国历史文献记载中“沃沮”的遗存,虽然也存在着一些出于对文献理解不同而产生关于沃沮内部部属划分及对应的歧义,但仍可以将其作为东北地区汉晋时期古族古部地理分布研究的一个基点。
在牡丹江中游分布的汉晋时期考古学文化主要是东康类型,在当地该类型的分布可能比较密集,仅在宁安的镜泊湖附近的发现就达数十处之多(27)。器口作椭圆形的所谓舟形器和带柄的陶勺是该类型陶器比较突出的特点,筒形罐和乳钉状纽表明了其同长白山山地考古学文化间的联系以及在东北地区考古学文化系统中的归属,而柱状耳和浅盘的豆则有可能是团结文化影响的结果。通过[14]C的测定,东康遗址F2陶瓮中出土炭化谷物的年代为公元255年±85年(树轮校正为公元315年±95年),大体相当于中原的魏晋时期。[14]C年代测定结果同牡丹江下游地区的海林河口和振兴遗址的发现相符,在这两处遗址都存在着与滚兔岭文化年代接近的东兴类型被与东康类型较多联系的河口三期遗存所重叠的现象。
进入牡丹江下游,汉晋时期的遗存分别发现有东兴类型和河口三期两种遗存,在河口与振兴遗址都存在着前者被后者叠压或打破的层位关系,因此两者的年代先后关系应当比较明确。然而尽管两者年代大体前后相接,但文化性质可能却大相径庭。东兴类型拥有较多的大鼓腹瓮、罐和角状把手,因此体现了与滚兔岭文化更为接近的面貌,而河口三期则是以筒形罐为基本特征,乳钉状纽十分发达,存在着椭圆形口器和陶勺等,反映着与东康类型较多的共性。通过牡丹江下游诸遗址堆积提供的先后关系,也可以间接的证明关于东康类型的年代至少部分的晚于滚兔岭和团结文化的结论。牡丹江下游汉晋遗存与周邻文化之间的亲缘关系,充分体现了该区域在文化地理中的特殊性质。汉晋时期的两类遗存在牡丹江下游的先后出现很可能是来自三江平原北部的滚兔岭文化和源自牡丹江中游的东康类型先后向该地区扩张的结果,由此似乎也可以表明牡丹江下游地区汉晋时期的这两类遗存都不具备独立命名考古学文化的条件,可能还是将其分别视作由原生区域或本体文化中分离出来的地域类型更为适宜。
汉晋时期黑龙江区域考古学文化反映了比较纷杂的样相,特别是一改自白金宝文化以来松嫩平原考古学文化系统更为发达的趋势,作为东部文化系统分布区的三江平原成为人类历史活动十分频繁的区域。通过各地的发现,基本可以确认黑龙江区域汉晋时期的遗存中以滚兔岭文化的数量最多且分布最为密集,文化的影响也比较广泛,因此滚兔岭文化应当是两汉时期主要以三江平原为核心势力范围的强势考古学文化。
按照对东北地区考古学文化系统的总体认识,滚兔岭文化无疑应当属于以长白山—千山为轴向的东部文化系统,即中原文献记述体系中的“夷”人系统。然而如果对比于汉晋时期同系统的东南诸考古学文化,滚兔岭文化与之最大的区别是缺乏陶豆。大约自新石器时代较晚阶段起豆形陶器就作为东北地区东部考古学文化系统的一项比较稳定的特征而存在,到了战国两汉时期陶豆在东部所流行的范围和程度都更为发达,也成为与东北西部文化系统相区别的最重要陶器器用特征之一。
徵之于文献不难发现,在中原史家笔下恰恰有“东夷饮食类皆用俎豆,惟挹娄不”的记述(28),尽管目前尚无法证实文献中所谓“俎豆”的指向就一定包含着考古发现中所见的“豆”形器具,但如就所谓的夫余、沃沮等已取得学术界广泛认同的考古学文化中都含有相对发达的陶豆来看,滚兔岭文化在器用方面与之最突出的变化确实是缺乏陶豆。即使以黑龙江区域的情形看,围绕着滚兔岭文化的团结文化、东康类型以及庆华遗存等都有陶豆的存在,而恰恰可能由滚兔岭文化扩张形成的所谓东兴类型却也没有豆的发现。
将滚兔岭文化视作挹娄遗存的认识当然不能仅仅着眼于陶豆的有无,如果从文献记述的地望、气候、物产以及生活习俗、居住形式等各方面来看,滚兔岭文化确实与文献记载中的挹娄存在着较多的相符之处。而如果目前学术界所确定的吉长地区的泡子沿类型与绥芬河流域等环彼得大帝湾区域的团结文化分别属于夫余和沃沮的认识无误的话,则将滚兔岭文化对应于文献记述中挹娄的结论应当不会存在太大的出入。
虽然滚兔岭文化应当属于挹娄的遗存,但接续其后的凤林文化是否也属于挹娄则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目前就陶器而言,凤林文化无疑从滚兔岭文化中继承或汲取了一定的因素,但也出现了更多的新因素,特别是在滚兔岭文化绝少见到的陶豆,已成为凤林文化陶器器用的基本组合。因此凤林文化之于滚兔岭文化究竟是同一谱系文化的新陈相因,还是外来文化对原住民文化因素的借鉴或吸收,仅据现有资料显然尚都不足以说明。其实对两者关系的疑问,还可以由遗存分布的差异得到反映,当前在三江平原北部所见到汉晋阶段的遗存,实际上可能绝大多数都应当属于滚兔岭文化,前面所提到的陶豆很少发现就是一个证据,同时牡丹江上游东兴与河口三期的文化属性则反映了滚兔岭和凤林两支文化的势力消长。而如果是同一集团族群的自然发展,这种由遗存分布所体现的人口密度或人类活动能力的巨大差异将如何解释?因此尽管两者在分布地域中有所重叠、年代先后相接,文化特征又有所联系,但仅据目前的资料仍不宜简单地将两者视作同一文化谱系前后相继的发展阶段或部族集团,当然也不能简单地将凤林文化归属于“挹娄”或其后裔。
尽管文献的追溯可以上溯到上古时代,但中原王朝致力于对东北地区的大规模开发或经营实际上应当以战国后期燕国的一系列活动为起点,其中最重要者莫过于秦开驱东胡。实际上所谓的秦开驱东胡的事件并非仅仅是燕国势力对辽西等东北西部的诸胡系部族的打击或驱赶,通过这一行动,燕国取得了东北南部的大量土地,如就燕长城以及燕国于新辟之地所筑城邑界定的大致范围而言,整个今之辽宁以及内蒙古东部甚至吉林的南部也都被纳入到中原王朝的版图之中。燕亡之后,统一集权的秦汉帝国对东北的经略也没有松懈,绥中渤海之滨的姜女石秦汉行宫表明中央政权对东北的重视,而汉武帝的四郡之设更牢固地确立了东北地区相对于中原王朝的从属地位。
对原住民集团的驱赶和具有相当规模的殖民活动当然要引起东北地区古部族原居民的异动,目前考古学上所见到比较突兀地出现在吉长地区的邢家店北山墓群(29),就应当与这一大的历史背景有关。可能正是中原势力的北扩,迫使东北南部部分的原居民集团向更北的区域转移,从而导致来源于吉林南部山地所谓宝山文化的细柄或镂孔陶豆在吉长地区的大量出现(30),而泡子沿类型北进所引发的庆华遗存形成于松嫩平原东部,可能也是连锁反应之一。随着中原文化所施加影响的不断深入或拓展,东北地区的原居民文化也自然会进入调整的状态,而那些率先适应并能够吸收先进文化或技术的集团可能就会借机发展壮大自己,形成新的格局。中原式铁器特别是铁制农具在东北东部的广泛发现,说明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及其作用,而汉晋阶段黑龙江东部地区人类集团活动的繁荣,无疑也应当是这一大背景下的产物。
在传统知识中黑龙江区域位于高纬度地区,由于受到气温较低等自然条件的限制,历史上人类大规模的开发较之自然条件优越的中原等地要晚许多。若就所谓史前文化的发展而言,也确实反映了环境因素影响的事实。然而到了汉晋时期,反映人类活动的物质文化遗存分布密度在一些区域却得到了极大幅度的增长。例如在向来认为是所谓“北大荒”的三江平原,属于汉晋时期的遗存就发现了近两千处,而处于三江平原腹心的七星河流域更达到了超出现代居民点密度的现象。虽然其中不能排除存在着古代居民集团受土地利用频率限制或季节气候变化而频繁更换居地的因素,但仍能够反映当时在中原先进文化和技术的影响下,农业生产形成了一个飞跃的事实。经过了汉晋阶段的发展,黑龙江区域的农业文化逐渐成为了主导,东部地区人类集团的势力可能也超出了西部,此后的靺鞨、女真分别自东方兴起,先后建立了渤海与大金,无疑应当与汉晋阶段东部诸考古学文化的积累不无联系。
附记:本文的形成得益于黑龙江省的三普工作和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近年来相关的发现与发掘。在历年的参观、考察中得到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伟、赵永军、田禾、刘晓东诸学友诸多的教益和启发,特此致谢!
注释:
①国家文物局.黑龙江省不可移动文物目录[Z].北京:2011.
②在统计之前笔者根据以往发表的资料对普查登录信息进行了初步校核,将一些通过调查、发掘确认明确存在汉晋时期的遗存、而在普查登录的年代信息中却未有体现的对象也纳入到统计的范畴之中,因此本文的统计结果与三普发布的数据并不完全相符.
③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七星河——三江平原古代遗址调查与勘测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346~376.
④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大安汉书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A].东北考古与历史(一)[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136~140+88.
本文所指“汉书文化”的概念,即以往所习见的“汉书二期文化”,由于近年来的发掘表明汉书遗址存在着多个时期的堆积,已不能使用“二期”来命各自白金宝文化结束到汉代这样一个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参见张伟.关于黑龙江省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几点看法——以嫩江流域青铜至早期铁器时代为例[J].北方文物,2008(4):14、15.
⑤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宾县庆华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88(7):592~600.
⑥张伟.红马山文化辨析[J].北方文物,2007(3):1~16.
⑦a.许永杰,李陈奇,刘晓东.黑龙江考古的世纪思考[J].考古,2003(2):3~10.
b.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黑龙江[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126~128.
⑧据介绍在五常白旗遗址发现有相当于两汉时期的泡子沿类型遗存.参见:
a.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世纪黑龙江省考古大检阅——近年来我省考古新成果展示[N].黑龙江日报·多媒体版,2011-1-31.
b.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黑龙江[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126.
⑨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滚兔岭遗址发掘报告[J].北方文物,1997(2):6~15.
⑩a.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友谊县凤林城址1998年发掘简报[J].考古,2000(11):24~34.
b.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友谊县凤林城址二号房址发掘报告[J].考古,2000(11):35~41.
c.黑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黑龙江友谊县凤林古城址的发掘[J].考古,2004(12):50~65.
(11)黑龙江省博物馆等.黑龙江省绥滨县蜿蜒河遗址发掘报告[J].北方文物,2006(4):12~20.
(12)裴红善.黑龙江省穆棱市四方台遗址调查简报[J].北方文物,2006(3):18、19.
(13)李砚铁,刘晓东,王建军.黑龙江省依兰县桥南遗址发掘及相关问题[J].北方文物,2001(1):1~9.
(14)林沄.论团结文化[J].北方文物,1985(1):8~22.
(15)a.黑龙江省博物馆.东康原始社会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1975(3):158~168.
b.黑龙江省博物馆考古部等.宁安县东康遗址第二次发掘记[J].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3):42~47.
(16)a.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黑龙江海林市东兴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96(1):15~22.
b.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黑龙江海林市三道河子乡东兴遗址1994年考古发掘简报[J].北方文物,1996(1):2~6.
c.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黑龙江海林东兴遗址1992年试掘简报[J].北方文物,1996(2):26、27.
(17)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口与振兴[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18)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遗址1980年清理简报[A].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二)[C].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444~452.
(19)万大勇.黑龙江省嘉荫仁合古城调查简报[J].北方文物,2003(1):23、24.
(20)吉林省文物工作队.通榆县兴隆山鲜卑墓清理简报[J].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2):65~69.
(21)潘玲.黑龙江友谊县出土的鄂尔多斯式青铜釜探源[J].北方文物,1994(3):127、128.
(22)a.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吉林大安渔场古代墓地[J].考古,1975(6):356~362.
b.白城市博物馆.吉林大安县后宝石墓地调查[J].考古,1997(2):85、86.
(23)吉林市博物馆.吉林市泡子沿前山遗址和墓葬[J].考古,1985(6):497~507.
(24)思晋.望海屯遗址略记[J].北方文物,1987(1):19~22.
(25)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文物管理站.黑龙江桦南县小八浪遗址的发掘[J].考古,2002(7):37~48.
(26)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方正于家屯汉代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2009(6):26~42.
[27]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宁安县镜泊湖地区文物普查[J].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2):56~69.
(28)(晋)陈寿.三国志·魏志·东夷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9)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农安县邢家店北山墓地发掘[J].考古,1989(4):300~309.
(30)马健,金旭东,赵俊杰.再论邢家店类型遗存及相关问题[A].边疆考古研究(第11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165~173.
标签:考古论文; 松嫩平原论文; 中原文化论文; 文物论文; 中国东部论文; 牡丹江论文; 中原论文; 中原集团论文; 西汉论文; 陶豆论文; 博物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