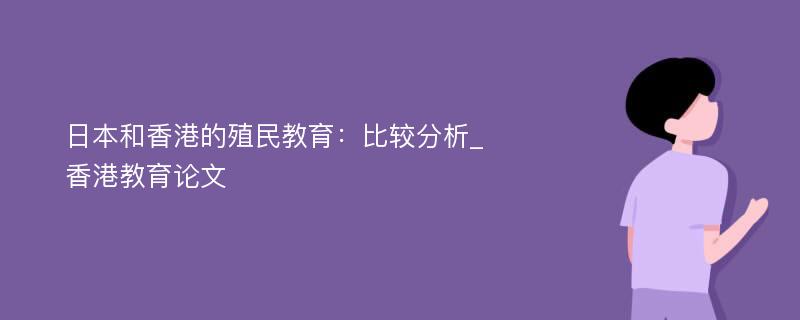
日本殖民教育与香港:一个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香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1年,香港刚刚经过了被英国割据一百年的历史,二次大战的炮火又使香港陷入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统治之中。在日军占据香港的三年零八个月时间里,香港在社会经济和文教等方面都遭受重创,也使这一时期的香港教育在日本殖民政策统治下几乎陷于停顿。
由于教育遭受前所未有的破坏,同时日本殖民的历史较为短暂,因此在香港史料中记载甚少,香港教育历史研究中也大多忽略不计。即便是专门研究日占时期香港的著作,也视此时的教育为香港教育的黑暗时期,涉笔极少,这为本文的研究带来不少的困难。
从目前资料情况看,主要可资参考的香港教育史料都集中于1941年之前和二次大战之后。与此相应,有关香港教育历史的研究也都关注二次大战前后,而尤以香港早期教育史研究为多。于日占时期的香港教育,从研究资料和研究成果来看,都相当薄弱。
日占时期香港教育专门研究,至今仅见梁炳华(1995)《香港在日占时期的教育概况》一文,载于1996年胡春惠主编、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出版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其余如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高添强、唐卓敏编著的(1995)《香港日占时期:1941年12月—1945年8月》;1993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关礼雄的《日占时期的香港》。其中,涉及此时期的香港教育也仅限于一些简况或片段的论述。另外,还有一些回忆性质的文章、书籍。
第一手资料也很有限。可资参考的有当时反映官方意识形态的报刊,如《香港日报)等,以及记录当时政策法规的,如香港占领地总督部的《总督部公报》(1942-1945)。
然而,本文研究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梳理日占时期香港殖民教育的历史情况,另一方面也期望探讨日本和香港的历史关系,以及比较日本与英国在香港殖民教育的政策和特征,以深化对殖民主义教育的认识,故而在视野上推展,又使可资利用的史料有所融通而扩展。最后,力图用历史和比较的研究方法,来呈现日本殖民香港时期在文化教育上的真实图景。
香港地处欧亚交通的枢纽,19世纪是日本人乘船去欧洲的必经之地。无论是漂流的渔民,或外访使节团和文人、政客,日本人与香港的交往早在19世纪就已开始。作为英国在东亚扩张的桥头堡,日本对英国在香港的发展表示关注。
英国早年在香港开办的英华书院,其所出版的部分书籍和报刊,在日本幕末时期曾为专门负责翻译的“蕃书调所”重印,在日本知识界广泛流传。在英华书院于1870年停办之前,其一直是日本历次过港使节团必访之地,并充当着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日人益头骏次郎记载,英华书院有英人和华人共事翻译工作,除翻译出版四书中的《孟子》、《论语》等,尚有《博物新编》、《地利全志》以及《遐迩贯珍》和《六合丛书》等。其中,《遐迩贯珍》是最早用铅字排印的中文杂志,起初由伦敦会的麦都思任主编,1856年改由理雅各为主编。《六合丛书》则是西方传教士所办的综合性杂志,1857年1月26日在上海创刊,墨海书店刊行,大部分文章出自英人伟烈亚力之手。
随着日本明治维新后以侵占亚洲大陆为目标的“大陆政策”的逐步推行,虽然当时还未有侵占香港之心,但已视其为通往台湾、华南和印支各地的门户,日本在香港的军事情报以及商业活动得以明显地发展。自1874年起,日本一直派员来港从事搜集军事情报的活动。经济上,也从小型的商业活动逐步扩展到煤炭、纺织品等方面的贸易。在19世纪末,香港开始成为日本在海外的重要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与香港有关系的日本近代有名的政治评论家德富苏峰。德富苏峰原是进步平民主义的鼓吹者。甲午战争前后,从平民主义走向了国权主义,提倡出兵朝鲜和征伐中国,发表《大日本膨胀论》等肯定侵略战争的文章,并逐步倾向军国主义。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先后出任大日本文学报国会会长和大日本言论报国会会长等,其提倡的以皇室为中心的国家主义,一度成为日本言论和思想界的主流。1896年,他途经香港而后发表《香港三日》和《有关香港之管见一二》。前文为旅行杂记,后文则涉及香港的历史与现状、香港与日本的商业关系,以及对台湾的利害关系。在后文中,他探讨当时英国殖民统治在香港的经验,并将英国殖民者对香港的管制方法与俄国进行比较。他称:“英国人在给予商业自由的同时,每用英国作风去训练和统治当地人。俄国人管制商业的自由,但对当地人却十分放任。英人如严师,动辄为子弟所怨愤;俄人如强迫酒徒喝酒,每为当地人感激爱戴,以此可知其术之巧拙。若不能如英人之使当地人畏服,或不能如俄人之笼络当地人,只招其轻侮,则国势决不能膨胀于世上。”他明确希望日本国民和明治政府,能够多认识香港,以便借鉴香港而加强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以与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一争高低。
时至20世纪30年代,日本在香港已有了巨大的经济影响力。随着30年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英国本土风雨飘摇,无力顾及包括香港在内的海外殖民地。这时,日本在吞噬了半个中国之后,开始窥视包括香港在内的英属殖民地,以成为进攻西太平洋其它地方的最佳跳板。
香港在沦陷前,办学相对自由,办学形式也较多样,但英语是官式语言,而官立和津贴学校始终是港英政府支持的重点。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及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中国内地人士大量来港,致使香港教育空前发展,也成为中文教育最为蓬勃发展的时期。
日本占领以后,以军事为主的殖民政府对待教育,主要是将之作为达致军事和政治目标的辅助工具,教育受到了削弱。日占时期,全港学校1937年时有1177所,学生人数约12万人,至1945年7月萎缩至46所。其中,中学15所,小学31所,学生人数从1944年的7000余人减至4780人。1945年8月,日本殖民当局面临战败形势,为减低经营学校的困难,成立香港教育刷新会,提出“合并经营计划”。在联合中学和小学及其分校过程中,又废止中小学共8所,使全港中小学校数进而缩至38所。一位目睹当时教育凋敝的日籍牧师写道:“自战争爆发,日军占据香港以来,外籍教师已悉数撤离,志节忠贞高尚的年轻人又不肯在日本占据下的沦陷区工作,所以相率避离,深入中国后方。各家长生活日戚,也没有余力送子女上学,此地也似乎早已不能作充分的教育活动。”
进而究之,一方面日方为减轻香港在人口及其粮食等方面的战时压力,采取强制性的归乡政策,导致人口大量减少。1942年1月,军政厅即制定华人疏散方案,由民治部成立“归乡委员会”(后改为“归乡指导委员会”),从陆路和水路驱散港人。直至日占末期,居港人口从战前的约150万仅余60万人左右。另一方面,在于受日本军政府所颁布的私立学校规则(香督令第十六号)的限制。所谓私立学校,多为华人团体资助的中小学校,华人在香港经营学校以及从事教育工作都须受到日本军政府的严格控制。其规则规定,私立学校创办、学校名称、种别、地点、设备、创办人,及校长、职员组织、各学年教科书目、经费及维持方法,都须受占领地总督之严格监督。教员均须取得占领地总督之认可证,否则不能聘用。校长及教员若被认为不适当时,得令其解职或取消其教育认可书。适当不适当,自然在于军政府的掌握之中。结果,在主要由华人团体资助的中小学里,教职员既得不到职业和人身安全保障,也难以维持本身的生计。
专上学府,如当时仅有的香港大学和罗富国师范学院,由于被视为英属敌产而陷于停学。创建于1939年的罗富国师范学院,在战争爆发后,大部分学生没法回到中国内地继续学业。其因战时被征用为日本官员训练学校而获保存。建立于1912年的香港大学,由于被认为在军事和行政上对日军政府不会造成障碍,当时的校长与军政府达成协定,大学校园、设施、图书才得以基本保住。但是,教学、研究活动就此停顿。
相比华人学校困顿不前的情况,为日籍儿童所办的学校却受到优厚的待遇。日治当局在1942年9月成立“香港国民小学校”,仅从学校的医疗服务来说,日籍儿童的健康受到特别关注。校内没有诊疗室,聘请专科医师,包括内科、外科、牙科等。这与当时华人学校无法同日而语。
在高等教育方面,取而代之的是日治政府所创办的官立性质的东亚学院,这是一所典型的体现所谓东洋精神教育的学院。由于其为官立,故免收学费。其课程分为两大类:高等科主要培养师资和银行、社会机构的高级职员;普通科培养一般事务、书记和文书人员。科目分为五类:国语(日本语)、修身公民、体练(体育)、音乐和商业。其中,以日语和对日本的全面了解为主。日治当局对东亚书院投注了大量资金,然而在其招生时,虽则发出了700多份报名表,然收回的却只有200余份。事与愿违,效果并不理想,也未能改变高等教育的颓萎局面。
日占时期,正如日本首任总督矶谷廉介所称:“在军政下之香港,今后之统治建设,应共同协力,完成大东亚圣战,一洗香港从前之旧态,方能发扬东洋本来之精神文化”。在这方面,日本当局推行了一系列的殖民文化教育政策。如在颁布的香督令第十六号“私立学校规则”中,规定学校不得使用英语为教授用语,每星期内必须教授日本语四小时以上。除沿用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教材外,日治当局更从日本运来部分教材和日语教科书,以便教授日本语。同时,颁发香港总督部制定的中小学教材。当时的文教课长明确表示,“向来对于攻读日文,是拣取讲习会等处迅速使得学生能学会‘会话’,以便利其临时应用而已。惟今后想特别侧重小学校教育,且专力对于日本语有根本与有系统的教授。”
对于在香港社会推广日本语教育和认同日本文化,日治政府可谓不遗余力。在规定学生必须系统学习日本语外,更把熟悉日本语作为政府部门和大规模商业机构招聘员工的条件之一。利用电台、报刊、书店,甚至在工厂里,极力普及日本语。在日方的积极鼓励下,众多日语讲习所应时而生。与此相应,师资训练也仅限于建立“日本语教员养成所”以及“教员讲习班”,目的在于培训各学校教授日语的教师。日语讲习所主要着重日语会话训练,其同学校系统教育相配合,成为日语社会推广的重要机构。至1943年3月,全港已办有日语讲习所达41所,从这些日语讲习所毕业的学生达9000余人。
在“东亚学院”,规定每周32小时的学习时间中,高等科必须学习日语22小时,普通科学习16小时。“修身公民”科,更重东洋精神、日本事情、日本道德礼法等。其目的正如当时东亚学院院长所称:“为使对于香港占领地总督部总管辖地区内居住之中国青年,以东洋精神为原则,日本道德为基础,实行师范教育,而亦同时实施事务教育,目的即养成中国人成为真正东亚中国人,奉行日本一德一体亲善友好提携之实现,使共同向大东亚共荣建设之途迈进……该院所有教授科目,一切均采用纯正之日本语为教授前提,故以把握正大之道理,为中国青年一切学问之根柢,唤起大东亚民族自觉,同时确立大东亚战争必胜思想之根据及坚忍不拔之信念,此即东亚学院教育之第一要义。”
如此,日本语和日本文化的教育,从学校教育至社会教育、正规教育至非正规教育,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现殖民文化教育的体系。力图以此收制香港社会,推行教育日本化,灌输日本的观念、文化思想和价值取向,以达到统制目的及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意图。
在其它社会文化政策上,占领当局也采取日化和以华制华的政策。改官方语言为日语,港九主要街道改为日名,提倡过日本的节日,甚至侵占中国的事变被作为庆祝事件。成立日方监控下的华人团体,来指导、监察香港社会的运行。鼓励赛马、过中国节日以及反鸦片,制造华人对英人的仇恨,以巩固所谓“东亚共荣”的日本军国主义之政治文化本质。
与之相比,英国殖民者在战前也立英语为官方语言,在教育上也鼓励办中文学校,但重心依然是体现殖民文化教育政策的官立学校和津贴学校,中文教育的骤兴乃是战争的原因。但是,毕竟英日两国的政治文化背景有着历史的区别,英国的宪政政制和日本战时的军政统治有着很大的差别,这决定着殖民地教育与军事之间的关系。战前,香港的殖民政体与英国本土的政体一样,也是三权分立。其司法独立,另有行政局,其议员分为官守和非官守。还有立法局作为制定法律的机构,议员也分官守和非官守。其中,华人在行政局一名,立法局三名,人称“华人代表”,都是非官守。港督除了是最高民政长官外,还是军事最高统帅,但基本上属于宪政文官政治的沿用。日本在香港的战时政体,其以占领地总督为最高长官,其下由总务长官和宪兵队长统管民治部、财务部、交通部和报道部。总督由军人担任,基本形成了一个军政府的架构,与战时军事的关系甚为密切,并直接关系到教育的管制。
在教育政策推行的背后,英国殖民者在香港实行的是一种殖民地体制的延伸及转化,基本是通过“隔离式的官僚政治”,透过政府和社会的分离来避免政治。其以“行政吸纳政治”,即透过吸收社会精英和建立政治与社会精英的共识,而消灭社会政治化的种子。由于只有少数社会精英能够晋身于决策阶层,因而仍然不存在政治与社会精英共治的现象。
能够佐证这一现象的如在港英政府时代,不但香港被割让给英国的历史不会在中小学课程中提及,在小学社会科涉及中国历史部分于抗日战争也只字不提,即使在中学的中国历史科中相关内容也多为简单而空疏。一般官立和津贴学校的抗战史教学,只重时空、事件、人物等交代,流于陈述,立场模糊。教学多持价值中立,只是引导评论而已。在教育政策上,表现为刻意淡化民族意识、冲淡民族情绪的殖民主义精神。
总而言之,英国在香港的殖民政府以一个强有力的官僚行政系统去吸纳政治,在二战前后长期地维持着一个反政治、反参与的意识形态和非政治化的社会,去达到殖民统治合法化的目的。这与日本在军国主义的意识下,政治上推行皇民化,也有着明显的区别。因此,在殖民教育实施上呈现出宗主国文化强权输入和在殖民地本土转化的不同特征。
尽管存在殖民统治及其文化教育政策上的差异,殖民主义文化的本质,即以宗主国的价值观念及意识形态,取代被统治者本身的价值观念及意识形态,仍然具有一致性。只不过在殖民文化教育的表现形式上,英国的强权是内隐的,而日本的强权则是外显的。
日本占领香港的3年零8个月,在香港沦为殖民地的150余年的历史中,虽然只是一个相对短暂的时期,但由于战争以及日本殖民的原因,致使香港教育如同社会其它方面一样,经历了一个最为艰难的历史时期。尽管当时的日治政府并不完全扼杀教育,但青少年未能得到正确和全面的知识。加上学校数量急剧下降,经济的衰落,一般平民子女无法承受教育所需费用,导致产生更多的失学者。
比较英日两国在香港的殖民政策及其教育实行,可以使我们更加认识殖民文化教育带给香港社会文化和教育的历史缺损,认清殖民文化教育的真实面目。然而,本文的研究目的不仅仅在于此,更在于希望能够通过重温这段不该忘却的历史,以使之永远不再重演。
标签:香港教育论文; 香港论文; 英国政治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论文; 殖民扩张论文; 日语学习论文; 日语论文; 军事历史论文; 工业革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