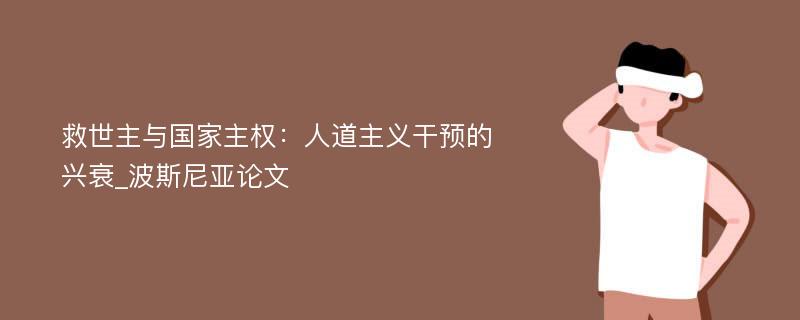
救世主与国家主权:人道主义干预的兴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道主义论文,兴衰论文,救世主论文,国家主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1年11月9日,乔治·布什(George W.Bush)创设了一个新的公众假日——世界自由日。那种认为美国能够,或者应该这样做的想法表露了华盛顿某种贯穿于冷战时期的思维定势。但在柏林墙倒塌之后,他们拉起人道主义这面旗帜,理直气壮地鄙视那些想让美国做好准备的懦夫和怀疑论者。
索马里、波斯尼亚、卢旺达和科索沃,全都是人道主义干涉分子欣然接受的危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漠视它们的独特性,将它们看作是一种单一现象——冷战后政权道德沦丧和极端暴力活动的一部分。他们呼吁使用武力——呼吁开战(尽管他们避免称之为战争)——如果这是他们为防止大规模暴力行为所采取的措施的话。虽然他们一般都希望这种动武能获得联合国的批准和认可,但他们往往准备好敦促美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带头,如有必要就单干。
然而,即使在世界自由日被宣告设立之时,在何时以及如何依据敌对程度激发同情上仍遇到了各种困难,这已使某些立场自由的鹰派人士停下来进行思考。对伊拉克的入侵分裂了他们。在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活动期间,他们当中有几位为奥巴马阵营所吸引,这不令人感到意外。然而,随着奥巴马总统逐渐减少右翼辞令及其前任的各项民主倡议,他也在划定其影响力的适度范围。一个务实的新时代似乎正在形成之中,而人道主义干预这一概念,要是没有死亡的话,也濒临死亡了。
在外交方面担负道义领导的代价是什么呢?认为生活在自由中的人应该采取行动来保护运气差的其他人,并断言伦理价值和人类团结在国际事务中占据着首要地位,这种见解是一个崇高但又很复杂的理想。国际准则也没有太多的帮助:例如,在宪章的不同要点上,联合国对于人权这种想法以及对于主权国家免受内政于预表现出了自相矛盾的姿态。虽然这是一个声称代表人类的组织,但联合国也是由各个成员国组成的一个联盟,它对于加盟的国家并未设置任何意识形态上的门槛。那么,在人道主义干预的年代里,联合国遭遇到了此前从未有过的界定自身的挑战,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恰恰是因为联合国在实践中缺乏驱动人道主义干预的这些理想,这明显也是一个美国的故事,一个专家学者和党派政治的故事,其中,左翼人士试图从里根的共和党政府以及新保守主义者那里夺取外交政策中的道德制高点。而在幕后,随着各个大学试图重新获得已输给了华盛顿各智库的某些政策影响力,它也是一个制度和智力较量的故事。但是,甚至在常春藤联盟各个公共政策学院率先推进这种新威尔逊主义之时,这种信条自身的各种内部矛盾却出现了。难道为他人做善事的同时也意味着为自己做善事吗?要是它确实意味着如此或者并不意味着如此,难道就应该更加担心吗?
大约10年前,在波斯尼亚和卢旺达、塞拉利昂和科索沃,当时人道主义干预的呼声在各种社论专栏和脱口秀节目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新自由国际主义的基础正在形成之中。通过将价值驱逐出国际关系这种顽固对话,一些学者想象出一种新的自由外交政策,并驳斥了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以及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的现实主义。但对于里根加诸于共和党的价值理念,包括对美国力量的崇拜,以及对独裁者的容忍,这些学者也予以了激烈的抨击。
这些自由派人士相信,所需要的是一种不同的、更为真实和彻底的言论。他们谈到人权,但是却不理会里根执政时期右翼政权的辩解。他们强烈反对里根政府重新恢复美国对国际法及国际事务中新规范的承诺。他们的指路明灯既不是修昔底德(Thucydides),也不是霍布斯(Hobbes),也不是冷酷的流亡的德国人——德国人受制于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后者塑造了冷战时代众多美国学生的思维——而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和康德(Kant)。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些开创性学术文章——对左翼和右翼都有影响——提供了一个起点:在这些文章中,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认为,民主政体天生就是爱好和平的。这种令人满足的含义是,如果现有的民主政体联合起来,并帮助世界其他地区实现民主化,那么美国的安全和国际和平都将会得以实现。
这一信息因欧洲的各种事件而得以强化。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鼓舞了共和党人的观点,即自由可能借助美国的武力威胁而得以扩展。但它也鼓励了自由派民主党人,这些人指望欧洲结盟,实现和平并迅速扩展至东欧,以此作为民主如何通过法治、市场扩展以及适合的国际机构而可能得以传播的一个模式。
20世纪90年代初是振兴那些机构的决定性时刻,似乎地位注定上升的不仅仅是欧盟。联合国秘书长欢呼,冷战的结束是使得集体安全成为现实、联合国重返中心舞台以及很好兑现承诺的一次良机。
然而,对欧洲主义者和联合国来说,失望近在咫尺。前南斯拉夫战争于1991年爆发,而次年发生的波斯尼亚战争对布鲁塞尔的自负构成了一个关键性的时刻。欧洲共同体及其监视机构——在当地被称为冰淇淋人——是没有权力的。但是,在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Ghali)及其副手明石康(Yasushi Akashi)领导时期,联合国要比没有权力更可怜。它通过对所有各方实施武器禁运的方式来阻止波斯尼亚人捍卫自身,并阻止接纳塞尔维亚人的所有建议。1992年春夏,随着有关大屠杀以及集中营的各种报道出现,大西洋两边开始摆出了实施干预的理由。
联合国在波斯尼亚的失败,使得两年后卢旺达的情况变得更加恶化,从而遭致了批评者的抨击。其中就包括美国的萨曼莎·鲍威尔(Samantha Power)和戴维·里夫(David Rieff),以及英国的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如同在大屠杀的教训中成长起来的其他人一样,他们背负着这一时刻的历史包袱,背负着面对种族灭绝采取行动的需要。并非巧合的是,无论是鲍威尔还是伊格纳季耶夫,都对波兰犹太学者拉菲尔·莱姆金(Raphael Lemkin)的著作产生了兴趣,后者发明了“种族灭绝”这个词语。
“决不重演”是一种令人敬佩的决心。但是,正如一些评论家在联合国成立后不久就指出的,即使联合国在纳粹时代就已存在,它也无干预德国内政的任何法律依据。一代人避免在大屠杀中相互勾结的这种急切决心,跟联合国的自身结构发生了碰撞。由于没有军队,受制于联合国安理会各成员国相互冲突的看法,以及不论在什么情况之下都未做好针对国家暴力活动作出快速反应的准备,联合国因此辜负了加利对其所寄予的厚望。
通过将理由强加给各个大国以及赢得公共舆论,干涉主义者用这种方式来设法克服这种体制上的惰性。但干预出现之时,他们并非是政策最终变化的主要推动者。北约1995年终结波黑战争的干预,是由英国和法国军事指挥官和政治家带头的,出于显然过时的原因——保护美、英、法的威信免受拉多万·卡拉季奇(Radovan Karadzic)准军事部队的羞辱。
可是,干预主义者的理想主义自有其用途,大西洋两岸的高官正在寻找一个冷战后的身份认同,而这些干预主义者则提供了一种身份认同。西方的军队可以被重新贴上“人类救世主”的标签——阻止种族清洗并让这些国家站稳脚跟,让难民重返各自的家园。
1999年围绕着科索沃的这场斗争证明,新的干涉主义已渗入了权力走廊。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是与前任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极为不同的一类人;她汲取了波斯尼亚和大屠杀的教训,实在太好了。作为美国道义领导地位的一位厚脸皮倡导者,她经常指责科林·鲍成尔(Colin Powell)将军不愿意参与其中,并在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那里找到了一位坚定盟友,这位来自格莱斯顿的人为信仰和原则而斗争的狂热,跟他的前任约翰·梅杰(John Major)的那种谨慎形成了对比。
当时,知识分子为在科索沃与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的较量挖空心思寻找理由,而公开的详述都比不上伊格纳季耶夫。波斯尼亚事件之后,他曾若有所思地说,当代知识分子的任务将是捍卫“普世众生不受与部落、民族和种族有关联的暴力和封锁”。他似乎有点缺乏自信,呼吁将捍卫西方的普世主义作为部落主义的一项替代方案。他并没有以人道主义理由阻止西方干预海外的权利;他的衡量标准是侵犯人权有否威胁到国际和平。
人权与国家安全的合并成为干预倡导者的一个特征。干涉主义者变得不太批评政府了,而且更习惯于向决策者提供其所需的那些论点。
2002年,担心人权的时刻终告结束,这场运动因小布什总统任期中更强有力的反恐重点而被撇到了一旁,伊格纳季耶夫坚持认为,为了让这场“运动”避开不相关性,它就必须公开捍卫基本权利并促进国家安全和国际稳定。它都是关乎帮助“普通人”建立强大“市民社会”的事情。
撇开现实主义者这种显而易见的批判,至少存在着两个问题。一个是被左翼兴高采烈地提到的,是美国以及参与人道主义对话的其他政府的可疑诚意。虽然令人惊讶的是,鲜有评论员反对“同情心政治”(politics of compassion)这种想法,但标准的左翼批判仍坚持合法领导的必要性,要么指望联合国,要么指望已被普遍接受的某种国际法。人们从来就未弄清楚过,各国为何突然之间签约加入在国际法方面一项新的、强有力的权力体制。
至少同样令人担心的是这样一种想法,即知识分子寄希望于的这些“普通人”可能并不如想象般的那样存在着。他们真是天生的民主党人吗?也有人认为,南斯拉夫陷入动荡是大规模民族主义和分裂运动遭遇政治上挫败的产物。但也有人说,卡拉季奇和弗拉尼奥·图季曼(Franjo Tudman)不是暴君,而是原来国家体制崩溃及随后出现的民主化的受益者。很快,有待专制制度诞生“市民社会”的这种思想在自身矛盾重压之下开始瓦解了。
正如《自由之战:人道主义干预的起源》(Freedom's Battle:The Origins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一书作者加里·巴斯(Gary Bass)指出的,传播民主可能不会使世界变得更加安宁。或许重要的是这些新近正在民主化之中的政体能否具备建立这些政治制度的成熟性。人们不必为了质疑一种“西方的模式”——不管它看起来像什么——是否可以被输出,就断定答案必然是欣然接受独裁盟友。
对许多人来说,对伊拉克的干预太为过分。在波斯尼亚,有人通过呼吁巧妙地融合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的前提这种方式来鞭挞西方的无所作为:因为“国际社会”不仅纵容大屠杀,而且还阻止这些受害者捍卫他们自身,而后者已经获得了国际认同,从而加速了波斯尼亚边界一次不可避免的重新调整。
那些对奥马尔斯卡(Omarska)集中营和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大屠杀的报道感到震惊的人士,因而加入到了支持西方干预的争论里。而事实上,正如已经看到的,正是这种非常现实的关注,塞尔维亚人羞辱了北约并使得大西洋联盟威信扫地,最终引发了1995年的那次干预。
无论是对人道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来说,科索沃的情况则更加模糊了。干预是先发制人的,旨在预防成为另一个波斯尼亚。而困难在于,塞尔维亚人强烈要求拥有主权而不是省份的所有权。但是,伊拉克却将人道主义干涉主义者一分为二。虽然有些人,如伊格纳季耶夫和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最初以人权理由支持入侵行动,但其他人则坚持认为,呼吁人道主义同情是不够的,也是华而不实的。这不是美国在寻找自己的灵魂,而是在被记者马克·丹纳(Mark Danner)称之为“永远的战争”中丧失了灵魂。对丹纳来说,阿富汗,尽管有其必然性——他在2001年10月写道:美国“除了军事回应别无选择”——是在美国所支持的选择上一大变化的开始。对伊战争是一次帝国的十字军东征。随着小布什政府野心的规模变得清晰,因此像丹纳这样的评论员重归乔治·凯南和现实主义者的审慎智慧上。这重新回到了1947年。
伊拉克战争爆发一年之后,如同许多人一样,伊格纳季耶夫本人也改变了主意。他表示,也许干预主义者的信条总是取决于一种令人无法接受的异想天开。萨曼莎·鲍威尔曾是他在哈佛大学时的同事,由于这次入侵事件而与他分道扬镳。小布什政府对联合国的蔑视成为原因的一部分。但对萨曼莎·鲍威尔来说,困难则是在于,解释为何一个由各国组成的组织在恢复主权方面应该比美国更有效。出于担心在伊拉克惨败后出现“人权领导权”真空,萨曼莎·鲍威尔提倡建立一个“相关者联盟”以保留火种。这样一支力量如何不同于小布什的“意愿联盟”,这一点并不清楚。
当然,人道主义干预这种想法并非是20世纪后期的一项发明。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在一个多世纪前对埃及的入侵,就具备了这种思想的一切特征,而且还可以追溯得更远。这种思想在20世纪90年代的重现,是全球事务自由主义思维独特形式在西方的再度盛行。如果自由价值是仅有的真正价值,那么就应该调动西方的力量和声望来推广它。而且不仅仅是为了推广它,更是为了将忍受艰难的人类从另一个西方的发明——国家主权这个想法的过度行为中拯救出来。随着美国在1989年之后地位的上升——以及一种浸透大屠杀各种恐怖行为的公共文化和面对邪恶时的无所作为——这种诱惑已将干预提升至一般的原则。正如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2008年所写的,通过大规模侵犯暴力行为,许多国家错失了使它们有权宣称拥有主权的这种无罪假定。这种世界性良知肯定胜过独裁者的自治权。
但就是在这里,这种知识分子的见解暴露了弱点。这并不是说,设法帮助他人或者有时为了帮助他人而动用武力是错误的。但是,要是没有动用这些手段的意愿,干预必定会导致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失败,并败坏自己的名声。正如1999年戴维·里夫在科索沃战争之后对干涉主义命运进行深思之后所说的:“我们的道义抱负已远远超过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甚或认知上的手段。没有任何捷径。”正如他所说,要么选择帝国主义要么选择野蛮行为,他(勉强地)和他人(不太勉强地)将他们自身置于行动的一边,而极少仔细考虑甚至最强大的国家可采取的手段也是那么的有限。
在索马里的惨败就是对这种情况的一个预警。随后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后果,使得我们承担起一种旷日持久的国家建设责任。推翻独裁者可能制止最严重的暴行。但希望他们垮台的西方舆论在这些年里却变得苍白了,为了从头开始建设民主制度,已耗费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且牺牲了许多(西方人的)生命。早在奥巴马当选之前,因伊拉克和阿富汗而造成的军事资源消耗,就足以表明应该警惕各类帝国事业,更不用提波斯尼亚和科索沃那些新机构的脆弱性。
震惊之下,一些评论员谴责了这种内向性;例如,丹尼尔·戈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最近对国际法的破产深为痛惜,并呼吁对各种令人困惑的人类之敌采取行动。但变乖了的美国新总统在2009年9月公开宣布,我们的民主概念太狭窄了,并宣布“每个国家将走上一条源自于自身民族文化的道路”。
这种新现实主义是值得欢迎的,但它也带有自身的威胁,尤其是一条普遍原则将被另一条普遍原则取代这样的风险。是否有一种在不惊醒西方帝国主义幽灵的同时为这些国家的受害者提供援助的方式呢?能在不发起民主全球远征情况下来支持民主价值观吗?也许吧。波斯尼亚、科索沃和伊拉克——选取这三个突出的例子——在重要性方面是各不相同。波斯尼亚有一个寻求干预、获得国际承认的政府,或者至少解除了武器禁运,因此,这种权利——主权的困境并不适用。相比之下,科索沃的情况则因宪法地位模糊不清以及缺乏普遍合法性而被搅浑了,更何况一场游击战争已经在进行之中。实际上,北约选择了支持反叛分子,而不是支持贝尔格莱德这个异己但又合法的政权。伊拉克是从波斯尼亚发出的光谱的另一端:在那里,干预意味着入侵另一个国家,一个获得国际公认的政权在该国已牢固确立起来。因此科索沃和伊拉克通过波斯尼亚所没有的方式对国际边界稳定性提出了质疑。而在伊拉克的例子里,则是对主权自身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对那些更为热心的干涉主义者来说,当将推翻独裁政权以及阻止大规模屠杀的机会搁在一边时,这类考虑代表了纯粹的教条主义。但是,他们中的深思熟虑者则已认识到,领导者对待本国人民的这种方式,并非国际事务中很重要的仅有问题。相反,如果过去这个世纪历史显示一切的话,那就是,清晰的法律规范以及普遍确保国际稳定也有助于人类福利事业。更不用说毁灭制度机构远比建立它们更加容易。因此自由主义对各种制度机构(国内的和国际的)特有的漠视受到了质疑。总之,人道主义干预时代的终结,也许可以被看作是西方力量逐渐减弱的一个迹象。但是,更积极地将它看作是国际关系中一种晚到的新的成熟性,这则是有可能的。
原文标题:Saviors & Sovereigns:The Rise and Fall of Humanitarian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