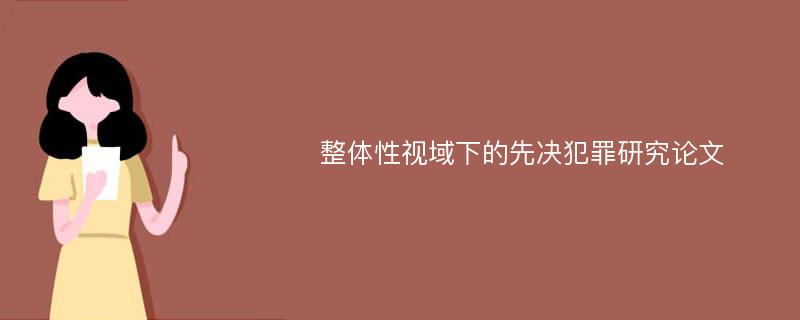
整体性视域下的先决犯罪研究*
黄陈辰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北京 100088)
摘 要: 先决犯罪是指由刑法所设置的,作为本罪成立之必要条件的犯罪种类,其具有判断前置性、构罪必要性、设置法定性的特征。帮助行为正犯化作为一种特殊的立法模式,其与先决犯罪存在与否不具有必然联系。在司法适用中:先决犯罪的认定只需证明犯罪事实存在即可,无需经过审判;根据双层犯罪概念,先决犯罪既包括不法层面的犯罪,又包括不法有责层面的犯罪;本罪构成要件要素对先决犯罪的规定在形式上主要有三种模式,即仅规定“犯罪”一词型、描述特定行为型、列明特定犯罪种类型,各模式中先决犯罪的范围不尽相同,应分别予以认定。在立法改进上:相关构成要件要素的语词表述应更加准确,以消除理解上的分歧;对先决犯罪的指向应更加具体,尽量采取目标明确的规定模式。
关键词: 整体性视域;先决犯罪;司法困境及解决;立法完善
在我国《刑法》分则中,一部分犯罪的成立以他人的行为[注] 虽然在赃物犯罪,例如洗钱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中,对于本罪的行为人能否是上游犯罪行为人的问题还存在争议,但目前学界主流观点采取的是否定说,即认为本罪的行为人不包括上游犯罪人本身,故此处表述为本罪的成立以“他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为前提。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793. 构成犯罪为前提,例如《刑法》第191条规定的“洗钱罪”的成立必须以他人实施毒品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等七类特殊的犯罪为前提,又如《刑法》第311条规定的“拒绝提供间谍犯罪、恐怖主义犯罪、极端主义犯罪证据罪”必须建立在他人实施间谍犯罪或者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的基础之上。由此可以看出,在这一类犯罪中实则存在两种意义上的“犯罪”,其一是刑法分则条文本身所规定的犯罪,其二是作为前述犯罪成立条件的犯罪,因为《刑法》在相关法条中规定的是前者,故本文称之为“本罪”,而又因后者具有前置性与先决性,是本罪成立的前提条件,故本文称之为“先决犯罪”。目前学界对刑法分则各罪中先决犯罪的分别研究较多,但整体性考察却付之阙如、鲜有论及,这种化整为零的研究思路确实能够对各部分有所认识,但通常很难得出全面、深刻的见解[注] [美]丹尼斯·舍伍德.系统思考[M].邱昭良,刘昕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4. ,正因如此,对先决犯罪的理解在实践中呈现出极其混乱的局面,其实际适用亦缺乏体系性与一致性,故本文欲从整体性视域出发,对先决犯罪的概念、认定、适用困境及完善思路进行研究,以期为填补这一学术空白抛砖引玉、奠定基础。
与正常组相比,模型组IL-17、RORrt蛋白表达升高,IL-10、Foxp3蛋白表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模型组相比,阳性组、黄芩茎叶黄酮组IL-17、RORrt蛋白表达降低,IL-10、Foxp3蛋白表达升高,具有剂量依赖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图4,表5。
一、先决犯罪概述
(一)先决犯罪的概念
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或特有属性的思维形式,是我们认识、讨论和理解相关现象的尺度与基础[注] 朱霖,陆劲松.形式逻辑基础[M].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17.23. 。因此要研究先决犯罪则应先对其概念进行分析与界定,在对其概念有了明确的认识之后再探究其具体理解与适用的问题。要明确一个概念,既可以从内涵角度着手,也可以从外延角度着手,本文拟通过分析包含先决犯罪的法律条文来归纳总结出先决犯罪的相关属性,再依据这些属性揭示出其内涵,进而使先决犯罪的概念得以明确。在我国《刑法》分则条文中,具有先决犯罪的罪名除上述洗钱罪与拒绝提供间谍犯罪、恐怖主义犯罪、极端主义犯罪证据罪外,还包括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包庇、窝藏罪等,通过对这些罪名及相关法条的分析可以总结出先决犯罪具有以下属性:
实验二:间歇采样重复转发干扰的采样周期Ts=3 μs,采样间隔τ=0.5 μs,干信比取40 dB,所得目标信息如表3所示,仿真结果如图4所示。
第一,判断的前置性。判断的前置性体现了先决犯罪之“先”,即在判断行为人之行为是否成立本罪时,应首先判断先决犯罪的成立与否,若先决犯罪成立,则得以继续判断行为人之行为是否符合其他构成要件要素及违法性、有责性阶层的要求;若先决犯罪不成立,则行为人之行为因不具备本罪相关构成要件要素而不构成本罪,不必再进行其他方面的判断。例如在涉及拒绝提供间谍犯罪、恐怖主义犯罪、极端主义犯罪证据罪的案件当中,首先应判断他人是否实施了间谍犯罪、恐怖主义犯罪、极端主义犯罪,若他人仅实施一般的违法行为而并未构成上述犯罪,则拒不提供证据的行为不构成拒绝提供间谍犯罪、恐怖主义犯罪、极端主义犯罪证据罪,只有在他人实施了间谍犯罪、恐怖主义犯罪或极端主义犯罪的情况下才有继续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符合“明知”“情节严重”等构成要件的必要。由此可见,先决犯罪成立与否的判断先置于本罪的判断之前,故先决犯罪具有判断的前置性。
第二,构罪的必要性。构罪的必要性体现了先决犯罪之“决”,即先决犯罪是本罪成立的必要条件,其存在与否直接决定了本罪能否构成。先决犯罪这个属性的最大作用在于将其与另一特殊情形区分开来,即某一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中既规定有“犯罪”又规定有“违法”,无论他人的行为构成“犯罪”抑或是“违法”,本罪均能够成立,例如在《刑法》第345条第3款规定的“非法收购、运输盗伐、滥伐的林木罪”中,犯罪对象为“盗伐、滥伐的林木”,据此来看似乎本罪的成立必须以他人的行为构成盗伐林木罪或者滥伐林木罪为前提,但根据《刑法》第345条第1、2款的规定,盗伐林木罪与滥伐林木罪的成立均需被砍伐的林木达到“数额较大”的入罪标准,因此即使他人的行为不构成盗伐林木罪或滥伐林木罪而只是一般的违法行为,行为人若实施了非法收购、运输的行为则在满足“情节严重”的情况下亦成立本罪[注] 根据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第6条、第11条的规定,盗伐林木“数额较大”以2至5立方米或者幼树100至200株为起点,滥伐林木“数额较大”以10至20立方米或者幼树500至1000株为起点,非法收购盗伐、滥伐的林木罪“情节严重”以20立方米或者幼树1000株为起点。因此若他人盗伐、滥伐林木的数量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构成盗伐林木罪或滥伐林木罪,行为人非法收购与运输的行为只要满足“情节严重”的条件,自然构成本罪;但即使他人盗伐、滥伐的数量未达到盗伐林木罪与滥伐林木罪的入罪标准,只要行为人非法收购、运输的总数达到“情节严重”,亦构成本罪。例如:甲从乙、丙、丁三人处各收购其滥伐的林木8立方米,乙、丙、丁三人因滥伐林木量未达到入罪标准,因此均不构成滥伐林木罪,但甲总共非法收购的滥伐林木数量为24立方米,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构成非法收购滥伐的林木罪。 ,在此种情形中,他人实施盗伐林木罪或滥伐林木罪并非行为人构成非法收购、运输盗伐、滥伐的林木罪的必要条件,因此其不属于该罪的先决犯罪。
“互联网+”背景下启迪桑德对我国环保服务企业的发展……………………………………………………陈 卓 房 进(9.82)
双方对峙了一会儿,一只冥河盗龙突然从侧面冲了上来,看来它是想冒险打破僵局。反应迅速的肿头龙注意到了冥河盗龙的动作,它马上低着头冲了过来。眼看双方就要撞到一起了,这时,冥河盗龙一下子跳了起来,后腿努力向前伸出,想用脚上锋利的镰刀爪刺伤肿头龙。只听“咚”的一声闷响,紧接着发出一阵尖厉的叫声。原来冥河盗龙不仅没有伤到肿头龙,自己反而被撞了出去,重重地摔落在树丛中。由于强大的惯性作用,肿头龙又向前跑了好几步才停下来,它喘着粗气,身上的肌肉仍然紧绷着,随时准备撞击下一个目标。看到自己的同伴被肿头龙撞飞,就连骨头断裂的声音都清晰可辨,其他冥河盗龙退缩了,它们可不打算赔上自己的性命,一个个灰溜溜地逃走了。
通过对上述先决犯罪相关属性、特征的归纳与分析,本文将先决犯罪定义为:由刑法所设置的,作为本罪成立之必要条件的犯罪种类。
(二)先决犯罪的认定
1.先决犯罪的认定标准
前述对先决犯罪属性的归纳与概念的界定已经足以为其划定出一条较为清晰的认定边界,但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如此,在对其进行具体判断的过程中仍存在着一些相对模糊的地带,即帮助行为正犯化与先决犯罪间的关系问题,需要予以明确与澄清。
一般认为,帮助行为正犯化是指将共同犯罪形态中其他犯罪的帮助行为提升为实行行为,使其独立成罪的一种立法模式[注] 张小虎.犯罪实行行为之解析[J].政治与法律,2007,(2):99. ,因此易产生一种观点,即认为凡是属于帮助行为正犯化情形的罪名,其成立均需要以原本共同犯罪中正犯的存在为前提,而该正犯所构成的犯罪即为本罪的先决犯罪,意即属于帮助行为正犯化情形的罪名均包含先决犯罪。但需要注意的是,上述观点是对帮助行为正犯化的一种误解,实际上帮助行为正犯化包含两个层次的含义,“广义上来讲,帮助行为的正犯化泛指刑法分则中所有帮助行为的入罪化,即对于违法、犯罪行为的帮助行为,通过新增罪名或者罪名修正的形式予以入罪化的一种立法模式;”[注] 于冲.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类型研究与入罪化思路[J].政法论坛,2016,(4):165. 而从狭义上来理解,帮助行为正犯化指的是一般意义上帮助犯的正犯化,即上述“将共同犯罪形态中的其他犯罪的帮助行为提升为实行行为”的情形。广义上的帮助行为正犯化因包括“对违法行为的帮助”[注] 例如《刑法》第354条、第359条规定的“容留他人吸毒罪”与“容留卖淫罪”,吸毒与卖淫本身不构成犯罪,而只是一般的违法行为,但容留他人吸毒与卖淫的行为之社会危害性则达到了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因此刑法分则对该种以容留形式为他人提供帮助的行为予以正犯化,将其规定为独立的犯罪。 ,故与先决犯罪间没有必然联系。至于狭义的帮助行为正犯化,即帮助犯的正犯化,可以具体分为两种情形:第一,帮助犯的绝对正犯化,即刑法条文将帮助犯提升为正犯,与其他正犯没有任何区别,其成立不以之前共同犯罪形态中的实行行为存在为前提;第二,帮助犯的相对正犯化,即对于某一罪名而言,正犯不存在时,帮助行为能否被认定为实行行为不可一概而论,而应根据其独立危害性的大小以及对正犯的依赖性程度进行具体判断,例如《刑法》第358条第4款规定的“协助组织卖淫罪”,若他人的行为构成组织卖淫罪,那么协助的行为固然成立本罪,但若他人的行为不构成组织卖淫罪,协助的行为仅在其本身严重侵害了社会管理秩序且具有独立可罚性时,仍然可以成立本罪[注] 张明楷.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J].政治与法律,2016,(2):4-5. 。而无论是帮助犯的绝对正犯化还是相对正犯化,刑法之所以对其进行正犯化处理,正是因为帮助行为独立危害性与可罚性的提升以及其对正犯依赖性的减弱,故正犯化后的犯罪为独立的犯罪,其成立并不必须以正犯的存在为前提。
泰森突然恼怒地骂了一句:“妈个比,找的都是什么人啊!”我觉得他不是在骂我,就又接着说:“咱们出去简单吃一点吧,你们要是不饿,那我出去了。”
2.包含先决犯罪的条文梳理
在我国《刑法》分则中,包含有先决犯罪的条文主要有:
第一,如前所述,虽然先决犯罪与本罪关系紧密,但对二者应分别予以评价,不可混为一谈。在对本罪的判断中,整个刑事诉讼程序是围绕本罪展开的,先决犯罪仅作为一类构成要件要素而存在,故此时只需证明他人的行为引起了法益侵害的结果且符合客观犯罪要件即可,至于其是否应受刑罚处罚则不影响本罪的成立[注] 黎宏.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性质及其适用[J].法律适用,2017,(21):37. 。
《刑法》第311条规定的拒绝提供间谍犯罪、恐怖主义犯罪、极端主义犯罪证据罪。本罪的罪状为“明知他人有间谍犯罪或者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行为,在司法机关向其调查有关情况、收集有关证据时,拒绝提供,情节严重的……”因此行为人的行为要构成拒绝提供间谍犯罪、恐怖主义犯罪、极端主义犯罪证据罪,必须以他人行为构成间谍犯罪或者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为前提,上述三类犯罪即为本罪的先决犯罪。
《刑法》第191条规定的洗钱罪、第312条规定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第349条规定的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此三类犯罪的犯罪对象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或毒品犯罪中的“毒品”,故其成立均以他人构成相关犯罪为前提,而这些相关犯罪即为此三类犯罪的先决犯罪。需要注意的是,有部分学者认为上述三种犯罪中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可以理解为包括未达到相关数额标准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注] 黎宏.刑法学各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412. ,因此行为人要构成上述犯罪无须以他人实施相关上游犯罪为前提,故上述三种犯罪中并不包括先决犯罪。但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仍主张“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不包括“违法所得及其收益”,例如张明楷教授认为,若上游行为只是违法行为,那么掩饰、隐瞒该行为所产生的所得及其收益则没有妨害刑事司法活动,进而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注] 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1100. ,马克昌教授认为《刑法修正案(六)》取消了1997年《刑法》规定的“洗钱罪”中的“违法”字样即已表明了“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不包括“违法所得及其收益”的立场[注] 马克昌.百罪通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273. ,王彦强博士认为在立法明文要求赃物犯罪的行为对象必须是“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且我国采取严格区分“犯罪与违法”二元制裁体系的情况下,主张“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包括“违法所得及其收益”的观点显然有超溢语义范围、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注] 王彦强.论上游犯罪罪量因素对赃物犯罪成立的影响[J].政治与法律,2017,(7):40. 。本文赞同学界主流观点,即“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不包括“违法所得及其收益”,据此可以推断出,行为人要构成上述赃物犯罪必须以他人实施相关上游犯罪为前提,故相关上游犯罪即为上述赃物犯罪的先决犯罪。
《刑法》第241条规定的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第416条规定的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前者的犯罪对象为“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后者的犯罪对象为“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由此可以推断出,行为人要构成上述犯罪必须以他人实施拐卖妇女、儿童罪为前提[注] 对于此处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中的“绑架”是指向《刑法》第240条第1款第(五)项中以绑架的形式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还是指向《刑法》第239条绑架罪中的绑架行为,在理论界尚有争议,本文赞同前者,相关理由将在下文中予以阐述。 ,若他人并未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罪,而仅实施前述民间送养行为或“放飞鸽”的行为,则行为人即使有所谓的收买行为或者不解救行为,也不构成上述犯罪。因此拐卖妇女、儿童罪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与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的先决犯罪。
《刑法》第310条规定的窝藏、包庇罪、第349条规定的包庇毒品分子罪、第355条规定的走私、贩卖毒品罪、第417条规定的帮助分子逃避处罚罪。窝藏、包庇罪的犯罪对象为“犯罪的人”,包庇毒品分子罪的包庇对象、走私、贩卖毒品罪中药品的接受对象以及帮助分子逃避处罚罪的帮助对象均为“犯罪分子”。由此可知,行为人要构成上述犯罪必须以他人实施犯罪进而属于“犯罪的人”或“犯罪分子”为前提,故上游犯罪为上述四罪的先决犯罪。但需要注意的是,窝藏、包庇罪中存在例外情况,即根据《刑法》第362条的规定,“旅馆业、饮食服务业、文化娱乐业、出租汽车业等单位的人员,在公安机关查处卖淫、嫖娼活动时,为违法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情节严重的,”以窝藏包庇罪论处,此处的“违法犯罪分子”既包括犯罪的人,也包括违法的人[注] 叶良芳.刑法分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310. ,因此即使他人仅实施一般违法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亦能够构成窝藏、包庇罪,故此类窝藏、包庇罪不包含先决犯罪,因而不属于本文的研究内容。
《刑法》第414条规定的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本罪的罪状为“对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负有追究责任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不履行法律规定的追究职责,情节严重的……”虽此处的“犯罪行为”描述的是行为主体的职责范围,但综合该罪罪名来看可知,本罪的犯罪对象为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故本罪的成立以他人实施制售伪劣商品犯罪,即《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一节规定的九个罪名为前提[注] 莫洪宪,余书金.“两法衔接”之渎职犯罪法律适用难点探析[J].江汉论坛,2017,(10):127. ,若他人并未实施制售伪劣商品的行为或虽制售伪劣商品而仅为一般违法行为,则行为人的行为不成立本罪,因此制售伪劣商品犯罪为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的先决犯罪。
3.不能推导出先决犯罪的几种特殊情形
但上述结论不利于对相关犯罪的打击与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因此本文认为,先决犯罪应指广义上的犯罪,即达到构成要件不法程度的行为,但其并不一定需要具有有责性,理由如下:
(1)构成要件中的“犯罪嫌疑人”不能推导出先决犯罪
(2)构成要件中的“违法犯罪”不能推导出先决犯罪
在某些犯罪的构成要件中规定有“犯罪嫌疑人”等内容,此处虽含有“犯罪”二字,但其只是在“犯罪嫌疑人”一词中的固定用法而已,并不单独表示犯罪,且犯罪嫌疑人仅指在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以前受到刑事追诉的人[注] 陈光中.刑事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74. ,其仅具有犯罪嫌疑而并不一定真正实施了犯罪,故由此不能推断出包含“犯罪嫌疑人”字样的犯罪必须以他人行为构成犯罪为前提。属于这种情形的罪名有:《刑法》第247条规定的刑讯逼供罪与暴力取证罪、第316条规定的脱逃罪与劫夺被押解人员罪、第400条规定的私放在押人员罪、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等。
某些罪名的构成要件中规定有“违法犯罪”的内容,其具体包括“违法犯罪行为”“违法犯罪活动”“违法犯罪信息”“违法犯罪分子”等,如前所述,这些构成要件要素虽规定了“犯罪”,但其同时亦包含“违法”,因此行为人要构成本罪并不必须以他人实施犯罪为前提,他人仅实施一般违法行为亦可,故构成要件中的“违法犯罪”不能推导出该犯罪包含有先决犯罪。属于这种情形的罪名有:《刑法》第285条第3款规定的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第294条第3款规定的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第287条之一规定的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第362条规定的包庇罪等。
报警显示界面可以实时显示采集到的信号并作分析和报警。图4在人手触摸光纤情况下上位机界面采集到的时域波形。
(3)其他规定有“犯罪”字样但不能推导出先决犯罪的情形
例如《刑法》第295条传授犯罪方法罪的罪状为“传授犯罪方法的……”此处的“犯罪方法”指的是犯罪的手段、经验及技能[注] 刘志伟,左坚卫.传授犯罪方法罪中若干问题探究[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2):88-89. ,其并不能推导出先决犯罪,即行为人的行为要构成本罪并不以他人实施犯罪为前提,只要行为人实施了传授的行为即可,至于被传授者是否掌握、接受了犯罪方法以及是否利用行为人所传授的犯罪方法实施犯罪均不影响本罪的成立。属于这种情形的罪名有:《刑法》第107条规定的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第287条之二规定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注]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规范属性在理论界尚有争议,本文采取目前的主流观点,即认为其属于帮助行为的正犯化,不以他人的行为构成相关网络犯罪为成立前提,因此其不包含先决犯罪。 等。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除上述构成要件中出现“犯罪”等字样的情形易与先决犯罪产生混淆外,其他某些犯罪中所规定的特殊要素也存在被误认的可能,在具体判断时需要仔细甄别。例如在《刑法》第167条规定的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与第406条规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中,“诈骗”要素极易被误认为行为人构成上述两种犯罪需以他人实施诈骗犯罪为前提,但仔细分析后可以发现,诈骗罪的基本构造是“行为人实施诈骗行为——对方陷入错误认识——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注] 黎宏.刑法学各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327. ,而根据上述两罪的罪状表述,其成立仅要求行为人因严重不负责任被诈骗,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或特别重大损失,而并不要求诈骗人因此获得财产,故上述两罪的成立并不以诈骗人构成诈骗罪为前提,因而“诈骗”要素不能推导出诈骗罪是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的先决犯罪。属于此类情形的还有《刑法》第345条第3款规定的非法收购、运输盗伐、滥伐的林木罪、第358条第4款规定的协助组织卖淫罪等。
二、先决犯罪的司法困境及解决
普通犯罪仅作为一种独立的犯罪存在,而先决犯罪的角色定位却具有双重性,其既有自己独立存在的意义,同时又是本罪成立的前提,这种身份上的二元性导致了其在司法适用中的复杂境遇以及对其理解的争议与分歧。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对先决犯罪的研究思路主要是在各罪中进行分别探讨,这种方式虽能够解决单一罪名中先决犯罪的理解问题,但由于没有全面统一的视角,故从总体上看仍缺乏体系性与一致性,因此应化零为整,从整体上对先决犯罪进行分析,以探求相应的解决之道,而这也正是本文的研究意义之所在。通过对各罪中有关先决犯罪的争议进行归纳与梳理,可知其在司法适用中主要存在以下三点困境,而本文也从此三个方面分别提出了解决的对策与建议。
(一)先决犯罪的认定是否必须经过裁判
本罪的成立以他人行为构成先决犯罪为前提,但对于先决犯罪的认定是否必须经过法院审判,即是否只有从裁判结果来看行为人的行为被定罪处罚才意味着其构成先决犯罪,则存在争议。部分学者认为先决犯罪与本罪在实体上形成共生关系,他人的行为只有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并经过法院审判才能被认定为构成先决犯罪,持此观点的学者所提出的主要理由是,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的明文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因此从符合程序正义的角度来说,在审判之前,不得认定他人的行为构成先决犯罪,否则有违无罪推定的原则,不利于他人权利的保障[注] 李炜,严妍.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司法实践若干疑难问题探析[J].福建警察学院学报,2010,(2):48-49. 。但从刑法学界对洗钱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窝藏、包庇罪中先决犯罪的研究来看,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只要有证据证明存在先决犯罪事实即可,至于其是否经过审判,则不影响本罪的成立[注] 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560. 。
本文赞同无须经过审判、只需证明犯罪事实存在的观点。主要理由如下:第一,实践中存在这样的情况,即本罪的行为人已经被抓获归案而先决犯罪人尚处于在逃状态,或者本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先决犯罪查处难度大、所需时间长、审判进度慢,因此从功利的角度而言,如果一律要求本罪必须等到先决犯罪审判完毕后才能处理,则既会导致对此类犯罪的打击不力,又有害于被害人相关权益的保护,毕竟迟来的正义非正义[注] 马克昌.百罪通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271. ;第二,赞同先决犯罪认定无须经过审判的观点并不违背无罪推定的原则,因为虽然先决犯罪与本罪之间具有密切联系,但其各有不同的犯罪构成,应对其进行独立评价,因此在本罪中,先决犯罪只是作为本罪的一个构成要件要素而存在,对其仅需要进行事实层面的判断即可,而不用将其纳入刑事诉讼程序中加以评判,故在本罪的认定中先决犯罪人也未被作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而加以追诉,因此不会对其产生不利的后果。概言之,仅对先决犯罪进行事实层面的判断不会剥夺先决犯罪人在程序上享有的无罪推定的权利,在本罪中认定先决犯罪事实的存在也不会直接得出先决犯罪人的行为构成犯罪的结论,要对其定罪处罚仍需将其置于刑事追诉程序之中予以判断,因而能够确保程序正义[注] 肖晚祥,苏敏华.上游犯罪行为人尚未定罪,如何认定洗钱罪[J].人民司法,2008,(2):76. ;第三,虽然存在本罪行为人被定罪后,先决犯罪人经过刑事诉讼程序被认定为无罪的情况,但可以通过相关的救济程序予以解决,此即效率与公平间的博弈与平衡,属于价值衡量的问题;第四,对于先决犯罪应该按照通俗的含义进行理解,而不是从规范意义上去评价,尤其是对于窝藏、包庇罪等妨害司法类犯罪而言,其社会危害性本身即在于对先决犯罪的侦查、起诉、审判等刑事司法活动的顺利进行产生干扰和妨害,使得先决犯罪无法查明,若对于本罪的成立又要求先决犯罪必须经过审判,那么则会导致循环论证、追诉效率低下、对相关犯罪打击不力的严重后果[注] 黎宏.刑法学各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412-413. ;第五,从法益侵害的角度来看,对于妨害司法类犯罪,只要他人具有犯罪嫌疑,司法机关就会展开侦查等一系列刑事诉讼活动,而若行为人实施窝藏、包庇或者洗钱、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等行为,同样会妨害司法活动的顺利进行,从而构成本罪,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行为人已经确定、案件事实清楚、司法机关不可能展开刑事侦查或其他司法活动的情况下,即使行为人实施所谓的窝藏、包庇或者洗钱、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等行为,也不妨害司法活动,进而不构成本罪[注] 例如甲嫖娼的事实清楚,公安机关不可能对此行为进行立案侦查,因此“窝藏”甲的行为不妨害司法活动,不构成窝藏罪。 ;第六,对于洗钱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等赃物犯罪而言,相关司法解释的内容也体现了先决犯罪的认定无需经过审判的观点,例如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赃物罪解释》)第4条第1款规定,“刑法第191条、第312条、第349条规定的犯罪,应当以上游犯罪事实成立为认定前提,上游犯罪尚未依法裁判,但查证属实的,不影响刑法第191条、第312条、第349条规定的犯罪的审判,”又如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解释》)第8条第1款规定,“认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以上游犯罪事实成立为前提,上游犯罪尚未依法裁判,但查证属实的,不影响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认定。”
同时应当看到,先决犯罪的认定无须经过审判、只需证明犯罪事实成立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充足的理由,在司法实践中也得到相关案例的支持,例如在《刑法修正案(六)》以及《反洗钱法》施行后全国法院审理的第一起洗钱罪案例中,虽然实施上游诈骗犯罪的犯罪人“阿元”尚未被抓捕归案,但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在依据相关证据证明存在信用卡诈骗犯罪事实的情况下,依法认定本案四名被告人构成洗钱罪[注] 参见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07)虹刑初字第719号刑事判决书。 。
(二)先决犯罪是否包括不法层面的犯罪
按照传统学说的观点,不负刑事责任的行为是不可能成立犯罪的,因此先决犯罪必须满足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三个阶层的要求,不包括不法层面的犯罪。正因如此,传统学说认为,父母明知12周岁的儿子杀人而对其进行窝藏的行为不构成窝藏罪,因为12周岁的人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不能成为故意杀人罪的主体,因此不满足窝藏罪中“犯罪的人”这一要求。
第三,设置的法定性。设置的法定性是对先决犯罪来源合法性的体现,即先决犯罪必须是由刑法所规定与设置的,而不能通过其他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随意进行增减。但需要注意的是,此处为“设置的法定性”而非“内容的法定性”,因此强调的是相对于其他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而言,先决犯罪必须由刑法进行设置,而并非指必须在刑法条文中明文规定“实施……罪”“犯……罪”“有……犯罪行为”等字样,故在刑法分则中除了明确规定上述字样的明示先决犯罪外,还存在需要经过推导、分析才能得出的默示先决犯罪,例如在《刑法》第241条规定的“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中,法条虽未明文规定该罪的成立必须以他人实施相关犯罪为前提,但从条文表述中可知该罪的犯罪对象为“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即《刑法》第240条规定的犯罪分子以出卖为目的,拐骗、绑架、收买、接送、中转的妇女、儿童[注] 黎宏.刑法学各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253. ,由此可以推断出要成立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必须以他人实施拐卖妇女、儿童罪为前提,若他人的行为只是法律所认可的民间送养行为或构成诈骗罪的“放飞鸽”行为[注] 根据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出台的《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第17条的规定,不是出于非法获利的目的,而是迫于生活困难或者受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私自将子女送与他人抚养,收取少量“营养费”“感谢费”的,属于民间送养行为,不构成拐卖儿童罪。“放飞鸽”指的是行为人与涉案妇女串通,由行为人假装将该妇女卖给他人,在拿到钱后再设法帮助该妇女逃脱的行为,因为在此种情况下行为人并未真正实施拐卖妇女的行为且其也没有拐卖妇女的意图,因此不构成拐卖妇女罪,而应根据具体案情将其行为认定为诈骗罪或其他犯罪。 ,那么行为人即使有所谓的收买行为,也不构成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因此拐卖妇女、儿童罪是本罪的先决犯罪,且为默示先决犯罪。
在刑法分则条文中,有些罪名的构成要件虽含有“犯罪”等字样,但其只是固定的语词用法而并不单独表示犯罪,或者虽表示犯罪但不能由其推导出本罪的成立必须以他人实施该犯罪为前提,因此此类犯罪中不包括先决犯罪,但因其易产生混淆,故本文在此处做一判别。
由表2还可知,273.75 K反应体系水合物的转化率为70.18%,273.95 K反应体系的转化率约为69.28%,说明温度越低,甲烷生成水合物的条件越温和,越有利于甲烷生成水合物,因此,甲烷的最终气体消耗量和水合物的转化率随反应温度减小均呈递增趋势。
综上所述,帮助行为正犯化是一种特殊的立法模式,其表明刑法对某些帮助行为的强调与重视,但并不必然导致正犯化后的犯罪中包含有先决犯罪,或者可以说,帮助行为正犯化与先决犯罪存在与否无关。
第二,对于赃物犯罪而言,“为无刑事责任能力者的危害行为掩饰、隐瞒赃物,对无责任能力者再次危害社会会起到诱导、鼓励的作用,因而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对这种行为不进行严厉打击,不利于预防犯罪,也不利于保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注] 马克昌.百罪通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996-997. 因此,应认为即使他人的行为仅达到符合构成要件不法的程度,也不影响本罪的成立,并且在赃物犯罪中,先决犯罪包括不法层面犯罪的观点也得到相关司法解释的支持。例如《赃物罪解释》第4条第2款规定,“上游犯罪事实可以确认,因行为人死亡等原因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不影响刑法第191条、第312条、第349条规定的犯罪的认定。”又如《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解释》第8条第2款规定,“上游犯罪事实经查证属实,但因行为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等原因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不影响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认定。”
第三,对于妨害司法类犯罪而言,其侵害的法益为司法机关对先决犯罪进行侦查、起诉、审判的正常司法活动,而这一点不会因为先决犯罪是否满足有责性的要求而有丝毫不同,只要存在犯罪事实,司法机关就会展开侦查、审理,而先决犯罪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等有责性阶层的问题也只有在司法机关进行调查后才能确定,在正式确定之前,司法活动仍会正常进行,因此行为人在这种情况下实施窝藏、包庇等行为仍然会对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造成妨害,进而应将此类行为认定为构成相关犯罪。
第四,对双层犯罪概念的理论提倡与立法回应为“先决犯罪包括不法层面犯罪”的观点提供可行性支持。在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中,“犯罪”的概念一般被划分为三种类型,即形式犯罪概念、实质犯罪概念与混合犯罪概念[注] 杨俊.对现行犯罪概念的反思——兼论混合犯罪概念之提倡[J].浙江学刊,2014,(2):147-157. ,但无论是哪一种类型,其都是整体意义上的犯罪概念,仅具有一个层面上的含义。随着德日阶层犯罪论体系在我国刑法领域逐渐被接受,一些学者开始主张从不同层面对“犯罪”的含义进行解释,进而提出双层的犯罪概念[注] 黎宏.我国犯罪构成体系不必重构[J].法学研究,2006,(1):47-50. ,即“不法意义上的犯罪”与“不法有责意义上的犯罪”,前者指的是行为仅满足三阶层体系中构成要件符合性与违法性阶层即可构成犯罪,后者指的是行为必须满足全部三个阶层的要件才能构成犯罪[注] 付立庆.违法意义上犯罪概念的实践展开[J].清华法学,2017,(5):82-83. 。同时应当看到,我国《刑法》中也有不少条文采取了双层的犯罪概念,例如《刑法》第15条第2款规定,“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此条中的“犯罪”即指不法意义上的犯罪,否则将会导致主观心态的重复。正是因为我国刑法理论与立法实践对双层犯罪概念的接受,使得认为先决犯罪包括不法层面犯罪的观点并未超出“犯罪”一词可能具有的含义,因而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
第二,亚太地区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50%以上,贸易总额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近一半,全球贸易和商业保持持续且包容性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16]该地区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将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所以美国也必须确保自身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以防止在亚太地区被边缘化并藉以维系自身经济的持续繁荣。因此,在密切同该地区的经贸往来的同时,美国也必须寻找和巩固在东亚地区的战略支点,以继续保持自身对东亚地区事务的塑造能力,而南海问题正是几个重要的备选“支点”之一。
(三)先决犯罪的具体范围如何
各个具体罪名当中先决犯罪的范围互不相同,但通过整体分析可以发现其仍有规律可循:本罪中的相关构成要件要素对先决犯罪的规定在形式上主要可以分为三种模式,即仅规定“犯罪”一词型、描述特定行为型与列明特定犯罪种类型。分述如下:
1.仅规定“犯罪”一词型
此种模式指的是在构成要件要素中仅规定“犯罪”一词以泛指一切犯罪,属于此类的罪名主要有《刑法》第310条规定的包庇、窝藏罪、第312条规定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第417条规定的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在这些犯罪中,构成要件要素对先决犯罪的规定没有任何限制,故其可以指任何犯罪,例如在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中,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向任何犯罪的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帮助其逃避处罚的,均构成本罪。
2.描述特定行为型
此种模式指的是相关构成要件要素规定特定的行为类型,进而由该行为推导出先决犯罪的范围,例如《刑法》第349条规定的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的罪状表述为“包庇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的……”,故由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的行为可以推断出本罪的成立以他人构成《刑法》的347条所规定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为前提[注] 王燕飞.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疑难问题探讨[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130. 。属于这种模式的罪名除上述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外还有《刑法》第241条规定的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第349条规定的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第355条规定的走私、贩卖毒品罪、第416条规定的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在这一类罪名中,往往通过对特定行为的分析即能够推导出先决犯罪的具体范围,但也存在有分歧的地方,即对于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中“绑架”的理解,有观点认为此处的“绑架”仅指《刑法》第240条第1款第5项所规定的行为类型,故本罪中先决犯罪的范围仅包括拐卖妇女、儿童罪,但另一种观点认为此处的“绑架”除第240条规定的情形外,还包括第239条绑架罪中的绑架行为,因此本罪中先决犯罪的范围为拐卖妇女、儿童罪与绑架罪。对此问题本文赞同前一种观点,因为若按后一种观点进行理解,则会出现不协调的现象:在妇女、儿童被绑架时不解救的,构成本罪;在年满14周岁的男子被绑架时不解救的,则成立其他罪名或无罪,这是极其不合理的[注] 首先,不解救被绑架的年满14周岁的男子的行为若无罪,毫无疑问是不合理、不均衡的;其次,此种行为若被认定为其他犯罪(如玩忽职守罪),也是不合理的。因为(1)此处根据犯罪对象来区分不解救被绑架妇女、儿童罪与玩忽职守罪这两个罪名缺乏依据,没有理由将不解救被绑架的妇女、儿童的行为单独规定为一个罪,因为在绑架罪中妇女、儿童相对于年满14周岁的男子并没有过多的特殊性。(2)两罪的法定刑不相同,若按后一种观点理解则可能出现量刑不一的情形。参见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1270. 。
3.列明特定犯罪种类型
记者从济青高速铁路有限公司获悉,根据济青高铁联调联试及运行试验安排,2018年8月21日-24日,济青高铁济南东站至胶州北站顺利完成了最高运行速度385km/h的试验检测工作。济青高铁设计速度350km/h,按照《高速铁路工程动态验收技术规范》要求,联调联试和动态检测时,综合检测列车最高测试速度应达到设计速度的110%。
列明特定犯罪种类的模式指的是,相关构成要件要素通过规定先决犯罪的类型来确定先决犯罪的具体范围,属于此种情形的罪名有《刑法》第191条规定的洗钱罪、第311条规定的拒绝提供间谍犯罪、恐怖主义犯罪、极端主义犯罪证据罪以及第414条规定的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注] 虽拒绝提供间谍犯罪、恐怖主义犯罪、极端主义犯罪证据罪的罪状表述为“间谍犯罪或者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行为”,但因其并不是直接规定“间谍行为或者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行为”,而是仍落脚于“间谍犯罪、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之上,因此要明确拒绝提供间谍犯罪、恐怖主义犯罪、极端主义犯罪证据罪先决犯罪的范围,最重要的还是要先判断上述两类犯罪的含义,故此罪中构成要件要素对先决犯罪的规定模式属于列明特定犯罪种类型,而非描述特定行为型。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亦是如此。 ,在此种模式中,一般根据特定犯罪种类就能够对应到刑法分则中特定的罪名,例如制售伪劣商品犯罪等,但也存在一些容易产生分歧的地方,这些分歧主要集中于洗钱罪与拒绝提供间谍犯罪、恐怖主义犯罪、极端主义犯罪证据罪中的部分先决犯罪,以下进行详细说明。
(1)洗钱罪
根据《刑法》第191条的规定,洗钱罪的先决犯罪(即其上游犯罪)包括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七类,其中认定存在争议的主要是毒品犯罪与贪污贿赂犯罪,而剩下五类犯罪的范围则相对确定。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指的是《刑法》第294条规定的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以及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实施的其他犯罪,例如抢劫、诈骗、非法经营等;恐怖活动犯罪指的是具有恐怖主义性质的犯罪,例如具有恐怖主义性质的绑架、劫持航空器等犯罪;走私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指的是《刑法》第三章第二、四、五节所规定的犯罪。
对于毒品犯罪的范围,一种观点认为是《刑法》第六章第七节所规定的各种有关毒品的犯罪[注] 赵秉志,李希慧.刑法各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43. ,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刑法》第六章第七节所规定的犯罪中,不能产生犯罪所得的罪名,例如非法持有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罪不应该包含在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中[注] 曹子丹,侯国云.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精解[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506-507. 。本文赞同前一种观点,因为后一种观点中所列举的犯罪并不一定不能产生犯罪所得,例如代他人保管毒品或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的行为仍然可以获得相应的报酬,而这些报酬即为相关犯罪的犯罪所得[注] 王作富.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上)[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3.489. 。因此,此类犯罪仍然可以成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故毒品犯罪的范围指的是《刑法》第六章第七节所规定的犯罪。
对于贪污贿赂犯罪的范围,一种观点认为是《刑法》第八章规定的各项犯罪[注] 黎宏.刑法学各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153. ,而另一种观点认为第八章之外的其他贪污贿赂类型的犯罪,例如《刑法》第163条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也应属于洗钱罪上游犯罪中的贪污贿赂犯罪。本文赞同后一种观点,因为洗钱罪的罪状表述是“贪污贿赂犯罪”,而没有直接采用《刑法》第八章的标题“贪污贿赂罪”。因此,不能将二者直接等同,且在我国对于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规定较窄的情况下,宜适当进行扩大解释[注] 阴建峰.论洗钱罪上游犯罪之再扩容[J].法学,2010,(12):78-79. ,因此不应将其仅限于第八章规定的犯罪类型。
其人刚直,所纠察弹劾之人,不论身份贵贱,一概按律论处,因而不为周遭大臣所喜,被陷害带兵讨贼。周处虽知此战必败,却也悍不畏死,仗剑出征,最终以身殉国,被追封为平西将军。西戎校尉阎瓒上诗说:“周处全臣节,美名不能已。身虽遭覆没,载名为良史。”
(2)拒绝提供间谍犯罪、恐怖主义犯罪、极端主义犯罪证据罪
拒绝提供间谍犯罪、恐怖主义犯罪、极端主义犯罪证据罪的罪状表述为“明知他人有间谍犯罪或者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行为,在司法机关向其调查有关情况、收集有关证据时,拒绝提供……”,因此其先决犯罪类型为间谍犯罪、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的范围一般不存在争议,其是指具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性质的犯罪,例如以制造社会恐慌为目的的劫持航空器罪、绑架罪等。但对于间谍犯罪的范围则存在不同的观点,狭义的观点认为此处的间谍犯罪仅指《刑法》第110条规定的间谍罪[注] 王作富.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下)[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3.1227. ;广义的观点认为除了间谍罪以外还包括《刑法》第111条规定的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注] 陈兴良.刑法全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1021. ;最广义的观点认为此处的间谍罪是指《反间谍法》第38条规定的构成犯罪的行为[注] 姚建龙.刑法学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386. 。本文赞同广义说,因为本罪规定的是“间谍犯罪”而没有直接使用《刑法》第110条的“间谍罪”,故不可简单将二者等同。另外,本罪的目的是为了查明具有境外背景的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故对其先决犯罪的范围不可过于限定,否则将导致本罪的设定失去意义,因此宜将本罪中的“间谍犯罪”理解为间谍罪和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
三、先决犯罪的立法改进与完善
刑法研究具有两个不同的面向和视角,即刑法立法论和刑法司法论(又称刑法解释论或刑法教义学)。立法论是以刑法应当如何制定的应然性为出发点,其理论追求是为刑法的完善提供指导,因此其往往涉及对刑法条文的批判与修改;而司法论则是以刑法应当如何理解的实然性为出发点,其根本目的是为刑法的适用提供理论依据,因此其往往涉及对刑法条文的解释与补正[注] 陈兴良.刑法教义学的发展脉络——纪念1997年刑法颁布二十周年[J].政治与法律,2017,(3):3. 。虽然有学者主张在通过对刑法条文进行解释即能够实现刑法的任务与目的时,则无需对法条进行批判与修改[注] 张明楷.也论刑法教义学的立场与冯军教授商榷[J].中外法学,2014,(2):360. ,但笔者认为针对目前的刑法规范固然应以解释为主,不过从为下次刑法修正提供参考的角度而言,适当的立法建议亦有其存在的意义。因此,对我国《刑法》分则中先决犯罪的研究也应当从这两方面分别展开,上文主要从司法论的角度出发,通过对相关条文中先决犯罪的解释来解决其在适用中所存在的困境与问题,而下文将主要侧重于立法论的视角,对先决犯罪的完善提出相关的立法建议。
虽然微电子技术听起来是一个距离我们生活很遥远的高科技,但在日常生活中,微电子技术服务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电子设备的芯片就是微电子技术的具体表现,它是我们用的手机、玩的电脑、看的电视、用的洗衣机、空调等电气中的核心构成部件。可以看出,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微电子技术。
改进后,安装整体式托辊支架时,只需沿限位块推行至固定螺栓孔位置,再安装托辊支架固定螺栓,便于整体式托辊支架安装定位。同时,整体式电缆托辊支架受下限位块的支撑,减小了托辊支架固定螺栓的支撑作用力。另外,在更换任一托辊时,无需再拆卸托辊支架,有效的避免了托辊支架固定螺栓出现滑丝现象。因整体式支架受上、下限位块的限位作用力,避免了电缆托辊支架的倾斜,解决了垂直托辊与支架底板摩擦问题。
(一)语词表述应更加准确
从上述先决犯罪的司法适用困境中可以看出,相当一部分争议的产生是由于法条中的具体语词表述存在不明确的地方,因而导致理解上的分歧,例如对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中先决犯罪的具体范围之所以产生争议,即是因为该罪的构成要件要素中规定有“绑架”一词且未做任何限定,而《刑法》第239条绑架罪与第240条拐卖妇女、儿童罪中均有“绑架”的行为方式,故导致对该罪中的“绑架”应如何理解产生了不同的观点。因此,要避免对先决犯罪的范围与含义产生误解,最根本的方法在于语词表述应更加准确,避免产生歧义。例如在上例中,既然绑架罪与拐卖妇女、儿童罪均具有“绑架”的行为方式,那么为保证对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中先决犯罪范围的准确界定,无论立法者采取哪种观点,都应该根据相应的观点对相关构成要件要素进行有针对性与区别性的表述:若立法者主张本罪的先决犯罪仅为拐卖妇女、儿童罪,那么即应当去掉“绑架”一词,仅表述为“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若立法者主张本罪的先决犯罪还包括绑架罪,那么应明确规定“对本法第239条、第240条中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负有解救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消除理解上的分歧。
(二)对先决犯罪的指向应更加具体
上述构成要件要素规定先决犯罪的三种模式中,仅规定“犯罪”一词型由于指向的明确性而使得其所规定的先决犯罪的具体范围不存在任何争议;但在描述特定行为型与列明特定犯罪种类型中,仅有部分行为或犯罪种类能够清晰地指向具体犯罪,而另外部分则由于语词本身的含混性与相关犯罪分类的模糊性导致对先决犯罪认定的分歧。因此要明确先决犯罪的具体范围,则需要对此部分构成要件要素加以改进,并在之后的立法中尽量避免此种规定方式。首先,若先决犯罪包含一切犯罪种类,则直接在构成要件要素中规定“犯罪”一词即可,无需做任何限制;其次,对于需指向特定犯罪的情形,在能够指向特定法条的情况下尽可能采取此种模式,例如上文所述,将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的罪状规定为“对本法第239条、第240条中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负有解救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使得该罪的先决犯罪能够直接指向刑法第239条、240条规定的犯罪,以消除分歧;再次,在无法指向特定法条的情况下应尽可能的使用具体的表述方式,例如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的构成要件要素表述为“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其虽为列明特定犯罪种类型模式,但清晰地指向了《刑法》第三章第一节所规定的相关犯罪;最后,对于某些特殊的犯罪,若实在无法通过立法改进的方式确定其先决犯罪的具体范围,例如拒绝提供间谍犯罪、恐怖主义犯罪、极端主义犯罪证据罪中的“间谍犯罪”,则只能依靠刑法解释对其含义予以明确。另外,有学者提出可以采取参见罪状的方式对相关犯罪中先决犯罪的范围进行确定,例如按照《反洗钱法》的规定来确定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等[注] 谢常红,游训龙.我国洗钱罪原生罪的立法困境与对策探析[J].求索,2013,(10):189-190. 。但笔者认为,参见罪状需要参考其他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然而其他法律的立法水平、明确性程度等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加之《反洗钱法》属于行政法律,其规制对象为一般违法行为,故不可当然的将其作为确定洗钱罪先决犯罪的依据,因此采取参见罪状的观点仍有待商榷。
四、结论
本文从整体性视角出发,在归纳、总结的基础上对我国《刑法》中先决犯罪的认定及其司法困境、立法完善进行了分析与思考:在司法适用中,先决犯罪的认定只需证明犯罪事实存在即可,无需经过审判,且其包括不法层面的犯罪,同时,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对先决犯罪的规定在形式上主要有仅规定“犯罪”一词型、描述特定行为型、列明特定犯罪种类型三种模式,各罪中先决犯罪的范围应分别予以认定;在立法改进上,构成要件要素的语词表述应更加准确、对先决犯罪的指向应更加具体。这种分析方式突破了传统研究中仅针对各罪先决犯罪进行考量的限制,有利于保持先决犯罪适用的体系性与一致性,进而再反过来指导对各罪中先决犯罪的分析与理解。但同时应当看到,本文只是对先决犯罪的初步研究,尤其是在立法建议方面稍显单薄,因此,还需要进行更多、更加深入的研究与探讨。
3.黑社会组织。如前所述,目前我国大陆还不存在黑社会组织这种有组织犯罪的最高发展形态。从现阶段的国情以及“打黑”形势来看,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大陆出现黑社会组织的可能性非常小。
A Study on Prerequisite Crime from the Holistic Perspective
HUANG Chen-chen
(Criminal Justice College of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China )
Abstract :The prerequisite crime is a special kind of crime, it is the precondition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incipal crime and it stipulated by the criminal law. Prerequisite crime has three characteristics: it has prepositive judgment, it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principal crime and also it is set by law. There is no inevitable connection between taking the aider as principal offender and prerequisite crime. During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prerequisite crime only needs to prove the existence of the fact and no need for trial. According to the two-tier concept of crime, prerequisite crimecontains the crime on illegality level. The constitutive elements of principal crime stipulates prepositive crime in three modes: only stipulate the word “crime”, describe particular behaviors, list specific types of crime, and the scope of prerequisite crimes in each type shall be determined separately.In terms of the legislative improvement, the words of constitutive elements should be expressed more accurately to overcome divergence in understanding and the directive on prerequisite crime should be more specific and try to adopt goal-setting models.
Key words :holistic perspective; prerequisite crime; the solution of judicial dilemma; legislative perfection
*收稿日期 2018-11-15 该文已由“中国知网”(www.cnki.net)2019年2月25日数字出版,全球发行。
作者简介 黄陈辰,男,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2018级刑法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刑法学。
中图分类号: DF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69X(2019)02-0076-11
DOI. 10.19510/j.cnki.43-1431/d.20190225.002
标签:整体性视域论文; 先决犯罪论文; 司法困境及解决论文; 立法完善论文;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