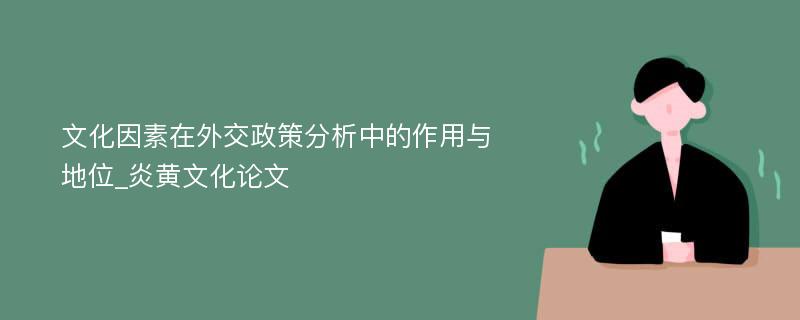
外交政策分析中文化因素的作用与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政策论文,中文化论文,地位论文,因素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已经成为一个对当今社区、地区、乃至整个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受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影响,不少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或多或少都吸取了文化研究的观点,把文化作为其研究所考虑的变量之一,文化与外交、文化与国际政治日益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对文化的研究已经远远超越传统上以文化输出和文化压迫为标志的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是构成一个国家的国家特性(nationalattributes)的一部分,也是影响一个国家外交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变量,因此日益受到研究和分析外交政策学者的重视。(注:英文的如Martin M.SampsonⅢ,"Cultural Influences on Foreign Policy,"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eds.,Charles Hermann et al.(Boston:Allen & Unwin,1987);Valerie M.Hudson ed.,Culture & Foreign Policy(Boulder,Colorado: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7);中文的如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计秋枫、冯梁等:《英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本文拟就外交政策分析中文化因素的作用和地位进行一些探讨。
一、难以界定的文化概念具有清晰可见的基本特点
文化是社会科学中最容易理解又最难解释的东西。容易理解是因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外在的表现形式,我们生活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而且通过一些常见的渠道(如电视)经常会接触到其他文化,或直接与其他文化背景的人交往,我们对它非常熟悉。难以解释是因为文化内隐结构非常宽泛、含糊和难以界定。对文化简单的概念包括,文化是“人类制造的那部分环境”,“人脑的软件”,“人们相互共享的意思、认识和价值观”,“一套强制日程”等。(注:Hudson ed.,Culture &Foreign Policy,p2.)有人提出文化是一系列指导一定群体的人交流、思考,以及人与人之间或者人与环境之间相处的规则;另一些人认为文化是“社会中形成的一个群体共享的观察和行为的标准”。有些人提出,文化“在某种含义上是一种指导一个群体的人们相互关系的规则。它可能是看不见的含糊的,但它决定一个群体与其他群体的不同。”19世纪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泰勒将文化定义为“复杂的集合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理论、法律、风俗及人们作为社会成员所拥有的其他任何能力和信仰。”(注:Sampson Ⅲ,"Cultural Influence on Foreign Policy,"p.385.)美国学者克罗易勃和克鲁克霍恩列举了164种文化的定义后,认为“文化”的概念难以把握,勉强作了一个他自己的定义,即文化是“一种源自行为的抽象概念”。(注:朱瀛泉:“导言”,《英国文化与外交》,计秋枫、冯梁等著,第16页。)哈德森(Hudson)对各种各样的比较有影响的对文化的定义进行比较后指出,对文化不同概括可以分为三类,第一,“文化是有意义的组织(organization of meaning)”,第二,文化是“价值喜好(value preferences)”,第三,文化是“人类计谋的模板(template for human strategy)”,并从这三个方面探讨文化对外交决策的影响。(注:Ibid.,p.5.)
虽然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关于文化的基本概念,但文化的特点是明确,能够看得到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成过程是缓慢的,其核心内涵,或基本的价值观念是数千年文化积淀的结果。在从文化角度研究或分析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时往往与对这个国家的历史和传统的研究分不开。儒家思想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核,至今都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为人处世,乃至中国的外交行为。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产品对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都产生影响,最后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博大内涵。台湾学者石之喻在《中国外交政策的精神:一个心理文化学的视角》中认为尽管环境不断变化,传统的信仰体系,如儒教、道教和佛教仍然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文化源泉。(注:Chih-yu Shih,The Spirit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A Psychocultural View(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0).)在研究中国文化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时,不同的学者选择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产品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来研究其文化内涵对现代中国外交的影响。国内出版的《美国文化与外交》与《英国文化与外交》也是采取历史的叙述方式探讨两国文化与其国家外交政策的关系,基本上是从文化的视角阐述两个国家的外交史。
第二,一个民族文化的基本内涵,或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观念一旦形成,具有跨时代的稳定性,超越承载和显现这种文化的任何人和政权。人代代相传,朝代频频更替,政权不断改变,但一个国家文化的基本内涵和基本价值观念,或者与文化因素紧密相连的生活和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等则是相对稳定的。美国文化根源中清教思想对美国外交的影响也不仅仅局限于哪一届政府,而是贯穿于美国历史的始终,只是在不同的时期因为国内外客观形势的变化表现不同而已。如早期的“美国例外论”和“孤立主义”,而此后的“门罗主义”,冷战结束以后老布什的“世界新秩序”谋计和今天美国政府不断强调的“人权外交”都可以找到贯穿始终的一条线,那就是源于清教文化的“优越感”、“使命感”和“天定命运”等观念。
第三,文化的影响超越群体、阶级和政治党派而普遍存在,其影响表现在家庭、社会、企业和政府部门等社会的各个方面。如在企业文化中,美国强调公平竞争,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个人的创造权和发明权),而中国则强调集体利益,知识产权观念淡薄。在饮食文化中,中国强调用简单的工具做出色香味俱全的食品,以显示自己技艺的高超;而美国人则是绞尽脑汁改善工具,以便自己做饭时能够更加快捷省事,并不讲究质量。在校园文化中,中国重考试,美国重应用,中国强调集体(班),美国突出个人。在家庭文化的差异中,中国重关系,而美国则重平等;在对儿童的教育过程中,中国人常说子不教,父之过,而美国则强调父母尊重子女的权利,因此才会出现在中国成长而移居美国的家长,常常因为“虐待”子女而受到惩罚等在中国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怪事。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对外政策都希望以美国的方式来改变世界,只是不同的政党选择的手段多少有些不同罢了,他们体现的都是美国的文化精神。
第四,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优秀的一面,也有其颓废的一面。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化是完美无缺的,因而也就不存在一种文化优越于另一种文化。列宁曾经说过,“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注:《列宁全集》,第20卷,第15页。)例如,东西文化相比,“以西方重物质,中国文化重精神的区别来讲,重物质则重生产,开源以致富,但重物质有极端个人主义倾向,”“中国重精神则有讲信义、重亲情的美德,但也有善空谈而不愿实践的问题。”(注: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M],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1页。)因此从文化不同的侧面可以对外交政策进行不同的解释。如1998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布的《中国国防白皮书》指出:“中国实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还渊源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有爱好和平的传统。中国古代思想家曾提出过‘亲仁善邻’的思想,反映了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就希望天下太平、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这种思想表现在军事上,就是主张用非军事手段来解决争端、慎重对待战争和战略上后发制人。”(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国防》白皮书,1998年7月。)而美国学者江忆恩(Johnson)引用中国古代的《吴子兵法》、《司马法》、《尉缭子》、《三略》、《六韬》、《唐太宗问对》、《孙子兵法》等有关军事战略的典籍来阐述中国文化的另一个方面,即中国的战略文化。(注:Alastair I.Johnson,Cultural Realism: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
第五,每种文化对该文化载体的影响是普遍的,但并不具强制性或约束力,因此对不同的人的影响可能有所不同,对不同的人影响在不同的时间内也不是永远不变的。内森和罗斯针对文化的影响说,“对连续性和变化都起作用的一个媒体则是文化。行为习惯、态度和信念以及往事的记忆,影响着现今的举止,但这一影响并非不可抗拒,也不是预先确定不变。文化是一种保留节目,既不规定连续性,也不妨碍变化。如同历史一样,文化包含多多少少与某一特定问题有关的许多可能性,它们加在一起,为社会角色所选择的几乎任何一种活动模式提供一系列先例。”(注:[美]安德鲁·内森,罗伯特·罗斯:《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M],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页。)如虽然中国文化中强调尊老爱幼,但虐待父母也并不少见;美国文化中强调“民主”、“自由”,美国常常要求其它国家实行美国式的社会制度,但在国际上却频频推行霸权主义政策,是最不讲民主的国家;基地组织以伊斯兰教义为旗帜,却从事着违背伊斯兰教义的恐怖主义活动。因此内森和罗斯在谈到中国文化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时说,“对于中国人来说,也像对于美国人和别的人来说一样,暴力不是文化的产物,而是需要和机会的产物。”(注:[美]安德鲁·内森,罗伯特·罗斯:《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M],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29、30页。)
二、文化影响外交决策和外交行为的主要途径
文化是影响国家对外政策制定以及国家外交行为的重要变量,其影响主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而体现出来。首先,文化影响国家外交政策的内容和目标。这是早期研究文化与外交政策关系的学者所普遍强调的,即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决定这种文化载体对外政策中的特定文化价值观念。如一些学者将美国外交史上的孤立主义和扩张主义激情归因于美国文化中“个人动因(private initiative)”,以及“权力是建立在商业和经济发展基础上”的观念;一些人把日本1941年偷袭珍珠港归因于“日本传统的思维框架中天生的极其危险的……与生俱来的文化上的,非物质上的倾向。”(注:Martin M.Sampson,"Cultural Influence onForeign Policy".)冷战结束以后兴起的建构主义理论则认为,文化不仅影响国家行为的各种动机,而且还影响国家的基本特征,即所谓的国家的认同。邢悦利用文化学理论中关于文化功能的内容提出,文化的定位功能为确定对外政策提供了观察世界及自身的视角;文化的定向功能决定了对外政策的价值追求;文化的规范功能为对外政策的选择限定了范围;文化的认同功能为对外政策中确定与别国的关系提供了文化基础。(注:邢悦:“文化功能在对外政策中的表现”[J],《太平洋学报》2002年第3期。)如在中国文化中有“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言必信,行必果”,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等传统,中国领导人常常引用这些格言在对外政策中强调互相尊重,求同存异,一贯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在西方有人提出“文明冲突”论后,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由于各民族在历史发展、社会背景、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等方面有差异,存在一些矛盾和分歧是难免的。”“不同文明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对话和交流,彼此借鉴,取长补短,在发展和丰富自己的同时推动人类文明走向新的繁荣。”(注:江泽民:《对沙特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的演讲》[N],《人民日报》1999年11月3日。)对比而言,美国往往强调其文化中人权自由等思想是所谓人类的普遍价值,表现在外交上就是“己所欲,必施人”,把推行美国价值观念、社会模式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表现为以意识形态对抗和反共,冷战结束以后则又表现为对美国基本价值观念的扩展,即克林顿政府所提出的扩大民主和自由经济的共同体。布什总统在2002年9月30日向美国国会提交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的美国需要处理的三大安全战略问题,其中之一就是通过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努力把“和平、发展、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从文化角度分析国家对外政策及战略关系的学者认为,国家战略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即“战略文化”。例如研究中国外交的美国学者金淳基(S.Kim)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指出,“中国现在的扩军政策与即将来临的军事威胁很少有关系;它所反映的是一种一个世纪的民族屈辱感所带来的‘战略文化’。”(注:Samuel Kim ed.,China and the World: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3rd ed.(Boulder:Westview Press,1994),p.14.)内森和罗斯则认为,“在中国的战略思想中,有两个经久不衰的象征:长城和空城计……长城是一个软弱的象征,因为它表明中国易遭入侵。它又是一个力量的象征,因为它表明中国经济和文化优越,而且有能力创造工程奇迹和保持警惕,阻挡外敌入侵。”“空城计是强弱兼备的又一个象征”。长城与空城计既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象征也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因此他们把他们的系统阐述中国外交的书定名为《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
其次,文化影响决策者并通过决策者影响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外交政策是由能够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民族性的人来制定的。一个国家历史上长期沉淀下来的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长大的,能够成为这个国家利益代表的国家领导人的基本价值观念、信仰、基本的思维、行为方式和处世态度。这些属于文化范畴的观念为他们的行为提供了一个观察问题的“透镜”,影响他们对世界的看法,限制着他们的基本思维方式。这种特定的文化特点构成了领导人的“心理环境”的一部分。反过来,代表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领导人则反映了本民族特征的文化需求。他们在制定外交政策的过程中必然有意无意地把存在于他们意识深层的文化价值观体现出来,使本国的外交政策不同于他国的外交政策。如《美国文化与外交》一书的导言指出:“国家只有通过其内部结构培育出来的代表国家利益的精英人物才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与影响。这些活跃于国际舞台上的人物是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之所以成为一个国家的杰出人物,显然是因为他们的言论或行为符合了国家的民族精神,体现出了反映本民族特征的文化模式。这样,他们在制定或执行政策过程中,必然有意或无意地把存在于他们意识深层中的文化价值体现出来,给本国的对外政策打上明显的烙印。”(注: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第2-3页。)正是因为美国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天定命运”的思想观念,才使美国领导者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外交理念拥有美国的特点,如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卡特的“人权外交”等等。如近代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蹂躏的历史给中国人留下的屈辱记忆,促使中国领导人在对外政策中特别强调主权不能干涉的原则,坚持把独立自主作为中国外交的根本指导思想。毛泽东强调,“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注:《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78页。)邓小平则强调,“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了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了国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会容许任何国家来干涉自己的内政”。(注:《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1-332页。)
再者,文化影响对外政策制定的机制和过程。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影响其基本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而后者则制约着这个国家总的外交政策制定的机制和过程。美国的三权分立,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日本和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等都可以从它们建国初期的历史以及文化背景中得到某种解释。如美国文化鼓励个人主义,强调“民主”、“自由”、“平等”等,建立在这种政治文化基础上美国政治体制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避免权力的过分集中,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特权和腐败,三权分立和不同部门之间的制衡,是美国政体的主要特点。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则使影响和制衡美国外交的因素大大增加。这种政体使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往往是一个官僚政治斗争的过程。研究外交决策的官僚政治模式不仅源自美国,而且最适用于研究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不仅行政内部有矛盾,而且行政和立法部门之间也是矛盾重重。(注:Morton H.Halperin,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Washington D.C.:the Brooking Institution,1974).)发展中美关系最大的障碍——《与台湾关系法》,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结果。
桑普森(Sampson)从文化角度对日本和法国的外交决策机制和过程进行比较以后提出,日本的外交机构具有很多日本家庭组织的特点,重资历、级别明显、强调和谐、决策过程和政策变化都相对缓慢,比较容易预测等。而法国的外交机构和决策过程具有法国文化的特点,权利相对集中、突出个性、协调性差、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也具有个性化的特点。(注:Martin M.Sampson,"Cultural Influence on Foreign Policy".)派伊(Pye)对日本文化的研究同样指出,日本文化对日本政府的决策过程影响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下属具有采取主动的很大余地同时又保护上级自尊”,在这种传统决策过程中,每一个决策基本上都是从下层开始的,一旦到达最高领导人那里时,基本是形成了一致的意见。(注:Lucian W.Pye,"Political Psychology in Asia,"in Margaret G.Hermann ed.,Political Psychology(San Francisco,California:Jossey-Bass Publishers,1986),p.470.)派伊对印度政治文化的研究指出,“印度的社会化过程和印度教的教义结合并共同形成了印度政治文化中计划的理想化和对政策落实方式的不重视”的特点。在印度,“政治中庇护(patronage)关系要优先于政策考虑。不管是尼赫鲁还是甘地都不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制定政策。父亲坚持其理想的计划,很少考虑可以操作的实验;女儿越来越不考虑政策的创新,而把她的精力集中在通过庇护性的决定建立和保持一种支持。”如果从日本文化、印度文化对决策过程的影响来看,日本文化中的依附关系产生一种合作和谐的命运共同体,从而能够形成目标一致的合力;而印度文化中建立在依附关系上的安全感使人不需要考虑效率的检验,建立一种可靠的关系本身就是目的。在印度政治中,决策的核心不是长远的目标,而是如何才能建立一种接触和联系。(注:Ibid.,pp.475-476.)
最后,文化影响到一个国家外交政策执行和实施的方式和手段,从而使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拥有独特的文化和民族特色。外交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和交流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行为和艺术,从某种程度上说,“一方面表现出其独有的历史、文化特性,另一方面又反映出它对其他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国家所采取的态度,因此外交除了具有人们通常所熟知的国家或社会集团属性外,同时还具有人文属性。”(注:朱瀛泉:“导言”,《英国文化与外交》,计秋枫、冯梁等著,第17页。)外交是由代表国家的人之间相互交往的一种社会现象,特定的文化中的规范、习惯,以及为人处世的方式影响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打交道的形式。且不说外交礼宾和礼仪中对特定民族文化习性的尊重,特定文化中人与人相处的方式不仅影响到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优先考虑的内容,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外交政策制定、落实的方式和手段。如在中国人际交往中,重面子,讲关系,反映在外交行为也十分突出。对于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外交,中国常常强调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分清敌与友,强调站在哪一边的问题,如早期的“一边倒”,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目前则强调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永远属于第三世界”。在对待其它国家的关系方面往往以它们与自己主要敌人的关系问题来确定,在外交史上的表现包括“以美划线”,“以苏划线”,以及建立“反霸统一战线”等。这些都是以国家间的矛盾和相互关系为标准来确定中国外交政策的选择的。至于中国文化中重礼仪,既表现为外交行为中的崇尚礼尚往来,强调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也表现为对“礼仪”、“面子”的过多考虑,即台湾学者石之愉所说的中国的“面子外交”。一些西方学者也提出,“中国外交重视‘给面子’和‘顾面子’……相互给面子可以是一种有用的讨价还价的手段……如果中国能让它的对手相信,为面子着想,中国的灵活性有限,就可以使对方的要求不至于过分。”(注:[美]安德鲁·内森,罗伯特·罗斯:《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M],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三、文化因素在外交政策分析中的地位
尽管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国家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是由于文化的两面性和影响的非强制性,其影响并非一直存在并受到人民的一贯重视的。正如在社区忙于进行阶级斗争的年代不可能有社区文化之说,在企业抓革命,促生产时代,不可能奢谈企业文化;在人们在津津乐道“地道战”、“地雷战”的时候,更不可能有什么娱乐文化;在人们食不裹腹的时候也根本不可能奢谈什么饮食文化。从文化角度分析或研究外交政策,或研究文化因素对外交决策的影响也是如此。在冷战时期,经济的、政治的、或者是意识形态冲突的范式能够解释外交政策或国际关系的时候,文化因素几乎很少提及,如今在旧的范式不足以解释外交政策的时候,文化就开始被重视了。哈德森指出,文化的影响被认为是解释外交政策的“最后一个选择”,其它理论不能解释的行为都可以认为是由于文化的因素在发挥作用。(注:Hudson ed.,Culture & Foreign Policy,p.2.)如在文化因素的作用凸显的情况下,有一些学者提出了“文化决定论”来解释拉美国家发展的滞后。他们指出,南北美洲历史上都是欧洲的殖民地,独立时间相差无几。然而,美国和加拿大早就成了发达国家,而拉美依然是发展中国家。这一差别的根源是文化在发挥作用。独立后的北美洲人受新教文化的影响,善于创新和探索,并富有勤奋精神;而独立后的拉美人受伊比里亚天主教文化的影响,被视为“傲慢、浪漫和散漫”的代名词。和东亚国家相比,东亚人重视教育与储蓄,信奉“先苦后甜”,不管工作多累,在士气上都愿意尽职尽责和服从上级,并将劳动视为生活和个人价值的源泉;而拉丁美洲人反其道而行之,因为拉美人喜欢消费,因此大多数拉美人的储蓄率低,只得依赖外资。(注:江学时:“对第三世界若干问题的认识”[J],《国际经济评论》2001年第5期。)亚洲也有不少人相信近年来亚洲经济上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亚洲文化的产物,亚洲文化优越于文化上颓废的西方文化,因为亚洲文化具有“秩序、纪律、家庭责任感、勤奋工作、集体主义、节俭等”优越点,而西方文化“自我纵容、懒惰、个人主义、犯罪、教育差、不尊重权威,以及‘思想僵化’等”。(注:[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前者导致了亚洲经济的繁荣,而后者导致了西方的衰败。
针对夸大文化作用的认识,对文化决定论持批评观点的人指出,强调文化作用的人把除了厄尔尼诺现象以外世界上所有不好的东西都归因于文化因素。如有人针对李光耀把儒家文化看作是新加坡成功的原因指出,如果文化因素是发展的决定因素,那么作为儒家文化发源地的中国为什么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得不到发展,儒家文化的积极影响为什么非要等到现在才发挥其积极作用。新文化运动时期,不少中国的精英(如人们熟悉的鲁迅)曾把中国儒家文化看作是中国落后的根源;而20世纪后期的不少中国人,以及一些西方的社会学家赞美儒家文化是中国进步的根源。正如亨廷顿所说,“华人领导人无论想要为专制主义辩论还是为民主辩护,他们都从其共同的中华文化而不是从引进的西方观念中寻求合法性。”(注:[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页。)文化被认为是导致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军事灾难的根源,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而美国经济和社会制度的“衰落”时,不少日本人便摆脱了对西方模式的幻想,相信他们的成功的根源一定存在于自己的文化之中,日本文化成了日本经济繁荣的动因。但这样的逻辑则解释不了目前日本经济的持续萧条。同样,任何国家的对外政策都是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而调整的,同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可能因时、因势而不同,具有一定稳定性的自变量文化很难与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的应变量外交政策之间建立起稳定的因果关系,因此文化更不能预测国家外交政策的未来。
尽管文化因素在外交政策分析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学者来从这个视角对国际关系和国别外交进行研究,但是,应当明确的是,文化与其它因素是互为补充和互为借鉴的。所谓的“文化帝国主义”正是建立在帝国主义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基础之上的,而文化的侵略则往往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侵略相辅相成。文化因素有时也会与其它因素发生矛盾。如文化本身就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但文化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其它方面又不完全一致,有时候甚至会发生矛盾。在外交决策过程中过于强调文化利益(特别是意识形态的利益),则会导致国家根本利益受损和国家总体外交政策的失败。在研究和分析外交决策的过程时过于强调文化因素的作用,会忽视其它因素的作用和影响。文化只是影响外交决策的一个因素,而且远非决定因素,它只能和其它因素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外交政策分析强调从多层次、多角度分析影响一个国家外交决策和外交行为的因素。从文化视角来研究和分析外交政策,只是为外交政策的研究增加了一个视角,丰富对外交政策的研究而不能替代其它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