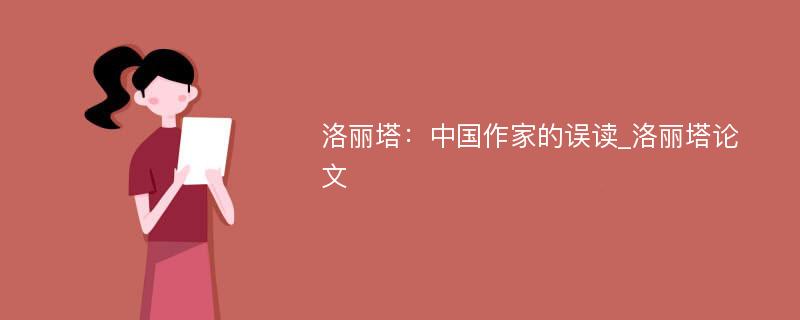
《洛丽塔》:中国作家的误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误读论文,中国作家论文,洛丽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洛丽塔》(Lolita,亦译《洛莉塔》、《罗丽塔》)是俄裔美籍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著名小说。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成年男子对一个少女的控制不住的乱伦情感,小说将可怕的欲望与主人公充满自我谴责的情感困惑刻画得入木三分。同时,这部小说也“与20世纪美国文化的主题息息相关”——因为它明显违反了公共道德的基本准则。正如美国评论家莫里斯·迪克斯坦指出的那样:“《在路上》是对无政府主义的个人自由进行具有爱默生风格的赞美,把书中的主人公变成了一个反对传统文化的神话式人物,而《洛丽塔》则假装对离经叛道和变态心理做了一番个案调查,对凯鲁亚克热情赞誉的那种道路旁边的美国文化进行了讽刺。”如果说《在路上》充满了“垮掉的一代”的疯狂激情,那么《洛丽塔》则处处闪烁着学者的讽刺机锋——这是“一部由一系列文学典故和许多具有讽刺意义的名字组成的超小说。……”① 此外,在美国,由于《洛丽塔》引起的文学论战甚至被看做“美国文学由现代派向后现代派(或从传统精英文化向当代大众文化)过渡的代表性作品”。因为这部小说“让欧美批评界百思不得其解,百解难以奏功”。②
据统计,《洛丽塔》中文版至今已有10个不同的版本。1989年,漓江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就不约而同推出了不同译者翻译的《洛丽塔》。到了2005年底,美国兰登书屋、英国企鹅出版社、法国伽利玛出版社、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不约而同推出了这本小说的纪念收藏版,上海译文出版社也隆重推出了“字数最多、没有任何删节”的《洛丽塔》“全译本”。由此可见这本小说的生命力之长久、影响力之深广。
中国作家眼中的《洛丽塔》
当代作家中,苏童曾写过一篇《读纳博科夫》。他在文中写道:他从纳博科夫的书中感到了“睿智而又锋芒毕露的气质”。读《洛丽塔》,“是一口气把书读完的”,因为他“喜欢这种漂亮而简洁的语言”,他说他敬畏“纳博科夫出神入化的语言才能。准确、细致的细节描绘,复杂热烈的情感流动”。他还从那个乱伦故事中读出了“感人至深如泣如诉的人生磨难”,“乱伦和诱奸是猥亵而肮脏的,而一部出色的关于乱伦和诱奸的小说竟然是高贵而迷人的,这是纳博科夫作为一名优秀作家的光荣。他重新构建了世界,世界便消融在他的幻想中,这有多么美好。”而当苏童谈到“亨伯特带着洛丽塔逃离现实,逃离道德,逃离一切,凭借他唯一的需要——十二岁的情人洛丽塔,在精神的领域里漂泊流浪”时,③ 也很容易使人想到苏童小说中的“逃亡”主题——从《1934年的逃亡》(虽然此篇发表时《洛丽塔》的大陆版尚未问世)到《逃》……那一个又一个关于逃亡,也是关于“人生磨难”的故事。据报道,当新版的《洛丽塔》面世时,作家叶兆言也准备到书店里去买本新的,看看它到底多了些什么内容。④ 由此可见作家对《洛丽塔》的浓厚兴趣。
王朔说过:“我喜欢纳博科夫的《罗丽塔》,那里面没有社会的震动,全是个人的东西,写的是一个人的精神境界。我喜欢这种。”⑤ 他对《洛丽塔》的这一认识与他关于自己的“写作动机萌动于世俗生活的刺激”的表白正好吻合。⑥ 有趣的是,《洛丽塔》讲述的是一个成年男人对于一个性感少女的乱伦之情,而王朔笔下的故事开始常常是玩世不恭的青年对纯情少女的逢场作戏。发表于1984年的中篇小说《空中小姐》中,女主人公王眉对一个玩世不恭的“没用的人”的爱就是“孩子似的既纯真又深厚的依恋”,这样不对等的爱带给王眉的当然是痛苦。而她的因公殉职最终还是感动了“没用的人”,使他“感到自己在复苏”。发表于1985年的《浮出海面》(与沈旭佳合作)也是一个玩世不恭的“无业游民”与一个渴望真爱的舞蹈演员于晶的爱情故事。但到了1991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动物凶猛》那个描写“文革”中少年男女之间的情感纠葛的故事时,就出现了放浪、叛逆的女孩于北蓓和“天生具有一种妖娆气质”的“性感”女孩米兰的形象。她们是“盛开的罪恶之花”,都喜欢玩世不恭的高氏兄弟,因为他们“集明朗、残忍、天真于一身的迷人气质”。而她们“对道德、秩序的挑衅”也使得小说中的“我”“用看待畜生的眼光看待女人”。我们不难从于北蓓和米兰的故事中看出洛丽塔的影子。发表于1992年的中篇小说《过把瘾就死》,则是一个麻木不仁的男人与一个因为无聊而恋爱,结婚以后又多疑、喜欢吃醋、大闹的女子杜梅之间彼此折磨、却终于无法分离的悲剧故事。从《空中小姐》、《浮出海面》那样讲述玩世不恭的男人捉弄纯情女子的故事到《动物凶猛》和《过把瘾就死》那样的“坏女孩”、“泼妇”与男人一起游戏人生、或者彼此折磨的故事,是可以看出王朔创作风格变化的某些轨迹的。联系到王朔说过“要写一部《飘》(Cone with the Wind)”⑦ 的追求,也是可以看出他1990年代对“坏女孩”和“泼妇”形象的特别关注的。因为《飘》的主人公郝斯嘉(Scarlett O'Hara)正是一个有点“坏”和“泼”的气质的女性形象。
池莉也曾经谈到过自己反复阅读《洛丽塔》的感受:“一部小说,诱惑得人彻夜无眠,这就是好小说!……感谢《洛丽塔》,除了美丽我的人生之外,它还激活了我的许多思想。”“《洛丽塔》写不健康的人和不健康的意识,但是,它是一部好小说”,它使池莉明白:“好的小说首先应该非常感性,它应该诱惑读者,刺激读者,使读者在小说的暗示下,体味他自己的生命经验,发挥他自己的想象能力,或者说提高他自己对世界的判别能力。”作为一位畅销书作家,池莉还意味深长地指出:“《洛丽塔》没有获得什么大奖,是读者的热爱使它成为名著与经典。尽管畅销的并不都是名著,但是真正的名著都应该是畅销的。如果没有广泛的知名度,如果没有广泛地影响人类社会,何谈名著呢?”⑧ 池莉是“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擅长描写普通市民的喜怒哀乐、烦恼人生。她的作品一直颇受广大读者的喜爱,畅销不衰。但她也写出了《一夜盛开如玫瑰》那样反映知识分子微妙情感的作品。婚姻失败的大学女教师苏素怀“永远是智慧与冷峻的”,然而她仍然有着“被伺候被支配的愿望”,在那个孤独的晚上,她的“理智可怜地挣扎在纷乱的情绪边缘”,以至于她竟然对陌生的出租车司机(一个“充满了雄性气息的男人”)产生了“一种小羊羔一般的迷人情调”,并因为司机的男子汉气概而将他引为“天生的知己”!他们甚至在短时间里发展到鬼使神差相拥接吻的地步。然而,那最终不过是一时的逢场作戏。他们彼此在通报姓名时使用假名的做法相当具有讽刺意味地揭示出了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虚伪风气。看,《一夜盛开如玫瑰》正好是“写不健康的人和不健康的意识”的作品,能“诱惑读者,刺激读者”。甚至,苏素怀在孤独的夜晚渴望疯狂一把的情感和乘出租车的奇遇也很容易使人想到《洛丽塔》(那也是一个“在路上”的故事)。当然,池莉写出了当代一部分女知识分子渴望疯狂的情绪,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在这个“跟着感觉走”的年代里,连知识分子这个最具有理性的阶层也渴望品尝非理性的人生滋味了!
再看看海男,这位女作家说过:“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是我喜欢的书之一,这部经典著作在五十年代曾经成为禁书,直到如今,仍有一些国家将其视为‘描写色情的淫书’加以查禁。《洛丽塔》是一部机智而温情的书……是一部哀艳的书和色情的书,但里面的色情使我们面对着世界和人在肉体中震颤的活力和勇气,因而我认为纳博科夫身上肆意存在的这种狂热的哀伤确定了《洛丽塔》的命运。”⑨ 她的小说《我的情人们》、《花纹》、《私生活》、《情奴》、《情妇》、《妖娆罪》……都散发出浓厚的色情气息。她善于写男女之间紊乱的性爱关系,但常常流于一般化,而且笔力分散,缺乏独到的心理与哲理深度。
具有不同的创作风格的中国作家从《洛丽塔》得出的启迪也很不一样。这一现象本身就昭示了《洛丽塔》的丰富性。
《洛丽塔》与欲望叙事
首先值得注意的,也许是《洛丽塔》的“私人性”(因此也必然具有色情性)。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大潮必然导致了欲望的解放。在摆脱了“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枷锁以后,文学回归了表现人性的传统。如果说1980年代初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祖母绿》那样的爱情故事表现的是人性的美好与感伤,那么,卢勇祥的《黑玫瑰》那样的“伤痕文学”和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那样的“反思文学”则在控诉了黑暗政治扭曲人性的残暴的同时,也披露了人性的脆弱,并以比较大胆的笔触触及了欲望的主题。《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1985年发表以后曾经引发了一场关于“性文学”的争鸣。这场争鸣的结果是不少作家纷纷涉足“性文学”的创作——王安忆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岗上的世纪》、铁凝的《棉花垛》、《玫瑰门》、刘恒的《伏羲伏羲》、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罂粟之家》、莫言的《金发婴儿》……都是刻画性蒙昧、性放纵、性压抑直至乱伦的名篇。这些作品集中发表于1986到1988年两年间,正好与理论界的“弗洛伊德热”、报告文学中反映性观念变化的作品纷纷问世(如苏晓康的《阴阳大裂变》、麦天枢的《爱河横流》、戴晴的《性“开放”女子》等等)同时,与英国作家D.H.劳伦斯(Lawrence)《查太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亦译《恰特里夫人的情人》)中译本在1986年底的一度被查禁(也因此而得到更迅速的流传,并最终重新公开出版),共同折射出那个躁动年代的精神特质:思想开放、观念巨变、激情汹涌、欲望膨胀。在这样的背景和心态下,《洛丽塔》的四个中译本在1989年出版,就是水到渠成之事了。
解剖人性,而且是通过对情欲和性心理的刻画去揭示情的困惑、性的神秘、欲望的不由自主、命运的变幻莫测,已经成为198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的一个基本主题。“先锋小说”、“女性文学”、“新写实小说”、“新生代小说”等等热潮都在这里不期而遇。
同样是“性文学”,比起《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洛丽塔》显然少了那么一层浪漫的色彩,而多了一些罪感。纳博科夫虽然在小说中十分深入、细致地刻画了男主人公亨伯特对于洛丽塔的病态的激情(恋童癖倾向和乱伦行为),同时也经常点染他的自责与无奈——小说开篇就是这样的自白:“洛丽塔是我的生命之光,欲望之火,同时也是我的罪恶,我的灵魂。”亨伯特清楚地知道:“我一直粗心大意、卑鄙愚蠢。……我对这个可怜的性感少女的欲望竟然这么强烈。”而这强烈的欲望是与“一阵阵的内疚混杂在一起的”。还有:“无论我可以找到什么样的精神慰藉,无论提供给我什么样可以被光映现出的永恒真理,什么也不能使我的洛丽塔忘掉我强行使她遭受的那种罪恶的淫欲”。还有:“在我们反常、下流的同居生活中,我的墨守成规的洛丽塔渐渐清楚地明白:就连最悲惨痛苦的家庭生活也比乱伦的乌七八糟的生活要好。而这种生活结果却是我能给予这个无家可归的孩子最好的东西。”由此可见,“恶魔会对我进行引诱——随后加以阻挠,让我内心深处感到隐约的痛苦。”——在这些内心的痛苦自省中,亨伯特不得不面对“卑劣的自我”,常常发出“我卑鄙无耻,蛮横粗暴”的叹息。这样,《洛丽塔》就没有止于深刻的欲望剖析,而是将欲望与欲望带来的自责之间的痛苦纠缠刻画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作家还将亨伯特的困惑写出了某种典型意味——他还有这样奇特的自我辩护:“大多数渴望跟女孩子保持一种刺激的、发出美妙的呻吟的身体(而不一定是两性)关系的性罪犯,都是一些消极、无害、胆怯和机能不全的陌生人……我们不是性的恶魔!我们并不像大兵那样强奸妇女。我们是一些不快乐的、性情温和、目光哀怨的上流人士,智力非常平衡。可以在成年人面前控制自己的冲动,但只要有机会去抚摸一个性感少女,就准备少活上不少年去达到目的。”于是,亨伯特的痛苦就具有了上流社会男人们相似体验的典型意义。因此,《洛丽塔》就不仅“与20世纪50年代美国文化的主题息息相关”,⑩ 而且具有了人性批判的普遍意义。更可悲的是,洛丽塔是一个“幻象”,一个“想象出来的洛丽塔”。事实上,她既性感迷人,又粗俗放肆,而这样的缺憾也具有深广的社会背景:“现代的男女同校教育、青少年的风尚、营火旁的欢宴等已经叫她这样的姑娘不可救药地彻底堕落了。”这个迷人的少女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我是所有雄性动物的朋友。……思想和言行都十分肮脏。”她“把天真和欺诈、妩媚和粗俗、阴沉的愠怒和开朗的欢笑结合到了一起”。而这样一来,一个成年男人的苦苦追求和深深自责就与一个“坏女孩”的粗俗纠结在了一起,并由此呈现出了辛辣的讽刺意味。尽管纳博科夫本人一贯主张:“从一个长远的眼光来看,衡量一部小说的质量如何,最终要看它不能不具备诗道的精微与科学的直觉”,(11) 尽管他在小说创作与欣赏中“讨厌象征与寓意”,强调“《洛丽塔》并不带有道德说教”,(12) 但这并不能抹杀《洛丽塔》天然赋有的丰富人性意义与深刻社会意义(包括显而易见的道德寓意),因为“洛丽塔身上既有一股充满诱惑力的天真劲儿又有一种粗俗放肆的庸俗感,这两者混合在一起正代表着新文化所产生的一种典型的暧昧观念,这种观念很快就会变成反正统文化。……不但《洛丽塔》、《裸露的午餐》(Naked Lunch,1959)、《恰特里夫人的情人》,《北回归线》(Tropic of Cancer)和《南回归线》(Tropic of Capricorn)等许多在美国长期遭到禁止的作品很快就要发表了,而且许多流行文化也纷纷呈现出一种骇人听闻、狂热不安的特点”。(13)
这样,《洛丽塔》就具备了当代小说的两大要素:一是多角度揭示人生的复杂性,就像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指出的那样:“小说的精神是复杂的精神。每一部小说都对它的读者说:‘事情并不像你想的那样简单。’这是小说的永恒真谛”。(14) 在一个乱伦的故事中写出人性的困惑,写出理智的脆弱,写出期待与结果的巨大差别,还写出了对一些经典理论的有力质疑(例如书中多次出现的对弗洛伊德理论的讽刺),写出了爱情幻灭与现代教育、现代社会风尚之间的深刻联系,这样也就深刻揭示了生活的复杂性、哲理性。二是欲望叙事。现代社会是思想解放的社会,也是人欲横流的社会。这样,对于现代社会的文学描述就难免带上欲望的色彩。从《尤利西斯》到《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从亨利·米勒(Henry Miller)的《北回归线》到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的《夫妇们》(Couples),从纪德(Andre Gide)的《背德者》(The Immoralist)到杜拉(Marguerite.Duras)的《情人》(The Lover),从日本的“私小说”到郁达夫的《沉沦》,从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到中国的“新写实小说”,无论是欧美文学,还是东方文学,欲望(尤其是性或爱的欲望)都成了作家们探究人性、感悟人生、宣泄苦闷、回首往事的重要主题。可以说,在人类的文学发展史上,没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像二十世纪的文学这样强烈地渲染了人的欲望、深刻地剖析了人的欲望,并且为推动现代的世俗化生活进程发挥了不可小看的作用。在这方面,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态势尤其引人注目。在中国文学中,一方面有“诗无邪”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有“宫体诗”、《金瓶梅》那样张扬人欲的文学传统。有了“诗无邪”的圭臬,就必然会产生张扬人欲的文学观(以李贽的“人无不载道”说(15)、袁枚的“情所最先,莫如男女”说(16) 为代表);“诗无邪”的圭臬越是抑制张扬人欲的文学观,张扬人欲的文学观也越会更加强烈地表现自己。而被压抑的欲望一旦喷发出来,其迅猛燃烧的规模也会更加强劲。这,就是当代“性文学”的浪潮日益高涨的重要心理原因。进入1990年代以后,以贾平凹的《废都》、女性文学中的“身体写作”思潮、诗歌界的“下半身”写作为代表的“性文学”的此起彼伏、前赴后继、聚讼纷纭,都一再证明了这一点:在冲破了“禁欲”的牢笼以后,在与思想解放的浪潮相伴而行的人欲横流的洪水中,“性文学”已经成为世俗化时代的一个文化标志。虽然,《废都》的社会意义之深、之广又是“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所难以比拟的。
乱伦的故事
《洛丽塔》是一个乱伦的故事。小说中有这样的句子:“我怀着一种乱伦的激动,已经把洛丽塔看成我的孩子”,而洛丽塔也在与亨伯特试图找一个词去描述他们之间的关系时笑着说了一句:“那个词是乱伦”。乱伦,是人类最原始的恐惧之一。(17) 明知这一点,可仍然有许多乱伦的悲喜剧在不断上演,可见在原欲面前,人类的禁忌也那么苍白无力!
同样,当代中国作家也写出了不少乱伦的故事——早在“伤痕文学”中,就产生了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那样发生在姐弟之间的乱伦故事,那是因为政治原因造成、在双方并不知情的条件下发生的。但苏童发表于1987年的中篇小说《1934年的逃亡》则有一个指向人性神秘的主题:“无法解释天理人伦”,“枫杨树老家……充满倒错的伦理”:地主陈文治与贫农陈宝年有亲缘关系,后者以自己的妹妹与前者换了十亩水田;他们都有旺盛的性欲,又都对女长工蒋氏心怀淫欲;在陈宝年娶了蒋氏又遗弃了蒋氏以后,陈文治抢走了蒋氏。并在奸污了蒋氏以后将她投入了塘中。陈宝年的徒弟小瞎子则在陈宝年嫖妓时害死了他。从而攫取了陈宝年的竹器店……这样,苏童就写出了性欲的强大足以摧毁正常的人伦关系。这样对于纵欲的刻画写出了人的兽性,意义与《在小河那边》已判然迥异。再看发表于1988年的中篇小说《罂粟之家》,地主刘老侠“血气旺极而乱”。他看上了父亲的姨太太翠花花,就害死父亲,占有了翠花花;而翠花花后来又与长工陈茂有染,并为陈茂生下了儿子沉草;陈茂则在与翠花花生有一子(沉草)以后,又迷上了刘老侠的女儿、翠花花的仇人刘素子。陈茂后来闹革命,引起翠花花和刘素子的愤怒。刘素子唆使沉草杀了陈茂,然后与翠花花一起自焚。在这个错综复杂的故事中,人们的爱恨情仇与紊乱的性关系密切相关。还有发表于1989年的中篇小说《妻妾成群》,颂莲在成为陈佐千的妾以后对陈佐千的儿子飞浦产生了暧昧的情感,只是因为飞浦的懦弱而没能如愿……1991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米》的主人公五龙先后与米店老板的女儿织云、绮云发生了变态的性爱;他和绮云生下的一双儿女(米生和小碗)因为一点琐事也发生了哥哥杀了妹妹的悲剧;织云的儿子抱玉竟然勾搭上了米生的妻子雪巧,米生的弟弟柴生则因为知情而勒索雪巧,由此进而引发了米生和柴生的斗殴;柴生和他的妻子乃芳还盼着五龙早死,以便继承遗产……这一切都纷乱无比。欲望、仇恨,成为五龙与冯家姐妹一切悲剧的源泉。就这样,作为“先锋小说”与“新写实小说”代表作家的苏童便通过他的“枫杨树老家”冷酷地解剖了人性的阴暗、疯狂、残忍和迷惘。他笔下的主人公常常发出的“天问”是:“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五龙难以把握他的情欲”。
同样喜欢《洛丽塔》的叶兆言在1990年发表了一个特别的乱伦故事《去影》:一对师徒之间的乱伦故事。青工迟钦亭性格内向,处世腼腆,“像个女孩子”。他的师傅张英注意到,“男孩子相貌像他这样文静和漂亮实在不多见。”她处处照顾这个徒弟,出于一种“特殊感情”。在失恋以后,在有过偷窥姐姐和女工洗澡的经历以后,迟钦亭开始注意到张英。在激烈的情感混乱中,师徒之间发生了性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张英是在发现了徒弟的性苦闷以后,“出于拯救的伟大目的……一次次战胜徒弟的不良企图”。她认定“是因为她的无畏献身,有效阻止了迟钦亭的进一步堕落。……张英像块仁慈的大海绵,把蕴藏在徒弟身体内部的罪恶因素吸得一干二净,并且最迅速地进行了净化处理。……对于一个婚后生活极为和谐的女人来说,拯救了一个处在深渊边沿孤立无援的小伙子,张英觉得自己的行为无隙可击。”这样,一个乱伦的故事竟然阴错阳差与拯救的主题重合在了一起。这样,《去影》比起《洛丽塔》来,就多了一层亮色。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肯定性爱具有拯救人心的积极意义方面,王安忆已经探索在先了。《小城之恋》就通过蒙昧年代的性爱故事表达了这样的主题:“他们只有以自己的痛苦的经验拯救自己,他们只能自助!”尤其是女主人公,“经过情欲狂暴的洗涤,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干净,更纯洁,可是没有人能明白这一点,连她自己也不明白”。《荒山之恋》中也有这样的主题:“女的和男的在一块才自然,才是本性,才是天意。”在题为《面对自己》的创作谈中,王安忆也这么表达了自己的人生观与文学观:“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孤独地与自己作战,因此,他又不尽是孤独的。这一场战争是人类共同的……我的文学,就将是为这些个孤独的战场进行艰难而努力的串联与联络,互相提供消息,告诉人们,他们并不是孤独的,整个人类就在他们身后。”(18) 这样的思考与《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的主题也有相通之处。而叶兆言的《去影》则是在一个乱伦的故事中再次强调了性爱(哪怕是乱伦的性爱)的积极意味。
此外,刘恒的中篇小说《伏羲伏羲》讲述了一个侄儿与婶婶之间的性爱悲剧——那爱起于性欲,止于自尽。这样,就写出了乱伦对于生命的毁灭意味。陈染的中篇小说《与往事干杯》则讲述了一个具有传奇意味的、不自觉的乱伦错误:少女漾漾因为害怕父亲而在一个邻居男性长辈那里找到了朦胧的爱,后来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那个男人在异国的儿子发生了热烈的性爱。当她无意间发现了真相的时候,她体验到了“一股近乎于乱伦的情感”,并立刻斩断了情丝。因此,这个故事在隐隐中传达出了主人公对于乱伦的恐惧(那恐惧深深埋藏在人性的深处),同时也寄寓了命运捉弄人的主题。这两个故事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地写出了乱伦的悲剧,与上述苏童的作品息息相通,而与《去影》迥然不同。虽然刘恒、陈染都不曾谈到过《洛丽塔》的影响,但他们的上述作品在主题上与同时期苏童、叶兆言的相关作品的不谋而合(或者也许存在着彼此的影响),还是可以使人很自然地想起《洛丽塔》的。
但这里,有一点是值得强调的:无论上述中国作家是怎样写出了乱伦的悲剧或喜剧意义,但在两点上显然缺乏纳博科夫的大师气象:一是《洛丽塔》在渲染欲望时不太注重淫秽场面的细致刻画。相比之下,中国作家对于一些色情细节的刻画与渲染显然就难免有“媚俗”之嫌了。二是《洛丽塔》中经常闪现出的作家个性的锋芒——这锋芒就常常体现在作家将自己对于一些著名思想家和文学家的尖锐批评在小说中或隐晦、或直截了当地写了出来,从而显示了作家个人对于人性与文学的独特见解上。例如书中多次讽刺弗洛伊德的理论“杂乱无章”,关于亨伯特的设计“已经完全不是下意识的冲动,而成了对纯理论的欢乐的合理追求”的认识、关于亨伯特欣赏洛丽塔的性感之美“并非如同有些骗子和巫医所说的那样艺术天资是性的次要特征,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性不过是艺术的附属品。它是一种相当神秘的狂欢”的议论、关于“二十世纪中期有关孩子和父母之间关系的那些观念,已经深受精神分析领域喧嚷的充满学究气的冗长废话和标准化符号的污染”的看法,以及“不论精神治疗大夫在我后来‘抑郁消沉的时期’怎么蛮横地对我加以盘问,我还是找不到可以跟我少年时代的任何时刻联系起来的任何公认为真实的思慕”的讽刺……都与许多文艺理论家跟在弗洛伊德的理论后面亦步亦趋的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并且的确具有发人深省的力量。此外,书中还有几处或明或暗表达了作家对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梵高(Vincent Van Gogh)、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这些经典文学家、艺术家的非议,也颇有特色。这些批评无疑为这部描写世态人情的作品增添了相当浓厚的思想与学术的色彩。在这方面,《洛丽塔》与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的《地下室手记》(Notes from Underground)、钱钟书的《围城》、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魔山》(The Magic Mountain)、毛姆(Somerset Maugham)的《刀锋》(The Razor's Edge)、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作品一样,具有“智慧小说”的品格。而这样兼备思想锋芒、智慧光辉的小说,在当代中国的“性文学”中,显然缺乏。中国作家可以写出人性的深度,却常常写不出学理智慧的玄妙来。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中国的古典文学中,乱伦的故事并不少见。《水浒传》中潘金莲勾引武松的尝试(虽然最终没能得逞),《红楼梦》中贾珍与秦可卿的乱伦悲剧,都是尽人皆知的例子。然而,这些故事虽然可以证明中国自古就有乱伦的叙事,在全书中只是插曲。而《1934年的逃亡》、《罂粟之家》、《米》、《去影》、《伏羲伏羲》这样比较集中地刻画伦理的混乱、欲望的强烈的当代故事,也因此而不同于那些古典小说中的乱伦插曲了。相比之下,这些当代作品与《洛丽塔》在文学品格上显然更相似(虽然在气象和境界上有明显的高低之别):通过乱伦故事写出欲望的强大、理性的苍白、命运的莫测。
对《洛丽塔》的误读说明了什么?
现在,让我们回到王朔、池莉和海男对《洛丽塔》的认识上。
在王朔眼中,《洛丽塔》“里面没有社会的震动,全是个人的东西,写的是一个人的精神境界”。这话不无道理,但也失于偏颇。乍一看去,《洛丽塔》的社会性不那么明显,但正如美国学者指出的那样:“纳博科夫利用亨伯特这个人物对某种美国式的淫欲进行了讽刺。残酷无情而又无罪的亨伯特对他们所要得到的东西是直言不讳的。他关心的只是为得到那个姑娘又不被捉获而必须采取的那些策略。对美国野心的奇特的讽刺、把青春理想化以及亨伯特的无耻的个人主义”都表明了“纳博科夫戏谑了美国式的一心一意和实体感。”(19) 另一方面,“洛丽塔身上既有一股充满诱惑力的天真劲儿又有一种粗俗放肆的庸俗感,这两者混合在一起正代表着新文化所产生的一种典型的暧昧观念。这种观念很快就会变成反正统文化。”(20) 由此可见,《洛丽塔》的社会意义和文化底蕴是不应被忽略的。这意味着,即使是一个十分“个人化”的文学作品,也会或深或浅地赋有一定的社会性。而这一点,甚至是纳博科夫本人也好象故意无视的。因为在他看来:“通过阅读虚构小说了解一个国家、了解一个社会阶级或了解一个作家,这种观点是幼稚可笑的。”“每一个严肃的作家,手捧着他的已出版的这一本书或那一本书,心里永远觉得它是一个安慰。”(21) 这种偏颇的文学观念可能与纳博科夫厌倦政治的性格有关,但它不应该、也不可能抹杀《洛丽塔》乃至一切优秀文学作品的那个基本特点:个性(因此而与众不同)与社会性(因此才能为世人传阅)的水乳交融。说到王朔,他的作品的个性主要体现在他解构伪“崇高”的“新京味小说”上,而他的作品的社会性则相当宽广——从《橡皮人》、《顽主》写玩世不恭的青年心态到《动物凶猛》那样相当特别的“文革”回忆,从《我是你爸爸》那样探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个“五四”时期就提出来的老问题再到《许爷》那样描写失意者魂断异国的悲凉故事,甚至连《过把瘾就死》这样的看似十分纯粹的爱情故事也写出了当今青年在婚恋生活中的躁动情绪……。
还有池莉关于“好的小说首先应该非常感性,它应该诱惑读者,刺激读者,使读者在小说的暗示下,体味他自己的生命经验,发挥他自己的想象能力,或者说提高他自己对世界的判别能力”以及“真正的名著都应该是畅销的”的说法,也值得商榷。“感性”固然是小说的基本特点,但因此忽略了理性、智慧性也显然失之片面。池莉作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因为善于生动描写小市民的烦恼人生而产生过“轰动效应”。然而,恰恰是因为反反复复地描写那些“一地鸡毛”的琐碎生活(一个十分明显的例子是,2002年的《有了快感你就喊》几乎就是1987年的成名作《烦恼人生》的重写,只不过主人公的身份变了),难免给人以自我重复的印象。评论家陈思和在1990年就注意到,同为“新写实小说”,方方发表于1987年的《风景》“价值远在池莉的小说之上”,就因为《风景》“证明了野蛮也是表现都市生活的尺度”,“强调生存现状的既定性,发掘生存本身的意义而不涉及其价值评价”,(22) 这样就显出了《风景》的理性特色。由此可见,小说应该有“感性”,但优秀的作家是不应该止于“感性”的。至于说到“真正的名著都应该是畅销的”,其实也不尽然。许多名著都遭遇过被冷落、甚至被禁的厄运。而许多畅销书也已被时间证明了是过眼云烟。
而海男的许多性爱故事则是在刻画男男女女之间开放的、混乱的爱情故事上做文章。以出版于1994年的长篇小说《我的情人们》为例,小说的题记是:“这部小说在私人的意义上献给那些爱过我、并且为我所爱的先生们”。书中介绍的女主人公苏修的“真实情人”就有十六个(包括一名德国青年),此外还有“幻影情人”八名。海男在谈到这部作品时说过:“《我的情人们》也许是一部真实的故事,也许是一部虚构的故事”,女主人公“生活在他们(那些情人们)之中,她深爱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23) 小说写出了一个多情女青年的复杂情感生活,却因为写得太随意而流于松散、肤浅,缺乏应有的心理与哲理深度。那些男人们好像道具一样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女主人公在他们之间的自由穿行也缺乏必要的心理转换剖析。海男没能将自己的爱情体验写出心理与哲理深度,与她只将《洛丽塔》看成了“一部哀艳的书和色情的书”,而没读出其中的社会与心理的深厚底蕴显然有关。
王朔和池莉、海男对《洛丽塔》的“误读”在当代中国作家中是很有代表性的:作家们常常在阅读外国文学名著时带入了自己比较鲜明的个性眼光,各取所需,直至只取最合自己口味的一点,却因此而忽略了其他——忽略了外国文学名著的丰富性、复杂性。这样的“洋为中用”其实往往只是以外国文学名著作为了自己写作风格的“旁证”。因此,这样的“洋为中用”常常也妨碍了自己走向更阔大的文学境界。如此说来,对于作家们来说,如何不断深化自己欣赏外国文学名著的目光,怎样努力写出既得外国名著神韵、又有自己个性的力作也就成了不可小看的问题了。
注释:
① 引自[美]萨克文·伯科维奇主编:《剑桥美国文学史》[第七卷,散文作品,1940—199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6—218页。
② 赵一凡:《后现代主义探幽》,《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
③ 《苏童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95—197页。
④ 张英、黄敏:《50岁〈洛丽塔〉,11张中国脸》,《南方周末》2006年3月16日。
⑤ 《我是王朔》,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94页。
⑥ 《欣赏与摈斥》,《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
⑦ 《我是王朔》,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98—99页。
⑧ 《最是妖娆醉人时》,《世界文学》2002年第2期。
⑨ 《我的阅读及语词回顾》,引自邱华栋、洪烛主编:《一代人的文学偶像》,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256页。
⑩ [美]萨克文·伯科维奇主编:《剑桥美国文学史》[第七卷,散文作品,1940—199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5页。
(11) 《优秀读者与优秀作家》,《文学讲稿》,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6页。
(12) 《关于一本题名〈洛丽塔〉的书》,见《洛丽塔》,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499—500页。
(13) [美]萨克文·伯科维奇主编:《剑桥美国文学史》[第七卷,散文作品,1940—199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页。
(14) 《被忽视的塞万提斯的遗产》,《小说的艺术》,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
(15) 《藏书》卷三二《德业儒臣前论》,引自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066页。
(16) 《小仓山房文集·答蕺园论诗书》,引自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页。
(17) 参见[奥]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第一章“乱伦的畏惧”,台湾志文出版社版。
(18) 《文学报》,1987年1月1日。
(19) [美]丹尼尔·霍夫曼主编:《美国当代文学》(下),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370—371页。
(20) [美]萨克文·伯科维奇主编:《剑桥美国文学史》[第七卷,散文作品,1940—199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页。
(21) 《关于一本题名〈洛丽塔〉的书》,见《洛丽塔》,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501—502页。
(22) 《自然主义与生存意识》,《马蹄声声碎》,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103—104页。
(23) 引自刘以林:《构思我们自己的宗教》,《我的情人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6—7页。
标签:洛丽塔论文; 纳博科夫论文; 1934年的逃亡论文; 文学论文; 中国作家论文; 小说论文; 人性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罂粟之家论文; 伏羲伏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