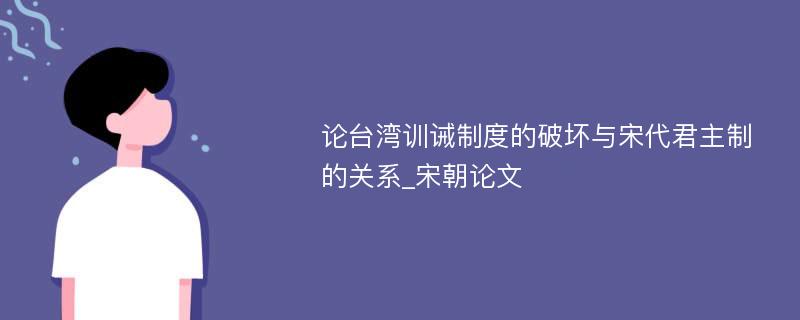
宋代台谏系统的破坏与君权相权之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君权论文,宋代论文,关系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宋代中央监察系统的台谏,与君权、相权并举,在君主官僚政治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之地位,并颇似近代西方的三权分立。但它不可能成长为近代意义上的三权制衡的权力结构。这是相权寻机干预、舞弊破坏、君权常常失误的必然结果,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应归结予君主专制制度。所以不能指望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出现真正的三权制衡结构和权力系统。
宋人往往把中央监察系统的台谏,与君主、宰执三者并举,揭示出台谏系统在宋代君主官僚政体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是汉唐、明清所无法比肩的。“朝廷有大政事,而台谏得以议其不然;人主有小过失,而台谏得以救其弗逮;百官有大奸慝,而台谏得以斥其所为”〔1〕。宋人的这段议论表明:宋代君主官僚政体已有意识地将台谏官僚圈提升进中枢权力结构中,从而形成君主、宰相、台谏之间分权制衡的政治格局。三权分立是近代西方社会的产物。不过,在宋代封建君主政体的母腹中,人们似乎也能探测到这一胎儿。关键在于,这一胎儿能否由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母腹顺利娩出?本文试图从宋代台谏系统的破坏与君权、相权之关系,对此,略作论析。
一、令人费解的历史表象
元修《宋史》时指出:“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2〕。然而, 纵观三百余年宋代台谏系统的制度规定及其运作过程,却呈现出种种令人费解的历史表象。举其要者,大体有三:
其一,相对健全完善的制度和程序不断地被蔑弃和破坏。
宋代台谏制度包括选任、回避、言事、监控等方面的内容。在选任制度上,宋代确立了侍从荐举、宰执不预、君主亲擢的遴选原则及相应程序。在回避制度上,宋代不仅强调了台谏对宰执的亲嫌回避,也完善了台谏系统内部的职事回避原则。在言事制度上的健全程度更令人称道:宋代台谏官不仅对台谏长官与同僚、而且对相权与君权都享有监察独立的特许权;而风闻言事的原则、公文关报的制度、取索公事的规定和出巡采访的途径,则确保了台谏监察的信息来源;在言事方式上,宋代不仅对上疏与面奏这两种基本言事方式建立了一般程序,还确认了在特定情势下,台谏可采用副本与露章等特殊的章奏形式及合班、留班、伏阁等非常的廷奏方法向君主建言。在对台谏系统的监控方面,宋代君主不仅通过戒励型、指令型和宣谕型诏令对台谏系统进行协调监控,还设月课、御宝印纸、台谏章奏簿对言事官实施定期的、量化的考绩,同时对台谏官的升黜奖惩也有一整套有章可循的激励、调节与惩戒机制。〔3〕
总之,如果仅从制度层面而言,宋代台谏制度尽管还有疏误弊陋处,但毕竟以其显著的合理性、系统性和严密性,大大超越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其他朝代,充分体现了封建君主政体在监察制度上所能达到的成熟程度。
然而,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宋代台谏制度的既定原则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蔑弃和践踏。即以选任制度中的君主亲擢制而言,原应是宋朝历代君臣的共识,但是,靖康初年的钦宗,秦桧死后的高宗和绍定亲政时的理宗,都分别重申“立为定制”、“以革前弊”,〔4〕这反证其废而复行,行而复废,已几经折腾了。旨在“防有司不能尽公”的台谏与宰执的职事回避制度的命运亦复如此,南宋洪迈即指出:“此制亦不能常常恪守”〔5〕。在言事制度方面,风闻言事原则形同虚设的现象,在仁、神、孝宗朝都一再出现〔6〕;而台谏言事的法定程序也屡成空文,台谏上章入而不报,台谏面奏累月不见,在哲宗以后更是司空见惯的。至于对台谏的监控,仁宗时始设的台谏章奏簿实属奇绩,但元祐、靖康与乾道时却各有臣僚建请创置,个中正透露出台谏章奏簿置废无常的消息。毋庸赘言,宋代台谏制度中被蔑弃破坏的原则与程序还远不止此。
诚然,制度史研究应该区别制度的条文规定和实际运作的差异,然而像宋代台谏系统这样,制度上相对完善,运作中却屡遭破坏的现象,倒是既令人困惑,更发人深思的。
其二,台谏系统运作的历史轨迹呈现出时振时衰、振衰不定的波状曲线。
宋初,太祖、太宗两朝对台谏制度未甚注意。真宗始着手台谏制度的整顿,天禧元年(1017)则置御史谏官的诏书,是宋代台谏系统走上新轨的标志。经真、仁两朝的制度完善,台谏系统进入较佳运行状态,故宋人说:“台谏郑爱职在国初则轻,在仁宗之时则重;在国初则为具员,在仁宗之时则为振职”〔7〕。英、神、哲三朝,台谏系统的运转基本上尚属正常,但君权、相权等干扰台谏系统运作的破坏因素已由潜在趋向表层。徽宗即位,台谏系统在短期正常后,即因蔡京弄权、徽宗昏愦而陷入危机。其后直至宁宗即位以前,虽在靖康初年、高宗初期与孝宗前期几度出现过令人一振的气象,总体上表现出振衰不定的波动状态。从宁宗即位起迄宋末,虽有理宗绍定更化时的一度振作,却只是死水微澜,台谏系统名存实亡。纵观宋代台谏系统运作的历史过程,振衰不定是其一大特点。
前已指出,宋代台谏系统业已形成了相对健全的制度与程序,按这套制度与程序行事,仁宗朝确实也出现过台谏系统运作的黄金时期。然而,好景不长,盛时难再。在台谏系统一蹶不振的南宋后期,不少史家与学者对这一现象不乏痛惜、针砭和感慨,却把根本原因的探究留给了后人。
其三,在宋代台谏系统遭受破坏的过程中,君权与相权的恶劣作用错杂纠葛,令人剪不断、理还乱。
这一现象与以上两种历史表象交织在一起,更容易导致有关论点的对立。究竟是相权还是君权起着根本的先决性的作用?随着这一问题的解决,其他两种矛盾现象也将迎刃而解。
二、相权对宋代台谏系统的破坏
在宋代分权制衡结构中,台谏代表了中央监察权,宰执所代表的相权则是中央行政权。依据政治学原理:行政权在受到监察权监督时,天然地具有反制衡的离心倾向。总是试图凌驾或实际凌驾于监察权之上。宋代相权与台谏系统监察权之间的关系也不例外。其反制衡的一般方式一为合法地利用制度的疏漏,一为公然地无视制度的规定。其具体手法如引用亲故、荐举软懦,台谏虚位,阙员不补,寻隙伺机、罢黜异己,名为迁除、实夺言官等,不一而足。
至于权相,鉴于台谏系统在中枢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深知为了专擅政局、扼制舆论、排斥异己,不能仅凭君主宠信,还必须使台谏完全成为相权的喉舌与鹰犬。故而宋代权相从蔡京到贾似道无不把操纵台谏系统视为擅权专政的至关重要的步骤。秦桧弄权的第一步即是“择人为台谏”,韩侂胄干政得手也得力于“唯有用台谏”〔8〕。继秦桧为相的汤思退效颦未成的根本原因就是“台谏不由其门”〔9〕。正反两方面例证充分说明:控制台谏系统在一般宰执通向权相之路上起着事关成败的作用。除了变本加厉地袭用相权对台谏系统反制衡的一般手法,宋代权相各有其独自的伎俩。
其一,假借御笔,移易台谏。
这一手段为蔡京,韩侂胄所惯用。蔡京事无巨细都假托御笔施行,御笔自然也成为其除罢言官、控制台谏的护身符。韩侂胄袭用蔡京故伎,“台谏给舍,屡有更易”,“御笔寖多,事势烜赫”〔10〕。御笔内批本是保证君主亲擢或监控台谏的手段,权相轻而易举地拉过大旗作为操纵台谏系统的虎皮。
其二,弹去执政,补以言官。
这一一箭双雕的手法是秦桧发明的。《宋宰辅编年录》卷16引《遗史》揭穿其用心:“时执政皆由秦桧进,少忤桧意,则台谏探桧意而弹击之,桧或谕意台谏使言其罪。既已罢去,则继有章疏夺其职,或犹未已,又有章疏,然后责偏州安置或居住。于是为执政者皆惴惴然备去计,不以为荣。而遭罢斥去,亦谓份当如此耳。名器于是轻矣。”这样,秦桧便即使执政不可能进而觊觎其独揽的相权,又能将执政显位作为网罗台谏的诱饵。他独相十七年,执政如走马灯似地更换了二十八人,其中“由中丞、谏议而升者凡十有二人”〔11〕。唆使言官弹去执政而补其空阙,而“台谏之权在桧矣”〔12〕。
其三,每除言路,必兼经筵。
此术由秦桧首创而为韩侂胄仿效。由于经筵官能经常侍讲君侧,权相便利用其职任之便达到交通台谏、窥伺君主的目的。秦桧让其兄、子相继任职经筵,传导风旨给那些兼任讲读的台谏官,故往往“经筵退,弹文即上”〔13〕。秦桧死后,这种兼职一度减少,韩侂胄干政复用秦桧故伎,重演台谏官无不兼职,经筵的场面。
其四,检审副封,代拟言章。
采用此法的是史弥远、贾似道。副封,即台谏将言章副本封呈权相,供其审查。史、贾竟觉得副封还不够直截了当,史弥远专政弹章谏草干脆由“府第付出全文”〔14〕,贾似道弄权,言官奏稿“全疏出于似道”〔15〕,台谏完全被权相玩弄于股掌之间。
面对权相对台谏系统肆无忌惮的破坏,宋代台谏官不外乎面临以下三种选择:第一种是追逐势利、丧失名节者,则恬然“以公朝之执法,为私门之吠犬”〔16〕;第二种是廉耻尚存、气节不足者,则“平居未尝立异,遇事不敢尽言”〔17〕。第三种是忠于职守、敢于谏诤者,轻则罢黜言职,重则“随陷其祸”〔18〕。也许正是基于上述种种历史表象,人们往往把宋代台谏系统的欹覆与破坏归咎于相权。
三、君权对宋代台谏系统的破坏
宋代君主对台谏的态度始终处于一种矛盾心态中:为着政权的长治久安,他们认识到必须重视台谏系统的作用与价值,因而多以好谏纳言为标榜;但从个人的好恶予夺出发,君主又力图摆脱台谏系统的监督制衡,在台谏议论违背其意志欲望时尤其如此。即便对台谏制度进行全面整顿的真宗,在台谏“多所论列”时,也“颇厌其数”〔19〕。好谏从谏与拒谏玩谏,两种看似对立的态度与行为就是这样矛盾地存于宋代君主的身上。宋代君主拒谏玩谏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追究风闻,责令分析。
作为宋代台谏言事制度之一的风闻言事原则,指的是台谏言事允许事实小有出入,即便君主也不能追究其风闻来源,但是,君主在对台谏论谏表示不满、反感时,便以个人意志责令台谏“分析”章奏,追诘台谏消息来源。这种分析,表面上似乎是君主对台谏论列的人或事感到不详确或不妥当的情况下令台谏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实际上体现了君权对台谏言事权的压制,势必导致台谏官迎合君主的好恶,进而使宋代业已确立的台谏对君权的独立言事原则形同虚设。“才有失实,即坐左迁”的言官〔20〕,两宋大有人在。在君主追究风闻、责令分析的高压下,台谏官只能或承旨言事,或杜口缄默,或摭拾细碎。由于“亲旧可得其详,庶免风闻之误”,既无承旨言事有失风节之嫌,又无杜口缄默难以塞责之苦,台谏官便多搜寻亲故琐事作为论奏题目,以至南宋绍兴后即有民谚说:“宁逢恶宾,莫逢故人”〔21〕。君主对台谏言事制度的践踏与破坏,亦由此可见。
其二,无所可否,不报不行。
这是宋代君主拒谏玩谏时对台谏章疏采用的惯伎。宋代对台谏奏稿,在制度上原就规定了合理反馈的程序,但君主却视制度为虚设,让台谏章奏如泥牛入海。早在元祐更化时,右正言刘安世论事连上二十疏,已遭“一切留中,无所可否”的命运〔22〕。南宋高宗以后,台谏“连章累牍,入而不报”〔23〕,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即使号称“小元祐”的端平更化时期,理宗对言官奏札仍然是“但有报可之虚文,曾无施行之实事,甚者不唯不见之施行,亦且不闻于报可”〔24〕,则其他时期可以想见。台谏言事制度中的面对制,也因君主玩忽而经常废弛不行。元祐时,台谏官已“百余日不得一至法座之前”〔25〕。南宋光宗以后,台谏面奏,更是“逾月而不见”〔26〕,反映出君主破坏台谏言事制度后,使言事官处于不事论谏、怠于职守的状态。
其三,横加罢黜,伪予优迁。
君主一旦拒谏,便往往滥用君权,罢黜台谏。仁宗时的谏废皇后,英宗时的争辩濮议,都有大批台谏因君主私意而遭黜逐。及至理宗,言官“易置不常,殆如传舍”〔27〕。为了避免由于横黜言官而背上拒谏恶名,君主们又玩弄起“阳饵以美迁,阴夺其言责”的手法。这一现象神、哲之际已有所用,光宗以后则成为君主玩谏的故伎,台谏“稍稍伉直者,多不得久于其职,大率优迁其官以去之”,以至正直之士痛诋其为“近世最弊之法”〔28〕。君主这一做法对台谏官名节与正气的打击摧残尤为严重,在名节颓然扫地、正气荡然无存的同时,代之而起的是另一种追求:“台谏之官,专为仕途之捷径”〔29〕。
其四,宣谕节贴,回护调停。
在宋代对台谏系统的监控机制中,君权保留了宣谕的手段。所谓宣谕,就是君主出于权宜,对例应属于台谏监察范围的个别人、事,颁下表明自己倾向、处置的特殊的谕旨。这是宋代台谏系统在制度层面上的疏漏,为君主以个人意志来干预台谏系统的正常运行留下了余地。不过,大体说来,哲宗以前,宣谕还较少君命至上的味道,常表现出与台谏调节、协商的倾向,台谏不满宣谕继续论谏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徽宗以后,宣谕成为君主拒谏玩谏的惯用手法,降至理宗,“权凶逸罚,交章请(论)罪,则谕止之;扈带私授,抗疏论列,则谕止之”〔30〕,宣谕之滥之弊,一至于此。所谓节帖,就是君主本人或宣谕言官对弹章谏草做删节更换的手脚。此举由高宗首开先例,到理宗时台谏言章更是“每加节贴而文理不通”〔31〕。“事有窒碍则节帖付出,情有嫌疑则调停寝行”〔32〕,在理宗朝成了家常便饭。君主的宣谕节帖、回护调停,使台谏相对于君权的独立言事原则成为一纸空文,而台谏系统则沦为君权随手玩弄的摆设与恣意掩饰的屏风,其“精神风采亦日销月铄而已矣”〔33〕!
由于君主自觉、不自觉的拒谏与玩谏,台谏系统名存实亡的命运是无可避免的。
四、对君权相权破坏宋代台谏系统的综合分析
以上从静态角度分别论述了相权与君权对台谏系统破坏的不同手法。不言而喻,两者的作用都是恶劣的。倘若从历史表象来看,相权所扮演的角色似乎更令人注目。其表现为二:其一,相权对台谏系统的程度不一的反制衡倾向,无论是权相专政时期,还是非权相执政时期,基本上都是存在的。这正如王应麟指出的:“台谏为宰相私人,权在下,则助其搏噬以张其威;权在上,则共为蔽蒙以掩其奸”〔34〕。其二,相权对台谏系统破坏的恶果最显而易见,往往导致权相甚至权奸之相的专政,蔡京、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的擅权祸国都与此有关,此即王夫之所说的“巨奸且托台谏以登庸”〔35〕。或鉴于此,宋人几无例外地将台谏系统的破坏归罪于相权。
但是,倘若把君权、相权与台谏监察权所构成的分权制衡的政治格局放到封建君主政体的大系统中,并将君权、相权对台谏系统的破坏作综合、连动的考察,即可发觉上述见解显然是肤浅的,不够到位的。只消将相权对台谏系统的反制衡与君权的失误结合起来分析,不难发现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君权与相权在对台谏的反制衡上不仅沆瀣一气,而且总是君行臣效的。
且以台谏阙员为例。据陈东揭露,蔡京为相,“动以数年不除一谏官,意欲掩上皇从谏之圣,以绝天下议己之言”〔36〕,似乎徽宗是从谏圣主,问题都出在蔡京身上。实际上台谏阙员,建制废驰,是君相有目共睹的,蔡京所为显然是得到默许认可的。而台谏阙员不补的情况,早从仁宗起就累朝不绝。皇上一旦感到台谏监察权对君权的制衡超过自己所能接受程度,他们也会采用包括台谏虚员等手法来拒谏玩谏。
前面所述的君主在禁内设置的台谏章奏簿几经废置的事实,也是这一方面的例证之一。与君主所置台谏章奏簿相对应,宋代中书亦设台谏言事簿,作为中书岁终考绩台谏官的依据。其初置于真宗景德时,其后,仁宗至和二年,神宗元丰三年复下令重置;宋室南渡,高宗建炎二年诏中书置簿后,孝宗乾道二年、宁宗庆元元年、度宗咸淳元年,又一而再、再而三地颁诏命中书重设台谏言事簿。由此可见,其废置不常的命运一如君主禁内的台谏章奏簿。显然,没有君主自废制度的前例,相权是断不敢擅作主张将中书的台谏言事簿弃之如敝屣的。这种上行下效的反制衡行径,必然导致台谏官责任心与正义感的淡薄,赞成台谏系统的形同虚设。
其二,由于君权的放任和失控,为相权利用台谏制度的固有弊漏,进而操纵台谏系统,开放了合法的通道。
在宋代台谏选任制度中,虽以宰执不预的原则剥夺了宰执荐举言官的权力,却又保留了宰执进拟制,在制度层面上为相权染指台谏官的入选留下了合法的边门。进拟制使宰执有权“具可充台谏官人姓名奏入”〔37〕。虽然宰执进拟原规定两人以上集体进拟,然而,当君主对某一宰执特别宠信时,便特许其单独进拟。这样,由于君权的放任失控,宰执共同进拟便与宰执个人密荐毫无区别了。司马光、秦桧都因人主特旨密启过台谏人选,韩侂胄擅权,“名为密启,实出己意”〔38〕。撇开上述三人密启的用意及后果不论,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大大超越了制度弊漏的许可范围,而他们之所以能如此做,无不是人君纵容的结果。因而,秦、韩之类权相私引台谏、豢为鹰犬,从根本上说,实是君权放纵所造成的。
在对台谏官升黜进退上,宋代在原则上虽也规定宰执不得与闻,但因言官迁调黜罢往往“令中书勘令取旨”〔39〕,相权得以合法地拥有进退台谏的部分权力。权相秦桧以私意移易台谏,还堂而皇之地对高宗声称:“进退百官,臣之职也。倘以臣黜陟不公,愿先去位”〔40〕。由于相权攫取台谏迁黜权较干预台谏选任权更为容易,故得以恣行其奸。他们往往是玩弄明为迁除、阴夺言职的伎俩。当然,相权之所以拥有这部分权力,也还是由君权分割的结果。而君权之所以不把台谏的迁调升黜权全部收归己有,其根本思路与保留宰执进拟制是同出一辙的。然而,由于君权的放任与失误,相权是完全有机会有可能将制度上的合法空子变为冲决整个台谏系统的突破口的。
总之,宋代台谏系统的确存在制度层面上的弊陋,但是,第一,这种宋人都已直觉到的制度上的弊陋却是封建君主制下无法克服的,因而这种留有弊陋的制度是封建君主政体所能作出的最好选择;第二,这种制度上的弊陋,由于君主明智昏庸等个人因素的控制或放任,再加上宰相忠正奸佞等个人德行的参数,从而使宋代台谏系统的运作出现振衰不定的波状曲线状态。
其三,君权自坏台谏制度,为相权控制、操纵、破坏、倾覆台谏系统开启了方便之门。
在台谏选任制度上,只要君权不失控,还是有其制度合理性的。然而,率先自毁其制的却是君权自身。神宗出自对王安石的倚任,首开“使大臣自择台谏官”的先例〔41〕。元祐宰相司马光、吕公著与隆兴宰相张浚也都分别奉诏荐举过台谏官。及至高宗,干脆命秦桧将台谏人选“呼至都堂”,“与之议论”〔42〕,然后决定除授与否。君主对台谏选任制的有关规定置若罔闻,使台谏监察权沦为相权的喉舌与附庸,完全是题中应有之义。
台谏职事回避制度的命运亦复如此,最先自溃堤防的仍是君主自己。例如,宰执亲戚不得选充言官的规制早在治平时就由英宗特旨破例。又如现任宰执曾任举主之人不得出任台谏的条文,早在仁宗朝就遭到来自君权的蔑视。再如台谏兼权职事不能是宰相属官的原则,也因君主的特旨徒为空文等等。君主率先破例,这就为后来秦桧、韩侂胄之流交通台谏窥伺君主提供了机会。就这样,台谏对宰执的职事回避的主要内容几乎都因君权本身的破坏而废弃殆尽了。
正是由于君主本人的随心所欲与君权自身的失误失控,相权才有可能公然无视与恣意践踏台谏系统的制度规定。
总之,综合考察君权、相权对宋代台谏系统破坏的动态过程,即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君权是这种破坏的始作俑者,而相权则是尾随其后的推波助澜、兴风作浪者。
五、君权失误是宋代台谏系统破坏的根本原因
现代政治学认为:一种相对完善的政治制度一经确立,只要严格按规制、程序运行,虽不能达到人们期望的最合理程度,却可防止出现人们担忧的最坏结局。这一原理也可移用来分析宋代台谏系统。当君主、宰执、台谏都自觉而坚决按照制度与程序规定维护台谏监察权时,台谏系统就能正常运作,分权制衡的政治格局也能基本维持,仁宗时期是一度出现过这种局面的。这种局面虽然离近代西方三权分立制衡的合理性还不能同日而语,却可以防止君权专断、相权坐大等封建统治危机的出现。
但是,宋代由台谏、宰执、君主构成的分权制衡格局先天地隐伏着产夭折的遗传基因,这种基因是从封建君主政体的胎盘上得来的。就宋代分权制衡态势而言,台谏系统享有的是监察权,相权拥有的是行政权,两者大体上能与近代西方三权分立中的监察、行政权相对应,唯有君权属于例外。在封建君主制下,君主不但握有最高立法权,而且握有最高行政权,即使相权在法理上仍应听命于君权。不仅如此,台谏所代表的中央监察权最终也不是超然独立的,仍必须对君权负责,宋人常说的“台谏者,陛下之台谏”〔43〕,形象深刻地揭明这点。因此,君权在宋代分权制衡格局中便处于一种自相矛盾的地位:一方面必须自觉地将自己放在制衡格局的三鼎足之一的位置上,一方面又必须成功地承担起维持这一制衡格局的最高主宰的使命。只有君权把以上双重角色都处理好,分权制衡才能安然维持,台谏系统才能正常运作。然而,君权享有的那部分最高行政权,按政治学原理而言,也天然地具有反制衡的倾向,也总是试图凌驾或实际凌驾于台谏监察权之上。不仅如此,君权所拥有的立法权也缺乏应有的权力制约,在封建君主制下诏敕就是法律,仅就立法权这点而言,君权也天然地要求摆脱分权制衡的羁绊。近代西方君主制国家的分权制衡是以虚君为其必要代价的,而这在中国封建君主制下是绝无可能的天方夜谭。因此,由君权、相权、台谏监察权构成的宋代分权制衡的政治格局,从其形成之日起就潜伏着君权畸重的失衡因素。
历史在这里玩弄着悖论。宋代台谏系统在制度上的健全与地位上的上升,其目的是为了制衡相权与君权,使封建君主专制政权能长治久安,而封建君主制又必然地规定君权为这一制衡结构的最高主宰者和唯一调控者。这样,以分权制衡为其初衷的政治结构最终仍不可避免地滑入君主独裁的怪圈。在封建君主制下奢望跳出这一怪圈是不可能的,惟一可能的只有指望君主个人的贤明公正的主宰与调节,使台谏系统运作得较为正常些,制衡结构维持得较为长久些。但是,世袭制下贤君明主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这就预示着宋代台谏系统与制衡结构的历史命运。
于是,便可以发现这样的历史现象:当君权自觉接受与坚决维护台谏监察权,并成功调控由君主、宰执、台谏构成的制衡结构时,台谏系统便运作正常,制衡局面能基本维持;反之,台谏系统便名存实亡,制衡结构便欹侧倾覆。宋代台谏系统在徽宗以后虽屡遭权相破坏,却仍能因其后君主的重视而几度“振扬风采,正气稍伸”〔44〕,台谏系统运作进程中之所以出现时振时衰、振衰不定的曲线状态,其根本原因盖在于此。
另一方面,既然君权是分权制衡权力结构的最高主宰者和唯一调控者,而在封建君主制下,“法者,天子之法也”〔45〕,因此君主完全可凭藉君权更变或废弃包括台谏制度在内的制度法令,使业已相对健全的台谏系统的制度、程序行废无常或徒为空文。如果说,徽宗以前,台谏、封驳制对君主擅改典制还有相对的制约作用,那么,自徽宗风行御笔、取代诏旨后,君权受制衡的情势因之一变。〔46〕“崇宁四年,中书奉行御笔,时蔡京欲行其私,意恐三省、台谏多有驳难,故请直以御笔付有司,其或阻格,则以违制罪之”,大观三年,进而规定违背御笔“以大不慕认”〔47〕。御笔之行,是宋代君权恶性膨胀的一个标志。自此以后,由于台谏、封驳对君权的制约力被釜底抽薪了,因而君主径行御笔变乱制度便畅通无阻了。不仅如此,由于御笔可以不由中书共议、给舍封驳、台谏执奏,相权在操纵台谏系统、破坏制衡结构、通向权相之路上也必然千方百计地利用君权的放任,借助御笔的权威,蔡京、韩侂胄便是这样做的。
由于封建君主制造成宋代分权制衡权力结构的实质仍是君权独尊,因而这是一种不稳定结构,随时会因君权的失误而导致制衡结构的换衡和台谏系统的破坏,在这种情势下,相权确实是最有可能僭位成为业已失衡结构的主导性权力的,并进而把这种失衡趋势与破坏局面推向极端。因此,在历史表象上,相权往往表现为制衡结构倾覆、台谏系统破坏的最严重的因素。然而,问题的症结在于:相权之所以能够僭夺制衡结构的主导权,控制台谏系统的监察权,归根结底是以君主对制衡态势的调节失控为其前提的。由此可见,分权制衡的欹侧与台谏系统的破坏,其始初的、根本的原因必须归咎于君主专制下君权的失误。而在世袭君主制下,这种君权的失误可能避免于一事、一时、或一朝,而不可能历朝诸帝都长久如此。因此,宋代由台谏、宰执、君主组成的分权制衡的权力结构,只要有一个既身处其中又主宰其上的君权存在,便绝无可能孕育出近代意义上的真正的分权制衡的权力结构来。在封建君主专制的桎梏下,其命运只能是胎死腹中。
注释:
〔1〕《东塘集》卷8,《论台谏当伸其气》。
〔2〕《宋史》卷390,《论赞》。
〔3〕关于宋代台谏制度可参见笔者《宋代言官选任制度述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宋史研究论文集》)与《宋代台谏言事制度述论》(台北《大陆杂志》89卷5期,1994年11月15日出版)。
〔4〕《宋会要》职官55之16、21。《后村大全集》卷63 《陈尧道监察御史(制)》。
〔5〕《容斋随笔·三笔》卷14,《亲除谏官》。
〔6〕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称《长编》)卷169皇祐二年九月辛亥。
〔7〕《宋史全文》卷7引吕中《大事记》。
〔8〕《宋史》卷380《勾龙如渊传》卷474《韩侂胄传》。
〔9〕《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下称《要录》)卷187绍兴三十年十一月庚子。
〔10〕《絜斋集》卷13《黄公行状》。
〔11〕《宋史》卷473《秦桧传》。
〔12〕《要录》卷151绍兴十四年五月乙丑。
〔13〕《老学庵笔记》卷6。
〔14〕《鹤林集》卷18《应诏封事》。
〔15〕〔16〕《黄氏日抄古今纪要逸编》。
〔17〕《宋史》卷408《陈宓传》。
〔18〕《宋史》卷473《黄潜善传》。
〔19〕《长编》卷91天禧二年三月甲寅。
〔20〕《范忠宣公奏议》卷上《奏论责君子太重奖小人太深》。
〔21〕《宋稗类钞》卷2《谗险》。
〔22〕《长编》卷417元祐三年十一月月末条。
〔23〕《絜斋集》卷13《黄公行状》。
〔24〕《清献集》卷8《殿院奏事第一札》。
〔25〕《尽言集》卷12《乞早补谏员》。
〔26〕《清波别志》卷上。
〔27〕《鹤林集》卷20。
〔28〕《止堂集》卷1《论优迁台谏沮抑忠直之弊疏》。
〔29〕《清献集》卷8《殿院奏事第一札》。
〔30〕《耻堂存稿》卷1《应诏上封事》。
〔31〕《清献集》卷8《殿院奏事第一札》。
〔32〕《宋史》卷408《吴昌裔传》。
〔33〕《耻堂存稿》卷1《应诏上封事》。
〔34〕《困学纪闻》卷15。
〔35〕《宋论》卷4《仁宗》。
〔36〕《少阳集》卷2《辞诰命上钦宗皇帝书》。
〔37〕《范忠宣公奏议》卷下《奏举彭汝砺》。
〔38〕《四朝闻见录》戊集《臣寮雷孝友上言》。
〔39〕《宋会要》职官17之8。
〔40〕《挥塵录·后录》卷11《周葵言梁仲谟语去位》。
〔41〕《司马温国文正公文集》卷44《请自择台谏札子》。
〔42〕《要录》卷126绍兴九年二月戊午。
〔43〕《要录》卷178绍兴二十七年十一月戊辰。
〔44〕《宋史》卷390《论赞》。
〔45〕《嘉祐集》卷5《申法》。
〔46〕《宋史》卷472《蔡京传》指出:“熙宁间, 有内降手诏不由中书门下共议,盖有大臣阴从中而为之者”。这表明御笔手诏神宗时已出现,但其盛行则是徽宗朝。
〔47〕《独醒杂志》卷8,《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