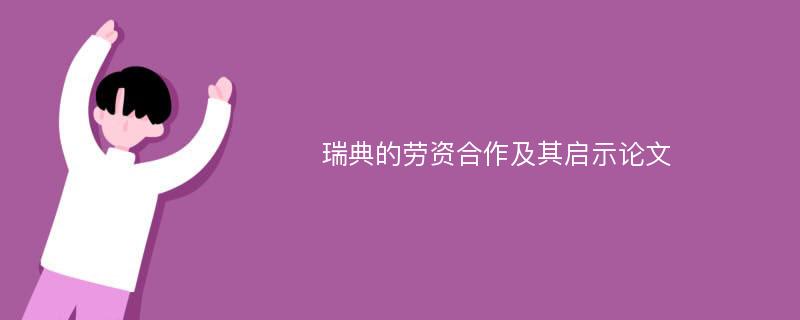
瑞典的劳资合作及其启示
张忠波
(渤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锦州121000)
摘要: 在瑞典劳资双方通过集体谈判制度确定工资水平,解决劳资争端,谈判破裂才由政府仲裁。政府还积极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调节分配,通过“公平分配”缓和了阶级矛盾,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一些经验值得借鉴。
关键词: 瑞典;劳资合作;启示
一、促使瑞典劳资走向合作的若干因素
(一)阶级力量对比及苏联、美国模式的弊端是其时代背景
历史上瑞典的劳资关系也曾十分紧张过,比如1909年的大罢工有30万工人参加,占工人总数的89.8%,虽然给资方造成重大打击,但在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镇压下失败了,斗争没有获得之前主张的实际权益。瑞典当时的阶级形势及所处的国际环境使劳资双方意识到,谁都没有压倒性的力量优势,资方虽略占上风,但面对高度组织化、富于战斗精神的产业工人也难以为所欲为,工人们也知道推翻资产阶级不太现实。势均力敌的劳资双方如果都不妥协,“恶斗”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出路只有妥协。同时,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实践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也引发瑞典人的思考,希望走出一条有别于苏联和美国的所谓“中间道路”,这也是理解瑞典劳资合作思想及实践的重要时代背景。1917年俄国爆发无产阶级革命,激烈的阶级斗争引发的内战一直延续到1922年,苏联的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自然引起瑞典资产阶级的恐惧,但是随着高度集权的经济社会管理体制的建立,斯大林模式的弊端也引起瑞典工人阶级和有识之士的疑虑和反思。他们认为苏联的道路是非民主的,实际上放弃了人人具有同等价值的思想,从而剥夺了每个人平等参与和创造未来的权利,是不足取的。1929年爆发于美国,进而席卷资本主义的大萧条也给瑞典沉重打击,经济濒于崩溃,劳资冲突激化,惨痛的现实也宣告了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理念的幻灭。走出一条不同于苏联和美国的“第三条道路”逐渐成为共识,秉承“人民之家”理念的社民党顺势走上前台,带领瑞典进行了一场以混合经济为基础、劳资合作为纽带的有瑞典特色的福利国家实践。
少年夫妻老来伴。经过几十年的磨合,浓浓的亲情已经融入双方的生命,相互陪伴,相互忍让,相互包容,是多数老年夫妻的相处之道。当然,也有一部分老年人不甘心面对平淡的生活,无法忍受另一半的缺点,这样的婚姻会变得越来越浮躁,婚姻中的问题与矛盾也会变得越来越棘手。一般来说,夫妻之间要注意一些细节,才不会让婚姻产生“裂缝”。一旦出现“裂缝”,要学会适当加点黏合剂。
投身脱贫攻坚的青春身影,把希望和信心带进大山深处;“脑洞”大开的创业团队,为放飞梦想努力打拼;风华正茂的年轻法官,甘当法治建设的“燃灯者”;激情满怀的青年人才,扛起航天报国的千钧重担;沙场练兵的勇毅战士,用方刚血气筑起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
(二)社民党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
建党伊始,社民党也把消灭私有制、建立工人阶级专政作为奋斗目标,但在挫折面前,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对传统思想进行了修正。理论的转变以汉森提出“人民之家”的理念作为标志,他在1921年的讲话中说:“我们奋斗的目标不是建立工人阶级专政,不是用一个新压迫取代一个旧压迫。我们所追求的是在民主的坚实基础上和绝大多数人民支持下,给受压迫的社会阶级以平等以便废除阶级,给所有瑞典人一个美好家园。”[1]在这一思想的引导下,职能社会主义思想产生并逐渐成熟。理论家卡莱比认为,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不是天生的、也不是永恒的,更不是可以随心所欲行使的绝对权力,它只是国家赋予一些人对于某一物品的支配形式。因此,国家有权力通过立法对其进行限制、改造,也可以赎买、剥夺。工人阶级通过经济斗争、政治斗争所获得的8小时工作制、工资集体谈判、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其他经济福利,已经使工人阶级获得了对生产资料的部分权力,从而极大限制了资产阶级的支配权。由此,社民党不再把生产资料国有化作为直接奋斗目标,而是把目标专注于借助普选权和多党制赢得政治权力,利用赢得的政治权力对资本家的“所有权”进行限制和改造,使雇佣工人能够对收入分配、生产管理乃至于投资决策施加愈来愈大的影响,最终赢得控制权,把资本决策权由私人转移到民众手中。社民党于1983年正式提出的“基金社会主义”就是这种思想的延续和发展,尽管“基金社会主义”由于资本家的激烈反对最后不了了之,但却是我们把握瑞典社民党指导思想演变及其精髓的一面镜子。
(三)瑞典学派经济思想的指导
瑞典学派的奠基人是威克塞尔,他在其著作《利息与价格》中揭示了资本累积过程的原理,对资本主义市场机制能自动调节进而达到充分就业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是“混合经济”的最积极的拥护者。所谓“混合”不仅是指所有制形式的多元化,也包括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比如收入分配。他认为:“世界不存在个人收入天然就能有合理分配的格局,往往是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阶级一般不能取得他所应取得的收入份额,这就要求有合理的社会对分配进行干预。”[2]林达尔认为政府可以将私有财产通过税收转变为共有财产,主动调节收入分配,使大众的需要得到更好满足。另一位代表人物林德伯格主张:普通消费品的生产决策权属于企业,消费决策权则属于大众,而诸如国民经济统计、宏观经济稳定、公共产品供应、收入分配、环境保护等决策权力属于国家,分权与集权的适当结合最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他还指出,瑞典的经验表明,适当地缩小工资差别,不但不会降低效率,反而会提高效率,因为它有助于防止社会动乱。由此可见,尽管经济学家们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其背后的基本要义则都倾向于用“有形之手”对“无形之手”进行积极适度的干预,要两手并用,否则就会孤掌难鸣。
(四)福利经济学的影响
某公路试验路段全长500m,起讫桩号为K30+200—K30+700,道路设计标准为二级公路,双向四车道。路面结构使用7cm的半柔性混合料代替原路面结构的7cm粗粒式沥青混凝土,施工过程中按照母体沥青混合料铺筑、水泥砂浆制作、水泥砂浆灌注、表面处理和养生等路线进行管理,并严格控制施工质量标准。
(五)善于妥协的历史传统
更具历史意义的事件是,在社民党斡旋下,劳资双方于1938年签订“萨尔茨耶巴登协定”,由此正式确立了具有瑞典特色的集体谈判制度,“使劳资间冲突的处理程序化、审理化,并将解决劳资冲突的权力集中化”[7]。集体谈判的精髓有两点:其一,解决劳资冲突的主要途径是谈判,谈判先在地方进行以解决矛盾,谈判破裂再提交中央一级协商解决,是否罢工或闭厂的权力由各自中央级组织行使;其二,如果劳资双方中央及谈判也协商无果,需要在三个月之内提交作为第三方的劳工法庭仲裁解决。集体谈判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缓和了劳资矛盾,减少了因罢工等冲突造成经济和社会损失。1944年社民党提出《工人运动战后纲领》,为战后的社会保障制度绘制了蓝图。1948年实施新的养老金法,建立了国家基本养老金制度,并提高了标准,1960年实施收入关联型补充养老金制度。1949年实施工伤安全法,1951年开始实行强制性的健康保险制度,社保制度日趋完善。
二、瑞典劳资合作的实践及其绩效
20世纪50年代总工会提出了“团结工资”政策,旨在实现不同行业间工人收入的同工同酬,这促进了工人收入的均等化,同时也有助于淘汰落后企业,提高了瑞典经济的竞争力。1983年社民党政府正式提出“职工基金法案”,虽无果而终却也从一个侧面彰显了瑞典劳工阶层的“强势”地位。1997年,劳资双方为适应新的形势签订了《工业发展与工资形成协议》,再次重申了和平解决争端的精神,出现争议可以申请国家的第三方仲裁,调解失败可以罢工或闭厂,但必须按照《协议》的规定进行。
著名学者罗斯托在《妥协政治》中曾总结到,在瑞典政治中,决定只能从妥协中产生。追溯瑞典历史,早在1626年,瑞典从欧洲大陆引入等级制度,形成了贵族、教士、市民和农民四个等级,取代了原有的贵族议会,进一步巩固了国王权力。但是相较于东方君主的绝对权威,瑞典国王的权力则有赖于权势贵族的支持,因而贵族还处于比较强势的地位。但即便处于最低一级的农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相对自由的,拥有不少权利进而可以发挥重要的政治作用。“他们能够影响到教士的任命以及参与当地的决策——最初是参与地方法律的制定,后来甚至能参与国家法律的制定。”[5]这一等级制度于1626年得到正式认可,国王甚至设立宫廷总管监督其运行。有四个等级推选的等级代表构成了所谓的“四级议会”,它同国家政务会共同构成了当时的瑞典国民政府。虽然最大的权力为国王和贵族掌握,但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以及民主意识的发展,下层等级的权力呈现出不断增加的态势。随着阶级构成和力量对比的变化,1866年“四级议会”被近代两院制议会取代,直至1971年演变为一院制议会。与此相伴的是社会阶层的多层次化和多党制产生,以及政坛经常出现的联合组阁现象。以1991年议会席位分配为例,在全部349个席位中,社会民主党占138席、温和党(保守党)80席、自由党33席、中央党(农民党)31席、左翼党(共产党)16席、基督教民主党26席、新民主党25席、环境党0席,代表“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民主党一党独大,这也是瑞典主流价值观在政治上的体现;区别于美国式两党制之下的赢者通吃,社民党、温和党之外的小党林立有利于非强势阶层、集团发出自己的声音和诉求,这恰恰是深入人心的“人民之家”理念的有力的诠释。
1902年在社民党领袖布兰亭领导下,10万工人参加了旨在争取男子普选权的大罢工,最终取得胜利。1906年的“十二月妥协”为后来的集体谈判奠定了基础,总工会承认雇主拥有录用工人、分配工作和解雇工人的权力,资方则接受工人结社、不受迫害和集体谈判的权利。1928年,瑞典议会通过《集体协议与劳动法庭法》,对在劳资协议有效期内违反“和平义务”,擅自进行罢工或闭厂的工人和雇主进行惩罚,使劳资矛盾的解决走向法制化。1934年社民党颁布实施《失业保险法》,失业保险制度由此建立。“1935年,政府开始对低收入家庭提供贷款。1935年社民党政府修改了原有的养老金制度,使其成为所有低工资收入者都适用的养老金制度。1936年社民党政府颁布了农业工人标准工作时数法。1937年出台的新的法案规定给收入较低的母亲发放抚养补助金,给新安家的年轻夫妇发放政府贷款;1938年,瑞典议会批准给所有工人每年两周带薪假期”[6]。
这些举措缓解了劳资矛盾,使瑞典从欧洲劳资矛盾最尖锐的国家,逐渐成为劳资冲突相对“罕见”的资本主义国家,基尼系数长期稳定在0.25左右,个别时期会低于0.2或者高于0.3。稳定的阶级关系降低了经济发展的政治成本,使劳资能积极合作专注于做大“蛋糕”。从1870年到1913年,瑞典迅速实现了工业化,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瑞典都是当时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瑞典是除日本之外经济发展最快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劳资合作的确功不可没。
福利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是社会经济福利最大化,实现途径之一是不断提高国民收入,另一个是促进国民收入的均等化。“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同样的货币量对穷人的效用远远大于对富人的效用,因此国家可以采取收入转移的方式把高收入者的部分收入直接或间接地转移给低收入者。”[3]与此相对应的社会政策就是充分就业和“贫富拉平”,比如遗产税、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以此来解决市场失灵造成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对立。1942年《贝弗里奇报告》发表,英国政府开始着手建立福利国家。受此影响,瑞典加快了各项福利规划的落实,总的趋势是福利内容不断丰富,以1988年为例,其内容包括医疗保险、父母保险、基本养老金、附加养老金、市政住房补贴、工伤保险、儿童补助、抚恤金等;同时,受惠范围不断扩大,以养老金为例,1946年以后逐渐覆盖了全国人口。相应的福利开支也是水涨船高,人均福利开支相较其他国家一直位居前列。资料表明:“1983年度OECD23个成员国人均社会保障费支出平均为1929美元,其中瑞典人均社会保障费支出为3649美元,荷兰为3113美元,法国为2961美元。”[4]
三、瑞典劳资关系“和谐”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一)一定要高度重视,不能掉以轻心
在此期间,联想首台自主设计的台式机“天琴”电脑,推动了整个电脑台式机行业的工业设计革命,结束了中国电脑台式机生产使用统一标准机箱的时代,开始形成品牌企业工业设计百花齐放的局面。
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16,之后一路攀升,1985年为0.24,1990年为0.36,1999年达到了0.4,2004年为0.47,2009年更是达到了0.49,2012年为0.474。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15年1月2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9,连续第6年下降,但仍高于国际公认的0.4的贫富差距警戒线。2016年的数据为0.473,略有上升,说明了利益格局的固化趋势,调整难度很大。与此相伴,劳资纠纷、冲突愈演愈烈,极端事件屡见不鲜。2009年7月,因民企北京建龙集团控股通化钢铁(占66%股份),遭上万通钢职工反对,北京建龙集团派驻通钢的总经理陈国君被扣押为人质,并遭殴打,最后不治身亡。自2010年1月23日富士康员工第一跳起至2010年11月5日,富士康已发生14起跳楼事件,引起全社会乃至全球的关注。2012年12月4日下午,汕头一家内衣厂被职工刘某纵火,14人死亡,1人重伤。刘某在该厂工作一年,因老板经常少算工资,决定辞职,最后结算工钱时,老板丈夫又以其虚报计件为由扣下500元,遂酿成悲剧。反映出当前我国劳工权益保障制度的缺失,劳工阶层在劳资关系中,特别是在非公经济领域中处于弱势状态。
瑞典经济学家林德伯克曾特别强调劳资之间的“合作”气氛,“特别是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所谓福利国家的实践,作为促进瑞典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8]。如果当前的劳资关系现状不加以改变,将进一步加剧分配不公,持续累积可能波及社会稳定,动摇党的执政基础。
(二)一定要对症下药,不能久拖不决
学者阿萨·布瑞格斯认为,市场经济国家必须从三方面修正市场的自发力量:一是保障个人和家庭获得最低限度的收入;二是帮助个人和家庭应付诸如年老、疾病、失业等不测事件;三是确保所有公民不论什么阶级、何种地位都能平等地获得基本的、普惠式的公共服务。可见,国家是克服市场缺陷,维护公平正义的主导力量。
在非公经济领域完善各级工会组织,强化工会力量,逐步建立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是当务之急。当前在非公有制企业要么没有工会组织,要么力量羸弱,因此应当在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下,在各级地方政府的配合下,在各行业、各企业建立和完善工会组织,特别是要积极动员各类劳工入会。以此为基础,以行业性工会作为劳工利益代表,同企业主或其代表组织进行工资协商,处理劳动争端。同时,建立第三方的专门劳动仲裁法庭或委员会,对双方谈判进行监督、仲裁,这是劳资两利,也有利于国家的“三赢”制度。经济学家奥坎认为劳资双方通过集体谈判签订长期雇佣协议,增强了企业的稳定性和保障性。“这一点在‘专业市场’尤其明显,因为在这个市场上劳动力教育程度高,有机会在专业上不断进取。在这些市场上,就业保障系数较高,雇员有机会深造,工资不允许上下浮动。”[9]因此集体谈判对双方来说是共赢,雇员和雇主之间“有形的握手”也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强化政府职责,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治本之策。以瑞典为例,即使有集体谈判制度,经过初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也在0.4以上,例如1992年甚至达到0.5038,但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再分配调节,则下降为0.2841。因此应借鉴瑞典,适时开征房产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一般财产税,将个人所得税计征单位从个体调整为家庭。在社会保障方面,重点是扩大其在个体、私营企业的覆盖范围,发挥税收和社保制度在分配上的强力“拉平”作用,实现劳资和谐,促进社会和谐。
参考文献:
[1]高锋,时红.瑞典社会民主主义模式:述评与文献[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5.
[2]缪一得,杨海涛.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245.
[3]杨玲.美国、瑞典社会保障制度保障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117.
[4]孙炳耀.当代英国瑞典社会保障制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86.
[5]尼尔·肯特.瑞典史[M]吴英,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25.
[6]袁群.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历史、理论与实践[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66.
[7]黄安淼,张小劲.瑞典模式初探[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121.
[8]黄范章.瑞典“福利国家”的实践与理论——“瑞典病”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26.
[9]克拉斯·埃克隆德著.瑞典经济——现代混合经济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165.
中图分类号: K2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4630(2019)05-0041-04
收稿日期: 2019-06-30
作者简介: 张忠波(1974—),男,辽宁沈阳人,副教授,法学硕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责任编辑 韩冬梅]
标签:瑞典论文; 劳资合作论文; 启示论文; 渤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