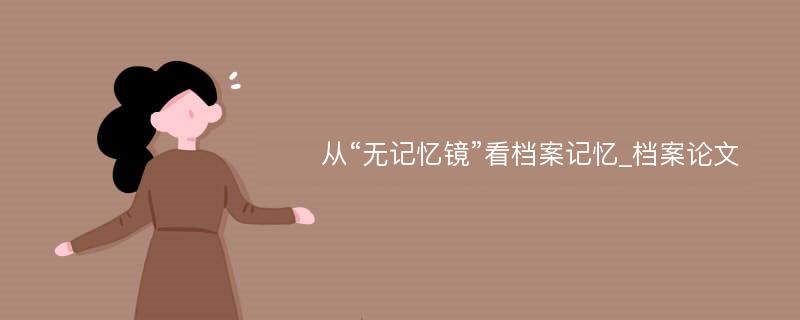
从“没有记忆的镜子”看档案记忆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记忆论文,镜子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70
美国学者林达·威廉姆斯在《没有记忆的镜子》(1993)一文中说“在利用计算机炮制画面的电子时代,摄影机是‘可以撒谎的’,影像已经不再是以前被称作照应着物体、人物和事件的视觉真实的‘有记忆的镜子’,而是变成了对真实的歪曲和篡改”。[1]当今社会,科技统治世界,科技时代的产物比任何时代都难分真假,造假现象层出不穷。人们几乎对周围的一切事物都产生了怀疑。PS一张与足球明星贝克汉姆的合照是很多普通人都可以做到的,用语音处理软件模拟不同人的声音已不足为怪,不久前奥巴马大跳骑马舞的视频让众多网民难辨真假。摄像机变得似乎不再是机械复制客观事件那么简单。但是人们却越来越依赖于视听媒介传递信息,人人可以摄像,可以轻易传播、篡改、获取影像,同时也要面对无处不在的摄像镜头,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生活在“纪录片的社会”[2]。“历史已经变成收集影像的活动,这类影像唾手可及,只要按一下遥控器的按钮。”[3]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温·托夫勒也从“记忆力的革命”角度论述了人类记录方式的变革导致了社会记忆形态变化这一现象。在中国,兴起于20世纪末的档案记忆观,坚持“把档案与社会、国家、民族、家庭的历史记忆联结起来,强调档案是一种社会记忆”[4]。2001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了首届档案学博士论坛,主题就是“21世纪的社会记忆”,并出版了同名论文集,影响很大。“数字记忆”“电子记忆”“城市记忆”“企业记忆”“社会记忆”等问题研究逐步成为档案学研究的热点。
从社会记忆构成的三要素“主体-中介-客体”思考,档案学者丁华东认为档案记忆的研究是从中介的角度切入社会记忆研究的。即研究档案或档案馆作为特定的媒介记录了什么样的过去,以及人们如何利用这些媒介来建构社会记忆[5]。纪录片的概念众说纷纭,但其核心都是“排除虚构的电影”,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最接近原始记录的影像载体。纪录片既可以与档案并列作为社会记忆的一种媒介,在一定条件下,它也以一种特殊媒介形式的档案而存在,这是档案与纪录片的逻辑结合点。所以分析纪录片发展中遇到的如何保持记录的真实性问题也会对深化档案记忆观的思考带来一定的启示。
1 科技变革与纪录电影
电影的发展是以与其相关联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先导的[6]。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到“便携式摄像”再到如今“数字化”,人们对纪录电影的争论摇摆在“真实”与“虚构”两个极点。20世纪60年代,随着便携式摄影机及同期录音技术的成熟,以“直接电影”和“真实电影”为代表的纪录电影向30年代主张对生活事件进行“搬演”“重构”的传统纪录电影提出挑战,“直接电影”和“真实电影”都提倡电影的原始记录的本性,努力再现生活的原貌,并排斥画外音解说,靠纪录片中人物的同期声传达信息,不同的是,“直接电影”的拍摄者力图使自己处于事件之外,以偷窥者的身份去观察、去记录,拒绝一切可能破坏生活原生态的主观介入[7],如美国导演弗雷德里克·怀斯曼就把摄像机安置在警察局、医院、福利机构等公共场所,用镜头解剖各种机构与人复杂的关系,让观众自己去思考,他不给予任何意见和参考;而“真实电影”的拍摄者不是被动等待事情发生,而是主动干预和挑拨,甚至人为制造事件,目的在于表现本质的真实[8]。90年代后,随着更简易的记录手段的出现以及影像篡改技术泛滥,“新纪录电影”认为“纪录片可以而且应该采取一切虚构手段与策略以达到真实”[9]。
阿尔温·托夫勒在他的《第三次浪潮》中说到的社会记忆的三次革命:“第一次革命将人类共有的记忆和个人记忆储存在个人的大脑中”,“第二次革命把社会记忆扩展到人们大脑之外,如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第三次革命人类记忆存储工具不再是消极静止的,而是积极能动地向社会记忆输入生命,使这些符号再次被人脑所吸收、加工、组合。”[10]同样,纪录片发展到今天,已呈现出了“现象真实”与“本质真实”的矛盾,影像记忆也不再是静止地储存在大脑和图书馆、档案馆。
2 档案的“原始记录性”与纪录片的“真实性”
在档案学界,档案的原始记录性一直作为档案的重要特征受到关注,学者对档案的原始记录性也基本达成一种共识:档案内容的真实性高于其他文献材料。而在档案记忆观的研究受到高度关注的影响下,人们对档案真实性的问题也愈加重视,由此也引发出三个疑问:一档案内容本身是否完全真实的问题;二如何确定档案形成过程的选择与遗忘、中心与边缘的问题,尤其随着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发展成熟,学术界开始强调隐藏在文字背后的真实以及政治结构和权利关系对社会记忆的操控,档案也被认为是“官方”的记忆,边缘人群的记忆被选择性遗忘;三是如何对待“现实主体认知与历史主体认知之间的分歧”[11],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必然受到所处社会的政治、文化、观念等的影响,历史上被销毁的未装进档案盒的文件对现代人来说未必没有价值,历史上因为可以证明官方统治的英明、社会繁荣而被保留下的历史文件,对于现代人来说,也许它成了证明当时制度腐败、束缚经济发展的直接证据。针对档案真实性的疑问,有的学者认为“断不可仅从档案自身去寻找所谓的‘真实’,而是应立足于社会记忆的大场景,把档案所包含的记忆片断,连同其他相关联的社会记忆共同拼接起来”[12]。
档案界真实性的三个疑问同样存在于纪录片的发展中,如果抛开影像篡改技术不谈,那么摄像机的机械复制的特性是否就可以保证记录的真实性?“纯粹的客观真实对于个体来说是不可见的,它们表现在人类符号真实性上,我们在纪录片中所见到的只能是符号真实”[13],符号背后的真实可能更多的要有历史学家去呈现。影响纪录片真实性的因素可以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纪录片的背后站着导演的意志和选择。导演可以决定选择拍摄什么不拍摄什么,从什么角度拍以及如何对素材进行剪辑。记录1934年9月纳粹党举行党代会议以及一系列群众集会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被后人称为“不可饶恕的巨大成功”,导演莱尼·里芬斯塔尔运用了近拍远摄、推拉摇移、俯瞰与仰角等一切电影手段,极力展现了数百万狂热民众对阿道夫·希特勒如同神灵般的膜拜,法西斯的声誉在这部没有一个镜头是扮演或重构的影片中被推向了巅峰。后来很多反法西斯电影却利用《意志的胜利》的素材,剪辑出了反法西斯影片,如《普通的法西斯》把很多《意志的胜利》的镜头资料与二战期间其他画面素材进行剪辑重构,使每一片段都跟前一片段形成尖锐对比,堆积如山的白骨和狂呼希特勒万岁的人群、死亡的集中营和嬉戏的纳粹士兵、大批德国战俘和戈培尔的演说等等。这些镜头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通过剪辑却形成赤裸裸的、鲜明的画面对比,把纳粹党的声誉打入了万丈深渊。
再次,摄像机对被记录者真实性的干扰。当人们将自己作为被拍摄而且要被别人观看的影像展现在摄像镜头前的时候,他已经给自己戴上了面具,进入了非真实状态。被拍摄者由于受到摄像机的注意而产生一种自我虚构的反应,从心理学上的“霍桑效应”中或许可以的得到解释。20世纪60年代,法国人类学家让·鲁什认为,这种被摄像机激发出来的自我虚构的部分是更本质的真实,是通过“谎言讲述真实”[14]。美国纪录片大师罗伯特·德鲁认为只要选择的事件够大,就能减少在场人员对事件的干扰。同时,以自我为中心的政治人物会往往太专心自己的事情,而不去注意拍摄。然而在21世纪“纪录片时代”,面对随处可见的摄像头,很多人可以很轻松地立即进入拍摄状态,而这种堪称演员水准的表演状态是很难判断真假的。
另外,一旦涉及人的思想,绝对客观真实是不存在的。2012年,中央电视台推出《走基层百姓心声》系列栏目,记者随机采访普通百姓诸如“你幸福吗”此类问题。节目播出147人,半数以上的不假思索地回答“幸福”,但节目播出后就有观众说“现在社会上这么多的孩奴车奴房奴,觉得大家有点说假话,真的有很多人这么幸福吗”。深入思考会发现,我们从镜头上看到的下意识回答“幸福”的这种反应是真实的,但是受访者给出的答案未必是真实的想法,也就是所谓的“符号真实”。第一,采访背景是在国庆狂欢的氛围之下,人的情绪是被限定的;第二,从心理学角度看,受访者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他的回答往往是附和性的;第三,面对央视《新闻联播》巨大影响力,受访者自然会顾虑自己的回答会造成何种后果。然而这一系列的思想波动,摄像机是无法捕捉到的。
最后,纪录片也存记录者与观众分歧性的疑问。例如荣获第三十届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人道奖纪录片”的《高三》全程记录了一个高三班78名学生及班主任在高三一整年的学习和生活。内地80%的学生观众认为这是一部励志片,导演周浩却很生气别人说这是一部励志片,因为他只想客观地记录一群十七八岁的孩子在特殊情境中的成长:也有观众认为它是对中国“应试教育”的大批判:美国观众却把它当做政治片来看,因为“一场考试就能决定一群人未来的命运,这就是政治”[15]。虽然影像记录具有主观性,但这种主观性又可以是全方位的。一千个导演可以拍摄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哈姆雷特又被无数观众重新吸收、加工、组合,形成立体式的影像记忆。
由于人们意识到摄像机在某种真实面前是无能为力的,纪录电影的发展在80年代初进入低潮,但是在90年代初欧美一些国家出现了一批与传统电影迥然有别的纪录片,这些纪录片主张“电影无法揭示事件的真实,只能表现构建竞争性真实的思想形态和意识”[16]。
从上可知,人们对纪录片“真实性”和对档案“真实性”的认识过程有一定的一致性:它们都最初被视为一种“真实性”的记录,随着人们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关注这种“真实性”的“复杂性”。此外,关于档案以及纪录片在社会记忆价值上的“选择与遗忘”“中心与边缘”的问题,人们也开始从理论逐步走向具体实践。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纪录片只停留在空乏的议论上,使政治变成生活的标签[17],引起了人们的逆反和抗拒心理。而新时期纪录片则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影响观众日常生活的事件上。
3 从视听档案到文献纪录片
从严格意义上讲,纪录片并不符合经典的档案定义:档案的实存状态不是人类某个实践活动的最终产品,而是它的伴生物。未经剪辑的影片素材或毛片才算是档案,而纪录片更像是档案的“编研产品”。数字技术的变革不仅促进了影像技术的发展,同时为不同载体、多种格式的影像进行转换、剪辑和整合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利用影响技术改变记录的真实性提供了可能,同样的一段事实用高速摄影拍摄再用普通速度播放,即可带来不同的视觉感受,从而产生不同的心理影响力,甚至导致事实记录的失真。另一方面,自电影产生以来,人类遗留下的这些无法估量的影音遗产已足以达到形成多部全新的影片的要求,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东西方掀起了一股以“视听档案”作为创作素材的热潮,这种“利用以往拍摄的新闻片、纪录片、影片素材以及相关的真实文件、档案、照片、实物作为素材进行创作”[18]的纪录片,在我国被称为“文献纪录片”,很多以“档案”“往事”为名目的电视栏目往往如此,在英文中,与之相对应的是“汇编影片”或“编纂影片”(compilation film),如我国的《周恩来外交风云》、美国的《越南:电视上的历史》等,原来的视听档案成为“档案的档案”。文献纪录片的价值在于它不仅表现过去一段历史的影像,更重要的是这段影像是纪录片人眼中的历史,附着了时代的痕迹,“因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即便是历史题材,也是站在今天我们的视野范围去读解”[19]。
值得一提的是,影视界出现了新的文献纪录片的创作趋势,创作者并非被动地“摘录”或原封不动地陈列他们所能获得的“视听档案”来证明历史书上提到的真实,而是把“历史”作为“面对、诘问与质疑的对象与主体”,把“影片”作为“拷问的场所”,“视听档案”则是“双方面对面的‘呈堂证物’、‘文件’”[20],创作者以一种高度批判性对视听档案进行“不忠诚的忠诚”地再诠释与再创造。“‘历史’一词并非是那些被记载的、被承认的重要历史事件,更重要的与不可遗漏的,‘历史’一词包含‘个人史’”[21],如同台湾导演陈界仁在一次访谈中说到:在冷战时期“不论是卡通、历史战争片或外星人入侵地球,甚至爱情影片等,其实都是为了将冷战合理化,而通过娱乐影像的洗脑教育”[22],这就引出一系列命题:谁操控了影像,人们如何通过影像来确定自身的记忆,如何记录影像以及影像如何成为档案等等。像陈界仁导演这样一位经历了父子两代作为反共救国军以及台湾38年戒严时期的人而言,他强烈感受到台湾官方对某些历史事件的缄默,于是他用自己所能掌握的方式把历史与台湾当代社会联系起来来重思失忆的种种过去。他的纪录片《凌迟考》从一张清朝犯人凌迟处死的照片开始,照片中受刑者被捆绑、被肢解、被灌食鸦片,在极度的痛苦下,竟面朝天空露出微笑。这张照片于1905年由一位法国士兵拍摄后,一百多年以来一直被西方各种报纸杂志以及学术界转载、引用与阐释,以至于它在1997年正式出现在中国刊物之前[23],西方已经从宗教、情欲、酷刑甚至美学等角度作了各种解释,这些解释并不是中国人真正的记忆,而是西方殖民主义思想对弱势文化的强行介入,也是为了满足西方对东方的猎奇心理罢了,这张“符号真实”的凌迟照片由于一百多年在中国历史上的空档,而且照片中无论施刑者、受刑者还是看客都早已不能说话,所以它对中国人来说是“没有记忆的镜子”。纪录片《凌迟考》是过去与现在、现在与未来的交织,是透过表面符号或固化信息来思考现实社会,是留给未来人的当下人对过去的反思和现在的记忆。
4 结语
纪录片以立体性、多层次、全方位的方式展示历史的方法以及纪录片研究的发展必然为档案资源体系的建设与档案记忆观研究带来新的启示。档案资源体系不应该仅仅是过去所发生事情的“证据”,而应成为主动吸收社会多方面思想同时又积极向社会记忆输入源头活水的符合信息资源构成理论的科学体系。档案部门在收集官方的影像资料同时,应充分重视被忽略、被遗忘的民间记忆,如民间组织影像、家庭影像档案、作为艺术而产生的纪录片以及作为学术研究而拍摄的影像等等,在此基础上,应该关注影像背后被遮蔽、被抹去的历史真实。
档案与电影交叉性研究要更多的借鉴电影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的知识成果,如电影在人类学中的应用而形成的影视人类学,人类学影片通过直接的影像拍摄来再现特定民族或人种的文化,以达到抢救和保存人类正在消失的文化遗产的目的,如反映萨满教在我国鄂伦春族的衰落情形以及残存影响的《最后的萨满》、少数民族生活状态《清水江流域苗族的婚姻》等。由于人类学影片对“原始记录”、“保存目的”、“边缘性题材”、“毛片与成片区分”的强调使人类学影片具有了某些档案的特征,因此电影这种具有对客观物质世界机械复制特性的工具,在人类学中的应用与在档案学中的应用可以达到互相映射的作用。“如果说照相和电影影像不是有记忆的镜子,如果说它们更像是波德里亚尔所说的镜像大厅(a hall of mirrors),那么,我们解决这种表现危机的最好办法,也许就是去做莱兹曼和莫里斯所做的事情:展开这些镜子的许多镜面”[24],对于档案记忆观亦是如此,这也许应该成为今后档案学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切入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