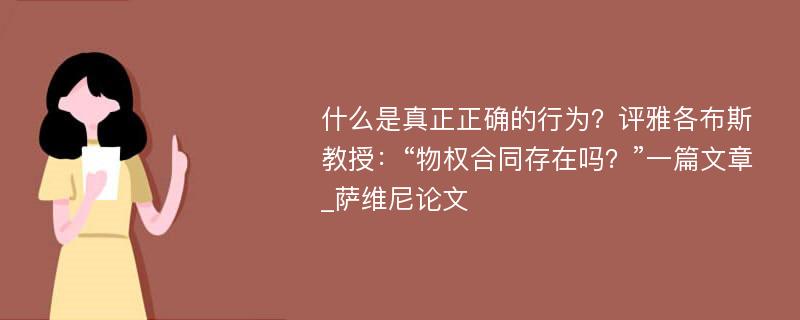
物权行为到底是什么?——评雅科布斯教授“物权合同存在吗?”一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物权论文,到底是什么论文,一文论文,布斯论文,教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概说
雅科布斯的《物权合同存在吗?》一文已经面世,德文版面世较早,发表在《萨维尼基金会法律史杂志:罗马法部》,(注:[德]霍·海·雅科布斯(H.H.Jakobs):“物权合同存在吗?”(Gibt es den dinglichen Vertrag?),载《萨维尼基金会法律史杂志:罗马法部》(Zeitschrift der Savigny-Stiftung für Rechtsgeschichte,Romanistische Abteilung),第119卷(2002年)(以下简称德文版),第269-325页。)中文版刊登在《十九世纪德国民法科学与立法》一书的后记中。(注:[德]霍·海·雅科布斯:《十九世纪德国民法科学与立法》,王娜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后记:物权合同存在吗?”(以下简称中文版),第160-219页。)
该文是基于作者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振山关于物权行为理论的讨论而撰写的,旨在回应讨论中涉及的相关问题,同时作为该书的后记。(注:为行文简单,如未作版本说明,即为中文版。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德文版相关部分。)本人曾经参加了文章提及的讨论,而且该文主题与本人作品主题相关,(注:田士永:《物权行为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主题相近的专著还有:王轶:《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肖厚国:《物权变动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故对该文十分关注。雅科布斯的文章,是目前为止德文文献中从法律史和基本法理角度对物权行为所作的最为清晰的说明,颇值注意。
物权合同是由谁最先提出的?是如何提出的?这是讨论的主题,也是雅科布斯的文章的线索。根据该线索,雅科布斯在文章第一部分简单交待了文章的写作背景和德国学者对物权合同理论的整体态度,在第二部分简单分析了立法中的物权合同,在此基础上,作者的分析进入作为文章主体的第三部分——物权合同的创立。文章对物权合同理论的发展及其发展中所体现出的理论背景的分析,有助于中国学者了解物权行为的本来面目。
二、物权合同提出的过程
自费根特莱格(Wilhelm Felgentraeger)之后,(注:威廉·费根特莱格(Wilhelm Felgentraeger):《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对转让学说的影响》(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s Einfluβ auf die übereigungslehre),1927年,莱比锡(Leipzig)。)德国学者一般将萨维尼视为物权合同理论的最早提出者,中国学者也不例外。(注:如王泽鉴:“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之检讨”,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1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2及页以下;梁慧星:“我国民法是否承认物权行为”,载梁慧星:《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注1;陈华彬从日文资料作的表述也基本是从萨维尼开始的。参见陈华彬:《物权法研究》,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157页及以下。孙宪忠的作品提及“胡果·格老修斯(Hugo Grotius)等人提出并发展的意思表示理论,以及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法律行为理论”,但详细分析的仍然是萨维尼的理论。参见孙宪忠:《中国物权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63页及以下。)杨振山在讨论中提出德文文献中谁最先使用物权合同概念这一问题,雅科布斯当时不能确信究竟是不是萨维尼首先使用了这一概念。经过分析,他的结论是萨维尼确实使用了物权合同的概念,但“将创建物权合同学说的功劳归于萨维尼一人的做法不符合实际”(第174页),因为在此之前,古斯塔夫·胡果(Gustav Hugo)已经提出了关于物权合同理论的全部内容(第174页)。
胡果是历史法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普赫塔对他的评价极高(第177页)。在研究罗马法原始文献的过程中,他提出了物权合同理论的基本内容:“转让需要转让人的意思和出让人的意思”(第186页),并且优士丁尼《法学阶梯》的作者之一迪奥菲尔也认为转让所有权需要具备转让所有权的意思(第186页)。之所以得出如此结论,是胡果坚持了罗马法对债的认识。罗马法中的“债”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束缚”(第183页),“债权是一种权利,其针对的对象并非物,而是另外一个人;债权使这个人失去对享有除某个债权中所指的行动的自由权以外的全部普遍自由,这个行动因为被排除(此排除并不排斥他人)出自由的范围,所以不再是可以作的行动,而是必须作的行动”(第183页)。(注:这一表述与萨维尼权利分类的学说及基本一致。参见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当代罗马法体系》,第1卷,1840年,柏林(Berlin),第53节。中译参见萨维尼:“萨维尼论法律关系”,田士永译,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第7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1-12页。)因此,所有权取得方式中不包含债的关系,尤其不包括买卖。(注:胡果说:“虽然他知道,通过买卖只能产生针对出卖者的债权,无论如何无法单凭买卖取得物上的对世权;但如果你问他,如何得到该物,他会说,通过买卖。”可见,胡果已经明确区分所有权转让与作为其原因的买卖。但陈华彬在介绍胡果和格吕克的见解时则指出:“他们还不能把物权与作为其原因的买卖、赠与等明确区别开来。”前引陈华彬:《物权法研究》,第162页。《合同法》第135条的规定同样表明,“通过买卖只能产生针对出卖者的请求权”,所有权的转移尚需出卖人履行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至于如何履行该义务,一般学者很少分析是否需要意思表示要件。崔建远认为基于法律行为发生物权变动需要具备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主观要件是指当事人已为欲使物权发生变动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可以存在于买卖等合同之中。参见崔建远:“无权处分辨”,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1期,第6-9页。)这就将债权从所有权转让的要件中排除出去(第184页),但是,所有权转让又有名义与形式的问题,所有权是在占有开始之后产生的(第185页),因此,将债权请求权作为所有权转让的名义并不正确(第185页)。债权请求权仅仅是给所有权转让中的名义以名称,而该名义作为“占有的开始”区别于债权请求权,因此,名义只能是占有“开始”的形式和方法,即转让人的意思和受让人的意思。与债权请求权真正相分离的名义,只能是一个区别于发生债权请求权合同的合同,这个合同只能叫作物权合同(第187页)。
“萨维尼的物权合同理论只是在胡果的意见基础上,在胡果已经开辟但没有最后完善的道路上完成了最后一步”(第188页),因此可以说,“在建立物权合同理论的过程中,是胡果逆‘时代潮流’,完成了主要工作,而萨维尼则在胡果认识到当时潮流发展的绝境后,为潮流向新方向发展铺平了道路”(第177页)。可见,雅科布斯在物权行为理论的学说发展史给胡果以开拓者的地位:创造性的工作早已经由胡果完成,萨维尼不过是集大成者。(注:在法律与历史的关系问题上,古奇指出,胡果最早认识到“一个民族的法律,只有通过民族生活本身才能被理解,因为法律也是那个生活的一部分和表现。”参见[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30页。当然,胡果只是指出了道路,而首先走上这条道路的荣誉,应当归属于他的学生埃希霍思。萨维尼致埃希霍思的信件表明,他也承认“如果我有任何成绩的话,那是由于我遵循了那条已经找出的道路”。参见前引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第131页以下。可惜的是,古奇的介绍和分析未引起重视。)这一点,对于评价萨维尼的学术贡献,不仅仅是对物权行为理论的贡献,还是他对历史法学派的贡献方面,都值得重视。(注:胡果的影响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例如,何勤华认为历史法学派以胡果和萨维尼为首,但具体内容的分析,却未涉及胡果。参见何勤华:《西方法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6页及以下。广为中国学者使用的博登海默的作品,在历史法学派中同样只介绍了萨维尼而未介绍胡果。参见[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81-85页。)
如果认识到胡果的理论与萨维尼的理论之间的关系,在理解物权合同理论发展中就会认识到,物权合同理论的发展,纯粹是法学理论演绎的结果,是基于法学理论内在统一的需要而发展出来的理论,尽管该理论具有诸如交易安全等效果,但这仅仅是物权合同理论带来的好处,而不是物权合同理论本身提出的依据。雅科布斯文章的优点在于,通过学说史的分析,清楚说明了理解物权合同理论应当具备的知识背景,这一点是其他德文作品所欠缺的,同时也是中文文献不足的地方。
三、物权合同提出的思路:私人自治的体现
通说认为,物权行为理论旨在保护交易安全,这一点在德国学者的作品中有所体现,(注:萨维尼之后德国学者抽象性功能的认识转变,耶林起到了重要但却有些修正主义味道的作用,相关分析参见,田士永:前注4引书,第95-104页;第346-356页。)在中国学者的作品中也比较明显。(注:不管是肯定物权行为理论者如孙宪忠,还是反对物权行为理论者如梁慧星、陈华彬,都强调物权行为理论的交易安全保护功能。孙宪忠认为区分原则的实践价值一是保护非违约当事人的请求权,二是确定物权变动的时间界限,保护第三人的正当利益。参见孙宪忠:前注6引书,第175-178页。梁慧星主编的《中国物权法研究》中,反对物权行为理论的第一个理由是该理论属于19世纪而不属于20世纪更不属于21世纪,第二个理由就是质疑物权行为理论的交易安全保护功能。参见梁慧星主编:《中国物权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73页。)如果认为物权合同理论是为了保护交易安全才提出来的解释,这种“目的论的解释”(第194页)可真就有点“大炮打蚊子”了(第192页)。因为按照雅科布斯的分析,“物权合同学说随着债的概念的发展而完善,并非因保护交易的思想”(第187页)。
债的概念是什么?胡果分析罗马法原始材料得出的结论是,“在诉讼外形成的请求权中,债权人会问:请求权针对谁?当某种法律关系产生的请求权受到侵害时,在这种诉讼中,债权人也会问:请求权针对谁?但是在所有权中,没有人会问请求权针对谁。因为所有权的请求权是对世权,而不象债和诉讼那样,与世界上的其他人都毫无关系”(第183页),因此,“债是一种权利,其针对的对象并非物,而是另外一个人;债权使这个人失去对享有除某个债权中所指的行动自由权以外的全部普遍自由,这个行动因为被排除(此排除并不排斥他人)出自由的范围,所以不再是可以作的行动,而是必须作的行动”(第183页)。对债的这一理解,在萨维尼的作品中同样有所体现。(注:关于萨维尼的权利理论,参见前引萨维尼:《当代罗马法体系》(第1卷),第333-345页。)
既然债仅仅是涉及他人行为,那么所有权转让当然就需要关于所有权转让的意思表示与受让的意思表示的一致,而不仅仅是关于债的意思表示(第186页),这样,胡果基本上完成了物权合同理论的主要内容。既然胡果已经完成了该理论的主要内容,因此,萨维尼的主要贡献不在于提出该理论,而是“在胡果为建立私法体系而开始的思考基础上的继续发展”(第189页)。至于讨论所有权转让的法律基础无效或者不存在的情形下所有权转让的效力问题时,萨维尼认为“源于错误的略式转让”(注:其中的“略式转让”通常译为“交付”,但它并不现代法中占有转移意义上的“交付”。因此,萨维尼并不是认为现代法中占有转移意义上的交付是合同。孙宪忠在分析交付的性质时,认为交付不是事实行为,并且引用了萨维尼“交付也是一个契约”的论述,但是,该分析缺乏说明力。孙宪忠一方面认为交付是占有转移,另一方面又认为“没有当事人之间这种确定发生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只有事实状态的标的物的转移,不能成为物权法上所说的交付,或者不能发生物权法上交付的效力,即有效的物权变动的效力”,这样,就把占有转移的效力转变成物权变动的效力,显然隐含了占有是物权的前提。但是,该书前文却提到占有是事实状态,占有并不必然表明主体拥有权利。参见孙宪忠:前注6引书,第251-252页;第83页。)也是“完全有效”的,是因为他根本没有考虑当事人误以为存在有效原因而转让所有权的情形,该问题应当在后面的章节讨论(第193页)。由此可以判断出,萨维尼同样认为物权行为理论是先验正确的(第192页、第194页),不需要从目的论的角度加以说明。(注:雅科布斯在这里同样批评了自己的老师弗鲁沫(Flume)在这一问题上的见解。后文同时也指出弗鲁沫在非债清偿基础的给付效力问题上也没有附合他的老师舒尔茨。这似乎有点仿效其师的意味。但是,这种认真对待学术而不是看人说话的态度,颇值学习。)
雅科布斯的分析,仅仅考虑了物权行为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坚持法学体系的要求,对于物权行为理论所体现的民法体系背后的理念并未加以深究。这也许是出于述而不作的想法。但是,如果我们结合萨维尼的权利理论进行分析,就会发现物权行为无非是贯彻物权法中的私人自治而已:权利乃是人对标的的意思支配,债权是人对他人行为的意思支配,物权是对人对物的意思支配;人按照自己的意思改变对他人行为的意思支配,形成债权行为,按照自己的意思改变对物的意思支配,形成物权行为。(注:萨维尼:同注7引书,第333-345页。萨维尼关于权利本质的见解,曾经为中文文献所提及,但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其理论说明更是不为学界所重视。)
四、余论
雅科布斯的文章,值得重视的不仅仅是上述两方面内容,还有许多见解也颇具价值。
一般提到《德国民法典》时,总会把它与五编制法典编纂体例相联系,(注:例如,谢怀栻曾明确指出,德国民法典在形式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它的五编结构。参见谢怀栻:“大陆法国家民法典研究”,载《谢怀栻法学文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407页。同时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6页。)但雅科布斯明确指出,“德国民法典编纂的体系特点并不是五编制,也不是在法典的开始设置总则编,而是对债法和物法截然分开”(第182页至第183页)。如何区分物法和债法,似乎是一个值得重视并且已经得到重视但其结果尚不能令人满意的问题。
雅科布斯关于反对物权合同理论的概括,也非常有意义。他概括了对物权合同理论的两类批评:来自日耳曼法学家的批评和来自比较法学家的批评(第161页至第166页)。这种对反对见解的归纳,有助于我们发现批评意见的共同之处:日耳曼法学者的反对意见集中在物权合同理论并非日耳曼法所固有,因此不应坚持;比较法学家的意见集中在其他国家不采物权合同理论,德国也无必要采此理论(第161页至第166页)。同样,如果留心分析,似乎还可以进行其他研究,例如,日耳曼法学家反对物权行为理论的理由似乎与纳粹的法律学说之间存在某种联系。(注:雅科布斯关于该问题的见解,通过反驳拉伦茨的见解得到体现:“拉伦茨确信这些作者的看法都不是由政治意识决定的;诚然,如果民族思想能不属于政治意识,那么拉伦茨的看法就是正确的。”对此还应当进行详细的分析。参见田士永:前注4引书,第379-380页。)
对中国立法是否应采物权合同理论,雅科布斯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认为“中国立法在法学界未澄清这一问题之前,不应该在法典中规定它”(第166页)。这一建议不应该被简单认为中国法不应采物权合同理论,而应注意到其前提是“法学界未澄清这一问题之前”。理解雅科布斯的建议,应当与他在该书中区分影响立法的政治因素和技术因素的见解相联系,这也许是他将该文作为该书后记的一个理由。与此相关,值得中国法学界反思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已经澄清了物权合同理论问题?进一步还应当考虑:我们已经澄清了民法中哪个问题?民法典的理论准备是否已经充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