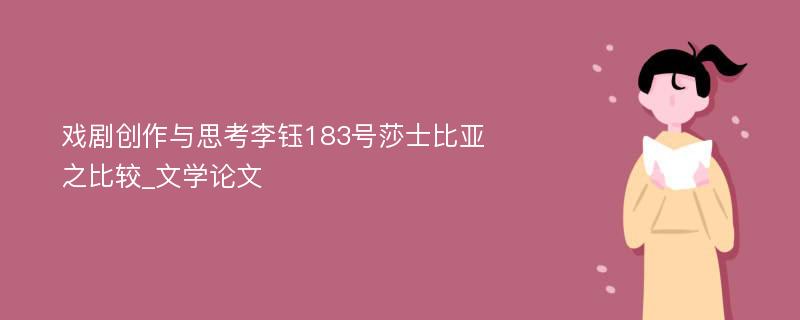
戏剧创作与偶数思维 李渔#183;莎士比亚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莎士比亚论文,李渔论文,偶数论文,戏剧论文,思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成双作对
对称,是自然界生态平衡的一种形式美,也是人类的心理和文化特征之一。在文学艺术创作中,对称被广泛地运用着。无论是东方的李渔还是西方的莎士比亚,在他们的作品中,处处向你显示着这个自然美的法则和心理、文化特征。
对偶,对联,或对仗,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先秦以至近代,全部古典作家都是这一文化的传承者,而李笠翁则是一位入了魔的对偶癖。
我国的古典作家大都编纂过自己的作品全集,一般收录诗歌和文章两大类。李渔的《一家言全集》却不然,除诗文之外,还辑录楹联178题(有不少为一题数联)之多。这在我国士大夫文集中是不多见的。笠翁登山临水,好作诗也好作楹联,不用说,诗中有联,联中有诗,诗联二位一体,是这些作品的共同特色。他登庐山,登金山寺,登燕子矶,登黄鹤楼,以及游其他名胜古迹,无不留下了属对工整的楹联。楹联,是文章与书艺的统一体,是我国的民俗文化之一,又是庭园装饰艺术之一。凡宫观寺院,楼台亭阁,酒肆歌场,官邸民宅,无楹联便不雅。长期以来,民间无论婚丧嫁娶,祝寿贺迁,无不以楹联相赠。笠翁在浙久负文名,除了他本人应酬亲友的联作之外,自然也成为四方登门求联的作家。以卖文鬻艺为生的笠翁,对于上门送润笔求联者,自然是乐于从命的。久而久之,成双作对的艺术思维,就在笠翁心理上积淀而形成了定势。这就是李渔成为千古作家中的对偶癖的原因。
在我国的古典文学中,辞赋、骈文、律诗,都是以对仗为基本特征的体裁。但是,散文、小说和戏剧,则很少有人在对仗上下功夫者。笠翁却不然。他的小说,不仅继承“三言三拍”在题目上做对联,而且叙事语也是三行一联,六句一对,以纷至沓来的通俗对偶辞刻划人物,描绘情景,讲述故事。例如:《谭楚玉戏里传情,刘藐姑曲终死节》中有:“别人把他当做心头之肉,他把别人当做眼中之钉”;“情愿守我的贫穷,不敢享你的富贵”;“先把几句傲世之言,挫去他的骄奢之色;后把许多利害之语,攻破他的利欲之心”;“远追严子陵的高踪,近受莫渔翁的雅诲。”《妻妾败纲常,梅香完节操》中有:“小似他的,当嫁不肯嫁;大似他的,要嫁不好嫁”;“无中生有,是里寻非”,“寒不与衣,饥不与食,忽将掌上之珠,变作眼中之刺”;“躲了雷霆,撞了霹雳,不见菩萨低眉,反惹金刚怒目”;“孩子不是容易领的,好汉不是容易做的”;“看不过孩子受苦,忍不得家主绝嗣”。读笠翁小说,类似这样的联语,教你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接。小说语言如此,戏剧语言更是锦上添花。在笠翁十种曲里,人物的上场诗和下场诗,以及各种按曲牌填写的唱词,其中对偶触目皆是,这倒不奇。因为对仗是我国古典诗歌体裁的本色,是题中应有之义。奇的是人物道白,都是一篇一篇的微型骈文。例如《蜃中楼》里的柳毅自报家门道:
“小生柳毅,字士肩,潼津人也。眼空千古,才擅一时。唾余舍去尽奇珍,词颦怎效;社刻投来皆苦海,诗眼难青。时流争羡风姿,道我飘飘若神仙之侣;古道常留颜色,所云噩噩似羲皇上人。不幸早背椿萱,未谋家室;六亲羞附,四壁甘贫。”
这种骈体道白,在笠翁剧作中并非个别现象,而是通则。不论生、旦、净、末、丑,都会象柳毅这样自出自对地说话,不过根据人物身份之不同而有雅俗之分而已。以骈体写道白,高则诚《琵琶记》已开先河。但这一特色也早已遭到本色派戏曲家们的一致讥诮。笠翁对本色派的批评居然置若罔闻,而且变本加厉,这说明他不仅嗜偶成癖,也是他勇于在戏剧创作上和理论上自成一家、独树一帜的表现。
笠翁之酷爱对称,尤其体现在他的小说、戏剧的结构上。他的浪漫小说和浪漫喜剧都是以传奇式爱情为主题,这些作品中的爱情故事多由平行并列的两条线索纠结而成。正如《蜃中楼》传奇第五出里借剧中人东华上仙之口所说的:他的爱情文学常采用“四个男女”、“两对夫妻”的双线结构。例如小说《鹤归楼》,描述两对才子佳人——郁子昌与围珠小姐、段玉初与绕翠小姐的悲欢离合故事。属于这种结构的笠翁喜剧更多。《蜃中楼》描述柳毅与舜华、张羽与琼莲两对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故事,《意中缘》描述董其昌与杨云友、陈继儒与林天素两对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故事,《风筝误》则描述一对才子佳人与一对净丑夫妻之间的种种交叉误会。但由于笠翁还醉心于传统的一夫多妻制,所以他的浪漫文学双线结构并非总是“四个男女”组成的“两对夫妻”。基于一夫多妻制,他常常在剧中安排两组夫妻,每一组都是一夫二妻或一夫三妻。例如《慎鸾交》是两组一夫二妻,《奈何天》是两组一夫三妻。
在中外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里,有一个三反复模式,凡关键性情节均反复三次。三顾茅庐、三让徐州、三气周瑜、三休樊梨花、三难新郎、三戏白牡丹,以及普希金的《金鱼的故事》等均是。可是在李渔的浪漫喜剧里,却有一个二反复模式,凡关键性关目,均不多不少反复两次。在《意中缘》里,前有和尚假意替杨云友做媒,后有道婆真心替杨云友做媒;前有丑阉人黄天监冒充新郎,后有俏女子林天素冒充新郎。在《风筝误》里,前有净角戚友先放风筝放进旦角詹二小姐院子,后有生角韩琦仲放风筝放进丑角詹大小姐院子;前有韩琦仲“惊丑”于詹大小姐,后有韩琦仲“诧美”于詹二小姐。这种二反复模式,也体现在剧本的出目上。如《意中缘》,第25出“遣媒”是对第7出“自媒”的照应,第28出“诳姻”是对第11出“赚婚”的照应。再如《巧团圆》,第24出“认母”是对第11出“买父”的照应,第33出“哗嗣”是对第5出“争继”的照应。笠翁喜剧中大量阴错阳差的巧合与误会,无不是成双作对地出现。
但是,笠翁剧作中的自我反复并非前后照葫芦画瓢式的自我雷同。雷同是与创新相悖的大忌。笠翁的二反复是形似而实异,往往是美丑善恶的强烈对照。好比诗歌里的押韵,后一字与后一字韵母相同,而词义各异。《意中缘》里的“自媒”和“遣媒”两出戏,是媒约之言的反复,但前者是暴露恶德,后者是昭彰善德;“赚婚”和“诳姻”两出戏,是婚姻骗局的反复,但前者是骗人下火坑,后者是送人进福窝。在《巧团圆》里,“买父”、“认母”都是歌颂主人公姚继敬老惜孤的美德,但两出戏在“卖”字上做的文章正好相反,“买父”是悬标明卖的结果,“认母”是被装在袋子里瞎卖的结果;“争继”与“哗嗣”都是写宗祧纠纷,但前者讽刺为钱财而争父,后者赞美为人情而争子。
总之,笠翁喜剧的成双作对艺术特色,全方位地体现在辞藻、人物、故事情节、细节等各个方面。
对偶也是莎士比亚剧作的一个显著艺术特色。爱情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抒情对偶辞是著名的。在莎翁喜剧中,也不乏脍炙人口的抒情对偶辞。试看《仲夏夜之梦》第一幕第一场的对偶辞:
赫米娅 我向他皱着眉头,但是他仍旧爱我。
海丽娜 唉,要是你的颦蹙能把那种本领传授给我的微笑就好了!
赫米娅 我给他咒骂,但他给我爱情。
海丽娜 唉,要是我的祈祷也能这样引动他的爱情就好了!
赫米娅 我越是恨他,他越是跟随着我。
海丽娜 我越是爱他,他越是讨厌我。①
(朱生豪译文)
莎翁剧作的对偶特色也体现在人物设计和情节结构上。他的许多浪漫喜剧,如同笠翁一样,是由“四个男女,两对夫妻”搭成的双线结构。例如:《维洛那二绅士》描述凡伦丁与西尔维娅、普洛丢斯与朱利娅两对恋人的悲欢离合故事;《无事生非》描述克劳狄奥与希罗、培尼狄克与贝特丽丝两对英雄美人的婚恋曲折经过。
但是,莎翁一如笠翁,并非死抓住“四个男女,两对夫妻”一成不变。笠翁把一夫多妻制引入双线结构,化出了六个男女两组夫妻,八个男女两组夫妻之类的对称情节。西方自基督教化之后,一夫多妻制便已消亡,莎翁只能在一夫一妻制前提下去打破“四个男女,两对夫妻”的格局。
以双倍“四个男女,两对夫妻”的人物设计,形成复式双线结构,是莎翁喜剧双线结构的变种之一。例如在《皆大欢喜》中,四个男女贵族组成两对贵族夫妻,四个男女平民组成两对平民夫妻。这样,两两相对,两对贵族夫妻自成一个双线结构,两对平民夫妻亦自成一个双线结构,两对贵族夫妻与两对平民夫妻又形成一个双线结构,从而建构起多层次双线结构系统。
双线一楔子,是莎翁经常采用的结构模式。在许多浪漫喜剧中,莎翁设计了三对恋人。但他们在剧中并非鼎足三分,而是以两对恋人生发出两条爱情线贯穿全剧,而以第三对恋人作点缀性描绘,穿插在剧中或剧尾。这些剧作仍然是双线结构,只是在双线之间插入了一个楔子而已。《错误的喜剧》以大安提福勒斯与露西安娜、小安提福勒斯与阿德里安娜这两对夫妻的故事为主体,而以小德洛米奥与露丝这一对夫妻的故事点染于其间。《驯悍记》以彼特鲁乔与凯瑟丽娜、路森修与比恩卡这两对夫妻的故事为主体,而以霍坦西奥与寡妇的成婚点缀于剧末。《威尼斯商人》以巴萨尼奥与鲍西娅、葛莱西安诺与尼莉莎这两对夫妻为贯串线,而以罗兰佐与杰西卡这一对恋人穿插于剧中。《爱的徒劳》是双倍双线一楔子。剧中由八个男女贵族配成四对恋人,即那瓦国王与法国公主、俾隆与罗瑟琳、朗格维与玛利娅、杜曼与凯瑟琳。此外,还有亚马多与杰奎妮妲这一对平民恋人穿插在其间。
在莎翁喜剧的双线结构里,还有一楔再楔乃至三楔者。如《仲夏夜之梦》,主要是描述拉山德与赫米娅、狄米特律斯与海丽娜这两对恋人之间的种种爱情危机与对爱情的重新确认。为烘托他们的爱情危机,莎翁在剧中穿插了仙王仙后的爱情危机;为烘托他们对爱情的重新确认,莎翁在剧末又缀以公爵成婚以及剧中剧皮拉摩斯与提斯柏的忠贞爱情。
一般地说,莎翁浪漫喜剧里的情侣数目,大大超过了笠翁浪漫喜剧。笠翁一般为两对或两组,莎翁则多为三、四、五对,给人以眼花缭乱之感。但若细加辨析,这些情侣们纷纷登场亮相的喜剧,其实都没有超出双线结构的范围。
主次相依
对称是原始视觉艺术和古典视觉艺术的基本特征。因为对称使观赏者的左右两个大脑半球所接受的刺激处于平衡状态,从而产生一种极其舒畅自然的心理反应。但是,随着艺术史的发展,严格的对称越来越少,而由平衡的心理体验所取代。基于这一要求,在一幅由两部分组成的构图中,上一部分应小于下一部分,否则给人以轻重倒置的不稳定感;纵深部分应小于前置部分,否则令人感觉前后两部分大小不一。这一视觉艺术中偏正结合的对称原理,体现在语言艺术中,就是双线结构的主从相依法则。
李渔《一家言·器玩部》有论“忌排偶”一则,指出“胪列古玩,切忌排偶”,即不可“左置一物”,右必置“一色相俱同者”。这就是反对严格的对称。但是他却主张偏正结合、主从相依的对称。他说“天生一日,复生一月,似乎排矣。然二曜出不同时,且有极明微明之别,是同中有异,不得竟以排比目之矣。“笠翁的这种视觉艺术对称观,一以贯之于他的戏剧艺术结构观。
笠翁戏剧理论中有所谓“立主脑”和“减头绪”的主张,其实质是要求剧本结构做到主次分明。他说:“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宾,原其初心,止为一人而设。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终,离合悲欢,中具无限情由,无穷关目,究竟俱属衍文,原其初心,又止为一事而设。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②在这里,笠翁强调的一面虽然是作为“主脑”的“一人一事”,但同时也指出还有作为“陪宾”和“衍文”的其他人物和关目。他是主张“主脑”与“陪宾”相依存的。为什么笠翁在论述这一主从相依原理时特别强调不可喧宾夺主呢?这就与他那个时代的戏剧创作密切相关。他指出:明代戏剧创作的大弊是“头绪繁多”,“令观场者如入山阴道中,人人应接不暇”。③这种情况,在笠翁之前,已有不少戏剧评论家指出过。徐复祚在《曲论》中批评过张伯起《红拂记》“头脑太多”;祁彪佳在《远山堂曲品》中批评过柳某《翡翠钿》“头绪过繁,大有可删处”。由此可见,李渔在总结元明清以来戏剧结构的创作经验时,提出“立主脑”和“减头绪”口号,乃是有感而发;而作为这两个口号的理论基础,实系主次相依的对称法则。
笠翁以自己的戏剧创作,实践了自己的戏剧理论主张。他的浪漫喜剧,多系主从相依的双线结构。例如《玉搔头》,写皇帝携宠臣朱彬微服私行,访寻佳丽。二人访至妓女刘倩倩家,皇帝与刘倩倩缔婚,朱彬与刘家厨娘缔婚。两对夫妻,前主后从。第8出“缔盟”,写皇帝与倩倩一见钟情,山盟海誓;其间同时穿插几笔,交代朱彬与厨娘的缔亲情节。第11出“赠玉”,写皇帝与倩倩赋别,难分难舍;末了也将朱彬与厨娘的难分难舍点染几笔。这种主子配主子,臣仆配臣仆,以臣仆烘托主子的双线结构,不禁使人想起了莎翁《错误的喜剧》和《威尼斯商人》。
笠翁的其他双线结构喜剧,也多是主次分明的。《风筝误》以韩琦仲、詹二小姐为主线,以戚友先、詹大小姐为副线;《慎鸾交》以华中郎、王又嫱为主线,以侯永士、邓蕙娟为副线;《意中缘》以董其昌、杨云友为主线,以陈继儒、林天素为副线;《奈何天》以阙里候连娶三美为主线,以袁滢娶一丑二美为副线。但笠翁喜剧的双线结构也有个别主次不甚分明的,就是《蜃中楼》。此剧捏合元杂剧《柳毅传书》和《张羽煮海》,以生角饰柳毅,以小生饰张羽,可知笠翁初衷以柳毅故事为主线,以张羽故事为副线。剧本第20出以前,写二生同觅佳偶,而以柳毅的动作线为主。第6出“双订”和第18出“传书”为突出描述柳毅与舜华的爱情故事之重场戏。前一场写喜情,后一场写哀情。因此,在前半本戏里,主次是分明的。但自第20出以后,直至第30出结束全剧,这十出戏的主角转到了小生饰演的张羽身上。原《柳毅传书》中的柳毅至龙宫传书的情节,在第20出“寄书”里已移花接木由张羽来完成。接下去,原《张羽煮海》中的煮海情节,原封不动地保留在下半本戏里。很显然,这是由于捏合两个故事未能化成一炉,以致出现这种所谓“两家门”的结构缺陷。剧本第26出里,丑角在吊场的末尾有“两京十三省”的念白,这是明代的行政区划。明代以北京为首都,以南京为陪都,并分全国为十三省。这说明李渔作此剧时尚未入清,是他的早期习作。明乎此,我们对李渔在理论上强调“立主脑”却在创作上把不定主脑的反差现象,就不会以为奇怪了。
莎翁虽然没有在理论上提出过主次分明的双线结构主张,但是,他的浪漫喜剧中的情侣不论是两对、三对,还是四对、五对、六对,其基本形态还是属于主次分明的双线结构。例如《温莎的风流娘儿们》有两条爱情线索。一是二女戏一男,即福德太太和培琪太太捉弄害单相思的福斯塔夫。这颇似我国《红楼梦》里的王熙凤设圈套捉弄害单相思的贾瑞。二是三男争一女,即斯兰德、卡厄斯和范顿争娶安小组。两条线索,前主后从。后一条烘托前一条。又如在《威尼斯商人》的双线结构里,巴萨尼奥与鲍西娅的故事是主线,剧中的主要情节如安东尼奥向夏洛克借高利贷,三匣传奇,以及法庭斗智等,都是为表现这一主线而设。葛莱西安诺与尼莉莎的故事,则属于烘托式的副线。至于《皆大欢喜》这种复式双线结构,就具有多层面主从相依的特色。在奥兰多、罗瑟琳与奥列佛、西莉娅这两对贵族情侣中,前主后从;而这两对贵族情侣与另两对平民情侣,又构成前主后从的另一层面的主从相依关系。有些莎剧貌似头绪纷繁,颇给人以“剪不断,理还乱”之感。但只要你牢牢抓住了它的主从相依双线结构这个纲,就不致迷离扑朔如堕迷魂阵了。
映衬对照
恰如中国文章学里的对仗法则有正对与反对之分,在戏剧学的结构法则里也有映衬与对照之别。映衬相当于正对,对照相当于反对。笠翁喜剧以及莎翁的喜剧和悲剧,无不蕴含着丰富的映衬和对照。
对仗是中国古典诗歌格律之一。对仗分为正对和反对两种。上下两句,在字面上互相映衬者谓之正对,在字面上彼此对照者,谓之反对。李渔《一家言》诗文全集中的正对和反对,触目皆是,唾手可得,估计超过其全部文字的50%。他把这两种对仗技法运用于戏剧结构,就产生了正对型的双线映衬结构和反对型的双线对照结构。
笠翁的《意中缘》、《蜃中楼》、《奈何天》都属于映衬式的双线结构。《意中缘》描述四个男女画家——两对才子佳人故事。董其昌、陈继儒都是隐迹于西湖的著名书画大师,杨云友、林天素都是沉沦于社会底层并擅长模仿董、陈二名家手笔的才女。杨善模董,林善仿陈。由于这种笔墨姻缘,成就了董杨之婚与陈林之恋。董杨之婚遭遇了一场无赖骗婚才女的波折,陈林之恋也遭逢了一场佳人身陷贼营的波折。这一剧二线,从人物到情节,彼此相似,互相映衬。《蜃中楼》也属于这种情况。在《奈何天》传奇里,徒唤“奈何天”者,不止丑夫阙里侯的三房美妻,还有一个被丑妻害得家破人亡的潘貌才子袁滢。剧中的两条美丑姻缘情节线,彼此映衬,相得益彰,由此更加突出了封建时代士大夫心目中的美丑姻缘之不幸。
笠翁浪漫喜剧也有不少是对照式的双线结构。《风筝误》是一出对《奈何天》的翻案戏。《奈何天》专写美丑姻缘并为之鸣不平,《风筝误》则为才子佳人式的理想婚姻唱赞歌。剧中的韩琦仲与詹二小姐是一对才貌相兼的夫妻,是剧作家以及他那个时代士阶层婚恋审美理想的载体。戚友先和詹大小姐,则是一对村夫丑妇,是那时代士大夫婚恋审美理想的负面价值的载体。两对夫妻,正反对照,黑白分明。《慎鸾交》又是另一种对照。该剧中的两对夫妻,都是才子佳人,但是两对才子佳人却有截然不同的命运和表现。华中郎的大妻主动劝夫纳妾,反之,侯永士的大妻却反对丈夫纳妾。华中郎本无意纳妓为妾,但既纳之后,就克始克终,不因富贵而改变初衷;侯永士却反是,他一心要纳妓为妾,然而一旦红袍加身,就要毁弃前盟。总之,两对才子佳人,从正反两面寄寓着剧作家的伦理价值取向。他肯定的是落后的一夫多妻制及其制度下的宽容大度的“贤妇”,也肯定了对爱情的坚贞不渝;他批判的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一夫一妻制,以及抵制丈夫纳妾的“妬妇”,也批判了富贵易妻的错误行为。恰如剧中人卜康民对华中郎之父所说:侯永士与华中郎“一反一正,竟是两股绝妙的文章”。笠翁借剧中人之口,把揭示主题思想的正反对照双线结构和盘托出来了。从这一双线对照的内涵看,作为新旧交替时代的文化代表人物的李渔,其思想矛盾是极为鲜明的。类似的双线对照结构,也出现在笠翁小说中,如《鹤归楼》、《遭风遇盗致奇赢,让本还财成巨富》等都是。
莎翁浪漫喜剧的双线结构,同样分为映衬式和对照式两种。
映衬式是莎剧双线结构的主流,不但喜剧中有很多,悲剧中也有,例如《李尔王》里的李尔被女儿抛弃,葛罗斯特被儿子抛弃,主从二线互相映衬。莎翁喜剧中类似这样的结构占一半以上。《无事生非》中有两对情侣:克劳狄奥与希罗,培尼狄克与贝特丽丝。前一对先和后吵,后一对先吵后和。两个故事指向一个共同主题:爱情的本质乃是两性之间在婚恋审美理想上的完美和谐的统一,而争吵则是与爱情本质背道而驰的。剧情告诉人们:两个争吵都是无事生非。剧本标题Much Ado About Nothing就是揭示这一主题的,如果用中国谚语对译,也可以叫做“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温莎的风流娘儿们》是一出揶揄单相思的喜剧。福斯塔夫对福德太太和培琪太太的爱情是单相思,斯兰德和卡厄斯对安小组的爱情也是单相思。两线互相烘托。《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是《一报还一报》式的双线结构。该剧副线是海伦背弃了墨涅拉俄斯,主线是克瑞西达背弃了特洛伊罗斯。换一个角度说,就是帕里斯破坏了墨涅拉俄斯的婚姻,狄俄墨得斯也破坏了特洛伊罗斯的婚姻。从民族关系上说,就是特洛亚人破坏了希腊人的婚姻、家庭与爱情,希腊人也破坏了特洛亚人的婚姻、家庭与爱情。莎翁的这一创作意识,颇与中国佛教的报应文学相似,即所谓淫人妻女者人亦淫其妻女。此外,《错误的喜剧》、《爱的徒劳》、《第十二夜》、《威尼斯商人》、《仲夏夜之梦》、《皆大欢喜》等,都属于这种映衬式双线结构。
对照式双线结构在莎翁喜剧中略少一些。《驯悍记》由两个爱情故事组成。一个是彼特鲁乔妙计赢得凯瑟丽娜的爱情,另一个是路森修妙计赢得比恩卡的爱情。凯瑟丽娜的悍泼与比恩卡的温顺形成性格对照。比特鲁乔以悍驯悍,路森修以情取情,形成情节对照。莎翁的《维洛那二绅士》写一对好友凡伦丁和普洛丢斯先后坠入爱河的故事,在这一点上颇与笠翁的《蜃中楼》相似,但二剧在处理朋友关系上截然不同。《蜃中楼》里的好友在寻偶中互相帮助,《维洛那二绅士》里的好友在寻偶中变为情敌。两剧结构产生这种映衬式与对照式的差别决非偶然,而与中西不同伦理规范息息相关。李渔虽然有不少商人气质,但其思想核心仍属于中国的传统儒教。儒家五伦中的第五伦,是关于朋友之间的人际关系道德准则——守信。《蜃中楼》里的柳毅和张羽的关系,就是这种道德准则的艺术化。西方伦理学德目中无五伦,无论贵族平民处理朋友关系,除了感情纽带之外,别无伦理约束。尽管文艺复兴时代的西方人看重友谊,就象《威尼斯商人》中的安东尼奥与巴萨尼奥;但若友谊与自身利益发生矛盾,即使牺牲友谊也不算恶德,正如普洛丢斯说的:“自己比朋友更宝贵”。普洛丢斯本来答应协助凡伦了偕恋人西尔维娅私奔,但一转眼就去向西尔维娅的父亲告密,并处心积虑夺取西尔维娅。他的背信弃义行为与柳毅、张羽的信守诺言行为正好针锋相对。普洛丢斯的这种自我中心主义,乃是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精神动力。莎士比亚对此是持批判态度的。他的批判武器当然不是中国的儒家五伦,而是人文主义。
偶数思维
美籍华人学者张光直指出:中国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其结构特点是“成双成对,左右对称”。张氏还认为:“二分制度是研究商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关键”。其显著表现有:小屯商代的宫殿——宗庙分为东西两列;商代王陵分为东西两区;龟版上的卜辞分为左右两组;安阳商代诸王礼制分为新旧两派(据董作宾甲骨卜辞研究);同一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分为AB两种风格(据Bernhand Karlgren统计)。④这种人类幼年时期视觉艺术(青铜器纹样)与语言艺术(卜辞)的对称性结构的出现,是基于同一艺术心理机制即偶数思维法则的。
文学作品中的对偶、对仗和双线结构,是作家的偶数创作心理外化的结果。在艺术构思中,想到坏人坏事,同时就联想到另一桩类似的坏人坏事,或与之相反的好人好事。这种联想的结果,不是产生映衬式的对仗或双线结构,就是产生对照式的对仗或双线结构。
李渔小说《重义奔丧奴仆好,贪财殒命子孙愚》,描述富翁单龙溪的子孙无情,奴仆重义,就是将子孙与奴仆加以对照。在小说的结尾,笠翁生发议论,又把这一对照翻了一番,变成复式对照,即将小说中的义仆百顺与明嘉靖年间的义仆徐阿寄媲美,将小说中的单氏子孙与春秋时齐桓公之五子并论,从而得出结论:“这四桩事,却正好是天生的对偶”。这说明,无论艺术思维或逻辑思维,都受对偶心理即偶数思维的制约。
在现实生活中,笠翁每遇到一桩可入传奇的事,一旦进入创作,就会化奇为偶。《生我楼》、《巧团圆》、《意中缘》等作品均如此。这种从素材到作品的化奇为偶现象,最足以显示偶数思维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
清初王士祯曾记述琐闻一则如下:
“顺治初,京师有卖水人赵逊者,未有室。同辈聚金,谋为娶妇。一日,于市中买一妇人归,去其帕,则发毵毵白,居然妪也。逊曰:‘妪长我且倍,何敢犯非礼?请母事之。’居数日,妪感其忠厚,曰:‘聚钱本欲得妇耳,今若此,反为君累,且奈何?吾幸有藏珠一囊,纫衣中,当易金为君娶妇,以报德。’越数日,于市中买一少女子,入门,见妪,相抱痛哭,则妪之女也。盖母子俱为旗丁所掠而相失者,至是,皆归逊所。妪即为之合卺成礼。妪又自言洪洞人,家有二子。今尚存珠数颗,可鬻之为归计。乃携婿及女俱归。二子者固无恙,一家大喜过望。妪乃三分其产,同居终其身。”⑤
焦循以为笠翁传奇《巧团圆》的题材采自这则琐闻。⑥可信。因为笠翁与王士祯为同时代人,上述颇富传奇性琐闻在当日必不胫而走,流布朝野。于是王采录为笔记,李创作为戏文。不过李从此一妪,又虚构出一叟。
真实生活中发生了买母奇事,笠翁的艺术虚构里就出现了买母、买父奇事两桩——《巧团圆》。同样地,真实生活中有了龚芝麓、顾媚这一对画坛名士与名妓,笠翁的艺术虚构里就出现了董其昌、杨云友与陈继儒、林天素这两对画坛名士与名妓。尽管董其昌、陈继儒也都是真实人物,但李渔把他们双双纳入一剧,无疑是偶数思维的心理定势所决定的。
笠翁不仅将生活奇遇化单为双,而且将前人传奇化单为双。他的《蜃中楼》,就是把两本单线结构的元杂剧——《柳毅传书》与《张羽煮海》变成联珠合璧的。
无独有偶。莎翁喜剧创作的“打炮戏”《错误的喜剧》,也是将前人作品《孪生兄弟》中的一对孪生兄弟增为两对,加以改编而成。
通观李渔的全部文学创作,几乎所有的重要艺术构思,都要自我反复一遍。其戏剧故事在小说中反复一遍,如《巧团圆》与《生我楼》,《比目鱼》与《谭楚玉戏里传情,刘藐姑曲终死节》;其每一剧作构思在另一剧作中反复一遍,如一男求三美的《奈何天》与三美求一男的《凰求凤》;其剧中重要关目,在同一剧中反复一遍,如《意中缘》里的天阉假新郎黄天监与女扮男装的假新郎林天素,“天监”与“天素”者,天生之假丈夫是也。
尤其是,笠翁毕生剧作不是九个或十一个,正好是十个五双,也决非巧合。笠翁十种曲的五双配搭如下:
《比目鱼》与《巧团圆》。二剧均写一男一女的爱情波折与悲欢离合;男主人公均系流落异乡的孤儿,以沉沦于社会底层开始,以荣登黄榜告终。二剧均以起“死”回生关目结束:《比目鱼》里的刘文卿夫妇剧终时找到了“亡”女,《巧团圆》里的尹小楼夫妇剧终时发现了“亡”儿。
《蜃中楼》与《意中缘》。二剧均写一对好友在情场上的互相帮助,均写两对才子佳人的可意姻缘。二剧各两组婚姻,均彼此映衬。
《风筝误》与《慎鸾交》。二剧均写两组姻缘,但一组美满,一组有缺陷,两组婚姻互相对照。
《怜香伴》与《玉搔头》。二剧均写一夫二妻的婚恋佳话,男主人公均改名易姓而获致佳偶,女主人公均结为异姓姊妹。《怜香伴》里的“并封”与《玉搔头》里的“媲美”,均写二女并受皇恩,不分轩轾。总之,二剧均系舜娶尧之二女神话原型的再现。
《奈何天》与《凰求凤》。二剧均写一男三女的婚恋纠葛。媒婆穿插于两剧中,是制造婚姻纠纷的宵小。《奈何天》里三女拒一男,同避“奈何天”;《凰求凤》里三女求一男,共聚“求凤堂”。
对上述五双剧目作出宏观把握之后,我们就会相信:偶数艺术思维定势决定了笠翁每创作一个剧本,必然要再创作一个与之相匹配。他的剧作一如他的楹联、律诗,及其他充满了骈四骊六的散文、小说,总是成双作对地构思和写作出来的。
这种偶数思维也不仅为李渔所独具,而是中国传统的艺术思维,几乎绝大多数古今作家都不可能跳出这一思维模式。即使现代文豪鲁迅,他编文集都有一个成双作对的爱好。如《呐喊》对《傍徨》,《朝花夕拾》对《故事新编》,《二心集》对《三间集》,《伪自由书》对《准风月谈》之类。由此我们看到了汉族文学的一个根本文化特征——偶数艺术思维。但这一心理机制中西不分,只不过在中国汉族文学中表现得特别突出而已。
偶数思维的心理机制,是客观世界对称法则在人的主观上的反映。黑格尔论述外在美时指出:平衡对称是抽象形式美的一种。这种美的法则体现在自然界的大量事物上。例如:人有两只眼睛、两只胳膊、两条腿;矿物、植物、动物等的构造,也基本上符合对称法则,如花瓣的形状和排列。⑦不过,黑格尔是站在唯心论立场来论述这个问题的。他把抽象形式美的对称法则作为第一性,而把自然界的大量对称现象作为第二性。我们只要把被他颠倒了的因果关系颠倒过来,就是正确的了。这就是说,意识形态中的对称美,乃是客观存在中的对称美的反映;对称美的客观存在,培养了人类的偶数思维法则。
注释:
①莎剧《仲夏夜之梦》第一幕第一场对偶辞的原文如下:
Hermia I frown upon him,yet he loves me still.
Helena O that your frowns would teach my smilles such skill!
Hermia I give him curses,yet he gives me love.
Helena O that my prayers could such affection move!
Hermia The more I hate,the more he follows me.
Helene The more I love,the more he hateth me.
②李渔:《间情偶寄·词曲部·结构》。
③李渔:《间情偶寄·词曲部·结构》。
④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第46、第63页。
⑤王士祯:《香祖笔记》,卷四。
⑥参见焦循《剧说》,卷三。
⑦参见黑格尔《美学》,商务印书馆,第一卷,第173-178页。
标签:文学论文; 威尼斯商人论文; 李渔论文; 艺术论文; 戏剧论文; 仲夏夜之梦论文; 对偶理论论文; 维洛那二绅士论文; 张羽论文; 风筝误论文; 男女思维论文; 喜剧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