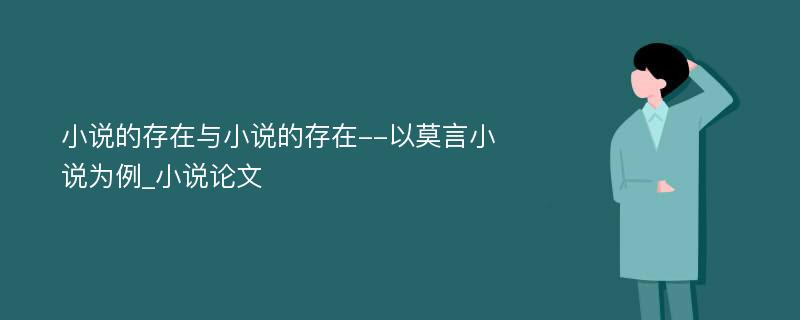
存在的小说与小说的存在——以莫言长篇小说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长篇小说论文,说与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的长篇小说热,不仅使走向社会边缘的当代文学重新焕发生机,为文学在市场经济社会找到了新的生长点,也造就了少数美学意义上的真正的作家。当许多人感慨、抱怨当代长篇小说作者的鱼龙混杂和作品的粗制滥造,并由此期盼、呼唤当代文学大师的出现时,事实上,一些在“新时期文学”初、中期就崭露头角的作家正借助长篇小说这种最有可能抵达经典的文学样式,创作了具有当代文学经典和准经典性质的作品,向文学大师和巨匠的高峰攀登,莫言就是其中最优秀的代表之一。首先,在当代文坛上,很少有作家如莫言,始终保持如此旺盛的长篇小说创作态势,在不到20年时间内,创作出近十部长篇小说,总计约四百万字①;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在当代文坛上,很少有作家如莫言,长期如此执著于对长篇小说文体的探索创新,他的每一部长篇小说的问世,几乎都以其不同凡响的题材、主题、内容、结构、叙述方式、语言和艺术风格,不断激活着人们日渐麻木的审美感觉,震撼着众多读者的心灵,引发了他们阅读欣赏的兴趣,有的不仅成为国内图书市场上的“畅销书”,也在域外产生了轰动,并成为文学研究和批评者反复言说的对象,开拓了一片片新的话语空间。② 在长篇小说日益大众化、商业化、网络化、泛文学化的今天,莫言长篇小说在文学上所取得的成就、在美学上所树立的标高和同时获得社会与读者的广泛认同,是当代很少有作家能够企及的,在“消解经典”、“大师缺失”的所谓“后文学时代”,莫言几乎是一个奇迹。他的“反现实”的小说又如何获得了现实的承认?他的存在意义上的叙事又如何在大众文化语境中获得了存在?他的天马行空、独立不羁的思想、汪洋恣肆的想象与奇异的叙述方式,又如何具有一种美学的普适性而与大众接通?本文试图从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美学思想和罗贝尔·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思想的结合中,对此作出辨证阐述。
一、小说:对存在的探索和发现
20世纪80年代中国作家中许多人在创作上深受米兰·昆德拉的影响,譬如,已故作家王小波对昆德拉“不懂得开心的人们永远不会懂得任何小说艺术”的说法就情有独钟。③ 但是,就目前的资料来看,似乎还没有证据表明,莫言在创作上直接受到昆德拉的影响。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用昆德拉的小说美学思想来解读莫言,前提是破除对昆德拉的误读。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人们常常对于昆德拉本人比对于他的小说更感兴趣,它体现了对于昆德拉一种普遍的误解,即是把他看作一个不同政见者,一个政治性作家。这种误解既有着冷战时代的背景,更来源于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即总是将作家置于一定的政治、宗教、道德的意识形态话语之中,甚至将作家本人的经历、立场、态度与其作品完全等同起来。对此,昆德拉感到悲哀。为了消除这种误解,他的回答是:“你是共产主义者吗?——不,我是小说家。”“你是不同政见者吗?——不,我是小说家。”④
昆德拉之所以一再强调自己是一位小说家而不是别的什么,因为对于他,做小说家不只是实践一种文学形式,而是“一种拒绝与任何政治、宗教、意识形态、道德、集体相认同的立场。”这种立场来源于他对小说的基本看法:小说是对存在的探索和发现。在昆德拉的小说词典中,“存在”不是一个抽象的哲学范畴,而是指在小说的历史基础之上,小说家以自己的方式,自己的逻辑去发现和思考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在政治、宗教、意识形态领域中没有发现和思考的东西,从而建立的不同于现实世界的小说世界,不同于哲学思想的小说思想。在昆德拉看来,小说世界是一个未知的世界,小说是对确定性的怀疑:“全部小说不过是一个长长的疑问,深思的疑问(疑问的深思)是我所著小说赖以建立的基础。”小说是对可能性的发现:“发现只有在小说才能发现的,这是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没有发现过去始终未知的一部分存在的小说是不道德的。认识是小说的唯一道德。”由此可见,“存在”只存在于小说中,存在于小说家的发现中。譬如卡夫卡在《判决》中发现的不是孤独的厄运,而是孤独的被强奸,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发现的不是不同政见者,而是媚俗。由此产生了小说的思想。小说的思想不同于哲学的思想,它是“以自己的方式,自己的逻辑,一个接一个发现了存在的不同方面”,而“存在的所有方面都是作为美被小说发现的”。小说的思想需要具体人物、具体境况来滋养,因此,“小说是通过想象出的人物对存在进行深思”。昆德拉说:“真正小说式的思想(比如自拉伯雷以来的小说所经历的)从来是非系统化的、无纪律的,它与尼采的思想接近,它是实验性的,它将所有包围我们的思想体系冲出缺口,它研究(尤其通过人物)反思的所有道路,努力达到它们的每一条尽头。”就此而言,小说家走到了哲学家的前面:“小说在弗洛伊德之前就知道了潜意识,在马克思之前就知道了阶级斗争,在现象学者们之前就实践了现象学。”
“对存在的探索和发现”是昆德拉小说美学思想的核心与基石,在此基础上,他建构了自己独特的、丰富的小说创造美学,并且贯彻在自己的小说创作实践中。它们主要是:(一)对存在的不确定性的发现和认识,需要借助个人化的经验、想象和梦幻,只有小说才能担当此任。“小说是个人想象的天堂”。(二)对存在的探索与发现,是无法用意识形态与道德价值观来认识、判断的,因为一旦如此,发现的就不是小说的世界而是现实的世界,产生的就不是小说的思想而是哲学的思想。所以,小说是“道德审判延期的领地”。(三)幽默精神和游戏方式。在昆德拉看来,只有以幽默精神和游戏方式,小说才能切入存在的主题,发现和探索存在的可能性、不确定性。他说:“小说的智慧与哲学的智慧不一样。小说不是从理论精神中产生,而是从幽默精神中产生。”“不懂得开心的人们永远不会懂得任何小说的艺术。”(四)反抒情化和优美风格。昆德拉认为,将道德审判延期的小说必然拒绝抒情化与优美风格。他以卡夫卡为例,认为他不喜欢小说文风的抒情化,他唯一只受一种意愿的支配:识破、理解、捉住诸人物行动的意义,因而他的小说指向存在。(五)昆德拉认为,“小说具有非凡的合并能力”,它在结构上应包容现代世界的复杂性而又不失小说结构的清晰明确。由此形成了昆德拉杂语式的复调结构小说。而贯穿这一切的永远是存在的主题,正如昆德拉所言:“简炼的艺术对我来说是一种必须。它要求的是:永远直接地走向事物的中心。”
当然,昆德拉主要不是小说理论家,而是小说家,他无意于建立一个小说美学思想的理论体系,而只是要表达自己对小说的看法。但正因为这些看法既扎根于小说的本性,又源于他的生命体验,是他在小说创造实践中对自我与存在、小说与存在关系的深刻的思考、顿悟,并内化为他的小说创作驱动力和外化为他的小说风格,所以,对于那些在遵循小说历史基础上,创造了“小说的世界”和“小说的思想”的作家而言,即使他们没有读过昆德拉的著作或不是自觉地接受他的思想,他们的小说创造在内在本质层面仍然与昆德拉有许多相通之处,同样是对存在的探索与发现,莫言就是属于这样的作家。我们也正是从此意义上,认为以昆德拉的小说美学思想来诠释莫言,才能够真正揭示莫言小说内在的本质和其独创性的奥秘。
二、存在意义上的莫言长篇小说
凡是阅读了莫言的长篇小说(特别是被人们反复称道的《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四十一炮》、《檀香刑》、《生死疲劳》等作品)的人,都不难从中发现诸多上述昆德拉所揭示、阐释并实践的小说美学特征:“天马行空”的狂放想象,将道德审判延期的直逼生存本相的叙事,充满着幽默和游戏精神的怪诞的叙述风格,顽童视角的狂欢描写,反抒情风格的对丑恶、鲜血、死亡、酷刑、变态的暴露,泥沙俱下的杂语式写作,复调的结构……如此与昆德拉的小说美学惊人地契合,这在莫言,不仅是与昆德拉同作为小说作家的一种叙事艺术上的东西方呼应,更重要的,是由其两者小说创造的共同内在本质所决定,即对存在的探索和发现。
莫言的长篇小说从题材、主题上来看,似乎可以分为历史与现实、城市与乡村、成人与儿童等不同题材,但这是仅就他创作的视角而言,从叙述功能上来看,他的所有长篇小说都是对现实的穿透,而指向存在,即指向昆德拉所说的“人的可能的场所”,“是一切人可以成为的,一切人所能够的”场所。所以,我们发现,在莫言的小说中,无论是故事、情节、人物、环境、行动、语言、细节,都大大逸出了日常生活的轨道和正常的逻辑和理性,充满了怪诞、荒谬、变形、变异。如《红高粱家族》中的荒诞的战争、血腥的杀戮、疯狂的野合、神奇的死亡、隆重的殡葬,《酒国》中的盛宴,《天堂蒜薹之歌》中的骚乱,《丰乳肥臀》中的恋乳癖、“东方鸟类中心”和“独角兽乳罩大世界”,《四十一炮》中的肉食节大游行,《檀香刑》中的酷刑、官虎吏狼美女蛇,《生死疲劳》中的六道轮回,等等。“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不同,莫言将生活还原为最基本的形态:吃、喝、生育、性爱、暴力、死亡等等与生命本身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就是肉体生命,关注的是生命的物质形态,比如人的肉体需要和人性的生命力状况等,而不是文化的观念形态,诸如善、恶、文化原型之类。”⑤ 诚然,莫言是在有意识地追求一种小说美学创造上的自由,许多论者都充分地肯定了这一点,将他的小说视为“自由的小说”。但是,我们知道,自由被赋予意义,才具有价值。莫言的小说之所以引起普遍关注,震撼人们的心灵,蕴藏丰富的可供言说的内涵,不仅仅得之于叙述方式上的“自由”,更重要的是它是小说本体的自由,即小说家试图通过对存在的探索和发现,获得审美创造上的超越。用昆德拉的观点来说,只有在对超越现实的存在领域的探索和发现中,才能“捉住自我”。“诉说就是一切”的背后,是作家在充满了不确定性、各种可能性的存在中对自我的发现和肯定,莫言在《四十一炮》后记中对此作出了诠释。他认为:“在这本书中,诉说就是目的,诉说就是主题,诉说就是思想。”紧接着,他又写道:“所有生活中没有得到满足的,都可以在诉说中得到满足。这也是写作者的救赎之道。”⑥ 在莫言看来,并不是所有“诉说”都可以使作家获得这种满足的,譬如许多反映和表现现实生活的小说;只有这种“诉说就是一切”的存在意义上的小说写作,才可能使作家获得超越现实、精神上的最大自由。
存在意义上的莫言小说,建构了昆德拉所说的“小说的世界”。这是一个十分独特、无比丰富,令人匪夷所思的世界,充满了存在的不确定性、各种可能性和人性的复杂与荒谬。这个世界当然有历史与现实的镜像,但当莫言从存在的视野去处理历史与现实的素材时,“他的基本思路是从生命的体验里,从精神的直觉中升腾的。”⑦ 因此,就有了不同于文化伦理意识形态的“小说的思想”。当一些人从文化伦理角度指责《檀香刑》等作品时,莫言以存在意义上的“大悲悯”阐明了他的“小说的思想”:“大悲悯不但同情好人,也同情恶人。”“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才是真正的悲剧,才可能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才是真正的大悲悯。”⑧
由此,莫言的长篇小说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特征:(一)观察世界的民间视角。在莫言看来,只有在民间世界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现实才会退场,对存在的自由探索和发现才有可能。正如他所说的:“民间写作,实际上就是一种强调个性化的写作,什么人的写作特别张扬自己个人鲜明的个性,就是真正的民间写作。”⑨(二)想象世界的独特方式。虚构的小说都离不开想象,但作家用何种方式想象,与他对世界的认识紧密相连。正如许多论者指出的,莫言的想象不仅是“天马行空”的、怪诞的,而且直接从民间魔幻、神话、传奇中汲取资源。(三)独特的“地理世界”。东北高密乡,既是莫言的故乡,更是他为自己小说世界创造的一个“存在空间”,他在这个空间里讲述的那些故事与人物,便具有了存在的逻辑性和合理性。借助这“原乡的情怀与乌托邦的想象”(王德威语),莫言自由地进行着对存在的探索与发现。(四)杂语的、多声部的叙述方式,使存在的各种可能性,各种不确定的声音都得到充分的显示。(五)莫言虽然写了十来部长篇小说,但在结构上几乎每一部都不重复,既不与他人相似,也不与自己雷同。他在小说结构上的创新精神已为许多人所称道,他本人也很看重。他说:“我们之所以在那些长篇经典作家之后,还可以写作长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在于我们还可以在长篇的结构方面展示才华。”⑩ 在我看来,莫言非凡的小说结构的才华,来自于他对存在的探索与发现。换言之,当莫言试图通过长篇小说,“以自己的方式,自己的逻辑,一个接一个发现存在的不同方面”、“发现只有在小说才能发现的”时,他必然要打破常规的小说结构方式,创造出一种能够使其最充分、最自由地进行探索和发现的结构。譬如《生死疲劳》,“这部作品的主题有一个二重奏结构——在宏大方面,讲述了黑暗政治对人之生存与心灵的摧残;在微观方面,则叙说了贪欲对每个‘人’的无情吞噬。如此黑暗的批判性主题,因借用了西门闹转世投生的‘畜生’视角,而有了诙谐、幽默、讽刺的外貌。‘重’在智力的作用下转化为‘轻’。”(11)
显而易见,存在意义上的莫言长篇小说更加抵达文学的本性,具有当代一般小说所不能比拟的精神意蕴和审美特质,甚至具有某种文学经典的性质,即“具有原创性、典范性和历史穿透性,并且包含着巨大的阐释空间”(12)。
三、“文学事实”中莫言长篇小说的存在
然而,当我们对存在意义上的莫言小说给予充分肯定时,还只是一种美学的评价,换句话说,是站在文学自身立场上的评价。而在今天,这种评价显然无法回避这样的追问:在这“严、雅、纯”文学被边缘化、大众时尚文化大行其道的时代,当文学阅读和欣赏已经成为一种消遣娱乐的文化消费时,像莫言这样的对存在探索和发现的“人类性小说”,还能够赢得读者的青睐、获得图书文化市场的认同吗?
这是一种从“文学事实”出发的追问。“文学事实”是法国文学社会学家罗贝尔·埃斯卡皮提出的重要范畴。他认为,文学社会学言说文学,不仅仅是指涉具有抽象美学意义的文学自身,而是要面对处于特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构成文学生产与消费的现实关系,作为某种社会活动、过程和结果的文学事实。因此,文学社会学应当“将作家作为某种职业的人来研究,将文学作品作为交流方式来研究,将读者当作文学商品的消费者来研究。”这样,主要由作家、作品与读者构成的,原先只属于文艺美学范畴的文学创作和欣赏的关系,便成为现实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文学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作家成为生产者,作品成为产品与消费品,读者成为消费者。其中,核心内容是读者问题。在文学社会学看来,所谓读者不仅是审美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文学欣赏者,更是置身于文学生产与消费现实关系中的、图书文化市场上的文化消费者。埃斯卡皮甚至认为:“从商品角度着眼,唯一真正的读者是书籍购买者。”他据此区分了“理论上的读者”,即“可能存在的读者”和“事实上的读者”,即文学读物的消费者、图书的购买者。当一个作家将创作既是作为一种使命,又是作为一种职业时,他首先当然要从自我实现需要和价值立场上考虑“可能存在的读者”,去寻求“知音”:“把作家同可能存在的读者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文化修养上的共同性、认识上的共同性以及语言上的共同性。”但在文学生产和消费现实关系中,他同时又必须考虑“事实上的读者”。因为,“在一本书的价值和它拥有的读者数目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在一本书的存在和读者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13) 这一文学社会学视野中的“文学事实”,揭示了文学不仅具有思想认识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还具有文学消费价值,笔者曾将此称之为“文学的第三种价值”(14)。
从“文学事实”出发来看莫言,必须指出他的创作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他虽然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文坛得名,但他创作的鼎盛期是在90年代以后,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二是他虽然也创作、发表了若干中、短篇小说,但主要从事的是长篇小说创作。前者使莫言无法脱离90年代的“文学事实”,即图书文化市场、文学消费对文学生产的制约,使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职业化的作家不得不考虑“事实上的读者”和“文学的第三种价值”。后者使文学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变得更加现实、尖锐。众所周知,与诗歌、散文、中、短篇小说可以在各种文学刊物上发表相比,长篇小说由于其体裁、篇幅的特点,发表的方式、形态,主要是通过出版,成为图书。即使是那些首先在刊物上发表的长篇小说,后来也大多作为图书单独出版。而一旦长篇小说图书化,就意味着它要走向图书文化市场,就更加要考虑作为文学消费者的读者的需求。事实上,90年代的“长篇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图书文化市场运作的结果。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在长篇小说的出版中引入了“畅销书”机制。所谓“畅销书”,是指“销量极大的书”(Best-Seller),它当然不仅仅是指文学书籍,或长篇小说,但由于长篇小说的特点,在诸种文学种类中,其最有可能成为畅销书。因此,随着作家的进一步职业化,随着图书文化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包括版税制的实行等,当代越来越多的作家转向长篇小说创作,其中有许多是80年代的“先锋作家”。而一旦他们从事长篇小说创作,就无法做到“拒绝读者”,而像过去那样一味地进行“文学试验”;反之,一些作家面对新的“文学事实”,自觉调整自己,在守护小说的文化美学价值前提下,努力使自己的小说不仅能够进入图书市场,同时成为畅销书。
莫言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当他面对90年代的“文学事实”,决定致力于长篇小说创作时,就开始自觉地在揣摩大众读者的文学欣赏趣味。他说:“我一直在思考所谓的‘严肃’小说向武侠小说学习的问题,如何吸取武侠小说迷人的因素,从而使读者把书看完,这恐怕是当代小说唯一的出路。”(15) 莫言并没有因此降低、甚至放弃自己的文学追求和标高,像有些人那样走向“媚俗”,反之,作为一个曾经的“先锋作家”,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他不仅创造了存在意义上的长篇小说,文体结构上也不断有所创新。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他又非常看重读者的接受。他说过:“我不愿四平八稳地讲一个故事,当然也不愿意搞一些过分前卫的、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东西。我希望能够找到巧妙的、精致的、自然的结构。”(16) 他还说过:“不知是不是观念的倒退,越来越觉得小说还是要讲故事,当然讲故事的方法也很重要,当然锤炼出一手优美的语言也很重要。能用富有特色的语言讲妙趣横生的故事的人,我认为就是一个好的小说家。”(17) 莫言在这里虽然说的是结构和故事,但是反映了他自9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苦苦思考和探索的一个问题:如何在小说的美学标高和大众读者的接受两者之间找到一种张力、保持一种平衡?作为这种思索的结果,莫言找到了一条“严肃”小说通俗化、人类性小说中国化的创作道路,使他的小说成为独特的东方式的存在小说。其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倒是可以借用评论家对张爱玲小说的评价:“她没有像一般雅文学作家那样,只在知识分子的情怀中来表现作家对人生的看法,而是经由表现通俗,由通俗的平凡性直达人生的存在性思考,完成了文学对人生的大跨越。”“通俗性与存在性的结合,在通俗的层面给你讲故事,故事是热闹的、世俗的、日常的;在存在的层面给你震撼,这震撼是深刻的、超越的、广泛的。”(18)
《檀香刑》是莫言这方面的一次成功实践。用莫言自己的话来说,《檀香刑》是他的创作过程中的“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是对民间说唱艺术的撤退。莫言写道:“在小说这种原本是民间的俗艺渐渐地成为庙堂里的雅言的今天,在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压倒了对民间文学的继承的今天,《檀香刑》大概是一本不合时尚的书。”(19) 这里的所谓“不合时尚”,当指的是不合学院派和先锋批评家的“言必称希腊”的“时尚”,但却符合中国老百姓对小说的阅读口味、习惯、兴趣。如前所述,《檀香刑》是存在意义上的人类性小说,但从接受角度来看,它又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具有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的“中国小说”。其既体现为外在方面,如用“猫腔”这一中国民间说唱艺术来引领、串联小说,用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情节来支撑小说,用传统的“起转承合”来结构小说等;更体现为小说所描写的各色人物,如孙丙、眉娘、钱丁、赵甲、小甲等,都是地道的中国民间传奇中的人物,小说不仅让他(她)们演绎了一幕幕令人回肠荡气的完全中国式的传奇故事,更是写出了这些人物的个性、心理、行为的充分的“中国化”,中国的文化积淀、中国的文化心理等等。这正体现了莫言对严肃小说通俗化的独特理解与追求,小说的通俗化,绝不仅仅是艺术表现形式上的由雅入俗或雅俗结合,而是在通过小说对存在的探索和发现时,确立了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新的创作立场和视角,这就是本土立场和民间视角。正是这样的立场和视角,一方面,如前所述,使作家可以充分地、自由地建构“捉住自我”的“小说的世界”和表达“小说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征服、赢得了读者。
继《檀香刑》之后,莫言又创作了《生死疲劳》。这部作品一问世,同他的前几部长篇小说一样,既获得了批评界美学意义上的很高的评价,又引起了“事实上的读者”的广泛关注,成为图书市场上的“畅销书”。只要看一看近二十年来莫言长篇小说的发行量和网络上众多读者对莫言小说的评价,就会深感:莫言的长篇小说不仅具有思想价值、美学价值,同时还具有文学消费价值,后者不仅没有削弱前者,还使前者落到了实处。因为,如萨特所言:“正是作者和读者联合一致的努力,才使这种具体而又假想出来的客体即精神作品得以问世。世上只存在为了他人和由他人创造的艺术。”总之,莫言存在意义上的小说获得了“文学事实”意义上的小说的存在,找到了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纯文学”的出路,这就是埃斯卡皮所说的:“首要问题在于实行优秀文化的大众化,也就是说用多少是清晰的方式和多少是可以松动(渗透)的方式消除隔在文人圈子和工业化圈子之间的障碍。”(20)
四、莫言的启示
(一)莫言的创作告诉我们:文坛是无须悲观的,“后文学时代”同样会产生好作品。那种认为市场经济和文学注定不能通约,进而断定在市场经济社会条件下,由于作家职业化,“严、雅、纯”文学必然走向衰落,必然不会产生文学大家和文学经典的论调,是不符合“文学事实”的。在莫言看来,作家的工作与社会上的民间工匠没有本质的区别。一个编织筐篮的高手,一个手段高明的泥瓦匠,一个技术精湛的雕花木匠,他们的职业一点也不比作家们的工作低贱。对此他解释道:“前几年我每次回去,村里的人就对我说:你应该去做官,当了官,我们好跟着沾点光。我对作家这个职业的比较低调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我的乡亲。”(21) 但是,如前所述,莫言并没有因此放弃文学立场和对美学标高的追求,而是创作了具有人类性、超验性、审美性的存在意义上的小说,抵达当代文学经典。作家的职业化与作家在创作中对思想和美学的意义、价值的追求是否一定是矛盾的呢?莫言的经验提供了很好的回答,符合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一部文学史告诉我们,从出版业出现以后,职业写作即以写作获得生存资金已成为部分文人可能的存在方式,因而它使文学艺术走向市场成为现实。正如埃斯卡皮所言:“在了解作家的时候,下面这一点不能等闲视之:写作,在今天是一种经济体制范围内的职业,或者至少是一种有利可图的活动,而经济体制对作家的影响是不能不论的。”(22) 不可否认,被批评家反复诟病的1990年代长篇小说的粗制滥造现象,的确与市场经济体制对作家影响有关,但是,作家职业化并不必然导致创作的粗鄙化、低俗化。莫言等一批当代优秀作家同样属于这个行列。
(二)莫言的存在意义上的小说在图书文化市场上不仅获得了存在,有的还成为“畅销书”,这一“文学事实”告诉我们:在市场经济时代,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不是注定矛盾的,那种认为读者不再阅读和欣赏“严、雅、纯”文学的论调,同样是没有根据的。当然,不可否认,文学消费越来越成为大众读者的消遣娱乐休闲需要,大众文化所以才风行天下。但是,即使是在图像时代、泛文学时代,读者也不是铁板一块的、一边倒的,真正优秀的、超验的、诗学意义上的小说永远有着其特定的读者。从文学社会学角度来看,所谓“事实上的读者”,即书籍的购买者是具体的、个别的,“其实并不存在什么读者们,只有读者,阅读的人(就形体而言)是独在的。”他们的文学消费心理是复杂的:审美心理、求新心理、从众心理、逆反心理、偏爱心理、求实求廉心理、名人效应等等;他们的文学需求也是多种多样的:健康的需求和不健康的需求并存,潜在的需求和现实的需求并存,多样性需求和层次性需求并存,怀旧性需求和求新性需求并存,等等。(23) 正是这多方面的文学消费心理和需求,使得许多大众文化读者文学消费方式多样化,他们在接受大众文化的同时,又是优秀文学作品的欣赏者和“事实上的读者”。1990年代以来,许多优秀的长篇小说,它们的思想文化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有的得到主流文化的褒奖,有的获得精英批评的认同,但同时又成为图书市场上的“畅销书”,就很能说明问题。而莫言的个案,则更有代表性。文学作品的价值不等同于读者的数量,“畅销书”也不意味着就是好作品。但是,莫言等作家的作品接受事实告诉我们:如同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鲁迅、沈从文、张爱玲等人一样,在大众文化时代,追求人文价值和美学标高的作家不是注定被读者拒绝的,优秀作品、文学经典与“畅销书”不是不能通约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真正写出了莫言所说的“人类性小说”。
(三)存在性的小说在“后文学时代”何以能够存在并得到发展?莫言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他找到了一条严肃小说通俗化、人类性小说中国化的道路。莫言以自己鲜明的小说思想和创作实绩激活了我们对小说本性的思考:小说这一古老的文学样式,来自民间,来自世俗社会,读者主要是大众百姓,所以,天然地具有通俗的性质,具有“与世俗沟通”的精神、“浅显易懂”的美学特征和“消遣娱乐”的功能。只是在很长时期内,小说这种通俗化的特质,被古代的“文以载道”和现、当代革命宏大叙事以及1980年代启蒙宏大叙事和先锋文学试验所遮蔽、消解。面对1990年代的“文学事实”,以莫言等为代表的当代小说作家,重新继承了这一传统小说美学特性,使小说回归本原、回到自身。从莫言的小说,我们可以看出,小说的通俗化,绝不仅仅是指形式上的通俗易懂、雅俗共赏,而是小说从宏大叙事走向日常叙事,从庙堂走向民间,从载道走向游戏,从贴近社会走向探索人生,从现实走向想象,从精英走向大众,从洋化走向中国化。丹尼尔·贝尔说过:“在文化中始终有一种回跃(ricorso),即不断转回到人类生存痛苦的老问题上去。”(24) 20世纪90年代以莫言等中国作家为代表的对小说通俗化的追求,就是这样一种文化上的“回跃”。莫言的小说还告诉我们:小说的通俗化既不等同通俗小说,更不是降低小说的美学标高,反之,先锋思想和前卫艺术完全可以借助传统的、民间的、通俗的形式来表达,在对存在的探索和发现基石上建构的“小说的世界”和“小说的思想”完全可以做到富有“可读性”。被奉为先锋作家的代表人物罗布·格里耶说过:“可读性是小说价值系统中的第一要义。”(25) 同样曾经作为“先锋小说家”的莫言深谙此道,在当代作家中,很少有作家能够像他,既创造了存在意义上的小说,又如此地使读者感到“开心”和“有趣”,因而赢得了众多“事实上的读者”,成为图书市场上的“畅销书”。从此意义上讲,莫言对严肃小说通俗化、人类性小说中国化的追求和实践,既是回到小说本原,更是走向小说发展,使当代作家走出了为自我写作与为社会写作、守护文学与走向市场、精英立场与大众读者需要、文化审美价值与文化消费价值的矛盾、困惑,在两者之间获得了某种平衡、统一,从而使小说这一古老的文学样式,在新的社会形态和新的文化语境中找到了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通道。“莫言现象”的意义正在于此。
注释:
①莫言自1987—2006年期间先后创作、发表和出版的十部长篇小说是:《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酒国》、《食草家族》、《丰乳肥臀》、《红树林》、《四十一炮》、《檀香刑》、《生死疲劳》。
②据路晓冰《莫言研究资料·附录》统计,近二十年来,关于莫言的研究评论文章,见诸于比较有影响的报刊的,至少有三百五十篇左右。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③王小波:《小说的艺术》,《我的精神家园》,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149页。
④本文凡昆德拉的言论,都引自米兰·昆德拉著《小说的艺术》,孟湄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米兰·昆德拉著《被背叛的遗嘱》,孟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⑤王者凌:《“胡乱写作”,遂成“怪诞”——解读莫言长篇小说〈生死疲劳〉》,《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6期。
⑥莫言:《诉说就是一切——后记》,《四十一炮》,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444页。
⑦孙郁:《莫言:与鲁迅相逢的歌者》,《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6期。
⑧莫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
⑨莫言、王尧:《莫言、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0页。
⑩莫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
(11)李静:《不驯的疆土——论莫言》,《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6期。
(12)黄曼君:《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13)[法]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0、86、90页。
(14)参见拙文:《论文学的第三种价值》,《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3期。
(15)转引自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6)莫言、王尧:《莫言、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页。
(17)莫言:《旧创作谈批判》,《莫言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18)刘锋杰:《想像张爱玲》,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19)莫言:《檀香刑》后记,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
(20)[法]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0页。
(21)莫言:《以低调写作贴近生活——关于〈四十一炮〉的对话》,《文学报》2003年第1423期。
(22)[法]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第12页。
(23)[法]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第120-122页。
(24)[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59页。
(25)转引自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
标签:小说论文; 莫言论文; 文学论文; 长篇小说论文; 消费文化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四十一炮论文; 生死疲劳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