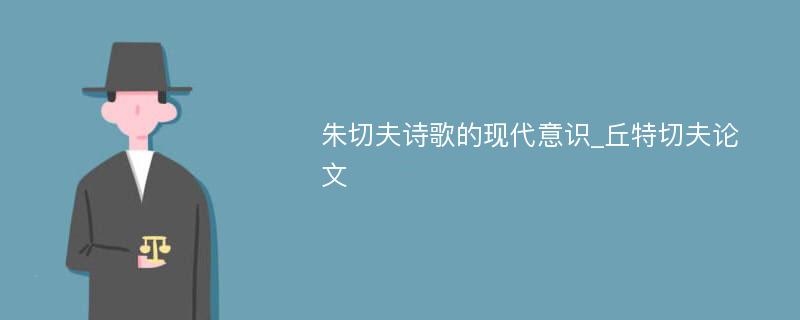
丘特切夫诗歌的现代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歌论文,意识论文,丘特切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丘特切夫的诗是一种哲理抒情诗,它把深邃的哲理、自然的形象、丰富的感情,通过瞬间的境界,以精炼清新的形式表现出来,达到了相当的艺术高度,在俄国乃至世界诗歌史上,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前苏联文艺学家指出:“作为当今最受欢迎的诗人之一,丘特切夫暂时还是十九世纪最费解的诗人之一……其诗作费解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这位天才诗人绝对独特的创作手法。他的思想是那样明显地超越了自己的时代,以至他的作品已经与二十世纪的诗篇产生共鸣,并积极参与了当今时代对世界和人的认识。”[①]这说明丘诗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的确,丘诗深刻、系统地探索了自然、生命、心灵的奥秘,充分表现了现代人骚动不宁的内心世界——它失去了平衡与和谐,混沌一团,充满了惊慌、不安与疯狂,进而积极参与了当今时代对世界和人的认识,这使得我们20世纪的读者读这位19世纪古典诗人的诗就象读同代人的诗一样。丘诗的现代意识体现在其诗歌的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
文学是人学。随着社会的日益发展,文明的日益进步,人类对自身本质问题的思考也越发摆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文学是人认识自己的强有力的工具,对人的本质问题的思考更是列为重点。而哲学研究的正是人的本质问题,因此,现今世界各国文学与哲学的结合已呈现水乳交融之势。文学哲学化,可以说是本世纪以来世界文学现代性的一种标志。飞白先生指出,丘特切夫“用抒情诗回答着哲学的问题”[②]。丘诗与德国古典哲学家谢林的“同一哲学”密切相关[③]。丘特切夫以自己独特的个性气质与丰富的感情融合了谢林哲学,同时创造性地加以背离,以诗长期、系统地探索自然、生命、心灵等本质问题,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与哲学的结晶品,实现了诗与哲学的圆满融合。丘诗的现代性不只是诗与哲学的结合,更重要的是这种诗与哲学的结晶品在思想内容方面所体现的现代意识,即:以诗对自然、心灵、生命之谜等人的本质问题进行执着、系统的探索,用抒情诗回答哲学的问题。它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永恒自然面前的矛盾与困惑。当自然作为部分,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时,诗人把自然当作美景欣赏,宣称自然象人一样,有着活的灵魂,有着自己的个性、语言、生命和爱情(《大自然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并从中看到人的生命的变化与自然变化的同一性(如《春雷》、《山中的清晨》、《恬静》);当自然故叶已坠、新芽方萌的新陈代谢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在作为个体的诗人面前,显示出永恒循环的特点,与个体的人那生命的一次完结性形成鲜明、强烈的对照时,诗人深感自然的强大、永恒与人生的脆弱、短暂,恐惧、悲哀袭上心头,随即渴望投入并融化于这永恒的普在之中(《灵柩已经被安放进墓穴里》、《春》)。然而,人永远不能摆脱个体的“我”,因此,只能永远处于惊慌、恐惧、迷惑、矛盾之中。矛盾、困惑的诗人继续矛盾、困惑地探索着人的本质问题。一方面,他认为,尽管自然永恒,人生短暂,但人总不能在这世上白走一趟,他得证明自己生命的价值,因此,他渴望,他斗争,他力图以自己奋斗的成果来证明生,从而否定死,超越死。首先,他愤怒地否定那代表永恒的上帝:“在创造中,没有上帝!在祈祷中,没有理性!”(《你的眼睛里没有情意》)在此基础上,诗人进一步探讨人的生活目的及性格发展,在《两个声音》一诗中,他通过自我分裂、自我争辩的形式,表现了人生的目的在于不屈的斗争,他认为在这个意义上人高于神,从而对那些高踞于无差别境界的奥林匹斯众神表示了极大的蔑视:“让奥林匹斯的众神以羡慕的眼光/看着骁勇不屈的心不断奋战。/那在战斗中倒下的,只败于命运,/却从神的手里夺来胜利的花冠”,体现了力求证明自我价值的现代意识,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诗人又强烈地感到:人奋斗过了,老了,被证明了的生命的价值已随时间的流逝而渐渐模糊,甚至完全失去意义——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已把上一代连同他们的时代忘得干干净净(《不眠夜》)。在社会中这令人恐惧,在永恒的自然中,这更叫人揪心:人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人,“不过是——自然的梦”:“不管人建立了怎样徒劳的勋业,/大自然对她的孩子一视同仁,/依次地,她以自己那吞没一切/和使人安息的深渊迎接我们”(《在这儿,生活曾经如何沸腾》),人生则是瞬间的梦幻般短暂,甚至无所谓的,最后剩下的,只是自然那茫茫的无限与永恒:“一切随之消失,甚至痕迹!/有我或无我,有什么需要?/一切照旧,风雪依然悲泣,/仍是如此黑暗把草原笼罩”(《伴随我多少岁月的兄弟》)。在这里,丘诗已迥然相异于一般浪漫主义诗人对自然的无限倾倒与顶礼膜拜,而把自然作为人的对立面,让人产生强烈的压抑感,表现了人对此产生的空虚感乃至虚无感,表现了人内心的骚乱、惊慌、恐惧与矛盾,很有现代意识。由此,诗人那颗“寻水者”的心灵对大自然产生疑惑:“大自然,这个古怪的司芬克斯,/老爱用自己的考验把人们折腾,/哦,也许自从世界第一日开始,/就没有什么谜语藏在它的心中”(《大自然,这个古怪的司芬克斯》)。进而,产生了本体论上的非理性的神秘主义。在其代表作《沉默》一诗中,他表示:“沉默吧,隐匿你的感情,/让你的梦想深深地藏躲?”“思绪如何对另一颗心说?/你的心事岂能使别人懂得?/思想一经说出就是谎,/谁理解你生命的真谛是什么?”飞白先生对此诗曾进行过精辟的论析:“这首名作不仅表现了现代西方的异化主题,同时也深刻地表现了丘特切夫对‘存在’的本体的态度。诗人认为:思绪之所以不能让人理解,不仅是由于社会的庸俗和肤浅,其更本质的原因是理性的词句在说明非理性世界(包括外在世界和内心世界)时的无能为力。能说明神秘的无底深渊的,唯有沉默,唯有心灵与宇宙的沉默的契合。”[④]
第二,人在宇宙中无所适从的尴尬局面。诗人终生热爱自然,研究自然,并透过自然去研究人、人的心灵和生命。可自然是如此的神秘深沉,充满了如此多的不解之谜,诗人越研究,越感到疑惑,以致不得不发出浩叹:“大自然,这个古怪的司芬克斯,/总爱用自己的考验把人们折腾。”由疑惑产生恐惧,进而发现人在宇宙中无所适从的尴尬局面。由于受谢林哲学的影响,丘特切夫的宇宙往往体现为“深渊”与“混沌”。他既爱这个“深渊”或“混沌”,又害怕它们。这种又爱又怕的矛盾充分体现了人在宇宙中无所适从的尴尬局面,并促使他一再去描写黑夜。在他看来,白昼是一幅金线编织的幕,而“夜”比白昼要真实而有活力得多,因为它来自那个神秘的“混沌”世界,显露了那个万物从中诞生的“无底的深渊”,但诗人对此又深感恐惧,因为黑夜坦露了“混沌”世界的全部“恐怖与黑暗”,而自己和黑夜之间却“没有遮拦”(《日与夜》)。在《午夜的大风啊》一诗中,他对午夜更加明显地表现出自己这种无所适从的两难心境:一方面,午夜的大风唱着歌,在对人暗示着“那原始的混沌”,人的心灵“感到多么亲切,听得多凝神”;另一方面,诗人又深感忧惧,请求午夜的大风“别把这沉睡的风暴唤醒/那下面正蠕动着怎样的地狱!”在《庄严的夜从地平线上升起》一诗中诗人高度集中而又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人在宇宙中无所适从的尴尬局面:“庄严的夜从地平线上升起,/可爱的白日啊,我们的慰安,/立刻象一幅金色的画帷/被它卷起,露出无底的深渊。/外在的世界梦幻似地消失……/而人,突然象孤儿,无家可归,/只有站在幽暗的悬崖之前/软弱无力,赤裸裸地颤巍。”这种在宇宙面前无家可归的“孤儿感”入木三分地表现了人无所适从的尴尬局面。读惯了以各种荒诞手法来表现人在宇宙中无所适从的尴尬局面的20世纪的读者,读到这些诗,自然备感亲切,也许还感到某种稚拙与朴实。
第三,异化的主题。德国古典哲学以对工业文明的忧虑和反思为重要的标志,费希特、谢林在科学技术、工业文明对人的异化问题上作出了积极、深入的思考。诗人、戏剧家席勒对此更是作出了全面、深刻的反思,他指出“现在,国家与教会、法律与习俗都分裂开来,享受与劳动脱节、手段与目的脱节、努力和报酬脱节。永远束缚在整体中一个孤零零的断片上,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一个断片了”[⑤]。深受德国哲学与文学影响的丘特切夫在德国生活长达20多年,当时的欧洲经历了法国革命,一切旧的秩序已被粉碎,新的秩序正在建立,整个欧洲还处于动荡之中。作为一个天才的诗人,丘特切夫既深深感到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人的异化,又敏锐地意识到社会现实秩序的脆弱,预感到社会巨变即将来临,从而产生一种空虚与孤独之感。这种空虚与孤独感,更进一步加深了诗人对异化的全面理解。丘诗中的异化主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对人的异化。在诗人看来,当时的世纪是“犯罪的、可耻的世纪”(《轻快地睡吧——睡成愉快的石头》),是“绝望的,怀疑的世纪”,“病态的、没有信念的世纪”(《纪念M·K·波里特科夫斯基》),而当时的俄国社会,到处是死一般的沉寂,一切都“坠入铁一般沉重的梦里”,生活的表现形式就象“热病患者的梦呓”(《在这儿,只有死寂的苍天》),一切都被监禁在贫困之中,“没有声音,色彩和运动”(《归途上》)。在这样一个严酷的社会里,人的一切都深深异化了:人的主动性、人的个性被异化了,因为一切都被预先规定好了——人的思想如此,尽管它“想要凌云上溯”,但达到一定的高度,就会被一只无形的巨掌,打断“倔强的飞翔”(《喷泉》);人的活动也是如此,一股溪流从旁边经过,而杨柳俯身也不能触及它,并非杨柳想要俯身,而是某种外在的力量使它俯身又注定它够不到水流,人的个性不也如此(《杨柳啊……》)?在此基础上诗人进一步表现了异化主题的另一方面——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异化,即人与人的疏远化、孤立化,无法沟通思想感情,而这,是20世纪文学尤其是现代派文学的中心主题。《沉默》、《我的心是一群幽灵的乐土》等诗深刻地展示了这一主题。飞白先生指出:“在哲学上,他(丘特切夫——论者)觉得社会的人际关系对人说来已成了异己的力量,人已无法与人沟通和实现感情交流。他终于发出了‘沉默吧’的沉痛的呼吁:满腔感情已不能再托付给别人了,因为你的热忱将被看作伪善,你的忠诚将被讥为愚蠢,你的信赖将会受人欺骗,你的爱心将会换来冷酷。那么,把炽热而闪光的感情与梦想都深深地隐匿起来吧,让它们自生自灭吧。再没有别人来观赏它们了,只有你自己爱抚地观赏它们象美丽的星座一般冉冉升起,只有你自己默默地目送它们在西方徐徐沉没……”[⑥]
第四,矛盾的两重心理与生命的悲剧意识。在20世纪文学特别是现代派文学中,人的本质问题得到高度重视,因而表现矛盾的两重心理与生命的悲剧意识便成为文学的重要主题。丘特切夫则由于意识到自然的强大,永恒与人生的脆弱、短暂,意识到人在宇宙中无所适从的尴尬局面,意识到社会对人的异化,人与人关系的异化,而产生矛盾的两重心理,进而产生深刻的生命的悲剧意识。丘诗中生命的悲剧意识主要通过矛盾的两重心理展示出来。诗人往往以矛盾对比的方式直接展现自己复杂的矛盾对立的内心世界,如《两个声音》之自我分裂、《沉默》之外界与内心的矛盾,个人与他人的无法沟通,在《海上的梦幻》与《哦,我的未卜先知的灵魂》两诗中更是直接指出:“两个无极,两个宇宙,/尽在固执地把我捉弄不休”,并使他终生“处于两重生活的门槛”。这样,他就能象现代派作家一样,由客观世界转到内心世界,充分展现出只有现代人才有的那一份内心的矛盾、不安、惊慌、恐惧和骚动,并由此而体现生命的悲剧意识。诗人一方面热烈地渴求和谐与平静,力图进入普在生命,以换来内心的平静(《春》,《灰蓝的影子溶和了》);另一方面,他又喜爱夜、风暴、雷雨、骚乱与混沌,他呼唤夜、呼唤混沌(《春雨》、《夏天的风暴是多么快活》);一方面,是对大自然美妙活力的歌颂,对生活的热爱,尽情歌唱鲜花烂漫的5月的欢乐,红红的光,金色的梦和美妙的爱情;另一方面,又对大自然的神秘力量深感疑惑与恐惧,对人世深感厌恶,公开表示“我爱这充沛一切却隐而不见的恶”(这个恶就是死亡)(《病毒的空气》)。爱情,在思想成熟时期的丘特切夫那里,也成为混沌世界本源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它作为一种自然初始便留下来的宿命的遗产,必然具有母体的种种特征,是一种原始的、无法控制的力量,因为自然界本身总是处于敌对力量的从不间断的冲突之中,这样,诗人在其著名的“杰尼西耶娃组诗”中,不仅表现了这种原始性:“我认识她已经很久,还在那神话的世纪”(《我认识她已经很久》),表现了这种原始热情的盲目性和毁灭性:“我们的爱情是多么毁人!/凭着盲目的热情的风暴,/越是被我们真心爱的人,/越是容易被我们毁掉”(《我们的爱情是多么毁人》),而且,从爱情的欢乐中看到不幸,从彼此的接近中看到彼此的敌对:“两颗心注定的双双比翼,就和……致命的决斗差不多”(《命数》),并发现:“有两种力量——两种宿命的力量”,一种是死,一种是人的法庭(《两种力量》),一种是自杀,另一种是爱情(《孪生子》),一种是幸福,另一种是绝望(《最后的爱情》)。在这方面,丘特切夫超过了此前、同时代及稍后所有歌颂、表现爱情的诗人、作家,对人性中的爱情心理层次作了更新、更深、更现代的开拓,向世界诗坛奉献了“杰尼西耶娃组诗”这一不可多得的瑰宝。半个世纪后,英国的劳伦斯才深入这一领域,作出了类似于诗人的探索。总之,在丘诗中,到处是矛盾、对抗、互相排斥以及正在形成的爆炸,以及各种情感的对立统一:喜气洋洋与毫无希望,强烈的兴奋与感情的麻木,满怀信心与悲观怀疑,感觉的丰富与心灵的空虚,春天的愉悦与秋天的忧愁,无忧无虑地把握世界的美与悲剧性地听天由命,脱离人群孤独地沉溺于内心生活与对人的爱与同情……这一切,深刻地展示了一个现代人一样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展示了类似西方现代派的生命的压迫感、异化感、幻灭感,体现了深刻的生命的悲剧意识。
第五,拒绝扰攘的现实世界,向往永恒、纯净的天界,即:厌弃庸俗、忙碌的物质追求,追求高洁、宁静的精神世界;厌弃短暂、纷纭的现实,追求永恒、纯净的天国。由于上述四方面原因,诗人也象许多现代派作家一样,厌倦了扰扰攘攘的现实世界,渴望走出人世的“山谷”,力图登上山顶,飞向天空(山顶,天空在丘诗中是纯洁与永恒的象征)(《尽管我在山谷中营着巢》、《啊,多么荒凉的山林峭壁》),力求“忘掉自我,和瞌睡的世界合而为一”(《灰蓝的影子溶和了》)。诗人还象波德莱尔一样,力求以自己的诗歌创造一个“人工的天堂”,使自己的灵魂有所寄托,以尽情展示自己的内心隐秘,表现自己对人、自然、生命、心灵之谜等本质问题的探索,因此,他对发表诗歌几乎没有兴趣,而只是尽情地陶醉于自己以艺术创造的“人工天堂”之中,这是其诗长时期未能形成重大影响的原因之一,也是其诗现代意识的一种表现。
丘诗的现代意识在艺术形式方面也有鲜明的表现,包括非理性、潜意识、直觉、瞬间境界,多层次结构以及通感手法等几个方面。
费尔巴哈曾指出,谢林“将理性化为非理性”[⑦],谢林哲学中的非理性对现代非理性主义的形成,有重大影响,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谢林的审美直觉强调通过事物本身,从事物的内部来认识事物,因此也是非理性的,它综合了自我中有意识与无意识东西的同一性以及对这种同一性的意识。深受谢林哲学影响的丘特切夫接受了这种非理性和这种审美直觉,在自己的诗作中探索混沌,探索心灵,表现梦,挖掘潜意识,因此,飞白先生指出,丘特切夫的“全部诗歌创作,仿佛就是一座沟通理性与非理性、意识与无意识的桥梁。他的诗中,汪洋梦境在生活的四周喧哗,混沌之世在我们的脚下晃动,无声的闪电在天边商议神秘的事情,秋景的微笑露出了‘面临苦难的崇高的羞怯’……通过他的笔触,一切事物都获得新的神秘的光彩”[⑧],这方面,最著名的诗作主要有:《好似海洋环绕着地面》、《庄严的夜从地平线上升起》、《夜间的天空》、《秋夜》等。丘特切夫把谢林的非理性与审美直觉变为自己把握世界、表达情感的艺术方式,从而实现了自己诗歌创作的大转变,创作出许多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品,突破了早期的古典与浪漫式的风格。
丘特切夫运用这种非理性的审美直觉,通过“瞬间的印象”(或“永恒的瞬间”)来领悟或把握自然的整体,直探自然、心灵、生命之谜,这样,其诗的抒情境界是瞬息即逝的,诗的表现形式是短小精悍的,大多在8—16行左右,显得凝炼而含蓄,精致又深沉,优美而富有立体感,达到了相当的艺术高度。这种瞬间的印象极富现代感(现代派特别强调瞬间印象),在丘诗中俯拾即是,如《幽深的夜》:“是幽深的夜,凄雨飘零……/听,是不是云雀在唱歌?……/啊,你美丽的黎明的客人,/怎么在这死沉沉的一刻,/发出轻柔而活泼的声音?/清晰、响亮,打破夜的寂寥,/它震撼了整个的心,/好象疯人的可怕的笑!……”全诗抓住听到黎明时分云雀歌声的瞬间印象,一反对云雀歌声赞美的传统,而把它称作“好象疯人可怕的笑”,特别突出了这幽夜死沉沉的气氛,突出了在这种气氛中云雀歌声对自己心灵的震撼,这种手法本身就很有现代感。
由于重视直觉,自然与精神又是一回事,丘诗中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客观对应物,出现了象征,形成多层次结构。而寻找客观对应物,寻找象征,运用暗示、烘托、联想等手法,造成多层次结构,这正是现代派诗人所致力追求的艺术效果。自波德莱尔强调“对应论”,认为可见的事物与不可见的精神之间有彼此契合的关系,把山水草木当作向人们发出信息的“象征的森林”,主张用有声有色的物象来暗示启发微妙的内心世界,这种“对应论”就成为现代派诗人的信条之一。丘特切夫形成这种类似于“对应论”的观念与波德莱尔无关,主要受谢林哲学泛神论的影响,尤其是谢林《论自然哲学观念》中著名的论点:“自然应该是可见的精神,精神应该是不可见的自然”,对他影响极大,使得他透过自然追索心灵、生命之谜,形成类似于“对应论”的观念和多层次结构。丘诗的多层次结构主要表现为客观对应物或通体象征。丘特切夫往往让自然景物作为思想与情绪的客观对应物平行地、对称地出现,从而使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互相呼应,在诗歌结构中形成两条平行的脉络,出现两组对称的形象。两组平行脉络的相互交错,丰富了诗歌的情感层次;两组对称形象的交相叠映,深化了诗歌的思想内涵,如《波浪与思想》、《世人的眼泪》、《喷泉》、《在戕人的忧思中》等诗。丘诗也常常运用象征。他的象征往往是通体象征,给人以丰富的暗示与联想。他的通体象征往往造成双层乃至三层结构,如《杨柳啊……》、《天鹅》等诗具有表层与深层双层结构,表层结构是全诗极力铺写的杨柳与天鹅,深层结构在于表层结构所象征的人生哲理;《海驹》则构成三重结构。初看,它描绘的是一匹真正的马,它“身披浅绿的鬃毛”,“时而温驯、柔和、驯熟,/时而狂躁、疾蹦乱跳”,甚至跑得“大汗淋漓”,“热气蒸腾”,这是第一层——语言层;到结尾才点明是海浪:“听,你的蹄子一碰到岸岩,/就变为水花,响亮地飞升!”从而使写实中又多了一层象征,这是第二层——结构层;它写的不只是马与海浪,它主要表现的是人的心灵与人的个性,这是第三层——意义层。
由于外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互相呼应,又由于直觉的有意识与无意识的结合,自然与精神的统一,丘特切夫在诗歌创作中往往能自由地超越各种界限,而使用通感手法,把各种不同类型的感觉杂糅在一起,如:阳光发出了“洪亮的、绯红的叫喊”,视觉与听觉沟通,又如:“她们以雪白的肘支起了多少亲切的、美好的幻梦”,化无形为有形,而他的“沉静”是“敏感的”,“幽暗”是“恬静的”、“沉睡的”、“悄悄的”、“悒郁的”、“芬芳的”……自从兰波发展了波德莱尔的“交感论”,提倡应成为“通灵者”以来,通感手法已成为现代派的一种法宝。丘特切夫的通感手法与波德莱尔、兰波等无关,与谢林哲学密切相连,但很有现代感。
由上可见,丘诗的确极富现代意识,他不愧为俄国象征派的祖师,也不愧为当今俄罗斯读者最多、对当今俄罗斯诗歌有着积极影响的古典诗人之一。
注释:
①吕进主编《外国名诗鉴赏辞典》,第529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②飞白著译:《诗海》(现代卷),漓江出版社,第804页,1990年。
③参看拙文《丘特切夫的哲理抒情诗与谢林哲学》,载《湘潭大学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4期。
④⑧飞白《试论现代诗与非理性》,载《外国文学评论》,1987年第2期。
⑤席勒《美育书简》,第234—235页,徐恒醇译,中国文联出版社,1989年。
⑥飞白主编《世界名诗鉴赏辞典》,第234—235页,漓江出版社,1989年。
⑦《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第598页,商务印书馆,197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