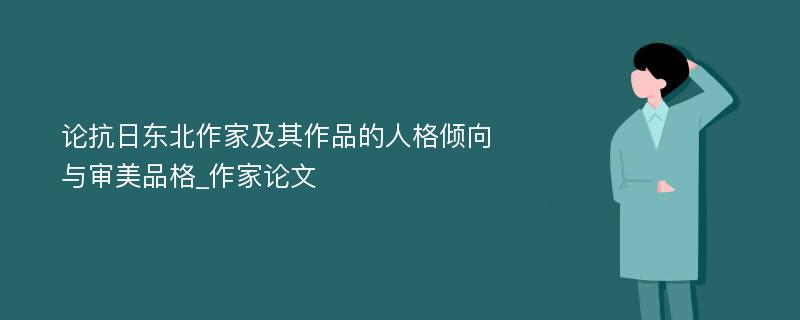
论抗日东北作家群及其作品的人格倾向和美学品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品格论文,美学论文,人格论文,倾向论文,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24(2013)01-0013-05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上,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当年那些以笔为刀枪英勇宣传抗日的作家,他们的诞生、成长以及为国捐躯的经历及其作品不只是中国现代文学画廊里的浓墨重彩,更是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全体中国人的真实写照。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同仇敌忾的抗日炮声里崛起于中国文坛的20世纪30年代流亡的东北作家群。这些作家的不屈的人格、坎坷的人生经历、充满激情的作品,尤其是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人物画廊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人物形象,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财富,这一群体表现出来的共同人格倾向和美学品格,值得我们重新发掘和认真的研究。
一、具有“建安风骨”特色的慷慨悲情和忧患意识
中国历史上的建安时期一般是指从黄巾起义到魏明帝景初末年,历经几十年。在东汉末群雄争霸、逐鹿中原的争夺兼并中,曹操不但完成了统一北方的理想和抱负,还把不少优秀的知识分子——大批文士紧紧吸引到自己的阵营里来,并逐渐打造出一支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邺下文人创作队伍。建安诗歌便是社会由分裂动荡趋向统一这一历史时期的产物。“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可以形象概括这一时期的时代特征。当时的建安文人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了这一惨烈而动荡的社会现实,他们一方面有着开阔的胸襟、远大的理想抱负、积极的人生态度;一方面在创作实践中又形成了直抒胸臆、质朴刚健的艺术风格:梗概而多气、慷慨而悲凉,为中国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风范。
流亡的东北作家群的抗日文学与古代建安文学相比较,尽管相隔近两千年,但由于共同的民族潜在意念、情愫的趋使,由于时代特征作家生涯的某些相近,使得他们的创作显示出某种相一致的思想倾向和艺术品格,这就是慷慨悲歌的创作激情和敢于直面黑暗的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忧患意识。
因而当我们有意无意将建安诗歌和东北作家群的抗日文学作品进行对照后发现:那“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的惨景不正是罗烽在《第七个坑》中所描写的“九一八”事变中血肉横飞、死尸遍地的沈阳城的写照吗?那“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蔡琰《悲愤诗》)的哀鸣,在白朗笔下则是面对比洪水还残忍的日伪政权,灾民宋子胜的怒喊:“弄死吧,弄死吧!这样红胡子年头,这样窝囊的日子……够啦!”(《轮下》)那“冉冉老将至,何时返故乡”(曹操《却东西门行》)的慨叹到了端木蕻良的笔端则是“什么时候我能回到家里去再吃一次那柔若无骨的香水梨”(《有人问起我的家》);那“男儿宁当格斗死”(陈琳《饮马长城窟行》)的壮志在骆宾基的报告文学中体现得如此淋漓尽致:“我还回到前线去,我有右胳膊就行”(《我有右胳膊就行》);那“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刘桢《赠从弟》)的气节,正是舒群所塑造的仁人志士中的一个——宁死也不下跪的王海的人格象征(《死亡》);那“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曹植《白马篇》)的壮举,也出现在萧红作品中,众乡亲向天盟誓:“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生死场》)
这些“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的建安诗句,和相隔近两千年流亡的东北作家群的抗日文学,在思想情感、作家人品、写作风格、艺术表现等多方面,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动荡不安的年代,民不聊生的现实、年年不断的战乱使得这样一批在白山黑水间成长起来的关东大汉、松江女侠,面对日寇铁蹄下的半壁江山,产生了一种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情怀,而这种情怀又化成了和建安文学相近的慷慨悲歌,这些都在流亡的东北作家群的抗日作品中的英雄志士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二、伴随刀光剑影、记载抗日经历具有强烈怀乡情结的“回忆文学”
中国文学从屈原的《离骚》开始,就奠定下一种创作传统,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素材,从“回视”的角度将人们带入那流逝的岁月中。这具有较浓自叙传色彩的“回忆文学”在“五四”以后的中国新文坛上,应反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之呼声得到了可喜发展,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叶绍钧、沈从文、巴金等人的作品都或浓或淡地体现“回忆文学”的特征。
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又诞生了一种“乡土文学”。它是由蹇先艾、许钦文、王鲁彦等作家“被故乡所放逐”,在异地创作的回忆童年、思恋故乡的“隐现着乡愁”的作品而得名。这种“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斯,雨雪霏霏”的乡土文学早在《诗经》中就体现出它的魅力。可见《楚辞》与《诗经》这中国文学两大源流对中国现代作家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至少由这两种审美形态构成的传统文化渊源,深深积淀在绝大多数中国作家的集体无意识或潜意识中。因而当我们翻开东北作家群的作品时,便会感受到这两种远古文学形态的影响,同时又有东北作家群自己的风格。
东北作家作品的自叙传特点,比较成形的应从萧红、萧军的《跋涉》集算起,但到了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萧红的《呼兰河传》、萧军的《第三代》、骆宾基的《幼年》中,自叙传特点和“乡土文学”特征彼此渗透、水乳交融,形成东北作家群独特的叙述方式和艺术风格。
但我们应看到,抗日时期东北作家群的怀乡恋故不是一般意义上成年对天真、纯美的童年的依恋,也不是单纯的游子对家乡一人一事、一草一木的感怀,更不是从“寻根”的角度对田园牧歌般东北乡村文化的反思。东北作家群的乡土文学是建立在强烈的反帝爱国的民族情感上的具有浓重政治色彩的乡土文学;他们的自叙传也不是只从个性解放角度所反映出的冲破封建家庭束缚、争取婚姻自主的反礼教呼声;而是伴随着侵略与反侵略的刀光剑影、记载自己走向抗日道路的自叙传。他们怀的乡是日寇铁蹄践踏蹂躏的家乡;他们恋的则是在双重压迫下相依为命的亲人故友。
端木蕻良在《大地的海》后记中就曾这样描述着家乡的亲人:“我的故乡的人们则是双重的奴隶。在没有失去的时候,是某一家人的奴隶,失去了之后是某一国的奴隶”。[1]而他那篇干脆取名为《乡愁》的小说,则是通过一个小孩的梦境,回溯了那“甜适而安静”的故乡和爸爸浑身是血离家出走抗击日寇的情景。最后在疾病折磨下的星儿的喊声“爸爸、老叔、奶奶……我要回家去”,[2]道出了一颗幼小的心灵对日本强盗的深仇大恨,“愁”在这里得到了升华,染上了强烈的抗日色彩。这种由乡愁变国恨的艺术构思,显然超出了20年代单纯写“乡愁”的“乡土文学”,它使我们不难看出,“五四”时代反帝反封建、争取民主进步的社会与作家的使命感,在30年代抗日运动的社会条件下更加突出了。
东北作家群创作中的自叙传色彩,尽管是与乡土文学特征糅和而成的,但有时又表现出独立的自叙传风格。以东北作家反映监狱生活的作品为例:罗烽的《狱》、白朗的《生与死》、骆宾基的《可疑的人》、舒群的《死亡》、端木蕻良的《被撞破的脸孔》、林珏的《女犯》、萧军的《羊》和塞克的《流民三千万》等都是建立在这些作家几乎都受过铁窗之苦的生活经验基础上,用塞克的话讲:他们都是“黑水边的流亡者”和“铁狱里的归来人”(《流民三千万》),[3]这些作品是控诉日伪反动统治、国民党腐败政权的真实写照。这凝结着作家深刻的亲身体验和牢固的情绪记忆的“铁窗文学”,是东北作家群对“五四”自叙传文学和“乡土文学”的继承和发展,是烙有深深的时代印记和标有鲜明政治内容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是准确意义上的“国防文学”。
三、以超常性格与传奇人物为主体的具有浓郁浪漫主义色彩的形象系列
从总的倾向来看,东北作家群是属于现实主义创作流派。然而以下诸因素又为其创作染上了浓郁的积极浪漫主义色彩。
一是时代因素。勃兰兑斯在谈到一位作家时说:“他的时代却有一种看不见的精神力量,迫使他作为一个作家接受浪漫主义的理论,并按照浪漫主义的手法写作。”[4]172东北作家群亦如此。故乡沦陷、日寇猖獗,他们“略地、奸淫、抢劫、焚烧和屠杀,把亡国危险最后地加在中国人身上”,[5]“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6]在这样一种中华民族命运攸关之时,这群将国难、民忧、乡恨、家仇集于一身的东北作家,在“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这一时代精神力量的感召下,将满腔热血凝聚笔端,为配合抗战产生了一种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浪漫主义文学。
二是生活因素。东北作家中除了端木蕻良、李辉英、穆木天外,大多数都生长在贫寒或较贫困的家境中,其中萧红、舒群、罗烽从童年时代就命运多舛。长大成人后,这些东北作家又无一例外地蒙受了“九一八”的灾难。端木蕻良参加救亡活动被学校开除,后来又险些落入国民党的魔爪;舒群、罗烽、萧军、金人、塞克等都有过坐牢的遭遇;萧红当时则是国难和己难兼于一身,其情景更是惨不可言。可见在东北作家群产生和形成的历史进程中,坎坷的个人生活经历,不仅构成了他们丰富的创作素材,还渐渐培养起他们对待不幸命运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坚忍不拔的英雄主义气质,为东北作家群浪漫主义创作因素产生奠定了必要的生活积累和心理准备的条件。
三是情感因素。东北作家群具有一种慷慨悲歌式的爱国主义激情,这种激情又往往导致了他们创作中的浪漫主义倾向。正如勃兰兑斯所说:“浪漫主义诗人的光荣就在于他内心燃烧着的最炽烈、最激昂的感情。”[4]74故国沦陷,山河破碎,对每个有爱国心的作家来说,都容易染上这炽烈激昂的情感。尽管东北作家群还称不上真正意义的浪漫主义诗人,但他们确如当年歌德那样:“灵魂的热变成了达到沸点的炽热,用烈焰烧光了一切坚固的形式、形象和思想。”[4]180他们的作品“似乎整个民族的悲哀与愤怒都一下子在其中得到了宣泄”。[4]207因而东北作家群没有受艺术形式束缚,而是让艺术激情冲破了各种创作陈规,甚至随意想象到细节失实、尽情抒发到长篇议论、大胆夸张到形象粗糙的地步,这种创作倾向显然不是现实主义而是具有相当成分的积极浪漫主义因素。
四是理想因素。积极浪漫主义一个重要的美学特征,是对未来充满信心,对理想抱定必然实现的信念;而且这种理想之光无论在多么黑暗的时代都放射着异彩。东北作家群出走时的家乡是暗无天日、强盗横行的屠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维持其在东北的殖民统治,始终保持着庞大的军事镇压机器。它有号称百万的关东军,十几万伪国军,还有多如牛毛的日伪警察、特务、宪兵。有人形象地说日本侵略者“用刺刀挑开了东北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7]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固然真实再现了这“黑暗的一页”,可也预示了打败侵略者、解放全东北的光明前景。《边陲线上》结尾就写到:“黎明晨色中插在远处峰巅的旗帜,更有劲地在狂风吹袭中,庄严而勇敢地摇摆着,摇摆着,极其迅速地摇摆着。”作者笔下这面黎明中的战旗,是不可辱的中华民族的象征,是流亡的东北同胞对打回老家去这一天的殷切期望,也是骆宾基等东北作家一种“浪漫主义渴望的形式”——“憧憬”。[8]
而这些因素反映在他们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就是他们常把时代的精神力量、作者本人的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与对未来的理想信念统统凝聚在一点,集中体现在他们笔下那些传奇般的、理想化的超常人物性格上。以骆宾基的《边陲线上》为例,骆宾基的长篇小说《边陲线上》将东北义勇军作为一支主要的抗日武装,进行了刻画和描写。不但把他们英勇杀敌的英姿展现在读者面前,而且还逼真的写出了他们艰苦卓绝的生活和斗争。更塑造了刘强、王四麻子等抗日志士的形象,奏响了抗日的主旋律。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四麻子这一人物。在日本兵面前他有些畏缩,但他始终相信“日落酉时”。部下朗世魁投奔义勇军,他心急如焚,而且终于被局长罚了五千元的赔偿;但他仍然敢当面催日本人的房租。当刘房东被日本人指使的汉奸逼死时,他暗暗地发着誓:“满洲国……这不让人活下去的国度啊!但我要活下去,我要开辟一条路,我一定要……并且趁着这癸酉年,我要看着这些恶霸们倒下去,和落日一样;我要来痛痛快快的拍几下掌。”正因为基于这样的思想基础,上集结尾时他终于走上了抗日的道路,最后英勇战死在沙场上。王四麻子,随着抗日的主旋律由弱到强,奏出了中华民族不做亡国奴的战歌,是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
主人公刘强是刘房东的儿子。但他和其父大不相同。刘房东自私到极点,除了自己的老婆孩子和家产、地租之外,他只是躺在床上抽大烟;刘强无私得有些不近人情,在抗日战场上他听到父亲死去的消息后,他不赶回家去奔丧,而是要“为了祖国,为了大众”而战斗下去。这样一位英勇顽强、誓死抗日、大公无私的人,虽然有一定程度的理想主义色彩,但也正是在这一人物身上凝聚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力量,也体现了作者本人的乐观主义、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的激情与对未来的理想信念。因此,在他眼中:“父亲是个浸沉在自己一切打算里的人”,季伟刚“变成了个奇怪的家伙”,关唯吾等人“是一些政治投机者”,琬玲“那么装腔作势”……其事实也恰恰如此,关键时刻,关司令叛变,会长投降,投机者发了财,颓废者送了命。这一插曲虽然表面上似乎与抗日的主旋律没有什么直接关联,其实质仍依附于抗日这个大主题。它告诉读者只有那些深受灾难的广大劳苦人民,只有那些没有个人目的抗日志士才是抗日的中坚力量,才是赶走日本侵略者的胜利因素,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四、反帝反封建主题双向制约下的东北乡村风俗画
众所周知,中国新文学常常会涉及到反帝、反封建这两个政治主题。到了30年代,这一孪生主题在力量对比上开始发生明显变化:随着民族矛盾的上升,反帝主题逐渐壮大;但无论它怎么壮大都跳不出它所反映的中国这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文化圈层。因此从本质上看,中国的反帝文学从来没像中国早期反封建文学那么单一,它从郭沫若的《女神》、郁达夫的《沉沦》开始,就一直是反帝反封建这两个孪生母题的产物。
随抗日烽火崛起于文坛的东北作家群,从严格意义上讲应是抗战文学的作家群体。然而由于他们展示的大多是几千年来被封建枷锁牢牢禁锢的中国农村社会,而且又是远离中原、比较封闭、地处边陲、开发较晚的东北;再加之“五四”反帝文学中兼反封建的传统,因此东北作家群的抗日文学中常弥漫着一层东北封建文化氛围,表现最突出的是在东北作家笔下经常出现的对观察天兆、占卜、算卦这些封建文化习俗的描写。
端木蕻良《鴜鹭湖的忧郁》里来宝和玛瑙对“月亮狠忒忒的红”是“主灾”还是“主兵”的争执;骆宾基《边陲线上》王四麻子按“天干地支”说得出“今年岁在癸酉,正正日落酉时”、“日本准败”的结论;白朗《轮下》中胡来、李二虎关于“满洲”两字竟有四个“三滴水”而推出必涨水的论断;特别是《寒夜火种》中,马加用相当多的篇幅刻画了陆大娘、徐老八、秃六、尤其是王七先生对日本侵略者及其傀儡政权——伪满洲国近于谶语的诅咒。这些描写不单是为作品增添一层浓厚的东北农村封建文化而展现的;妙则妙在作者将鲜明的反日爱国的政治色彩,作为人民超常态的愿望溶解在东北封建文化的氛围中,进而深刻揭示出无论是用科学的历史观,还是用反科学的迷信论都是要得出日伪政权必将覆灭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结论。从此意义上看,“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9]的抗日统一战线原则,是有其广泛的社会基础的。
然而我们还要看到,尽管封建文化及其它形态的封建产物在全民抗战中,从客观上起到一点反帝作用;可若要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推翻日伪统治,靠占星、算卦、测字是无济于事的。《寒夜火种》中陆大娘之子陆有祥、《边陲线上》中王四麻子等被“逼上梁山”参加抗日武装、《轮下》中胡来和李二虎被日寇抓走都深刻说明了要坚决反帝,就必须彻底地反封建。于是东北作家群的抗日文学又浓淡不同渗入了反封建因素。“五四”以来反帝反封建这一双重主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赋予了更新的内涵。如果从东北作家群创作心理角度分析,这种用封建文化来寄托人民反日心愿的艺术构思与前面提到的逆反心态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不过一个是将人间现实夸大变形,一个是努力让人信服冥冥之中有神佑,最终二者在抗日救亡这个焦点上重合了。
总之,无论是在东北作家群的人格倾向,还是他们其人其作品的美学品格上,都让我们深深懂得:在70年前为捍卫民族尊严、保卫祖国领土、打击外来入侵者而英勇战斗甚至献出自己年轻生命的这一军歌嘹亮的队伍中,自然少不了那些“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东北作家群”,尤其是他们的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相当重要的,重新审视他们并发掘作品的美学价值,在当前也是大有必要的。
标签:作家论文; 文学论文; 东北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乡土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端木蕻良论文; 骆宾基论文; 浪漫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