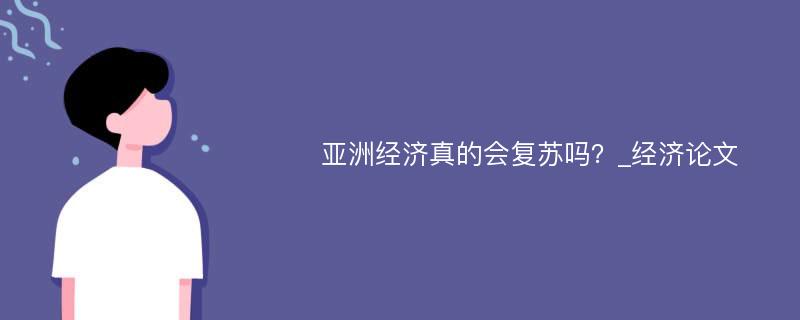
亚洲经济真会复苏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洲论文,真会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两年前,泰国曼谷出现了一种可怕的病毒。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病毒具有很强的传染能力。它迅速传染到了整个亚洲及其以外的许多地区,经常使经济看似强大的国家成为受害者。人们还一度认为它会传染到全球各个角落,但在最近几个月却没有新病例的报告,以前的患者也大都度过了最痛苦的时期。像其他大病新愈的人一样,他们感到轻松了,甚至有些欣喜若狂,尽管他们离真正的痊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现在庆祝胜利还为时尚早。一方面,亚洲的情况好转仍是局部的事情。韩国复苏得最快,其经济今年可能会增长5%, 但即便如此,其国民产出也比1997年以前的趋势线要低14%。虽然日本的经济总量比所有遇到麻烦的亚洲国家的经济总量之和还要大,但它尚未出现任何可信的经济好转迹象,而且人们都预测即使它的国内生产总值停止下降,其失业率也仍将继续上升。在亚洲危机期间,中国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但它现在所面临的金融压力却在不断地加大。
另一方面,如果去年夏天笼罩在这一地区上空的经济即将全面崩溃的气氛已经完全消失了,那就未必完全是一件好事。因为经历了这场危机的亚洲并不能确切地知道该如何去避免下一场危机。导致1997—1998年亚洲危机的经济脆弱性依然存在,而且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经历了这场危机后,亚洲长期的经济发展前景比两年前所预期的要差得多。
让我们首先来弄清楚这场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吧。
亚洲流感
一些力图使自己显得明智的权威评论家,总是告诫人们不要随便将某一看法推广成一般性结论。他们说,每个国家都不一样,一国的情况不能适合于整个亚洲。这显然是糊涂的看法,因为,这些国家在短短的几个月内相继陷入经济危机,肯定有某些共同的原因。
实际上,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韩国在这场灾难中的前因后果非常相近(日本则是个例外)。在每一个国家,投资者们——主要是发放了短期贷款的外国银行——都同时希望撤出自己的资金。其结果是造成货币与银行的复合危机:银行不能将其资产迅速转换为现金所造成的银行危机,和恐慌的投资商力图将长期资产转换为现金,并将泰铢和卢比兑换成美元所造成的货币危机。面对经济崩溃,政府没有选择。如果他们任其货币贬值,必然出现通货膨胀,而且那些有美元债务的企业必将破产;而如果他们试图以提高利率的办法来捍卫本国货币,上述企业也将因为债务负担和经济萧条而倒闭。事实上,这些国家后来采取了折衷的办法,而且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这场危机是对不恰当的经济管理的惩罚吗?同大多数陈词滥调一样,“任人唯亲的资本主义”这一诱人的名词由于触及到问题实质而流行起来:政府和企业之间过分暧昧的关系确实导致了大量的不良投资。亚洲企业至今仍盛行的财务结构——资产比重太小,负债比重过大,而且这些负债主要由主办银行的“软贷款”组成——也使这些国家特别易于丧失信誉。但是这一惩罚对“罪犯”肯定是不恰当的,而且许多现在回想起来很愚蠢的投资在当时看来却是很合理的。美国现在每年向海外投资3000亿美元,但如果设想一下它的资本帐户突然由净流入变成了1 万亿美元的净流出(从经济规模上看,这相当于遭受危机的亚洲国家资本流出的总和),那美国的金融系统会有多坚固呢?
在没有政策可以选择的情况下,人们对政策的主要反应会是“支持”吗?当亚洲的事情看起来似乎都出了问题时,有许多激烈的批评;而现在当情况刚刚好转时,有一些人又对政策有信心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指出,韩国的复苏证明它建议的政策是正确的。不要担心IMF的其他委托人会做得更糟,也不用担心马来西亚——它拒绝IMF的帮助,并推行资本管制的观念——经济看起来似乎正在好转之中。相比较而言,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对任何好的消息都充满自信,即使其周边国家经济也已开始回升。
其实,一个公正的观察家很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制定政策时考虑或者不考虑IMF的建议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预算政策、利率政策、 银行改革——不管各国政府采取何种政策,所有可能外逃的资本都逃走了。当没有更多的资本可以逃走时,这些国家的自我康复能力就开始起作用了。那些为这些国家的痊愈出谋划策的金融博士,一方面确实给它们提供了有益的帮助,但另一方面,他们就如同中世纪的医生一样,总把放血作为治疗所有疾病的唯一方法。
患者能完全康复吗?这取决于“完全”的含义。韩国的工业产值现在已经超过了其危机前的水平;如果你所指的复苏不仅指恢复增长,还包括使这一地区的业绩恢复到过去被人们认为是亚洲平均状况的水平,那么,它们就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而且,还有两个充分的理由可以证明,它们不可能走到那里。
首先是一位泰国经济学家向我描述的“企业家阶级被砍头”的情况。我们有理由说,亚洲发展中国家没有几个真正西方意义上的公司。那些字面上看来是现代公司的一些机构,事实上是一些发展得过快的家庭企业,这些企业的增长主要依靠老板的个人财富及其通过银行贷款扩张财富的能力。尽管亚洲国家在修复其遭到破坏的银行方面已取得一些进展,但这些银行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提供或愿意提供它们过去曾提供的资金,而且那些在危机中遭受损失的企业家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提供必要的抵押担保了。现在能找到的其他出路有:这些国家可以产生一个新的企业家阶级;它们可以向外国公司的资本和技术敞开大门;它们可以改革并实现金融现代化(包括制定可行的破产程序)。但是,现在——也许还包括今后几年,这些国家很可能会由于它们所面临的严峻考验而不断被削弱。
其次,甚至在危机爆发以前,就有迹象表明,亚洲已经进入了收益率递减的阶段,那里的经济迅速增长只不过是靠不断投入大量的资本来维持的,而且大部分资本还来自国外。(我1994年在《外交》杂志上发表的那篇《亚洲奇迹的神话》,曾概括了这种情况。)但在将来,它们可能无法获得那么多的资本:外国投资者也许不再外逃,但他们也不会再像几年前那样大规模地投入资金了。因此,尽管亚洲经济开始恢复,在一两年内可能会达到1997年以前的增长速度,但危机过后的增长趋势也许会比人们先前预期的要低得多。
复苏会中途夭折,情况会再度恶化吗?至少在不久的将来,发生像1997—1998年那样的现金困难看来是不太可能的。短期外债大部分已经偿还,贸易上的大量盈余(这是货币贬值和经济萧条的产物)使那些遭受危机打击的国家重新获得大量的外汇储备。大概需要几年,不负责任的借贷才会使亚洲重现1997年的情景。
但不幸的是,亚洲危机仍可能会再次发生。这是因为,一些国家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日本综合症
甚至早在人们能想象“亚洲”和“危机”会在同一个句子中出现之前,日本就已经遇到了麻烦。在那个岛国上没有像最近从其邻国传出的那样的好消息,那里所能听到的最好的消息就是去年的经济已经停止下跌。如果说亚洲发展中国家所患的是一种可能致命的但持续时间较短的急性病,那么日本所患的则是一种消耗体力的慢性病,而且没有出现缓解的迹象。
日本到底出了什么毛病?不久前,它还被看好为世界经济领导的当然继承人。但众所周知,它的服务行业效率极低。虽然日本是出口大国,但在采用新技术方面却进展缓慢。日本银行业管理混乱,且长期没有得到治理(这与周遭的穷邻居的情况是一样的)。但是,就常人的眼光看,目前最为明显的束缚日本经济的“绳索”却是一种美德:消费者的谨慎和节俭。即使是在零利率的情况下,日本居民的储蓄额仍比企业愿意投资的数额要大得多。结果,日本发现自己自30年代以来第一次陷入了可怕的“流动性陷阱”,而国内的整个私营部门实际上正努力地积累现金。由于没有购买行为,销售就成了泡影,反之亦然。由于现金的减少,经济便产生了持续不断的低迷,生产每年都远低于生产潜力。
日本为什么陷入这种困境?也许是由于日本在80年代末的金融泡沫破裂后从未复苏,也许是由于日本令人忧心忡忡的人口问题(日本符合劳动年龄的人口1997年达到高峰,预计今后几十年会稳步下降)。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决策者尚未找到解决办法。
治疗“流动性陷阱”的典型处方是财政上的助推启动:利用赤字使经济活起来,使投资者投资,使消费者消费。但是在经过几年扩大赤字后(日本今年的预算赤字是战后和平时期最大的),日本经济却没有显示出赶上的迹象,而政府债务却增加到了令人担忧的地步。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日本应该超越传统的货币政策规则,放弃物价稳定目标,实际不实行适度的通货膨胀(这样将会使借钱比持有现金更具有吸引力)。但是日本银行仍顽固地采取正统做法。
在这个时候,日本政府似乎仍希望局势能自行好转。大量的公共工程项目已使去年经济迅速下跌的速度减缓,并且推动了今年的经济增长,第一季度的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7.9%。 但是没有迹象表明日本出现了真正的和能自我支撑的复苏。而且,情况非常容易大大恶化。确实,人们特别容易看到日本将陷入严重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日本将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公司最终开始“理性化”,即裁掉大批不需要的工人;因害怕失业,谨慎的消费者变得更为紧张;支出下降引致更多的人员失业;经济萧条使物价下降、公司债务负担加重,并使现金成为更具吸引力的资产。如果这一系列梦魇式的事件开始发生,真不知道日本政府能够或者愿意做什么。当利率接近零时,常规的货币政策已经起到了最大的扩张作用;而当政府债务和赤字都很巨大时,财政进一步扩张的空间也就不大了。
对日本的担忧必然会影响到亚洲整个地区的前景。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是主要的出口市场,另一方面也因为从日本传出的坏消息肯定会影响到人们对整个地区市场前景的看法。但这也可能是一个兆头,因为日本综合症不一定只限制在日本。
人们可能曾预期中国的经济问题会与印尼等低收入国家类似,而不同于相邻的那些富有的发达国家。但事实上,中国却没有染上这场流感,因为中国的外汇政策既防止了“热线”的外逃,也避免了它的大量流入。(尽管这些政策造成了低效率和腐败。)其经济增长率的下降,是因为人们的消费能力低于生产能力——随着国有经济改革的深化,人们担心失业;同时随着社会的逐渐老龄化,人们也在为养老而存钱(这可能是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时所没想到的一个副效应)。难以令人置信的是,中国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也正在经历一场较为明显的通货紧缩,并正在采取日本模式的扩大赤字的措施来应对。
中国尚有很大的政策空间:利率在零以上;政府预算赤字和债务相对较小。但据说,那些破产的国有企业和无偿还能力的银行都有数额巨大的隐形债务。最后,中国会同日本一样,被迫运转印钞机——这等于宣告人民币的贬值。这样,邻近的国家,特别是香港的日子就会更难过了。
总之,亚洲在今后两年中可能不会遇到过去两年曾遇到的同样的问题。但陷入新的困境的可能性却很大。
教训
逆境出现时也伴随着一线希望:逆境可能造成损失,但也会使人得到宝贵的教训并强迫他们进行改革。亚洲的危机是否已为将来的经济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答案是一个肯定的“也许”。危机已医治了最严重滥用“任人唯亲的资本主义”的一些事例,并且冲淡了这种危险的信念:“亚洲的价值观”使得这个地区无懈可击。这场危机也淡化了自由市场的基本原则,因而也起了好作用:一些国家在自己做好准备之前,因为受到压力而向世界开放资本市场的可能性已减少;而美国把经济外交的主要目的看做是使世界成为对冲基金的安全场地的可能性也减小了。而且最为重要的是,这次危机加强了民主趋势,使得某些家长式的铁腕人物再难以自称他们懂得最多。
但是,一种危险的自满情绪正在上升。是在1996年,当墨西哥经济开始复苏时,决策者和投资者的行动都好像认为墨西哥发生的事件只是一次性事件,绝不可能重演。但事实证明,那次事件只不过是一年以后的亚洲危机的一次彩排。现在,由于世界经济并没有彻底崩溃,人们都开始认为我们已控制了局势。投资者和一些国家可能会愚蠢到再犯同样错误的地步吗?毫无疑问,当然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