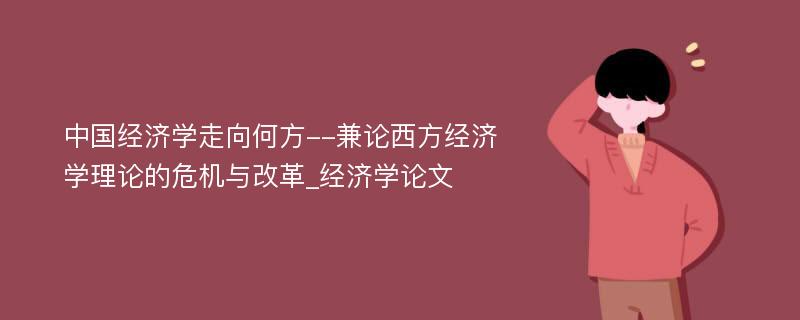
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兼论西方经济理论的危机与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方经济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何处去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变革与发展,中国经济学界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表现之一就是长期受到排斥和批判的西方经济理论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中国经济学家接受、传播和应用。这是一个很值得称道的进步。经济学(其实也包括其他学科)的进步只能在开放中实现。然而,诚如杨继绳同志所指出的:由于“先天的不足”和“过重的负担”,繁荣背后的中国经济学“千疮百孔”,处境“尴尬”〔1 〕。客观地说,经济学(也包括西方经济学)的危机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此情形下,中国经济学应该如何学习和应用西方经济理论,中国经济学者应该如何研究“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这就是我们从对“经济学包括西方经济学正面临危机与变革”这一事实的反思中所想到的。
一、经济学的任务或经济学家的使命
从过去到现在,经济学都在向人们告知这样一个定理:一个人或一部分人所从事的活动,抑或是他们提供的物品或服务,只有在它能满足和适合社会的某种需要时,它才会被社会承认和接受,也才有存在的可能和价值。
古代(也包括古典)经济学家把经济学定义为一种“致用”之学、一种“经世济民”之学。这的确是社会所需要的。如果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必然产生社会的分工,因而会有一部分人专门从事知识的探索的话,那么,只有有“经世济民”之用的经济学才是人们(或社会)所需要的,因而只有那些从事“经世济民”之学的人的劳动才能够被承认,才具有价值。
这里有人会争辩,根据上面的结论,有些学科,比方说哲学,是不是失去了存在的依据?的确,有些学科不具有“经世济民”之用,但是,它们却有着充分的存在依据,这就是,它们是根据分工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它们的任务或使命在于提供关于宇宙、社会人生等方面的知识。对此,人们或社会同样存在着需求。因而并不违背分工原则。相反,如果经济学放弃“经世济民”之用,也去致力于比方说“认识世界”的研究,则违背了分工的原则,因而也就推翻了存在的依据。
而且,我们说,正是由于经济学的“致用”之学的性质,才使经济学尽领风骚,以至于拥有了“社会科学的皇后”(萨缪尔逊语)的桂冠;才使经济学家得以出入官场政厅,得到决策者的顾与问;也才出现了经济学科的壮大与发展。而且,毫无疑问地,各不同经济学派的兴衰交替,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学的“致用”之学的性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伴随着新古典经济学药方的屡屡失灵,经济学家在政府乃至社会中的地位一落再落,以至于在西方产生了经济学能否担当起“经世济民”、“治国兴邦”之任务的怀疑。也由此产生了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或目的是认识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的经济学“新论”。因而他们越来越多地将经济学研究限制在建立一个由观念构成的演绎体系之中,以求“心灵和思维有所依傍”。而今,这种思想也开始影响一部分中国的经济学家。
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与人们努力了解自身及其命运的内在愿望分不开的,因而有一种“知性追求”的成分。但是,我们绝不能用“仅此而已”来解释科学的存在和发展。事实上,“认识世界”的诠释解释不了为什么是经济学而不是其他社会科学学科长期受到人们的青睐和政府的重视;也解释不了其他许多科学,如军事科学、化学科学、电子科学等的存在和发展。并且,如果科学仅仅是为了认识世界,那么很难想象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因此,“认识世界”并非科学的唯一目的,甚至不是一种主要目的。
应该说,正是科学的“改造世界”的任务,要求科学家去认识世界;正是发展经济、提高人类的物质文明的水平的任务,要求经济学家去研究经济理论。并且,如果考虑到经济学家所说的资源的稀缺性,经济社会总是把资源用于最需要的用途,那么,满足于“认识世界”的经济学家是不应该得到经济资源的。更进一步,他可以获得认识世界的精神成果,却不应分享改造世界的物质成果。这是产权的逻辑。
当然,从改造世界的逻辑中,推导不出经济学家应该成为现实问题的奴隶的结论。特别是在承认知识和学问的内容是互相联系的时候,就更是如此。
经济学家的使命是向社会提供有“改造世界”之用的知识而不仅仅是“认识世界”的知识,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谈论的分工理论和需求理论的结论。
二、西方经济理论的危机与变革
提起西方经济理论,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各种各样的假设,然后是各种各样的曲线和一些结论的推导。这就是现代的西方经济学(当然不是全部)。它被称为“标准理论”或直呼为“理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客观地评价了这种经济理论,他说:“标准理论已日益数学化,雅致而又精确,同时,也日益未能正视社会中的经济问题。”〔2〕
那些乐此不疲的人把这称为“经济科学”。但是,也有很多人提出了否定的看法〔3〕。当然, 什么是科学还是一个有待很好定义的概念。但是,毫无疑问,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尤其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首先,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看,直观意义上是个人和厂商,而实际上或深层次上的研究对象却是一个抽象的、无摩擦的“理性”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是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同时他还具有完全信息;而市场则是无摩擦的协调之手,“均衡的钟摆”在摆动,一切都是那么“完全”和完美。理性世界不需要政府,其实理性世界也不需要经济学家。
其次,从新古典经济学分析问题的方法看,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是用演绎的方法来获得结论。且不说这种方法本身可以成为人们批评的对象,最成为人们批判的焦点的是许多经济分析,甚至整个体系的展开都建立在少数几个不真实的假定的基础上。
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受到批评最集中的地方,而且我们看到,对于这些批评,西方经济理论很少作出过有说服力的回答。然而,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中存在的缺陷却不止这些。
第三,从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尤其是学术经济学研究所使用的分析工具看,越来越多地倚重于数学,把经济分析演变为简单的公式推导。这不能不说是对人类经济行为的简单化处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人类行为的贬低。历史上有许多思想大师不止一次地指出过,对于人的行为的研究,不能像自然科学中的研究一样,因为二者之间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和特点。现代行为科学也已充分地展示了人类行为(当然包括经济行为)的复杂性。
另外需要指出,对于可供经济分析使用的数学工具,必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美国纽约大学Courant 数学研究所著名数学教授莫里斯克莱茵指出:“19世纪初的创造,包括令人奇怪的几种几何学和代数学,迫使数学家们极不情愿地勉强承认绝对意义上的数学以及科学中的数学真理并不都是真理。……事实上,数学已经不合逻辑地发展。其不仅包括错误的证明,推理的漏洞,还有稍加注意就能避免的疏忽。这样的大错比比皆是。这种不合逻辑的发展还涉及对概念的不充分理解,无法真正认识逻辑所需要的原理,以及证明不够严密;就是说,直觉、实证及借助几何图形的证明取代了逻辑论证。”〔4〕毫无疑问, 经济学研究也需要数学。但是,对数学工具的使用不仅要认识到数学工具在经济分析上的局限,而且要认识到数学工具本身的局限,这远比盲目地相信有意义的多。这当然是对那些真诚地运用数学工具的经济学分析所言。而现实中当然并不是所有运用数学工具的人都是真诚的。
第四,体现在上述三个方面的局限中的,那些经济分析者的世界观不是别的,正是几个世纪以来的经典或正统的科学观。所谓经典的科学观是指由牛顿、笛卡尔所确立的科学思维模式,在那里,“科学”的概念被认为是超越时空的、普遍适用的。但是这种观念已经过时,被证明为错误的。正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GULBENKIAN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主席华勒斯坦教授所指出的:“无论人们怎样真诚追求普遍性,迄今为止,在社会科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普遍性的期待从来没有真正地实现过。”〔5 〕现代自然科学已经向科学工作者有力地证明了“时间之箭”(arrow of time)的重要性, 科学真理本身是具有历史性和相对性的。“一个远离均衡状态的系统具有种种时间上的不可逆的条件,单单具备了对‘规律’和初始条件的认识不足以预测它的未来状态”〔6 〕(着重号为引者加)。有鉴于此,不只是西方经济学,而是整个经济学,难道不需要一场思维革命吗?
早在80年代,一些严肃的、有责任感的西方经济学家就对西方学术经济学的这种状况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对于经济分析中数学方法的滥用,已有许多著名经济学家提出过尖锐的批评。美国经济学家里昂惕夫的批评可以作为一个代表。他指出:正统经济学“‘这个皇帝是赤身裸体的’,但是似乎置身于美国当前学术性经济学行列中的人谁也不知道这一点,或者谁也不敢这么讲。……事实上,经济学工作者中的许多人是从数学领域转入的,这样,专业经济学杂志上就连篇累牍地充满了数学公式。这将读者从一套似乎有理而完全是任意的假说引到了精确的却是无关的理论结论。……年复一年地,经济学家在继续建立大量的数学模型,而且更为详细地探讨这些模型的性质。同时,经济计量学家将所有可能的代数函数式用于基本上是同样的一些资料,这些都无助于进一步深入地理解一个现实经济系统的结构和运行”〔7〕。
同样,对于西方学术性经济学所深深依赖的演绎主义方法的批评也是一针见血。美国经济学家艾克纳认为,它们已经破坏了科学研究的精神,已经远远地背离了科学。而另一位经济学家彼得·E ·怀尔斯则认为,这种方法与科学意义上的方法相去甚远,这种方法加上大量的抽象和经济决定论,“使经济学成了一种假科学的智力游戏”。而美国《华尔街时报》的资深经济学编辑小阿尔弗雷德·马拉伯则从另一个方面——实践效果方面总结说:“一项经济理论常构想于象牙塔中,然后被计划者们争相应用,而令人难堪的是实践证明其真实效果与预期的相去甚远。”〔8〕
出于对西方经济学现状的忧虑,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不无失望地说:“经济学向何处去尚不明朗。”
也许我们应该承认,到目前经济学还确实不能被称作科学。虽然这一结论令经济学家们不能容忍,也让非经济学家听来沮丧,但是,我们却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这当然并不意味着这一状况是不可改变的,也就是说不意味着经济学将来不能成为一门科学。而且,我们相信,经济学正在沿着通往科学的道路上前进。诺思教授的忧虑除了过于悲观以外,还带有静态观念的不足。实际上,西方经济学发展正在酝酿着一场变革。
在西方经济学研究走出象牙塔的道路上, 特别值得一提的有:(1)有限理性学说的提出和发展,这主要地应归功于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Herbert.Simon)的卓越的发现。 他本人也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2)不确定性的引入。 首次明确地将不确定性引入经济分析的,当推弗兰克·奈特(Frank H.Knight)。1921年, 奈特在《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中,将不确定性与投资和市场的分析联系到一起。而肯尼斯·阿罗则对不确定性分析的深化作出了贡献;(3 )交易成本概念的分析和应用,这主要是指由科斯开创的产权经济学派的贡献;(4)制度变迁理论。由诺斯等人开创的“新经济史学派”, 将更多的经济变量纳入经济分析中来。正是上述经济学研究上的发展,使经济学研究正在走出新古典的世界,日益回到现实中来,而且我们可以期待,通过各国经济学家共同的不懈努力,经济学正在向通往科学的道路上迈进。
三、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之路
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先后遇到了两个方面的选择。首先是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应该说做出这一选择,我们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的。但是在实践上,经过纵向的(历史的)和横向的(国际的)比较,我们毕竟已经得到了明确的答案,即使问题并没有全部解决。其次,是随着前一问题的解决所提出来的中国经济学发展之路的选择。按照事情发展的本来逻辑,也许应是第二种选择的首先解决。但是,这种次序颠倒的事情,在各国历史上也确实并非首例。
比较两种不同的选择,前者的答案也许更确定些,这一方面是因为摆在我们面前,可供我们选择的道路,有些被实践证实,有些则已被实践证伪,因而备选方案并不多;另一方面是因为在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上,虽然也存在利益冲突,但问题的解决,毕竟可以产生一个多数人获益的结局。并且如果说人是理性的行为者,因而在看问题时并不忽视长远利益,就像考虑到未来的生活而不将全部收入今天消费掉一样,那么人们就更会看重改革的收益。这样,在这一选择上就存在较大的共同激励。
然而,作出后一选择则不同,与前一选择相比,它要显得复杂些。这种复杂性不仅是因为问题本身有更多的可选方案,更重的主观色彩,而且因为,对经济学发展道路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由少数人作出(主要是经济学家),而且在作出这一选择时,经济学家可以较少地顾忌其他社会成员的意见。因为这一选择对其他社会成员的影响并不那么直接,特别是把经济学研究看作一种职业时就更是如此。因而,其他社会成员缺乏对经济学家的选择实行监督的激励。而作为经济学家,他们也是理性行为者,一方面他们不难认识到自己的态度或观点,在多数情况下不能变成政府或社会政策,因而对社会他们并不负有太多责任;另一方面,如果能把学问搞得玄一点,让别人看不懂,似乎可以增加经济学家的获益(垄断收益)。而且如果这一点做到了,也可以使自己招致较少的批评(风险规避)。或者退一步说,假设一些前提,通过演绎,得到一个完美的工艺品,即使并不实用,也可以让人观赏。这一方面尤其适合西方学者。
上述分析说明,经济学发展道路的选择面临较大的复杂性,它更大程度上带有个人选择的特点,比较难于取得一致。而在这一说明过程中,我们并没有把经济学家看作是超理性的人,而是把他们也当作理性人。关于这一点,并不含有对经济学家不敬或个人攻击的味道,而且我们认为,理性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有的制度安排。经济学家之所以如此行事,部分地要从现行制度安排中寻找答案。但是,即使如此,经济学家也还是有义务回答“学了经济学有什么用”的提问,这实际上是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另一个不同的问法。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经济学家才算是回答了自己为什么要向社会提供这样一个产品——经济学,也才算说明了自己的劳动为什么是社会所需要的,也才算证明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如果我们承认经济学应对社会有所“功用”或贡献,那么,中国经济学发展道路的选择,就不再仅仅是经济学家个人的事情。它关系到社会的每一个成员,而且从长远看也关系到中国经济学的成长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未来。
如何选择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之路,或者如何发展中国的经济学,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通过前两部分的分析作出了回答。在这里,我们作如下具体说明。
第一,经济学的功用或经济学家的使命,不仅仅是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它应对改造世界有所贡献。当然,改造世界未必是一个立杆见影的事。经济学家不应像商人一样急功近利。
改造世界的经济学,本质上讲是植根于现实的经济学。植根于现实的经济学当然包含有置根于本国的含义。但是,从植根于本国的含义中得不出否定他国的结论。改造世界的经济学所反对的是从书本到书本(如80年代以前的“诠释学”),同时,也不赞成任何意义上的文字游戏或思维游戏。
第二,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不能不遇到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这样两点:(1 )如果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是人类共同的财富,那么我们的问题就不是借鉴与否,而是学习和掌握。而即使是学习和掌握,中国经济学人也不能忘记,“世界上不存在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这一不幸的事实。尤其考虑到作为社会现象的经济问题的复杂性,这一点就更忽视不得。(2 )我们对西方经济理论一方面要吃透其理论本身依存的体系,而不是只找几个自己认为是有用的理论生吞活剥,另一方面又不能不看到现阶段西方经济学的局限性,特别是考虑到西方经济理论也并不曾很好地解决他们自己的经济问题,因此,保持清醒与掌握吃透至少同样重要。
第三,经济学是很讲究分工的。自亚当·斯密以来,人们就对分工赞誉倍加。分工创造劳动生产率,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这就是存在协作,即保持着对外部的协调的联系。毫无疑问,经济学研究也应有分工,这样才能有深入的研究和避免肤浅的结论。但是,科学研究的分工不等于关起门来,闭眼不看有关学科的发展。否则,就不可避免地在避免了肤浅的同时产生片面。而理论研究中的“协作”工作还得由研究者自己来做。否则,理论家生产出来的,充其量只能是一堵堵的墙,而肯定不是楼。在谈到关于知识分工问题时,汪丁丁博士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发现,我们的社会进入一个非常痛苦的状态:一方面,我们需要发展,我们很依赖分工;另一方面,人们的知识结构发生越来越大的偏离,造成社会道德、伦理上的分歧(法学上称为“知识的局部化”)。可惜的是经济学家对此没有太多的关注……”其实,知识的局部化不仅造成了道德伦理上的分歧,而且直接地妨碍了分工状态中的知识自身的发展。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既要精深,更要博大。
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一个太大的题目,一个太重的任务,中国经济学家任重而道远。
注释:
〔1〕杨继绳:《显学的危机》,《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2〕道格拉斯·诺斯:《动态经济世界中的经济理论》, 《经济译文》1995年第3期。
〔3〕参见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4〕[美]M·克莱茵:《数学:确定性的丧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
〔 5 〕[美]华勒斯坦:《开放的社会科学》, 北京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第53页。
〔6〕同上,第66页。
〔7〕参见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8 〕[美]小阿尔弗雷德·马拉伯:《迷惘的预言家——当代经济学家的历史》,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
标签:经济学论文; 科学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经济论文; 西方经济学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数学论文;
